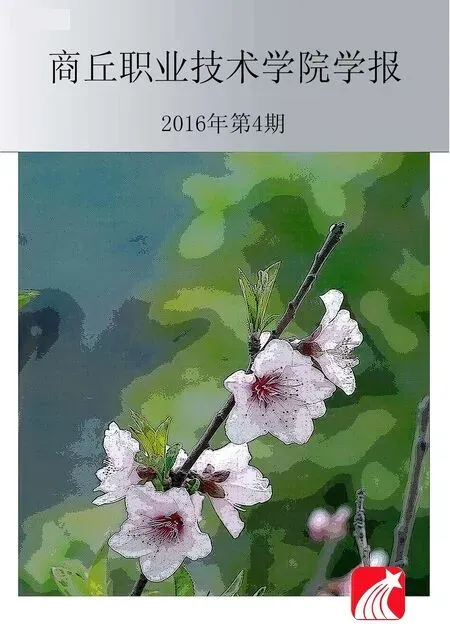繁昌保卫战研究综述
赵文强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繁昌保卫战研究综述
赵文强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繁昌保卫战是抗战时期中共参与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战例,也是新四军战史上的著名战役。在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历次繁昌保卫战中消灭日伪共计千余人,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县城,屏障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徽州、屯溪重地,对开辟和巩固皖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效牵制了日军南进,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因繁昌保卫战的战略意义重大,而学界对此研究并不详实,所以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对拓展繁昌保卫战的研究十分必要。
新四军三支队;繁昌保卫战;研究综述
繁昌保卫战是新四军战史上的著名战役,其战略意义重大。从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三支队从南陵移驻繁昌开始至1941年1月新四军北移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三支队在“铜(陵)、南(陵)、芜(湖)一带同日寇进行了大小200多次战斗”[1]46。新四军三支队奋勇杀敌保卫繁昌,意义不可小觑。笔者在检索了与“繁昌保卫战”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搜集、整理国共两党关于“繁昌保卫战”及其前后的相关档案史料后,对“繁昌保卫战”作如下综述。
一、繁昌保卫战研究资料概述
第一,专门性研究论文成果较少。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的不完全统计发现,论文中提及保卫繁昌的有近八百篇,以繁昌保卫战为主题展开研究的论文有十余篇,然而真正以繁昌保卫战为题,着重研究发生在这座小县城数次保卫战的研究成果仅有4篇。这四篇论文分别是:张金锭,张雷:《五次繁昌保卫战》(载《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8期);卓凤鸣:《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载2006年4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文集》);沈宫石:《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敌胆寒》(载2011年6月24日《安徽日报》);朱磊:《繁昌保卫战:粉碎日军扫荡皖南计划》(载2015年7月28日《中国国防报》)。可以说繁昌保卫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或者说学界确实小觑了繁昌保卫战的意义。
第二,在档案史料上,国民党方面的战报、电文比较丰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新四军·参考资料》(2)收录大量自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三支队在繁昌地区抗击日军、收复县城、破坏敌伪等情况致蒋介石的电文,顾祝同给蒋介石每周一报,这些电报集中反映了新四军并非国民党造谣者口中所谓的“游而不击,不游不击”,而是坚决履行三战区长官部命令,在皖南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新四军·参考资料》(3)中,收录部分伪政府在1939年底就新四军在繁昌附近伏击日军给伪行政院的呈文,不仅从侧面反映了新四军卓越的战绩,而且也为我们展现了繁昌保卫战惊心动魄的史实。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五)中收录了近四百页关于叶挺、项英对新四军作战地区敌我力量、敌我策略、地形条件的分析以及新四军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12月在大江南北的战绩概要等。其中,第三支队在1939年战斗和破坏次数最多,因此关于三支队的记录也最详实,这部分战绩概要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孟繁纶所报,因此相当可信且研究价值极大。由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博物馆、军部旧址博物馆联合主编的《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一书,收录十余篇刊登在当时新四军的“喉舌”《抗敌报》中有关三支队在繁昌数次战斗的详报,这些详报清楚地记载了三支队在历次战斗中的歼敌、伤亡和缴获情况,能够为繁昌保卫战的研究提供考证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收录1940年《新四军战绩纪略》一文,此文反映了新四军六次保卫繁昌的战斗详情以及新四军在皖南进行反扫荡过程中与繁昌人民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同时,该书还收录了邓子恢《关于铜南繁地区如何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一文,此文反映了敌伪在铜繁地区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以及新四军的对策,能使我们了解繁昌保卫战前后铜繁地区的敌我情况以及三支队在皖南抗日前线的统战策略。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新四军将领论抗日游击战》一书,收录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论保卫皖南的防御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三支队在历次繁昌保卫战中的光荣战绩,肯定了三支队对保卫皖南的重要作用。由新四军战史编辑室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新四军战史》,其中有一节叙述了三支队在1938年12月下旬进入铜繁地区后,于1939年五保繁昌的作战过程。2015年8月由芜湖市档案局(馆)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书,以芜湖抗战为主线,结合芜湖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新华日报》(1938年—1945年)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整理编纂而成,其中“抗战篇”收录了几篇关于繁昌保卫战的档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第三,关于繁昌保卫战和三支队在繁昌地区作战的回忆文章较多。《新四军·回忆史料》(1)和《新四军往事》均收录了时任三支队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对繁昌保卫战的两篇回忆文章《新四军三支队战斗在皖南前线》和《繁昌保卫战》,他不仅回忆了三支队从新四军建军、岩寺整训、青戈江接防、繁昌保卫战、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而且着重记录了1939年11月三次较大的繁昌保卫战,就战斗内容来讲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学界目前关于繁昌保卫战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根据也来源于陈仁洪的回忆。
二、繁昌保卫战研究现状
如前所述,繁昌县城虽小,但作为皖南门户对破坏和威胁日寇在长江的航运以及协同友军作战意义重大,并且它处在皖南抗日前线,属于沦陷区范围,新四军第三支队数次保卫繁昌的战斗,在拱卫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长官部过程中是发挥巨大作用的。但由于档案资料较为分散以及其他一些历史原因,学界并未对新四军在皖南时期的繁昌保卫战给予重视,所以相关研究论述较少。笔者现结合目前学界仅有的部分研究内容,对其现状做一总结,供学界参考。
(一)关于繁昌保卫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次作战的战况本身
张金锭、张雷在《五次繁昌保卫战》中,以叙事性手法着重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1939年的五次繁昌保卫战作战详情叙述出来,语言通俗,颇具文学韵味,但议论较少,且绝大部分内容系陈仁洪的战斗回忆,因此其学术价值并不大。朱晓明、蔡朋岑《保卫繁昌——1939年11月新四军在皖南》一文,在叙述了三支队从闽北转战皖南的过程以及繁昌的战略意义后,着重分析了三支队在1939年11月三次较大的繁昌保卫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最艰难时期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史实。沈宫石在其《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敌胆寒》一文中,根据采访繁昌县党史办主任伍先华等所得口述及部分档案,着重介绍了在第四次繁昌保卫战时塘口坝血战的史实和三支队卓有成效的民运工作。虽是一篇访谈报道,但打破了学界对繁昌保卫战研究仅关注战役、战斗本身的局限,从群众动员等角度入手分析繁昌保卫战胜利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朱磊《繁昌保卫战:粉碎日军扫荡皖南计划》一文,从战史背景入手,分析繁昌地理位置、敌我情况,继而叙述第四次繁昌保卫战的战斗情况,大篇幅分析了繁昌保卫战的战斗意义,虽然窥探不出其史料支撑,但也不乏为繁昌保卫战研究者提供了可考的方向。
(二)围绕谭震林在繁昌时期的研究比较丰富
谭震林是我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跟随毛主席,1938年他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实际领导三支队在皖南前线开展正面战场的局部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虽然在1955年授衔时因已不再担任军职干部未被授衔,但依然掩盖不了其优秀的军事才能。研究谭震林与繁昌保卫战的文章多以三支队移驻繁昌地区,前后参与繁昌保卫战为主线,展现谭震林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领导民运工作开展的情形,反映新四军与繁昌群众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评价多见为皖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做出积极的贡献。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后留任三支队民运科工作的汪大铭在《一束难忘的回忆——缅怀谭震林同志》中,以其部分日记为基础,回忆谭震林在繁昌时期高度重视民运工作并亲历亲为的情况,为繁昌保卫战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可以利用的回忆性史料。其他相关文章可见叶之茂和高增运、张学分别在《谭震林与繁昌保卫战》《谭震林在繁昌保卫战中的贡献》的回忆。
(三)关于繁昌保卫战次数存在较大争议
1938年12月至1940年12月,三支队在铜繁地区对日作战二百余次,但繁昌保卫战究竟进行了几次?新四军老前辈和学界对此认识并未统一。第一种观点认为,繁昌保卫战共五次,但具体指代时间还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五保繁昌发生在1939年这一年。例如:张金锭,张雷认为:“1939年,五团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取得了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2]75。童志强认为:“在1939年这一年中,在谭震林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大规模繁昌保卫战就有5次。”[3]64朱煜认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在谭震林领导下,于1939年11月至12月22日在繁昌进行五次保卫战”[4]156。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1940年1月6日《论保卫皖南的防御战》一中提到繁昌保卫战时,说道:“特别是最近以民生支队为主,精团配合,坚决保卫繁昌的战役,在繁昌及繁昌附近之汤口坝、铜山等地,连续打破了敌人五次大举侵犯繁昌的战役企图”[5]208。他指的也是1939年底的五保繁昌。而汪春水认为:“两年间,三支队在繁昌与日军的战斗就有近 200 次,其中有五次规模较大的保卫繁昌的战斗,先后毙伤日军少佐以下800余人,取得了‘繁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6]。第二种观点认为,繁昌保卫战共六次。例如:《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始末》载“新四军六次保卫繁昌”[7]13。第三种观点认为,繁昌保卫战共七次。《泾县文物志》就指出军部指挥过“七次繁昌保卫战”[8]42。汪大铭回忆在九月中旬他调回军政治后,“连续七次的繁昌保卫战,前五次是由谭司令亲自指挥的”[9]74。而且谭震林在1983年8月应邀为《繁昌县志》的题词中写到“抚今忆昔心潮涌,七战七捷记犹新”[1]23,也指出繁昌保卫战是七次。繁昌保卫战次数虽然存在争议,但是从日军频繁出兵想要夺取这座县城的军事行动,足可见繁昌战略意义重大。为了理清史实原貌,研究清楚繁昌保卫战究竟打了几次还是很有意义的。
三、对繁昌保卫战研究的思考
从近四十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新四军研究的档案史料、专著以及学者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对新四军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对新四军三支队在铜南繁地区的研究只有零星几点,因而对繁昌保卫战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繁昌保卫战是中共参与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战例,三支队在前线与敌、伪作战,又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仍能取得如此之大的重要战绩在新四军抗战史、中共抗战史乃至抗日战争史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将其研究现状与这一课题本身的重要性相比,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
首先,研究方向有限,仅限战斗情形或人物事迹。目前学界现有成果多利用回忆史料研究繁昌保卫战,鲜有利用档案史料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缺乏对史实的争鸣与考证。即使有的利用了国民党方面的战报等,也只是简单堆砌,缺乏逻辑,并未详细成文,学术研究价值不高。三支队进驻繁昌后作战二百余次,消灭敌伪千余人,如此大的战绩仅围绕谭震林的战场指挥进行研究似乎在整个战略意图上缺乏一定的支撑。尽管三支队是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赴铜繁前线抗日,但新四军江南一半兵力部署铜南繁地区,在战略上必然受到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局甚至中共中央的指导,而学界对此研究尚属空白。同时,指挥繁昌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仅在于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官兵的顽强抵抗,大战斗背景下群众的支持和其他统战策略的成功也是战斗取得胜利的因素。其次,在研究深度上,学界小觑了繁昌保卫战,并未给予其在战略意义上的高度重视,因而研究不够深入。繁昌是皖南的门户,位于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凸出部分,是敌我两军的前沿阵地。新四军第三支队以初建时的四营兵力在铜南繁前线这个敌伪友顽犬牙交错的地区,不仅担负着保卫皖南的任务,而且在1940年还承担长江沿岸布雷任务,其战略地位可想而知。但是,学界并未对繁昌保卫战给予高度重视,因此相关研究仍值得探寻。历次繁昌保卫战是否全部取得胜利,这一点也有待考证。
(二)在档案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新四军研究的逐步开展,关于繁昌保卫战的研究才得以出现,但数量极少。目前关于繁昌保卫战公开的档案资料主要集中于《新四军》系列丛书,其余史料比较分散。研究成果多靠回忆研究,缺乏对历史史实的考证,这对于研究繁昌保卫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目前公开出版的官方档案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类似皖南事变那样专题式的档案史料书,并且学界对项英在皖南时期的功过争议较大,因而关于三支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许多细节性的史实问题还有待挖掘、整理和研究。因此,在档案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方面,要求国内学者挖掘更为广泛的史料,加以考证分析,并且应拓宽视野,大量挖掘日军在皖南地区作战的档案、回忆,了解日军作战企图和详情,才能使繁昌保卫战的研究更加详实。
(三)在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方面
对于研究原则和方法而言,无论是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其他新闻记者,在研究史实问题时应秉承的是“论从史出”的原则,而不是随意的夸大或贬低历史真相或历史人物。在方法上,也应该多方取证,结合各方史料进行考证;还应重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尤其是战斗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不能只是依靠老战士回忆或是几则战斗电报,一蹴而就的将档案简单堆砌,不加斟酌。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对档案史料多方考证,然后成文。
四、结语
档案史料的分散并不能成为探究史实真相的迷雾,历史原因的积淀也不该是拓展研究深度的阻碍。由于学界在繁昌保卫战的研究上仍存在大量不足,那么如何进一步拓展繁昌保卫战等规模虽小但战略意义重大的战役、战斗研究?在此,笔者不妨提几点建议,供学界参考。一是加强档案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尤其是皖南军部对数次繁昌保卫战的指示以及日伪方面的战略意图和具体作战部署。对这类重要战役、战斗的档案史料,或可按年编排,也可按省编排,出版专门性档案史料书,便于学界研究和争鸣。二是应拓展战役研究角度。不仅仅局限在战斗本身,还应关注大战斗背景下的统战工作、民运工作以及繁昌保卫战如何以少胜多的战术研究等问题。三是加强比较研究,敌伪与新四军数次争夺繁昌,而我军以少胜多,这样的战役完全可以与其他战役进行战略战术上的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点和特色,积累经验。
[1] 方基权.谭震林的繁昌情[J].党史纵览,2001(5).
[2] 张金锭,张雷.五次繁昌保卫战[J].福建党史月刊,2002(8).
[3] 童志强.谭震林在皖南[J].江淮文史,1993(1).
[4] 朱煜.新四军:拍摄随笔记事历史故事系列[J].贵州档案,2003(2).
[5]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将领论抗日游击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 汪春水.热血谱写繁昌战歌[N].芜湖日报,2011-06-20(3).
[7] 古言.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始末[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8] 安徽省泾县文化局.泾县文物志[M].1986.
[9] 汪大铭.一束难忘的回忆:缅怀谭震林同志[J].革命人物,1985(2).
[责任编辑袁培尧]
The Research Reviewed on the Battle ofFanchang
ZHAO Wenqiang
(CollegeofLawandPoliticalScience,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The battle ofFanchang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examples of positive battlefield leadership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ut also the famous battle on the war history of new fourth army. During 1938 to 1940,the third team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mounted to destroy the thousands of Japanese troops in the past numerous battle,successfully defended theFanchangcounty town,and formed the barri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southernAnhuiprovince,Huizhou, andTunxiarea, which i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set up and consolidate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the south ofAnhui. Moreover, it effectively restrained the Japanese attack of the south,enlarge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new fourth army,and made a blow to the Japanese arrogance. Because the numerous battle ofFanchang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rategy,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develop the research.
the third team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he battle ofFanchang; research reviewed
2016-04-18
赵文强(1993- ),男,山西晋中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研究。
K265;E297.3
A
1671-8127(2016)04-0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