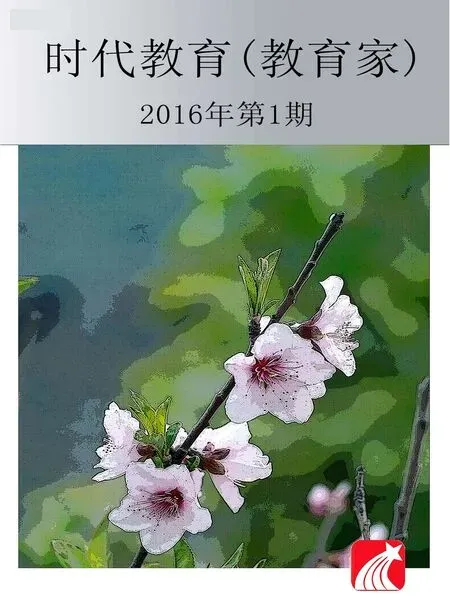重建乡村教育的尊严
重建乡村教育的尊严
88年前,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中,对乡村教育发出了这样的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此言正契合当下。“城满,乡弱,村空”已成为中国教育生态的普遍现象。
乡村大地的孤寂,不只是有机农耕的死寂,乡土中国是天地国君亲师一体的文化系统、或教育系统。乡村大地不仅承载着万物,同时是我们的母亲、老师和道之所存:乡野的牌匾和石碑上,有先贤的教诲和事迹,过去的乡绅与现在的乡村教师,不仅为人师表,还身承着礼仪、教养和风俗的文明示范。
过去,中国的城市也是扎根、生长于乡土之上,比如,让我们流连忘返的阆中古城,有礼尚往来,有芳邻世交,人与街道、与大自然并没有被混凝土隔绝。十年前,国外建筑师曾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太多师法洛杉矶、休斯敦这一类摊大饼的“卡通城市”,而让大城市失去了有机的街道生态,堵车令人抓狂。城市规划者们似乎忘记了,任何建设、文明的创造都应该师法大自然这个导师,让城市,有城市的样子,农村,有农村的样子。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忘记了。2013年12月,“2013美丽乡村教育”公益评选颁奖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阆中教育以其朴素的本色、恒久的探索和别样的风采,当选“中国2013美丽乡村教育”。
过去,现代知识人曾经想当然地以为,传统中国是农耕文明,是落后的,保守的。殊不知正好说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明确反对商业,提倡农业。柏拉图甚而把《荷马史诗》赶出了“理想国”,而把写《农耕与时日》的诗人赫西俄德请了进来。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始重商业。
厘清这一糊涂已久的认知,是想说明,中国的乡村教育本来就是美丽的,乡村足以涵盖现代文明,为探究阆中乡村教育,本刊记者分三次、二小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深入到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本期封面《阆中的样子》):
在思依小学的体育器材室,记者看见有垒球、棒球和师生自制的宝剑枪棍;
在洪山小学,记者见到了勇夺全市小学女足亚军的女球星;
在白塔中学,圆形的开放书架上是每个班级轮流推荐的书目;在阆中实验小学,学生将自己读过的图书拍卖,形成了有规律的跳蚤市场……
阆中教育人说,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的精神家园,我想起了诗人柏桦《晚清笔记》里的一节:
学校即教堂,在那里
我们念念有词,宛如庄严的歌唱——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在中国,孔子早就教会我们何为忠恕之道
我们的精神是一种心境,它随遇而安
在家庭教堂里,我们以《孝经》开篇
没有激情,因激情属于宗教
从不伤感,因伤感属于色情
我们这些世世代代胆小且不怕痛的民族
虽惊恐于风景中的恋爱
却也欢喜杨柳树下闹哄哄的生活……
本刊主编 文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