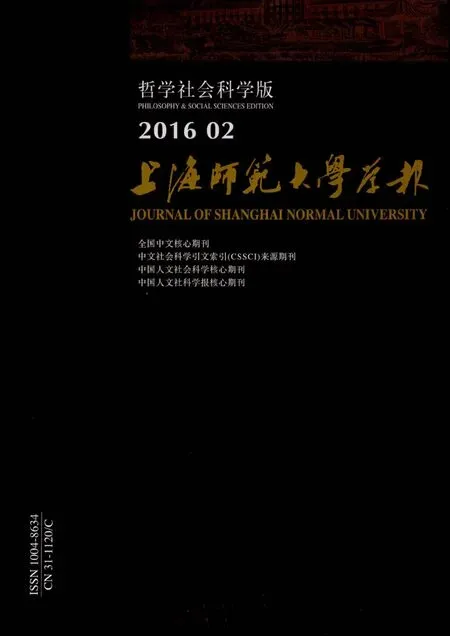劳动之美与节俭之德的现代价值
张自慧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从人类历史长河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第3卷,P508)的同时,还创造了经济价值、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习近平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时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2]但毋庸讳言,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和各种消极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解决了生存之忧后,人性中的惰性因子和享乐思想开始消解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勤劳节俭之德。一些年轻人认为勤俭的传统已经过时,他们讲排场、轻劳作、重享受,向往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有些富人将昔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束之高阁,沉溺于物质享受,醉心于声色犬马,挥金如土,生活奢侈;少数领导干部懒于政事,奢于生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3]随着劳动之美被贬抑、节俭之德被边缘化,国民的道德素养、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劳动之美的必然性
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实现自身价值和理想的必由之路,是人类财富和幸福的来源,也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创造了美。”[4](P46)人类对劳动的热爱源于劳动之美,以及由劳动之美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那么,为什么劳动可以创造美?
其一,劳动创造了人类生活之美。人在劳动中学会直立行走,看到了一般动物无法看到的精彩世界,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乐;日复一日的劳作,使人练就了健康的体魄,获得了生命的活力;劳动是“一切物质的富源”,[5](第3卷,P196)其创造的物质财富解决了人类的生存之忧,为美好的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李大钊说:“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5](第3卷,P196)陈独秀说:“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成就的。”[6](P214)纵观历史,人类正是通过劳动和抗争,一次次摆脱自然力量和落后生产关系的奴役、束缚和伤害而获得自由,从而拥有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其二,劳动赋予了人类智慧之美。劳动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赋予了人类非凡的智慧,并最终使之成为“万物之灵”。为了生存,人类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小到镰刀锄头,大到飞机轮船,不同的工具带来了不同的社会生活,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到21世纪的机械播种、互联网世界。人类在劳动中产生智慧,又运用智慧改造世界,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美丽梦想,创造了美轮美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无论是作为古代文明奇迹的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泰姬陵、秦始皇兵马俑,还是作为古代文化经典的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罗马法典、“五经四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劳动催生的“智慧之花”。
其三,劳动滋养了人类心灵之美。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1](第3卷,P538)一个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社会是一个民风淳厚、守望相助、充满仁爱的社会。人的劳作过程是生命力的展现过程,是陶冶性情、砥砺品行的过程,也是纯洁心灵、提升道德的过程,而懒惰成性、不思进取则会让人精神颓废、道德堕落,乃至危害社会。正如陈独秀在其创刊的《劳动节纪念号》上所说,“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并指出该“新伦理”“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5](第3卷,P403)这表明,劳动使劳工的心灵变得纯洁、人性走向美好、道德变得高尚。追溯人类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出,劳动的持久重复性磨炼了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培养了人的互助精神,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培育了人的纯洁和善良,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劳动规律则教会了人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劳动赋予了人类生活之美、智慧之美和心灵之美,是人类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因此,热爱劳动应是人类社会的“首德”,应是每个想拥有幸福生活、非凡智慧和善良道德的人必然之选择。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对劳动美的讴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尚书·周官》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诗经》中有多首讴歌勤劳、抨击不劳而获的诗歌,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击壤歌》)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再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大雅·绵》),都呈现出人们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而《诗经·魏风·伐檀》则将坐享其成、贪婪成性的奴隶主比喻为不劳而获的硕鼠,讽刺和斥责了当时严重不公的社会现实。劳动之美的诗意境界在其后的很多诗作中也都有体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人们对回归自然的农耕生活充满了美好联想和向往。南宋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让人们感受到劳动所带来的欢愉和满足。毛泽东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则以洋溢的激情歌颂了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力,彰显出劳动的自豪与壮美。
二、节俭之德的应然性
节俭是中西方公认的美德。在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农业社会,节俭以其内在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为古人所崇尚。在中国,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世代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7](P28)的古训,勤俭节约,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生活。在古希腊,节俭的美德也为人们所称颂,“节制”(内含节俭)与“智慧、勇敢、公正”被并列为“四主德”之一。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资产阶级把惜时、守信、节俭、进取、公平作为必须遵循的道德信条。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节俭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节俭之德的应然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节俭悖论”说,他认为节俭与贫困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一个社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就业不足”,[8](P97)节俭会减少消费,减少消费使得总需求减少,进而就业量减少,社会、家庭必然贫困。他倡导人们加大现期消费,甚至“举债支出”,认为“举债支出虽然是‘浪费’,但在得失相抵之后可使一个社会致富”。[8](P82)中国近年来面临市场疲软、消费乏力而导致的经济发展减速,少数学者也提出“节俭”阻碍了经济增长,呼吁放弃传统的节俭美德;媒体和民众中出现了宣扬消费光荣、消费爱国、节俭过时的现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以驱动内需,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于上述思想、观点和政策的推波助澜,“月光”、“日光”、透支等非理性消费行为在年轻人中渐成时尚。那么,节俭之德真的过时了吗?
第一,节俭是人性的内在需要,“无节制,不成人”是人性定律。人类脱胎于自然,有动物的本能需求。但作为万物之灵,人始终有一种超越动物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就是理性。只有具备了理性,人才能真正成为人。正如《礼记·冠义》所云:“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仲尼燕居》云:“礼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这表明,君子的行为是以合乎理性为准则的,而理性的实质就是节制不当的欲望,以合适的分寸做人做事。人是情感与理智兼有的生命存在,柏拉图用“灵魂马车”对人类的理性与情欲做了形象的阐释。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马车”的御车人,其驾驭着理性和情欲两匹马,“当理性战胜情欲时,人就获得完美的人格;当情欲战胜理性时,人便成为速朽的动物”。[9](P219)面对膨胀的物欲,“不节制的人是一个奴隶……他是他肉体的俘虏,是他欲望或习惯的俘虏”。[10](P35)因此,弗洛姆说,“欲望之无节制”会导致“自我的瘫痪和最终的毁灭。”[11](P131)人要成为人,就要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节制没有边际的动物性欲望,并让节俭成为生活习惯,成为美德和人性的内在需要。
第二,节俭符合“中道”伦理,能给人持久的幸福。丢弃节俭之德,追求奢侈享乐,人们可能获得一时之快乐,但接踵而至的将是身心健康的伤害和真正幸福的丧失。正如《吕氏春秋·本生》所云:“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节俭是人对待物质享受的一种中道,节俭之德合乎“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实质是反对极端、追求和谐适度。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犹不及”,倡导人们力行中庸。《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和”就是通过节制达到最佳的“度”,而达到适度境界的手段就是“礼”。《礼记·仲尼燕居》云:“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古人通过“克己复礼”来“节制”不当欲望,把握行为分寸。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德性就是中道”[12](P34)的思想,他认为凡事都有过度、不及与适度三种情况,“中道”是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状态,而节俭正是吝啬和奢靡的中道。亚氏的美德伦理学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是“生活优裕,行为良好”的状态;幸福是合乎理性和“中道”的活动,是美德的实现。他反对将幸福仅仅归结为快乐,尤其反对那种把快乐仅归结为感性快乐的纵欲主义。在他看来,失去“中道”德性的贪婪奢侈行为不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主要是精神上的体验,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美德的赞誉。适度消费的节俭行为合乎“中道”伦理,是人类持久幸福的源泉。
第三,节俭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有钱不能任性。每个公民都有合理消费、获得幸福的权利,但基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有限性,一部分人奢靡的生活必然损害他人消费和幸福的权利,特别是当奢靡的生活方式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时,奢靡者就成为公众之敌,成为公平正义的破坏者。亚当·斯密指出,“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无论就哪一个观点来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13](上卷,P313)但有人认为,物权法赋予了个人支配自己物品和财富的权利,有钱就可以任性,就可以生活奢靡。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是双重的存在,既是“自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存在”,任何个人的消费行为都关涉自然、社会和环境。既然自然资源是公共的而非私人所有,那么任何浪费资源的奢靡行为都是对公平正义原则的藐视与践踏。“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14](P106)因此,财富的增多和物质文明的发达不能成为奢靡生活的理由,相反,“文明益进,则奢侈益杀”,[15](P201)对违反公平正义的奢靡之行,全社会都应对其进行抨击和遏制。
第四,节俭合乎消费伦理,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任何财富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都渗透着人们辛勤的汗水,节俭的生活方式既是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更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同时,节俭也是符合消费伦理的行为。节俭不是吝啬,而是合理、适度地消费,其追求的是“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道德境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节俭的内容也不断被更新,在消费的量和质上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看,节俭没有过时;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看,节俭依然需要。在提倡低碳生活、绿色经济的今天,必须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节俭观的崇尚与信仰,破除当下普遍流行的享乐主义消费倾向,引导人们构筑合理适度的消费观。心理学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呈非线性平衡关系,超过一定范围,两者之间呈现反比关系,过度消费不仅对人的生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对人的心理健康也十分不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都市人群心理疾病的频发更多是物质高度丰裕而精神极度贫乏所致。因此,人们要从消费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就必须节制欲望,追求简约合理的物质生活和充实丰盈的精神生活。
三、勤劳与节俭之德的现代价值
勤劳与节俭是人类的优秀品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德和秩序之基。勤劳是节俭的基础,没有勤劳,节俭就失去前提和动力;节俭是勤劳的延续,没有节俭,勤劳所得之财富就会浪费殆尽。正如古人所云:“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16](P132)尽管21世纪的人类已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勤劳与节俭仍是渴望幸福的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美德与良习。
第一,以勤劳战胜懒惰,以节俭遏制奢靡,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储恒久的精神动力。自古以来,懒惰和好逸恶劳就被视为败德和万恶之源,因为懒惰是一种毒药,它既毒害人们的肉体,也毒害人们的心灵,会导致精神抛荒和品德沦丧,是滋生邪恶的温床。“懒惰会吞噬一个人的心灵,就像灰尘可以使铁生锈一样,懒惰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17](P86)在中国,几千年来勤俭之德推动和支撑着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尚书·大禹谟》中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语句,告诉人们惟有克勤克俭,方能家国兴旺。据《帝王世纪》记载,自唐代开始,二月二被正式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每年此时大地解冻,天气转暖,皇帝都要率文武百官“御驾亲耕”,以垂范天下。臣民百姓则遵循“生民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颜氏家训》)的训条,视勤劳为兴家之本,坚信“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并世世代代“勤俭自持,习劳习苦”,[18](P796)完成齐家之重任。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倡导借助尚俭以促善,利用杜奢以祛恶。孔子强调“政在节财”(《孔子家语·辩政第十四》),主张“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墨子告诫当权者:“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总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当下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倡导民众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在西方,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谴责懒惰,歌颂劳动,认为“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并提出了懒惰是耻辱的思想。[19](P10)韦伯认为勤劳节俭之德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一种节俭勤奋,而非奢侈豪华。”他赞赏新教徒的“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20](P30)强调“新教伦理特别不能容忍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认为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20](P128)他还提出了“劳动是一种天职”[20](P140)的思想,充分肯定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我奋斗品德,严厉抨击“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20](P128)并得出了勤俭节约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近代“劳动价值论”的创始人洛克认为,大自然尽管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一切东西,但是却仅仅是提供了一些生存所需要的“质料”而已。只有通过人们的劳动才可能将这些东西转化为“面包、酒和布匹等日常所需用而且数量很大的东西”,[21](P153)这里已表达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精神”的雏形。斯特劳斯认为,自然法禁止人们浪费,“对自然法感到恐惧的,不再是贪婪之徒,而是暴殄天物之徒”。[22](P242)综上可见,勤俭之德不仅关系到一人之成败、一家之祸福,还关系到民风之淳厚、国家之兴衰。今天,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享乐懒散之行、奢侈消费之风,只有以勤劳战胜懒散,以节俭遏制奢靡,才能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以劳动教化人性,以节俭淬炼理性,构筑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厦。劳动和节俭不仅是创造硕果和获得持久幸福的手段,而且是净化灵魂和升华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华民族道德大厦的构建离不开勤劳和节俭的优良品性。劳动是道德产生的母体,是美德和健康人格形成的基础。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视为接受“天降大任”者磨炼意志、提升德性的必由路径(《孟子·告子下》)。黑格尔则明确指出,劳动是人及世界的“中项”,劳动具有教化作用,“劳动的实践教育首先在于使做事的需要和一般的勤劳习惯自然地产生;其次,在于限制人的活动,即一方面使其活动适应物质的性质,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使能适应别人的任性”。[23](P209)他认为,有无教养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能做别人做的事而不表示自己特异性的人,至于没有教养的人则要表示这种特异性,因为他们的举止行动是不遵循事物的普遍特性的”。[23](P203)劳动作为一种实践教育,能够使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将人教化成为真正的人。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则提出了教育起源于劳动的思想。他说:“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劳动使一个人的道德变得高尚。”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劳动教育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劳动能使人“心地正直”,[24](第1卷,P114~115)要“努力使每个受教育者懂得自己对他人的生活、健康、精神安宁和幸福负有劳动的责任和道德的义务,要使其认识到拒绝劳动、拒绝责任和义务是卑鄙可耻的”。[24](第1卷,P103)他强调儿童的道德成熟性、精神上的“成年”,取决于对待劳动的态度,取决于劳动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重视劳动的教化作用,《国语·鲁语下》云:“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亡善则恶心生。”在孔子讲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射”和“御”两门课都是劳动教育课。梁启超也非常重视劳动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万恶惰为首,百善勤为先”,反对不劳而食、借祖宗福荫的做派。他列出了四个最易遵守的“道德公准:同情、诚实、勤劳、刚强”,认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要以这四个道德公准的传授为主”。[25](P3339)可见,劳动有助于完善人性和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通过培养青少年热爱劳动的品质,可以使其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另外,膨胀的贪欲和脆弱的理性是人类修养德性的两大障碍因素,而节俭之德有助于遏制贪欲,淬炼理性,因此古人提出“俭以养德”,[26](P28)把节俭作为砥砺道德的磨石。相反,奢侈是危害德性的行为,它既败坏富人也败坏穷人,不仅促使前者占有财富,而且促使后者觊觎财富,并使国家沉湎于萎靡和虚荣之中。任何物质财富都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晶,因此放纵物欲、暴殄天物,既是对宝贵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人类劳动的践踏,更是一种“道德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下,应大力倡导勤劳节俭之德,抑制懒散奢靡之行,为构筑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厦、建设风清气正的文明社会奠定牢固的基石。
第三,以勤劳节俭之德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自由、平等、友爱、尊重劳动、创造幸福、崇尚和谐等都是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皆与勤劳节俭之德密切相关。蔡元培曾说:“勤则自身之本能大,无需于他;俭则生活之本位廉,无人不得,是含自由义。且勤者自了己事,不役人以为工,俭者自享己分,不夺人以为食,是含平等义。勤者输吾供以易天下之供,俭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实有烛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谛,而不忍有一不克致社会有一不获之夫,是含友爱义。”[15](P232)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勤劳节俭之人都是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友爱理念的践行者。同时,尊重劳动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尊重劳动可以从两个层面诠释,从微观角度讲,每个人的节俭行为都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从宏观角度讲,全社会要给劳动者以地位、尊严,让每个人因劳动而光荣、因劳动而幸福。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做到的。尽管韦伯将勤劳和节俭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和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使得劳动被异化,劳动的幸福感不复存在,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无以保障。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时指出:“劳动对工人是一种外在的,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感到自己不是幸福,而是不幸的。”[4](P54~55)恩格斯说:“如果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1](第2卷,P404)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劳动走出异化,回归其本真与美好。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所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注)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呼吁:“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27](P251)邓中夏在其创办的《劳动音》中指出,我们(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的新社会)“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综上所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愉快而幸福地劳动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才能真正被尊重,劳动人民才能真正有尊严和人格。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应高擎“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大旗,将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社会主义奉行的四大核心价值观念包括尊重劳动、缩小差别、关爱底层和人类联合一致行动。”这四大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大旗”,其中“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坚持的第一核心价值主张”。[28]尊重劳动就是要承认任何劳动的价值,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是“要强调和认可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确认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承认劳动是人存在和展现本质的唯一方式”。[28]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不仅要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在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以平等的心态尊重他人的劳动,以主人翁的精神爱岗敬业、诚信奉献,以勤劳节俭之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29]
崇尚节俭、和谐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关心普天之下的劳动者、与邻为善、济贫扶弱、爱护环境、以天下为己任是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需坚守勤劳节俭之德,以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风尚,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节俭之德是无私之德、自律之德,中国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离不开国人的节俭之行。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仍的危机,更需秉承“天人合一”之理念,倡导“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消费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社会主义社会开辟持久美好的未来。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2015-04-29(1).
[3] 温美荣.勤俭从政与政府行政成本关系研究[J].行政论坛,2014,(2).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 陈独秀.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7] 钟茂森.朱子治家格言[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9] 向培风.智慧人格——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10]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人类的18种美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2]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
[16] 杨继盛.杨忠愍公遗笔 训子言 乐言 家诫要言 庞氏家训 温氏母训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M].宋景堂,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8] 曾国藩.曾国藩全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9]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0]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21] 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M].赵伯英,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2] 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6] 诸葛亮.诸葛亮集[M].段熙仲,闻旭初,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
[27] 陈独秀.陈独秀语萃[M].唐宝林,编.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28] 何云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张的新诠释、新概括[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9] 何云峰,刘严宁. 劳动是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和人的价值与尊严之根源[J].青年学报,2015,(3).
——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