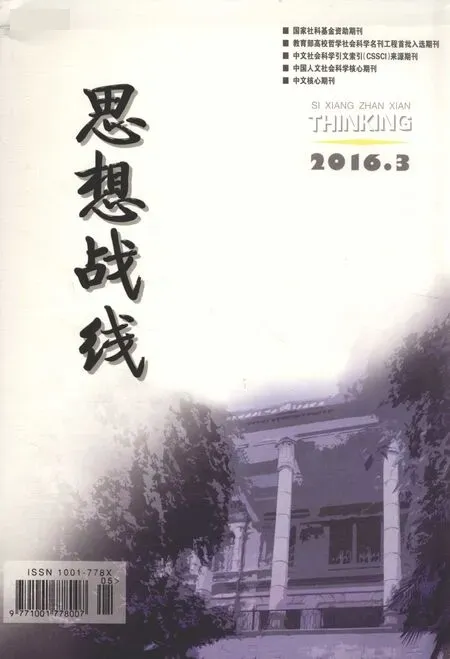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
孙 竞,张 文
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
孙竞,张文①
摘要:由唐入宋,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与之相伴随,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宋朝廷一改前代“轻济贫重恤穷”的救助传统,首次将贫困问题纳入国家社会保障的范畴。为了甄别贫困人口以便进行社会救助,宋朝廷设立了类似于现代社会贫困线的贫困救助标准。一条标准行之于乡村,以占田20亩以下者为贫人;另一条标准行之于城市,以家业钱在50贯以下为贫人。纵向上看,宋代社会贫困线的推出,标志着社会保障思想较之前代发生重要转变,即国家对于贫困问题的正视与责任;横向上看,与迟至17世纪才开始履行国家济贫责任的英国相比,宋代的济贫实践无疑具有超前性。
关键词:宋代;社会贫困线;社会保障
如众所知,由唐入宋,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明显变动,学界往往将其称之为唐宋变革。反映到社会经济层面,突出表现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与贫困人口的增多。与之相伴随,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现实倒逼改革,对此,宋朝廷一改前朝“轻济贫重恤穷”的传统,首次将贫困问题纳入了社会保障的范畴。*关于宋代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可参见张文《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一、问题的提出:唐宋变革与贫困问题
中唐之前,由于名田制与均田制的存在,土地兼并受到抑制,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均等。但实行两税法之后,“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页。。尤其是宋开国后不立田制,“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乾兴元年二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69页。,社会贫富分化程度迅速加剧。其中,失地农民一部分沦为佃户,另一部分则涌入城市,成为城市流民。由此,经济层面的变动演化为一场社会危机,贫困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宋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与传统仁政表达的需要,形成了以贫困救济为主、医疗救济为辅的济贫制度。*关于宋朝的济贫制度,可参见张文《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与该制度相匹配,社会贫困线的制定成为各项济贫措施以及其他社会政策执行的前提与依据。从而,宋朝廷在对待贫困问题上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突破,出现了近似当下社会贫困线的概念。
对此,学界亦有所关注。较早关注该问题是王曾瑜,其在《宋朝阶级结构》中以阶层划分的视角提到了宋代社会贫困线问题,认为20宋亩为“贫下之民”的认定标准。*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我们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宋朝社会救济研究》中曾经专门谈论了宋代的社会贫困线问题,认为宋代社会贫困线的制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的出现标志宋朝廷已经将贫困问题纳入国家责任的范围之内。*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此外,台湾学者梁其姿与日本学者夫马进亦从民间慈善的角度讨论过传统社会的贫困观问题,其二人都认为,宋代是传统社会贫困观念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具体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6页)以及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0~42页)。大体而言,以上研究成果虽开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但对社会贫困线社会意义的阐释仍然不足。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贫困线定然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一种折射,标志着贫困问题已经被朝廷所正视,以至于需要制定一套长期的济贫制度。此外,贫困线也是对当时执政理念与国家伦理的反映,意味着宋朝廷较之前朝进行了理念更新与伦理自觉,以至于将贫困问题纳入了自身职责范围之内。
二、宋代之前有无社会贫困线?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贫困人口由两类人组成,一为“穷民”,即鳏寡孤独四种人伦缺失者;另一类为“贫民”,即经济匮乏者。梁其姿认为,大约在宋代之前,“贫富只是笼统的经济分类概念,贫人并不构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类别。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贫民之所以形成社会问题,通常并非单纯地由于经济匮乏,而是由于缺乏家族乡里的相助,古书中不见将纯粹生活困苦的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类别来讨论,而将鳏寡孤独这四种在人伦上有缺憾的人等同为贫人”*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页。。所谓鳏寡孤独,孟子的解释是:“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2上《梁惠王章句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也就是说,先秦时期贫穷救助的主要人群为“穷民而无告者”。即便是更早的商代,亦如此。周人在追忆商代祖甲时,认为其得以在位30多年的原因在于“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无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可见,先秦时候人们往往将“穷民”视为贫困人口。换言之,当时对贫困的定义忽视或者淡化了经济匮乏这一层面,而是基于人伦缺失,即“无告者”为贫,“穷民”即“贫民”。究其原因,美国学者博杜安认为,在前现代社会,“贫困是日常生活的显著特征。大多数人都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自己视为穷人”*[美]史蒂芬·M.博杜安:《世界历史上的贫困》,杜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页。。梁其姿也持类似的观点,她认为“贫穷不构成一个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早期社会的主要构成者是贫人”*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年,第130页。。
秦汉时期依旧将人伦缺失者视为穷民,汉律规定国家须向“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页。提供救济。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开始出现了具有经济含义的贫困线,在皇帝赏赐与灾荒救济中,朝廷开始划定一个基准作为恩赐或者救济的标准。汉元帝元初元年(48年),以立皇后之故,下诏要求对“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9页。。这里的“赀不满千钱者”,是指“极贫者”,相当于最低的贫困线。此外,在汉代的灾荒救济中,亦存在三万钱或十万钱两条贫困线。如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水旱严重,流民众多,诏令“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汉书》卷10《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8页。又如,绥和二年(前7)诏:“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汉书》卷10《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7页。由上可知,汉代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开始形成了依照资产多寡、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贫困线标准。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即汉代的社会贫困线仅仅在皇帝赏赐与灾荒救济中出现,是一种临时性的界定,也正因为如此,汉代的贫困线非常不稳定,仅从现有史料来看,存在千钱、三万与十万三种划分。我们推测,汉代的贫困线应该是一种浮动的临时赈济线。
演至隋唐,虽然在史籍中存在近似贫困线的记录,但是隋唐时期的社会贫困线依旧延续了秦汉时期的特点,呈现出临时性与地区性的特征,仅仅在特殊时期有所体现。如安史之乱后,关中亟待恢复,德宗要求各地进贡耕牛以便分配给农户,但最初德宗要求只分配占田在50亩以上者。对此,袁高认为,“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旧唐书》卷153《袁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88页。,应该两三家合为一组,分配耕牛以助耕种。
但是,我们在看到隋唐在贫困线上对秦汉继承的一面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隋唐在贫困观念以及贫困救济方面亦存在突破的一面。而这种突破,为宋代社会贫困线的正式推出开启了端倪。夫马进曾指出,自北魏开始,中央朝廷对待鳏寡孤独的救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一改汉代由国家直接救助的方式,而是向鳏寡孤独者授田,通过土地保障其生存。*[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页。唐代沿袭了自北魏以来的以授田为主的保障措施,依照均田制,唐朝廷向所有的鳏寡孤独者支给口分田40亩。*[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韩国磐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6页。与之相对应,唐律也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在对农村穷民救助方式发生改变的同时,城市中的贫民问题亦开始浮出水面。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城市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尤其是在中唐之前,传统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为皇室与官僚,工商业者极为有限,城市管理也甚为严格。因此城市中并没有太多的乞丐等流浪人群。随着城市经济职能的增强,城市流浪人群开始出现。为了对其进行保障,南北朝几乎同时开始在首都设立专门救济城市乞丐的官方救助机构。*[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7页。而唐代亦继承了这一趋势,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长安设立病坊。*董诰等:《全唐文》卷704《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24页。
综上,到了宋代不立田制,因此宋朝一方面不可能延续唐朝对穷民授田的规定,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乡村贫民数量激增,一部分又流入城市,使得城市中的乞丐大增。贫民问题开始成为宋王朝不得不正视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从而将其纳入各项政策的考量之中。而这一切,都为宋代社会贫困线的推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宋代社会贫困线的确立及实施
北宋建立于唐末五代动乱之后,宋王朝为图长治久安,对社会救济事业极为重视,“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史》卷178《食货上六·振恤》,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35页。与前朝相比,宋代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是扩大了朝廷保障的范围,将自先秦以来所忽视的“贫民”阶层纳入朝廷责任。其中,社会贫困线的确立是一项重要标志。
由唐入宋,社会经济层面最为重要的变动在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大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小土地所有者日益贫困乃至破产,“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赈贷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狈无策,只有流离饿莩耳”。*董煟:《救荒活民书》卷1,《中国荒政全书》第1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页。换言之,由于土地兼并不再受抑制,贫富差距在农村急剧扩大。曾经在均田制下能够勉强糊口生活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保障之后,要么沦为占田极少的贫下四、五等户,要么成为无田的佃户,抑或涌入城市,成为流民。作为社会的下层,“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六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048页。。
正如前所述,宋代之前的王朝往往将救济人伦缺失者“穷民”视为日常施政的内容,而对于“贫民”,则采取忽视的态度。因为在名田制、均田制下,小自耕农尽管占田不多,但是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惟有贫困大面积发生的灾荒时期,朝廷才会进行救助。但到了宋代,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贫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呈现长期化与普遍化的趋势,并对社会稳定与王朝统治构成威胁。世异则事异,面对新形势,宋朝廷从传统仁政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出发,突破了旧有“轻济贫重恤穷”的救济观念,开始正视贫困人口的存在,并着手予以解决。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正月,“澶州言民诉水旱二十亩已下,请不在检视之限”,对此,太宗专门下诏驳斥:“朕每恤蒸民,务均舆赋……欲惠贫下之民,岂复以多少为限?自今诸州民诉水旱二十亩以下者,仍令检勘。”*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802页。由此,占田在20亩以下的五等户成为宋代定义“贫下之民”的具体量化标准,同时也成为宋朝廷在推行军政、民政等措施中认定贫困的基准。从灾害的检视、赋税的蠲免到劳役的征发,占田20亩的贫困线标准一直被宋朝廷多个部门予以认可并执行。神宗时,曾规定第五等户或产业在50贯以下的免出役钱,而50贯大约等于北方20亩左右土地的价格。*周宝珠:《简明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8页。迨至绍圣二年(1095年),监察御史陈次升在奏折中依旧将“土地不及二十亩者”称之为“贫下之民”。即便到了南宋,20亩的贫困线标准依旧在官方推行,如淳熙四年(1177年),湖南路以20亩作为曲引钱的免征标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麴引钱》,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5页。
综上可知,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应用范围,20亩作为社会贫困线的标准在宋朝廷的日常施政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此以外,宋朝廷还将“五等版籍”下划分出的乡村下户,即四、五等户视为贫民,“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贫困之民”。*刘琳等:《全宋文》卷7148《乞给降钱会下本路灾伤州郡下户收籴麦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12册,第252页。换言之,乡村四、五等户的评定亦发挥着一定的社会贫困线的功能。
结合王增瑜先生的研究,其认为宋代乡村下户第四、五等户的占地情况普遍在几十亩到一二亩之间。*王增瑜:《宋朝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50页。由此可见,宋朝廷以占田亩20作为“贫下之民”的标准是符合宋代乡村实际情况的。
对宋朝廷而言,贫困线是其实行社会救助的依据与标准。因此,取得贫民身份是能够为乡村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具体分述如下:
其一,蠲免。宋朝廷秉持“天下租赋,当先富后贫”*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田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的理念,对乡村贫民的赋税或所欠官府钱物多有免除。如熙宁七年(1074年),令灾伤州县“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无以输者……尽蠲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111页。。又如天圣元年(1023年),由于草价腾踊,“四等以下户悉蠲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二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316页。。以上是对赋税的减免,此外,宋朝廷对贫民的差役亦有减免。如神宗时期实行保甲法,以20亩贫困线为免除服役的标准:“元丰八年四月,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并第五等以下田不及二十亩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4,元丰八年四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484页。
其二,赈济。无论是无偿赈给,还是有偿赈粜,贫民一般享有优先得到赈济的权利。如司马光曾在治平四年(1067年)提出,在赈济贫民时候,应该“各从版籍,先从下等,次第赈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6《上神宗乞选河北监司赈济饥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38页。。就具体赈济内容而言,一般可分为实物赈济与货币补贴两类。如建隆三年(962年),“诏赐沂州饥民种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6《国用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2页。,直接给予贫民食物。此外,根据“胎养助产令”的规定,“乡村五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27页。,即乡村贫民能够获得生育补贴。
其三,借贷。即将救济物品以借贷的方式暂时性给予受助者,以助其摆脱困境。对于接受朝廷赈贷的贫民,往往能够获得免息的优惠。如熙丰变法时,依照青苗法规定,凡支借常平米第四等以下人户皆可免出息钱。*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7之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15页。
以上是乡村贫困线的优待情况。在日常行政中,宋朝廷一般将坊郭户户等制度下划分出的六等、七等以下视为贫人。如宋仁宗时,欧阳修曾将“六等已下”称之为“贫弱之家”*刘琳等:《全宋文》第16册卷691《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655页。。宋徽宗时推行均粜,规定“坊郭第六等已下、乡村第五等以下均免。”*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548页。迨至南宋,依旧如此,如高宗曾诏令“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27页。。由此可见,宋朝廷往往将坊郭户中的六、七等以下与乡村户中的五等户相提并论。换言之,尽管宋代户籍制度中将坊郭户与乡村户分列,但在评定其贫困程度时候,两者具有潜在的、相同的评判标准。因此,宋朝廷习惯性地将坊郭户六、七等以下与乡村户五等以下一并认为是贫民。由此,可将乡村社会贫困线的20亩标准换算成家业钱,以此作为城市的贫困线标准。依前文所述,20亩农田大约价值50贯。那么,宋代城市的社会贫困线标准也应该在50贯左右。事实上,宋朝廷也的确将50贯视为城市的社会贫困线。免役法刚刚推行时曾规定,“坊郭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但后来发现200贯的蠲免标准对城市坊郭户而言过于优厚,提举司认为“轻重不均”。由此,元丰二年(1079年),“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宋朝廷将城市免输役钱的标准恢复为与乡村同等的50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270页。
结合程民生先生的研究,宋代城市中等坊郭户的家业钱在100贯左右。*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8页。而坊郭下户多为“闾阎之人,以数百钱为资生之策”,家业钱一般维持在30贯上下。*刘琳等:《全宋文》第263册卷5927《论土木之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如“第七等一户高荣,家业共直十四贯”。*刘琳等:《全宋文》第32册卷692《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可见,50贯作为宋代城市的贫困线是符合实际的。
虽然同样是贫民,但由于宋朝廷的济贫机构大多分布于朝廷,城市贫民无疑能够获得更多的朝廷救助。换言之,城市贫民身份的实际意义要比乡村贫民更加显著。
其一,蠲免。与乡村贫民一致,城市贫民亦享有蠲免赋役的福利。如神宗时推行免役法,规定“坊郭自六等一下勿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22页。。此外,城市贫民有时还会被蠲免房钱。由于许多贫民在城中并无私人房产,多为租借公私房舍居住,每到冬季,往往无力支付房钱,遂被逐出,冻饿而死。对此,宋朝廷每到寒冬到来,总要下诏蠲免城市贫民的公私房舍钱,“国朝祖宗以来,惠恤孤贫,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则放公私房钱”*刘琳等:《全宋文》第98册卷2129《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札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其二,赈济。与直接向乡村贫民赈济粮食不同,对城市贫民的赈济手段较为丰富,既有食物赈济,也有货币补贴。如乾道九年(1173年)闰正月十七日,“诏雪寒,细民艰食,令临安府将贫乏不能自存之家,左藏南库支会子六千贯,丰储仓拨米三千石付临安府,分委有心力官日下巡门散赈济,每名支钱二百文,米一斗。务在实惠,不得减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5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64页。又如“张咏镇蜀日,春粜米,秋粜盐,官给券以惠贫弱”。*《宋史》卷315《韩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03页。
其三,居养。根据宋朝廷颁布的养济法与安济法,宋朝廷需要对城市贫民中的乞丐进行救助,对其提供住宿、医疗与食品。居养法规定:“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65页。“安济法”规定:凡户数上千城寨镇市,一般都要设置安济坊,用以收治贫困患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5,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67页。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地方里正甚至一般平民均有责任将其送入安济坊收治。*洪迈:《夷坚志》之《夷坚乙志》卷5《宋固杀人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就宋代乡村的实际情况而言,一般民户家庭“大率户为五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0,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199页。,“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方回:《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四库全书本,第14页。换言之,宋人认为五口之家一年至少需要十八石粮食来维持生活,20亩的农田,能够提供的粮食也正好在十八石左右,“夫有田二十亩之家,终年所收不过二十石”。*刘琳等:《全宋文》第37册卷1592《奏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但是“一年食十八石”是依照“人日食一升”而确定的,若比照宋朝廷救荒的口粮标准,“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或“人日二升”*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7之8~9、59之1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14页,第5848页。,则“人日食一升”是一个偏低的标准,甚至没有达到朝廷灾荒救济的口粮标准,再扣除朝廷的赋税,能否维持五口之家的温饱都很难说。所以,如果援引当下对贫困线的分类概念,宋代的社会贫困线类似于绝对贫困线,即以满足人体基本活动所需的最低营养水平划定的。*[英]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匡小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结合前面所述,凡是符合社会贫困线的要求、取得贫民资格的城乡居民,能够获得相对应的贫困救助,这说明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已经具备了与当下社会贫困线相接近的社会功用:朝廷通过贫困线来识别贫人,并为之提供系列的社会保障服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客户在平常时期并不在法定救济之列。原因在于客户平时并不向国家交税,而是向地主缴纳地租,所以对客户的救济责任在于地主。*关于宋代地主阶层对农民的救济,可参见张文,陈宇《慈善与枷锁:论宋代地主对农民的救济》,《思想战线》2013年第4期;以及林文勋《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如“据乡村五等人户逐户计口,出给历头”,这里仅限第五等主户享有救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065页。又如淳熙九年(1182年),宋朝廷直接将借贷种粮、救济客户的责任交予地主,“劝谕上户,遇有流移之民未复业者,收为佃户,借与种粮。秋成之时,量收其息。其旱伤州县佃户贫乏不能布种者,亦令佃主依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9 之66,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362页。
四、宋代社会贫困线的社会意义
第一,标志着贫困问题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正如前所述,宋代之前,传统社会保障的主要对象除了灾荒期间之外,平时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穷民,即鳏寡孤独无告之民。而对于贫民以及贫困问题,则基本上是处于被淡忘或者忽视的状态。究其根本,主要在于授田制度的存在。对于农民而言,在授田制度下,其多少能够获得一份田地,从而可以维持生计。除非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否则依靠国家授田,小农一般可以保持温饱。对于国家而言,授田制度意味着可籍此获取财赋与劳力,是帝国统治的基石。因而国家也极力维护这一制度,抑制土地兼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较为均等,贫困问题并不突出,只有非常时期的自然灾害以及正常时期的鳏寡孤独者,才构成社会问题。这也是汉唐社会“轻济贫重恤穷”的存在逻辑。
迨至中唐,“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页。,“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48《民事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764页。由此,“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40《财用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565页。。田制的变化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贫困问题开始呈现常态化的趋势,无田地则无怙恃,失地农民成了新的“无告者”,严重威胁着城乡社会的稳定。对于秉持“守内虚外”国策的宋朝而言,这是不能无视的。二是田制不立,国家不再授予农民土地,但依旧收取农民租税。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宋代农民已经近乎当下纳税人的意味,而国家为其提供社会服务乃自身职责所在。而且,就传统的仁政思想而言,宋朝廷也需要救济贫民,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是由唐入宋,贫困问题被纳入社会保障的演变逻辑。
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划定一条社会贫困线来判定贫困与否,以此作为国家救济之依据,也实属必然。由此,“一个不同于传统恩赐性质的、具有前近代国家责任性质的、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宋朝建立起来。”*张文:《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第二,为宋朝廷一系列社会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自唐代建中两税法确立“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之后,传统社会的赋税制度开始由“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75页。方向转变。宋代社会贫困线的推出实质上也是适应了“唯以资产为宗”*董诰等:《全唐文》卷465《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49页。的新趋势。
综合张方平所言的“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以上差科,所以惠贫弱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107页。加之前文曾引用的“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可知宋朝廷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非仅停留于社会救济这一个层面,而是将其纳入了国家日常施政之中,进行综合治理。
若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来考察,宋朝推行具有量化意义的贫困线标准,无疑较之前代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标志着宋代的社会保障实践开始呈现制度化的特征。宋朝曾经颁行了多部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如报灾检灾法、元丰乞丐法、居养法、安济法、劝分法等,其意图在于将朝廷的社会救济活动固定化与持久化。而社会贫困线的设立,正是宋朝制度化努力的一部分。
第三,宋代的济贫实践在东西方福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宋代推出社会贫困线、将贫困问题纳入国家责任的范畴之内,具有明显的超前性。
15世纪之前,无论是西欧还是中东、非洲等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宗教与家族救济,朝廷并不承担主要责任,“西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教会在济贫方面相媲美,中东甚至在法律层面禁止出现官办的济贫机构”。*[美]史蒂芬·M.博杜安:《世界历史上的贫困》,杜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3页。直到中世纪晚期的英国,随着大批农民进城成为雇佣工人,因失业造成的偶发性贫困开始困扰着工商业城市,加之英王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之机关闭了诸多修道院,削弱了基督教的济贫功能。由此,英国国会才于1601年通过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案》,被迫在国家层面开始承担济贫的责任。之后,由朝廷履行社会救助职能的执政理念才陆续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与之相比较,宋朝对待贫困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无疑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一方面源于自先秦以来的仁政思想,“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4《大禹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缺乏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承担相应职能的宗教组织。加之“家国同构”的社会特征,“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2《洪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宋代的济贫理念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自然更加成熟。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西欧诸国开始承担济贫责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对待贫民的态度与宋朝依旧具有较大差距。受新教伦理的影响,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社会普遍认为上帝会奖励那些勤劳工作的人们,换言之,当时的贫困问题被视为一个道德问题,意味着懒惰、鲁莽与挥霍。基于此观念,西欧国家对贫民的救济往往将救助与惩戒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场针对懒惰的斗争”*[美]史蒂芬·M.博杜安:《世界历史上的贫困》,杜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7页。。相比之下,宋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更加具有人道的意味,不仅给予食品与医疗救助,亦从赋税减免等多个角度进行安抚,体现了国家对人民应有的责任,尽管其思想渊源未超出传统仁政的范畴。
(责任编辑 王文光)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再分配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2AZS005);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宋代贫富差距问题研究——以北宋城市为中心”阶段性成果(CYB2015062)
作者简介:孙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