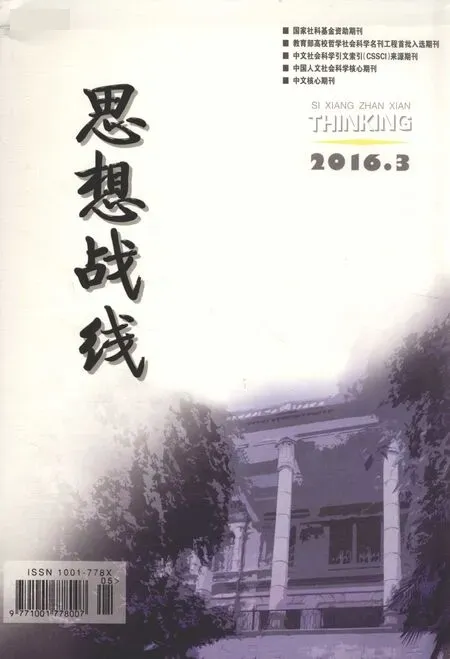环境正义的分配范式及其超越
王云霞
环境正义的分配范式及其超越
王云霞①
摘要:作为全球绿色运动中的重要一脉,环境正义是民权运动、反有毒物运动、学界推动、原住民斗争、工人运动,以及传统环境主义共同孕育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囿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传统正义论的影响,环境正义的研究范式一直被分配正义所主导。但正义之内涵远不止于分配维度,而应有更宽泛的意义和指向。学者们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和现实的环境正义斗争实践表明:将正义和环境正义之“正义”内涵归约和简化为单一的分配视角是有失偏颇的。正义实际上是集分配、承认、能力和参与等四种维度于一身的统一体。基于此,对传统正义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反思,并积极重构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就显得非常必要,对推动正义论,尤其是环境正义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环境正义;分配范式;承认正义;能力正义;参与正义
一、环境正义的兴起
环境正义是在全球环境保护浪潮中产生的一种绿色环境运动。它和传统环境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将对“环境”一词的理解从荒野、湿地、国家公园、濒危野生物种转向了“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环境正义的前身是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指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有毒危险废弃物处理厂和污染企业的选址上存在种族歧视的行为。它暗含了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批评,但由于承载的感情色彩太浓,加之涵盖范围又过窄(似乎只有有色人种才会遭遇环境非正义行为),因此不久便被环境平等所代替。环境平等是指对所有人(并非只是有色人种)免于环境危险物的一种平等保护。但与“正义”一词相比,“平等”的内涵显然并不那么宽泛和更具包容性。所以,环境正义很快就将环境平等取而代之。关于环境正义的发端,学者们的看法各有千秋。有“环境正义之父”之称的美国著名黑人社会学家布拉德主张,1967年非裔美国学生因休斯顿市1名8岁黑人女孩淹死在一个垃圾倾倒池而进行的抗议活动是环境正义运动的肇始;有学者则将1968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因支持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垃圾清运工的罢工斗争而被暗杀的事件视为环境正义斗争的开端;还有学者将环境正义追溯到美洲原住民500多年前面对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进行的抗争。
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瓦伦县由众多非裔美国人掀起的抗议有毒废弃物倾倒的斗争事件——也即“瓦伦抗议”,被公认为是环境正义真正兴起的标志。它被视为美国乃至世界环境正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当局在以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白人为主要居民的瓦伦县修建了一个填埋式垃圾处理场,打算用来储存从该州其他14个地区运来的PCB废料,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在多方寻求正义无果的情况下,愤怒的人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由几百名非裔妇女、孩子以及少数白人组成的人墙封锁了装载着有毒垃圾卡车的通道,并与当地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冲突中,有500多人被逮捕。“瓦伦抗议”虽以失败告终,但却预示了一种与传统主流环境主义大相径庭的全新环保运动——即以社区为基础,以少数族裔及低收入阶层为核心力量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出现。
环境正义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如果把它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这条大河就是无数条支流汇聚和共同孕育下的产物。环境正义运动至少有6个来源:*参见Luke W. Cole and Sheila R. Foster, From the Ground Up: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0~30.1.民权运动。民权运动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和歧视,并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长期以来,非裔美国人在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承受着白人的恶意种族歧视,在环境恶物的承担上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企业和政府的目标,这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而由其掀起的环境正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民权运动在环境问题上的延伸,因为它表达的是非裔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对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诉求,反对的是环境问题层面上存在的任何种族主义歧视。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的这种天然联系也使其受益良多,如在组织领导、斗争策略以及理论武器等方面环境正义都借鉴了民权运动。有学者指出:
通过对种族歧视、社会正义等问题清楚有力的表达,环境正义运动将自己建立在对民权运动的修辞学策略的继承之上……总之,正是将自身不合比例地暴露于环境负担之下看作是对民权的侵犯,环境正义成功地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融合到了民权的框架中。*Stephen Sandwies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David E. Camacho (eds. ),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political struggle: Race, Class, and the environment, Durban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9.
2.反有毒物运动。它是指由贫穷社区的居民发起的抵制和反对处理有毒废弃物的设施,如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化炉等设在自家后院的一种运动。由草根群众发起的反对有毒物运动(NIMBY,不要在我家后院)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爱河事件”。*爱河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一起化学污染泄漏事件。爱河是位于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一条大水沟,曾被胡克电化学公司在1942~1945年间用作垃圾填埋场。1950年,胡克公司以1美元的价格将垃圾填埋区转让给了当地教育局。随着学校、居民社区在爱河的相继建立,居民们的身体健康开始出现状况。1978年,美国国家环保局等对该社区的室内空气及地下淤积物进行检测后,证实爱河地区存在大量有毒化学物质,会导致人和动物患上癌症等疾病。1980年5月19日,两名美国环保局官员被爱河社区的居民扣留。他们吁请白宫发起救助,将在垃圾填埋场上建立起来的社区中的无辜居民永久撤离。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也使广大民众乃至政府开始关注有毒有害垃圾对社区居民健康的影响。3.学界的推动。在研究环境正义方面最声名显赫的学者有布拉德、李、查维斯、布赖恩特以及毛海等,他们对有色人种、低收入人群等美国社会弱势群体不合比例地承担环境恶物事实的揭露,在点燃、发动和促进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布拉德通过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地区的土地使用模式后,发现该地区垃圾倾倒地对非裔美国人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该研究首开美国学界研究环境种族正义之先河,也由此奠定了布拉德在该领域的领袖和先锋地位。由布拉德和其他学者组成的“密歇根小组”还定期讨论彼此在环境正义领域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种族与环境危险物的发生率”。不仅如此,他们还给美国国家环保局官员写信,要求与之会面并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本土的环境非正义行为。此举带来的最大成效就是美国国家环保局很快成立了“环境平等办公室”(后更名为“环境正义办公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1994年签署了环境正义政策的重要国家性文件——“第12898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实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的环境正义》),由此把对环境正义的重视上升到国家层面,而这正是得益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推动。4.美洲原住民的斗争。作为环境种族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美洲土著部落自欧洲殖民者入侵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争取土地自治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即使在美国获得独立后也从未间断。它给环境正义带来了几个世纪的自治斗争以及对土地资源掠夺式开发予以抵制的宝贵经验。5.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也为环境正义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在美国,“每年大约有2 500万工人在工作场所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物质的侵害。其中,每年死于与此相关的并发症的工人大约在5万到7万之间”。*Patrick Novotny, Where We Live, Work and Play: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 New Environmental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ers, 2000,p.41.出于对工作场所安全和自身健康的关注,农业工人对DDT等危险杀虫剂掀起了抵制活动,工业工人们也开始对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大声呼吁。在一些地方,“工会和工人们甚至加入到社区居民反对有毒废弃物和污染的队伍中来”,*Patrick Novotny, Where We Live, Work and Play: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 New Environmental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ers, 2000, pp.41~42.这大大促进了环境正义的发展。6.传统环境主义者的推动。传统环境主义者主要指长期活跃在环保运动前沿的主流环境保护组织,如塞拉俱乐部、地球之友、荒野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等。它们长期致力于荒野、湿地、濒危物种、水等公共资源的保护,在促进美国政府制定环保法律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关于环境正义与环境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环境正义是传统环境主义在当代最重要的发展形式之一”,*Walker Gord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ncepts, Eviden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ge, 2012, p.17.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正义并非主流环境主义的拓展和延伸,而是对后者的一次大逆转和反叛,因为二者“来自不同的世界”。*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Environmental Justice: Creating Equality, Reclaiming Democra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公允而论,虽然环境正义和环境主义在主张、目标和正义指向上都大相径庭,*参见王云霞《环境正义与环境主义:绿色运动中的冲突与融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但主流环境组织还是在很多方面促进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如雇佣环境正义组织中的成员,声援环境正义斗争等。
由民权运动、草根反有毒物运动、学者、工人,以及原住民等形成的强大力量,最终汇聚成了1991年“第一届有色人种领导高峰论坛”的召开。它对环境正义运动的“总体目标、发展策略、行动计划及国际合作等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些共识,为环境正义运动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高国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环保运动》, 见徐再荣等《20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 277页。如论坛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如尊重神圣的地球母亲,保障所有人免于有毒有害废弃物和核试验的生产处理威胁,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本土民族的自治权利,保障人们平等的环境权益,以及反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破坏性行为等。*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October 27. 1991, http://www.ejnet.org/ej/platform/html.论坛本身也标志着环境正义已发展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被广泛关注的社会运动,是环境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二、环境正义的早期研究范式:分配正义
“正义”是自古希腊以来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亚里士多德最早将正义区分为两种形式:分配性正义和惩治性正义。在他看来,前者涉及各种各样的好处和坏处应当如何分配,后者则关乎如何处罚非正义行为和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等。一直以来,正义就被理解为是关于“分配是否正义”的问题。这种思想倾向在罗尔斯出版《正义论》后更是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这部对后世有着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的恢弘巨著中,罗尔斯对正义作出了这样的界定: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对罗尔斯而言,正义即是社会利益的恰当分配,而“关于公平的正义”就是“关于分配是否公平的正义”。所以尝试提出一种更合理的分配原则,就成了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目的。
《正义论》无疑是代表现代正义理论的巅峰之作,而罗尔斯有关正义论的主张也几乎成为了理论界的惟一风向标。这体现为在《正义论》出版后的将近40多年里,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文献都将正义界定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商品能否得到公平分配”的问题。*David Schlosberg,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正义理论仅在对分配的考虑和关注中才真正有效。正义的最基本问题即是:
一个社会应当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对其生产的各种福利(资源、机会与自由)和为实现这种福利而产生的负担(成本、风险和非自由)进行分配。*Brighouse Harry, Justice, Cambridge: Polity, 2004, p.2.
由此,正义的核心框架就被理解为:在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时,必须关注“分配什么”以及“如何分配”。
对正义的上述诠释很长时间以来影响了包括环境正义在内等领域的研究范式,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有关环境正义的研究文献至少有95%都是围绕分配正义进行的”。*David Schlosberg,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如此高的数字比例,既彰显了环境正义的早期研究路向,也反映出罗尔斯对理论界的巨大影响。因为既然环境正义的研究是在分配正义的主导范式下展开,在这种理解框架下,将环境正义解读为“关于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能否得到公平分配”就成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受此影响,学者们在研究环境正义时,大多热衷于对有色人种、低收入阶层等社会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恶物进行揭示。例如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就曾在1987年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有毒废弃物与种族》*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with Hazardous Waste Sites,United Church of Christ,1987.的研究报告。这份在环境正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献,将一个深藏于美国社会的丑恶事实,也即“环境种族主义”推到了公众和政府面前。报告指出,美国商业危险废物处理厂和废弃物填埋场的选址与其周围社区的种族状况有着惊人的相关性:越是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越容易成为有毒废物处理设施和废弃物填埋“最理想的场所”。该委员会于2007年发布的新报告《20世纪的有毒废弃物与种族:1987~2007》,*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 1987~ 2007,United Church of Christ,2007.再次印证了环境种族主义歧视的事实。布拉德则在《在美国南部各州倾倒废弃物》*Robert. D. Bullard,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中详细考察了美国南方各州有毒废弃物的堆置、填埋、焚烧,以及污染性企业如何不成比例地靠近少数族裔和穷人居住区的状况。1993年,在由他编辑出版的《直面环境种族主义:来自草根的声音》*Robert. D. Bullard, Confront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1993.中,布拉德把对环境种族正义关注的目光扩展到了整个联邦,并延伸到了国际层面。关注的议题更是涵盖了有毒物和废弃物设施的选址、城市中的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农业工人与杀虫剂、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权、可持续发展,以及有毒废弃物和风险技术的出口等等。除运用大量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外,学者们对环境正义的描述性研究也大多秉承了分配正义的致思理路,如多布森就致力于“对构成分配正义的各种要素,如分配正义的主体(分配者和接受者)、分配的内容、分配的原则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并试图在环境可持续的框架内建立起一种多元的环境分配正义体系”。*参见王韬洋《西方环境正义研究述评》,《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1期。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分配在环境正义的研究范式中长期独领风骚的局面。
三、“正义”内涵的扩展与分配范式的超越
应该说,将分配作为理解正义之内涵的思维路向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人们在评判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或优劣时,最容易作为判别依据的往往是该社会所生产的福利或负担是否被公平、公正、合理地进行了分配。但问题是,这种理想的分配正义形式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知道,人们的身份通常是借助被他人承认而被塑造的。当周围的人或身处的社会反馈回来的信息限制、贬低或是轻视了某些个体或群体的形象时,他们就可能受到歪曲,遭受伤害。而如果人们因为肤色、性别、经济地位或是身份特征而不被社会认可和尊重,在此情境下,又如何做到分配上的公平、公正?如果不被社会认同,又何以确保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因为不被社会承认,就意味着一些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弱势者,这种弱势地位会大大限制甚至阻碍他们在社会分配善物和恶物时,有足够的发言权和决策机会。由此,必然导致分配正义的落空。另外,如果社会在完成了分配后,并没有促进人们内在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相反却大大削弱了这种能力,那么,我们又何以判断这种分配是“正义”的和“好”的?有鉴于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正义归约和还原为只是分配上的问题,或许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Iris Mariz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分配正义尽管是正义论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维度,但仅从这一角度入手并不足以把握“正义”的全部内涵,正义实际上有着更为宽泛的意义和指向。
事实上,很多学者正是在对传统正义论的反思和解构中,看到了分配范式的缺陷和不足,并开始了多视角拓展正义内涵的尝试。其中,被广泛热议的首推“承认正义”。承认作为“对群体身份及其差异的一种肯定”,*Ryan Holifield,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Risk Assessment: Negotiating and Translation Health Risk at a Superfund Site in Indian Count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102, no.3(March 2012), pp.591~613.在社会正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他人的承认不仅仅是一种起码的礼貌,更是“一种重要的人类需求”。*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6.而不承认或是错误的承认不但会给他人带来心理上的伤害,而且会造成社会压制。这种压制“会将他人的身份置于错误、扭曲甚至被剥夺的境地”。*Fraser Nancy,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Grethe B. Peterson(eds. ), The Tanner Lectures in Human Value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8, p.7.所以,在存在社会群体差异和一些群体被赋予特权而另一些群体被压制的地方,社会正义首先需要追问的并不是“分配的最好模式是什么”或“什么是最好的分配”,而应该是“哪些因素会导致不公正的分配”。*Iris Mariz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在“权力作为一种干预机制会决定承认政治的方向和范围”*Ipshita Basu,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Re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Trib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dia’s Jharkhan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43, no.6,2012, pp.1291~1312.的社会现实中,不难想象这样的情境:一些人享有特权,另一些人的尊严和价值却得不到承认。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在分配产品时,又如何保障这些人的利益,实现真正的公平?事实上,某些群体被有意或无意地“不承认”或“不识别”恰恰是分配不公产生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美国,少数族裔就常常因为其种族身份而被歧视。他们甚至被看成社会的“垃圾”,成为有毒废弃物侵害的对象。可见,不公正问题和分配上的不正义往往与人们的尊严和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有效认同有很大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不承认或错误地承认导致的分配不正义属于一种“文化和制度上的非正义”。*Fraser Nancy,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Grethe B. Peterson (eds. ), The Tanner Lectures in Human Value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8, p.7.而如果分配上的差异是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过程导致的产物,对正义的考量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需要考察导致不平等分配产生的“幕后真凶”,而不应也不能满足于只是构建一种理想的分配模式。
能力正义也是理解正义内涵的又一重要维度,它要求社会制度的安排应致力于让人们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Peri Roberts, “Nussbaum’s political liberalism: justice and the capability thresho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40, no.7,2013, pp.613~623.但正如前文所述,当人们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对其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务的决策当中时,势必会造成社会的福利或是负担不能得到公正分配。这种后果又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能力,特别是内在潜能的充分发挥,从而导致能力上的不正义。例如,未经原住民同意就单方面做出禁止其捕鱼或打猎的规定,会影响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损害其“情绪健康方面的能力”。*Scott Leckie, Ezekiel Simperingham, and Jordan Bakker, Climate Change and Displacement Reader,London: Routledge, 2012, p.186.所以,必须重视对能力正义的研究。在这方面,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见解。斯朗斯伯格认为能力正义是“分析并理解人们特定需要”*David Schlosberg,“Climate Justice and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for Adaptation Policy”,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6, no.4,2012, pp.445~461.的有效方法。森和努斯鲍姆指出,在衡量和判断社会是否实现了正义时,不能只靠分配正义,而应同时关注商品和财富的分配如何影响到人们的福祉和功能的发挥。概言之,衡量社会正义与否,不单要看商品的分配是否合理公正,还要看被分配的商品是否转化成了个人能力的最大限度发挥。这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正义不能只重视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还应致力于使正义的受众的内在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以使其获得所需要的“将对物的占有转化为幸福生活”的各种能力。因此,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努力将生产的物品转化为公民能力的最大限度发挥,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让人们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努力使个人获得实现其目标的机会,那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增加人们占有的商品数量,而是要努力将商品转化为人们实现其目标的能力。”*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74.可以说,能力正义是对“过分关注财富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应对和纠偏”。*Jerome Ballet, etc.,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85. no.1 ,2013, pp. 28~34.
和承认正义和能力正义一样,参与正义也是衡量社会正义的又一重要指示器。参与正义其实就是程序上的正义,也即“决策制定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公正、公开”。*Kimberly R. Marion Suiseeya, Susan Caplow, “In pursuit of procedural justice: Lessons from an analysis of 56 forest carbon project desig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23, no.7, 2013, pp.968~979.参与正义要求可能被决策影响到的人拥有“知情同意权”,有权对和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参与正义意味着所有可能被未来政策影响到的人都有权利参与到对决策的制定当中,而不应被排除在外。因为严肃对待公共生活中的差异的重要途径就是在公共行为的情境中增加人们参与的机会。而当有平等的权利决定自身行为时,当从事公共活动被看作个人自我发展的必要状态之一时,人们就必须拥有“决定这种公共活动的参与权”。*Gould Carol, “Diversity and Democracy: Representing Differences”, in Seyla Benhabid (eds. ),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81.参与正义能否实现,关系到分配正义的实效性,而后者的失效也往往是由于出现了“程序上的非正义”——人们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对其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决策当中来。因此,在考虑分配正义时,必须把对参与正义的考量结合进去。如果说改善分配正义的原则和实践,即社会的利益和负担非常重要,那么,改进参与正义的原则和实践——“在社会的决策制定中个人拥有自我决定的平等权利也同等重要”。*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Environmental Justice: Creating Equality, Reclaiming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4.参与正义说到底,是“社会正义的一个要素或一种状态”。*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
对正义内涵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理解并非是要推翻或否定传统的分配正义研究路向,而是希望通过拓展和延伸正义的维度,赋予理解正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平台。因为现实的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妇女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可持续发展,以及反新自由主义运动本身就反映出人们对正义更为多样化的理解。而当今形形色色的环境正义运动更是对正义理论发展趋势在实践中的最好确证。如非裔美国人的反环境种族主义运动就是对自身尊严、价值长期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一种不满和抗争,而世界各地原住民对土地自治权及其文化独特性的捍卫同样表达了他们对承认正义的重视。同时,区域和全球的各种环境正义斗争也反映了草根们对参与正义的强烈渴望:希望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能够为自己代言”,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被排除在外。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在对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和参与正义的关注中,草根群众同样表达了对能力正义的价值诉求。在他们眼中,一种真正的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在社会能使人们的健康、安全和幸福得到充分保障,内在潜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这些环境实践充分说明:无论区域还是全球层面的环境正义运动,人们对正义的理解都没有拘泥于对分配维度的惟一诉求,而是倾向于将其看成是集分配、承认、能力和参与正义于一体的更为多元化的集合。概言之,现实的环境正义运动不仅关注环境风险的不平等分配问题,同时也关注与这种不平等相关的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缺乏承认的问题,被压迫族群在环境决策中缺乏代表和发言权的问题,以及环境恶化以何种方式削弱了个体和社群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问题。总之,环境好处和坏处的公平分配虽然是环境正义的核心要求,但一个狭窄的分配方式会从根本上“遮蔽环境正义运动多样化的诉求”。*Leire Urkidi, Mariana Walter,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nti-gold mining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Geoforum, vol.42, no.6, 2011, pp. 686~695.为此,我们应该提供更为宽泛、多样化和实用化的对正义概念的理解。必须注意到,“分配范式并非正义理论,尤其是正义实践中的惟一尺度。分配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也总是和承认、政治参与和能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David Schlosberg,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5.
遗憾的是,尽管环境正义实践处处彰显出人们对正义的多向度追求,但学界很长时间以来并未将对正义多视角的解读运用到对环境正义的研究当中。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才有了转变:承认正义方面,学者们认为,在考虑分配正义时,必须将承认正义考虑进去。因为承认正义会影响甚至决定分配正义的过程和结果。有学者指出:
承认缺乏是分配不公的基础。如果某个群体面临着来自文化贬低、政治压制和结构层面的多重障碍,那么决策过程中的真正参与是不可能的。*Beatriz Bustos, etc., Coal mining on pastureland in Southern Chile: changing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as guarante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dx.doi.org/10.1016/j.geoforum.2015.12.012.
参与正义方面,学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生态民主”,环境正义的框架应注重民众参与的权利和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性。能力正义方面,学者们认为,与环境有关的决策和行为应努力消除“阻碍人们(尤其是穷人)通过提高生存能力而获得幸福的结构性障碍”,*Vijay Kolinjivadi, etc., “Capabilities as justice: Analys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through social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118, no.10, 2015, pp.99~113.并建立和增加社区自治的能力空间。因为人们之所以能被政治行动号召并行动起来,除寻求分配上的公正外,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个强烈愿望:拥有自我决定权,以保留和延续自己的文化。这些论述表明,学者们对承认正义、能力正义和参与正义的探讨正成为环境正义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之一。
从早期囿于对分配维度的单向考察,到超越分配正义的致思理路,并从承认正义、能力正义和参与正义等多种维度阐释和论证环境正义的内涵,这一对环境正义的研究路径不仅大大拓宽了传统正义论和环境正义之“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表征着正义论领域,尤其是环境正义领域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向,是环境正义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方向。
(责任编辑廖国强)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理论维度研究”阶段性成果(15BZX039)
作者简介:王云霞,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陕西 西安,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