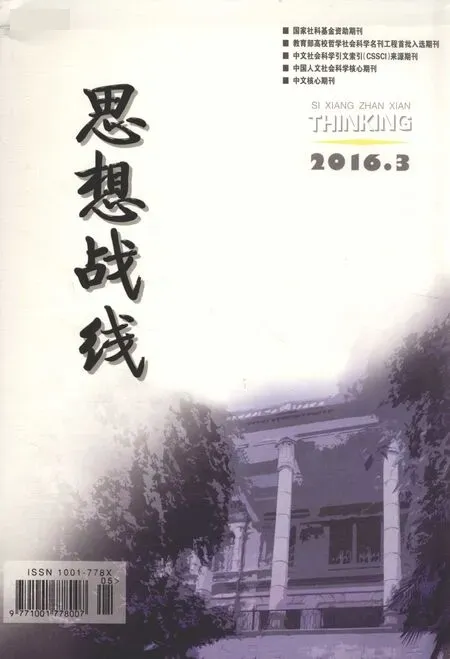论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客观性、主观性与反身性
马腾嶽
论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客观性、主观性与反身性
马腾嶽①
摘要:追求更合理的民族志方法论与知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努力的目标,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于1988年发表《论民志权威》一文,提出既有的各种民族志理论无法摆脱作者个人主观性,主张应倡导一种更为多声与众声喧哗型的新民族志。2014年,北京大学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为文,从客观论立场撰文对克利福德的观点进行批评。然笔者主张,对于当代社会科学而言,对科学的理解不应再框限于实证主义对于客观性的要求,而应包容对不同形态的知识追求。从单声走向多声民族志,展现后现代研究者面对不同形态知识表现出的更大的反身性、包容与谦卑。
关键词:詹姆士·克利福德;蔡华;客观性;主观性;反身性
一、 楔子
2014年6月,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发表了《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以下称《当代》)一文,*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对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论民志权威》(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笔者所采用的版本是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以下称《权威》) 一文中的诸观点提出了批判。
在蔡华教授文章付梓刊印前数日,笔者因参会与蔡华教授相遇于鄂西恩施的湖北民族学院,聆听蔡教授于会议发表该文章的观点。在蔡教授发表后的数天会议期间,我们围绕着他的文章进行了多次人类学理论的讨论与争辩。蔡教授坚持民族志存在客观性,为一“科学活动”;而我则支持克利福德的后现代人类学立场,尊重多声与主观性。最终,我们同意各自把民族志方法论的不同观点,化为文本,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刊载出来。相信这种理论立场上的争议,对于深化与开拓中文民族志研究是有益且重要的。通过学术争论(academic debate)来深化理论是西方学术界的常态,但中国人类学界缺乏不同理论学者对理论进行学术争论的传统,从而无法通过争论对话来开拓与深化理论的差异与特点,并把这些成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志研究与人类学知识的创造上。这个机缘与想法是本文诞生的楔子。
在进行争辩之前,笔者先说明自身的理论观点。在理论态度上,我倾向于支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反对把民族志功能定位在追求实证人类社会的规律,否认把社会视为客观自存事物,反对人类学者对于社会的研究具有绝对客观性的宣称,而应尊重研究过程中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不同主体的不同声音。我支持民族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人类社会多元性的理解,以及理解个别社会与人群如何创造生活中的意义,并在各种意义中生活。当代的民族志研究,不能忽视来自地方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影响。人类学者进行研究时,无法抹拭自身的存在,不同的人类学者具有不同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Henrieta Moore,“Anthropolog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8.而其位置性会作用于研究者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志成果,故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或主观性(subjectivity)均无法消除。同时,古典民族志作品中被研究者被消音,由研究者代替发言的那种“单声”民族志作品,已经不符合当代民族志的潮流。在我看来,在后现代主义下,人类学者把自身的主体性,通过反思与反身性,书写入民族志作品中,而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共同呈现于民族志作品中,不论在研究伦理与书写策略上,都是必要的。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精神是尊重多元与差异。我尊重蔡华教授的理论选择与学术观点,但认为有必要把他对于克利福德批评的观点再作厘清,同时梳理出双方论点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通过这种双重性的争论,把在现代主义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在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主观性,两种不同理论取径的差异性突显出来。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真假良窳之辩,而是厘清脉络、突显不同理论范式的差异,对于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特色进行梳理。
二、蔡华论点
蔡华教授《当代》一文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克利福德在《权威》一文中对于各种不同形态民族志权威观点的批判,反对克利福德所批判的民族志无法脱离作者“主观性 (subjectivity)”的看法;其次是从支持“科学”的立场,来讨论科学与民族志之间的关系;第三,蔡华教授以他纳人研究的田野资料反证克利福德观点的缪误,说明他支持“客观地观察异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并且忠实地再现之乃一项可为的事业。……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而且它是支撑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之信念。
蔡华教授与克利福德的理论取径是对立的。基于对社会科学客观性信念的坚持,蔡华教授对于克利福德《权威》的批评,特别集中于其主张人类学研究无法跳脱主观性的观点。蔡华教授分析克利福德对于主观性的看法为:
人皆具有主观性,民族志者或信息人都是人,所以他必然为主观性所羁绊*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克氏的这篇论文旗帜鲜明:面对他性,人类学家可能做的不是客观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它,而是歪曲它。*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对此,蔡华教授回应:
倘若事情果真如此,对人类学而言,准确地说,是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这无异于末世降临,而且是一个永远无法救赎的末世。*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为了反证克利福德《权威》对于主观性的关注,蔡华教授提出:
作为异文化的他性可能被认知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论证认知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确定性。具体而言,民族志者是否可以排除认识活动中的主观性?是否可能保持政治上、道德上和价值观上的中立(或者说,纯粹的观察者是否可能)。*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当然,作为克利福德《权威》的批判者,蔡华教授对于排除主观性的可能性所持立场是正面的。在文中,蔡华教授以他自己1988~1989年在云南泸沽湖的“纳人”研究为例,以数页的文字篇幅回顾他个人的田野调查,论证“客观的观察和忠实的描写异文化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使命”。*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完成对民族志客观性的肯定分析后,蔡华教授指责《权威》的主观论:
克氏……论证,人类学家(更准确地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面临三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绝症:任何话语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在中性的政治立场,个体无不处于主观性的绝对统治之下。……被克氏宣布破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蔡华教授批判克利福德的三种绝症,在反复审阅《权威》与《当代》两份文本后,笔者追问,为何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包含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观性,但主观性对民族志并非是一种致命的影响,而是一种几乎必然存在的性质,不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的主观性,都构成民族志重要的成分。而在蔡华教授的观点中,主观性若不能克服,则是与生俱来的绝症与末世降临。为何克利福德在指出主观性不可避免后,非但不丧失民族志的价值,并借由把民族志视为是一种“多声作业”(polyphonic works)的新形态,以此来说明民族志并非是“对‘他者’真实的一种经验的或是诠释(the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circumscribed ‘other’reality)”,*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而是一种至少由“两者(作者与报导人)共同的建构性协商(but rather as a constructive negotiation involving at least two)”。*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然而,蔡华教授却以自己的田野调查报告为例证,*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指出“(克氏)‘以没有中性的话语’这一全称判断为由,以论证民族志书写之不可能性,似是而非,是一个伪命题”,*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从维护民族志客观性的可能性上否定克利福德的观点。
蔡华教授对克利福德的批评,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中现代与后现代、客观与主观论两种不同的范式与思维间的差异。笔者认为,从蔡华教授对克利福德的批评中,可以分析出克利福德与蔡华教授双方在四个方面存在根本差异:(1)民族志是否具有客观性;(2)主观性是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品质;(3)社会科学反思层次不同;(4)“科学的”的定义见解不同。分析如下。
三、詹姆士·克利福德与其研究
在回应蔡华教授之前,笔者首先对詹姆士·克利福德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克利福德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文化批评与文化人类学。他的作品,特别是关于人类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引起人类学与民族学界极大的重视与争议,并随即扩散到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成为后现代人类学发展中,批判实证主义重要的声音。*Jocelyn Linnekin,“Review”,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2004,vol.60,no.4,p.566.其中,1986年与马库斯(George E. Marcus)合编的《写文化》(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以及1988年独著的《文化的矛盾》(ThePredicamentofCulture:Twentieth-CenturyEthnography,Literature,andArt)*James Clifford,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两本书,引起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本书基本上延续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0年出版的《文化的解释》(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一书中,反对人类学的操作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理论脉络。在《写文化》中,克利福德进一步推动民族志脱离实证主义,主张民族志不应仅是对于他者的单向书写,而“任何对于他者的书写同时也是对于自我的创造 (peosis)”,*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23~24.强调民族志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反映的仅是“部分的真理 (partial truths)”,*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26.而文化话语的分析不再可能只是一个“‘有经验’观察者 (‘experienced’observer) ”对于风俗的描述与诠释。*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14.民族志经验与参与观察概念(participant-observation idea)被视为是有问题的,*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14.在对田野工作的描述中,研究者的反思取代了客观性的经验描述,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形式。最终,克利福德大胆地说明他的意图,就是要“移除(dislodge)某些人与群体自认为可以把握再现他者的基础”。*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22.
两年之后的1988年,克利福德单独出版《文化的矛盾》(Thepredicamentofculture)一书,这本书的第一章《权威》中克利福德针对1920年以来的四种形态民族志与其宣称具有的权威(authority)进行了批判,包括经验式(experiential)、诠释式(interpretive)、双声对话式( dialogical)与多声对话式( polyphonic)。克利福德分析了这四种形式的民族志各自的发展、弱点、重要性、对于其后民族志的影响,并对这四种形式的民族志所宣称的权威逐一提出批判和弥补修整的建议,还对20世纪各种民族志权威的形成与缺点进行了梳理。*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这其中,克利福德特别对民族志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诠释(interpretation)所依赖的研究者田野经验(experience)能力提出质疑,指出把个人的田野经验转译成民族志文本时,有着许多作者无法控制的“多重主观性与政治限制(multiple subjectivities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面对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困境,克利福德主张民族志事实上是“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包含了作者与报导人的声音,民族志知识主要来自于报导人,当代民族志应打破传统的单一作者(single author)的理念,给予民族志合作者作者的地位,*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同时,他也分析了这种“多作者乌托邦 (Utopia of plural authorship) ”目前尚不可实现的原因。*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根据笔者从克利福德《写文化》和《权威》的文本中所摘出的重点,可以清楚地理解克利福德的理论基础是相当“后现代”的,他反对把人类的文化与社会视为是自为客观事物,同时也主张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作者单方面的作为,而是与报导人间双向的、互为主体的结果。民族志研究无法摆脱作者与报导人之间多重主观性与各种政治限制下的权力关系,反思因而是研究过程与结果中必要的成分。而面对民族志研究中无可避免的权力不对等,克利福德提出“乌托邦”解决之道是,把研究对象报导人也变成作者,以包纳不同的声音,来解决多重主体性与单一作者可能产生的问题。
四、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对客观性的肯定与反对主观性的无法避免,是蔡华教授批评克利福德的主要观点。克利福德在《权威》一文中指出民族志存在主观性,主要的目的在于承认民族志作者无法规避主观性,更无法逃脱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限制,面对主观性解决的方法不是强制民族志作者返回到客观性的追求上,而是扩大民族志声音的来源,让作者与被研究者的不同声音共同出现于民族志作品中,让各种不同的主观性同时体现在作品里,借此免于作者单一主观性对于作品的操作,以及缓冲平衡各种可能的政治限制。然而,细观蔡华教授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在《当代》中选择了与克利福德完全相反的道路,而有着强烈的科学主义与客观主义主张。蔡教授在《当代》的观点,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诠释学、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欲超脱实证主义与功能论限制的后现代人类学发展路线存在对立性的差异。笔者认为,蔡教授《当代》对于克利福德的批评,出发点乃基于一种“拨乱反正”的态度,维护民族志作为一种客观科学工作的信念。在论证策略上,蔡教授以自己的纳人研究为例,认为受过良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可以避免并排除主观性的影响。
无可否认,西方自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世纪法国学者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采取了极端经验论的立场。*黄光国:《从科学哲学的演变论学术创造力》,载《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台北:松慧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页。实证主义奠定了现代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基调,也吸引了诸如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等早期社会科学学者的注意,并依此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最初的方法论,*参见[法]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对现代人类学奠基者马凌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学的主要范式。在此脉络下,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所谓科学常被等同于自然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我认为,在《当代》一文中,蔡华教授在知识与方法论上对于客观性的坚持与看法,并未能跳脱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社会学客观性的规范。蔡教授主张作为科学事业的民族志,应:
客观地观察异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并且忠实地再现之乃一项可为的事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整个社会科学活动并非徒劳。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他也指出:
关于土著文化的细节应当怎样解释,民族志者没有发言权。后者的使命是学习和记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最终分析该社会的运作机制。……当民族志工作旨在认识一种民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拓展知识空间(而不是要改造社会)之目的时,民族志者应当且可能立于完全中立的学术立场(含政治立场)。*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与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要求“社会科学从主观意识阶段迈向客观实际阶段”*[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3页。与在“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6页。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看法是一致的。就这些关于客观性的观点而言,笔者的看法与蔡华教授相差甚大,申论如下。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自然之物,独立客观存在,是经验可以客观观察之对象。从迪尔凯姆发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之后,100多年来对于“客观性”的追求,如紧箍咒般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指导规则。笔者认为,迪尔凯姆所谓的客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强调“首先与根本是要‘把社会事实当成事物来看’(the first and most basic rule is to consider social facts as things)”。*Emile Durkheim,The rule of sociological method,W.D.Halls Translated,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2,p.60。单引号部分为原文。其次则是“研究态度的客观性”,迪尔凯姆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者应“避免个人主观感觉的材料趋于主观性的危险……,社会现象如果能排除个人主观的感受,就能客观地反映出来,排除越彻底,反映也就越客观”。*[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36页。第三则是“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包括“因果关系”与“共变法”等研究规则的确认。*[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02~115页。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曾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真理,而这三种客观性的提出,更被奉为社会科学的圭臬。由笔者从蔡华教授《当代》一文中梳理出的原文“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的客观性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蔡华教授对于科学的民族志的看法,并未跳脱迪尔凯姆的客观性三种原则。
即便迪尔凯姆的理论与准则曾一度被奉为社会科学的真理,笔者认为,这个真理也正在后现代的潮流中被冲刷而逐渐崩坏。迪尔凯姆对客观性要求“把社会事实当成事物”来研究,主要目的是要建立社会科学的科学基础,把社会客体化为如自然之物的独立客观实体,可以中立客观地进行观察分析。但迪尔凯姆使用“当成”一词,恰恰说明了社会事实自身其实并不是事物,而是为了实证科学的目的被当成是事物。就研究态度的客观性而言,作为社会科学的奠基者,迪尔凯姆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态度上保持客观性,排除主观性,把研究者设想为既参与研究社会又可以超脱于社会之外的神人。针对这一点,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理解,但在迪尔凯姆的时代,他疏于对权力的关照,不理解权力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绵密的影响。事实上,权力关系不仅影响研究者,同时也影响着被研究者,知识与权力故而存在紧密扣合的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迪尔凯姆承袭了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追寻“因果律(causal law)”的观点,但无视人类社会与文化诸现象过于复杂,常不存在对应因果关系的事实。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客观性预设基础的众多根本性缺失,使得在当代基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已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诸多不满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者另起新灶,他们主要对抗的就是实证主义这种强调“客观性”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试图将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宣称的客观性中解放出来,并要求关注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去除客观性的神化。包括福柯(M. Foucault)、萨义德(E. Said)、克利福德等人皆是。就人类学来说,如阿萨德(Talal Asad)、*参见Talal Asad,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London:Ithaca Press,1973。海姆斯(Dell Hymes)、*参见Dell Hymes,Reinventing Anthropology,New York:Pantheon,1972。庐古德(Lila Abu-Lughod)、*参见Lila Abu-Lughod,“Writing Against Culture”,in Richard G.Fox ed.,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1,pp.115~137。斯塔金(George W.Stocking,Jr.)*参见George W.Stocking,Jr.,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等人,他们不仅关注知识/权力结构,更严厉地批判人类学产生的根源──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批判传统民族志知识缺乏对于权力的反思。正是在这个脉络下,诸如福柯详尽地论述了权力与真理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在所有社会都如此……”,*[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23页。最终推导出他的名言“历史,是权力的话语”。*[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62页。在《东方学》中,萨伊德从一个整体性的观点,指出经历过几个世纪的书写,对于西方人而言,东方事实上是一种被西方“东方化”(Orentalized)*[美]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的东方。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美]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东方学因而应被“视为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美]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页。就人类学而言,阿萨德则更直言不讳深刻地批判人类学的发展是肇基于西方与第三世界不平等的权力接触,而最可悲的是,“就当时的人类学而言,人类学无法对殖民体系下的不平等世界提出任何的挑战,即便社会人类学者所研究的社会对象就正处于这样的殖民体系中”。*Talal Asad,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London:Ithaca Press,1973,p.1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脉络下对客观实证论采取批判态度的学者,他们的论证并不是从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方法去推敲客观研究是否存在。相反,他们站在社会科学历史的峰岭上,从整体的面向与高度来思考社会科学的各种危机与可能性,同时强烈地关注笔者前述的“位置性”。打个比喻来说,整体人类学事业如果是一幢大楼,个别的人类学者分别担任砖瓦工、水电工、运送工,每个个体工人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楼不断地增高成长,但是只要这幢大楼是盖在地震带上,它就是一幢危楼,这是根本的结构基础问题。站在一个扭曲的不客观的位置上进行研究,难以实现客观性的结果。
客观性被解构了,如何防止主观性被无限伸张,成为了取代客观性的新神话,从而成为新的课题。要解决这幢知识危楼的问题,首先便在于人类学者个人与科学社群集体性的反思。
五、反身性与反思
笔者对于蔡华教授《当代》一文的第二项批评,是蔡教授忽视了“反思”(reflection)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存在着差异,忽视“反身性”(reflexivity)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从而无法同意克利福德《权威》一文乃是基于对实证主义、权力支配等问题的全面反思后,对传统民族志客观性权威的批判。
反思(reflective)与反身性(reflexive)是当代社会科学常使用的两个概念,皆有反过来思考自己想法的意思,一般的使用者与作者对于这两个词并没有严格的区分,*Mats Alvesson and Kaj Skoldberg,Reflexive methodology: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5.在中文的使用中,也常以反思一词统称两者。*例如王明珂便在《汉藏历史关系的新思考:一个反思性历史研究》中,将reflexivity一词译为反思性,而不使用反身性。 参见王明珂《汉藏历史关系的新思考:一个反思性历史研究》,《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10年第3卷第2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其中的差异,认为“反身性”具有双重(double)的意思,“反身性是指不同层次的事物处于互动状态且彼此影响。而反思则是指特定方法或是特定诠释层次的反思”。*Mats Alvesson and Kaj Skoldberg,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248.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身性可以说是一种更全面的反思。
反身性与客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所有性质的研究都是重要的。*Charlotte Davies,Reflexive Ethnography: a guide to researching selves and others,London:Routledge,1999,p.3.然而,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说,反身性具有不同的面向与层次(level)。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反身性着重于如何与被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如何进行最严格的实验程序,以获得客观的数据,*Charlotte Davies,Reflexive Ethnography: a guide to researching selves and others,London:Routledge,1999,p.7.但社会科学的反身性则不在于此。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已清楚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察者一直是在场的,社会科学家无法如自然科学家一般隐身于观察仪器之后,而必须现身于田野与报导人之前。人类学者的在场,不论是低调的侧身观察,还是积极地参与报导人的各项行动,都会涉入并影响到所欲研究的群体和个人,同时也会被研究的群体和个人所影响。*关于这一点蔡华教授的观点与笔者不同。蔡华教授指出:“即便在田野观察中,人类学家的在场或多或少会有影响,那也无可大忧。”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田野研究中不仅存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还包括相互影响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皆无法被抹拭。人类学者的在场必需被承认、展现与使用,这种反身性的参与和涉入经验,在当代已成为民族志作品的一部分。*Judith Okely,“The self and scientism”,in Judith Okely ed.,Own or Othe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6.反身性已成为人类学者重要的研究基础与过程,研究者与报导人同是人类主体,具有自身的情感、情绪与价值观,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田野经验是研究者与报导人之不同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深度生命互动,没有任何田野经验是可以被复制的。反身性要求研究者时时检视自我,检视自我所处的结构与位置,检视自我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避免各种因素扭曲研究成果。反身性因而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品质,民族志中作者深刻的反思性话语,成为带领读者认识另一文化的重要依据。*Charlotte Davies,Reflexive Ethnography:a guide to researching selves and others,London:Routledge,1999,pp.3~25.在承认反身性的基础上,除了克利福德之外,诸如马库斯与库什曼(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参见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2,vol.11,pp.25~69.罗萨多(Renato Rosaldo )*参见Renato Rosaldo,Culture and truth,Boston:Beacon Press,1989.等人类学者,都已针对所谓客观化的民族志书写,提出深刻的批判。*参见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2,vol.11,pp.25~69;Renato Rosaldo,Culture and Truth: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London:Rout ledge,1993.
在各种反身性活动中,对于研究者“自身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 of the self)”*Amanda Coffey,The ethnographic self: field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London:Sage,1999.的反思,是许多学者格外重视的。一切的研究活动从研究者自身开始,然而研究者并不是机器,而是人类主体,有着许多与生俱来、建构或是被建构的身份位置性,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或族群、社会地位、国籍身份,这些位置性不仅会影响研究者如何看待他的研究对象、如何形塑研究者的研究观点与取径,还会影响被研究者采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提问。例如,在田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男性人类学者基本上难以对女性生理现象的文化描述进行调查,诸如月经、乳癌这些女性生理现象的医疗人类学访谈,大都是由女性人类学者完成。另一方面,许多社会的狩猎活动或是渔业活动,基本上禁止女性参与,相关的研究多由男性学者完成。
而在众多影响人类学研究的位置性因素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可能非政治与权力关系莫属。
人类学的发源始于西方殖民时期的扩张,早期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地知识,而不存在客观中立的问题。弥尔斯(David Mills)指出大英帝国殖民时期人类学者与殖民当局,基本上是共谋(complicity)与共生(symbiosis)的。*David Mills,“British Anthropology at the End of Empi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4-1962”,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2002,vol.6,p.186.人类学者为维护学科发展的资源,强调人类学应独占所有对殖民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适当性。*David Mills,“British Anthropology at the End of Empi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4-1962”,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2002,vol.6,p.186.今日世界已走在去殖民的道路上,然而,各种权力支配关系仍存在于国家之间与国家之内。总的来说,今日人类学仍是一门属于支配者的学科,人类学的研究仍具有方向性,是强国向弱国、核心向边陲、都市向村落、强者向弱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学科。蔡华教授在《当代》中详细列举他本人在云南泸沽湖对纳人的田野调查,说明客观研究与客观知识的存在与可能。但究其根本,笔者要追问这种“客观研究”的基础是否是客观中性的。为何我们从不见住在永宁山区里的纳人来研究首都北京?或是放大一点,为何沿海发达地区的学者来研究西南边疆社会的多,西南边疆社会学者研究沿海发达地区的几希?再放大一点,欧美人类学者到第三世界研究者众多,第三世界又有几位学者能去研究欧美社会?所谓人类学民族志客观知识,事实上存在着核心vs边陲、支配vs被支配的关系,无法规避权力话语,而这正是传统民族志在后现代思潮中最受批判之处。这也是克利福德《权威》一文中要求多声、多作者,扩大民族志声音来源,包纳更多不同声音的原因。
蔡华教授《当代》一文,严格来说是一篇具有反思性的文章,特别以他个人实际的田野研究为例,证明民族志客观研究的可行。《当代》一文的反思性是无疑的,但是这种反思将民族志置于了自然科学主义对客观需求的层次上,而非当代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者对自身的多重反身性,以及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性的经验上。就此而言,我认为蔡华教授对于客观研究的反思,是基于一种实证科学主义客观性的朴素反思。这种以实证主义反思态度生所产出的民族志作品,固然对于我们理解纳人亲属有所帮助,但它所追求的客观性,事实上仍无法脱离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与意志。
就研究方法的逻辑性而言,蔡教授说“关于土著文化的细节应当怎样解释,民族志者没有发言权”,*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但又提出民族志者“使命是学习和记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最终分析该社会的运作机制”。*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从叙述的逻辑与经验事实来看,两段文字明显有矛盾之处;前者说明民族志者对于文化解释没有发言权,故而具有客观性,但是后者所谓的“最终分析”,却仍是由民族志者完成。即便在同一田野地,不同报导人对自身文化细节的解释与描述也可能有多种差异。选择哪个版本、如何从数百小时的访谈中截选需要的材料,以及最终的分析角度,都仍掌握在民族志者手中。民族志者作为最终的作者,负责田野材料的筛选、分析,选择合适对话的理论,并形成最终的民族志文本,一切都基于民族志工作者的经验选择,民族志无法逃离作者主观性的选择,乃不辩自明之事。
六、结论:何谓科学与民族志出路
对科学 (science)的忠诚与坚持是蔡华教授《当代》的立论基点,这点是笔者十分尊敬与认可的。克利福德《权威》一文并未否认科学事业的重要性,甚至就民族志的科学权威而言,克利福德也未否定科学权威的重要性,而是深究各种形态民族志所宣称具有之权威的缺失。就事实而言,一个民族志作品的权威与否,也并非仅靠作者的自我宣称便能得到认可。反之,一部好的作品,就算作者默默无闻、作品低调出版,假以时日,科学社群也可能发现它的重要性,赋予科学性的权威。克利福德《权威》所争议的,是哪一种形态民族志,其权威更为适宜。
在此,在争论客观的vs主观的、单声的vs 多声的,争论哪种民族志更具有科学的权威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先回归什么是“科学”这一议题。科学一词原本是古希腊文,本意就是“知识”(knowledge)。*Udith Okely,“Part II The debate”,in Tim Ingold ed.,Key debates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Routledge,1996,p.36.关于当代知识的内涵,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与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都指出,在当代的科学中,对于知识的旨趣与理解表现在三种知识论与方法论上,分别是:(1)经验──分析取径;(2)历史──诠释取径;(3) 批判取径。*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Beacon Press,1971;Richard Bernstein,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hiladelphia:Univ.of Pennsylvania Press,1978,p.235.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看法,所谓“科学”将不再坚持孔德与迪尔凯姆以来科学实证主义者所要求的以“客观”为惟一准则,而将可以对不同知识形态给予包容。
人类学确实有许多知识论、方法论与道德上的困境与争议,但并不是绝症。放弃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知识,可以转而追求更为多元宽广的知识形态。除了克利福德《权威》一文所谓的“多作者”之外,诸如晚近“原住民人类学”(indigenous anthropology)、“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的提出,就是希望原住民与女性人类学者,从自身的位置出发,提供不同的、多元的知识与声音。另外,今日举世人类学发展已经走向实践方向,应用与公共人类学正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参见马腾嶽《英美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之历史、争议与发展》,《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中立”是一个相对概念,一个文明的、健康的学术环境,不是设定中立的标准(谁的中立才是中立?),而是应当保障所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声音都可以得到尊重,彼此可以争议、对话,共同丰富学科的内容,拓展学科深度。
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志理论而言,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科学知识论与方法论,西方社会已经争辩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争议虽尚没有结果,但乐观地说,这个争议的过程已增加了社会科学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可能性。《权威》一文中,克利福德以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比喻单声的、作者支配(authorial control)型的民族志,而以多声的(polyphonist) 的腹语者(ventriloquist)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权威》中克利福德以福楼拜与狄更斯两位作者的文学风格,比喻单声与多声的民族志。笔者转借于此。比喻多声的、众声喧哗型的民族志。关于民族志的合理书写与形式,西方争论甚多,但迄今也没有完成库恩(Thomas Khun)所说的范式移转(paradigm shift),而呈现百花齐放、各家功夫并陈的现象。众声喧哗的民族志或许尚不是主流范式,但是众声喧哗的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发展却已是事实。
我在本文最后回应蔡教授在《当代》中的提问:
作为异文化的他性可能被认知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论证认知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确定性。*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我认为,对于异文化的他性的认识当然是可能的,这是人类主体得以彼此交流交往的前提。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任何对异文化的认识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的认识,无法完整地外推到其他研究者身上。即便两位研究者同时同地进行研究,其成果不必也不会完全相同。我对某文化他性的认识只是众多认识中的一个认识,让不同认识、包括研究者与当地人的认识,得以并同呈显出来,这也是“众声喧哗”。众声喧哗的另一层意义,不是反对认识他者的可能性,而是放弃蔡华教授所谓的“确定性”后,从而接受理解他人过程中,所存在着的各种 “不确定性”。我的理解仅是众多理解中的一个“理解(understanding)”,而不是具有排它性的惟一确定性“解释(explanation)”。
蔡华教授忧心在众声喧哗中民族志丧失科学客观性,我却欣赏众声喧哗里民族志的纷杂与差异。从福楼拜到狄更斯未必是一种“进步”,进步这个词已预设了它自身的价值。但从扬弃单声到接纳欣赏多声,却必然包括着研究者的更大的反身性、包容与谦卑。它宣告人类学者的声音只是构成知识的众多声音的一部分。
放弃单声与对自身作品客观性宣称的权威可能是痛苦的,但只有放弃单声与对自身作品客观性宣称的权威,才能见到不同主体相互对话、多声并陈的缤纷。过往半个世纪,人类学常重复上演自我否定的戏码,新的理论每每尝试否定超越之前的理论,这种自我否定并未让人类学弱化,反而总在浴火重生后飞翔更高。一个缘于殖民主义的学科在去殖民半个世纪后,尤能保存它独特的学术价值,原因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①马腾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大学特聘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