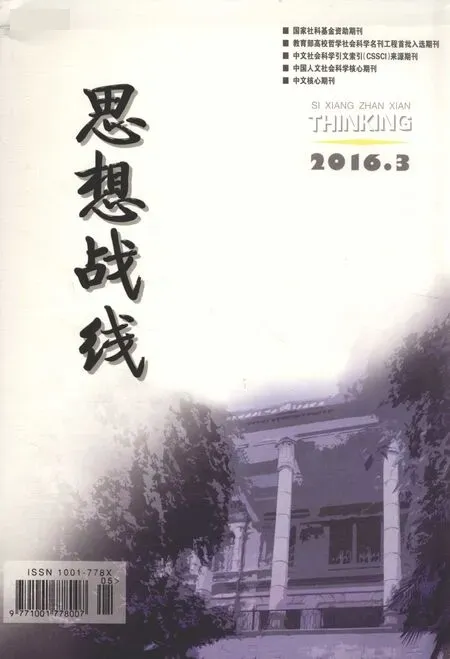冷战后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失败
——以伊拉克“失败国家”建设为例
曹海军
冷战后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失败
——以伊拉克“失败国家”建设为例
曹海军①
摘要:一般而言,国家建构可以分为内生性国家建构和外生性国家建构两种类型,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遵循的是经典的内生性国家建构模式,而冷战后的“失败国家”,大都是在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实施的外生性国家建构模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输出,对处于“后冲突”或“后战争”状态下的“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伊拉克的国家建构,非常典型的体现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范式演变和路径选择。全面总结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国家建构战略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失败国家;国家建构;伊拉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福山“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自由民主一路高奏凯歌。苏联解体,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却陷入了“超级大国的迷思”。一方面,在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乘胜追击”,大力输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战略。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纽约世贸大厦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陆续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国际社会扮演了单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的解放者形象。事与愿违的是,接受以美国主导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不但没有因祸得福,摆脱奴役与落后的命运,反倒陷入了“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或“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的悲惨境地。伊拉克等国不但没有成为美国推销“新自由主义”和输出“选举式民主”的福地,反倒深陷泥潭,成为了“帝国的墓地”和典型的“失败国家”。
冷战结束后,由于种族、族群和民族冲突等原因,南欧、北非、中东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内战不断的状态,这类国家被称之为“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为恢复和平,实现民族和解和国家重建,进入“后战争”或“后冲突”时代,国际行为者纷纷构筑各种“合法性”形式,干预或参与“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败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与和平建构(peace building)的三重变奏。国家建构特指国家强力机关和政府机构的建立,民族建构强调主权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和族群建构,而和平建构则是“后冲突时代”“国际或国际行为者为实现和平制度化而采取的行动,可以理解为无武装冲突即消极和平的状态,以及作为积极和平组成部分的少量的参与性政治”。*曹海军:《国家构建理论:范式转移与模式构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和平建构常常体现为各类平叛活动(counter-insurgency),以此来征服当地居民的人心。以“失败国家”的伊拉克为例,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存在着既相互支撑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国家建构需要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现民族融合,而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民族冲突则因复兴社会党政权瓦解而雪上加霜。和平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国家建构的权力中心化过程需要消解地方军阀的势力,而和平建构则需要政治上吸纳地方军阀的广泛参与,从而可能弱化权力的中心化。和平建构与民族建构的关系则涉及到原有族群和宗教势力的冲突,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就是典型。从宽泛的定义来看,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和平建构整体上构成了“后冲突时代”“失败国家”国家建构的完整战略架构和意识形态体系。
本文以伊拉克为例,阐述和检讨美国国家建构战略输出的失败与教训,希冀能为处于“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状态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提供某种启示。国家失败或者变得脆弱,一般来说是由于领导集团的寻租行为导致了国家的“空心化”(hollows out),进而丧失了提供维持基本社会秩序所需的诸如安全、国防等公共物品的能力,特别是韦伯式的合法垄断暴力的能力遇到了其他利益集团的有力竞争。就伊拉克的情形而论,原本在复兴社会党领导下相对强势的国家在美国的武力干涉下变成了“失败国家”,中央政府瞬间崩溃,丧失了合法的统治权威,国家建构也就顺势成为了国际共同体和外部行为者当仁不让的道义责任。2003年,美国以区域安全、侵犯人权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构成潜在的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自此,美国便面临着重建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伊拉克国家的世纪难题。
与其他“失败国家”国家建构的例子不同,伊拉克的国家建构几乎完全是美国一手操办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战略输出政策的直接实践后果。以2006年为分水岭,2003年到2006年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战略输出的实践,2006年末到2011年美军撤军后可以视为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战略输出的修正和调整。
一、冷战前后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演变
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是伴随着一系列军事占领、恢复秩序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战略行动而来的,而由此建立的新政权则是为了替代失败、崩溃或被颠覆的旧政权。与西方经典的内生性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不同,这类由外部力量武装干预的国家建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就由来已久。通过对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百余年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作为理论与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冷战结束作为分界点,分为冷战结束前期美国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理论与实践;冷战结束后期“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理论与实践;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反思与调整。
冷战结束前期美国国家建构的输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适逢美国首次参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国家建构。直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国家建构输出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历史传统,在理论上,强调要建立政治上稳定且忠于美国的“二等”国家,并将其作为对外投资和建立军事基地的前提条件。当忠于美国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美国政府往往会基于现实政治的权衡而容忍独裁政府的存在,甚至支持独裁政府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工具性目标和政治性修辞,而且鲜有成功实现的案例。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和经济利益至上是这一时期美国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建立能够得到当地人民支持的合法、稳定而有效的政府则不是美国的根本目标。冷战期间,美国的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达到了巅峰,输出国家范围从加勒比地区扩大到欧洲、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特别是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支持亲美的“反共政权”,此时的民主自由仅仅是在不与美国利益相冲突时,才受到支持的次级目标。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是美国自诩少见的国家建构输出的成功例子。
现实主义国家建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盛行,主要是由于美国特定的地缘性国家利益,而改进输出目标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并不是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核心目标,保障美国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才是根本目的。现实主义政治假定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建构目标只是建立和维系国际上业已秩序化的等级或权威的手段而已。在整个20世纪,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帝国,俨然一名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世界警察”,势力范围波及加勒比地区,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借此也广泛操纵相关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贸易政策。显然,这一现实主义政治思维并没有预设任何直接的合法性理论,除了世界警察的角色之外,这一时期的美国并没有考虑合法性的问题。即使是最具自由理想主义色彩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清楚,教会墨西哥人和其他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人民“选举一个好人”,实际上是为了遵循美国的政治偏好。*参见Knock, T.J.,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7.
冷战结束前期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主要困局在于,忠诚于美国的国家未必是得人心的合法国家,忠诚与合法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西德和日本或许是忠诚与合法相和谐的例外,而许多例子是忠诚于美国和失去国内民心并存的情况,后者往往在美国的庇护下推行军事独裁政体。针对这种悖论,一般情况下,美国是以对权威主义和独裁政权的支持来换取政治上的忠诚和依附。吉米·卡特总统率先对这一支持独裁者的国家建构输出原则提出了质疑,转而将改进人权状况和推动民主输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卡特认为,支持独裁者不仅削弱了美国自身的民主价值,而且民众对于独裁的不满势必会转变为持续的反美情绪,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参见Smith, T,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9.
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建构的战略输出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制约,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相互制衡而干预“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的内政外交,常常造成两败俱伤的政治僵局。为了培植忠于自己的盟友国家,美国不惜扶持独裁政府,而将其标榜的自由民主付诸东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新型国家建构输出战略呼之欲出。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新型国家建构战略输出的影子。在此所谓“历史终结”的时刻,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战略再次以崭新的形式复活,民主政府是惟一的合法政府形式,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繁荣惟一有效的运行体制,即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理论。至此,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开启了由现实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范式转变。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理论的基本信条是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推动民主输出,将合法性建构作为国家建构的前提,民主与合法性互为表里、相互支撑。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理论认为:第一,民主通过促进公共领域内公民之间的平等协商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具体措施包括推动多党竞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第二,民主通过促进政府对公民要求和预期的回应性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尽管民主并非尽善尽美,但比较而言,自由派认为民主较之其他政体形式更能回应普通民众的呼声,从而更有效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第三,较之其他政体形式,民主在程序的公平性上确立了国家的合法性。
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奉行“最小国家”的理念,国家职能仅限于规制市场失灵和支持市场调节机制,仅为公民提供剩余型福利,主张福利责任转变为工作责任。主张通过私有部门和自由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信条集中体现在升级版的“华盛顿共识”上。在公共行政领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理论来源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主张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运用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上,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服务外包”、PPP等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改革举措和治道变革。总之,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理论来看,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所主张的竞争性市场、有限规制、以及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职能范围,扩大了私有财产和私人权利的活动范围,这从长期来说是有利于保护和维系民主政体的。
而冷战后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原则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真理,从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干预到占领伊拉克,到处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如其倡导者所坚信的那样,是一种普世性的政治哲学。虽然不能如亨廷顿一般简单地将这一特殊性规约为“文明间的冲突”,但显然在宗教信仰多元的国家或地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始终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方面,由于传统和习俗等诸多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原因,对合法性的理解难以形成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原则与当地流行的制度实践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也时常发生冲突。其次,民主政治势必要改变所在社会的政治权力均衡,以及重新调整旧政权下的既得利益关系。“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的前身大都是专制或独裁政体,依系于原有政体的特权集团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坐视资源和利益向多数民众的转移。因此,新型的国家建构在理论上就存在着资源分配产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索马里等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这就导致了民主化和国家性(stateness)之间的不和谐,民主化如果无法建立在有效的国家建构之上,就会进一步恶化原有的族际冲突、社会分裂和政治不信任。再次,经济改革也常常需要打破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藩篱,产生民主化对经济利益类似的分配效应。最后,从现实角度考虑,新自由主义未必能够保证“失败国家”忠于美国和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幻想模仿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建构模式,对冷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法炮制,而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向左转”的例子,是新自由主义输出遇到的巨大挫败,对于“失败国家”来说则更是犹如噩梦来袭。
二、冷战后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在伊拉克的失败
罔顾历史文化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粗糙而缺乏系统规划的国家建构输出注定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在实践上的失败命运。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就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挽救伊拉克“失败国家”的灵丹妙药,也成为了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典型案例。
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建立在五项误导性的认识之上:第一,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源自新自由主义的乐观信条,坚信新自由主义的正统原则具有普世性,认为所有伊拉克人都是或将势必成为民主和自由的忠诚信徒。据此,美国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被专制政权压迫的民众的解放者,前副总统切尼甚至宣称,“我真的认为,我们会作为解放者而受到夹道欢迎”。*参见Packer, G.,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143.第二,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制定者们过分相信了萨达姆掌权期间流亡海外人士的看法。这些人士长期在西方社会生活和工作,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多数伊拉克人民的欢迎,因此,占领伊拉克是合法的。第三,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中并没有预料到伊拉克基础设施的破败程度如此严重。自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石油资源不但没有缓解恶劣的经济环境,反而衍变成为“资源诅咒”,导致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而美国政府却乐观地估计了伊拉克重建的经济基础,想当然地认为伊拉克丰厚的石油资源足以解决基础设施的恢复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第四,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并没有预料到,逊尼派政府倒台后宗教派系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第五,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没有预料到,伊拉克武装力量和警察力量已经羸弱到无法维持战后稳定的程度。
上述误导性的认识从一开始就预示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在伊拉克失败的悲剧。美英军队占领伊拉克后,军方负责伊拉克整体上的安保工作,而由退休美军将领加纳领导伊拉克的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ORHA),负责管理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服务等。2003年4月,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小组抵达巴格达,但却仅有25 000美元充作重建伊拉克政府部门的预算资金*参见Packer, G.,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143.。2003年4月28日,第一次以保护人权、创制自由宪法的会议便遭到了抵制,一个部落首领站起来抱怨道:“我们没有饮用水,没有电,没有安全,而你却在讨论什么宪法?”另外一位首领则质问“谁在负责我们的政治生活”?*参见Packer, G.,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144.面对纷至沓来的棘手问题,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小组很快被以布雷默(Bremer)为首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CPA)所取代。布雷默很快宣布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是伊拉克的最高当局,拥有主权地位,筹备建立临时过渡政府。
布雷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到任不久就着手推动新宪法的创制、民主选举和经济改革。临时政府建立后,临时管理当局于2004年6月解散,形式上将主权完整归还给伊拉克。2005年1月,大选产生了新宪法,5月伊拉克过渡政府正式成立。经过数月的磋商,成立了以马利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初步完成了民主的转型任务。在这一民主进程中,政治权力的均衡被严重破坏,伊拉克的传统统治势力是少数的逊尼派,这次转到了多数的什叶派,为此,少数的逊尼派联合抵制投票。
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临时管理当局着手对先前国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实施大规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大力推动对外投资和贸易开放。*参见Foote, C., Block, W., Crane, K., and Gray, S., “Economic Policy and Prospects in Iraq”,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8, no.3 (2004), pp.47~70.自由化的政策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急剧震荡和混乱。少数的逊尼派所在地区没有石油资源,战前依赖政治特权成为最富裕的社会群体。临时管理当局实施的经济改革动摇了逊尼派权力和财富的根基,偏向了什叶派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显然,多数的什叶派势必在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削弱少数的逊尼派的实力。布雷默将经济改革的努力作为他在伊拉克的最大成就,而事实上远远没有达到对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预期。截止2006年底,大规模轰炸什叶派阿斯卡里清真寺之后,宗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为内战。2007年,联军士兵伤亡上升到了战争的最高水平。伊拉克的军人和平民伤亡急剧上升,达到每月数百人。*参见Myerson, R.B.,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ading Bremer and the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p.112.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在政治上彻底失败,“民主优先”的战略不得不让位于“安全优先”的战略,战略调整势在必行。
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在经济上的破产则产生了更为深远且更具破坏性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乃至后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基础。“华盛顿共识”鼓吹私有化、解除市场规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看来,自由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优越于国家,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应该受到限制,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提供市场有效运转所必需的规则和制度。处于后冲突时代的“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为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场所。与之相呼应,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提供金融支持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挂钩。在美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扶持下,新型的国家建构根据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基本价值和信条建立起来了。而事实上,在缺乏政治稳定和法治环境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根本无法有效运转,更谈不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了。
三、“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伊拉克国家建构的新探索
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优先的国家建构输出的失败,撬动了“后”新自由主义(post neo-liberalism)时代的开启,东道主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建立在人民广泛支持基础上的安全国家成为了新的战略重心,国家建构的价值排序进行了调整和重组。
第一,和平建设是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前提,因此,安全无疑成为了这一轮国家建构战略调整的首要目标。进一步说,实现安全目标还需要在维和、法律实施以及安全部门改革等几个方面入手。第二,人道主义救援。这是仅次于安全的目标,启动难民回归、预防流行疫情、防止饥荒以及提供必要的避难所。第三,治理。作为国家建构的目标,治理更强调恢复基本的公共秩序和公共行政常态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第四,经济稳定化。经济的宏观稳定化表现为通货稳定,提供法律和规制框架,以利于国际和国内贸易的顺利展开。第五,民主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战略不同,民主化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并不是居于优位的目标。无论是政党建设、民主选举,还是言论自由等政治参与,都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有序推进。第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既是国家建构的手段,也是国家建构的目标,没有发展,其他目标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减贫以及改进基础设施,对于“后冲突时代”国家的国家建构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具体论述可参见Dobbins, J., et al., The Beginner’s Guide to Nation-Building,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7,p.xxiii.
2007年,小布什政府宣布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失败,着手推动新一轮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调整,以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基本安全和公共服务作为新的战略目标。首先,对安全的重视,从打击叛乱分子策略的改变中可见一斑。新策略以减少地面部队和平民伤亡为主要任务,运用“油点”(oil spot)战略,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和服务,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取叛乱信息,进而扩大控制区。这一策略将伊拉克的整体暴力程度降低了80%。*Robinson, L., Tell Me How This Ends: General David Patraeus and the Search for A Way out of Iraq,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p.98.与此同时,美军与伊拉克政府签署2011年撤军协议,以便伊拉克政府能够自主处理安全和服务问题。
这一波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调整,始于叛乱方与反叛乱方之间的权力争夺,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目的都是要争取人民接受其治理或权威的合法性”。*Myerson, R.B.,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ading Bremer and the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简称CFM.这里的关键是要争取“保持中立的中间派”,对他们而言,所谓合法性,就是要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安全。正如CFM所做的申明,“一个无法保护其人民的政府就丧失了统治的权利。合法性一个要素就是提供安全,公民们总是力求与能够保证其安全的集团结盟”。*Myerson, R.B.,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ading Bremer and the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简称CFM.p.16.进一步推论,“一个政府有能力提供安全,纵使没有与西方式民主相联系的自由,在人民看来也足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了,特别是当他们经历了严重的秩序崩溃之后尤为如此”。*Myerson, R.B.,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ading Bremer and the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简称CFM.p.37.
对于“后冲突时代”的国家,就民主而言,秩序显然优位于自由。尽管美国政府意识到了秩序、服务和安全对于“后冲突时代”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并试图修复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的缺陷,但事实上仍然面对着诸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难题与困局。
首先,在当地人民来看,类似于美国甚至是联合国这类的外部行为者,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此前,国际公认的通则是经过多边协商共识,在获得国际授权基础上的外部干预具有一定合法性。这种干预之所以具有一定合法性,乃是充当了“临时托管者”的角色,而托管者可以被当地居民视为一种合法的存在。显然,在外部行为者统治的人民眼中,这种国际合法性未必能够令外部行为者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有经过当地人民的同意,这种外部行为者帮助建立的国家即国家建构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即使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不具有合法性。CFM的文本里面并没有深入到对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的国家“托管者”角色的探讨,更多的是外部行为者和新建国家之间的行动博弈和利益交换。不过,这种利益取舍和交易并不能通过简单地支持地方政府就可以轻易解决。在赋予东道主责任和增加公信力的同时,美国必然会削弱和降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降低民众对其在该国存在和作用的支持。
其次,即使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是充分条件。在经历冲突后的“失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前提是运用强制力建立和施加社会秩序。而这种强制力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自利的激励。对于一个缺乏权威的“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这种自利性激励会将国家建构引向权力滥用,从而导致掠夺型国家,索马里的失败就是明证。一般认为,至少在历史上,民主是最有效的控制国家权力的手段之一。当然,民主需要配合自由、法治、分权制衡以及有限政府等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才能发挥约束国家权力的作用。否则,民主便会沦为“多数的暴政”或“少数的暴政”。因此,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固然重要,而限制统治者对权力的滥用可能更为必要,更值得优先考虑。
最后,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效而合法的国家可能未必是忠诚而可靠的国家。换言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输出战略虽然有助于解决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弊端,但在当地人民心中,营造合法的政府可能并不认可美国的价值观,也未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四、结论
总体而言,冷战后,由美国在经历冲突后的“失败国家”内,推动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是一个失败的范例。在这些国家建构的实验中发现,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但却改变了“后冲突社会”的政治权力平衡,挑战了旧政权的既得利益格局。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不但没有建立有效而合法的国家,相反,却将一个原本相对有效的国家变成了“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
这种对新自由主义的盲目自信,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无法真正解决“后冲突时代”“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症结所在。
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就凭借其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开始恣意扩张,在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推行霸权的同时,罔顾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后发生的抵抗和骚乱开启了权力政治的新时代。美国代表了全球霸权势力,为国际资本代言,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帝国,“新帝国主义”一时甚嚣尘上。这一权力框架强调的是帝国的非正式机制,美国的强制力强化了这一非正式机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尼格里(Antonio Negri)、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及迈克尔·曼等人认为,“新帝国主义”的“新”主要表现为,帝国不是建立在对领土的正式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资本的统治和依附之上。*有关新帝国主义的论述,参见Hardt, M.and Negri, A., Empire,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Harvey, D.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1953年,约翰·贾兰格和罗纳德·罗宾逊在一篇题为《自由贸易的帝国》的论文中指出,与殖民地统治的耀眼的权力比较而言,“非正式的帝国”对于不列颠更为重要。*Gallagher, J.and Robinson, R.“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6, no.1(1953).二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手段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依靠武力实施直接统治,另一方面通过自由贸易等市场力量实施间接统治,两种手段或方式在维系帝国全方位统治和实现多样化利益方面,实际上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一方面,殖民地国家纷纷赢得主权独立,另一方面,美国却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取代英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权力领导者和财富分配者。不过,与英国的直接殖民统治策略不同,伴随着殖民统治在汲取当地资源方面的成本大于收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资本权力却在上升和扩张,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地位,逐渐形成了“核心”和“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却遇到了非正式的等级秩序的主宰,以“市民社会的帝国”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开始崛起。西方国家利用这种市场不平等的非正式机制操纵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了获得外资或者外援,发展中的非西方国家被迫接受歧视性的贸易法规或者接受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条件。这样一来,表面上两个契约方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实际上成为了权力等级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这种霸权地位超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惟一超级大国。至此,美国的帝国意识愈益膨胀,利用非正式等级秩序即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达到统治世界的途径更为便利。与此同时,美国开始着手大规模的国家建构输出,民主政治输出,市场经济输出等等。
而现实的情况则是,以伊拉克为代表的这一轮国家建构的发展轨迹与西欧经典的国家建构典范完全不同,也与战后殖民地国家模仿宗主国的原型进行的国家建构大相径庭。就西欧的经典国家建构范式来说,总体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内生演化模式,而伊拉克等“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的国家建构则是一种国际国家建构(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伴随着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和平建设相互交织,内外力量持续互动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外部驱动型发展模式。外部势力和国际行为者的持续干预对加速、塑造和确定“后冲突”社会国家建构进程起到了主导作用。从具体进程来看,整个国家建构涉及到军事部署、民事能力建构(civilian capacity building)、以及发展援助资金。在这一进程中,外部势力和国际行为者基于外部行为者的策略、目标,通过多层次博弈影响了内部行为者的选择和行为,进而改变了传统国家建构中诸如权威、能力和合法性等核心要素的性质。国际和国内的互动过程将国家建构问题国际化,从而挑战了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传统理论。国家不再是绝对的主权,国际干预成为了新自由主义以和平建设和人道主义援助为名,达到扩张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以及大国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复合性政治后果。国际关系学者探究如何在地方精英之间做出选择,令一个政治派系凌驾于另一个政治派系之上,或者决定社会契约的边界。而比较政治理论则常常无法解释国家建构何时才能巩固或者何时变得脆弱,冲突何以继续下去。国家建构的国际化这一论题引起了对全球政治各个层次互动过程的争论,依次而论,地方动力、利益、文化和社会力量也将纳入到这一复杂框架中去理解。
国际干预与国内回应形成的复杂互动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对国际国家建构体制(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regime)演变的持续反思和重新评估。传统意义上,主导性的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对国内冲突的集体回应形成了一个正统的国际国家建构模式,即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组织的引导和监督下从战争转向和平,当由选举方式产生合法政府后,外部武装力量就会陆续撤军,实现主权的彻底回归。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国就是其中相对成功的案例。不过,这些成功的案例仅仅是少数,而诸如安哥拉、缅甸、索马里、卢旺达等国,要么陷入持续冲突,要么为政党纷争所扰,进入了“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的行列,卢旺达更是充满了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暴力升级行动,伊拉克则出现了上述所有情况。因此,在国际组织干预下成功实现和平建构和民主转型成功的案例遭到了全面性质疑和批判性反思。和平建构的模式远远无法适应新问题和新情况,和平建构、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相互交织,国际和国内互动日趋复杂,国际援助和重建“失败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威、合法性和能力等概念逐一展开反思。
国际国家建构战略的演变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以可持续和平为目标的维和行动,其中美国发动的两伊战争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等武装干预行动和国家建构输出,都引起了学术界对国际国家建构战略的广泛争论。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民主政治,还是包括诸如安全部门改革的能力建设,亦或是着眼于赢得人心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安全保障,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败国家”的重建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药方过于猛烈,导致本就虚弱的国家“虚不受补”,另一方面,单方面的外部干预式的国际国家建构从根本上忽略了作为东道国自身的国家制度能力建设。
(责任编辑张健)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13AMZ005)
作者简介:曹海军,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副教授(天津,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