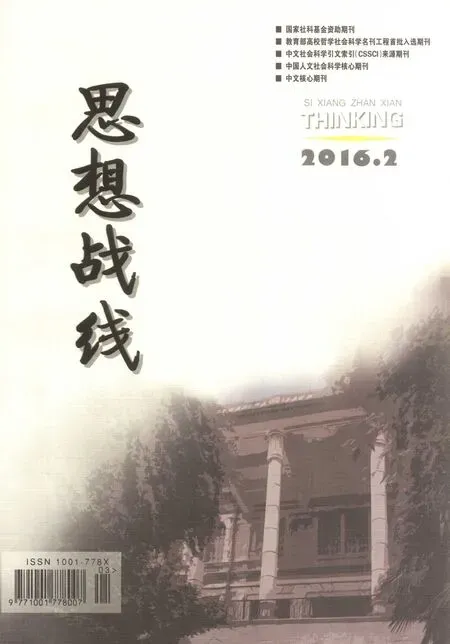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孙保全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孙保全①
摘要: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关键词:王朝国家;民族国家;边疆形态;边疆治理
边疆总是同国家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是边疆存在和界定的基础与前提。作为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边疆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地理空间,也是根据国家治理需要而被构建起来的产物。*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因此,边疆形态的演变,也必然受到国家主体的决定性影响。就国家类型而言,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无疑是个巨大的转型,这对边疆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直接导致了边疆形态的变迁。中国王朝国家的边疆形态是在前主权时代形成的,体现了王朝国家疆域治理的需要。而民族国家的边疆架构,则是在主权体制的框架下搭建起来的,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治理逻辑。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传统的王朝国家边疆逐步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边疆,这既是边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边疆民族国家化的过程。此过程中,中国的边疆形态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并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变。
一、王朝国家的疆域格局与边疆形态
从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自秦的建立至清的灭亡,中国一直处在王朝国家时代。王朝国家疆域格局的基本样式表现为,以“京畿”之地为核心,呈现出若干同心圆的分布形式,并且不同圈层的疆域具有不同的特征。诚如许倬云曾提出的,中国的传统疆域实际上由核心区、中间区与边陲区三个层次构成:“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中间区。”*许倬云:《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面对庞大的、异质性的疆域,王朝国家为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就需要对国家疆域进行合理划分。对于王朝国家而言,最基本的方式便是划定核心区和边缘区,这样也就有了内地和边疆。然而,对于入主中原的边疆少数民族而言,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在建立王朝国家之后,其原先生活的区域便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是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属性,二是政治心理上的核心属性。但是,随着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统治时间的推移,统治者会越来越以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待疆域结构,其国家认同越来越强于种族认同。而曾作为故土的区域,在疆域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会越发淡化,相反,作为国家疆域边缘部分的边疆属性则会愈加突出。如此一来,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内地—边疆”或“核心—边缘”的二分法,便成为划分中国疆域构造的一种常见范式。
在“内地—边疆”的视角下,王朝国家疆域的异质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内地同边疆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边疆地区不仅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且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也与内地存在很大差异。第二,在疆域架构中,核心区往往被视为王朝国家的根本,而边疆地区则处于从属地位。第三,在政治形态上,边疆地区也同内地大相径庭。在“内地—边疆”的疆域格局中,中央王朝往往不愿或不能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紧密控制。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广泛存在,与中央的关系较为松散,甚至呈现出时叛时服、“来来去去”的景象。因而,不同的边疆地区在保存各自独特性和相对自主性的基础上,是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存在的。
在中国王朝国家末期,疆域及边疆异质性、碎片化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第一,内地和边疆存在着族际上的内外分际。清王朝继承了明朝时期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政治区域。这一区域是汉族的聚居范围,与此相对应的是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区。第二,内地和边疆存在着政治上的内外分野。在内地的政区范围,中央政权拥有绝对性的控制力量,在地方政治制度上设置统一的“省”,在国家结构上表现为一种中央集权的特征。而边疆区域的地方政权不仅拥有较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国家权力在这一地区的渗透也十分有限。
这样的边疆现实,集中表现为晚清以后形成的中国“本部”与“属部”,以及“内中国”与“外中国”的概念。关于这样概念的产生,学界并无定论,但大多学者认为源于西方人的著述,*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9页。是西方人为分裂中国而炮制出来的。*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前线》1939年第2期。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概念一经使用便迅速流行,绝非完全是人为构建的结果,而是由于它切合了王朝国家疆域的现实形态。在此之前,人们也使用“中国”“中原”“海内”“海外”等类似的词语来表示内地和边疆的区别。而晚清以后,“中国本部”“属部”“内中国”“外中国”等概念正是沿承了这样的传统。
二、国家形态转变对传统边疆的挑战
近代以后,在外部力量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的国家演变进程再也无法沿着王朝更替的轨迹继续下去,国家形态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国的王朝国家时代,开启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这个进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得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得的民族国家特性对传统的边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碎片化的边疆形态越发不能适应时代需求。
第一,传统边疆形态与主权体制不适应。民族国家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拥有主权是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在主权体制下,国家将占有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视为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领土。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疆域具有同质性,无论内地或边疆,都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当中,主权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必须通过条约形式划定范围,以获取外部的主权承认,由此形成了边界。然而,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并未形成主权和领土概念,其间形成的边疆形态自然是非主权性和非领土性的。边疆不仅是多样性的,也是碎片化的,这显然无法迎合民族国家主权体制对同质性领土边疆的要求。另外,王朝国家的边疆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外部界线,而是随着国家能力与统治者意志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动。但是在民族国家时代,由于边疆的外部边缘线被边界锁定了,边疆的范围也就被稳固下来。
第二,传统边疆形态与同质性国族的构建不适应。民族国家不仅具有主权属性,还具有民族属性。这个民族是一国内所有居民经由国家力量整合而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当这个民族掌控了国家政权,获得了国家形式,就成为所谓的国族。在民族国家中,疆域的不同部分仅仅是同一国族生活的不同区域而已,而不应保持因文化要素形成的内外分际的破碎格局。这就否认了传统民族对疆域和边疆的排他性占有,或独立建立政治单位的权利。但是,中国王朝国家的边疆总体上是按照“华夷之辨”的文化范式来划分的,具有浓重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边疆和内地之间的文化差异。而这样的边疆形态同民族国家的国族属性是格格不入的。国族的构建要求将国内的不同文化民族进行整合,这是一个“求同”的过程,而传统的文化性边疆则不仅强调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还强调地域差异,这显然是一个“求异”的取向。这样一来,“同质”和“异质”之间的矛盾就被凸显出来了。
第三,传统边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统一性不适应。政治制度的统一性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民族国家为保障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和控制,需要在国体上实现主权在民,在政体上维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和主权性,要求国家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将其势力伸至境内最偏远的村民身上”,*[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这使得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必须通过统一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来实现。而在王朝国家时代,中国边疆的政治形态与内地相比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不同的边疆区域间,也由于各自特点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边疆居民的政治生活,往往是在特定的边疆政治和制度框架中展开的。伴随民族国家构建的开启,中国迫切需要构建起一套统一的政治制度,以实现对“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4页。在此背景之下,多样性的边疆政治亟待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向着一体化发生转变。
三、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形态
在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中,民族国家的产生对边疆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以至于人们对当下边疆及边疆治理的讨论,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展开的。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当中,传统的疆域和边疆,逐渐按照国族主义、主权体制的要求进行转型和重构,并初步形成了领土空间内整体性的边疆形态。
(一)国族构建与边疆形态的整体化
首先,“一国一族”*时论认为:“民族不同者,则独立为一国。”参见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1903年第28期。思潮对边疆的排斥。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初,将民族国家解读为“一国一族”并且将汉族等同于国族的观点,曾占据了主流地位。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掀起了一股“十八行省建中华”的社会思潮。在这一政治构想中,所要恢复和重建的疆域范围仅仅是历史上汉族聚居和统治的腹地区域,而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则持一种任其去留的消极态度。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所使用的十八星旗,也表达了“十八行省建国”的政治诉求,从而自觉地将边疆地区排除在外了。这类种族式的国族构建模式影响甚大,对国家疆域的整体性产生了解构作用,尤其是在广大边疆地区形成了一种排斥效应。
其次,“五族共和”理念对边疆的维系。辛亥革命以后,在反思“汉族建国”政治弊端的基础上,“五族共和”的国族理念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布:“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随后,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在各省代表会议上被确定为国旗,表明“五族共和”的国族观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时,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各族民众也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理念,并纷纷表示要“同谋五族幸福”。*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诚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洞见的,“中华民族由五个民族构成,这样的理论使得“中华民国”能够承袭清朝的边疆”。*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p.76.但是,“五族共和”理念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多元主义,而忽视了在“多元”格局之上国族的“一体”构建。由此统合起来的疆域构造在本质上仍旧是结构性和异质性的,不能满足民族国家构建对于整体性边疆的需求。
再次,“中华民族”认同对边疆的整合。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共同抗日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开始成为普遍共识,全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1939年,顾颉刚等人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周刊》1939年第9期。的观点,引发了强烈反响,在理论层面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构建进程。受此启发,蒋介石进一步提出了“宗支理论”*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认为中国境内并不存在多个民族,只有同宗同源的各个“宗族”。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的《民族政策初稿》更是直接鼓吹“中华民族一元论”。*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唯有中华民族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而国内的各个传统民族只是文化共同体,因此,不具备独立建国的资格。这样的中华民族构建进路,在理论上抵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族自决”口号的挑战,推动了边疆属性由“民族性”向“中华民族化”的转变,从而通过共同体建设的维度强化了疆域的整体性。
(二)主权发展与边疆形态的领土化
首先,主权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为边疆形态的领土化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认识并接受了主权观念,主权体制也开始从外部嵌入到王朝国家中。辛亥革命以后,这种主权体制得到进一步做实和发展。在国家政体从君主制到共和制转变的历史时刻,清帝逊位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使得国家主权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得以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京政府针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修约”及“废约”等外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巩固了中国主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国家能力有所增强,对领土至高性、排他性的主权管辖更加明显。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地位和声望有所提升。随着战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重建,主权国家大量涌现,主权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开始普遍推行。这样一来,中国能够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真正融入到新的世界体系。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得到外部承认,进而获得了实质性的内涵。
其次,陆地边疆形态的转变。近代以后,中国不得不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逐步划定国家疆域的外部界限,从而初步形成了断断续续的国家边界。民国时期,在这样的领土空间内,进一步按照主权原则对陆疆形态进行改造。一方面,对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进行整合。民国时期制定的几部主要宪法,都对边疆的领土属性进行了主权宣示,这是在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随着领土意识的深化,类似晚清时期根据“本末”“体用”标准形成的内、外中国的边疆观念便逐渐淡出了。另一方面,对中央和边疆地方的权力进行划分,使得国家主权归属到中央层面,从而加深了边疆的领土属性。在这一历史时期,边疆的地方权力不断受到限制,并被限定在地方政治的层面,而对于“军政、外交及其他有关全国一致之重大事项”,*《特派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赵守钰入藏训条案审查会审查意见》,载张羽新等《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则逐步交由中央政府处理。这样一来,边疆在政治上的异质性得到淡化,转而处于国家主权的统一管控之下,这也大大削弱了边疆的离心力,并且增强了边疆的整体性。
再次,海疆与空疆的界定与划分。领土是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近代以后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领土的范畴也变得丰富多样。中国若要获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和领土,就必须突破领陆的限制,构建起领海与领空的领土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海疆、空疆等多样性的领土边疆也就应运而生。一是,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构建海疆和促使海疆领海化。特别是“三海里令”*黄刚:《中华民国的领海及其相关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2页。的颁布与南海“十一段断续线”*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领土内海疆范围的初步划分。二是,在经历了近代以来陆疆领土大量丧失之后,国人对空疆主权表现得十分敏感。早在1919年于巴黎举行的“国际航空规章会议”上,中国代表就签署了《关于管理空中航行的公约》,该公约规定缔约国间彼此承认空中主权。当时的中央大学还绘制了《中国航空路图》,明确标注了中国的领空范围。*张其昀:《中国之领空》,《申报月刊》1932年第1期。在这样的条件下,虽然同王朝国家时代相比,中国的边疆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但是就领土属性这一根本性的标准来判断,其整体性却大大增强了。
(三)制度变革与边疆形态的一体化
首先,地方制度调整与边疆异质性的淡化。为实现国家政治一体化,民初政府颁布了著名的三道“划一令”,*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成为近代中国首批全国性整理政区的法令。针对边疆地区特殊性的政治生态,北京政府在省级层面设置了特别行政区域,为下一步推行省制做了铺垫。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地方制度的调整力度继续加大,尤其是规范了省、县两个基本行政层级。在边疆地带,大刀阔斧地开展了青海、宁夏、甘肃的分省,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的设省,以及西康的建省。在基层政府层面,开始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进县制,并为此广泛成立了设治局作为过渡性的县级行政机构。在这一时期,边疆区域的省制与县制改革,从地方政治层面大大推进了边疆的“内地化”与一体化。
其次,单一制的确认与央地关系的加强。民国初期,实施联邦制来统合异质性边疆的构想曾一度风靡。然而,随着对民族国家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以及国家能力的恢复与增强,对于联邦制的呼声渐渐淡出,中国最终选择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的确立,既符合民族国家构建要求,也符合中国的制度文化,对于重新定位边疆的“地方”属性,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方政治的规约,减弱边疆地区的离心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国家权力延伸与边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近代的边疆社会,既有地方军政势力,又有传统的民族和宗教权威,还有国际势力入侵形成的外部权威。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历届政府相继采取了怀柔性与强制性的手段,对上述权威加以限制、削弱、排除和统合。随着国家政权的渗透、国家制度和国家认同的强化,边疆地区的政治权威逐渐被置于到国家权威之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
纵观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大体上对边疆的整体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充实了边疆,加速了边疆政治的均质化;二是,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克服边疆地区的地方主义与分裂主义;三是,推动了国家政治的整齐划一,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政令的统一与执行。随着国家政权在边疆地区的渗透,边疆作为构成整个国家疆域的“地方”属性得以加强。这样一来,因多样性地方制度所导致的碎片化边疆,在政治层面得到了整合,边疆的政治形态也变得越发一体化。
四、民族国家建立与边疆形态的重构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传统边疆形态逐步按照主权体制和国族主义的要求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但在这一过程当中,边疆只是发生了“量”的变化,并未获得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性质。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正式形成,以及人民民主政权最终建立。由此,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从构建阶段进入了建设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开始真正有能力在民族国家框架中展开全面的边疆治理,从而开启了中国边疆形态演变的新时代。
第一,陆疆空间的基本划定。在民族国家时代,边界是边疆的外部边缘线,也是边疆的构成要素。边界的划定确定了边疆的主权和领土属性,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和固化了边疆的空间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获得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由此,作为国家疆域边缘部分的边疆,就呈现出领土边缘部分的形态,而这种领土性边疆形态的最终确立又是以边界的划定作为主要依据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时与周边陆地邻国之间没有一条边界线是通过双方平等谈判而正式划定的。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在经历了短暂的“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阶段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着手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划定边界。在这一时期,将近一半的陆疆边界在地图上得以标定。如此一来,中国陆地边疆的外部界线逐渐廓清,“有边无界”的边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陆疆的空间范围也基本确立下来了。
第二,边疆社会同质性的增强。陆疆的“边疆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异质性和“地”的异质性两个基本层面,而人的异质性又汇聚成为更加宏观的社会异质性。现代国家建设和疆域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边疆社会异质性,和增强其同核心区之间的同质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屯垦戍边、移民支边、进行“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重构政治文化等方式,在陆疆地区展开了全面的治理活动。经过这样的系统治理,边疆社会的政治体系得到统一、族际关系得以改善、经济有所发展、人口结构得以调整。边疆地区的社会面貌得到了极大改观,同内地社会的同质化水平大大地提升了,这在临近内地的边疆地带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得边疆的内部界线向外推移,由此,边疆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总之,“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边疆形态的整体化。
第三,立体化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在海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仅继承和改造了原有的“南海十一段线”,还划分了“东海一段线”*郭渊:《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3期。的海洋边界,并在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图》中进行了首次标绘。同时,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不适时宜地确立了中国12海里的领海制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领海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海疆空间,在国际上获得了苏联、朝鲜、越南、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广泛认可,*郭渊:《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3期。许多国外出版的地图和书籍也据此进行标绘。由于国际社会的公开承认,中国海疆在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主权意义,从而成为国家领土和领土性边疆的一部分。此外,随着主权体制的确立与拓展,中国的领空制度也更加完善,空中边疆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195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为维持中国空疆秩序、安全以及日常的飞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后,中国还加强了空中军事力量的建设与空疆的安全防控治理,并确定了航空工业“一五”计划投资以及《航空科学研究工作12年规划》。如此一来,在主权领土框架下,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实际上已经基本确立了陆海空三维立体的边疆形态。
总之,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系统而全面的治理,边疆的领土属性得到确立和巩固,边疆同内地之间的同质性大大提升,边疆的政治地理空间属性也得以强化,边疆形态发生了质的转变。由此,民族国家时代整体性的边疆架构正式建立起来了,这既是近现代以来过渡性边疆形态的终结,也是新时期中国边疆形态演变的开端。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孙保全,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研究人员(云南 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①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XKJS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