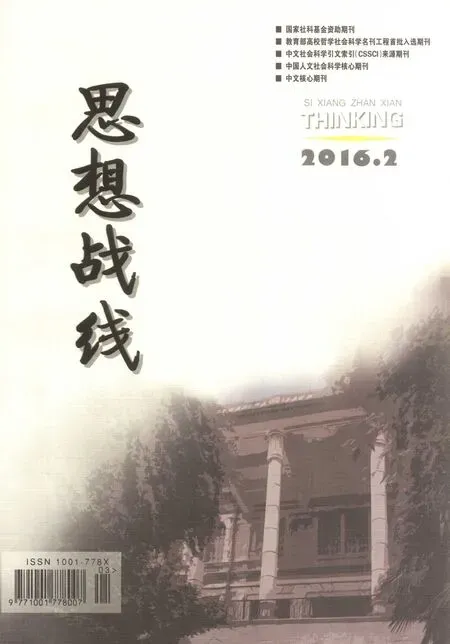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和文臻
与阿里耶斯对话
——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和文臻①
摘要: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关键词:死亡观;死亡地点;民族文化
一、从“驯服的死亡”到“野蛮的死亡”
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在《对于死亡的西方观念》和《面对死亡的人》两部力作中,系统梳理了西方人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有关死亡的理念和处理方式。*Philippe Ariès,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Philippe Ariès,L’homme Devant la Mort,Paris:Seuil,1977.他认为,欧洲人在很长时间内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死者一般在家中床榻离世,临终时刻有亲人陪伴,丧礼体现着公开性的社区参与,对亡灵的哀悼伴随着宗教仪式步骤,因而整个过程可以称为“驯服的死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处理死亡的方式慢慢具有更多的个体化色彩,然而死亡的自然属性继续被视为天经地义,牧师和亲朋好友仍是亲临死亡的见证者。至20世纪初,医学为人们提供了抗拒死亡的更多可能,死亡仿佛不应该发生。一旦有可能发生,必须用现代医学抗拒,即便死亡发生后,也要悄然处理,甚至穿戴丧服的传统也被视为令人不安的历史包袱。既然现代医学变为抗拒死亡的中坚力量,人们死亡的主要地点逐步从家中转移到病房,临终者往往在医院孤独离去,死者与生者的密切关系,由于死亡地点挪动被隔断。根据阿里耶斯考证,欧洲人将死亡的自然属性当做禁忌加以压抑和隐蔽的做法,于20世纪50年代演变成为惯习。由于这种惯习伤害人类悲悯情怀的表达,他将之称为“野蛮的死亡”。*[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上下卷,吴泓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提出“野蛮的死亡”概念的阿里耶斯非孤军奋战。英国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早在1955年就曾指出,西方国家在20世纪出现一个显著变化:人们可以随意地讨论性问题,但属于自然过程的死亡,却不再被讨论。*Geoffrey Gorer, “The Pornography of Death”,Encounter,vol.5,no.4,1955,pp.49~52.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罗斯于1970年也提出,死亡问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并认为,这一趋势与西方人以往对待死亡的平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Elisabeth Kübler-Ross,On Death and Dying,New York:Macmilton Publishing co.,Inc.,1970,pp.6~10.鉴于现代医学在人们有关死亡的态度转变中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有关现代工业国家人口死亡的研究,对现代医院的临终者和护理人员予以了高度重视。例如,巴尼·葛拉泽和安瑟姆·斯特劳斯于1968年提出死亡过程轨线说,认为死亡的过程好像一条抛物线,最高境界是“优逝善终”,但达到这一高度的条件是,重病患者在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处境的前提下,可以得到有质量的治疗和关爱,同时可以选择临终的方式和地点。*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Awareness of Dying,Chicago:Aldine,1965 ;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Time for Dying,Chicago:Aldine,1968;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Status Pass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但是大卫·赛德诺的医院田野志提醒人们,对善终的期待不能过高,因为现代医院的管理被常规化和标准化,医务人员对绩效的关注,屡屡超过对临终患者的关怀程度,临终关怀的质量受到医疗机构管理制度的限制,往往缺乏人情味。*David Sudnow,Passing on: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ying,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7.虽然观点各有不同,这些研究均与阿里耶斯提出“野蛮的死亡”的概念相互呼应。
在学术界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临终安养运动”,也与阿里耶斯对死亡医学化的批判不谋而合。*Marian Osterweis & Daphne S.Champagne,“The U.S.Hospice Movement: Issues in Develop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69,no.5,May 1979,pp.492~496.这一运动以医院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对“优逝善终”的期待为理由,反对不必要的医学干预对临终者尊严和自主性的伤害,主张以英国桑德斯女士在1967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家临终关怀院——圣—克利斯朵夫临终安养院为模式,要求在医院制度之外,成立结合姑息治疗与生命后期护理的临终安养院。*黄剑波等:《基督教与现代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了这一运动影响,日本第一家临终安养院于1981年出现,中国大陆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1990年建成于天津,中国香港第一家临终安养院于1992年开业,中国台湾第一家临终安养院于1990年接收患者。*Susan Orpett Long,“Negotiating the ‘Good Death’:Japanese Ambivalence About New Ways to Die”,Ethnology,vol.40,no.4,2011,pp.271~289;崔以泰:《中国临终关怀研究》,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76页;苏永刚:《中英临终关怀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1~55页;严勤,施永兴:《中国临终关怀现状与伦理探讨》,《生命科学》2012年第11期。
本文试图运用阿里耶斯对欧洲不同时代死亡观的分类和论述,结合笔者在云南丽江地区的田野调查,集中探索纳西族的死亡观和关于死亡地点的选择。
二、在丽江大河村解读死亡地点的意义
丽江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滇川藏交界位置,居民以纳西族为主。随着1997年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这个在当时仍然默默无闻的小县城迅速跻身为国内外知名城市,以观赏传统纳西族文化为主的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在当地独特文化被外人知晓的同时,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改变了纳西族原来相对闭塞的生活,使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使丽江人保持着较强的地方认同。
本研究发生在2015年暑期,田野工作地点在距丽江古城13千米的“大河村”。*考虑到死亡问题的敏感性,笔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人名和村名均为化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一共访谈了大河村的村民12名,还邀请了2名医生和2名当地的纳西族学者介绍纳西人的死亡观以及纳西人对死亡地点的偏好。在村内外的访谈大致是为了回答如下3个问题:(1)如何概括纳西族传统的死亡观和相关实践?(2)涉及死亡问题的纳西族文化传统发生了哪些变化?(3)历史上和当代的纳西人处理死亡的方式能否用阿里耶斯的死亡学说做出进一步的理解?
在展开田野调查之前,笔者梳理了有关纳西族死亡观的既往研究,并找到一名资深的东巴文化研究者——和力民先生了解纳西族死亡观与处理死亡方式的关联。*和力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纳西族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研究。在既往的研究中,有关纳西族死亡观的论述,较多的属于就殉情自杀问题展开的历史研究,针对当代纳西族正常死亡的研究则较少,专门讨论当代纳西族人死亡地点的论文或专著尚未见到。历史上纳西族殉情自杀问题之所以得到学者重视,是由于汉族社会流行的包办婚姻观念和做法传入丽江地区后,与纳西族历史上曾经盛行自由恋爱观的冲突,引发了连绵200多年的殉情自杀风潮。20世纪20~30年代,曾在丽江逗留过的俄国人顾彼得,在有关纳西殉情事件的记录中,将丽江称为中国的“自杀之都”。根据顾彼得的记录,纳西族的殉情者一般相约风景优美的地点吊死在树上或跳崖,以表达生不能同眠死能共穴的希望。*[俄]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李茂春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习煜华:《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在纳西族传统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一定要有归宿,否则就会回来打扰生者的生活,使得生者田里庄稼不好,家里人丁不兴旺。就正常死亡而言,死后操办的超度仪式就是把死者的灵魂引入祖先居住之地,即传说中的神山右面,将死者超度为祖先,让其与先祖一起在神山右面继续生活。据民间传说和东巴经典《执法杖》(上卷)等的描述,祖先之地是一个遥远的遍地鲜花、绿草成荫、牛羊满坡、可以过上神仙般生活的地方。*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56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236页。进入祖先之地,需要人在临终时还有一口气或通过超度仪式接上一口气,以标志着生命转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可能。由于标志承上启下的魂归祖地,将纳西人死亡观念与世代繁衍的希望链接在一起,正常死亡的特征之一即在家中或在家乡死亡,而不是他乡别处。
在纳西族的文化理念中,暴死、尸首不全或死在他乡而不通过超度仪式接上一口气的人,都不能魂归祖界,也不能前往“玉龙第三国”,只能四处游荡,因而常常捣乱贻害后人。但是在深刻影响纳西人死亡观的东巴文化中,殉情而死属于非正常死亡,亡灵可以经过东巴超度进入“雾路游翠郭”,即当代人用通俗方式所言的“玉龙第三国”。该地是纳西族为殉情男女创造的一个特别的生命归宿地。在那里,鹿可骑、山骡可以做工、风可听人使唤、石头可以剪裁成为衣服、没有流言蜚语、甚至没有蚊蝇、没有让人苦痛的疾病。同时,情死后的亡灵也可前往祖先之地,但需亡灵依附活人说出自己的愿望。如果有儿女在世,情死者可以利用活者的祖先身份接受超度,进入祖先之地。如果情死者没有儿女或希望永远与情人厮守,灵魂超度的目的地则是上面提到的“玉龙第三国”。
杨福泉认为,在纳西族的死亡观念中,死亡有其明确的自然属性。*杨福泉:《论东巴教中的生命树和死亡树》,《学术探索》1996年第3期。这是因为纳西族的先民从树叶发芽、变为青翠直到枯萎凋零的过程,感受到人从生到死的规律,并将这一规律以“生命树”的种种传说系统归纳解释,因而纳西族有关正常死亡和殉情死亡的观念并不消极暗淡,而是满怀对来世的渴望。*和力民:《祭风与殉情》,载《东巴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1~282页。另据刘祥远对纳西族生死观念的研究,纳西族与许多其他云南少数民族一样,有着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但不妨碍对死亡自然属性的接受。*刘祥远:《古代纳西族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27~44页。
根据笔者在大河村的观察和访谈,深受东巴文化影响的纳西族农民仍然希望,离世之际最好跟日常生活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样,待在家里,有亲人陪伴着,理所当然的死亡地点是祖房的火塘边。火塘上方“神柜”的左边是男人床榻,右边是女人床榻,在男人床榻的一端备有一个小床,当家人去世后,遗体就会放在这个小床上,直至出殡之日。值得注意的是,祖房的火塘边和神柜前,也是举办婴儿诞生仪式的地方。男女成年结婚时,也是在祖房的火塘边和神柜前举行婚礼。
总之,祖房火塘旁和神柜前的空间,既是家人生时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家人生死的临界地。生命初始地点与生命结束地点的重合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纳西族能够在信与行层面欣然接受生死相连的逻辑,对死亡的坦然态度宛如阿里耶斯描述的欧洲人被文化传统驯化的死亡。当死亡即将降临时,死在家中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意识仍然持续。笔者希望利用下面三个涉及大河村的案例说明此点。
案例之一:在家中去世的凤彩爷爷*案例来源于笔者田野调查。
据了解他的亲朋好友介绍,凤彩爷爷于1998年底因病去世。之前,老人住在丽江城里,生前就说死后一定要埋到大河村老家墓地。老人到年迈时肺肠胃都查出了问题,也到医院治疗过。在病情变为危机时,他被家人送到丽江市医院。在医院当护士的一位亲戚对他们说:老人起房盖屋辛苦一辈子了,坟前也有人浇水了,还是拉回去家里好。陪同的家属认为此话有理,决定把老人送回家里静养,而这个选择也正是老人自己的愿望。回到家里的一个下午,凤彩爷爷在院子中大树下静养休息,正好放学回来的孙子打招呼说:“爷爷,我回来了。”听到这句来自后辈的温暖问候后,老人一歪头就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在凤彩爷爷去世的几天内,为他举办的超度仪式和出殡仪式做得十分顺利。
在描述凤彩爷爷放弃继续医疗的经过以及死亡场景时,他的亲朋好友强调了老人希望从医院回到家里安养直到去世的夙愿,而且特别提到他的去世是发生在家中,有所有能来的亲人陪伴,而不是孤单地死去。对孙子回家的问候与凤彩爷爷死亡时间的重叠之敏感,更表现出陈述人对老人能够善终的认同,毕竟临终者的宽慰和安详地去世,是被生者所尊重和血脉的延续所烘托。陈述人认为,凤彩爷爷的超度仪式举办得顺理成章,正是在于善终之道是死在家中,之后才能顺利举办超度仪式进入祖先之地与祖先们团聚。另外,陈述者还特别提到,凤彩爷爷的亲戚在为他举办超度仪式过程中,为他念诵了他的父母、他的祖父祖母以及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名字,借以请求祖先为他指明通向祖地之路。在纳西族的生死信仰中,通往冥界之路看起来好似有三条,但只有中间的那条路可以让死者顺利找到祖先之地,而那条路需要祖先的帮助和指引才能找到。
在了解凤彩爷爷的情况时,一位陈述人告诉笔者,纳西人正常死亡的超度仪式过程其实大同小异。比如,在举办超度仪式之前,死者的家人还要到村头冒泉水的泉水口“买水”,把水烧开后为死者擦洗遗体,然后为死者抹酥油、梳头、穿寿衣。*“买水”指将硬币丢到泉水里之后汲水,其意是偿还泉水神对死者在世期间的恩惠。东巴祭司做完超度仪式后,遗体一般会被放在家里,三四天内再举行丧葬仪式。死后4周,召集比较近的亲友再聚一次,聚会的名称是“四七”,意为距离去世之日已有4周,然后依次举办1年斋和3年斋的祭奠活动。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说明,大河村纳西族处理正常死亡的态度和方式是努力地将死者和生者的象征距离缩短,而不是扩大。正如拉德克里夫对安达曼岛人的葬礼的描述,葬礼不能被看做恐惧和悲伤的感情结果,而应看作是在责任感之下严格受到控制的社会关系的维系。*[英]拉德克里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在这一点上,大河村居民的死亡观和处理死亡的实践,类似阿里耶斯所言众人参与的“驯服的死亡”。
当然,大河村纳西族处理死亡的形态也不完全等同于阿里耶斯所言“驯服的死亡”,这是因为殉情死亡在纳西文化中并不属于凶死,死者可以接受亡灵超度仪式,所以殉情者可以前往“雾路游翠郭”,或在祖先之地找到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纳西族的殉情死亡事件越来越少,丽江地区已不是顾彼得当年所说的殉情“自杀之都”,殉情而死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案例之二:医院去世的秀芝奶奶*案例来源于笔者田野调查。
秀芝奶奶原是大河村人,后来搬到丽江城里居住,于2002年2月3日因突发性脑出血而身亡。她的老伴当时还跑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医生家中求助,但医生没有在家。一个邻居问清楚情况后立即打通120急救电话,秀芝奶奶才被送到医院。到医院后,急诊室的医生对她家人说,她的情况比较危险了,意思是说抢救过来的可能性比较小,另外一层意思是问她的亲人要送她回家还是留在医院抢救。秀芝奶奶的老伴坚持要抢救到最后一刻。看到秀芝奶奶的老伴如此坚持,医生给秀芝奶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已经回天乏力。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如果患者还有一口气,医院有责任协助亲属把病人送回家。但秀芝奶奶已经是医学定义的死者,医生表示爱莫能助。秀芝奶奶的儿子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将秀芝奶奶送回到她在市里的家中。在秀芝奶奶断气前,家人在秀芝奶奶腮边放了“琀口”。这个“琀口”是一个红绸子包裹,里面放有7颗米,7根茶,7小粒金子。*如果死者是男性就放9粒米、9根茶、9粒金子或9粒银子。放入时用一根线拴住放到死者腮边,以表示灵魂已经接到这些物质的气息,并带着这些东西上路去找祖先了,放好“琀口”才可以顺理成章地回家办丧葬仪式。据和力民先生的解释,此处接气指的是接这些物质(米、茶、金子或银子)的气息,让死者灵魂带着这些物质的气息上路。然而现经过时间的流变,一般纳西族民众普遍认为“琀口”接的是死者口中尚存的气息,让死者不至于断气,使得死者的生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事后,秀芝奶奶的老伴认为,急救员当时没有让秀芝奶奶平躺休息是错的做法,急诊医生水平很差,也有过失。
从秀芝奶奶的过世可以同时看到,她的家人对现代医学和当地医院的期待与失望。她的家人首先到附近一个身为医生的邻居家中求救,而后同意用急救车送她到医院,他的老伴甚至在急诊室的医生暗示说没有抢救成功的可能性时,仍然坚持要抢救到最后一刻。这三个细节都充分说明,秀芝奶奶的家人相信现代医学有可能起死回生。虽然急诊室的医生用委婉的方式表示,已经没有抢救成功的希望,甚至问她的家人是否放弃治疗,及时将病人拉回家中,秀芝奶奶的老伴却坚持抢救到最后一刻。
秀芝奶奶的去世当然令她的家人感到沮丧,她的老伴甚至怀疑急救人员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措施,还怀疑急诊室的医生是否有应该具备的医学水准,但让她的家属进一步感到沮丧的是,医院居然可以派车将活着的患者送回家,但不能派车送死者回家。当然,在丽江小城的熟人社会中,这样的规章制度可以有所妥协。问题是,如此的规章制度显然令人感到异化。
从秀芝奶奶的过世还可以看到,她在医院的死亡仍然具有阿里耶斯所说驯服死亡的某些特征。她在医院断气前,家人看护着她,在她的腮边放了“琀口”。据和力民先生解释,包裹着米、茶、金子或银子的“琀口”,象征着死者带着人间的物质生活气息离去。纳西民众普遍认为,“琀口”等于“接气”,等于还存有一口气,接气之后生命才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延续。同时,“琀口”也是防范阎王饿鬼捣乱的“买路钱”。按照纳西族民间传说,亡灵在前往祖先之地的路途上会遇到各种妖魔鬼怪,需要东巴手持长刀开路,也需要亡灵自己带好粮食、茶叶、金银作为买路钱。由于使用了这个“琀口”,为秀芝奶奶举办的超度仪式才有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有了超度仪式的合法性,秀芝奶奶才能被埋在大河村祖坟。
案例之三:蘘平叔叔的凶死*案例来源于笔者田野调查。
据熟悉蘘平叔叔的村民和亲属介绍,他在世时,老婆已经领着孩子离开了大河村,原因是他经常酗酒、还爱赌博。人到中年时,他在自家坟地中喝下农药自杀,但动机不是殉情,而是绝望。在长辈允许之下,他的尸首被村民用柴油点燃焚化,骨灰被草草埋在靠近祖坟的地方,但没有被允许进入祖坟地界。虽然他选择祖坟作为自杀地点的动机,有可能是想从祖坟迈向魂归祖界之路。
从蘘平叔叔的死亡事例可以看出,由于他是穷途潦倒而喝下农药自杀身亡,他的离去,被众人认定为极不吉利的凶死。在大河村村民的观念中,凶死者是需要特别防范的亡灵,凶死者的尸首不能拉回家中。如果蘘平叔叔的死不属于凶死,而是在外地因交通事故或重病身亡,他的尸体仍然可以被拉回家中,但不能从正门进入,而要用后门。如果没有后门,家人就要把围墙拆开,将尸首搬进去,之后举办可以补上接一口气的超度仪式。但蘘平叔叔之死毕竟属于凶死,遗体不但没有被抬回家中举行仪式,而且连遗体也没有被允许埋在祖坟的正中位置,而只是草草地埋在了祖坟旁边。由于是令人恐惧的凶死,他的亡灵也不能成为举办超度仪式的对象,因而他不能踏上魂归祖界之路。
既不能同祖先团聚,也不能步入“玉龙第三国”的死者,在纳西文化中当属最为可怜的亡灵。对这样的死者,甚至悲悯情怀的表达都难以实现。假如是可以魂归祖界的亡灵或殉情身亡的男女,悲悯之心可以在丧礼过程中公开表达,而凶死者由于得不到仪式化的生死过渡安排,来自他者的悲痛情感也只能埋在心中。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更为重要的一个细节是,蘘平叔叔的尸首不能被抬回祖房。东巴文化研究者和力民先生解释,即便在正常死亡的情况下,死者要进入纳西族那个遥远的、遍地开满鲜花、绿草成荫、牛羊满坡的祖先之地,也需要严格的仪式化步骤。首先,遗体要抬到祖房的火塘边的小床上,之后点上油灯,还要将饭菜分给可能前来找麻烦的恶鬼,同时要为死者备好前往祖先之地的干粮。再有,在家中操办的法事和在祖坟举办的下葬仪式都要请东巴祭司,且不说还必须有家人和其他亲属的在场。仪式的公开性,标志死者生前的威望和死者家庭的荣誉,而且可以证实死亡的正常性,也就是死亡发生在家中、有亲人陪伴、有东巴司仪操办丧事、而且有对恶鬼和阎王防范的过程。反之,偷偷地送走亡灵会被外人怀疑为凶死。蘘平叔叔的骨灰被草草掩埋的道理正在这里。由于他的死因是凶死,他的身后事与祖房无缘,而发生在祖房的死亡才是纳西人在家中死亡的根本要义。
当然,在纳西族传统文化中,对于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为情死亡的处置,都有相应的仪式和规矩。但是在相互过渡,或者是说变通时,则可以从生死临界地上得到转换或者说转折。譬如,一个非正常死者,一般说来其亡灵是没有资格去祖先聚居地的。但是死者有儿女在世,其家人希望死者能够归祖列宗。那么,就得请东巴祭司来拯救死者亡灵,使之脱离凶鬼恶鬼的纠缠,把死者亡灵救赎到家里,在家里重新用鸡做放“琀口”仪式,然后为之做超度正常死者亡灵仪式。就这样,死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祖先。这一过程中,转折点就是把死者亡灵接回到家里,在家里为死者放“琀口”。在家去世的意义自然彰显。同样,情死者仍然可以通过一定形式,通过回到家里这一临界地转换成为祖先或者魂归祖先聚居地。正是如此,传统纳西族的死亡观是自然、有序、必然、理性,但又要充分表达对死者悲悯、关爱、赞美、期望和祝福的情感。所以说,纳西族的死亡观是既有理性的驯化死亡特征,又有悲悯情怀的文化内涵。其中不乏美丽智慧的赞美和精神上对死者的关爱和期待。
三、尾声
在《面对死亡的人》一书中,阿里耶斯按照历史时间的流逝,使用大量历史文献梳理了欧洲人的死亡文化史,将不同时期的死亡类型加以概括。虽然处理死亡的方式和类型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不断演变,而且经历了一个越来越个性化的历史过程,但阿里耶斯撰写的力作中,为读者展示出的最能形成鲜明对照的死亡类型,则是在历史长河上端的“驯服的死亡”,和在历史长河下端的业已被世俗化并被医学化定格的“野蛮的死亡”。用阿里耶斯的原话表述,欧洲人在过去“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且不太在意,这种传统态度与我们现今的死亡观形成鲜明对照:今天的我们是那么的怕死,我们甚至不敢说‘死’这个字。因此,我们把那种类似家中常客的死亡叫做被驯服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以前是野性的,后来才被驯化;恰恰相反,我们是想说它现在才变得野性难驯了,以前并非如此。早期的死亡是驯化的死亡”。*[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上卷《卧像的时代》,吴泓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页。
在上面引用的寥寥几句话中,阿里耶斯将老生常谈的文明概念彻底倒置:有信仰支撑的驯服死亡才是文明的死亡,它发生在过去,而不是在当代;信仰被剥离的死亡才是野蛮的死亡,它发生在当代,而不是在过去。
在阿里耶斯看来,从20世纪初起,欧洲人将死亡从社会中剥离的心理配置已经就位,在消除死亡的仪式化和公共性之后,人们对死亡的处理变成私人的行为。久而久之,呼吸机、监测仪、插管技术以及新药的出现,使得病危的患者也能长期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医院的重疹护理病房由此取代以往常见的死亡地点——家庭。常见的死亡地点的被挪动,将临终患者与其家属的实际距离和社会距离全部拉大,因而家庭本身也从死亡中剥离,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拒绝穿戴丧服的习俗以及法定服丧期的取消。丧服穿戴习俗的式微,绝非源于未亡人的无聊,而是社会拒绝卷入未亡人的悲伤情感,其结果是人类的悲悯情怀难以在死亡问题上得以彰显。阿里耶斯就此尖刻地写道:“服丧的泪水被视同为疾病的分泌物。”*[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下卷《野蛮化的死亡》,王振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14页。
在丽江城外的大河村,笔者试图借用阿里耶斯的目光审视纳西族对死亡地点的偏好,以此升华笔者对纳西族死亡观的理解。以上讨论的三个案例,可以说是笔者在大河村调查发现的浓缩。换而言之,大河村的纳西族农民家户,仍然相信一个人的离去应该发生在家中和家乡的地界之内。死者虽然独行,亲人却在两侧,此乃大河村纳西族农民认可的死亡方式。这也意味着对死亡最好发生在家中的期待。一位年迈的纳西族老人这样对笔者说:“年纪大的老人会尽量避免在别人家过夜,因为担心有突发情况而在别人家里突然离世。”*来源于笔者田野调查,以下同。
但在传统的过去和现代的当今之间,若用简单的两分法画出一道鸿沟,那就将大错特错。使用一个类似可见光谱的分析法,也许比较合适。可见光谱是人的视觉可以感受的光的强弱和色彩序列,如白光经棱镜或光栅散色后会呈出红、橙、黄、绿、蓝颜色构成的彩带,形成一串可见的、连续的、有差异的光谱序列。就丽江地区纳西族有关死亡的态度而言,我们可以在不同身份的人中见到不同的光谱颜色。如此的“视觉”在丽江医院心内科一位医生的谈话中可见一斑。
由于常常遇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琼芳医生在接受笔者的访谈中说道:“一般来说,我们丽江人还是要拉回去死的。当然现在更为现代了,或说思想更为开明,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也愿意在医院里进行最后治疗。不到最后不罢休,不放弃,宁愿赌一把,而在家里死去的观念更为淡薄了。同时,国家、政府鼓励共产党员火葬,不支持土葬,这样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直接从医院就拉到了火葬场。”这一陈述说明,至少在丽江地区的一部分纳西族党员和干部中,在家里死亡的习俗在慢慢消逝,医院反倒逐步成为一些体制化精英的生死临界地。
笔者在大河村的访谈中还获悉,一部分在外地长期工作成家的纳西族人,会在外地死亡后便葬在外地。因为在纳西族的文化理念中,只要有亲人在、尤其是有子女在的地方就是家,因而在较远的外地成家立业之后,人们较少选择回到丽江安葬,而是大多葬在子女所在的地方。但是一旦在外地工作的地点与丽江老家的交通距离不太遥远,这些人的尸骨往往还会被送回丽江葬在祖坟。例如,一个陈述人对笔者说,他知道有一个纳西人生前想要回家断气,家属也愿意配合,断气后,家属从医院买了打吊针的瓶子,让死者插着针头送到丽江,在象征意义层面表示到家才断气离世。由此可见,什么是死和什么是家的概念都具有伸缩性。
总之,大河村纳西农民仍然推崇民间信仰,认可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与此同时,阿里耶斯所言的“野蛮的死亡”,在一部分纳西族党员和干部中演变为制度化惯习。这种惯习的形成带有制度强制的色彩,也伴随着自觉自愿的成分。监管党员和干部的制度,毕竟会使得被制度管理的人们将制度化的要求转变为内在的接受和认同,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例如,在汉族社会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尸首火化规定,却随着制度化的要求变为几乎不再被质疑的习俗。*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1~197页;崔家田:《从“无序”到“有规”——一项关于殡葬改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8页。
笔者难以猜测阿里耶斯所言的“驯服的死亡”将会在丽江纳西人中保持多久。但如果在驯服和野蛮之间的选择余地都没有,结果将令人深深不安,因为那将是又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也将是又一个人类文化选择的泯灭。
(责任编辑 陈斌)
作者简介:①和文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