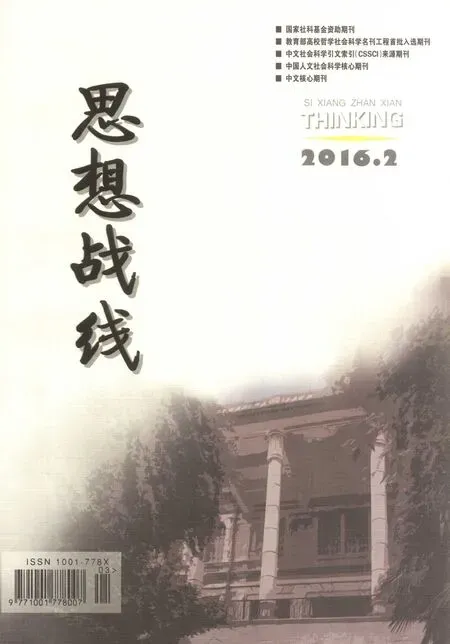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
潘天舒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
——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
潘天舒①
摘要: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北美地区产生和发展着一场影响深远的信仰实践活动,这一活动因其具有新宗教运动的特性,被称为“新时代运动”。借助民族志田野洞见,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这一案例进行审视,在以多元文化交融为特色的新时代信仰实践过程中,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宗教传统,成为西方信徒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并为其应对后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对“新时代运动”进行人类学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修正僵硬的宗教观,以便在研究和观察当代中国信仰生活实践时获得灵感和启示。
关键词:新时代宗教运动;文化全球化;多元信仰;人类学视角
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浏览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报纸或者新闻门户网站,总会在栏目分类版面看到与精神性或者灵性( spirituality) 顾问和咨询相关的内容:从传授瑜伽健身术和禅宗冥思打坐之道,到星象、水晶球或塔罗纸牌 (tarot card) 预测命运走向等五花八门的服务,不一而足。公众媒体大都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笼统地归入“新时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的笼统范畴。*笔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各大门户网站,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塔罗星象门户网站和风水命相论坛。尽管从字面上来看,这些广告试图从“愿者上钩”的信徒身上渔利,有着显而易见的商业目的。而难以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显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反主流文化产物之一的“新时代运动”,如今已经成为非常规意义上的“宗教经济”(religious economy) 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宗教经济,是指在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信仰教派采用各种策略,来吸引同道、信徒和追随者,从而形成市场竞争局面的文化现象。*Roger Finke,Rodney Stark,The Churching of America,1775~2005: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孕育产生的美国“新时代运动” 这一尚未引起国内学界广泛重视的多元信仰实践模式进行审视和探讨。在汲取田野洞见的基础上,本文力求展示:在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借鉴过程中,源于非西方文明社会的信仰传统,已经成为北美“新时代运动”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后现代条件下宗教文化互动的媒介,为其信徒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此外,“新时代运动”在欧美社会的盛行,也促使当代学者意识到宗教—迷信二元论的局限性,同时认真思考文化全球化条件下多元信仰路径传播的复杂性。
一、从乔布斯的“新时代”修行说起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在2005年6月14日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所作的嘉宾演讲中,特意提及他当年被迫辍学、饥寒交迫时的一段令他回味无穷的经历:每到周日,他会步行7英里到印度教克里须那神庙(Hare Krishna),为的是享用那里的素食美餐。*参见美国斯坦福大学官方网页,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作为美国“新时代运动”的重要产物,克里须那已经成为集聚东西方宗教传统元素的信仰组织。这一印度教派为乔布斯这样有着跨文化出身背景的年轻人,提供了满足自我启蒙需求、追求超世体验和探寻生命真义的资源。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新时代运动”所特有的神秘主义气息,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不甚合拍,然而经过重构的新时代宗教文化要义中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态度,以非制度化的个人修行为基础,自由选择适合自我身心自然发展信仰模式,则有助于北美中上层人士获取其传统价值系统所欠缺的文化资本,以及他们深刻反思和改造精神生活的灵感和驱动力。*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Richard Nice,tra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对于任何受过宗教人类学经典理论熏陶的人来说,“新时代运动”能从20世纪中期延续至今,形成一种难以依照常规来定义的信仰实践模式,的确有点不可思议。19世纪社会进化论重要代表人物、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Tylor),在其代表作《原初文化》一书中,不但首次在科学层面上对“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定义,还对人类社会宗教信仰起源和发展做了著名的“三段论”表述。*E.B.Tylor,Primitive Cultur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58.他认为,宗教发展也依照社会进化的序列,经过万物有灵论(也称泛灵崇拜) 、多神崇拜和一神教的演化过程。在初始阶段,泛灵崇拜源自人们对自然现象中精神魂灵成分的认识。泰勒这一认识存在着明显谬误。然而它却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推断:早期人类常常以为人死后魂灵会依附在生前所处环境之中,依附在山石或动植物的身上,而且那些在睡梦或幻觉中出现的魂灵,是实实在在的物体,不是虚幻的产物。随着文化的演进,人们开始认识到有些魂灵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成了太阳神、月神、雨神、太空神、地神、动物神、战神和农业神等等。多神崇拜也就随即开始。直到最后,一神教逐步代替其他诸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成为惟一的宗教信仰。
用当代人类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泰勒以宗教为考察重点而提出的文化演进假说,表达的无疑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要义。“欧洲中心论”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偏见,即认定西方社会是文明世界中心,非西方社会从文化、种族和社会形态来说,都处在落后愚昧阶段。在美国奴隶制度和欧洲殖民体系崩溃之前,“欧洲中心论” 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人类和种族差异的主流看法。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泰勒著书立说之时,正值大英帝国在全球大肆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黄金时期”。而泰勒就是通过与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和政府驻外官员的信件来往,才获得对非西方社会风土人情(尤其是“原始”宗教仪式)的描述性资料。他无法像后来的人类学者那样,通过田野体验进行研究和探讨。以19世纪哲学和达尔文学说为立论基础,泰勒将收集到的二手文字材料作为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试图提出一套有关文化进化的理论。他的基本假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社会始终处在不断更新演化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处在简单和复杂的社会形态当中的文化,是相互平行的,都有实现进步的可能。为得出相关结论,泰勒利用西方观察家的文字记录,对来自不同社会的文化因素,如技术、家庭、经济、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进行比较。由于一神教占据当时西方宗教的主导地位,故而泰勒做出与社会进化同步的宗教演化三段论假设也不足为奇。
当然,泰勒如能多活100年,亲眼目睹这场20世纪60年代的“新时代运动”得到英美社会中上层人士追捧的情形,定会惊叹不已。被泰勒认为是最为“原始” 和简朴的万物有灵论,恰恰是当今“新时代”追随者们最重要的信条之一。万物有灵论不但没有作古,而且还成为当今力争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各类环保组织的精神源泉。此外某些泛灵崇拜的信仰特征在当今仍然存在,比如说,人们相信天使的存在和亡灵的探视,以及“新时代运动”宗教仪式中水晶球的使用等等。*Martin D.Stringer,“Rethinking Animism:Thoughts from the Infancy of Our Discipline”,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no.5,1999,pp.541~556.
另一位在宗教人类学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华勒斯 (Wallace),他曾对人类社会的主要宗教类型作了如下划分:与采集渔猎社会相适应的萨满教、与部落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氏族公社型宗教、符合酋长领地社会特征的奥林匹斯多神崇拜,以及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以教堂组织为核心的一神教。*A.F.C.Wallace,Religion:An Anthropological View,New York:McGraw-Hill,1966.他在划分宗教类型时,使用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拜神” (cult) 概念。在他看来,“拜神”不一定是那种围绕某一拜神首领的怪异且难以持久的信仰形式。他修正的“拜神” 概念,泛指任何与控制或者崇拜超自然力量有关的信仰实践体系。这些有组织的信仰体系,具有治病祛邪和求雨消灾等各种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华勒斯的宗教类型划分,是在一种新进化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且其思考方式,仍然是通过技术发展的成熟度与宗教崇拜形式复杂程度的相关性展开的。此外,华勒斯对于特定历史和政治条件下宗教复兴运动发生的研究,也未必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时代运动”多源头和多元的文化表现特征。*A.F.C.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8,no.2,1956,pp.264~281.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很难依靠泰勒和华勒斯这两位不同时期的宗教人类学理论大家的洞见,来全面理解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催生出的这场史无前例“新时代运动”的复杂动因、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首先,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时代运动”,其首要特征就是摈弃以教堂为中心的一神教组织模式。而且从一开始,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鼓动者,都是英美主流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其中不乏影星麦克莲恩、克鲁斯和前甲壳虫乐队主唱歌手哈里森这样的名人。更有意思的是,像万物有灵论和风水这类理应被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潮流湮灭的词汇,早已成为充分显现“新时代运动”标志的典范性语言符号。
二、“新时代运动”有何新意?
在宗教社会学的视域内,“新时代运动”一般可被归入“世界肯定运动”(world affirming movement) 的范畴,其涵盖面极为宽泛,涉及当今盛行欧美的多元信仰系统、宗教实践和生活方式。其内容之繁杂,包括所谓异教或非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传导,如克尔特占卜术、美国印第安土著信仰,以及萨满等源自亚洲的神秘主义信仰、风水话语体系和禅宗冥思等等。对于后工业化时期西方世界中那些内心渴望获得灵性感召、努力探寻不同于传统说教的生活方向,并且对正统宗教失去兴趣的人们来说,“新时代运动”以其兼收并蓄的容量,提供了其求之不得的精神食粮,并由此构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产业。
由于“新时代”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不断使用,容易产生歧义。为此,宗教学专家希勒斯(Paul Heelas)在其学术撰述中特别强调“新时代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深刻影响。他指出:“新时代” 之所以“新”,是因为接受这一精神信仰形式的人数,在过去的30年中日益增加,而未必是其精神教义有何新意。其次是“新时代运动”中的“运动”一词,也会让人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等同起来。严格地说,“新时代运动”并不是一个有组织和行政协调中心的实体。众多“新时代运动”的信徒和追随者甚至还不愿被贴上“新时代”的标签。在英国,“新时代运动”常常与“新时代旅行者”所提倡的另类生活方式混为一谈,完全忽视了此运动旨在强调个人精神追求的要义。*Paul Heelas,The New Age Movement:Religion,Culture,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Post 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6,p.16.因而希勒斯在书中勾勒出了“新时代运动”作为对精神需求的反应所具有的三大基本特征:首先,“新时代运动”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解释,而不是告诫人们应该如此生活和对待生命;其次,它告诉人们如何追求完美的境界,并提供获得拯救的手段。*Paul Heelas,The New Age Movement:Religion,Culture,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Post 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6,p.18.在现今的英美社会,“新时代运动”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经济”模式,已成为一个蓬勃的文化产业。各类以帮助人们体会、感悟和发现他们真正精神潜质和力量的冥想团体、超验展示活动、灵性或者精神性研讨会以及训练班层出不穷。
对美国当代社会史略有知晓的人都知道,1965年美国移民法废除了有关优先考虑原籍欧洲居民移民申请的条款。这一对所有申请人一视同仁的新移民政策修订实施之后,客 观上使新美国人的来源变得更为丰富,也为催生多元文化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历过包括贵格教、震教、基督降临教和摩门教等宗教运动的冲击。而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体现平等原则的移民法之后,来自亚洲的移民数量激增。在亚洲新移民中,不乏各类善于指点不同于基督和犹太宗教路径的精神导师。他们带来的鼓励信仰探索和实验的开放态度,与年轻一代人中的反战情绪遥相呼应,也使得这一在美国乃至西方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新时代运动”,有了相当的受众基础和传播土壤。
借助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出:通过涵化和融合多种信仰文化而出现的“新时代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在后工业化发达社会中出现的某种“宗教合成主义”(religious syncretism) 现象。“新时代运动”就其显露的宗教性而言,的确非同寻常。虽然文化形态的借鉴模仿和对于(输入地)特定语境中的社会道德要求的适应性,向来就是世界范围内任何宗教传播的特点,然而在已知的绝大多数宗教信仰体系中,从领袖和权威到普通信徒,无一不把维护宗教传统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条。而“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恰恰是最不把教条放在眼里的。他们倾向于怀疑和否定那些被神学家说得头头是道的宗教教义价值。在“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看来,人们在宗教实践中,应该选择最适合自身情况的精神信仰,并且摈弃来自于已经建立宗教秩序内的权威话语。也就是说要实践“新时代运动”的理 念,其参与者就得遵从自身灵感的召唤,聆听发自内心的声音,在信仰方面选择正确的实践方式。正如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屈顺天(James L. Watson) 所指出的,这种注重“做法正确” 的人生观(orthopraxy)与注重“思想正确” (orthodoxy)的人生观,对于理解繁复的宗教实践并且获取宝贵的洞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James L.Watson,“Orthopraxy Revisited”,Modern China,vol.33,2007,pp.154~158.
在北美,“新时代运动”的影响随处可见,但本身的凝聚力不强,所以多数宗教社会学者觉得很难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因而人类学家布朗(Michael Brown)费时多年,对“新时代精神性”(New Age Spirituality)和“另类灵性”进行的民族志考察,就显得弥足珍贵。布朗的研究聚焦于一种被称之为“渠道沟通”与灵媒接触的方式,即利用经过变化的意识状态来“体验从其他时间维度和向度捕捉到的精神能量”。*Michael Brown,The Channeling Zone:American Spirituality in an Anxious 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viii.他所关注的这些“渠道沟通者”,相信自己能运用经过改变的意识状态来连接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可以从集体无意识,甚至于植物、异度空间或者某一历史时期获得。*Michael Brown,The Channeling Zone:American Spirituality in an Anxious 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从1990到1995年,布朗以参与观察者身份来仔细揣摩和研读的“渠道沟通”,可以说是新时代灵性中最受误解的一种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多将这些声称能通灵的信徒视为有怪癖的江湖骗子。福音基督徒们则认为,所谓“渠道沟通”,就是在与撒旦魔鬼做交易。但数以千计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完全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与灵性世界的沟通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在布朗看来,通灵介于宗教与疗法之间,包含来世再生、正面思维的力量、整体论、激进相对主义和自我扩展等方面的内容。他的研究综合了多种手段,包括:亲自参加专业通灵者组织的工作坊、讲座、非正式的家庭讨论会和服务活动;对40名通灵者和收到通灵信息者的访谈;对与通灵相关的文献回顾。布朗尤其关注“新时代运动”思想与实践、19世纪唯心论和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布朗不无惊奇地发现,通灵这一非主流的现象虽然怪异奇特,其实蕴含着在北美当地(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的诸多元素,如个人主义、自我完善、个体复苏和以女性为主体的灵性,它是美国宗教历史发展的一条平行线。也就是说,信徒们的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将不同的文化因子进行组合,由此获得足够的精神内聚力和慰籍力,以适应这一令人焦虑紧张的时代。*Michael Brown,The Channeling Zone:American Spirituality in an Anxious 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三、“新时代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条件下的多元信仰实践
“新时代运动”不仅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美国社会宗教生活多元化和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生动表现,也是人们在社会发生剧变之时,试图以宗教价值观来稳定和重塑文化信仰体系的一种努力。“新时代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反正统和反教条的信条。而所谓“无组织” 和“无拘无束”,或许正是这一运动的具体运作特征的最好概括。首先在“新时代运动”中涌现出的成百上千、大小不一的团体,都有不尽相同的理念,通常会以世界上某一精神传统为主要理论导向。许多团体从像藏传佛教这类东方信仰体系中寻找精神源泉。也有一些团体整合印第安土著文化,同时加入些基督教的元素。单纯从其千变万化的形式上来看,“新时代运动”的实践者们都怀有“拿来主义” 的心态,擅长从其他的、尤其是非西方的文化信仰中汲取养料。
除了宗教信仰多元化这一社会背景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语境为美国“新时代运动”的成长所创造的可供“拿来” 的丰厚文化资源。“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们都坚信,他们应该借鉴任何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信仰传统,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体验。从实践层面上说,藏传佛教不应只属于藏人,印第安仪式不应只属于印第安土著居民,风水自然也不应只属于华人世界。“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似乎无意剥夺他们肆意借用的这些古老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只是认定,在个人精神修炼层面的扩展,是不受国家疆界束缚的。从这一点来说,“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是在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个跨国宗教文化传播者和非西方文化的消费者。当然这种跨文化“传教”的运作过程,不是通过在异邦他族设立类似于教堂这样的实体机构,而是用书籍、报刊、音乐、影视和因特网等构筑的文化空间实现的。我们有理由预见,“新时代运动”参与者们将成为非西方源头的信仰元素,借全球化之力向美国宗教生活领域扩展的一支有生力量。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变迁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传播和涵化。简单地说,传播就是一种文化介入的过程。通过交流和接触,某种技术知识以及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从一个社会流入另一个社会。历史上,发生文化传播的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在两个力量和发展程度大致相当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互相借鉴和模仿。这种传播是对等的。比如说,在20世纪中期,美国向英国输出了摇滚乐这种新颖的流行音乐形式;而到了60年代,英国则以“披头士”乐队作为一项文化产品,推向美国(这一事件被传媒戏称为“来自英国的摇滚入侵”)。第二种传播多半发生在实力不平等的社会之间,也可以说是一个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充满暴力和血腥(如美国向印第安土著推行同化政策所造成的文化灭绝后果),也可以借助市场和教育等途径,以微妙的方式促销某种理念和实践模式。美国在冷战时期向第三世界派出的和平队(Peace Corps),发扬宽容和仁爱的义工精神,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扶贫帮困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普及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最后一类传播中,强势文化也会吸收弱势文化的某些形态。比如说,殖民时期印度文化,对英国上层社会的消费方式和东方艺术品位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以掠夺为基础的文化帝国主义。伦敦塔内价值连城的印度珠宝和大英博物馆内取自古代埃及和中国的文物,便是这种不对等文化传播的最好例证。
一般来说,任何类型的文化传播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涵化(acculturation) ,即某种文化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变化。彻底的涵化,便是一种文化被完全同化之后失去原有特征。“新时代运动”的存在和壮大,使笔者看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涵化过程。“新时代运动”所显现的宗教文化传播路径,已不是从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以美国为代表) 向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扩散,*I.M.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而是具有多元和多源特征的信仰和学说,籍全球化之力,渗入北美社会,并对包括宗教实践在内的精神生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信仰传播的路径不一定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向边缘扩散。一些源于非西方文明社会的宗教信仰,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多元文化的相融合借鉴过程中,渐渐地为北美社会中上阶层的社会精英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源泉。
来自古代中国的风水文化,在英语世界被重新“发现”, 在新的非东方语境中发挥其固有的对于生命意义、人与自然(生态环境) 和谐关系的阐释力量。笔者注意到:在当今北美社会,主导风水文化产业的群体,已从早期华裔移民,转向具有基督教和犹太教背景,崇尚和欣赏东方文化的族裔。这些人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信仰。风水文化体系强调微观世界中各元素相容、身心平衡,以及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居室物件和景观设计来达到个人与外部环境和平共处的思想,为生活在西方工业社会背景下的人士,提供了一种能充分体现“新时代运动” 精神的新颖信仰模式。此外,形形色色的以新时代为题材的心理咨询和文艺作品,也充斥书店和唱片店。在笔者于哈佛大学和乔治城学院进行的人类学教学中,风水文化实践也常常是讲解社会空间塑造与地方文化生态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经典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和孔子、功夫、易经一样,风水已经成为英语语言中的词汇。学习、使用和掌握风水知识,也是一些英美社会中上层人士通过吸收象征资本,在文史知识和鉴赏品味方面维持其特权地位的一种手段。*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Richard Nice,tra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四、关注“新时代运动”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运动”所展示的多元信仰实践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亟须当代学界重新检视和分析的焦点议题。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宗教—迷信二元论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研究当代西方宗教时,倾向于选择制度化、机构化的正统宗教作为合适的研究对象,而忽视或者无视非主流但弥散于日常生活的“新时代运动”信仰实践。然而,“新时代运动”这一宗教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经典案例,为我们理解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多元信仰文化的日常实践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视角。
首先,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一朵奇葩,“新时代运动”昭示着在北美等后工业化发达社会内信仰生活的显著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宗教难以摆脱世俗化的冲击影响;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于神圣和超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使宗教形式更趋多元和“另类”。*Peter L.Berger,A Rumor of Angels: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New York:Doubleday,1969.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普通美国人正在失去对超自然和超验现实的兴趣。包括美国前总统夫人南希·戴维斯·里根在内的众多名人,都依赖星相学家的占卜和建议来安排自己和配偶的公事行程和日常生活。不少航空公司也避免在客机内设置第13排座位。由于“新时代运动”的存在,也使得相信死后再生的美国人有增无减。如本文开头所述,这场产生于精神领域的信仰重构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信徒执著地接受那些非西方(非正统) “无形”和“静默”宗教的召唤和导引,从而使美国宗教文化生态环境和发展方向,更加变幻莫测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ims Bainbridge,The Future of Religion:Secularization,Revival,and Cult Formation,Berkeley,Californi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5.
其次,“新时代运动”的多源和多元特征,也将促使学者们用具全观性和接地气的文化分析方法,来取代政客学者亨廷顿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观,直面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信仰杂交和融合的客观现实。在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之重建》一书中,他重弹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陈词滥调,指出呈单线发展的“西方文明和文化”与“伊斯兰文明和文化”“印度教文明和文化”以及“儒教文明和文化”,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按照他的思路,受伊斯兰和亚洲文化观念影响的社会,因为缺乏发展公民性的民主社会、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等机制,难以发展成为能够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的文明社会。在他描绘的政治版图上,生命力旺盛的非洲和拉美大陆文明竟无一席之地。*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在人类学者看来,亨廷顿的谬误数不胜数。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在论述中将“文化”视为长期存在于某一文明中一成不变的信仰价值体系。形成于北美社会“新时代运动”中的这种多元和多源的宗教文化,在信仰实践过程中与正统基督教文化大唱反调,可以说是对亨氏学说错用“文化”概念来制造精英话语的有力反驳。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和吹鼓手,并非是被亨廷顿轻视的非洲和墨西哥少数族裔信徒,而是来自于他所认定的、能足以代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中上层人士,其中不乏像拥有白人纯正血统的汤姆·克鲁斯、雪丽麦克·莲恩、乔治· 哈里森和理查德 ·基尔这样的影视文化名人。除了明星汤姆·克鲁斯在科学教(Scientology)起主导作用之外,*参见 《赫芬顿日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5/03/24/alex-gibney-tom-cruise-scientology_n_6930660.htm,2015年3月24日。多数影视名人在“新时代运动”中没有教主的地位,但由于他(她)们在大众传媒的曝光度,其推动作用不可低估。作为“新时代运动”早期的拥戴者,仰慕中国文化的雪丽麦克·莲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好莱坞亲华派演员。*参见James W.Sire,Shirley Maclaine and the New Age Movement(Viewpoint Pamphlet),Downers Grove:Intervarsity Pr,1988.与此同时,基尔这位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在成为达赖喇嘛的挚友之后,也加入到支持“藏独”的行列中。*参见《赫芬顿日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1/10/richard-gere-gets-blessed_n_417681.html,2010年1月10日。
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两股力量的影响之下,非制度化和非机构化的各类信仰形式,从塔罗星象、风水算命、藏传佛教到灵修冥想,也在当今中国高度繁荣的市场环境中,通过五花八门的包装,渐渐成为宗教经济产业运行的催化剂。无疑,作为精神文化源头之一的“信仰中国”,*参见徐以骅等《信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2012年第1期。在“新时代运动”中将扮演输出者和吸收者的双重角色,并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模式。如何以务实的宗教观来正视这一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既熟悉而又新鲜的信仰领域的社会事实,是学界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笔者认为,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美国“新时代运动”这一案例进行认真思考和解析,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全球化时代多元信仰实践时,突破以往过度依赖文本所带来的局限性。为了在整体上把握多元语境下欧美诸国信仰实践的特点,我们应该在研究中变通地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化分析和田野观察模式,以更多的实证调查来修正可能陈旧过时的宗教观(如宗教/迷信二元论),更为从容地因应“大国崛起”语境中,信仰生活领域的种种挑战和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 陈斌)
作者简介: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研究:美国经验的启示”阶段性成果(11JJD8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