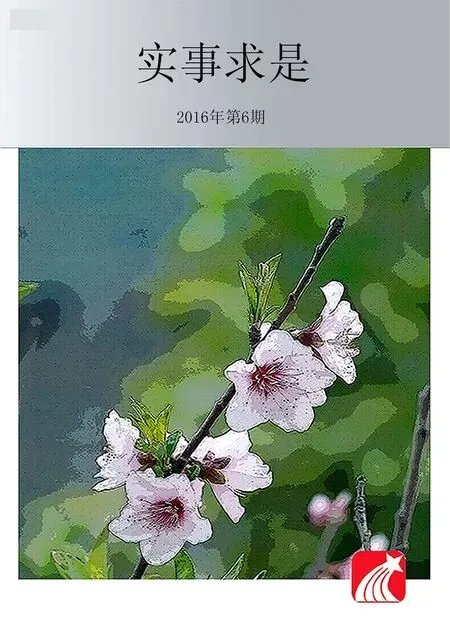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绿色发展理念探析*①
张潇潇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绿色发展理念探析*①
张潇潇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本文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向度、社会向度和人本向度为视角,思考和分析我国绿色发展问题。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生态社会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思想方面存在密切关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优势,将绿色发展与树立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努力为化解全球生态危机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生态马克思主义 绿色发展理念 关联 启示
生态危机在人类历史步入20世纪以后,警钟常鸣,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新要求之一,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面对生态危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之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对导致全球性环境恶化的根源进行反思,并寻求破解人类生态困境的主要思路与方法。[1]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绿色发展理念有着共同的生态愿景和深厚的绿色底蕴,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我国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促使我们不断发掘二者间的内在关联,为我们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思考我国绿色发展问题的新视角
绿色是发展的本色。特别是在经历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之后,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回馈自然,便成为全人类的共识。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的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强调一种整体的辩证思维范式,在追求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未来绿色社会,描述成一个具有全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社会,在这里,人类理性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实现人类全面自由的发展。本文拟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向度、社会向度和人本向度,对我国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思考。
1.自然向度。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活动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而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特斯(Foster)所指出的“自然是社会生活存在的先决和必要条件,其存在不依赖于自然的概念是否能够被清晰表达”。[2](P310)马尔库塞则指出了“被控制的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它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3](P128)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以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生态马克思主义突出人对自然的自觉协同。在某种程度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自然向度出发,以顺应自然的方式进行生态实践,防止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基本旨要,为我们推进绿色发展,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思路。这种思路着力改变的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着力避免的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所着力推动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2.社会向度。从社会向度思考绿色发展问题,是对自然向度的社会性思考。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而是与人类的社会历史相联系,是在社会历史中进行的活动。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人们生态实践活动的指导理念,必然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正如福斯特所说:“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价值结合是理解生态问题的唯一方法。”[2](P310)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物质需求,就要通过劳动把存在于自然中的物质资源转化成符合某种具体需求的社会财富,意味着人类不得不通过劳动满足和保障其客观需求。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视域下的社会活动,而这种社会活动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4](PP235~239)这样,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其社会性产生于客观的自然活动和需要。提出从社会向度思考绿色发展问题,决不是对人类客观的自然活动和需要的否定,而是告诉我们,维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关系的优化行动和协调统一,必须在解决人们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的自在运行之间的深层矛盾方面,突出社会利益的首要地位,实现现代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在生态活动中坚持把社会益效放在首位,人类才会在社会活动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3.人本向度。关于人类社会的共生,马克思已经指出了其本质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作为其生存状态是一种共同的存在,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5](P241)生态马克思主义则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出发,在发展中强调人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以保证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是其从人本向度思考绿色发展问题的基本内涵,并将生产劳动定义为这样一种活动:“作为主体的人运用工具(劳动资料)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作为客体的自然(劳动对象),把作为自己的本质的各种力量(劳动力)对象化,把自然变成人的自然,生产劳动产品,由此在变革自己的同时实现自我。”[5](P107)在人的视域里,保护环境和建设良好的生态根本出发点在于人的生态需要。这种生态需要是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满足生态环境的需要的前提下实现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换言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是衡量绿色发展的尺度。从人本角度思考绿色发展问题,目的是要改变人类生存现状,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通过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的发展、人的生态意识推动了我国生态实践的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也成为绿色发展的最终归宿。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必然要在人与自然的发展那里得到回应。人们在通过改变自然,创造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把人的本质对象化,人也获得了自我改变和自我发展,这种积极的回应也是绿色发展理念所追求与向往的,即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人本向度思考绿色发展问题所追求的价值理想。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流派,其本身就具有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一般关联。按照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意蕴,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存在未真正相互适应的薄弱环节。绿色发展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利用生态学的思维范式,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超越。绿色发展理念所追求的价值立场、所期待的社会愿景及实现的发展方式,内在地同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切合。
1.与“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关联。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发掘,主要体现在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对自然的支配”主张的解读。绿色发展理念在“对自然的支配”价值立场上重申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以符合生态需要的方式来改造外部自然,而不是回归纯粹自然形成的生态状况,不是坚持绿色发展同人对自然的改造相对立,其基本要求是在人改造外部自然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能破坏、恶化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使其更加符合人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在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时实现绿色发展理念与人对自然的改造相统一。
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总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弱”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类是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6](P41)但这并不是指人类不惜一切代价地向自然索取,不是“一种把
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6](P41)在佩珀看来,要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求按照有利于人类整体在自然界中持久生存和发展的目标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对待自然的狂妄自大态度和肆意掠夺行为。在这里,戴维·佩珀所指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6](P340)佩珀的这一观点,同绿色发展理念人对自然的改造应该符合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内涵规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绿色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实质剑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5](P251)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方,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但作为自然界中极小的一部分,人是无法彻底控制自然的,甚至连人活动的产物——人化自然也无法彻底控制。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的时候,不能仅仅从实用的角度进行生产活动,还应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控制”角度出发,考虑它们对人和自然的影响。[5](P252)当然,对自然的支配也绝不意味着可以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然。[7]可以说,绿色发展理念既不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生态意义上的人本主义”,[8](P166)是一种希望通过“支配”自然来实现生产力的增长,以保障所有人的物质福利的绿色理念。为此,对自然进行改造时,要考虑到我们“支配”自然这一行为的后果。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统治”(Mastery)和“支配”(Domination)进行详细的区分,他们只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不同于人对自然的“支配”,前者暗含征服和破坏,后者则是“人道地占有”。[6](P339)但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则应更多地按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观念来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更多地考虑人类活动可能给自然带来的后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进行生态建设,实际上不仅是要求终止继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在环境、资源可以承受的前提下,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按“美的法则”重新改造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使之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
在福特斯看来,唯物主义也有“支配自然”的主张,但“很明显,或者应该很明显的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2](P24)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关于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启示人们把价值观从人类中心或者生态中心转向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来,最终使人类的价值得到有效和可持续的保护。
2.与生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可能性在中国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我们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思想,不断探索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对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生态层面现代化的实现也制定了更高的标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北欧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一理论无法超越其社会制度的弊端,也验证了生态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具有生态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列·高兹在《政治生态学》一书中就多次提出要对社会主义进行生态重建①,即“走一条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9](P17)当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著名学者萨拉·萨卡同样认为只有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生态环境危机。不仅如此,他还勾画出一幅“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的蓝图——社会主义社会,并指明“这一次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10]像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萨拉·萨卡表明,问题不是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如何保护它”。[11]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在“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成功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保护这个世界”。[11]此外,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诘难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学家奥康纳点明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说“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已就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能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媒人,或者更谨慎地来讲,如果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可以说,某种婚约关系已开始了。”[12](P432)寻求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在生态社会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成为解决生态冲突的有效途径。然而,绿色发展理念在摒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弊端的基础上,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与制度上对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扬弃与超越;另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积极为生态现代化谋求新的出路。我们党所关心的本来就是物质与社会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社会主义下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可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社会主义因素,只是说中国的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更符合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内在的契合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就是生态社会主义。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任务,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这期间我们党所取得的一系列绿色理论成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与生态社会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差别。
3.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思想的关联。绿色发展理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情,坚持可持续发展”。[13](P134)特别是在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后,绿色发展理念所追求的实现自然的内在价值,并通过使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而实现这一目标,便显得尤为重要。人类由于自身的渺小,除了拥有能够表达自我存在的事物之外,并不能够拥有地球或者自然。人在从自然中获取生存、创造、享受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过程中对自然进行改造,但其对自然的使用必须使人与自然的平衡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的两极。但是,绿色发展理念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两极,并不对立,是新陈代谢平衡且相互依存的两极。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明确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其限度内开发”,[14](P136)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平衡的维持与调节。在坚持促进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是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掘最直接的体现。同样,在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导致结构性、富有成效的环境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的,[15](P83)故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奥康纳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界定“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个问题时,“可持续性”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态的和经济的问题。[12](P375)他不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过时,还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本质关系,从中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特斯同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方面扭曲了它的自然内涵方面”,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依据福特斯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16](P127)在福特斯那里,资本主义制度与合理农业间的矛盾只有由联合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来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才能够解决,[16](P120)即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同绿色发展理念的又一契合。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我们应该坚持一个怎样的立场?通过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自然历史、自然过程与自然周期的了解,以及获得能够改变世界的社会力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在利用科学与技术增加财富积累的同时,往往也享受着维持良好生存条件的特权。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为追求利润而无止境地破坏自然环境,是资本的本性,这一点可从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得到充分证实。因此,也只有在与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资本逻辑进行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因此,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所言“我们必须在代际公正(Intergeneration Equity)③原理的基础上,为未来后代保全地球的自然环境(生态系),同时,最终必须改变环境掠夺型生产及支撑这种生产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5](P53)
三、结论及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绿色发展理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过程中,将生态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重构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生产的无限性和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指导,正确对待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借鉴其中合理的、先进的要素,为我国化解生态危机,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选择。
1.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优势。生态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它是北美学者将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种理论尝试。[17](P15)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建构生产力的方式进行批判,也在实践中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进行批判。在政治层
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分为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一个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生态环境的问题首先视为是一种由社会弱势阶级或群体来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和加重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主宰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消除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才能够最终构建未来绿色社会。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消除贫困、捍卫公平与正义、追求人类根本利益等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当下社会主义运动仍旧处于低潮,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终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依然坚定。他们从理论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解决的不可行性,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18]具体而言,他们将绿色发展认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语境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根除生态危机的钥匙。从理论上对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中国人民给予了鼓舞与启示。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和优势来提高我们的生态理论水平和生态治理能力,为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对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制度优势,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和生态现实的基础,找到真正能够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生态发展问题的实践方式。
2.坚持绿色发展与树立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属于核心价值观问题,[18]是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生的灵魂问题。在他们看来,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发展、建成生态文明,取决于人们核心价值观的转变。从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出发,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对生态危机的化解。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揭示人类行为所带来的生态后果和与此相伴而生的人类福祉,是如何与当代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结构与特征相联系——生态系统的崩溃同人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退化是成正相关的。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最终化解,都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对人类核心价值观进行分析与修正,构建新的生态伦理、树立绿色价值观念,以正确的思想理念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同人们的生态诉求相统一。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有着悠久的历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国人“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也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19](P46)这种天人关系一直成为中国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部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当代解读,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时代精神的绿色重构,即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融入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而在人类与生态危机的战斗中实现一场思想革命。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梦想的追求,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的认识,[18]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进行新的诠释,不断反思与修正现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呼唤出从古至今存于人们内心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与渴求,并通过将核心价值观中的生态意识外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找到真正走出生态困境的道路。
3.努力为化解全球生态危机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生态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与自然共生与发展问题的关注,以及迫切解决生态危机的政治诉求。然而,生态危机在各个国家的程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一些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变化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不发达国家对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及后果却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20](PP621~646)中国作为大国为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党大力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生态危机所作出的正面回应。正如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1]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采取控制资源消耗的方式来保护环境,不论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如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可取且值得继续下去的。然而,由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却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以不可持续消费为代价的发达国家里。许多控制资源消耗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生态危机带给它们的困扰。毫无疑问,人与自然是否能够可持续地和谐相处下去,从根本上是与资源的消耗分不开
的。为了化解生态危机,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密集型的国家,必须将应对生态危机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减少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生产活动上。不幸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更注重于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环境,它们对外拓展和扩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生态危机的恶化,从而威胁到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态安全。对此,我们党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方面承担了其应尽的责任。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反映出我们党对本国环境问题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舟共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姿态。简言之,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应该理性地承担起保护生态,拯救地球的责任,利用自身优势来降低环境的消耗,减少全球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20](PP621~646)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诚如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于中国这个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国来说,“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21]是其应尽的使命。
综上所述,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里,无论是奥康纳、高兹、佩珀等人的主流阵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萨卡的非主流阵营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都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对我们如何选择人类发展道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启发,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共鸣。
[注释]
①所谓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是指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消费进行彻底的改造,参见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②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私有制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和社会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
③代际公正是指人类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对利益的享有也应保持公平,当代人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对后代人负责。
[1]石磊,赵宇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学内涵——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解读[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02).
[2]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
[3][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Yang Xingying,Sun Daojin:Unity of“Done”and “Undone”:Marxist Ecological Methodology,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Vol.10,No.6,2014.
[5][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6][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瑞尼尔·格仑德曼.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生态挑战[J].刘魁,张苏强,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2).
[8]刘增惠.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Andre Gorz,translated by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Ecology as Politics,South End Press,Boston,1980.
[10]Saral Sarkar,Eco-Capitalism:Can It Work?,03 June, 2014,Countercurrents.org.
[11]萨拉·萨卡.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可持续社会的路径选择[J].郇庆治,译.绿叶,2008(06).
[1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14]日本科学工作者会议编.向全球环境首脑会议的建议[M].东京:青木书店,1992.
[15]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6]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特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7]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8]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思考[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1(00).
[19]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0]Andrew K.Jorgenson,Brett Clark,“The Economy, Military,and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 Panel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1975-2000”,Social Problems,Vol.56, Issue 4.
[2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201/ c1024-27873625.html,2015-12-01.
责任编辑:李月明
F062.2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6.06.05
①*本文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才启动经费项目“社区自组织与生态治理场域建构耦合研究”(22431415010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