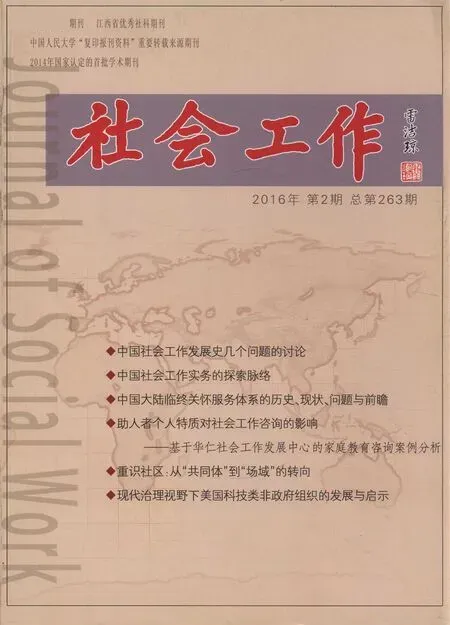重识社区: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
刘江
重识社区: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
刘江
摘要:社区结构随着社会变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么社区的内涵也随之变化和变迁,在结构多样的社区场景中重新认识社区内涵,是社区社会工作必须回应的议题。从静态视角看,本文通过对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社区解放论和类型学的对比分析发现,学术界对社区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地域性社区”到“脱域的社区”,再到地域性社区与脱域社区共同存在的发展路径。其中,分解法的类型学为研究者认识城市社区类型多样性特征提供了有效工具。从动态视角看,社区场域理论能有效回应社区多样性的特征,并从社区内各行动主体共同价值和紧密团结的社区网络入手指导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共同体城市社区城市社区社会工作
刘江,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候选人(上海200433)。
一、引言
城市社区承担了我国城市基层建设(或者基层治理)的重任。有学者提出疑问: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以社区作为载体对社区做了丰富研究,以及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为何城市社区建设效果仍不显著?桂勇(2005)认为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基本前提的错误。在当前城市社区中并不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总量及亲密感等消亡,而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结构与关系结构发生变化(Welman,1979;桂勇,2005)。这个回答的本质实际上在质疑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对社区本质的理解。如果城市社区问题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结构与关系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这种变化的结构呢?这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厘清社区本质内涵(本体)是什么。
为厘清社区本质内涵,本文从以下三个策略展开分析:第一,对共同体与社区内涵进行分析;第二,分析静态视角下的社区理论(包括社区消亡论、社区继存论、社区解放论、分解法的社区类型学);第三,分析动态视角下的社区理论(社区场域理论)。通过上述三个策略,本文发现,学术界对社区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本文认为,在当前人际互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分解法的社区类型学作为认识和分析社区的工具;使用社区场域论用于指导和建设类型多样的城市社区。
二、共同体、社区的内涵
对社区的认识无法避免对共同体概念的梳理。有关“共同体”与“社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国内有学者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认为,“社区”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德文Gemeinschaft,到英文community,再到中文社区的演变路径,社区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其内涵及外延都有扩展和延伸(陈美萍,2009;李晓非,2012)。
(一)共同体的内涵
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共同体)与Gesellschaft(社会)两个概念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当时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联结方式的变化。共同体(Gemeinschaft)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务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滕尼斯,1999),在共同体内起支配作用的是“本质意志”。实际上,滕尼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社会联系或社会结合的纽带的性质及其变迁(王小章,2002)。
正如滕尼斯(1999)所言“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可见滕尼斯是从人际关系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共同体,本质上它是一种同质性很强的熟人社会(周建国,2009)。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连结人们的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纽带,人们基于情感动机形成了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张俊浦、李朝,2008)。
综上,滕尼斯的共同体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中包含“情感”、“信任”、“认同感”、“亲密感”、“共同精神”等(冯钢,2002;胡鸿保、姜振华,2002;张云昊,2005;刘玉东,2011)。这同时也表明,滕尼斯的共同体自带强烈的价值和伦理意蕴(于海,2001)。
(二)社区的内涵
社会工作学术领域常用的概念是“社区”而非“共同体”,那么,如何认识和界定社区呢?社区的定义纷繁多样,美国学者Hillery(1955)收集了94种社区定义,并通过归纳法提炼出社区的三个本质内涵。他通过对94个社区定义的分歧(disagreement)与共性(agreement)的分析认为:在94个定义中,有64个定义认为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地域(area)、共同的联结(common ties)是社区的本质;有3/ 4的定义认为地域(area)、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社区的本质;同时,如果不考虑地域因素,社会互动和共同的连结二者作为社区本质特征的重要性将会增强。由此,他最终确定了社区的三个本质特征:地域、社会互动、共同的连结。虽然有学者认为社区的本质不仅仅只包含上述三个特征,但是Hillery认为上述三个本质特征是对社区界定的最低要求(at least permissible)。Hillery对社区本质内涵的归纳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对社区的认识。
Popple(1995)认为社区不仅带有地域与实体的意义,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与情感。Sanders (1975)认为社区包含三个层面:(1)侧重地理或结构的概念,指社区是一群居民共同生活的地区;(2)侧重心理或互动的概念,指社区是居民生活中互相关联与依赖的共同体;(3)侧重行动或功能的概念,指社区是居民互相保卫与共谋福利的集体行动。徐震(1980)在Sanders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应该包括地理、行动与心理三个特征,并指出社区以地理的社区为基础、以行动的社区为方法、以心理社区为目标。陶蕃瀛(1994)认为社区是一种地理空间单元、一种社会关系网、一种集体认同单元。
根据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社区的界定以地域为基础。社区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地域、以及具有共同体特征的社会联系。在上述概念界定中,社区的地域特征和共同体特征融为一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区可以被视为“地域性共同体”。
(三)共同体与地域的分异
前述有关社区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将社区的地域性和共同体特征融合为一体,并认为二者边界重合。这种基于“社群性”和“地域性”的社区观点在后来的社区研究中(尤其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扮演着绝对主流的角色。那么,地域性和共同体特征二者边界是否重合呢?
李易骏(2012)认为,在共同关系、认同、空间(地域)三者间,共同关系与认同较空间更不易被外人所发掘、也不易为外人所直接观察。因而不少人对社区概念的界定,是以空间为第一个元素面向,以可见的空间范围作为划分空间的界限。除此之外,学术传统上受到区位论的影响,实践中受到政府行政管理的影响都是将共同体与地域绑定在一起的重要原因。由于共同体和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区与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之间经常出现混淆。
事实上,这种强调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情感的观点在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界定中就已存在。在滕尼斯的界定中,社区与地方似乎并没有对等起来,他区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家庭、村落和宗教等形式。此时,空间的接近对于共同团体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似乎并不是必需的(郑中玉,2012)。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接近”。“空间”的重要性在滕尼斯那里似乎更多体现为有助于人们“相互习惯”、“熟悉”,形成“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也就是所谓的“默认一致”。“默认一致”是社区的内在本质最简单的表示。在滕尼斯看来,似乎“空间的接近”最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精神上的接近”而已。而“精神共同体”是“人的真正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因此,社区可能不再局限于“空间的接近”这个地理学的条件上。
Konig认为,社区作为强调用于居住的地域性的社区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已经相去甚远。“共同体”意指那些有共同点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当“共同体”被翻译为“社区”时,滕尼斯的共同体被加上了空间的特征(转引自James A. Christenson,1984)。如果滕尼斯的“共同体”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联系而不是大小不同的地域,那么即便是改变地域也不必然意味着改变“共同体”。
综合上述观点,共同体并不必然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经典界定中本身就暗涵了“脱域”的特征。这种“脱域”的特征为对社区的理解从“地域共同体”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此外,从共同体和社区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联系)这点出发,可以看出,社区/共同体内涵中从一开始就蕴含“关系”(或联系)视角,这点在有关社区/共同体相关理论的发展中会越来越明晰。后文将从与社区有关的不同理论梳理出能够融合地域与脱域分歧、并包含关系的社区理论。
三、城市社区:静态的视角
有关城市社区性质的经验研究开始于19世纪,产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转变了工业革命以前的人际关系、群体及组织模式,形成了高密度、异质性强、人口众多的城市生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城市社区的居民关系以及社区结构形态不断发生改变。西方有关现代化对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共同情感及邻里关系的影响展开了诸多研究,主要形成两类不同的理论倾向:一类是针对地域性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逐渐衰落而形成的“社区消亡论”与“社区继存论”;另外一类是针对城市居民超越地域限制进行社会互动而产生的“社区继存论”和“分解法的社区类型学”。
(一)社区消亡论:地域社区的消亡
社区消亡论可以追溯到滕尼斯、涂尔干、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和沃斯等人的相关研究。社区消亡论是最先对滕尼斯有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类进行回应的理论。社区消亡论强调,城市社会劳动力分工削弱了共同体的团结(Wellman,1979);城市里的初级社会关系变得“个体化、短暂且碎片化”(Wirth,1938)。城市居民不再被整合进单一的团结一致的共同体内,而成为不同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城市居民通过次级社会网络与城市联系(Wellman,1979)。
社区消亡论强调城市化对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改变,摧毁了城市社会中共同体社区存在的基础。在具体分析方法上,沃思等人提出了许多关于城市现代性的观点和证据,他们认为按照滕尼斯“共同体——社会”二分类的方法,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不复存在。它是对滕尼斯“共同体”内涵在现代化城市中的直接检验。
该理论得出社区消亡的观点,是因为它提前预设了城市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应该是紧密的、凝聚力强的以及地域性的。在经验分析过程中,当经验世界中观测到的现象与其对城市社区的预设相违背时,就断定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消亡。实际上,正如Wellman(1979)所言,该理论忽视了初级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在结构上发生变化,而不是在城市社会中消亡。
(二)社区继存论:地域社区继续存在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奥斯卡·刘易斯对“社区消亡论”发出质疑,并从经验层面给予回应。社区继存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人口集中本身并不会产生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或人格,如果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必然是由其它原因如社区或人们本身的某些特质(比如,城市居民的社会阶级、种族背景、家庭结构、文化性质、性别以及人生阶段等)而引起,绝不仅源于人口集中。费舍尔(1975)提出了所谓的“亚文化”。“亚文化”是指一群具有很多相似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的人,经过长期的相处,逐渐形成一种彼此了解并相互接受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亚文化”的特点是,处于同一个“亚文化”的人更容易在情感上、心理上形成共鸣,彼此认同,并提供相互帮助与支持。
虽然社区继存论验证了城市社区继续存在,但是它并没有针对社区消亡论的理论前提(即劳动力分工严重影响了初级社会联系的结构)进行批评。由于它关注的只是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等共同团结是否存在,而没有分析团结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位置(Wellman,1979),因此,它并不能从根源上驳斥社区消亡论。当社区消亡论把研究对象聚焦于城市中不同类型的亚群体时,它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城市化过程中某种特殊生活方式(比如城中村)存在的可能。虽然社区继存论没有从“共同体——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城市社区,但是,它却进入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即对城市社区局部文化(亚文化)的研究。因此,城市社区转变成各种亚文化群体。
(三)社区解放论:作为网络的社区
社区解放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持社区解放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滕尼斯的理论在其核心观点上是同义反复的,大多数滕尼斯的传统观点被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标准来评价,这种评价处于道德层次上的评价,它并不适用于经验研究(John D. Kasard & Morris Janowitz,1974)。Wellman(1979)总结认为,以往的研究把地域界限作为研究的起点,进而探讨地域界限内共同体互动和情感亲密程度。如果地域范围内找不到亲密情感,那么社区就消失。他断言预先设定城市社区是“情感团结”的方法混淆了社会互动类型的研究,社会学研究关注点应该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联系,而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不将群体或邻里边界作为真实的社会边界,它认为研究社区的重点在于研究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亲密关系,这些内容构成了个体的“个人社区”或“私人社区”(陈福平、黎熙元2008)。基于此,社区研究强调的是对社区结构的研究,而不是研究地域性社区,也不是研究社区内部是否保存共同体的特征。其研究视角实际上从以往对邻里、亲密关系和地域性社区生活等传统研究范畴转移到对个体的社会关系与网络的探讨中,社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关系网络构成的“社区”。
社区解放论的一大贡献在于它通过网络分析将关注焦点从地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并将焦点放在社会的结构位置上进行衡量,进而实现脱域社区与地域社区可以同时进行分析的目的。但是它对个人网络的强调又导致其忽略了地域空间的作用。Wellman(1988)自己也认为“把个人网络当作社区问题忽略了人们在其居住于社会空间中必须面对的生态学设置”。因此,过分强调网络可能导致其滑向另一个极端。
根据前面三个理论的论述和分析可知,这三种理论观点的核心在于讨论社区的地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陈福平、黎熙元,2008)。社区消亡论和社区解放论强调社区的地域性,但是忽略了社会网络。社区解放论强调社会网络来界定社区,但是忽略社区的地域特征。它们都不利于我们有效认识当前社会互动结构多变的社区现状。后文将从类型学角度论述既能分析脱域社区,又能分析地域社区的方法。
(四)类型学:一个整合的视角
从类型划分的角度看,滕尼斯有关“社会”和“社区/共同体”分类的突破在于他从以往有关农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关注中分离出来,将这些生活方式从他们熟悉的空间中分离出来,并且尝试辨别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Steven Brint,2001)。但是,滕尼斯有关“社会”和“社区/共同体”的分类并非基于社区的决定性要素,而是基于大量公共关系的对比联想。这种方法的结果导致分类抽象程度高,可操作性不强。Steven Brint(2001)认为,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形成的方法代表了社区概念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即聚合法(aggregate approach),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而另外一种更加适合当代社区分类的方法是分解法(disaggregate approach)。
分解法是从与社会联系有关的变量出发展开社区类型划分。该方法使用具体化的变量使得概念的界定(或类型划分)变得具体和精确。从分解法的观点出发,Steven Brint(2001)提出了“社区通用概念”(generic concept)的术语。作为通用概念的社区主要指:社区是人的聚合,这些人分享共同的活动、信念,并通过关系的影响、忠诚、共同价值和个体议题等联系在一起。这个定义重视的是“人”和“关系”,而互动的动机是最重要的因素。在Steven Brint对社区通用概念的界定中,社区成员间的关系不一定必须是排外的或者极度频繁的。这个定义只需要这些关系建立在影响、忠诚、共享价值,或者对他人生活的共同卷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通用概念并没有对聚合、忠诚、关系等要素提前预设强度或者程度。也就是说,与滕尼斯及其他学者分类的不同点在于它没有强制规定何种类型的社区应该是什么样(比如滕尼斯的社区应该是关系亲密的共同体)。
基于以上原因,Steven Brint(2001)从四个变量(维度)出发对社区进行类型划分:第一,互动的终极背景;第二,互动的初级动机;第三,互动的频率和成员的位置;第四,面对面的互动VS通过电脑媒介的互动。通过上述四个变量的划分,得出八个不同类型的社区结构:地域社区(communities of place),亲密团体和集体(communes and collectives),地方性朋友网络(localized friendship networks),扩散的朋友网络(dispersed friendship networks),活动导向的选择性社区(activity-based elective communities),信念为导向的选择性社区(belief-based elective communities),想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
从社区类型划分的标准看,分解法下的社区类型所选用的划分标准继承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社区内涵本质达成的共识,即人的聚合、共同的活动、共同的价值以及社会联系。它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将社区的界定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从而为认识类型多样的社区提供了比较有效的工具。分解法的类型关注社区的类型,但不对各个类型做任何提前预设(也即它不提前预设社区应该是什么);它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又不逃避社区本体论的追问。它从四个维度划分出的8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中既有地域性社区,又有脱域的社区。这种分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区研究长久以来“地域”与“脱域”的非此即彼的尴尬局面。相比以前的城市社区的理论观点,这种划分更符合大众社会社区类型多样化的特点。因此,本文认为在当前大众社会中认识或者定义社区时应该从不同的变量(或维度)出发对社区类型进行划分。
四、城市社区:动态的视角
前文对四个理论的论述和分析得出,分解法的类型学是认识当前城市社区类型多样性的有效工具。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其不足),即虽然它看到了当前城市社区中人与人之间互动结构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分类将社区作为静态的客体,并等待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用不同的标准去划分。从社区社会工作重视行动取向的特点出发,用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城市社区仅仅是社区社会工作的第一步。社区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过程中应该将社区视为动态的过程,为此,笔者将从社区场域理论展开分析,为动态的社区找到理论基础。
社区场域理论把社区集体行动作为社区的存在形式,并以此展开研究。该理论指出社区是居民、群体或组织,因解决地域性公共问题和增进地域性公共利益而形成的集体行动场域。社区场域理论坚持把积极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作为社区的本质,准确地把握了现代城市社区的存在形态,为开展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
(一)社区场域的特征
社区场域理论是由美国社区研究专家考夫曼提出,并经过他的学生威尔金森的系统阐释而得以确立的社区理论。该理论从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出发,提出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群体和组织,为了解决地域性集体问题、追求地域性集体福利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场域。Wilkinson(1970)认为,社区场域由行动者、组织和行动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与传统的功能论社区理论相比,它不是把社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我维持倾向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单元,而是把社区看成一个无明确边界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它不是把社区结构视为解释的起点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视社区行动本身为社区的存在形式,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Kaufman,1959)。
考夫曼注重社区场域中的社区行动。他认为,当研究者将社区当作互动的场域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对象时,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场域内发生的社区行动(community action)和互动(与人口的、生态的、心理等情境的互动,与地方性场域及大众社会中其他互动场域的互动)(Kaufman,1959)。社区行动是社区场域内的行动者、团体、组织等通过互动实现的。
(二)社区场域的形成和动力
社区场域如何形成?社区场域的形成依赖于这样的认知,即虽然不同的社会场域因不同的利益而具有不同特征,但是,重叠的场域因为人们居住在同一地方而存在,并能够在这一地域范围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就是“社区利益”。当社区利益通过连接与合作而得到确认时,社区场域就产生,这种社区利益能够确认和增强不同社会场域的社区共同感(Jeffrey C. Bridger, A. E. Luloff,1999)。社区场域行动的目标是要在不同场域中的行动或行动者之间创造一种连结(bridging),以增强不同利益场域之间的共同性(Jeffrey C. Bridger, A.E. Luloff,1999)。因此,社区场域形成的动力在于社区共同利益。
五、结论
从前文有关社区/共同体相关理论的演变的论述可以看出,社区/共同体理论经历了从抽象的类型学,到强调网络,再到分解法的类型学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城市社区经历了消亡、继存和解放。虽然认识和分析社区本质的方法存在差异,但是,它们拥有的共同前提是大众社会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传统社区的内涵(或本质),具体而言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构。虽然几个理论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且后来者对前面的理论都有否定并发展,但是,并不应该根据几个理论所对应的线性的时间轴来定位中国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应该选用哪种理论。相反,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景选择合适的视角指引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社区到商品小区,城市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转变的特点。受到行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社区结构的复杂性增加。在分析城市社区时,要采用地方化的视角审视城市社区。对城市社区的理解应该转向分解法的类型学。要从类型更加细致的角度认识当前多样化的城市社区结构,将具有地域要求的行政社区看成不同类型的“亚”社区(或共同体)的组合来对待和分析。
与分解法类型学将城市社区视为不同类型的“亚”社区(或共同体)相呼应,社区场域理论提出的通过社区行动推动社区发展的观点具有实务指导意义。城市“社区社会工作”需要明确的是它并不等同于“在社区内工作”。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的主体是社区内的居民及各个团体(或共同体)(如物业公司、业委会、居委会、其他社区内团体),目标是解决社区内的公共议题。公共议题的解决需要社区内各类团体共同行动。根据社区场域理论的指导,在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要将社区居民个体(或团体)作为行动主体,在社区共同利益的指引下凝聚社区居民(或团体);协助居民(或团体)识别不同时点社区的特征或问题,并通过社区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社区问题、实现社区改变。
[参考文献]
[1]陈福平、黎熙元,2008,《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社会》第5期。
[2]陈美萍,2009,《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3]冯钢,2002,《现代社区何以可能》,《浙江学刊》第2期。
[4]费迪南德·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5]桂勇,2005,《城市“社区”是否可能?——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6]胡鸿保、姜振华,2002,《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学术论坛》第5期。
[7]黎熙元、陈福平,2008,《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社会学研究》第2期。
[8]李晓非,2012《拿来,改造,中国式运用——社区概念中国化的思考》,《学术探索》第9期。
[9]李易骏,2012,《当代社区工作:计划与发展实务》,台北:双叶书廊出版有限公司。
[10]刘玉东,2011,《社区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质内涵——兼论中西方释义差异之根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陶蕃瀛,1994,《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实务》,台北:五南书局。
[12]王小章、郎友兴,1995,《都市的体验: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三种理论》,《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13]王小章,2002,《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浙江学刊》第2期。
[14]徐震,1980,《社区与社区发展》,台北:中正书局。
[15]于海,2001,《三个角度看社区》,《社区》第2期。
[16]张俊浦、李朝,2008,《社区:从一个社会学概念到一种基本的分析框架》,《甘肃理论学刊》第5期。
[17]张云昊,2005,《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8]周建国,2009,《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路径选择探究》,《江西社会科学》第11期。
[19]郑中玉,2012,《个体化社会与私人社区:基于中国社区实践的批评》,《学习与实践》第6期。
[20]Bridger J C, Luloff A E. ,1999,Toward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ruralstudies,15(4).
[21]Brint S., 2001,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Sociologicaltheory,19(1).
[22]Christenson J A.,1984,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Testing the spatial and communal hypotheses. SocialForces, 63(1).
[23]Fischer C S. , 1977,Networksandplaces:Socialrelationsintheurbansetting.Free Press.
[24]Fischer C S.,1975,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25]Gans,H.,1962. TheUrbanVillagers.Free Press.
Hillery G A. , 1955,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Ruralsociology,(20).
[26]Hollingshead A B. , 1948,Communit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condition.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27]Kasarda J D, 1974, Janowitz M.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28]Kaufman H F.,1959,Towardaninteractionalconceptionofcommunity.Soc. F.,(38).
[29]Lewis O.,1952,Urbanization without breakdown: a case study. TheScientificMonthly,(75).
[30]Popple, Keith. , 1995,AnalysingCommunityWork:ItsTheoryandPractice. Bristol: Open University Press.
[31]Sanders, Irwin T.,1975,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SocialSystem(3rd).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32]Wellman B, Leighton B.,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AffairsReview,14(3).
[33]Wellman B, Wortley S. ,1990,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ofSociology.
[34]Wellman B. , 1979,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35]Wellman B.,1982,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Socialstructureandnetworkanalysis.
[36]Wellman, Barry, ed. , 1999,Networksintheglobalvillage:Lifeincontemporarycommunitie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37]Wilkinson K P.,1970The community as a social field. SocialForces,48(3).
[38]Wirth L. , 1938,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编辑/程激清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2-0084-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