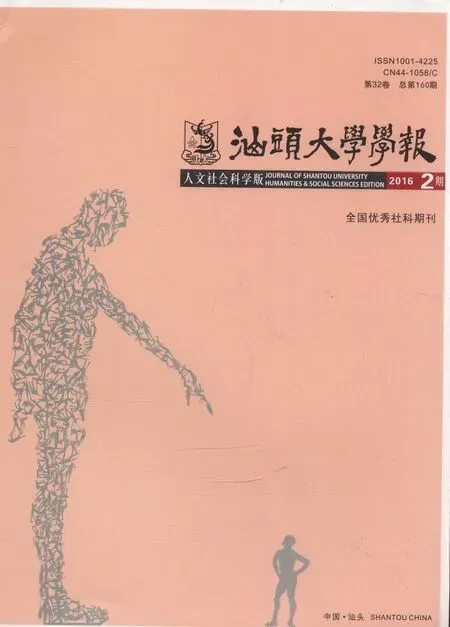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
——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杨正娟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
——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杨正娟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元杂剧的曲文在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等方面大量借鉴了抒情小赋的艺术形式;其戏剧结构、讲唱对话等则受到了俗赋的影响。同时,赋与戏剧所具有的诗性特征和共同的表达方式,又带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和共通性。《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最早的元杂剧刊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元杂剧对赋体的运用和借鉴,以及俗文学在雅文学影响和渗透下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元刊杂剧三十种》;赋体;抒情小赋;俗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中国文学的代表样式这样评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1文学样式和其创作的辉煌阶段并举的论述,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样式的不同风貌。但是,文学传统是具有继承性和借鉴性的,不同体裁之间从不是泾渭分明、各行其道,而是相互影响、吸收利用的。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的曲文描写对赋体的借鉴尤为明显,无论写景、抒情,还是叙事、状物,皆受到赋体的影响,且其艺术表现方式的讲唱性又与俗赋有着很深的渊源。本文即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对其曲文中赋体的运用进行综合考察,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动因。
现存的元杂剧传本中,最古的元杂剧集当推《元刊杂剧三十种》,它是现存唯一的元杂剧当代刊本。相较于众多明刊选集中的元杂剧,其面貌有相当的不同:其一,元刊本中的曲文大部分比明刊本数量多;其二,元刊本中大多数科白极简,有的甚至只录曲文而无科白;其三,元刊本不分折数,也不标“楔子”,每折套曲前绝少写明宫调。由此可见,明刊的元杂剧已较元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所以王国维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序》中评曰:“凡戏剧诸书,经后人写刊者,往往改易体例,增损字句。此本(指元刊本)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人秘笈矣。”[2]683孙楷第先生亦言:“学者欲究元曲秘奥,唯元刊本为可据。后人之刊元曲,于元曲从违虽有矜慎与孟浪之不同,要不能尽依原文无所更动也。”[3]421他们都认为元刊本反映了元杂剧的真面貌,这种说法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其只录曲文,宾白科介并不完整,甚至使读者无法弄清剧情。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供演唱者或票友用的“单片儿”一样的本子;或者是当时出版时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没有录入宾白,作家在写作时是有宾白和科介的。但是,借助《元刊杂剧三十种》,通过对其曲文的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元杂剧的结构、叙事和文体特征的。
一、对抒情赋的借鉴和运用
王国维对元杂剧的艺术特点这样评价:“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1]117意境,是他在《人间词话》中论词的一个术语,此处用来表述元杂剧这种叙事作品,并以写情、写景、述事三者为例,在此当指叙事作品所创设的独成一体的世界。王国维是将元杂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进行研究的,他不关注其舞台演出,并且认为其“关目拙劣”,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其曲文,这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雅文学观念。
我们可以将《元刊杂剧三十种》[4]中的作品,按照主要描写对象,分为历史剧(主要描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关张双赴西蜀梦》《关大王单刀会》《楚昭王疏者下船》《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赵氏孤儿》《东窗事犯》《霍光鬼谏》《辅成王周公摄政》《萧何月夜追韩信》和《诸葛亮博望烧屯》等;社会剧(主要描写历史人物的私人交往),包括《好酒赵元遇上皇》《薛仁贵衣锦还乡》《张鼎智勘魔合罗》《李太白贬夜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死生交范张鸡黍》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等;家庭伦理剧(描写家庭生活中的各类事件),包括《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公孙汗衫记》《张千替杀妻》和《小张屠焚儿救母》等;爱情剧(主要描写爱情故事),包括《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和《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等;道化剧(主要描写人物的度脱),包括《泰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和《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等。
纵观这三十个作品,可以看出,其题材以叙事为主,大多是描写历史战争中的某个重大事件或者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繁杂事务。但是,其曲文却包含了大量的抒情成分,或在纪事中,或在咏物中,或在写景中,这些甚至构成了作品曲文的主要内容。细观这些描写和抒情,可以发现,它们的表达方式带有很浓厚的“赋”的意味,与抒情赋的描写方式很类似。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5]134这里的赋主要指文人赋,其语言典雅,内容多体物抒情,即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而绮靡”。[6]241这类赋具有“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丈夫”[7]1756的“诵”的特点。除主流的汉大赋外,文人抒情小赋也不乏创作,并作为文人张扬个性、抒发情志的方式,在各个朝代皆有优秀作品出现。与大赋相比,抒情小赋由对外在物志的铺排转向了对自身心灵世界的描写。其语言简洁、结构短小、意象单一,多以一物一景为描写对象,触泄情思、兴发意趣。无论是纯粹咏物、即兴抒情、借物讽喻、言志明理,还是论文谈艺、园林闲适、试帖酬和、戏谑游戏,皆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审美意蕴。[8]
元杂剧融叙事、抒情于一体,“一本四折”的体制使其可以用相当的篇幅来状物抒情,且“代言体”本身的特色就是代剧中人物抒情,叙事反在其次。“末本”、“旦本”等一人主唱的体制对同一角色、不同人物的抒情又是极大的推动。因此,元杂剧在整体上表现的抒情性是其最主要的文学特征,也是王国维最为推崇之处。
《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写汉代严光拒绝刘秀邀请,甘愿隐居山林的故事。该剧人物极少,情节单纯,不像叙事作品,更像是一篇个人独白的“隐士赋”。该剧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严子陵对官场生活、荣华富贵的不屑和对隐居山林恬淡生活的满足之情。
“他子在鱼洲揽住收罾网,酒旗摇除沽村酿。畅情时酌一壶,开怀时饮几觞。知他是暮年间身死中年间丧,醉不到三万六千场。”“则咱这醉眼觑世界,不悠悠荡荡;则咱这醉眼觑日月,不来来往往;则咱这醉眼觑富贵,不劳劳攘攘!咱醉眼宽似沧海中,咱醉眼竟高似青霄上,咱醉眼不识个宇宙洪荒!”“我若烂醉在村乡,著李二公扶将,到草舍茅堂,靠瓮牖蓬窗,新苇席清凉,旧木枕边厢,袒脱下衣裳,放散诞心肠,任百事无妨,倒大来免虑忘忧,纳被蒙头,任意翻身,强如您宰相侯王,遭断没属官象牙床,泥金炕。”“我把这缦笠做交游,蓑衣为伴侣。这缦笠避了些冷露寒烟,蓑衣遮了些斜风细雨。看红鸳戏波面千层,喜白鹭顶风丝一缕。白日坐一襟芳草,晚来宿半间茅苫屋。”“巴到日暮,看天隅,见隐隐残霞三四缕。钓的这锦鳞来,满向篮中贮。正是收纶罢钓的渔夫,那的是江上晚来堪画处,抖搜着绿蓑归去。”“俺那七里滩,麋鹿衔花,野猱献果,天灯自现,乌鹊报晓。禽有禽言,兽有兽语。”[4]618-643
该剧曲文清丽流畅,语言生动,对偶、拟声词等大量运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不适和对乡间野趣生活的痴迷,明显受到了张衡《归田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抒发隐逸旨趣的田园赋影响,在写法上也多用铺排手法,一唱三叹,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为官的小心翼翼和隐居生活的恬淡自适,加以老农、渔夫等人物生活情景的点缀,呈现一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态。与叙事性的戏剧作品相比,该剧抒情意味十分浓厚,实是一篇清净淡雅的隐居赋。
与此类似的还有《李太白贬夜郎》。该剧用大量的笔墨写到了李白对酒的痴迷和酒醉后文思泉涌的才气:“酒如川,鹭鸥长聚武林源,鸳鸯不锁黄金殿,绿蓑衣带雨和烟。酒里坐,酒里眠,红蓼岸,黄芦堰,更压着金马门,琼林宴。岸边学渊明种柳,水面学太乙浮莲。”“正更阑人静也,波心中猛觑绝,见冰轮皎洁洁,手张狂脚趔趄,探身躯将丹桂折。”[4]461-462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不同,这些带有动作性的描写与赋的表现方式和审美意趣更为贴合,对喝酒情态的大肆铺排渲染,使得曲文在情感上更富感染力,在演唱上更有气势,与赋“登高而颂”的气势十分契合。
《死生交范张鸡黍》由正末饰范式,叙述自己与张劭的深厚友情,以及对张逝世的深痛悲哀。该剧多种手法并用,第三折用十六支曲子淋漓尽致展现了自己的悲痛心情,读起来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悼亡赋。“打的这匹马不剌剌的风团而驰骤,百般的抹不过山腰盼不到那地头。知他那里也故塚松楸?仰天号叫破我咽喉。那堪更树梢头阴风不住吼,荒村雪霁云收。猛听得哭声哽咽,才望见幡影飘飏,眼见的殢魄夷犹。”“疏剌剌惨人风过冷飕飕,支生生的头发似人揪。静悄悄芳魂迥野申时候,昏惨惨落日坠城头。残雪又收,寒雁下汀洲。景物正幽,村落带林丘。”“想对床风雨几春秋,只落得坟头上一杯交奠酒。从今别后,再相逢枕席上黄昏时候五更头。”“你怎听杜鹃蹄山月晓,你怎禁那蛩虫儿夜雨泣清秋,你听那寒鸦万点老树头。这几件儿终年依旧,似这般漫漫长夜几时休。”[4]602-604自己急于奔丧的心情、对对方才华和品质的由衷赞美、遥想对方地下面对的终年孤寂景物等等,加之以凄惨的环境描写,大量的叠字运用,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对老友的悼念和自己的悲痛。意象的铺陈、寓情于景的描写、反复的吟咏等赋之手法的运用正是本剧的感染力所在。
除了以上主旨更接近于赋的杂剧外,《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作品在描写或者抒情时大量运用了赋的表现方式,主要体现在叙事、写景、场面描写、刻画形象等方面。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很多作品没有科白,所以曲文兼有叙事的功能,但是这种“代言体”叙事带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纪事抒情在元杂剧中随处可见。《关张双赴西蜀梦》:“一个是急毡毡云间凤,一个是威凛凛山中兽;来时节玉蟾出东海,去时节残月下西楼;相逐着古道狂风走,赶定长江雪浪流。”[4]21《闺怨佳人拜月亭》:“分明是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恓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没盘缠,在店舍,有谁人,厮抬贴?那消疏,那凄切,生分离,厮抛撇!从相别,恁时节,音书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贴。”[4]30-48这些曲文的演唱应该是配合着角色的动作,边行边唱,在叙述行动的同时表达人物的愁苦悲戚,且用数支曲子,接连不断地反复表达这种凄苦情绪,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景物描写贯穿在元杂剧曲文的各个部分,无论是何种题材,都会有若干景物描绘,这种描绘往往寄托着人物的某种心情,或喜不自禁,或忧伤不已。《好酒赵元遇上皇》:“汤着风把柳絮迎,冒着雪把梨花拂。雪遮得千树老,风剪得万枝枯。这般风雪路途,雪迷了天涯路。风又紧,雪又扑,恰浑如杴瀽筛扬,却便似挦棉扯絮。”[4]129-130《张鼎智勘魔合罗》:“连连不住,荒郊一望水模糊。子见雨迷山岫,云闲青虚。云气重如倒悬东大海,雨势大似翻和洞庭湖。满眼无归路,黑洞洞雨迷四野,白漭漭水渰长途。”[4]414景物的描写既有夸张,又有铺排,将人物内心的忐忑、凄凉、烦闷等寄寓其中,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效果。
另外,杂剧曲文中还有一些场面、动作、景物描写,重在铺排渲染,“体物”的特征大于抒情。《公孙汗衫记》:“密布彤云,乱飘琼粉,朔风紧,一色如银,这雪交孟老骑驴稳。虽是孟冬时分,你言冬至我疑春。梨花片片,柳絮纷纷。梨花坠变为银世界,柳絮飞翻做玉乾坤。银瓶注鹅黄嫩。”[4]361用大量笔墨刻画了下雪的景观。《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焰腾腾火起红霞,黑洞洞烟飞墨云,闹垓垓火块纵横,急穰穰烟煤乱滚,悄蹙蹙火巷内潜藏,古爽爽烟峡内侧隐。烦烦的烟气熏,纷纷的火焰喷,急煎煎地火燎心焦,密匝匝烟屯合峪门。”[4]523则用了一连串的拟声词和动词来描写烧山时火势的凶猛。《小张屠焚儿救母》:“青天上云彩千重,四围有峰峦万朵。明晃晃金碧琉璃,高耸耸楼台殿阁。春昼暄,丽日和,袅春风绿柳如烟,含夜雨桃红似火。闹清明莺声宛转,荡花枝蝶翅翩跹,舞东风燕尾婆娑。”[4]789《张千替杀妻》:“杨柳晴轩,海棠深院,东风转,花柳争光,忙杀莺和燕。莎针柳线,凤城春色满娇园。红馥馥天桃喷火,绿茸茸芳香堆烟。红杏枝边斗蹴鞠,绿柳楼外打秋千。猛听的莺声恰恰,燕语喧喧,蝉声呖呖,蝶翅翩翩。我则见垂杨拂案黄金线,我则见桃花落处胭脂片。”[4]753以上分别以浓重的笔墨,从声音、色彩等方面描写了清明前后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其与剧情并无甚大联系,追求的可能是演唱时场面的热闹和丰富。
就形象刻画而言,这些戏剧往往抓住富有特征的某一场面或者某一方面、某一细节、某一过程,并加以铺排,刻画出意境,并创造出完整的形象,进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这样描写某些人小人诈富的嘴脸:“这等人夫不行孝道,妇不尽贤达,爷瞒心昧己,娘剜刺挑茶,儿焦波浪劣,女俐齿伶牙;笑穷民寒贱,羡富汉奢华;他有的驱驾,他没的频拿;挟权处追往,倚势处行踏;少一分也告状,多半钱也随衙;买官司上下,请机察钤辖。这等人忘人恩,背人义,赖人钱,坏风俗,杀风景,伤风化。倒能够肥羊法酒,异锦轻纱。”[4]162《诈妮子调风月》对小千户的嘲讽:“终生无簸箕星,指云中雁做羹。时下且口口声声,战战兢兢,袅袅停停,坐坐行行;有一日孤孤零零,冷冷清清,咽咽哽哽。”[4]111《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对人性受金钱引诱而扭曲的描写:“有你的不读书便出游,没你的不违法便下牢,你搬的世间事都颠倒,有你的不唱喏便唱喏,有你的不高傲便高傲。都是你鸦青神道。有你没你的我便猜着:使脱你的眼睛便十分怕,揣着你的胸脯增五寸高,更没差错分毫。”[4]250这些铺陈不求全求大,而是抓住某一方面的特征,以典型的事件或者环境、典型场面的铺陈,来刻画人物形象,抒怀言志。其中三字句、叠字句、排比句的运用又增加了铺陈的力度,同时显得更为平实通俗。
通过对《元刊杂剧三十种》曲文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写景、状物、叙事等都借鉴了赋的表现方法,其中尤以抒情小赋为甚,这些作品或以景物描写来渲染气氛、制造意境,烘托人物的个性形象;或以心理刻画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或以神情体态的描摹、生活习惯的铺叙、行动模样的刻画来凸显个性特征。其中又会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拟物寄意,使得曲文的抒情性更为含蓄、深邃,更有情景交融之妙,体现王国维所谓的“意境”之美。
二、俗赋影响下的戏剧结构
根据马积高①马积高《赋史》涉及《唐代的俗赋》时言:“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除去“敦煌”之限定,此处俗赋即指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程毅中等学者的观点,俗赋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叙事性、问答对话、散韵结合和诙谐嘲戏等。[9]俗赋对变文、讲唱、话本小说等的影响,不少学者已有精辟论见。至于赋与戏剧,冯沅君在《古剧说汇》中对赋与优人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没有具体涉及赋对戏剧结构、表现形式等的影响,也没有重点考察俗赋与戏剧之关系;日本学者清水茂在论述时,亦以《辞赋与戏剧》来为研究命名,也在某种程度上给考察以一定的模糊性。
就戏剧而言,宋代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文化迅速发展。除了“说话四家”,勾栏瓦肆的戏剧表演亦是通俗文艺的重要表现形式。宋金杂剧中的“冲撞引首”(表演小段的故事以引出后面的正杂剧)、“拴搐艳段”(简单的院本,略同印子)、“打略拴搐”(“数板”方式念诵的引子)等情节简单、以戏谑为主的表演都有明显的讲唱痕迹,而讲唱受俗赋的影响至深,这种表现形式自然会带有俗赋的某些特征。金院本的“说唱杂戏”(以说唱为主的戏剧性表演)如《讲来年好》《讲圣州序》《讲乐章序》《讲道德经》等基本上是讲经文的体现,也是讲唱文学在戏剧表演中的残留。
就叙事性而言,俗赋带有很强的故事性,并且基本上使用代言体,这种代言体中也包含若干叙述成分,此种表现方式在元刊本的杂剧中也有若干体现,如开场的“定场诗”、“自报家门”等,虽然是代言的形式,但是概括性的话语评价中隐含着作者的主观态度,至于情节发展中戏剧人物的“背科”,更是虚拟地脱离了规定情境而对角色代言体的突破。所以说,俗赋同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间的转变,可能只是由一个人的诵读变为若干人按照赋中人物分别说,表演的加入是为了戏剧效果更佳,而装扮则是某种程度上的尽善尽美之追求了。淳于髡、东方朔、郭舍人等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人物,《茶酒论》中标明的两个人物台词的次序,都为这种演出实践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此种演出与戏剧演出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戏剧脚本可能就来源于某些俗赋的讲唱和诵读。
就文体特征而言,俗赋或设客主,或用对话口诀形式,无严格限制,改变了大赋中抑客申主的固定表现方式,主客地位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性。唐代的参军戏里,苍鹘、参军二角色各有分工,历经宋金杂剧,到元杂剧的角色更为完整和系统化,每个角色都有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和表现方式,有利于演员快速熟悉戏剧剧本,同一角色亦可以在台上临时发挥,创作宾白。《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宾白科介的缺失,也说明了宾白科介的随意性。此外,问答形式有利于叙事的展开,可以扩充表现内容,延展叙事节奏,推进情节发展,这也是俗赋和戏剧叙事性的体现之一。
俗赋的讲唱带有戏谑游戏的性质,而元杂剧中的“插科打诨”即为此表现。由于《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宾白科介的缺失,我们只能从明代的元杂剧刊本如《元曲选》中看到科诨的记载。戏剧中大量的“打油诗”、人物自我介绍时的夸张自嘲等,都只是为了戏谑调侃,与剧情的发展并无必然联系,甚至如《窦娥冤》这样的悲剧、赛卢医和梼杌上场时的定场诗及若干喜剧性动作,都只是戏剧这种通俗文艺样式所具有的娱乐性表现。
另外,元杂剧由一人主唱,或旦唱,或末唱,存留着从长篇说唱形式脱胎而来的痕迹。剧中主要人物不一定唱,如某些剧作在楔子表演打斗之后,再由末或旦扮探子等来唱叙战斗场面,表明杂剧形成之初,人们还不懂得欣赏纯粹的戏曲,因而保留着更欣赏描述性演唱的习惯。俗赋、俗讲、变文等尤其注重讲唱过程中的事件、场面等的铺叙,这说明通俗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唐代以后由于市民阶层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戏剧、讲唱等蓬勃发展,俗赋失去了其存在的阵地并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马积高言:“唐以后,尚未发现俗赋的流传”。[10]9这种现象说明俗赋以其通俗而自由的表现形式,与宋元的说话四家、金元杂剧等相互交织渗透,使中国的通俗文艺朝着更为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叙事性和艺术性兼备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众多一流的戏剧杰作。
三、赋与杂剧发展演进之文化思考
冯沅君在《汉赋与古优》里对汉赋的作者、作品与古优的关系论之甚详,辞赋的体裁与戏剧的类似却很少提到。冯文提出“汉赋何以多问答体,且以体物为主”这个问题,可是其回答是:“简单地说,汉赋是‘隐书’的支派。”“隐书”是猜谜,她认为是优人的技能之一。“隐书”作为赋源的说法之一,亦说明了赋与早期戏剧的密切关系。[11]248当然,如果进入本体,从文体构成、结构特征、审美风貌等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辞赋与戏剧的某些共性。
首先,赋和戏剧都带有浓厚的诗性特征。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指出:“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12]他主要是站在政教的立场上指出赋的创作思想来源于《诗》。同时,赋受《诗》“六艺”之义的“赋”之表现手法的影响。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盖《诗》有六艺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13]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指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这就说明赋在艺术上“假象尽辞,敷陈其志”的突出特点是由《诗》的敷陈手法发展演变而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的“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更将这种说法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在赋的发展过程中,又受到诗歌的诸多影响。比如魏晋时期,赋的地位堕落、诗的地位重新兴起,文人诗歌的情感影响了赋,由此出现了抒情小赋的创作高峰。再如晋、唐和元、明两个历史阶段“以诗为赋”的现象,以语言的浅易化和情感的柔化为追求,在艺术表现、审美理想等方面均表现了诗歌的特征。[14]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同样体现了中国文学中的诗性特征。在文体构成上,其主要构成元素之一是诗歌,如人物的上场诗、下场诗、唱词、韵白和剧终的判词、题目正名,以及剧中大量援引或化用前人的诗句或诗意,无论抒情、写景还是述事,都注重诗意般意境的营造。同时,作者往往借剧中角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特别是历史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在元代科举一度废止、士人前进无门的现实中的尴尬境遇,均在剧中有所体现。元杂剧作家们大多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诗教传统在剧中有所体现。另外,象征性的脸谱艺术、虚拟化的生活场景、灵活性的时空观念和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之写意艺术等都带有典型的诗意色彩,也是中国戏剧独有的表现方式。
其次,从结构特征上而言,无论是体物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都体现了朱熹所谓“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的特点。大赋叙事状物讲究铺排夸张、堆砌渲染、极尽铺排的特点自不待言,抒情小赋在描写上亦会运用象征、夸张、比兴、烘托等手法,从不同侧面状物抒情,如江淹的《别赋》,从行人、居人、富贵、任侠、从军、绝国、伉俪、方外、情侣等各等人物身份上写人类的离情别绪,将别离之痛写得笔势纵横、苍凉悲壮。而元杂剧的曲文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状的描写和铺排。
总之,元代产生于市井巷陌的元曲杂剧,不仅为文士所接受,而且代替了诗文的正宗地位,并以俗文学活泼的生命力包容了雅文学因子,使之提升到更高的审美境界。元明时代是封建正统之雅文学的诗文趋向衰落、俗文学日渐兴盛的历史阶段,而辞赋文学在依附诗文创作的艺术困境中向元曲、杂剧、明拟话本、白话小说、传奇宾白等文学体裁的旁衍,是文学整体思潮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例,对其赋体表现方式的探讨,亦可算作这种思潮的一个旁证。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
[2]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诠赋: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许结.论小品赋[J].文学评论,1994(3).
[9]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J].文学遗产,1989(1).
[10]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清水茂.辞赋与戏剧[M].蔡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李金龙)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225(2016)02- 0053- 06
收稿日期:2015- 05- 25
作者简介:杨正娟(1986-),女,河南安阳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以《阿房宫赋》《赤壁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