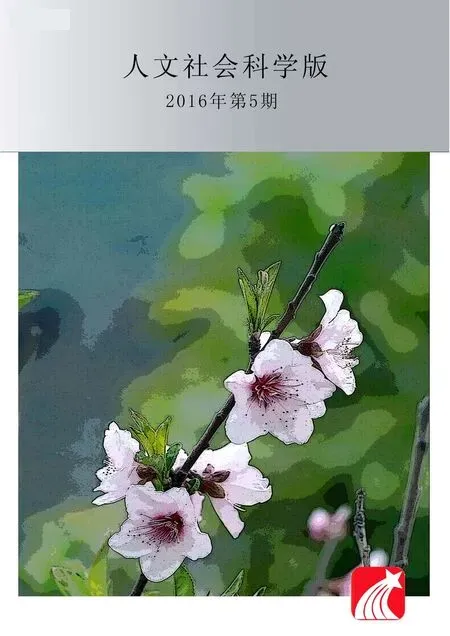疑古惑经与经世致用的史家风范
——欧阳修的历史观与治史方法
黄惠运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 吉安 343009)
疑古惑经与经世致用的史家风范
——欧阳修的历史观与治史方法
黄惠运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 吉安343009)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与宋祁合编《新唐书》,独著《新五代史》,一人独占两部正史,又编撰了《集古录》等金石学名著以及《崇文总目》等文献目录学著作。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即:重民至治,经世致用;实录简著,明微别嫌;金石证史,法严词约;疑古惑经,褒贬义例;轻天重人,损君益民等。
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史学思想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庐陵永丰人(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与宋祁合编《新唐书》,独著《新五代史》,一人独占两部正史,又编撰了《集古录》等金石学名著以及《崇文总目》等文献目录学著作。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欧阳修研究专家刘德清教授将欧阳修的史学思想概括为三点:不没其实,论辨正统;天人相分,反对祥瑞;整饬道德,标举名节[1]。这种概括,十分精辟,令人信服。笔者以为,欧阳修历史观的思想内涵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重民至治,经世致用
欧阳修在史著中解释了历史兴衰变动的原因,论说重人事的“盛衰之理”,阐述了重民至治思想。他解释“至治”的盛世说:“若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2]五行志。欧阳修指出,善治国者必须爱民,“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2]食货志欧阳修学古崇古,却反对泥古,提倡以史为鉴,经世致用,他说:“泥古之士,学者之患也。”欧阳修创设《新唐书·兵志》的目的就是“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 以为后世戒云。”[3]实际上是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北宋应对西夏军事形势出谋划策,为现实服务。欧阳修撰写的《王彦章画像记》一文,表达了他的历史文物保护利用和经世致用思想,他看到铁枪寺中王彦章的画像,在百余年之后,“岁久磨灭, 隐隐可见”, 于是“亟命工完理之, 而不敢有加焉, 惧失其真也。”[3]
二、实录简著,“明微别嫌”
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史传的叙事当以简要为主:“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6]欧阳修追求“简而著”的碑铭创作原则,他说:“然予考古所谓贤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铭见于后世者,其言简而著……今之碣者,无以加焉,则取其可以简而著者书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绛之人云。”[4]卷24欧阳修主张选取碑主生平事迹的大节来彰显碑主的声名,也就是“纪大而略小。”他在《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一文中说:“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更思之,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4]1020他在《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亦云:“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7]欧阳修认为:“铭者,所以彰善而著无穷也。”“铭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后世也。”碑志文的功能在于纪德昭烈,传名久远。
王彦章是五代朱温后梁王朝的名将, 在与后唐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战时他常持一铁枪, 骑马驰突, 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因梁末帝昏庸,小人乱政,在作战中被后唐军俘虏,不屈而死。欧阳修对王彦章十分崇敬,在搜集其史料过程中,发现了他的画像,写成《王彦章画像记》,体现了欧阳修“善善恶恶”的治史意识。欧阳修在文中盛赞王彦章“义勇忠信”“卒死以忠”的精神, 并且感叹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他不满于《旧五代史》记载王彦章事迹的残略,因此在私撰的《新五代史》中补充了许多有关王彦章的史料,其中包括其生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誓言。欧阳修具有强烈的表彰忠义、贬斥邪恶的治史主张。在欧阳修笔下,五代之人有资格列入《死节传》的只有三人,而王彦章居于首位,可见欧阳修不但“不伪梁”,而且丝毫不贬低后梁“忠节之士”的地位。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欧阳修效法孔子《春秋》笔法,“褒贬善恶,为法精密。”[7]
欧阳修通过评价石介表达了自己惩恶彰善的史学思想,他说石介“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8]他重视礼义廉耻的教化治理作用,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9]欧阳修认为“《春秋》辞有异同,尤谨严而简约,所以明微而别嫌,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地,圣人所尽心也。”[10]欧阳修不仅认为《春秋》笔法谨严,而且提出了“明微别嫌”的史学思想。欧阳修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两部正史中援引《春秋》笔法创制了以一字定褒贬的史法,如以攻、伐、讨、征四字来区别战争双方的性质以及自己的褒贬态度;以反、叛、降、附四字区别人臣背叛之罪的轻重,以示“明微别嫌”。章学诚高度评价了欧阳修“明微别嫌”的史法,称赞欧阳修《新五代史》本纪实胜前史,“其有佳处,则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11]朱温篡唐建立的后梁, 后代有些史家不承认其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坚持“不伪梁”, 在《新五代史》中撰写了《梁本纪》, 他解释说:“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 独不伪梁, 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9]
三、金石证史,法严词约
欧阳修晩年自号六一居士,他在《醉翁亭记》一文中说“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壸,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12]《集古录》一千卷是欧阳修重要的金石考古专著,欧阳修因为编纂了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集古录》一书,而成为金石学鼻祖、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
在刘敞等人的帮助下,欧阳修编纂了金石学名著《集古录》一书。刘敞,字原父,临江军新喻(原江西新余,今江西樟树市黄土岗镇)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世称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54卷。嘉祐三年(1058),刘敞以翰林侍读学士充任永兴军路(今西安市)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府事,将发掘所得的古器物,悉数购买收藏,分类整理,著录研究,同时,为欧阳修描摹、拓印、考订古器铭文,或赠送古器物,帮助欧阳修“考按其事”。如与殷、周史研究极有关系的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韩成鼎等古器物都是刘敞赠给欧阳修的。对此,欧阳修十分感激。他在《前汉二器》跋中说:“余所集录既博而为日滋久,求之亦劳,得于人者较多,而最后成余者原父也。”在《敦箧铭》跋中又说:“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在《毛伯古敦铭》跋中说:“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13]
《集古录》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金石学名著,这得益于周必大刻印《欧阳文忠公集》。周必大认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其文集遍行海内,惜无善本,以前刻印的诸本《六一居士集》“讹舛大甚”,有的“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有的“卷帙丛脞,略无统纪”。他“私窃病之,久欲订正”[13]。绍熙二年(1191)春,周必大和郡人孙谦益、丁朝佐、胡柯,旧客曾三异等人遍搜旧本,旁采先贤文集,互加编校,且编写年谱。同时,选派喻楫、胡彦等刻工数十人,重新刻印《六一居士集》。庆元二年(1196)夏,刻成《欧阳文忠公集》153卷,附录5卷,刋之家塾。此书编次、体例,“本出必大”[14]。周必大不顾年迈体弱,孜孜于刻书工作。他“率同志者朱黄手校如老书生”[15],“盖逐一字皆经眼,每一篇必经手”[16],由于编定精审,“遂为善本”[14]。周必大之子周纶又以所得欧阳修传家本(即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编次本),嘱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矣”[17]。从此,“周必大刻本”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上有名的“家刻本”,历代都被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欧阳修文集》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苏轼序、宋史本传、苏辙撰神道碑、韩琦撰墓志铭、苏轼、王安石祭欧阳修文,以及欧阳修为别人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祭文等,都是重要的史料。《集古录》这部金石学专著也赖以保存至今,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而刘敞编纂的《先秦古器记》却佚失不存了。
《集古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欧阳修编纂《集古录》一书千卷,又手写题跋十卷,即《集古录跋尾》,“古今巨观也。”欧阳修精于文字学,所题一笔一画,毫无懈意,精工极致,不仅保存了大量文物真迹,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依据。在《集古录》中,有解释不清楚的古器物铭文,欧阳修予以书录保存,“以待博学君子。”欧阳修写道: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于左。”[13]保存至后世辨认研究。汉郎中郑固碑,在《集古录跋尾》中也有记载,尽管其中数语今多漫没不见,但是,其史料价值不可泯灭,历久不衰。
欧阳修集古题跋的宗旨就是金石证史。他说:“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故每据碑以正史。”[18]卷9“余于集录正前史之阙者,多矣”[18]卷5“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9]卷41《集古录跋尾》中有很多考订史实之处。有关于名字的,如《唐书》载孔颖达字仲达,而唐于志宁所撰《唐孔颖达碑》则云字冲远,“可以正史传之谬。”[18]卷4有关于年龄的,如史书上说张九龄寿六十八,而唐长庆三年立的《唐张九龄碑》云六十三。有关于仕履的,史载:“张说卒,(张九龄)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碑云“副知”,到后来作相迁中书令始云“知院事”。欧阳修以为,“而至于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谬,当以碑为是也。”[18]卷9欧阳修实际使用了“二重证据法”,将文献资料与实物史料相互印证,尤其注重实物依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一书的金石证史价值不容忽视,与其瑰丽的文采异曲同工。所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说:“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20]
欧阳修是石鼓文发现后的第一个质疑者,后世疑石鼓文者所持论据多为欧阳修说法之拓展。欧阳修率先提出“石刻于秦”的年代问题。欧阳修提出“石刻于秦”说后,经过南宋郑樵提倡,至近人马衡撰写《石鼓文为秦刻石考》一文,遂成为定论,其后更有唐兰先生和郭沫若继续考证,其说直至不可动摇[21]。关于秦系石刻《诅楚文》的年代,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疑《诅楚文》为楚怀王时刻石,后来又修正此说,以为在顷襄王时。在欧阳修之后,董道、王厚之、王柏等人也有关于《诅楚文》年代问题的考证,但不出欧阳修所谓“非怀王则顷襄王”的说法。到了现代,经唐兰先生和郭沫若等的进一步考证,其年代为楚怀王时已成定论。
欧阳修秉承孔子《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宋史·欧阳修传》评价:“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褒贬”义例,譬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新五代史》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
《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书籍内容,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尤其在《十国世家》、《于阗录》、《司天考》等篇目中补充了许多史料,因此内容更加翔实,史料价值更高。欧阳修撰史,选材讲究,结构严谨,文字凝炼,不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颇受称道。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不应偏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22]《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疎,欧史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22]陈师锡《五代史记序》也肯定了《新五代史》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认为欧阳修“春秋笔法”的褒贬义例是司马迁、班固以来第一人,序云:“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9]
欧阳修对史事可疑之处也不轻易下结论,而是采取存疑候考的审慎态度。他说:“夫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9]卷18苏辙说欧阳修所撰的两部史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13]卷3所谓“《春秋》遗意”,也就是欧阳修史书义例所在。这主要表现为:叙事则寓褒贬,行文则求简约[23]。
四、疑古惑经,褒贬义例
欧阳修敢于疑古惑经,怀疑《易传》、《诗序》、《周礼》等古代经典,自称是孔子以后二千年来敢于疑古辨伪的第一人,开一代疑古辨伪的新风。他说:“今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余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于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与修同其说也。”[19]卷43在辨《诗序》上,《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两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阳修。”[24]欧阳修反对旧经学对《经》的歪曲,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之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之五六。”[19]卷18欧阳修肯定了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理学上的先驱作用和疑古惑经精神,他评价孙复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候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之多。”[19]卷27欧阳修既尊《春秋》为“经”,又认为《春秋》有“史”的性质,有别于孙复等人偏离史实而以意说经的作法,是把《春秋》书法谨严和《春秋》书事求实两者结合起来的史学名家[25]。
五、轻天重人,损君益民
欧阳修将历史盛衰变化的“理”着重体现在人事作用上。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26]欧阳修认为,《春秋》作为圣人之书,是“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也就是说圣人“笔削《春秋》”是立基于“人事”的[27]。“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欧阳修对唐庄宗政治生涯的总结,也是历代统治者治乱兴衰的自然之理,提醒统治者应当从唐庄宗的成败中吸取“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教训,唐庄宗之亡非由天命而是人事[28]。欧阳修关于兴衰在人事的思想具体表现在德政顺民、“损君益民”。他说:“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2]卷1“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呜乎,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2]卷37重人事就要别贤愚、善用人,他说:“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9]卷31治国当进君子退小人,他结合历史论述了“朋党”问题,他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9]卷17处理好“兵”的问题是重要的人事,他说:“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为兵,夫兵岂非重事哉。”[2]卷56欧阳修“重人事”的历史眼光和忧患意识是值得肯定的。欧阳修重人事就必然反对灾异、祥瑞说,他在《新五代史》中明确提出“书人不书天”的史学思想,他说:“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呜呼,圣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9]卷59他将旧史书中的《天文志》改为《司天考》。要行德政就要爱民顺民。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了“损君益民”思想,他写道:“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使民忘其劳与死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26]
欧阳修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方法是祖国传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他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眼光和彰善斥恶的史学品格,在我国史学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值得继承和借鉴。
[1]刘德清.欧阳修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文渊阁本.
[3]张连生.从《王彦章画像记》看欧阳修的史学思想[J].扬州文学,2007(6).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1021.
[5]吴怀祺.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J].史学史研究,1991(4).
[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8.
[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国书店,1986:1371.
[8]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M]//居士集.文渊阁本.
[9]欧阳修.新五代史[M].文渊阁本.
[10] 孙旭红.欧阳修与北宋《春秋》学[J].文艺评论,2011(10).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64.
[12]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13] 欧阳修.文忠集[M]//四库全书(第1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纪昀.(欧阳)文忠集提要[M]//四库全书(第1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周必大.文忠集·文忠周公神道碑(附录卷4)[M]//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 周必大.文忠集·孙彦伪谦益[M].文渊阁本.
[17] 于敏中,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M].文渊阁本.
[18] 欧阳修.集古录[M].文渊阁本.
[19] 欧阳修.居士集[M].四部丛刊本.
[2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亭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 顾永新.《集古录跋尾》的文献学考察[J].文献季刊,2001(1).
[22]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旧五代史[M].文渊阁本.
[23] 陈光崇.欧阳修的史学成就[J].社会科学辑刊,1982(1).
[2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文渊阁本.
[25] 吴怀祺.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J].史学史研究,1991(4).
[26] 吴怀祺.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27] 曾建林.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
[28]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责任编辑:刘自兵]
2016-04-20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庐陵史学研究”(JD1355);井冈山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庐陵史学研究”(JRB1202)。
黄惠运,男,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K 825.81
A
1672-6219(2016)05-00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