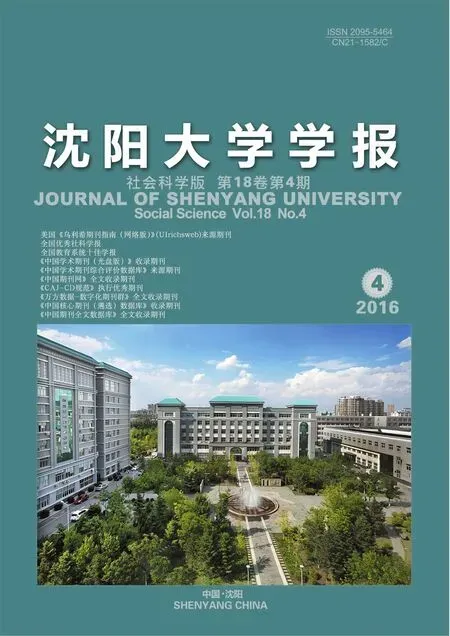花园与荒野之间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科幻叙事
张 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花园与荒野之间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照下的科幻叙事
张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510420)
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的文化转向出发重新审视科幻小说中独特的时空叙事性语言游戏之价值,认为其介于现实性和虚构性之间的叙事性值得进一步挖掘。
维特根斯坦; 科幻小说; 语言哲学; 现实; 想象
学界一直认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 1921)为代表,后期以《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1953)为代表[1]。 前期维特根斯坦主要考察命题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可以通过提供命题和世界关系下的逻辑描述,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了前期《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观点,认为词语的意义需要放回既定的语言游戏中考察[2]。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部著作《文化与价值》 (CultureandValue:ASelectionfromthePosthumousRemains,1977)和《哲学研究》一样,都是后人整理的维特根斯坦生前文字编纂。且《文化与价值》一书中超过一半的评论都是维特根斯坦在完成《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后所作(1945年以后)[3]8,可见《文化与价值》一书可归为维特根斯坦晚期的著作。将上述三部著作按时间顺序排列,可依稀摸索到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图像理论的逻辑哲学,到后期语言游戏中的哲学研究,再到晚期对文化的关注,其研究路径愈发宽广,从特殊到一般,从哲学到文化,实现了语言哲学的文化,甚至文学转向。
一、 文学之于哲学研究
在维特根斯坦之前,由于经典语言哲学语言观的束缚,文学在语言哲学视域内偏居一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提到其哲学思想主要受到前辈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罗素(Bernard Russell)的影响[4]4。 弗雷格视域下的命题,与名称类似,都具备含义和指称,其指称反映其真值。罗素对语言的理解是建立在真值和指称等逻辑概念上的,与科学语言不同,文学文本对世界的描述是不可验证的,所描述的大多是虚构的场景。罗素曾这样评价《哈姆雷特》,“该剧中的命题为假,因为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哈姆雷特这个人。”[5]277根据罗素的判断,文学文本中的论述为假,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文学文本不具有认知价值。
罗素对文学文本真值的判断影响了许多同代学者,在当时以指称为核心的语言观图景中,文学文本因为不具备现实指称物,而被边缘化。与罗素类似,许多哲学家基于真值和指称的概念,纷纷作出了相似的论断,还有哲学家认为文学文本的指称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存在于其他可能世界,在可能世界中为真。但无论如何,在以真值和指称为核心的语言观中,文学语言由于其本身的虚构性,都难以占据一席之地,作为语言的非常规使用,文学语言受到孤立,成为了脱离于其他语言、与现实世界脱节的边缘化语言游戏。
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我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曾对数位语言哲学大家进行了如下评述,“弗雷格是哲学家中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眼中的智者,罗素是商店橱窗画像中的圣人……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家、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哲学家,他那伟大的《逻辑哲学论》,信手拈来,便可谱曲。”[6]可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对某一语言表达的指称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指称不再被约定俗成地束缚在某一语言外部的个体现实元素上,否定了将语言放置于语言外部,而不参考语言获得其意义的实践过程的做法,因为“(语言)的图像本身无法外置于它自己的再现”[4]2.174。维特根斯坦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于其在语言中的使用”[7]43,把关注点从语言的指称转变到语言在具体语境下的应用,文学文本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适合的语境,是语言游戏的载体,意义在文学文本中诗意地栖居。
维特根斯坦不仅把文学纳入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还对文学进行了哲学化探究。关于哲学性和文学性之联系,在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的描述中便可见一斑,“他认为《逻辑哲学论》具有严谨的哲学性,同时兼备文学性”[8]。 可见,维特根斯坦将严格的哲学性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文学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指出哲学不属于自然科学,哲学的意义在于阐释思想,“(哲学这个单词要么在自然科学之上,要么在自然科学之下,总之它不能和自然科学并列。)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进行逻辑说明。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作品包含的内容从本质上而言是进行阐明。哲学的结果不是一系列‘哲学命题’,而是让命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没有哲学对思想的清晰鲜明阐释,那么一些思想就始终模糊晦涩”[4]4.111-112。维特根斯坦对文学性想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虚构或想象性语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小说可以在所谓的恰当(proper)状态下对语言展开研究。文学中镶嵌着人类生活、人类世界中的各种概念,并通过想象对这些概念进行不断地更新和测试。在《文化与价值》中,维特根斯坦对小说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将小说视为解决哲学或语法问题的途径:“为了理解概念,没有什么比构造虚构概念更重要的了。”[3]74通过创造虚构案例,哲学也许可以得到更好地研究,因为归根到底,哲学并不与现象联系,而与现象的可能性紧密相连。
二、 花园与荒野:小说的空间隐喻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的核心是:词语的使用比词语的意义要重要得多。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中最基本的层级是人类的活动。如此,困扰历代哲学家的难题虽未解决,但却消解了[7]109,133。语言栖居在语言游戏中,只能根据情境来定义。维特根斯坦后期的重要特征就是语言的情境性。语言游戏即语言的家园,语言和语言游戏之间是存与在之间的关系,这也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存在主义语言观。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视域中的语言游戏具有突出的空间性,是语言存在之所。该空间首先是基于人类具体语言实践的时空体,由人类的言语行为驱动,之后形成文本或话语空间,在此基础上,再抽象为具备某种地形特征的空间构型。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地域,像城市,像迷宫:“我们的语言可以看作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一个由狭窄的街道和广场,新新旧旧的房子构成的迷宫,而且这些房子还有不同时期所增加的部分。这座城市周围布满了许许多多新的街区,街区有笔直规整的街道和整齐划一的房子。”[7]19语言对于人类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语言是蜿蜒曲折的迷宫。你从一头靠近它,记住了自己走过的路;从另外一边,走另一条路到达同样的地方,却又不知道怎么走了”[7]203。 在《文化与价值》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提出了地图隐喻的小说理论,“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对某座城市十分之熟悉,能找到从城市的一处到另一处的最短路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几乎不可能纹丝不差地绘制出该市的地图。事实上,他越是努力画,画出的东西越偏离城市原来的模样。”[3]556这反映的是依据某种系统制图的愿望和系统性再现本身之不可能性之间的矛盾。“首先,这个尝试进行描述的人缺乏任何系统。他所遇到的系统都是不完备的,他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荒野之中,而不是那个他熟悉的布置妥当的花园。”[3]557“布置妥当的花园”带给人的家园式蔚籍转眼间变成了“荒野”带给人的惊异,从有序的花园,到混沌的荒野,从秩序井然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联系,到语言在语言游戏中任意地获取意义,维特根斯坦早期坚守的“明了的再现”(the 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这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布置妥当的花园随时会变成人迹全无的荒野。与维特根斯坦同代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提出过类似的双重感受,他指出恐怖的深层机制恰是熟悉中蕴含的陌生感。维特根斯坦对其进行了隐喻性的发展,从家园到荒野,人们在熟悉的城市中迷路,这种埋藏在熟悉中的异化,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本质的描述。小说展现给人们的是,人们在语言的家园中,但又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家园的陌生。文学体现着人们对于家园的双重交替认知——时而是精心布置的花园,时而是无人踏足的荒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作品通过创造想象性案例,揭示了日常语言实践熟悉中的恐怖。
三、 科学与想象之间的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彰显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小说介乎花园与荒野之间的空间性隐喻,科幻小说既是具备哲学探究性质的思想实验,又是反映科技影响人类生活形式的现代神话。下面就对照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花园与荒野的论述,对科幻小说与科学和想象的二重关系展开分析。
1. 科学:科幻小说中的“花园”
科幻小说文本中描述的世界与读者切身生存的世界截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基于物质和物理的合理性,而不是超自然或天马行空的无根据想象。科幻小说的根基是物质性的,而非超自然性,这也是科幻小说却区别于其他幻想小说的一大特征。科学是当今时代主导性的唯物主义话语,科幻小说的物质主义的根基也来源于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科学”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有着心照不宣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所指的科学不同,无论何种现象或假设在小说中加以提及,都意味着在小说文本中该现象或假设将在受控环境下得到某种程度上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作者要做的就是将科学设备置于思想的实验室中,专门回答“如果……?”(What if...?)这类问题,并给予解答这类问题所必须的养料[9]。格温尼思·琼斯(Gwyneth Jones)将科幻小说视为一种思想实验,一个精心布局的“如果……?”游戏,新奇和不同之处带来的影响或结果可以在其中得到演示。换言之,对于科幻小说而言,重要的不是科学的“真值”,而是科学的方法,对某一特定假设的逻辑推理。科学家有时自称自己是与“事实”和“真理”打交道的,而小说则与“想象”相连,是一种谎言。科幻小说对科学的使用,其意义并不在于赋予文本一种特殊的、接近真理的权威。
正如科幻评论家达科·苏文(Darko Suvin)所说:“科幻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叙事的主导性或虚构性‘novum’的霸权…由认知逻辑予以验证”[10]63。如果说,Suvin主要是从科幻小说的“科学”部分展开…评论,那么另一位科幻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则更多地关注了科幻小说文本的文学特征。他将虚构情节(“fabulation”)定义为任何“为我们提供与我们已知世界有着鲜明或极端的不连续性的世界,但却通过某种认知方式返过来面对这个已知世界”[11]。根据斯科尔斯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科幻小说既不同又相同,既陌生又熟悉,与已知世界的关系虽处于离散的非连续状态,却又能以某种认知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
关于科幻小说的时间性,虽然很多人认为科幻小说是在展望未来,但是大部分的科幻文本比起未来,更关注已经发生的过去。科幻小说的主导模式不是预言,而是追忆[12]44。 科幻小说不会把我们发射到未来;它用我们现在的故事与我们建立联系,比起现在和未来,它更加关注发展为这种现在的过去[12]46-47。 正如科幻小说作家、评论家勒奎恩(Ursula K.Le Guin)所说,“科幻小说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描述现在。”[13]可见,科学与现实是科幻小说中秩序井然的“花园”,给读者以家园般的慰藉,是变奏曲前的序章,熟悉而有序,是开展异化幻想的基石。
2. 想象:科幻小说中的“荒野”
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其描述的虚构性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于我们实际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种源于想象,而非经验性现实的虚构性文学,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子分支[14]1。牛津英文词典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科幻小说这一词条,将其定义为,“基于假定性的科学发现或令人惊叹的环境变化的想象性虚构,经常发生在未来外星球上,包含空间或时间旅行”[14]2。这里的“想象性虚构”将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realist)小说区别开来,现实主义作家需注重准确性,而科幻小说作者则利用想象创造我们现实世界中没有的事物。
苏文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创造了“novu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新”或“新的事物”,用来指代科幻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点”(复数形式为“nova”)。一部科幻小说,可以基于一个novum展开,比如H.G.威尔斯(H. G. Wells)的《时空机器》(TheTimeMachine,1895)中主人公穿越时空时借助的机器,更多情况下,科幻小说是基于互相联系的几个nova展开的,比如《星际迷航》(StarTrek)的进取号星舰上各种各样的未来主义技术。苏文于1979年对科幻小说进行了定义: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充分必要条件是对陌生化和认知之间互动的呈现,其主要的形式工具是替代作者的经验性环境的一套想象性框架[10]8-9。苏文认为科幻小说的主要“形式工具”就是novum。他进一步指出,科幻小说中的另一世界,由疏远(estrangement)和认知(cognition)决定,且必须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可以说,苏文提出的这种nova就是构成维特根斯坦“荒野”的要素,这些与现实世界不同点的有机组合给予读者以认知冲击,逐渐构建起一个疏离的虚构世界。
叙事是语言的核心功能。学习说话即学习讲故事。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OnCertainty,1969)中指出叙事具有不确定性,正如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作为波,物质是一种实践性现象,作为粒子,物质是空间性的,无时性的。这两种图景,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的术语来说即“不相称”(incommensurability),指的并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二者在逻辑层面上截然不同,相去甚远。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格式塔心理时候用鸭子/兔子画(duck/rabbit drawing)表达了类似的矛盾。同样的一幅画,不同的观察者,有时看到的是鸭子,有时看到的是兔子,但却从来不会同时既看到鸭子,又看到兔子。叙事不确定性原则表达的不相称性如下:读者对叙述/叙事过程(narration)和叙事话语(narrative)的认知是此消彼长的。我们对于故事或情节愈发确定,那对于叙事行为就越不确定,越模糊。同理,叙事者也是一个人的存在和一种行动的合成体。
文学创作是基于对其他世界的想象基础上的。想象虚构世界的文学从本质上有意地对现实保持沉默,而选择讲述我们现实世界以外其他世界的故事。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质的论述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并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①摹仿(Mimesis):再现我们的世界,客观地展现现实,又称“镜子观”,侧重时间性叙述;②叙事(Diegesis):想象其他世界,讲述故事,虚构性叙事,具有主观性,侧重空间性叙事 。在过去的几十载中,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关于虚构话语的逻辑和语义以及想象的本质都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虚构性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建构世界,参与想象性世界的创建,而非搭建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文学作品的语句不仅描绘了虚构世界的轮廓,同时还直接地描述着现实世界,导致虚构性作品在现实世界中也有真值。
正如耶鲁学派的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说,“文学作品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是用文字对业已存在的现实进行摹仿,相反,它在创建新的,补充性世界,元世界,超现实”[15]。1960年后,不再有学者对虚构文学作品秉持完全的摹仿论,即认为小说是对现实的再现。文学批评家们已经渐次放弃了文学的反映性图景。
作为幻想文学分支的科幻小说,更是利用想象在构建平行世界。正如时间研究学者J.T.弗雷泽(J.T.Fraser)所说,“语言是人类拒绝接受世界之原貌的主要工具……通过语言,我们得以对过去、未来或远方可能和不可能的世界进行描述”[16]。绝对意义上的事实叙事是被动的,好似一面镜子,丝毫不差地反映对面的一切。将叙事描述为“理性”是死路一条,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理性只是一个支持系统。它可以提供常规的连接;它可以发散情节;可以判断什么是可能的,可行的。只有想象才能带我们走出永恒现在的束缚。引导我们走向自由的故事才是人类的表达,这种自由为那些可以接受非现实的思想开放[17]。在谈论科幻小说叙事时勒奎恩指出“初始经验”的理性客观只有通过“二次阐释”的主观想象才能形成故事,保持理性就无法讲述故事,讲故事即用非理性的想象讲述谎言。在梦中,实践的方向通常感被空间隐喻取而代之,与幻想小说同源的科幻小说也是对空间的隐喻,不再关注科学的真值和对现实的如实反映,而关注科技的应用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实现了从科学真理到文化认知的转变,从科学是什么,到科学如何使用,从如何反映现实,到现实如何影响未来。
四、 结 语
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性为其铺垫了粗糙的地面,使想象根植于科学可行性的基础上,不至于在绝对光滑的冰面上打滑而失去方向,这片地面质感十足,时而是精心布置、无比熟悉的花园,时而是从未踏足、恐怖陌生的荒野,这种熟悉与陌生之间的交替贯穿着科幻小说的叙事时空:在时间上,科幻小说中的未来根植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性之上,在空间上,科幻小说中的外星球除了nova(不同点)外,还有人类现实社会的影子。维特根斯坦呼吁研究者回到粗糙的地面,让语言回归语言游戏,搭建了从语义向语用的桥梁。与之相似,科幻小说关注科学的社会、文化应用价值,基于科学的内涵,联通了科学与文化两大领域,在花园与荒野,有序与无序、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想象之间自由地徜徉。随之当代后现代主义的持续高涨,现代主义精英文化业已衰败,科幻小说中多元杂糅的叙事性蕴含着无限的可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李瑞青. 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J]. 沈阳大学学报, 2008,4:98-101.
[2] PROOPS I. The new Wittgenstein: a critique[J].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1,9(3):375-404.
[3] WITTGENSTEIN L, WRIGHT G H V, HYMAN H, et al. Culture and value: a selection from the posthumous remains[M]. Oxford and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4]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5] RUSSELL B. An inquiry in to meaning and truth[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2:277.
[6] EAGLETON T. My Wittgenstein[J]. Common Knowledge, 1994(3):152-157.
[7]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Great Britain: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8] WRIGHT G H V. Wittgenstein[M]. Oxford: Blackwell, 1992:81.
[9] JONES G. Deconstructing the starships: science, fiction and reality[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4.
[10]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1] SCHOLES R. Structural fabulation: an essay on fiction of the futur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2.
[12] ROBERTS A. Science fiction[M]. Routledge: USA and Canada, 2000.
[13] GUIN U K L.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M]. London: Futura, 1991:9.
[14] GIBSON J, HUEMER W. The literary Wittgenstein[M]. New York and UK: Routledge, 2004.
[15] MILLER J H. On literature: thinking in a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2:18.
[16] FRASER J T. Of time, passion and knowledge: reflections on the strategy of existenc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32.
[17] GUIN U K L.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oughts on words, women, places[M]. New York and Canada: Grove Press, 1997:45.
【责任编辑曹一萍】
Garden or Wilderness: Science Fictional Narrative From Perspective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ZhangNa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From the cultural tur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anguage-games of proper chronotopic narrativity in science fiction can be sharply revealed, whose unique narrativity between realist and fictionality is worthwhile for further elucidation.
Wittgenstein; science ficti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eality; imagination
2016-04-13
张娜(1986-),女,北京人,助理研究员、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
2095-5464(2016)04-0463-05
B 5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