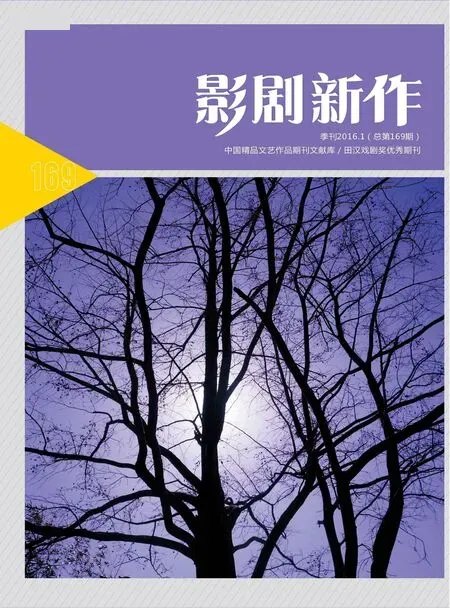施光南《囚歌》艺术形象塑造的音乐学分析
胡 丹
施光南《囚歌》艺术形象塑造的音乐学分析
胡 丹
施光南早期的成名作艺术歌曲《囚歌》是以叶挺的同名诗作作为歌词,作品通过特殊的旋律动机、调式、力度、表情等布局,将音乐元素与之巧妙地结合,塑造了革命者、黑暗势力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品艺术形象成功塑造的背后是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的综合呈现。
施光南 《囚歌》 音乐学分析
“音乐学分析”是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教授于1993年在其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音乐分析模式。他认为:“音乐学分析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 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1](P.39)
施光南众多的音乐作品,总能以鲜活的艺术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塑造过伟人、革命者、普通百姓,但不管哪个形象,经他音乐的渲染都变得鲜活生动,几十年来依然魅力不减。他学生时代创作的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的《囚歌》,是他的成名作。时隔几十年,至今依然引人注目,还被编入大学声乐教材,在各大舞台上传唱。施光南先生的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对于早年的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目前查询到仅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关注,其中亦涉及囚歌的研究,如周勤如《施光南《革命烈士诗抄》声乐套曲的艺术特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王响丽《施光南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布局及其形象塑造分析》(《大舞台》2012年第5期)两篇论文,上述两篇论文均从声乐套曲的布局结构以及宏观的形象塑造进行论述,前者对布局的艺术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也论述了《囚歌》的调式布局以及结构特点,后者在基于结构的基础上概括了《囚歌》的几个不同乐思的运用。从目前来看,尚无学者就其进行专题式微观分析研究。
对此,本文试图立足于音乐学视角重点从艺术形象塑造方面对《囚歌》进行微观分析与解读,以期更好地理解与彰显其艺术魅力。
一、施光南与《囚歌》创作背景
《囚歌》是施光南众多传世作品中一首早年创作的作品。歌词选自革命前辈叶挺的诗作,当年叶挺被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二号牢房,写于墙壁,署名“六面碰壁居士”。诗中叙述了一个被关押的革命者不被压力所屈服、全然不顾威胁利诱,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品质和高尚的气节,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该诗所塑造的革命者的形象感染了许多革命人和普通大众,许多革命者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曾有多位作曲家为之谱曲,较有影响的有施光南的同名艺术歌曲《囚歌》,罗忠镕的第二交响曲《在烈火中永生》等。
《囚歌》是施光南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创作的作品。他回忆该作品创作的情景时说:“特意选了一个节假日,学校里人们都外出了,教学楼中空荡荡的,一片寂静,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琴房里,饿了两顿饭,反复吟咏叶挺的诗章,想象和感受烈士当时的心态。……终于,乐思出现了,急忙到钢琴边记了下来。这时激情澎湃,几乎不停歇地一句句、一遍遍地推敲着,琴声、歌声中充满了那时的感受和气氛。”[2](P.24)可见,作者完全在这种精神感动之后并在自己设置的环境体验下才得以完成,该作品创作后得到大众的好评,至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成了一首经典之作。
二、《囚歌》艺术形象塑造的音乐学分析
(一)歌曲前奏的艺术形象分析
在歌曲中,冠于主体旋律之前的旋律称之为前奏。施光南极其注意作品中前奏的作用,“前奏不能看作仅是定调,间奏也不简单的是为了让演唱者换口气,如果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创作,它们在歌曲旋律中能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有时甚至是相当主要的作用,是体现作者的艺术构想不可缺少的部分”。[2](P. 130)在他的作品中,引子常常为主体艺术形象的出现营造预设一个良好的氛围。既为整部作品设置一个基本的情感基调,也让受众提前进入作曲家所营造的情境中。
《囚歌》在引子部分运用了洗练的音乐元素,共运用13个小节的旋律,营造一个监狱中的沉闷、压抑、阴森、恐怖的氛围,作为艺术形象的正式出场的铺垫式背景。第一小节旋律运用前短后长的音群组合而成的动机伴随mp力度以缓慢速度行进。音乐动机仿佛给人以沉闷之感,在配以p力度紧张的同度三连音钢琴伴奏,造成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似乎四处一片死寂,革命者的脚镣声打破夜的沉静。在第二小节接着出现同样动机,仅在第一音由
mi变成 re。第二小节似乎又是监狱中一声沉重的脚步。第一与第二小节两个由弱到强的音乐动机暗示声响的由远及近,表示革命者正由远及近走来。第三小节与第四小节安排了由极不稳定的ⅶ7和弦组成的两个声部,给人强烈的压抑感。作曲家还运用附点节奏交错进行,使之形成一种扭曲的进行曲风格,且音乐力度变成mf,暗示在黑暗中对现实抗争的力量。第五小节的最后半拍起,音乐性格有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变化,上行六度音程勾画出一个崇高的理想与甜美的愿望,紧接着出现一个带有三连音的附点节奏后再上行到mi,总体构成一个充满自由与飞翔的音乐主题。之后,接着上方三度的模仿,对主题的再一次强化。在第九小节处开始也是对前一乐句的模仿到达引子的最高点si,再下行到sol,引入唱词的低八度sol后结束引子段落。这连续的三个一个比一个强烈带有模进式乐句描绘了革命者的心理活动,寓意革命者盼望革命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成功,自由、幸福的生活一定会实现的愿望。
在长达13小节艺术化又兼具想象力的前奏旋律中,极具画面感。通过旋律进行与力度对比把囚牢的情境与革命者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神态坚毅、对革命抱着必胜信心的革命者跃然于欣赏者面前。引子为整个乐曲确定了一个艺术感情基调,把欣赏者平稳地引入到设置的音乐情境之中。
(二)作品主体旋律的艺术形象解读
作品主体的艺术形象塑造是灵魂,同时也是一部作品能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囚歌》从唱词开始,即进入主体部分。根据唱词,可以发现它包含三个不同角色:叙述者、反动派和革命者。作曲家在音乐中通过旋律情绪与速度、力度等元素塑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艺术形象。
作为事件的陈述者,在整个词作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其作用仅对情境起形象的陈述与传达。从诗作中分析,属于叙述者部分是前三句歌词,其中前两句是并列对比形式,第三句引出反动派角色。该角色总体均以旁叙的情感基调。作曲家抓住这种特点,运用西洋歌剧中宣叙调形式(他并没有照搬西洋歌剧运用同音反复形式),根据歌词本身结构和朗诵语调起伏的特点,再合以宣叙模式构成旋律。由于这种结合模式,在这三句旋律中,最具特色的是旋律音群组合体现了明显的汉语朗诵节奏。不仅节奏完全相同,在语调的强弱拍上也与旋律相合。从旋律与语调关系看,该句朗诵语势是中间高两头低,旋律也顺着语势运行。作品第二句在语言结构上与第一句相同,作曲家沿用了之前相似的节奏形态。第三句“一个声音高叫着”,依然运用朗诵节奏,音调设计也与语调有着明确的联系。另外,在此句是作为过渡句,欲引出反动派的角色出现,并在“高叫着”的音调中,出现mi,以此呼应与吻合朗诵节奏与情绪,以最终达到塑造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叙述者形象。
在唱词中,作为反动派角色仅有短短的两小句:“爬出来啊!”“给你自由!”从歌词来看,是反动派对革命者的利诱,同时也是对革命者人格的侮辱。作曲家在此却并没有完全依照叙述者形象的塑造方式。为了刻画反动派丑恶的嘴脸,作曲家在这两句中分别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前一句按朗诵语调应是高昂的情绪,却用ⅶ级分解和弦方式构成旋律,且用p的力度在小节中的后两拍起音,又在末尾运用以先强后弱的力度修饰长达4拍半的长音而结束。从这一句的音乐处理看,作曲家用类似于影视中的俯拍镜头去表现反动派,p力度记号的使用,使人感觉这一声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涌上心头,作曲家在上方标记的表情术语为“阴险地”也充分地表明了创作意图。后一句的处理与前一句截然不同,旋律仅仅只在中低音区用了肯定式允诺:“给你自由”。从这一句旋律设置可以看出,亦是作曲家的特意安排。这是为了表现反动派这个承诺是“信誓旦旦”,这为后面革命者的出场与毫不屈服起铺垫与衬托作用。
革命者形象是整部作品的重点,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刻画。在作品的第24小节最后一拍革命者形象“一出场”,就出现了前奏中崇高与甜美、向往自由的音乐主题配合革命者的唱词。此后,这一主题不断出现,以此来象征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第二句是第一句的重复,在两句间和第二句结尾均以该旋律高八度形式进行呈现,象征革命者掷地有声的回声。彰显其伟大形象,与此前反动派死气沉沉的旋律特色形成鲜明对比。两句后出现的旋律风格与之前抒情性旋律不同,根据歌词的内容,旋律用朗诵的方式一字一音地进行,似乎对反动派进行有力呵斥:“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里爬出”。其后的间奏采用前一句原样旋律,似乎是不绝于耳的回音。此后,再次重复配上歌词“我期待着”的革命者主题音调,把革命者的艺术形象与唱词再次融合,进一步将主题旋律形象与歌词相结合。此后,歌词“那一天”也使用在主题旋律上方模进形成的新旋律,给人以清新明亮之感,寓意对“那一天”充满期待。作曲家在表现“地下的火冲腾”时,使用回环曲折渐快式的旋律运行方式,在最后一字“腾”达到全曲高潮。此后用“啊”进行进一步情绪渲染,再次进入到具有宣叙风格带呼喊式一字一音的旋律,到达新的高潮。特别要说的是,此处作曲家为接续表达后一句,提前运用了五度伴奏支撑,顺利过渡到该句,为转调做中介。在歌曲的第48小节旋律转到 F大调,与原调形成下方小二度的远关系转调。用坚定如朗诵性的音调配上“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表现革命者与反动派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原样重复,后半部分以回环式的上扬再转到G大调,再次对英雄气概进一步升华。G大调部分的旋律是对前一句的非正常模进,再远关系转调进行到E大调。整大段皆因同一句歌词不断使用转调与模进,这是作曲家有意地通过改变调性的色彩来表现革命者情绪的步步高涨,最终在G调这一句旋律中达到顶峰。此后E调全曲最后一句歌词虽与前方一致,但处理却完全不同:前半句运用进行曲风格的旋律,表现革命者怀着高尚气节走向烈火与邪恶势力同归于尽,而“得到永生”一句却用长音构成旋律,以小跳与级进方式到达唱词中旋律的最高音,预示革命者预言的实现。伴奏以多次交替的方式再次奏响了革命者主题形象的旋律。简短的尾奏以快速三连音进行再以长音渐慢的方式到达g³结束整部作品。如此布局处理,象征革命者以自己的死换取革命的胜利,换取人间自由。上升型旋律进行正是表达革命者的“永生”,象征着革命烈士的永垂不朽。
三、作品艺术形象塑造的背后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塑造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艺术功力、才情智慧与丰富的情感。施光南正是兼具其所有才把一首短诗谱成一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具有戏剧性的艺术歌曲作品。整部作品角色分明,高潮迭起,耐人寻味,具有丰富的画面感,彰显了强烈的戏剧性。欣赏后如沐春雨,给人以精神的洗礼。笔者认为,施光南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完全是建立在感性与理性相交融的基础之上。
早在《乐记》就有“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的思想,因此,按一般创作习惯,曲作者根据歌词表达的内容进行诵读,在深入理解歌词表面上与隐含的深层含义的基础上,再“感于物”而成曲。作者在创作时,常常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作者所要表现的是牢房里革命者形象,而作者并未有过如此经历。于是,作者为了“感于物”,特地制造与牢房相似的情境,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叶挺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氛围之中。通过这种融入的方式感受对内容的“亲身体验”,而后根据情境创作。因此,这种方式比单纯依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显得更加深刻。作曲家通过这种方式倾注的情感与作品中的革命者情感相对接,在他看来,这是必要的。因为“音乐装不了假,作者如果不是倾注了真情,尽管能运用某些外在的效果以及矫饰的演奏、演唱造出某种感情,但这种音乐听起来必然是浅薄、虚假的。”[2](P.11)这就是施光南先生不但要充分理解歌词中的含义,还必须带着感情充分融入到作品之中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作品艺术形象塑造成功的要略之一。
为塑造更加完美的艺术形象,在理解与融入歌词意境基础上写出的作品才能动人。就整部作品而言,可能还存在逻辑上缺乏彼此之间联系,不具备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因此,还必须在依据真情流露写作的基础上加以运用恰当的作曲技巧,构筑乐曲的逻辑关系。在技巧的使用上,施光南并不使用复杂的创作技巧,而是注意运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技巧,使作品更加出彩。施光南在《囚歌》的音乐塑造上巧妙地运用了多种常见技巧,如对比与铺垫的结合,巧用语言魅力、典型主题旋律的贯穿等。
对比是作品《囚歌》中最重要的技法,正是因为运用了音乐对比处理才能更加显现出各个艺术形象美丑善恶,因此,诸形象之间才能更加立体。例如作品中三个角色之间在音乐的处理上就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作曲家在其中就用了不同的旋律乐思和不同的力度与速度来对三者进行比较处理。例如:革命者的音乐主题运用充满朝气与向往的旋律,叙述者用不带感情色彩的朗诵音调,而反动派则用低沉、支离的旋律表现其丑恶形象。就细化到句与句之间,这种对比也很常见,例如,唱词对应的第一、二句旋律就用了典型的对比手法:第二句的旋律模本取自第一句,但是为了强调“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强调“卑贱”,作者在“为狗”两字的旋律上取用了全曲的最低音re。通过这样明显的对比,明显地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人的高贵,狗的卑贱。以此为后续音乐发展提供了动力与铺垫。
另外,在该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整首乐曲用了大量的主题音乐的贯穿,从前奏到主体到尾奏都有使用,但是频繁的使用却并不显冗繁与凌乱,却是恰到好处。例如,在革命者形象用大六度上行紧接着三连音的到全曲最高音旋律,整个乐曲在不同地方不断有该形象的音乐出现,象征着革命者美好希望与对胜利的憧憬。但就在每一个主题艺术形象的出现,根据歌词的不同以及其力度速度的差异,所表达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例如,在前奏出现时象征着革命者的内心的描述;在革命者“出场时”,主题音乐出现在间奏,像是革命者掷地有声的回音;而在尾奏的再现却是象征着经过不断斗争之后所出现的光明与希望,最终达到胜利,光明战胜了邪恶。彼此旋律相同,含义却又各不相同,同一主题的贯穿表现了革命者的不同侧面的光辉形象以及他们对革命胜利的追求与向往。
此外,作曲家在该作品中还巧妙地运用了铺垫的手法,在《囚歌》的前奏部分运用了大量的音乐铺垫,使听众能立刻进入到作曲家创设的情境中。使用朗诵语调作为乐曲的节奏音调也是施光南先生在作品当中运用广泛的一种技法,通过语言节奏,直接传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特别是上文提到的关于革命者斥责段落和宣叙段落,正是利用这种绝妙的手法将反动派丑恶的嘴脸一览无遗地揭露。
除善于运用完美的技巧,施光南更注重对作品的雕琢,一首作品成型后,“面对自己写出来的曲子,则需要站在听众的立场来反复琢磨。除对旋律、和声、织体等各个细节进一步推敲之外,特别不能忘记整体效果的感受。”[2](P.123)强调注意乐句与乐句之间的意境衔接,乐段与乐段之间的层次对比。同时抓住整体的结构逻辑,从整部作品的角度出发去把握整体乐思的进行,经过这样反复的思索才能最终定稿。我们虽然现在无法得到施光南的《囚歌》的手稿,无法确定他究竟改了几稿之后才最终定稿,形成现在的版本,但根据《我怎样写歌》中在叙述《囚歌》创作情境时“几乎不停歇地一句句、一遍遍地推敲着”,《囚歌》的创作并不是一遍定稿,而正是在这种“一诗千改始心安”的创作态度中反复修改而成。
施光南正是为艺术创作付出巨大的艰辛与投入满怀的激情,加之他天才的音乐思维,才获得了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他把感性与理性巧妙地融合在作品之中,才使得整部作品熠熠生辉。
[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4YJC760068)、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5年)规划项目(编号15YS37)的阶段性成果]
[1]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J].《音乐研究》,1993(1).
[2]施光南.我怎样写歌 [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胡丹: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范干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