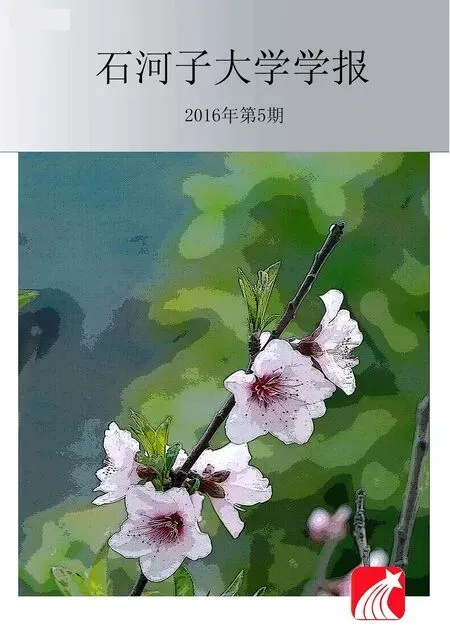对话与建构
——论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
颜同林,杨 洁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对话与建构
——论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
颜同林,杨 洁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新时期以来,现代作家林语堂的作品与思想逐渐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林语堂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众多研究者中,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在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中,论者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照,深入阐释了林语堂散文的“闲谈体”风格,挖掘出“性灵”文学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进而全面而独特地把握住了整个林语堂散文的文体特质与思想内蕴。
王兆胜;林语堂研究;“闲谈体”散文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1019.0106.008.html
新时期以来,与张爱玲、钱钟书等一夜之间突然走红的现代作家一样,林语堂也成为学界热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其相关研究自然成了一个学术热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的逐渐被重视,林语堂用中英文写作的作品被大面积地重新翻译、出版,大量的不同层次的读者开始喜欢、迷恋他的作品,这说明林语堂的作品被重新接受与认可,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存在,也有被再研究的文学史价值。继万平近、施建伟两位先生之后,学术界先后涌现了陈旋波、王兆胜、汤奇云等林语堂研究者。在众多研究者中,王兆胜独树一帜,著名的现代史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评价其是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王兆胜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照,对林语堂的各类作品进行个性化的全面解读,重新把握住了整个林语堂精神世界的实质,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缩小到散文研究来看,也是如此。本文对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进行剖析,试图洞察这一研究的整体风貌。
一
一位研究者的文学情怀,与他的人生经历相关,更与他学问中的追求与趣味相关。选择什么样的作家或什么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往往反映着研究者自己的个性、趣味和价值观。王兆胜以林语堂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学者的喜好或偏爱,更是其生命精神的选择与承担。王兆胜曾经说:“人的一生不论长短,就其思想和心灵来说,它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受过某些人的影响,我也是这样。但就文学、文化影响我的灵魂而言,有两位现代人最为突出,他们是鲁迅和林语堂”,“读鲁迅的作品,眼界容易开阔,目光容易深刻,情感容易深沉。然而,不需讳言,鲁迅及其作品总有一种深重、一种阴暗、一种窒人的气息,久而久之沉溺其间,也极容易受到感染,有时自己的内心也苦不堪言”,“然而,当我接触到林语堂的大部分作品时,我惊喜地发现林语堂与众不同的另一番格调,而这正可医疗鲁迅给我带来的内心不平衡和阴冷感”[1]1。无疑,王兆胜和林语堂在精神层面有更多的契合点,他洞察到了林语堂不同于鲁迅沉痛深刻的一面,发掘出林语堂作品所蕴涵的有别于“五四”以来大多数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正因为这样,他选择了林语堂,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对林语堂的分析中,大量穿插了对鲁迅、林语堂二人的比较,独特而深刻地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判断。
不容否定,在政治挂帅意味浓烈的年代,林语堂的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曾相去甚远,持久地受到各界的质疑与批判。要研究林语堂,不但需要有眼光,而且更需要勇气。林语堂曾评价自己:“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于这样一位赞同东方文化,也推崇西方文化的学者,曾长期被学术界漠视。这一点王兆胜有自知之明,他说:“我是非常郑重而不是随意选择林语堂的,至于说出其具体原因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概括一下,那也有几条原因。一是因为林语堂与鲁迅一样非常复杂,是个‘谜’、‘说不尽’;二是因为林语堂所富足的可能是自‘五四’文学、文化启蒙以来我们所欠缺的;三是林语堂给我提供了某些或者说许多认识自身、剖析灵魂的参照;四是林语堂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处在被误解、误读的尴尬境地。”[1]2王兆胜选择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在于文学品格的契合、精神追求的相似,也在于王兆胜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在学术界引起对林语堂本该有的关注和思考,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偏颇与不公现象。
更具体一步,王兆胜之所以对林语堂的散文青睐有加,正是因为林语堂散文影响、契合了王兆胜的散文观。由于有自己的文体观念和价值目标,王兆胜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客观地批评了当代散文作家存在的“迷失”与“局限”等问题。“时下的‘大文化散文’主要被理解为罗列知识和显示学问,似乎谁在散文这个筐子里装的知识越多,就越有学问,也就越有文化……在这些散文中,作家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很少发出光焰,更多的是向读者出售知识,某种程度上,不少‘大文化散文’成为知识手册的代名词。”[2]12王兆胜分析了余秋雨、王英琦、李存葆和李国文等人的“知识散文”的问题,批评他们的散文虽然崇拜知识,但缺乏灵动与活力,相应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观:“我认为,‘大文化散文’必须打破‘知识’的神话,以作家的精神和心灵为镜头,照亮和折射自然、历史、社会、人生和生命的经纬,这样它才不至于沉重难举、折翅而坠。”[2]12“在文化散文中,知识不是不可以用,但要用得精到,这既需要取舍,也需要节制,更需要用心灵之光照亮它,否则就会挤掉散文的精神空间,甚至窒息散文的生命。学问在散文中也可以显现,但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文中‘蕴含’着的,这颇似水中之盐。关于这一点,有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化散文’做得比较成功。像林语堂、王了一、梁实秋、张中行、季羡林、余光中、黄裳、林非、董桥等人的散文都是如此”[2]12。
总之,王兆胜选择林语堂及其散文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王兆胜本身是一名真正追求独特文化情怀的学者,在散文领域有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判断,能在众多研究对象中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数十年间,王兆胜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与中国文化》《闲话林语堂》《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等著作,涉及到林语堂研究的诸多方面,林语堂散文是其中一个主要板块,这样大大丰富了林语堂研究的内涵。在这著作阵列中,《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是王兆胜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被认为是从人生哲学、宗教观、文化观、文体等崭新角度解读林语堂,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譬如严家炎教授就评论说此书标志着林语堂的研究迎来一个新阶段。可以看出,王兆胜以个人之力,这么多年坚守对林语堂的热爱,涉及包括林氏散文在内的不同文体,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将林语堂深刻而广阔的文学世界与理想,清晰无误地呈现给了读者。无疑,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不论在林语堂研究上,还是放之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史上,也是如此!
二
对一个作家的研究,要深究其思想内涵和观念形态,就不得不探索其文体的特性。对于林语堂的散文研究,王兆胜显然深切地把握了这一点。王兆胜认为,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要从思想角度划分比较困难,如果从文体来入手就要容易得多。何为文体?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认为,文体主要看作者的‘叙述’方式和倾向怎样,换言之,文体主要表现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结构上。”[1]221进而,王兆胜将文体分为三类,一是教导式,作者以国家的拯救和发展为己任,以先驱者的身份向读者讲解、启蒙;二是忏悔式,往往不太考虑读者的感受,作家自说自诩、关注自我、痛快宣泄;三是对话式,作者和读者如朋友交谈,双方敞开心扉,彼此沟通学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两者是主力的发声,一者是向听众说“道”、启“蒙”、授“慧”,孜孜不倦,鞠躬尽瘁;二者是无视听众,不停地叙说自我的感情,表达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对于对话式,则注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积极倡导两者之间的互动。对于对话式的理论和实践运用的作家不只林语堂一人,但是涉足最早,用力最勤,喜欢至甚的,还要数林语堂。
林语堂的散文犹如一杯茗茶,在细细品味之时,令人有品味人生百态之感。为了将这一杯茗茶的香气呈现出来,王兆胜深入探究林语堂的“闲谈体”,将其概述为四个特征:一是,包容的心态。“闲谈体”视域开阔,心态广大,题材、人物、叙述等方面呈现包容性,宇宙万物、鸟兽鱼虫、生活琐事都是林语堂选取的内容,达到了包罗万象、百川归海之效。二是,闲适的格调。闲谈讲求的是舒缓从容的节奏,在雍容和平的氛围中,谈话者娓娓道来,听众俯首静听,人间世相,芸芸众生,畅所欲言。三是,闪现的心灵。真正的闲谈不是低级趣味的胡说八道,而是在和谐的气氛中各抒己见,妙语连珠,营造一种相互碰撞、迸发火花的效果。四是,灵健的语言。林语堂的闲谈体语言追求简单易懂,舍弃说教语言的生僻板滞,同时吸收古文的文雅,将文言与白话融合,互为取长补短。对于语言这一特点,王兆胜认为梁遇春语言过于西化,丰子恺过于文气令读者难解其赜,而林语堂突破了二人局限,极具语言的独特魅力,“林语堂曾用‘雅、健、达’概括自己的语言风格。林语堂随笔语言是雅与俗、实与虚、文与白、幽与畅、生与熟、辣与醇、方与圆等达到较好结合者,可读性较强。尤其是俗、实、白、畅、熟、醇、圆为林语堂的随笔增强了一种胶合力。林语堂虽阐发己见,但不是启蒙式的高人一等、独白式的自言自语和静思式的沉默不言,而是调子放低,心气放平,眼里心中都有读者在,是深入浅出的絮絮道来。语言也是经过‘化’的功夫,极得醇熟圆润之致。”[3]71
林语堂散文的“闲谈体”能够自成一派,说明其文体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对此,王兆胜心领神会,相应提炼出了类似的见解。一是,主张文学的独立品格。“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自由”“民主”“科学”,焕发了中国文学的新生机。但是在当时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主题曲,许多仁人志士呐喊抗争,将文学作为抗争的武器,使得“政治”对文学有过多的干预。尽管如此,也不应该将文学与政治等同起来,文学要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二是,重视与读者的交流。林语堂善用“谈”“说”“论”“记”“答”和“闲话”等字眼,将“闲谈”贯穿在整个作品中,采用对话、闲谈的方式构建全篇,和读者似朋友一样,双方敞开心扉,无所芥蒂,彼此交流。这种对话的方式不是单一的,不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也有“作者”与自我、“作者”与自然的对话等。“梁遇春和丰子恺随笔注重絮谈,但缺少些气氛,而‘我’与读者又有些距离。而林语堂随笔则不同,它是典型的絮语体,即与读者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题目、取材、观点、谈话角度和方式都是读者熟悉的,尤其是叙述者‘我’的态度不傲慢,不高人一等,完全将读者当朋友,心交心地相互交流。这种知己谈话方式可收到‘深入浅出’的艺术效果”[3]71。三是,对当下的散文行文有启发意义。在散文理论的探索中,更多人注重的是突围、变革和革命,而建设性的意见则显得淡弱多了。对于当下的散文文体,王兆胜认为普遍存在着一元化、机械化、庸俗化的思维缺陷。要么认为散文的核心即是“散”,“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么对散文进行“纯化”,严格按照“美文”规则行文。这两种观念都看到了散文文体的某些特性,但却进行了片面性的理解。对此,王兆胜坚持认为:“既然散文的形神都不能散,必须‘形聚神凝’,那么散文之‘散’如何体现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心’散,即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换言之,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这颇似珠玉金质包隐于石,更多的时候亦如高僧禅定。”[4]5由林语堂的“闲谈体”、散文格调与趣味,引发了王兆胜对散文文体的重新思考,在“形聚神凝”的基础上追求“心散”,确实不同凡响。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语调表现文字,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从而深入人的心灵,难道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么?在笔者看来,由研究对象的散文特质,引发研究者的散文观与文化情怀,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除了散文的“闲谈”特质之外,还有“性灵”必须得到彰显。“林语堂的‘闲谈体’最重要者还是‘性灵’和‘笔调’两项”[1]239。在闲谈中,畅所欲言,思想碰撞,独抒性灵。可见,“性灵”是林语堂“闲谈体”的精髓,有了它,就如同有山有水、花有香、鸟有声一样。何为“性灵”?在中国文学中,“性灵”最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5]1的句子。“性灵”发展为“性灵说”,成为一种文学观,却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在万历年间崛起文坛,他们在“性灵”思想上有继承,推崇解放文体,重视自述己见,主张文学进化。到了近现代,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提倡“公安派”的“性灵文学”的先行者。林语堂紧随其后,撰写了《论性灵》和《论文》两篇文章专门探讨“性灵”问题,公开倡导“性灵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将善良纯正的人性种子薪火相传,成为张扬“性灵文学”的旗手,在“性灵文学”史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性灵文学”的定义方面,林语堂说:“神感乃一时之境地,而性灵赖素时之培养。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6]238尽管“性灵”一词的意义模糊多变,性灵本身的含义复杂抽象,林语堂对于“性灵”的解释依然让普通读者有了相当的认知。值得强调的是,“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语境下,关注社会现实,批判传统文化成为主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溯源的“性灵文化”自然不受重视,甚至被一再否定。以“性灵”相标榜,无疑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承担更多的风险。
相比之下,王兆胜在追溯林语堂散文“性灵”思想的根源时,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契合与呼应,也是一种对话与建构。他从中国古代文化出发,在众多的形成因素中,剖析林语堂“性灵”思想来源,得出了精辟的结论——林语堂的“性灵”思想深受“三袁”的影响。以“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文学”,反对以理学为主体的儒教思想,推崇追求自由的精神,倡导注重享受的理念,鄙视重视名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公安三袁、林语堂、王兆胜之间心灵的对话,也是一种精神重构。这样我们不难理解王兆胜的一些论点,比如:“在‘性灵’上,林语堂得益于‘三袁’处最多,它几乎开启了林语堂文学人生的灵府奥心。也可以这样说,正是袁氏兄弟‘性灵’这把钥匙打开了林语堂的心灵世界,于是天地之风涌灌进来,而林语堂的生命之帆也就鼓动起来,并开始了自己‘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人生旅程。”[7]291“三袁”的“性灵”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可以概述为三个方面:一是真诚地表达自己。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三袁”倡导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这正是林语堂的文学主张,他将自己看为自然之子,也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自然山水。三是如何表达性灵。不追求章法句法,不注重浓墨重彩,而是平淡质朴地自抒胸臆,在“本色平淡”中突显“趣味”。林语堂为什么反对文学和政治捆绑,为什么反感左联作家,为什么倡导闲适性灵的小品文,王兆胜认为正是因为与“真诚”的性灵思想有关。同时,王兆胜还看到了林语堂在“公安三袁”上超越的一面,“公安三袁”的思想更多具有本土化,而林语堂深受西方影响,探索科学的力量,倡导民主和平等,以此表达“博爱”和“悲悯”的情怀。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上,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有顺承,更有推进,这一点难能可贵。显而易见,这种侧重于性灵的精神追求,是林语堂内心所企望与抵达的,也是王兆胜所企望与抵达的。
三
王兆胜标举了林语堂散文所具有的“闲谈”“性灵”等特质,对其传统思想渊源有所追溯。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兆胜还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高度,对林语堂散文思想进行立体还原,在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中,凸显了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智慧。
首先,从中国文化出发,作者提炼、总结了一种悲剧观念。从老庄、孔子、屈原,到杜甫、李白、苏东坡,再到鲁迅、茅盾、老舍等等,从古至今,中国文人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世界、对于生命、对于人生大多持悲剧式的体验。“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人以悲悯的人生态度,采取批判的眼光,指出国民的劣根性,倡导“立人”的主题,以此探寻中华文化的新路与复兴,尤其显得突出而高大。此时此地的林语堂,却南辕北辙地倡导“闲谈体”,主张“性灵”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自然成为了另类。比如鲁迅就认为林语堂主张闲适风格,文学远离政治,是不合时宜的。鲁迅是现代文学与思想的标杆,鲁迅推崇的文化成为文学界衡量文化的标尺,而鲁迅所批判的亦是文人们所反对的,部分学者认为林语堂的主导思想与“五四”新文学相违背,甚至批判林语堂为小资产阶级主义者。对林语堂的这种评价一直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主流文学圈对于林语堂的看法。对此,王兆胜用辩证的思维看待林语堂的文化理想与文学世界,提出林语堂的“闲谈体”实质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性之上这一见解。天地万物,人类作为其中一个生物,非常渺小,人类不能无视茫茫宇宙的存在,不能违反天地仁心的道德,这是人类具有的先验性悲剧命运。林语堂对生命的悲剧底色有着深刻的认识,生命的悲剧性是一种本质存在,人生、社会、现实是有悲剧性质的。而“闲谈”是林语堂对待命运的良方,是一种参悟悲剧命运后的豁然抉择。“林语堂的生命观和人生颇似袁中郎,一是强烈的生命悲剧式感受,二是善待人生、苦中作乐和逍遥自适的情怀。”[7]299譬如,公安“三袁”写过不少人生苦闷的文章,渲染人生之艰难、生命之无常,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与他们的生命体验有关。在悲悯人生无常的同时,“三袁”又持达观的态度,认为一个心灵强大的人必须超拔而出,有一种大精神的逍遥境界。一方面是体验人生虚妄,一方面又试图进行超越,是一种看透了人生的“苦中作乐”,也是一种追求脱俗的生命意识。林语堂认同“三袁”的人生观,在林语堂的散文作品中,骨子里隐含着一股扑面而来的悲剧意识,但又以乐观的精神、态度加以调适。从“三袁”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联系,从老庄、屈原诸人身上,自然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思想印痕。比如,“反抗绝望”“善处人生”是林语堂富有哲学思想的精髓。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庸”是林语堂的生活准则,倡导努力工作又要尽情享受,做人保持原则又要不泯童心,为文豪放不羁又要恪守文法。其次,林语堂推崇“半半的人生哲学”,追求“幽默”“闲适”“趣味”,在生活、事业、婚姻、人际关系上采取包容、体谅的态度。再次,林语堂提倡人要有一颗包容的心,要用美的心灵去看待世间万物。自然之美、人生之美、艺术之美是林语堂美学思想的精髓。王兆胜深入到林语堂的精神世界之中,揭示林语堂的传统哲学观念,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林语堂的本来面目,王兆胜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待林语堂时显得更为长远、透彻。
其次,从西方文化来看,其悲剧精神亦对林语堂产生影响。从17世纪的巴斯葛、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再到希腊文化中的死亡观念,他们的悲剧精神始终是林语堂世界的持续观照。众所周知,林语堂从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其文化中的“原罪”“苦难”和“悲剧”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林语堂的灵魂之中。林语堂虽不至于像虔诚的基督教徒那样信奉“原罪”,但他也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主宰着人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倒好像把‘苦难’与‘悲剧’看成是上天给人类的赐予,是与‘幸福’一起赐予的。这样,对上帝难以超越的悲感就成为林语堂悲剧人生观的来源之一”[1]64-65。对于林语堂作品中的悲剧性,王兆胜还看到了其他学者所没有关注到或思考较少的死亡问题:在林语堂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都有“死亡”问题。“‘死亡’在林语堂的文化本文中是一个‘情结’,它既在作品中影响着结构关系和抒情基调,而且反映了作者的生命底色及文化观念。可以说,‘死亡情结’是潜隐于林语堂文化观念、人生哲学中的一股潜流”[1]49。林语堂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死亡”描写,这是西方文化蕴含的悲剧精神的投射。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林语堂的世界中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交融汇聚、求同存异。要深入地了解林语堂,王兆胜认为最重要的是将林语堂放在世界文化坐标中,通过中西文化的冲突、融汇与整合,来分析林语堂的多元整合思维方式。一是运用“求同”的眼光,探寻中西方文化的共通点。与国粹派不同,林语堂认可西方文化,赞颂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的生产力,倡导其平等、自由、民主、博爱、道德、人性的特征;与欧化派不同,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是肯定的,他推崇儒家和道家文化,两者在人生、道德、智慧、快乐、幸福等方面对林语堂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是在“求同”的基础上,用“求异”的视角来追寻不同文化间的区分。一方面,林语堂认为西方文化过多地注重理性、逻辑、分析,这就造成了相对地忽略了感性和情感。另一方面,林语堂不是一味地接受儒家和道家文化,他批判道家文化“太飘逸”“太高远”,不能在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可见,林语堂在看待中西方文化时,既没有全盘接受,也没有全盘否定,他提倡将中西方文化相互补短,互相吸收,方能日趋完善。由此看出,林语堂的“闲谈体”散文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它具备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有着独特的内涵和中心。纵然他没有把否定变成恣意的发泄,而是把它当作追求研究目标的态度和手段。在盛赞林语堂融合中西文化的精神时,王兆胜也指出了其作品存在时代感薄弱、忽视人的社会能动性、“唯心”重于“唯物”等缺点。王兆胜对林语堂的散文研究能够在当今学术界独树一帜,与其宁静、朴实、舒缓、平淡的批评风格有很大联系,而批评风格背后的是他对“天地人心”的人生关怀。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求真求善的精神之上,这要求批评者需要有一个博大宽广的胸怀。王兆胜的批评立足于“天地人心”四个字,深求“天地人心”的人生观念,以求建立批判精神的两极坐标:人与天地。以此观念为坐标,王兆胜不仅非常推崇表达对天地、大地敬畏的文章,而且十分赞赏从自然的立场审视万物的胸襟和眼光,这也是林语堂对待天地万物的价值观。林语堂的散文正是“将‘天地’装在心间,然后发而为文则为‘天地至文’,为人做事则为‘天地间的大丈夫’”[7]293。“天地人心”是王兆胜与林语堂散文对话之后对人生的诗意建构和总结。
结语
总之,“天地人心”是王兆胜对个体生命的审美关怀,是王兆胜对研究对象具有理解同情之后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呈现,在平视中倾听,在对话中不断建构,正是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求,使王兆胜对林语堂的散文研究不仅能够深入探究其作品,而且能够全面、深刻地把握林语堂的散文思想哲学。他不仅克服了学术研究中惯见的一元价值评判,而且力求站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通的研究视野下,运用平和淡然的语言,以客观求真的批评精神与人文道义加以调适、品鉴。不言而喻,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下,已经耸立成为一面风中的旗帜,化为一股潺潺的清流之溪。
[1]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王兆胜.文化散文:知识、史识和体性的误区[J].甘肃社会科学,2006,(5).
[3]王兆胜.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J].学术月刊,2001,(5).
[4]王兆胜.“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J].南方论坛,2006,(4).
[5]刘勰.文心雕龙(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林语堂.论性灵·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任屹立)
Dialogue and Construction:On WANG Zhaosheng’s Research on LIN Yutang’s Proses
YAN Tong-lin;YANG 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Guizhou,China)
Since the new period,the modern writer LIN Yutang’s works and ideas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spread,and research of LIN Yutang has become a hot academic spot.Among the researchers of LIN Yutang,WANG Zhaosheng emerges as a unique researcher.In WANG's study of LIN's proses,he elaborates on LIN’s“chat style”,demonstrates the life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the“spirit”literary thought through comparative method and grasps wholly and uniquely the stylistic idiosyncrasy and mental implication of LIN’s proses.
WANG Zhaosheng;LIN Yutang studies;“chat style”prose
I207.6
A
1671-0304(2016)05-0036-06
2016-04-20
时间]2016-10-19 1:06
颜同林,男,湖南涟源市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诗歌理论研究;杨洁,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