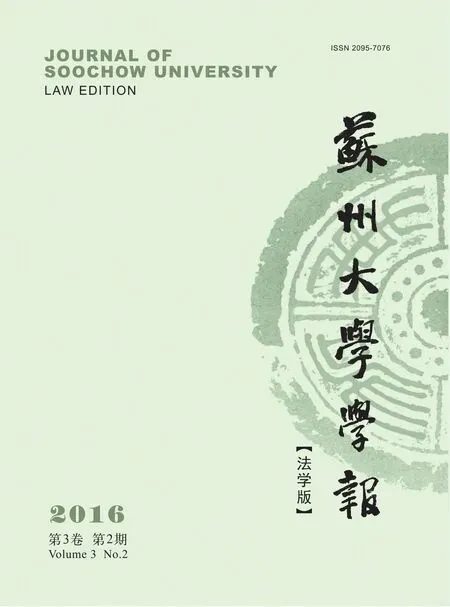罗兰诉克里斯蒂安案:扩张性时代的标志*
罗伯特 L.拉宾著 缪 宇*译
● 经典判例
罗兰诉克里斯蒂安案:扩张性时代的标志*
罗伯特 L.拉宾**著缪宇***译
通过罗兰诉克里斯蒂安案判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废弃了基于土地进入者的身份来认定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分类处理模式。但是,该案的当事人在陈述中并没有说明,引起损害发生的缺陷是隐蔽的还是显而易见的。该案当事人也无意废除上述分类处理模式。然而,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基于积极司法决策改变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将被告享有的保险作为认定注意义务标准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而要求土地占有人对所有土地进入者均负有通常注意义务。罗兰诉克里斯蒂安案判决对美国土地占有人责任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有一半的州在该案判决出台之后重塑了土地占有人责任法律。但该案判决也引发了对侵权责任法基本观念的再思考,即不当行为和不履行义务的区分。接受罗兰诉克里斯蒂安案判决还是维持分类处理模式,也体现了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张力。
土地占有人;分类处理模式;合理注意义务;隐蔽缺陷;责任保险
辉煌的岁月
回顾不久前的过去,观察20世纪中叶的侵权法图景,我们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偶尔的颤动,它们暗示着在加利福尼亚这片地震扰动之地上有些大事将会发生。比如,在Escola v. Coca-Cola Bottling Co. of Fresno①150 P.2d 436(Cal.1944).一案中,Traynor法官在协同意见书中呼吁,将缺陷产品案件的归责原则由过失责任转向严格责任。同一时期,通过Ybarra v. Spangard②154 P.2d 687(Cal.1944).案,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惊人地将事实自证规则(res ipsa loquitur)扩张适用到医疗事故案件中。四年后,Summers v. Tice③199 P.2d 1(Cal.1948).一案则在共同侵权案件中反常规地提出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转移。④本案实际上涉及到两个行为人实施的共同危险行为,虽然两个行为人均有过失,但无法证明究竟是谁造成了损害,此时由行为人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举证,行为人可以通过证明谁是真正的加害人来免除自己的责任,否则两个行为人须承担连带责任,但该判决并未对我国侵权法中类似的共同危险免责事由之争给出明确的答案参考——“Ordinarily defendants are in a far better position to offer evidence to determine which one caused the injury……In addition to that,however,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same reasons of policy and justice shift the burden to each of defendants to absolve himself if he can——relieving the wronged person of the duty of apportioning the injury to a particular defendant,apply here where we are concerned with whether plaintiff is required to supply evidence for the apportionment of damages.”)——译者注。但是,这些侵权法领域的现象可以很容易地被当作随机事件不予考虑。在1960年之后的20年多年间,并无实际证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重大改变,而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则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加利福尼亚法院将目光放在意外伤害责任基础框架的重塑上,而且,加利福尼亚法院重塑活动的范围之广,在美国侵权法中可谓是前所未有。以下案件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发展的全貌。在Greenman v. Yuba Power Products,Inc.①377 P.2d 897(Cal. 1963).一案和随后的一系列案件中②尤其是下面两个案例。参见Vandermark v. Ford Motor Co.,391 P. 2d 168(Cal.1964)(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新订的责任标准也适用于销售链上的其他被告,比如零售商)和Elmore v. American Motors Corp.,451 P.2d 84(Cal.1969)(在该案中,法院将严格责任扩展适用于因缺陷产品而受害的旁观者)。,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重新接受了Traynor法官在Escola案中的观点,为严格责任在产品致人损害侵权案件中的适用奠定了基础。而在Tunkl v.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③383 P.2d 441(Cal.1963).一案中,就免除过失行为责任的免责条款而言,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这些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在Muskopf v. Corning Hosp. Dist.④359 P.2d 457(Cal.1961).一案和Gibson v. Gibson⑤479 P.2d 648(Cal.1971).一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推翻了长期以来适用于过失责任的政府豁免权(governmental immunity)和家庭内豁免权(intrafamily immunity)。在Li v. Yellow Cab Co.⑥531 P.2d 1226(Cal.1975).一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推翻了共同过失理论,从过失责任产生时起,依据该理论,具有共同过失的受害人完全不能获得救济。在Dillon v. Legg⑦441 P.2d 912(Cal.1968).案和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⑧616 P.2d 813(Cal.1980).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降低了过失引起的精神痛苦获得救济的门槛。此外,在Tarasoff v.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⑨551 P.2d 334(Cal.1976).一案中,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期间对第三人施以暴力的威胁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为心理治疗师创设了一项须尽合理注意的义务。
在1968年——接近这一非凡时代的中点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Rowland v. Christian⑩443 P.2d 561(Cal.1968).一案做出判决,放弃了对应邀来访者(invitee)、许可进入者(licensee)或不法侵入者(trespasser)的分类,就土地占有人对土地进入者所受意外伤害应尽的注意义务而言,这一分类依据土地进入者的身份对这一注意义务进行了限制——从加利福尼亚成为联邦州时起,这些限制就是加利福尼亚侵权普通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⑪⑪对加利福尼亚法律的权威论述(在Rowland案之前的版本)援引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是1890年的案例,认为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仅负有有限的注意义务;第二个是1904年的案例,认为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也仅负有有限的注意义务。See B.E. Witkin,2 Summary of California Law 1444,1449(6th ed. 1960).⑫此后不久,侵权责任的紧缩时代(era of retrenchment)开始了,尽管这些里程碑案件中的大部分(并非Molien案判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得以保留了下来。See Stephen D. Sugarman,Judges as Tort Law Un-Makers:Recent California Experience with“New”Torts,49 DePaul L. Rev. 455(1999)(该文讨论了1984—1998年期间的加利福尼亚判例法,并且发现大部分判决转向了极为保守的模式). Sugarman将这种变化主要归结于在这期间任职的两位民主党州长所任命的法官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全国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了侵权法紧缩的现象,对此现象的类似评估,See Gary T. Schwartz,The Beginning and the Possible End of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Tort Law,26 Ga. L. Rev. 601(1992).但司法实践并没有就所有的这些紧缩现象展开讨论。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另外一宗判决中发出了紧缩时代的宣言,即Coulter v. Superior Court,577 P.2d 669( 1978)案,但是该案判决看起来却带来了重大分歧。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主人负有义务避免给社交客人不合理地提供酒类,该客人随后因醉驾导致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后来,州立法机关不仅推翻了该判例,而且也改变了一项早期判例(译者注:参见Cal. Bus. & Prof. Code § 25602 b),该判例对商业销售者也课以了民事责任。See Cal. Bus. & Prof. Code § 25602 (Deering 2003);Cal. Civ. Code § 1714(c)(Deering 2003). 州立法机关也修正了Rowland案判决所阐发的规则,但是仅仅是对该案判决要旨进行了轻微限制(在实施重罪的不法侵入者遭受损害的情况下)。Rowland案可以被理解为那些产生于非凡时代的开拓性判决意见的翘楚。⑫⑪对加利福尼亚法律的权威论述(在Rowland案之前的版本)援引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是1890年的案例,认为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仅负有有限的注意义务;第二个是1904年的案例,认为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也仅负有有限的注意义务。See B.E. Witkin,2 Summary of California Law 1444,1449(6th ed. 1960).⑫此后不久,侵权责任的紧缩时代(era of retrenchment)开始了,尽管这些里程碑案件中的大部分(并非Molien案判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得以保留了下来。See Stephen D. Sugarman,Judges as Tort Law Un-Makers:Recent California Experience with“New”Torts,49 DePaul L. Rev. 455(1999)(该文讨论了1984—1998年期间的加利福尼亚判例法,并且发现大部分判决转向了极为保守的模式). Sugarman将这种变化主要归结于在这期间任职的两位民主党州长所任命的法官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全国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了侵权法紧缩的现象,对此现象的类似评估,See Gary T. Schwartz,The Beginning and the Possible End of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Tort Law,26 Ga. L. Rev. 601(1992).但司法实践并没有就所有的这些紧缩现象展开讨论。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另外一宗判决中发出了紧缩时代的宣言,即Coulter v. Superior Court,577 P.2d 669( 1978)案,但是该案判决看起来却带来了重大分歧。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主人负有义务避免给社交客人不合理地提供酒类,该客人随后因醉驾导致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后来,州立法机关不仅推翻了该判例,而且也改变了一项早期判例(译者注:参见Cal. Bus. & Prof. Code § 25602 b),该判例对商业销售者也课以了民事责任。See Cal. Bus. & Prof. Code § 25602 (Deering 2003);Cal. Civ. Code § 1714(c)(Deering 2003). 州立法机关也修正了Rowland案判决所阐发的规则,但是仅仅是对该案判决要旨进行了轻微限制(在实施重罪的不法侵入者遭受损害的情况下)。
此外,透过对Rowland案的近距离观察,如果将目光抽离该案所处的特殊时点,考虑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1960年到1980年期间所持有的改革精神,就会发现,该案本身还是积极司法决策的典型例子。事实上,Rowland案可以被表述为多个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从最早的起源到如今,侵权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动态特征,而该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让我们能够探索那些赋予侵权法这一动态特征的基本问题: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张力,不当行为(misfeasance)与不履行义务(nonfeasance)的区别,责任保险在重新阐释(侵权法)体系的各项目标时可能发挥的作用,等等。而且,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做出里程碑式判决的背景下,该案从一开始就揭示了当事人对立陈述(adversary presentation)的不断变化,在该案中,上诉法院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当事人迫切关注的问题可能与上诉法院自身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下面本文将从这些维度来对Rowland案进行分析。
意见:里程碑即将出现
程序悖论
从Rowland v. Christian一案被上诉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时表现的内容来看,该案似乎不能再简单明了了。①该案的初审法院为Superior Court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该法院根据被告的请求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简易判决,随后原告提起上诉,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First District,Division 4,California——维持了初审判决,于是原告上诉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译者注。在指出原告James Rowland不服有利于被告Nancy Christian的简易判决而提起上诉后,法官Ray Peters以一种不置可否的方式开始阐述其判决意见,并重述了双方当事人在书面诉状中表述的案件事实。Rowland宣称,虽然Christian明知在她租赁的公寓里有一个有裂纹的浴室水龙头把手,但Christian没有就此向他发出警示,因此,当Rowland洗手后关闭水龙头时,由于水池的缺陷状况,他的肌腱和神经被割断。Christian则回应说Rowland是她的社交客人,虽然Christian承认她早已知悉浴室设备的缺陷——实际上她已经就此向公寓管理人提出了抱怨——断言Rowland也存在共同过失而且没有运用他的“视力”。Christian并不否认,在Rowland关闭水龙头时,瓷制把手在Rowland手中破裂,Rowland由此遭受损害,而这正是诉讼发生的原因。乍看起来,如果真有什么不对劲,那就是损害发生的细节并不清晰:水龙头的裂缝是显而易见的,还是隐蔽的?
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立即指出简易判决是一项“极端”的程序,这一评价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后来的裁判结果。随后Peters法官玩了一点花招。双方当事人都提交了宣誓书(affidavit)及其各自的请求(motion)和相反请求(countermotion)。但有些不可思议的是,Rowland没有声称缺陷是隐蔽的;除了在答辩中仅声称原告没有运用其视力以外,Christian也并未提到缺陷是显而易见的。Peters法官以引人注意的方式指出了这一事实方面的真空地带,指出,“没有任何相冲突的[被告方]宣誓书或[原告方]自认,原告在初审中可以认为,被告本应预见到原告不会发现这一危险。”②参见Rowland案判决第563页。
没错。然而,如果缺陷的隐蔽性是原告诉讼请求的必要因素——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告只是主张,作为一个社交客人,主人对他负有警示隐蔽缺陷的义务——那么疑惑在于,为什么虽然初审法院做出了简易判决但最终获胜的原告甚至连虚假主张(a colorable claim)都没有提出——即缺陷是隐蔽的,然而,被告可能已经在主张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motion for dismissal)中对事实进行了描述。简言之,在应予审理的事实问题方面,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巧妙地将主张负担(burden of pleading)转移给了被告,即由被告来主张缺陷不存在隐蔽性,而不是要求原告提出能够表明缺陷具有隐蔽性的事实。
当然,这一快速处理问题的方式仅在以下情况下才属必要,即被告仅对传统社交客人/获得许可进入的原告负担警示义务,这就要求隐蔽的缺陷在承认原告负有警示义务之前就已经存在。①上诉法院认为,仅当缺陷是隐蔽或无法察觉时,土地占有人才因没有对许可进入者发出警告而负过失责任,由于原告并未证明缺陷具有隐蔽性,因此维持了初审判决。——译者注。如果被告对进入其土地的客人负有一般性的合理注意义务,不论客人的身份是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还是应邀来访者,那么原告获得最终的胜利并不需要仰仗这样的处理方式。而且,让我们提前透个底,这的确是Rowland v. Christian案判决所支持的主张,即以权威的方式废弃依据进入者身份而定的分类处理模式。然而,奇怪的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致力于从程序上来为实体层面的问题(substantive display)进行粉饰,而实体层面的问题却从未为人所知。仿佛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随后的讨论和判决一无所知。
判决意见的结尾则更为怪异。Peters法官首先给出了一系列理由,表示依据进入者身份来限制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分类处理模式已经派不上用场,然后他回到了手中的案件,他写道,“(一旦关于土地占有人责任的古老概念被抛弃,原告的身份对这一责任而言不再具有决定意义,而且过失的一般原则得以适用,那么本案的结果就)并没有太大困难。”②参见Rowland案判决第568页。但令人惊讶的是,Peters法官随后看似无意识地改写了案件的事实。我们必须假设,Peters声称,被告Christian不仅知道水龙头具有缺陷且十分危险,而且“这一缺陷并不明显。”紧接着,他写道,“土地占有人意识到隐蔽的(危险)状况(concealed condition)含有致人损害的不合理风险”但没有警告(他人)或者修复的,她的行为即构成过失。③参见Rowland案判决第568页。
请注意这里的转变。虽然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到缺陷是隐蔽的还是显而易见的——与这一问题最为相关的是Christian的陈述,即只要Rowland运用了他的“视力”,他就会注意到水龙头有裂缝——但由于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了结该案件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性,这一缺陷突然变成了隐蔽的缺陷。然而,其后果就是,法院就这样对法律进行了完全没有依据的改变,从而Rowland案成为里程碑式的案件。但如果缺陷的确是隐蔽的,简易判决就是不当的,因为之前主流观点认为土地占有人对社交客人这一类进入者负有注意义务。④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土地占有人知悉的、存在于不动产上的任何隐蔽的危险状况”,土地占有人对社交客人负有揭示义务。See William L. Prosser,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 390(3d ed. 1964)(引用了侵权法重述第342条).下文将用较大篇幅对这一普遍的看法进行深入分析。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可以说加利福尼亚法院并不赞同这一通行的观点,而是要求某项要件必须存在,就像土地占有人罔顾他人而维持的陷阱(recklessly maintained trap),从而引出土地占有人对社交客人的警示义务。⑤正如审理Rowland案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指出的,“一般的规则是,不法侵入者和许可进入者负有维持不动产原状(在不动产上可能会存在缺陷状况)的义务,而土地占有人对他们则仅仅负有避免故意或恣意损害的义务。”参见Rowland案判决第565页。但即便如此,一旦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描述案件事实时认定缺陷是隐蔽的,只要接受了原告的理由,简易判决就会被轻易推翻,原告主张坚持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任何隐蔽的缺陷——不仅仅是弹簧枪类型的危险状况——都需要向社交客人予以警示。然而,到了这一步,本文并没有否定法院的立场。(按照进入者身份来限制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分类处理模式不得不滚蛋。
事实上,虽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Rowland案的判决意见中或者检讨上诉法院判决时从未提及,但在不到两年前,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已经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在Ross v. DeMond⑥48 Cal. Rptr. 743(Cal.App.1966).一案中,原告摔倒在漆黑的门前台阶上并严重受伤,因为门前台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下沉,导致原告朋友家的门廊显著升高,但是上诉法院还是明显不情愿地维持了原审判决,即原审法官不顾陪审团有利于被告的裁断而做出的相反判决。缺陷虽然可能由于门廊灯的阴影变得朦胧模糊,但它并非隐蔽的缺陷;实际上原告以前曾经来过被告的家中。在这种情况下,上诉法院受制于原告作为社交客人/许可进入者的特殊身份。但是在判决意见中,上诉法院倨傲地将分类处理模式比作“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而该上诉法院正好受制于这一分类处理模式理论。①参见Ross案判决第752页。法院讨论了Ray Peters法官——后来他撰写了Rowland案的判决意见,废弃了分类处理模式——早期作出的非常重要的两项判决意见,即Fernandez v. Consolidated Fisheries,219 P. 2d 73(Cal.App.1950)(在撰写该案判决意见时,Peters还只是上诉法院法官,他将该案定性为涉及到积极过失的案件——这是有限注意义务类型的例外)和Chance v. Lawry’s,Inc.,374 P. 2d 185(Cal.1962)(在该案中,按照Peters法官的意见,法院拒绝允许独立承包人通过尽到土地占有人的有限注意义务而受益)。
通过6∶1的表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受理了Ross案的上诉。但是该案最终在听审(hearing)之前得以和解。因此,可以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试图对此做出改变的预兆已经出现。一年后,Rowland的律师在远远不够理想的背景下提起了上诉,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地看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看起来已经觉得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论手头案件的细节如何。
理论基础:为新的体系构筑基础
然而,为何(依据进入者身份而认定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分类处理模式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看来是如此怪异?尽管受人尊敬的评论家曾质疑过这一模式的持续生命力,②See,e.g.,Fowler Harper & Fleming James,The Law of Torts ch. XXVII(1956).但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框架,依据土地进入者的三分——应邀来访者、许可进入者和不法侵入者——过去被美国各州法院广泛地接受,而且也基于声望卓著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对这一模式的长期接受而得到了有力支持。③Prosser中肯地阐明了这一理论框架:土地进入者被分为三类: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和受邀进入者。土地占有人对他们分别负担细分的义务。作为通用的模式,这些注意义务呈现出按比例增减关系(sliding scale),据此,随着访问者法律地位的提升,土地占有人负有的保护义务也就越多。参见注19,Prosser前揭书,第365页。《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在第342条(题目为:土地占有人知悉的危险状况)规定了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的义务,并规定:土地占有人就许可进入者因土地的危险状况而遭受的人身伤害应当且仅在下述情况下承担责任:(1)土地占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危险状况的存在,应当认识到该危险状况具有对许可进入者造成不合理伤害的风险,并且应当预料到许可进入者不会发现或认识到该危险状况的存在;并且(2)土地占有人没有尽到使危险状况安全化的合理注意,或者没有对许可进入者就该危险状况及其包含的风险予以警告;并且(3)许可进入者不知道或有理由不知道该危险状况及其包含的风险。参见1965年《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此外,这一分类处理模式也并非拒绝改变。随着时间流逝,一项更为细致的规则框架逐渐形成:商业组织对任何合法进入其不动产的人都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土地占有人发现并容忍不法侵入者进入土地的,不法侵入者即变成许可进入者;当不法侵入者为儿童时,应适用特殊规则,土地占有人对其负有合理注意义务。④参见注19,Prosser前揭书,第364-408页。然而,这些发展本可以被视为规则的灵活性,却被审理Rowland案的法院当作体现这一模式混乱不堪和过度复杂的证据。
基于一系列主张,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构筑了新理论体系的基础,然而,这些主张中的大部分,正如难以捉摸的隐蔽缺陷一样,并没有体现在双方当事人的辩论中。⑤我所获得的并研究的Rowland案卷宗,包括双方当事人从提交法律文书时起到最终发回重审后的和解为止所提交的每一项书面文件。这些提交的文件将在下文中讨论。事实上,比起土地占有人的义务,Peters法官在判决意见开头部分所阐明的内容更为引人注目。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该法典制定于近乎1个世纪前的1872年)笼统的文义,“任何人应对由于其在管理财产或人员时欠缺通常注意而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负责,受害人自己引起损害的除外”,⑥《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Mathew Bender,1968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迄今为止土地占有人负担有限注意义务的规则,比较反常。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的这一规定经常被理解为“我们过失侵权法的基础”。引人注目的是,原告的律师并未想到要在辩论摘要中提及这一法律规定。但是,很难据此苛责原告的律师,因为《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自远古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872年)就问世了,而与此同时,土地占有人对进入者负担有限义务的规则也已经存在——而且,与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法所支持的每一条无义务的规则(no-duty rule)或限制义务的规则(limited duty rule)相比,《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实际上是一项激励性的宣示性规定。①在上文以及注4-12提到了Rowland案时期的里程碑式案例中,只有Li v. Yellow Cab Co.案(注9)判决在实质上适用了第1714条,该案的判决出现于Rowland案的七年之后。有意思的是,该案的判决认为,《加利福尼亚民法典》旨在将该法典制定时施行的普通法予以凝练。但同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却认为,1872年的立法机构希望将法典条文进行宽泛解释——通过对条文的宽泛解释,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第1714条的文义中找到了从共同过失迈向比较过失的根据。参见Li案判决意见第865-867页。
但《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阐明一系列注意义务因子(duty factors)的关键——这些因素对于在个案中应否偏离通常注意这一“基本原则”具有决定意义——它们可能是意见书的独特标志。的确,这一均衡考量(balance of considerations),后来被称为Rowland义务因子,成为了加利福尼亚侵权法发展到今天的指路牌:
原告遭受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告遭受损害的确定性,被告行为和损害之间关联的紧密性,被告行为应受的道德谴责,预防未来损害的政策,对被告蒙受不利的程度和对被告施以注意义务、要求被告为违反义务承担责任对这一群体产生的后果,以及,就所涉及风险投保的可行性、成本和普及情况。②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4页。
将保险要素以斜体字表示是本文作者所为——而且此举是有目的的。事实上,Rowland义务因子并非源于Rowland案。它们一字不差地照搬自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10年前判决的一宗案件,Biakanja v. Irving,③320 P.2d 16(Cal. 1958).并且在后来的许多案件判决中都被援引④Rowland案判决意见援引了这些案件,以及Biakanja案。——只有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外:在之前的表述中,没有一项表述将保险作为决定一般注意义务(而非无义务或限制义务的规则)是否应当适用的因素。
很明显,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审理中是有所企图的。但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谋划并没有以当事人声明(suggestion)的形式得以实现。就像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到《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14条一样,既非原告也非被告提到过保险是能够影响到案件结果的因素。在损害发生时,尽管被告Christian只是一个公寓住客且收入微薄,却享有租客保险——以她的条件来说这是相当少见的。而且Christian的律师实际上是承保人的律师,而承保人是该案中有利益关系的真实当事人(real party in interest)。但是所有的这些细节在诉状、支持性宣誓书(supporting affidavit)、下级法院的判决和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中均并未被提及。就责任保险对土地占有人义务法重塑的重要性而言,我们所有的线索只有一点,即责任保险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首次作为政策考量引入的一项附加义务因子,而且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审理Rowland案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随后从司法上的可操作性(judicial administrability)和公平的角度提供了论据。这样,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看来,上文提到的土地进入者子类型的增多,只是致力于将一项过时的“封建遗产”——过度保护土地占有人——与现代性相适应,即通过扩展“积极运营”(active operation)和“陷阱”(trap)的概念来扩张通常注意这一要件的范围。⑤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5-566页。对于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来说,这种努力虽然用心良苦,但只是造成了混乱和过度复杂。他们以有效司法行政(judicial administration)的名义论证了完全抛弃这一分类处理模式的必要性,而不是继续维持这一分类处理模式。与此相对,Rowland案中的律师们则一心一意地在概念问题上展开了激战,在什么构成“陷阱”的定义上,双方存在矛盾——他们想到最远的事情只是暗示分类处理模式失去了活力而已。
从书面诉状、当事人的请求和辩论摘要来看,当事人也没有提到宽泛的“公平”准则(precepts of fairness),当事人只是忙于理论层面的精细化。然而,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长期以来诉诸于分类处理模式的作法并不耐烦,下面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此以最清楚明白的方式阐明的理由:
一个人的生命或肢体并不会因为他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土地或尽管获得许可但欠缺商业目的而应当在法律上受到更少的保护,他的损失也不会依法获得更少的赔偿。理性人通常并不会依据这些事项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且,为了确定土地所有人是否负有注意义务而关注于受害人的身份,即不法侵入者、应邀来访者、许可进入者,违反了我们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价值。①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8页。
稍后我将回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论断,即分类处理模式“违反了我们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价值。”现在,是时候将Rowland一案的判决意见放在一边,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案件的背后——目光不囿于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的事实,即积极主动的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构想(conception of litigation)漠不关心——来更详细地观察,一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仅仅是普通的案件,如何变成一项里程碑式的判决的。②我必须补充一点,Burke法官提交一份简短的不同意见书(持不同意见的还有McComb法官)。他认为,传统路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在法律中值得高度重视”,而且“侵权责任法的彻底修正更适合被纳入立法者的领域。”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9页。
简单的案件被改变
James Rowland要赶飞机,如果可以避免,他并不想离开他在机场的汽车,当时他将离开旧金山前往波特兰。Rowland去找他的朋友Bob Kohler,想着也许他可以把车放在Kohler寓所门口然后搭乘Kohler的车去机场。不幸的是,Kohler外出了。但Rowland想到,Kohler也许并未走远,而就在Nancy Christian的公寓附近,后者是他和Kohler的朋友,且当时Kohler一直在和Christian约会。Rowland曾经在Christian举办的聚会上到过一次她的公寓。于是Rowland给Christian打了电话,发现Kohler并不在Christian的公寓。但当他提到他打电话的原因时,Christian提出开车载他去机场。
当Rowland到达Christian的公寓时,Christian正在忙于给公寓喷漆,她在一个月之前刚刚搬进来。他们一起喝了点酒,然后Rowland请求在他们离开前往机场之前使用一下公寓的浴室设备。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侵权法的历史。有裂缝的浴室水龙头出现在了Rowland和他要搭乘的西部航空公司飞往波特兰的航班之间,这一水龙头严重割伤了他,导致其肌腱和神经被切断,Rowland因此需要住院治疗。损害发生的时间是1963年11月30日——正好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Rowland v. Christian一案做出判决的5年多之前。③实际上该案判决时间为1968年8月8日。——译者注。
在起诉状中,Rowland以标准的法律术语宣称,“上述浴室设施对所有使用它们的人来说非常危险,而被告们非常了解这一事实。”④请注意,这里的被告是复数。其他的被告是建筑物所有人。在对建筑物所有人的诉讼中,Rowland立即获得了更大的胜利。初审法官接受了建筑物所有人要求简易判决的申请——该法官并非审理Rowland v. Christian的初审法官,即使诉讼合并审理以后也是如此——做出了有利于Rowland的裁决。但是,对建筑物所有人的诉讼程序就到此为止了。这一诉讼程序一直被搁置到Rowland对Christian的上诉结束,随后Rowland对建筑物所有人和Christian的诉讼请求都以和解告终(对此下文将会展开讨论)。也许这些浴室设施具有危险性,但是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原告并没有提到这一危险是否具有隐蔽性。令人难以捉摸的是,Rowland在起诉状中之前声称,“浴室水槽中的冷水龙头上有裂缝,而且应当被更换”——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断言Christian早已知道冷水龙头上有裂缝(对此Christian并无争议)。但不论是Rowland的起诉状还是他的支持性宣誓书,都没有对浴室设施的描述留下只言片语。
在推进诉讼合并(joinder)这一方面,Christian也没能做的更好。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她在答辩状中毫无证据地提出Rowland“具有共同过失”而且他没有运用其“天然的工具,包括他的视力。”然而,在她的答辩状或为了支持她要求简易判决的请求而递交的宣誓书中,她并没有对水龙头的外观加以描述。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对水龙头的缺陷状况作出事实说明,然而就要求法院依据诉状驳回起诉的请求(motion for dismissal on the pleadings)而言,这一事实说明本来对妥善处理这一请求至关重要。
数年后,当我与Nancy Christian面谈时,她对在书面诉状中语焉不详的真实生活背景透露了更多内情。她回忆到,发生损害的公寓是她一个多月前搬进去的,这个公寓简直是个“猪圈”——完全是乱七八糟。事实上,她最终在绝望中搬出了公寓,当时楼上的租客为腾房提前对楼上公寓进行重新装饰,大量的蟑螂在装修期间蜂拥而至。
就水龙头而言,当她回想起来,裂缝实际上并不是隐蔽的,只是被灰尘和污垢掩盖了而已。她猜测Rowland可能并没有注意到缺陷。当然,这些观察言论是多年以后了。但Christian的回忆清楚地表明了律师业务活动的中立性——实际上,充其量,中立的是Rowland方律师,他仅仅希望避免简易判决,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原告方本可以提出虚假的事实说明:缺陷是隐蔽的。
但是,促使Rowland的律师对Christian这个收入微薄的年轻女性提起诉讼的首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不但不足为奇,而且同时也令人吃惊。不足为奇的是,Christian只是一个普通的被告;她被证实享有租客保险。同时,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有这样的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收入微薄的大城市公寓租客享有责任保险,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事实上,她投保并非出于个人责任的考虑,而是因为她有一些值钱的纯银银器,而这是她的传家宝。这些偶然性就是诉讼产生的原因——并且导致案件在不确定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走进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
Christian与她的律师在事实上并无关系,这对应了她在案件中名义当事人的地位。John Healy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保险辩护律师,他在该案中为Christian的承保人处理该案。Christian与他唯一的联系就是准备她的宣誓书和宣誓证词(deposition testimony)。出人意料的是,Christian实际上是Rowland的律师Jack Berman的好友之一——事实上Berman是Christian一个相当要好的朋友。诉讼开始了两个月后,Berman搬到了新的办公室,他将自己的地毯给了Christian,协助她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公寓变得更加宜居!甚至,我们可以猜测,虽然在当时这并不确定,Rowland雇用Berman——他之前主要是刑事辩护律师而非人身损害方面的执业者——作为自己的律师乃是出自Christian的建议,Christian在诉讼开始前就已经认识Berman有一段时间了。①虽然Nancy Christian想不起来她是否曾经将Berman推荐给Rowland,但她觉得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
一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认识Jack Berman和John Healy的律师告诉我,两者都属于“街头律师”(street lawyers)。这位律师并没有任何蔑视的意思。按照新闻报告的说法和一些目前仍然健在的朋友的回忆,Berman在刑事法庭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并且的确具有鲜明的旧金山人性格。②在《旧金山纪事》2002年4月12号A23版发布的一则讣告中,Berman的一群老友(都是具有政治联系的旧金山人)将他描述为,一个对拉斯维加斯赌桌充满激情的狂热赌徒;长期的爵士和职业拳击爱好者,喜欢流连于市政厅对面一家知名酒吧。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作为一名民权积极分子前往南方,而且从1982年起他甚至在那里担任地方初级法院法官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将他形容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参议员Dianne Feinstein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前,Berman很早就与她结婚了,这一段婚姻持续了数年(1956—1959)。但是,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最初并非民事诉讼中的原告的律师,而且从各方面看来,他也不是将他接手的案件推进到州最高法院的上诉律师。在参与到一宗看似惯常的不动产责任案件并担任被告律师这一点上,Healy看起来——至少在初审法院如此——更为内行。但与Berman一样,他也不是上诉律师。简言之,本案中并没有判例案件律师(test case lawyer)——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当Peters法官及其同事决定聆讯该上诉案件时,这一点在法官们所看到的书面记录中非常明显。
但只有在仔细研究土地占有人对社交客人应负有义务——当James Rowland命中注定式的遇到裂开的水龙头时——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这些书面记录。与其他州一样,加利福尼亚法院当时赞同按照土地进入者的三种身份——应邀来访者、许可进入者或不法侵入者——来认定土地占有人注意义务的分别处理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法院似乎以最为吝啬的方式赞同了这一模式。固然,就进入商业不动产的人而言,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Oettinger v. Stewart①148 P.2d 19(Cal.1944).在附带意见(dictum)中,审理该案的法院宣称,当土地占有人从事土地的“积极运营”(active operations)时,加利福尼亚法院承认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这是侵权法重述中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仅负有限义务规则的例外。在Oettinger案中,房东告知租客大楼中没有空房后,走下楼梯时意外摔倒落在租客身上,导致后者严重受伤。案中遵循了大部分州的作法,广泛地认可了土地所有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不考虑土地所有人是否认识到进入者的出现会带来经济利益这一特殊之处。如果Rowland在浴室中遭受的伤害发生在隔壁的咖啡馆,即使他仅仅是为了使用浴室的设施而在咖啡馆停留,咖啡馆的经营者也应对其尽到充分的合理注意义务。
然而,就进入私人住宅环境的社交客人而言,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问题上,下级上诉法院的判决充斥着混乱,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实际上也没有阐明这一问题。一些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表明,社交客人应当保持不动产的原状;换言之,如果土地占有人采取的安全措施对其直系亲属个人而言已经足够,那么土地占有人就没有义务采取更多的安全预防措施。②这是对加利福尼亚判例法中Ross v. Demond这一上诉案件的解读,在Rowland案判决出现的两年前,加利福利亚最高法院同意就此案进行听审(此案最终以和解告终)。Ross案判决援引了一些早期的判决,以支持判决中对许可进入者类型的严格限定。参见Ross案判决,载加利福尼亚案例报告第48卷(48 Cal. Rptr.),第747-749页。将其转换为适用于许可进入者的行为规则,这常常被理解为,加利福尼亚的土地占有人仅仅负有避免故意和恣意损害访问者的义务,除此以外土地占有人不负其他义务。③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5页。对这一有限注意义务的另一观察路径是传统普通法中对不当行为(misfeasance)与不履行义务(nonfeasance)的区分。因为故意和恣意的不当行为已经演变成一种积极的不当行为,故该行为会排除土地占有人通常享有的保护。事实上,通过宽泛界定主人的“积极运营”,司法实践已经在一些案件中将土地占有人负担的通常注意义务间接地扩展到社交客人身上。参见前注38,Oettinger案。我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以较大篇幅讨论不当行为与不履行义务的区分。
与此相反,大部分州认为,只要主人知道危险存在,且他有理由预料到这一危险不会被发现,那么他就必须对社交客人发出警示,这一规则也被《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所明确承认。④参见1965年《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简言之,侵权法重述要求土地占有人对已知的隐蔽危险予以警示,隐蔽风险由土地占有人的行为——近乎于轻率的不当行为(reckless misconduct)——引起的这一标准,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加利福尼亚法律的混乱状况,以及其他州在理论发展上的不均衡,大概可以归结为对一个概念的争议,即什么能构成“陷阱”。在早期,陷阱往往依靠弹簧枪这一例证来予以说明,在同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判决中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与土地占有人为了顾及自身利益而就一系列“陷阱”——如前院被遮挡的香蕉皮和饭厅地面中比较湿滑的部分——而应尽的义务相比,土地占有人对他人所负担义务极为有限。但是在William Prosser的与Rowland案同时期出版的一版侵权法权威著作中,“陷阱”获得了全新甚至更为广阔的含义:
[陷阱]最初是在看似安全但实际并不安全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重点并非在于有人故意造成伤害,也不在于任何积极的不当行为,而仅仅是土地占有人负有义务向许可进入者披露任何他所知道的土地上的隐蔽危险情况。这一重点逐渐成为了陷阱概念的一部分。⑤参见注19,Prosser前揭书,第390页。
在这一点上,Prosser参照的是被他称为“压倒一切的权威”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值得一提的是,Prosser本人就是《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的报告人。①同上注。与审理Ross案的法院的立场一致,Prosser在下一个脚注中援引了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的一项判决,Fisher v. General Petroleum Corp.,267 P.2d 841(Cal.App.1954),以表明偶尔还是会出现背离《侵权法重述》之路径的“例外”(也许有人会称之为倒退)(译者注: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在该案中认为《侵权法重述》第342条不符合本案的事实,也并非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值得注意的是Moore法官在协同意见书中实际上比较倾向于《侵权法重述》第342条)。但是Prosser在前一个脚注中又援引了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的另外一个案件,Newman v. Fox West Coast Theatres,194 P. 2d 706(Cal.App.1948),该案支持了《侵权法重述》的立场(译者注:事实上,该案判决意见为Moore法官撰写,他采纳了与《侵权法重述》第342条相同的立场,但是他明确写道,“对该上诉案件的判决并不依赖于《侵权法重述》第342条所确立的规则。”),从而隐晦地表明了加利福尼亚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
这就是当时Berman和Healy发生碰撞的战场。由于Berman并无法断言缺陷是隐蔽的,而即使对于在大多数司法辖区适用的规则而言,隐蔽缺陷也是一项(认定土地占有人责任的)基本要件(baseline requirement),于是,不足为奇地,Berman立即就失去了其用武之地——初审法院按照被告的诉状做出了简易判决。Berman并没有泄气,他代表Rowland向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坚定不移地坚持着他对案件的陈述,他在最初的上诉摘要(opening brief)中说到:“被告明知水龙头把手已经有了裂缝,而且也已经认识到有裂缝的水龙头已经构成了一种危险状况。”Rowland方仍然没有主张裂缝是隐蔽的。但在摘要的不到2页半的论证部分,Berman才几乎以一种事后补记(afterthought)的形式首次提出,“法庭面临的唯一问题是,裂缝是隐蔽的危险抑或是误导性的状况(deceptive condition)。”如果是这样,Berman继续写道,就无法阻止法院适用“作为无责任规则例外的陷阱规则”——但费解的是,Berman并没有在论证部分接下来的来几段话中对这一例外规则做出界定。
于是,“委聘条款”(terms of engagement)就确定好了:Healy在答辩摘要(reply brief)中指出,加利福尼亚从未接受过《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而且他认为,“所谓的”陷阱例外规则,“除了蓄意和故意的‘诱捕行为’(entrapment),诸如保有弹簧枪和其他隐蔽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一种虚构的说法。”与此相对,Berman在答辩摘要中以不超过一页的篇幅,对Healy的辩驳做出了回应,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法院在本案中适用《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到此,事情就结束了——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敦促法院在阐明隐蔽缺陷的含义之外来进一步大胆地重新思考分类处理模式的合法性(legitimacy)。②与此相反,在Ross案中,在主张该案只是一个原告可以作为受邀进入者或许可进入者获得救济的常规案件后,原告上诉人在提交给上诉法院的初始上诉摘要中主张废弃分类处理模式。参见Ross v. Demond案上诉摘要第15-17页。与Berman的摘要相比,Healy的答辩摘要只是在篇幅上更长,而且阐明了之前的现行判例法。在19页的答辩摘要中,一多半都在援引(大部分仅仅具有较边缘的相关性)两项早期的先例,这两项先例对土地占有人对许可进入者负担的义务进行了狭义解释。
上诉法院将目光放在了双方摘要中的论证部分上,并且很快就解决陷阱例外规则列举了的三种可能性:它并非加利福尼亚法律的一部分;按照被告律师的建议,它的含义极为有限;按照原告的建议,它的含义相对宽泛。③Rowland v. Christian,63 Cal. Rptr. 98,102-104(Cal.App.1967).随后,不足为奇的是,法院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法院非常明显地倾向于土地占有人仅负有有限的义务,如果土地占有人应当对社交客人负有义务的话——因为,“记录中的信息并没有任何事实性主张或没有证据的结论性主张,这些主张描述了水龙头的状况,比如它的外观、位置,以及照明状况,浴室状况……记录中也欠缺任何其他事实的信息,这些事实能够支持原告因隐蔽的危险而遭受伤害的结论。”④同上注,第104页。
事后看来,如果案件的主题只是从狭隘的眼光来看Rowland应否得到救济(而不涉及到分类处理模式的正当性),案件正是这样被上诉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那么原告向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申请对此案进行听审,就意味着这个案件就已经走到尽头了。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在Rowland案判决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并没有独立的辩论摘要制度;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只是基于上诉法院归档的辩论摘要重新复查案件——并审核听审申请(可能会达到30页甚至更多)。①See Cal. R. Ct. 28(Deering 1968). 1985年,案件复核申请书被限制在了30页以内。此前,对这种申请书并没有任何页数限制。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的评论对此予以了解释,即限制页数的原因在于当事人可以基于案情实质(on the merits)额外提交一份摘要。See Cal. R. Ct. 28(Deering 1985).在Rowland案判决出台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同意就此上诉案件进行听审后,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补充性摘要(supplemental briefing),而且在有些案件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在Rowland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则没有这么做。如果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同意了当事人的听审申请,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申请和答辩就成了对立双方当事人按照他们的认识来阐明问题的最后机会。一如既往地,Berman仅要求适用《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42条,而Healy则从上诉法院的判决中得到提示,严密地回应道当事人并没有最起码的关于隐蔽缺陷的陈述,而只有存在隐蔽缺陷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才应当重新审核有利于被告的简易判决。双方提交的陈词都不超过4页,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分类处理模式会被抛弃的可能性。②在当时的诉讼中也没有法庭之友(amicus parties),以便他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如果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其更大的企图给出了理由——比如,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补充性摘要——法庭之友会不会对此提交意见书,则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与Berman的申请书类似,Healy的申请书——即对原告向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提出就该案进行听审的请求做出回应——只有草草4页。看起来可以公平地说,双方律师的工作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双方在口头辩论中谈到了放弃分类处理模式的可能性吗?也许吧,但是对此我只能猜测,因为当时双方在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没有被誊写或记录下来。我曾与Rowland案时期的法庭书记员进行过交流,这一交流表明,在大部分案件中,法院在听取双方当事人口头辩论时,最终判决意见书的草稿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并交给了负责书写判决意见书的法官;简言之,在大多数情况下口头辩论只是走个过场。于是,极有可能的是,如果抛弃分类处理模式的可能性的确在双方当事人口头辩论期间被提到,那么这也是基于法官而不是当事人的倡议。③需要附带说明的是,Jack Berman此时也许已经得出了他需要一些外部援助结论。在案件相关的材料和论据中,Rowland的协同律师首次出现在Pacific Reporter(但并非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官方报告或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的报告)的批注(headnotes)中,“Jack K. Berman和Cyril Viadro,旧金山,代表原告和上诉人。”参见Rowland案判决,第562页(重点为本文所加)。在我与他人的多方交流中,这两点都得到了证实:Cyril Viadro在当时是一名著名的本地上诉出庭律师;Berman本人非常不愿意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就此案进行争讼。不管怎么说,Berman都被认为是在Rowland v. Christian案中胜诉并促成不动产占有人责任法改革的律师,而且该案从起诉到和解谈判都一直是他的案子。他仍然健在的同事告诉我说,Berman对这一成就极为自豪,而且事实上,他对被收录进了Kenneth James Arnold 的California Courts and Judges一书中(人物传记第63号,7th ed. 1995)也极为自豪——该书提到,Berman后来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在被收录进该书时恰好在这一位置上退休——该书出版于Rowland v. Christian案的近30年后,并在人物传记中以如下文字结尾:“Berman法官作为律师受理的重要案件包括Rowland v. Christian案,就不动产占有人负担的义务而言,该案废弃了应邀进入者、许可进入者和不法侵入者的区分。”无论案件经过如何,在Rowland v. Christian案件中,双方律师在战壕中的短兵相接以独特的方式确认了,法院按照自己的标准准备改进和重塑侵权法,一个非凡且主动的法院。
后果:对案件的评价
在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依据新定的标准——土地占有人对所有的土地进入者均负有通常注意义务——将案件发回重审之后,Berman将案件求助于旧金山的一个原告诉讼专家团Walkup律所、Downing律所和Wallach & Stearns律所,他们迅速地了结了案件。专家团中仍然健在的律师回忆,和解金的数字不到1万美元,这符合案件朴素的细节。④档案中有记录的来自Walkup律所的两名律师与我进行了面谈,在回忆起这一赔偿金总额时,他们没有区分代表Christian的保险人被告和建筑物所有人被告。我还找到了一位当时代表建筑物所有人的律师,并且与其进行了交流,他指出他的律所更多地代表了保险人,而不是被告个人,这与Christian的情况一样,她的律师也更多地代表了保险人而非她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定,每方的保险人各自支付了多少和解金。无论如何,就和解所支付的金额数量来说,Rowland案很明显并非那种令人难忘的案件。很明显,Rowland的伤可得治愈且不留下任何后遗症。实际上,据一个之前工作于Walkup律所的律师回忆,该案在调解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Rowland搬离了加利福尼亚并且定居了下来,他对于为了这件已经被他抛诸身后的事情而不得不回到加利福尼亚并露个面感到有些生气。在Nancy Christian的律师Healy为她办完宣誓作证以后,Nancy Christian对案件就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甚至懒得询问案件的结果。她再也没有见到Rowland。当然,这些事实并没有贬低该案的重要性。一些法律发展上的里程碑会对直接当事人的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其他的里程碑,如Rowland v. Christian案,则脱离了加利福利亚最高法院的控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当事人则继续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回顾过去。
里程碑式案件的影响:对法律的影响
基于以下两种原因中的任一原因,理论重塑都会具有极大的显著性:理论重塑对类似情况中的未来当事人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者,通过其他司法辖区法院对该理论重塑的接受,它会产生广泛的影响。Rowland案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典范。
未来的案件,类似的案情
想想最初当事人如何推进Rowland案本身,直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介入并废弃了分类处理模式。即使依据着眼于隐蔽缺陷而更加宽松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如果水龙头上的裂缝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在最后的分析中,Rowland没能在辩论中指明缺陷隐蔽的理由在于,缺陷并不具有隐蔽性,而且他在使用水龙头时认为,对他而言避免伤害并不成为问题——那么该案都不会进入到陪审团评议阶段(而是被直接驳回)。许可进入者仅能就隐蔽危险造成的损害受偿,这一要件会阻碍Rowland受偿。更一般地说,无论对Rowland案的事实进行何种说明,仍然会存在伤害系由非隐蔽性的危险状况等引起的诸多可能性:社交客人自身的健忘(想想在Ross v. Demond①参见Ross案判决,载加利福尼亚案例报告第48卷(48 Cal. Rptr.),第743页。一案中,顶部台阶与门廊平台之间被遗忘的空隙),疏忽或对风险的完全漠视。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中,即使遵循Rowland案判决所阐发的规则,被告也可以在陪审团面前提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共同过失的抗辩。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依据Rowland案判决所确立的规则,陪审团就案件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构成通常注意——消除危险还是警告义务——以及何种行为能够成为抗辩。与此相对,依据分类处理模式,更为频繁出现的情况则是:案件无法满足危险的隐蔽性这一基本要件。而只有满足了这一要件,案件才不会被即决驳回(summary dismissal)。②当然,即使在分类处理模式下,陪审团仍然有较大的决定空间。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正如我的描述所暗示的,Rowland案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这样的案件;如果原告做出了更清晰的陈述,指出水龙头的外观并没有体现出它的危险状况,有可能就由陪审团来讨论责任问题——至少原告得到的绝不仅仅是简易判决。
类似地,就受害人必须是许可进入者这一要件来说,该要件在Rowland案中也得以承认——被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并没有予以警示——在许多情况下主人对危险的认知可能还不如客人。想想Carter v. Kinney③896 S.W. 2d 926(Mo.1995).案的事实,在这桩最近发生在密苏里的案件中,法院坚守了传统的分类处理模式。在该案中,原告是一名社交客人和圣经学习小组成员,他为了参加聚会提前抵达了被告的房屋并在冰雪上滑到,而这些冰雪是被告前一天晚上最后清理车道上的积雪而堆积起来的。密苏里最高法院维持了简易判决并驳回了案件上诉,其理由在于,被告并不知道危险状况的存在,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说他对许可进入者并不负有警示义务。也就是说,即使在遵循Rowland案判决的司法辖区,法院也并非必然肯定土地占有人的责任。被告可能会主张原告具有共同过失,或者被告可以仅仅主张,合理注意义务并不要求被告在上午七点之前起床以便于为了即将到来的客人清理车道上的积雪。但是这些事项将由拥有相对自由裁量权的陪审团来决定,而不是按照分类处理模式基于被告欠缺对危险情况的认识而不予考虑。
因此,分类处理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分类处理模式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请注意,我甚至没有提到非法入侵者这一身份,类似地,非法入侵者作为一个独立的有限注意义务类型也被Rowland案判决所抛弃,Rowland案判决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简单地说,更多地适用于不法侵入者)替代了土地占有人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即避免对非法入侵者故意实施不当行为。①在判决意见的最后,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加上了这样的限定用语,“鉴于用来认定原告具体身份的特定事实,尽管原告作为不法侵入者、许可进入者或受邀进入者的身份会对原告的责任问题起到一定影响,但是原告的身份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参见Rowland案判决意见,第568页。但是,通过“一定影响”这一表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心中可能所想的,乃是不法侵入者可能会溜到不动产的偏僻角落,而在这一偏僻角落中,危险状况会给他人带来风险是无法预见的,从而在这样的案件中,土地占有人不负责任。当然,这与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全面认可合理注意义务标准完美地保持了一致。总之,抛弃分类处理模式的结果在于,当无法确定不动产占有人知道危险的存在和/或不动产上危险状况的隐蔽性时,决策权由法官转移到了陪审团。
未来的案件,其他地方
接下来讨论的是Rowland案在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影响。在1964年,当Prosser出版了其权威著作的第三版时,在Peters法官眼中,分类处理模式的废除虽然毫无进展但却有了一丝曙光。②关于Peters法官早期就倾向于废弃分类处理模式的信号,参见前注22。此时,Rowland的诉讼请求刚刚开始了它在加利福尼亚法院的漫长旅程,也没有其他普通法司法辖区认为,接受如Fowler Harper和Fleming James等评论家的意见是合适的,这些评论家建议分类处理模式应当被扫进侵权法历史的垃圾堆。③参见前注23,Harper & James前揭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分类处理模式的普通法渊源,英格兰已经于1957年通过立法废除了分类处理模式。参见1957年《占有人责任法令》(5 & 6 Eliz. 2,c. 31)。而美国最高法院则在Kermarec v. Compagnie Generale Transatlantique,358 U.S. 625(1959)一案中拒绝在海事案件中承认分类处理模式。在判决意见中,Peters法官援引了上述法令和案件。参见Rowland判决意见,第566页,第568页。然而在七年之后,当Prosser再次修订他的著作时,他认为有必要专门论述最近判决的Rowland案,并大胆谨慎地看看未来会如何。在当时,只有夏威夷追随了加利福尼亚的脚步。虽然如此,正如Prosser所言,“这些判决太新,以至于我们无法揣测它们在其他地方能否被效仿,尽管这的确是并非不可能的;……”④William Prosser,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 399(4th ed. 1971).
Prosser并没有活着看到他谨慎的预测成为现实。但在1984年,当John Wade和其他人出版了Prosser著作的第五版时,已经有八个州接受了Rowland案判决并完全放弃了分类处理模式,另外还有五个州虽然维持了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仅负有有限注意义务的立场,但取消了土地占有人对受邀进入者所负义务和对许可进入者所负义务之间的区别。⑤W. Page Keeton et al.,Prosser and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 433(5th ed. 1984).Prosser著作的第五版接着警告说,在1979年以后,以任何形式对Rowland案判决的接受都“遇到了急刹车”——第五版令人赞许地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这可能表明,司法实践越来越对20世纪60年代特定现象持根本不满的态度,即以宽泛的合理注意标准取代量身定制的侵权法规则。⑥同上注,第433-434页。相对来说,Prosser愿意接受分类处理模式的废弃,而令人惊讶的是,与此相对,考虑到接受Rowland案判决会带来的失去动力(loss of momentum),新的编撰者酸酸地指出,“至少,就传统上限制土地占有人对成年不法侵入者负担义务的背后考量而言,法院看起来获得了赞赏,而且,有建议主张,放弃过去多年发展而来的法学理论(jurisprudence),而代之以诱人的法律万能药(a beguiling legal panacea),而法院则更普遍地对这些建议采取了一种合理的怀疑主义。”不论这一概括观察的准确性如何,我最近对接受Rowland案判决的司法辖区进行了统计,该统计结果表明,Rowland案判决意见体现了持续的有说服力的影响:到2002年末,我发现已经有十个州完全放弃了分类处理模式,还有十三个州则仅仅维持了就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负担有限注意义务的立场。①已经完全放弃分类处理模式的州(至少有一项公开的上诉判决)包括: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夏威夷,路易斯安那,蒙大拿,内华达,新罕布什尔,纽约和罗德岛。就应邀进入者和许可进入者放弃了分类处理模式,但就不法侵入者仍然维持了有限注意义务立场的州包括:伊利诺斯,爱荷华,缅因,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新墨西哥,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田纳西,西佛吉尼亚,威斯康辛和怀俄明。在上述提到一些州中,以及剩下的坚持分类处理模式的州中,就分类处理模式的地位而言,在州内不同巡回法庭间偶尔会出现相冲突的判决意见。因此,自Rowland案判决作出以来,美国几乎一半的州都重塑了土地占有人责任的法律,这足以证明Rowland案判决的影响和十足后劲。
里程碑式案件的影响:引起广泛地关注
然而,对此,我们是应该看到其乐观的一面还是悲观的一面呢?在Rowland案判决作出的30年后,仍然有二十七个州坚持了分类处理模式,这的确意味着与放弃被法院称为“违反了我们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价值”的路径相比,可以说Rowland案判决更多地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②参见Rowland判决意见,第104页。当然,在维持分类处理模式的州中,可能有一些州并没有机会来重新考虑是否应当坚持分类处理模式,尽管在Rowland案出台三十年后,我认为这些州最多只是少数。
事实上,不言而喻的是,Rowland案促成了对意外伤害侵权责任之中心指导原则的再评估:不当行为(misfeasance)与不履行义务(nonfeasance)的区别。③在救助义务背景下的讨论,参见Richard A. Epstein,A Theory of Strict Liability,2 J. of Legal Stud. 151,197-204(1973)。关于现代运用,参见Harper v. Herman,499 N.W.2D 472(Minn. 1993).在最严格地适用这一指导原则时,通过拒绝将好的撒玛利亚人的道德认同(moral approval)转化为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该原则为个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作为一项伦理问题,当婴儿躺在铁轨之上,火车奔驰而来,假设旁观者拒绝实施没有风险的救援行为,这一点可能无法获得我们的赞同。但是在传统上,侵权法并不承认一个陌生人负有保护他人免受伤害的法律义务。
这一准则——没有积极行为的义务——是侵权法的一项主旨(leitmotif),但它也受制于诸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出的例外,尤其是特殊关系的存在。④参见1965年《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314A条。土地占有人对各类土地进入者负担责任的传统规则,也是这一主题的变种之一。⑤试想,在这一点上,依据传统的分类处理模式,应邀进入者类型体现了(土地占有人与应邀进入者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观念;尤其是土地进入者的出现可能会给土地占有人带来经济利益。此外,就“积极运营(active operations)”这一例外的后来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不当行为和不履行义务进行区分的直接回应:如果土地占有人从事了积极运营,承认谨慎行事的义务会带来实施行为的积极义务,就不再成为问题。在现代,将这些义务描述为中世纪保护地主豪绅理念的残余,只是一种混淆视听(red herring)的做法。更确切地说,主人为家庭成员提供合适的家庭环境,而且在主人看来这一家庭环境对家庭成员是不存在风险的,那么问题在于,除此以外,文明规范(norms of civility)对主人是否还有更多的要求?当不动产老化时,修复成本往往包含时间和金钱的大量耗费,这会导致房主将房屋的维护工作和风险消除事务推迟到其他日子,隐居在自己的住所中并凑合着过日子。退一步来说,虽然这么说有些异乎寻常,但住在年久失修的房子里——也可能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不是仅仅出于经济原因的话——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倾向,主人一般不会通过在不动产周围树立警示标示来予以补救。这种家常的事实是否违反了“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价值”,非常值得怀疑。
如果说法院对于将社交客人依商业访问者标准来对待还明显有些不情愿的话,那么土地占有人对不法侵入者也负担合理注意这一立场获得的支持就更少了。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在接受Rowland案判决主张提升社交客人之地位的州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州有意在改善不法侵入者地位方面也接受Rowland案判决。于是,再一次地,由于Rowland案判决意见对继续承认身份考量(即土地占有人对进入者负有的义务依据进入者的身份而定)抱有敌意,它取消了关于义务分析的一项基本规则。但是,这一问题(指如何对待不法侵入者)与如何对待社交客人并不一样。在传统上,对试图从自己的不当行为中获利的原告,一直不被侵权法看好。
不法侵入者就是这一类坏蛋的原型。让我们来看看加利福尼亚出现的一个案子,该案出现在Rowland案判决出台之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例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不法侵入者深夜爬上了学校建筑的屋顶,试图不法地拿走探照灯,却从天窗摔了下来,于是他选择起诉,然而,鉴于Rowland案判决带来的法律上不确定性,加利福尼亚学区决定与不法侵入者和解结案。①在该案中,不法侵入者最终四肢瘫痪,学区在和解时支付了26万美元,同时为不法侵入者的生活每月支付1200美元。参见Calvillo-Silva v. Home Grocery,968 P. 2d 65,71(Cal. 1998)对该案的讨论。该案引起了强烈的抗议,这促使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立法确定了土地占有人对非法侵入的冒犯者(criminal trespassers)仅负有受到严格限定的义务(a narrowly limited duty)。②《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847条(Deering 2003)。Calvillo-Silva案还讨论了第847条立法史中另一个关键案例,在该案中,摩托车盗窃者在农场主的田野里兜风,撞上凹坑以后严重受伤,并获得了接近50万美元的赔偿。参见Calvillo-Silva案判决,第71页。对于土地占有人使用弹簧枪刺戳不法侵入者来说,人道主义价值的确是一项有力的反对理由。但是,设置弹簧枪与允许在私人海滨物业上堆积有害垃圾——如碎玻璃——并明确标示“不得擅自闯入”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在学校天窗上涂鸦。将后面的这些疏忽也视为人道主义价值的欠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过度轻信。但这些疏忽可能是大多数不法侵入者遭受损害并就此提起诉讼的起因。不法侵入者有意识地游荡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并且随后在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法律在传统上对这些不法侵入者给予的关照较少。法律是否应当偏离这一传统(而遵循Rowland案判决),这似乎充其量只是一个有争议的主张。
到了这里,是时候再次承认Rowland案判决的说服力了——毕竟,接近一半的州都站在Rowland案判决要旨这边。这该如何解释呢?尽管没有魔术公式来权衡Rowland案中的各种因素,据我推测,如同事故法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责任保险——在Rowland案判决中,这一义务因子(duty factor)首次被明确作为一项一般政策考量被悄悄地引入了加利福尼亚侵权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③请比较Gibson v. Gibson 479 P.2d 648,653(Cal.1971)(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指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忽视责任保险的广泛普及性以及它对家庭内诉讼的实际效果。尽管在没有其他要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责任保险的存在就认定责任成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是否废除父母不对过失负责的免责事由而言,在对此做出明智的决策时忽视责任保险这一要素,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基于父母可能被要求向子女支付赔偿金这一过时的假定而不再考虑子女—父母诉讼。”)由于房主几乎普遍享有房屋保险,从保险统计的角度来看,不动产致害事件的发生也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而且不动产致害的成本相对有限(在不动产责任中,意外死亡或灾难性伤害极为少见)。④有趣的是,正如Nancy Christian购买租客保险基于单方原因——也就是说,为她的餐具投保——而非出于她可能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考虑一样,房屋保险主要用于满足抵押人并且保护房屋和个人财产免受不可预料的损害或损失,而非基于侵权责任的考量。从赔偿的角度来看,在当时,尊重房屋所有人的自主或惩罚不法侵入者(尤其是非重罪的不法侵入者)的呼声在许多地方已经减弱。当然,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侵权激进主义(tort activism)的全盛时期——的确属实,而且毫无疑问地,这一精神的痕迹仍然存在于今天的某些其他地方。
Rowland案判决从一个更为彻底的制高点进入了智识思潮(intellectual current),它获得了司法界的广泛接受;的确,就侵权法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进化而言,它可以被视为这一进化的主旋律之一。以免责事由或有限的注意义务的名义,依据身份来阻却过失行为责任的作法,成为了一项新兴范式——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以危险范围为基础的义务——的牺牲品。⑤对依据身份对过失责任进行限制的讨论,参见Robert L. Rabin,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ault Principle:A Reinterpretation,15 Ga. L. Rev. 925(1981)。这一观念转变的最著名例证可能是,纽约州最高法院在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⑥111 N.E. 1050(N.Y. 1916).这一产品致害案件中放弃了相对性(privity)要件。类似地,就基于合同产生的限制工伤救济的抗辩事由而言,批发式地通过劳工赔偿法律,就标志着对这些抗辩事由的拒绝。在1960年到1980年这段辉煌岁月之前,通过一些案件的判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对上述运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Muskopf案(拒绝了对政府责任的概括免责),Gibson案(类似地,否决了家庭内侵权的免责)以及Tunkl案(限制合同对过失责任的免责条款)。①参见前注6-8。Rowland案判决则在不动产责任案件中取消了基于身份的责任限制,从而站在了致力于推进这一新兴范式的最前沿。
结 语
假定案件在被发回重审以后没有以和解告终:James Rowland最后会胜诉吗?并不一定。在他们离开公寓前往机场前的那一刻——Nancy Christian可能正在换掉溅上油漆的衣服,Rowland临时起意决定使用浴室——Nancy Christian没有提到在使用水龙头时应当小心注意,这是否构成通常注意的欠缺?答案既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毕竟,在等候房主前来修理期间,这些设施被她持续使用长达一个月之久,却没有对她本人或客人造成事故。因此,Rowland因为没有运用他的“视力”而具有的共同过失(甚至自甘冒险)——这在当时仍然可能会导致Rowland完全无法获得救济——在初审中可能会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②就这一方面而言,Rowland在审前事实自认(pretrial admissions of fact)中明确指出,他此前去过Christian的公寓参加过一次聚会——并且使用过浴室设施。
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测Rowland案分别在十种场合再现,在五种甚至更多的场合中陪审团可能会持一项结论,而在其他的场合陪审团可能得出另外一项结论,这一结果看起来并不难想象。在这一点上,Rowland案会让人想起两个经典案例,Baltimore & Ohio Railroad Co. v. Goodman③275 U.S. 66(1927).以及Pokora v. Wabash Railway Co.④292 U.S. 98(1934).,它们的判决意见分别由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和Benjamin Cardozo法官撰写,他们在判决意见中形象地阐述了侵权案件中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张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法官和陪审团之间分配决策权的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研习侵权法的一年级学生会赞同Cardozo法官的观察结论:至少在当时,虽然固定规则要求司机在接近铁道路口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但(发生在铁路与公路)平交道口的意外事故(grade-crossing accidents)仍然在固定规则毫无意义时的各种情况下发生——正如Holmes法官所说的,好的人会停下并看看四周的情况,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走出车辆;通常注意这一标准的灵活性,适用于具体的个案,更有可能保证结果的公正。
但是Cardozo法官提出了一项进一步的限定,这与我们当前的关注直接相关。在给出了一系列假设的情形后——在这些情形下固定规则要求司机走出车辆,而这可能与通常注意相悖——他说道:
这样的例子足以证明,在制定实际上是法律规则的行为标准时必须小心谨慎。当(制定者)没有制定行为标准的相关背景经验时,就更迫切地需要小心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为标准并非行为以其习惯形式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而是人为创设出来的规则,并且这些规则被从无到有地施行。⑤同上注,第106页。
当然,分类处理模式是否体现这样的“行为以其习惯形式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是评估Rowland案判决时所要回答的问题。①与Rowland案同时期出现的另外一桩精彩的里程碑式判例是Gibson案,该案废弃了家庭内过失侵权的豁免权(intrafamiliy negligence immunity)。原告的父亲过失地指示原告在公路上走出汽车,并对拖在汽车后面的吉普车进行轮胎校正。随后,原告被经过的汽车撞上。尽管其他州在两种情况下采纳了豁免家庭内过失侵权的立场,但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废弃了这一豁免权,拒绝限制家长的责任。换言之,其他州采纳了基于规则的路径来调整以下具体情况:“(1)当所谓的过失行为涉及到家长对子女亲权的行使时;以及(2)当所谓的过失行为涉及到家长就子女的饮食、衣着、住宿、医疗和牙医服务之供给或其他方面的照顾行使一般裁量权(exercise of ordinary parental discretion)时。”参见Gibson案判决,第652页[引用了Goller v. White,122 N.W.2d 193,198(Wis.1963)]。[与此类似,纽约在“过失监督”的案件类型中承认了过失责任的例外,旨在尊重不同宗教群体和不同种族群体间抚养子女观念的多样性。See Holodook v. Spencer,324 N.E.2d 338(N.Y.1974)]。审理Gibson案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拒绝对家长因过失行为负担的责任给予任何类似的限制:我们拒绝了Goller案判决中蕴含的弦外之音,即在家长——子女关系的某些方面,家长得全权(carte blanche)对其子女实施过失行为……总之,虽然家长对子女享有运用亲权的特权和义务,这一特权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运用。应当适用的标准是传统的理性人标准,但要从家长的角色这一角度来观察。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对家长行为进行合适地校检:一个通常理性审慎的家长在类似情况下会做些什么呢?参见Gibson案判决,第652-653页。
在最后的分析中,就对Rowland案判决的接受而言,赞成的州和反对的州大致各占一半,这可能是妥当的。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张力无法以定论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张力意味着两者应当处于经典的比例关系之中,这一主题还体现在不朽的文学作品中。②比如,参见Herman Melville,Billy Budd.一方面,掺入这种相互冲突的压力(conflicting pressures),以实现广泛的风险分散和补偿目标,而且,另一方面,尊重个人在居住环境方面的自主,Rowland v. Christian里程碑式的重要性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黄文煌)
Rowland v. Christian: Hallmark of an Expansionary Era
Robert L. Rabin(Author) Miu Yu(Translator)
In the landmark Rowland v. Christian opinion,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abolished the categories of invitee,licensee,and trespasser,which had limited the duties owed by land occupiers for accidental harm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land entrant. However,the parties in the case did not mention,whether the defect was concealed or obvious. Both parties neither urged the court to reconsider the legitimacy of the categories nor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bandonment of the categories. Through the proactive judicial decision-making,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transformed the case and took insurance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general duty of due care of land occupiers,so that the land occupiers owed ordinary care to all land entrants. Rowland v. Christian ha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w of land occupier liability in America. Nearly half the states have recast their law of land occupier liability since Rowland v. Christian. Moreover,the decision provokes reassessment of fundamental point of tort liability:distinction between misfeasance and nonfeasance. Whether the Rowland should be accepted or the categories should be maintained,reflects the tension between rules and standards.
Land Occupiers;Categories;Duty of Due Care;Concealed Defect;Liability Insurance
D926
A
2095-7076(2016)02-0143-17
*本文为Robert Rabin和Stephen Sugarman 2007年出版的 Torts Stories(Law Stories)一书的第三章。本书的翻译已获授权。
**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