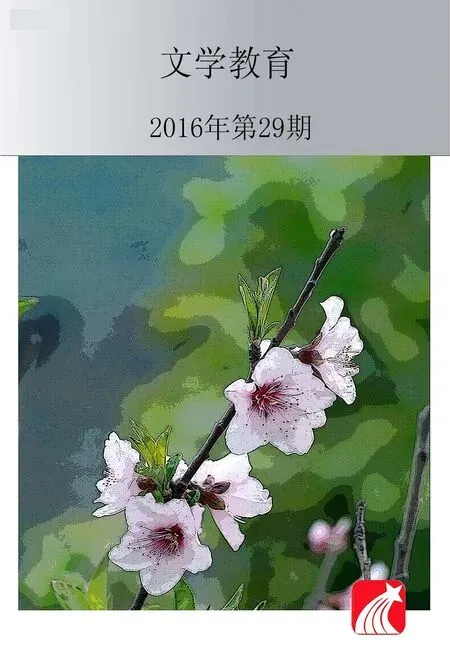简论散曲与词的差异
戴梦军
简论散曲与词的差异
戴梦军
作为曲牌体的音乐文学,散曲与词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区别。广义上来说二者都是诗歌的一种形式,但在格式、用韵及语言风格上都有诸多差异。简单地说,二者同而不同,探讨二者的异同是很有意义的。
散曲 词 异同
词和曲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配乐的长短句(曲牌体的音乐文学)。虽然宽泛地说,词与曲都是诗歌,但词有词牌,曲有曲牌,都要按照词牌、曲牌的格律创作,这是格式与诗最大的不同。词与曲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词被称为“曲子词”、“曲子”、“曲词”、“歌曲”等,曲被称为“词余”,散曲所用的曲牌中,许多源于词牌,体制格局方面,曲的小令与词的小令如出一辙。
尽管曲出于词,而且与词有不少共同点,但无论在形式还是特性方面,都与词有着明显的差异。不管在体式、韵律还是风格方面,二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词比较严谨,曲比较自由;词比较清丽,曲比较活泼;词比较雅致,曲比较俚俗;词比较含蓄,曲比较畅达。这些差异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与曲虽同为长短句,但比较而言,词的字数、句数、韵位都比较固定,词不能用衬字,至少在词律大致固定后是这样,而曲不仅可以而且大量使用衬字,甚至衬字比正文还多。曲极尽长短变化之能事,绝不会受到某种凝固形式的束缚而影响曲的表达力与生命力,是长短句诗体重的一个大的进步。词的同意词牌,字数、句数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而曲不但可以增加字数(增加衬字是正文以外的东西,无论其如何增加都不会影响正文的句数、平仄和韵位),还可以增损字句(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载三百五十个曲调中,注明“字句不拘,可以增损者一十四章”。即正宫的《端正好》、《货郎儿》、《煞尾》,仙吕的《混江龙》、《后庭花》、《青哥儿》,南吕的《草池春》、《鹌鹑儿》、《黄钟尾》,中吕的《道和》和双调的《新水令》、《折桂令》、《梅花酒》、《尾声》。可见曲中“增损”字句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二.散曲大量使用对偶句式,而词出现对偶的频率要远远小于散曲。在宋词的一个句组中,三个分句在意义上通常呈现出线形的结构,如汪元量词“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都为句组内三个分句语义连贯、顺序的,给人意象流淌的感觉。元散曲多用对偶,仍然是三个分句一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如元好问“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对偶的部分意义上是重复的,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
三.在音韵上,词曲也很有差别。第一,曲的用韵比词的用韵要密,往往通首句句押韵,甚至三字六韵,即一个六字句中,押了三个韵(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西厢》和清杨恩寿《词馀丛话·原律》说得很具体),而句句押韵之调也是不胜枚举(如黄钟的《贺圣朝》六句六韵,《昼夜乐》二十句二十韵);第二,曲要一韵到底,中间绝对不能换韵,但可以平、上、去互叶,而词可以换韵,词中用平韵则全调皆平,用仄则全调皆仄,如果平仄互叶则肯定已经换韵(如陈草庵的《中吕·山坡羊》虽然句句押韵,似乎限制较严,但它能够平、上、去互叶,实则更加自由);第三,词韵四声俱全,宋人词中虽然出现了入声字分化到平、上、去的例子,但入声韵在词中还是独立使用的,而在曲中,入声韵完全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被归并到平、上、去声的韵部中去,即所谓“入派三声”,这就打破了诗词中的许多规律,如“孤平”的问题,“平三连”的问题,“平仄相间”、“平仄相重”、和“平仄相反”的问题,在诗词中作为禁条的,在曲中都得到了解放,这也是长短句诗体中的一大解放。
四.在语言方面,口语方言用在诗词中就有些近乎俗,伤于雅,不符合诗词的体制与韵味;而用在曲中,则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所以曲中语言以口语为主,以天下通语为主。周德清《中原音韵》中说散曲要造语俊用字熟,“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曲之所以能曲达语情,曲尽人情,委曲尽情,曲尽其妙者,一是它适于自然音律的和谐美,二是它适于民间口语的生动美,散曲出于民间,且以“俗”为趣,市井俗语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缪钺《诗词散论》论词的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曰其文小,即用比兴,亦必取其轻灵细巧;二曰其质轻;三曰其径狭;四曰其境隐。词的特征恰好是曲的禁律。任讷《散曲概论》就词曲内容的宽窄,亦从四方面加以比较:一是词仅能抒情、写景而不可记事,曲则三者皆可;二是词的情调只宜悲不宜喜,曲则悲喜咸宜;三是词的格调可雅不可俗,可以纯而不可以杂,曲则雅俗咸宜,纯杂均可;四是词宜庄不宜谐,曲则庄谐杂出,幽默纷陈,嘲讥戏谑,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1]羊春秋.《散曲通论》,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
[2]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梁扬,杨东甫.《中国散曲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缪钺.《诗词散论》,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介绍:戴梦军,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