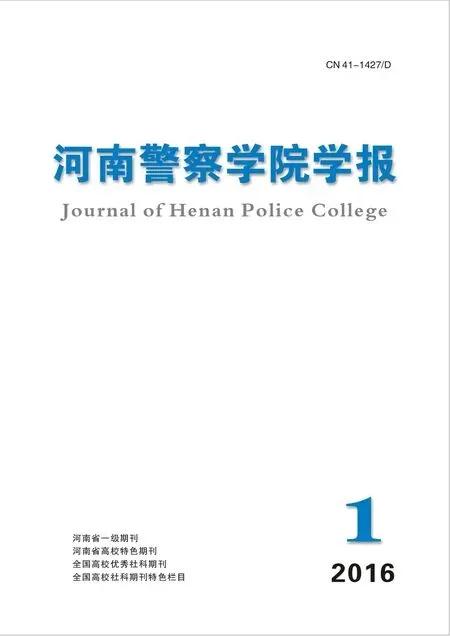中国受贿罪的立法历程考察
徐 岱,刘银龙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中国受贿罪的立法历程考察
徐 岱,刘银龙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受贿罪是中国贪污贿赂犯罪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罪名。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刑法修正案(九)》公布的刑事立法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受贿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犯罪构成体系,并日趋完善的。纵观整个立法历程,凸显出受贿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变化。内部变化表现为:行为方式向多样化发展、犯罪主体从身份论向职务论转变、犯罪对象的内容由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确立数额+情节的双重成罪标准以及加重刑罚处罚力度。外部变化表现为:整个贿赂犯罪罪名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严密的法网,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立法机关适时地修正和补充受贿罪,基本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反腐的需求,但仍有不足之处需继续改进。
受贿罪;受贿主体;受贿罪立法体系
腐败是历史性问题,更是当今社会的现实性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手段,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难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说:“腐败减少机会,造成普遍的不平等。腐败损害人权和良政,抑制经济增长,扭曲市场。腐败加剧环境问题,助长危险废物非法倾弃和动植物非法贸易。但腐败并不是什么巨大的非法力量,而是产生于人为的决定,往往受贪婪驱使。”①参见新华网《盘点世界各国反腐败“利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24/c_124123892.htm,2012年2月24日。中国惩治腐败犯罪近两年一直处于严惩态势,其中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1997年《刑法》由受贿犯罪、行贿犯罪和介绍贿赂罪共同组成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本文详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贿罪的发展历史,分析受贿罪的发展特点,明晰受贿罪的发展脉络,为其进一步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1979年《刑法》颁布之前受贿罪的立法情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国家并没有放松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和管理。针对个别人贪图享乐思想作祟,损公肥私,收受财物的现象,发动了“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腐败分子,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抑制和惩罚贪污现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严惩贪污的规定,1952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1952年《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其虽然不是一部正式意义上的法律,却起到了明显的管制效果。在1952年《条例》之中,强索他人财物和收受贿赂两种行为被归入贪污罪的范畴,独立意义上的受贿罪罪名并不存在,但并没有因此而放纵受贿行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企业也属于国有性质,犯罪主体本质上也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具体的入罪数额要求为一千万元,法定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由此可见,当时对于腐败也是采用重刑主义思想。1952年《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成文规定,具有开创性意义,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打击了腐败现象,对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1979年《刑法》至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的立法梳理
(一)1979年《刑法》确立了独立的受贿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时代。1979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受贿罪从贪污罪之中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犯罪构成体系,为之后受贿罪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之基。其中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全面分析1979年《刑法》对受贿罪的相关规定,可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受贿罪从贪污罪中独立出来,并归到渎职犯罪一章。第二,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较之前的1952年《条例》增加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做了扩大解释。第三,明确提出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素规定。第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仅限于收受财物一种形式,其行为方式相对单一,1952《条例》中已有的“索贿”没有规定。第五,1979年《刑法》对受贿的数额没做要求,究竟是因立法仓促而疏漏,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第六,1979年《刑法》的受贿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没有规定死刑。今天很多学者呼吁废除受贿罪的死刑步履维艰,从某种意义而言,折射出中国现在腐败之严重程度。

(二)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鉴于索贿和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1982年《决定》),对1979年《刑法》做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改,①其中把第一百八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适应了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详细考察本次《决定》的内容,可总结如下几点:第一,把索贿行为明确规定为受贿罪的一种方式,是1952年《条例》中“强索财物”的回归,从侧面也反映出国家工作人员索贿行为有死灰复燃之象;第二,确立受贿罪抽象数额入罪模式;第三,受贿罪的刑罚比照贪污罪之法定刑处罚,而不再有自己独立的法定刑;第四,法定最高刑提至死刑,刑罚由轻缓化走向重刑化;第五,去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简化了受贿罪的规定,扩大了受贿罪的打击面。
(三)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腐败现象愈加严重,现有的受贿罪规定已不能适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88年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文简称《补充规定》),对贪污受贿行为做出较之前更加细致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的各个构成要素。《补充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明确提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大受贿罪主体范围,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第二,犯罪构成要件中增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形式上更加合乎逻辑,体现出“权钱交易”的性质,实则增加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认定难度,时至今日学者仍然对其聚讼不已,一直被学界所诟病。第三,恢复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合理的规定,使构成要件更加完备。第四,对商业贿赂犯罪也作出了细致的规定。②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也反映出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钱交易,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实属一种变相的受贿现象,应当作为受贿罪论处。第五,对受贿罪的数额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明确具体数额的入罪标准。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处罚(第二条对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数额作出了明确规定,起刑点以2000元为基本标准)。由此可见,受贿罪由之前的抽象数额犯变为具体的数额犯,且加大了对索贿行为的惩处力度。第六,作出了单位受贿行为入罪的规定。①《补充规定》第六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受贿罪的规定弥补了受贿犯罪的立法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犯罪体系,满足了打击贿赂犯罪的社会需要。总而言之,1988年《补充规定》是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后制定的,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成为1997年刑法修订前处理贿赂犯罪的主要依据,而且为1997年《刑法》的修订夯实了基础,是1997年《刑法》贿赂犯罪的主要蓝本[1]15。
(四)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
该规定开启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的立法规定。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随着《公司法》的出台,对于非国有公司人员的腐败行为如何规制就成为司法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下文简称1995年《决定》),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行为作出规定。②其中第九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该行为的罪名定为商业受贿罪。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商业受贿罪从受贿罪中分立出来也是顺理成章。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中国全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多种成分并存的经济实体,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的现象,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为了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刑法对非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之举。该罪认定标准采取抽象的数额标准,索贿或者受贿,数额较大,就可以构成。根据1995年的司法解释,数额较大一般是指在5000元以上;量刑上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与1979年《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一样,刑罚较轻缓。相比之下,该罪的入罪门槛和法定刑,都比一般的受贿罪要宽和一些,有违刑法平等原则之嫌。
三、1997年《刑法》之后受贿罪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立法体系
(一)1997年《刑法》中受贿罪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一些破坏社会的不良行为,受贿犯罪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中国的第二部刑法诞生了,法条和罪名数量都大量提升,受贿犯罪的规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独立成章,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凸显其重要性。相比之前的规定,1997年《刑法》的规定有如下变化:第一,受贿罪的入罪数额标准由之前的2000元提高至5000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立法上明确将“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罪论处,③其中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早在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解答》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处。1997年刑法吸收了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并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改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扩张了受贿罪的行为类型;第三,增设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中的第一百六十三条,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其条款中增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述,和一般的受贿罪相呼应;第四,限缩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把“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从受贿罪主体中取缔,表面上看是缩小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实则把这部分主体分流到第一百六十三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中,也是对1995年《决定》的一个立法回应。
(二)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产生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了修正,把“公司、企业人员”扩展为“公司、企业人员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2007年11月6日,“两高”颁布司法解释,将其罪名变更为“非国家工作人受贿罪”。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单位,对公司、企业之外的一些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权钱交易”行为很难打击,也不利于保护这些单位的切身利益。通过对其犯罪主体的扩张,弥补打击漏洞,织密法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遥相呼应,不论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对打击受贿犯罪有很好的效果。
(三)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事立法永远不能把社会中所有行为都涵盖其中,传统的受贿罪规定也面临对花样翻新的受贿行为打击不力的困境。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收取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有一些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之前在职时的影响力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类似行为层出不穷。对这类人员,不具备受贿罪主体资格地位,亦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不能单独定罪,也不能按共犯论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第18条明确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对中国打击这一类型的受贿行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2009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做出明确规定,并把其列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由于该规定的主体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纳入受贿罪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其命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此次修订,不仅是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积极回应,也对中国进一步打击受贿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再者,该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受贿犯罪体系,将那些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和利用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余热”的人都纳入到受贿犯罪中,对受贿犯罪进行多元化的打击和预防,受贿行为才有可能有所收敛。
(四)《刑法修正案(九)》中受贿罪的发展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第四十四条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作出修改,受贿罪又有了实质性变化,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受贿罪数额:具体数额到抽象数额。即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替换以前的具体数额。这一改变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第二,受贿罪成罪标准:抽象数额+情节。这意味着我国受贿罪从此告别了单一的数额成罪标准,增加了情节衡量因素。这一改变具有很大合理性,通过数额和情节的双重标准,可以更好地判断受贿罪对法益的危害程度。诚如李洁教授所言:“影响受贿罪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仅包括受贿数额,其他内容,如行为的方式,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所谋取利益的性质,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否违背职务及其违背程度等,也对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影响,有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2]亦能有效打击受贿罪。第三,受贿罪刑罚: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不得减刑、假释。如果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被判处死刑且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基于犯罪情节的考量,可以同时决定在其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从受贿罪成罪标准到刑罚的改革,都凸显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表明打击受贿犯罪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受贿罪发展呈现出的特点
(一)受贿罪的内部变化
1.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多样化
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受贿犯罪自身的内容和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一部分行为类型逐渐从受贿罪中分离出去,独立成罪,使受贿犯罪的体系更加完整,法网更加严密,也更有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分子。时至今日,受贿罪自身有四种表现行为,分别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八条中:

第一,索贿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是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行为,也是受贿罪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行为方式。该行为的成立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成立,体现出索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大,不仅使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遭受严重损害,且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巨大毁损。一直以来,学者对索贿行为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索贿只包括行为人主动索取和要求财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除了委婉地索要财物之外,还应当包括要挟性地“勒索”财物,否则就不予办事。理论观点争议必须要有实践的回应才能明辨。一般意义上的索贿就是指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向他人索取财物,以谋取个人私利。然而,随着受贿犯罪愈加严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职务行为之际,乘机提出勒索财物请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受贿犯罪的本质[3]1066。诚如学者所言,“索取”之意,既包括主动要求贿赂的情况,也包括“以如果不交付财物就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打击报复相要挟”或者“如果不交付财物就拖延甚至拒绝办理应当办理的事项”的勒索行为[4]。要求、索要与勒索,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提出的非法要求,他们之间只有程度区别,没有本质差异,事实上也难以完全区分清楚要求、索要与勒索[3]1066。生活中这种性质的索贿行为越来越多,和敲诈勒索罪中的“勒索”行为相比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勒索财物行为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相关,能体现“权钱交易”的性质;后者与职务行为没有关联,完全是一种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通过威胁,使对方害怕而迫不得已交出财物的情形。
第二,收受贿赂行为。收受贿赂相比索贿,对方具有很强的主动性,给行为人主动送去财物,以博取自己的利益;行为人非法收取并接受他人财物,然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对方谋取利益。这种受贿行为,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方式。受贿人在该行为中相对较为被动,但在请托人主动送来财物以后,受贿人没有拒绝,即便有推脱之意,亦是半推半就,最终还是收下财物,并且在主观上也接受了财物。当然要严格与另一种情况相区别:如果请托人悄悄放下财物或只是交给其近亲属,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并不知情,该行为就不能定性为收受贿赂。再者,要想成立受贿罪,仅有收受贿赂行为要件还不齐备,还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素。1988年的《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受贿罪中增加“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1997年《刑法》沿用至今。对此要件,学界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其是客观要素,有的认为是主观要素,还有人主张其既是主观要件又是客观要件。在争执陷入僵局之时,也有学者提出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立法最终还是保留了这一要件。究其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以,这一要件旨在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3]1068。之所以保留就在于其能体现受贿的本质,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有没有实现暂且不问。正如学者所说:在现行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要件必不可少的要素,只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始于承诺,终于实现”,从承诺开始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1]357。
第三,商业受贿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在市场交易中,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有些经营者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和手续费实属变相的行贿行为,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易秩序,同时也侵犯了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早在1952年《条例》中就有关于“回扣”的规定,而1979年《刑法》对此没有规定。1988年《补充规定》以立法的形式对收受回扣、手续费的行为重新作出明确规定。1997年《刑法》没有设立独立的商业受贿罪,而是把其分散到各种行贿和受贿犯罪中。此种受贿行为必须是发生在经济往来中,且发生在平等的交易主体之间,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管理者与经营者的交往行为。经济往来的活动仅限于行为人代表本单位与外单位或者个人从事经济交往活动,也仅限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交往,不包括行为人代表国家或单位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凡是在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过程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都不能算是经济受贿行为[5]。如果是发生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可以直接按照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论处。市场交易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此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明折明扣”而且入到单位账上的,就不能作违法处理,更谈不上犯罪。对于“手续费”性质的贿赂,司法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一般是指市场主体为了承揽业务谋取商业利益,给予对方或其负责人作为完成交易程序的金钱报酬[6]。国家工作人员将其装入个人口袋,就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第四,斡旋受贿行为。斡旋受贿,又称为间接受贿,与直接受贿相对应,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后来就采用了斡旋受贿这个表述。1979年《刑法》对这一类型行为没有明确规定,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类似情况经常发生。对其规制无法可据。最早对此作出规定的是“两高”的司法解释,①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三个关于受贿罪问题中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处。”其最终通过立法在1997年《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确立下来。斡旋受贿不是独立的犯罪,和一般的受贿罪也不同,只是按受贿罪论处。要想明确该行为的内涵,首先要正确理解“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学术界对此争论很大,形成多种观点和学说:有“职务制约关系说”、“居中斡旋说”、“相互利用说”、“职务影响力说”等观点[1]408-409。其中“职务制约关系说”和“相互利用说”都有缩小斡旋受贿犯罪之嫌,不利于打击受贿犯罪。“居中斡旋说”显然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本意不相符,而且与介绍贿赂罪的撮合行为存在重合。“职务影响力说”相对合理,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吻合,但这里的影响力一定不包括领导和隶属关系。其次,何为“不正当利益”。在一般受贿罪中对谋取利益正当与否没有要求,在该行为中用“不正当利益”进行了限缩。换言之,斡旋受贿人若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就不能入罪。对如何界定“不正当利益”,学者众说纷纭,有“非法利益说”、“违法利益说”、“不确定利益说”。为此,“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对此作出明确解释,③1999年3月14日发布《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分子的通知》中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方便条件。”虽然该解释针对行贿罪作出了规定,但和贿赂犯罪是一致的。不过这里的“违法”不局限于法律和法规,还包括国家政策和部门规章,“违法”的外延比较广泛。
2.受贿罪的主体:从身份论到职务论的转变
1952年《条例》第二条明确提出了受贿行为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学校和企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1979年《刑法》颁布时,立法中增加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明显扩大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198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作出解释,对国家机关的内容进行细化,并在企业前增加了“国营”的限制,用“国家事业机构”替换事业单位。这一变化显然是对“国有”和“非国有”性质企业、事业单位作了区分,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明确把非国有企业的人员从受贿罪中剔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有的规定已不能满足惩治贪污贿赂的需要。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补充规定》明确提出,受贿罪主体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又一次扩大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有效打击受贿犯罪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1989年“两高”进一步作出解释④1989年“两高”通过《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对受贿罪的主体进一步细化。明确提出“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外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对受贿罪主体身份作出宽泛认定,只要“从事公务”就有可能成立受贿罪,不受其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打破了传统的重而又重的公有制经济,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各种性质的公司和企业不断出现,单一的受贿罪已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于是,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又增设了一个商业受贿罪(现在的非国有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对受贿罪的新发展,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把受贿罪中“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纳入到商业受贿罪,缩小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这一分立也使受贿罪陷入新的困境:罪名分立之后两罪在法定刑上的巨大差异,使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国有、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再次成为理论与实务界激烈争论的焦点[1]271。为此,1995年“两高”先后通过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但可以发现,二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很难把两罪主体明确区分,加之实践的复杂性,很难对司法实践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1997年《刑法》在吸收前面单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规定在不同章节。此次刑法修订基本上是对之前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承继,既没扩大亦没缩小。对“委派”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后来仍有很多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陆续出台。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①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其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七项)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按受贿罪规定论处。认为村民委员会在协助政府从事特定公务时,亦可作为受贿罪主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作出答复,②200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集体性质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提出:经过乡政府或者主管行政机关任命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在依法从事本区域卫生工作的管理与业务技术指导、承担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等公务活动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乡镇卫生院院长在一定范围内依照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对待。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和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四项内容作了详细的解读,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实践办案经验,对《刑法》第九十三条又一次细化。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通过答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了只要行为人的职务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或者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取得,不管其是通过何种手段,就应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而认定其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1]20。2010年11月,“两高”《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受贿罪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身份”,只要与相关职务有关就可以作为受贿罪的主体。
纵观受贿罪主体的发展变化,主线都在围绕“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范围可谓一波三折,其发展轨迹为限缩——扩大——再限缩——再扩大。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还会有更多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可以预知,将来的受贿罪主体仍将继续扩大(在没有分立其他受贿罪名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受贿罪的主体也遵循了身份——职务(公务)的变化,突破了受贿罪身份犯的界限,只要依法从事公务,其本身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正如孙国祥教授所言:“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传统的国家干部身份;也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有单位的正式编制;无论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无论是在国有单位,还是在非国有单位,只要行为人在从事公务活动,就应该作为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认定。”[1]321
3.受贿罪的对象:财物到财产性利益
受贿罪的对象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扩大受贿罪对象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经济迅速发展之后,新型的受贿行为方式多样化且日趋翻新,囿于立法对受贿罪犯罪对象限于“财物”的狭窄规定,导致打击受贿犯罪行为效力大打折扣。事实上,司法实践业已走在立法之前,对于一些“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已经开始惩治。1952年《条例》中受贿的对象明确规定为“财物”;1979年《刑法》把“贿赂”规定为受贿罪的对象;1988年《补充规定》把商业受贿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畴,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回扣、手续费”,但仍然没有突破“财物”的范畴。1997年刑法对于受贿罪的对象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更改,其犯罪对象仍然只限于“财物”。显然,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时期,这一立法规定尚可适应社会需求,实践中的受贿行为也大多只限于金钱和实物等财物。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温饱解决之后,人的需求就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投其所好的东西就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物”所能涵盖的。现代社会,人的需求和欲望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精神的、政治的、物质的利益,都可以成为行贿人与受贿人相互利用的“筹码”,特别是在就业、提干、住房、农转非、帮助出国等“热点”问题上弄权渎职,都为群众所深恶痛绝,其社会危害性有时甚于直接获取财物的受贿,不作为犯罪处理,难免成为犯罪分子以权换利的“避风港”[1]114。其实,“财产性利益”受贿犯罪和“财物”受贿犯罪本质相同,正如学者所言:“受贿人是直接接受或索取财产性利益,而间接、变相地接受或索取实物或金钱贿赂物,在形式上,受贿人接受的是财产性利益,而在实质上,受贿人接受或索取的是实物或者金钱。”[7]14
“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在实践中频繁出现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对于“由权钱交易的直接性的财物如货币、实物形式,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的间接性的财物贿赂如房屋装修、旅游服务、设立虚假债权、减免债务等,特别是以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物”[7]14的变相受贿行为,如不加以规制,有纵容犯罪嫌疑。鉴于以上客观事实,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了有力的回应。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作出认定。2007年7月“两高”通过《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多种受贿行为作出明确的认定,其中包括“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这种以“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受贿行为,被明确认定为受贿罪。2008年11月“两高”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贿赂的内容明确扩大至财产性利益。①其中第七条明确提出:“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可见,中国的受贿罪对象由传统的“财物”已经转变为“财产性利益”,既是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积极回应,亦能有效地惩治受贿犯罪。
4.受贿罪成罪标准:非典型数额犯
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作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8]。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不论是抽象数额抑或是具体数额,受贿罪的成罪标准都是一种典型的数额类型。《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成罪标准作了明确的修改,即由“单一数额”改为“数额+情节”的双重评价标准。换言之,受贿罪的成立既可以通过数额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亦可通过受贿的各种情节来衡量是否入罪,其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数额犯。当然,数额在受贿罪中仍然是其考量的主要因素。这一修改意义重大,通过立法适时修改成罪标准,使之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受贿罪本质使然。
5.受贿罪的刑罚加重
受贿罪一直是我国打击的重点对象,其法定刑也相应较高,除了1979年《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外,其余都有死刑的规定。针对我国腐败现象的严重态势,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提升了受贿罪的刑罚,加强受贿罪的处罚力度。如有受贿犯罪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且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基于犯罪情节的考量,可以同时决定在其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一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终身监禁”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徒刑”,大大提升了受贿罪的刑罚。这一规定不仅满足了司法实践对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亦是对民众反腐呼声最好的立法回应。
(二)受贿罪的外部变化
贿赂犯罪,包括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若想更好地打击这种现象,仅仅凭借受贿罪这一个罪名是远远不够的。众所周知,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通常成对出现,在刑法理论上将其称为“对向犯”。因此,单一惩罚受贿犯罪不是有效的路径选择,难以在源头上制止。结合司法实践,经过相继的刑事立法,我国在不断完善受贿罪自身犯罪成立和刑罚的同时,亦对其外部相关的犯罪加强立法,织密法网,很好地配合了打击受贿罪的需要。现有的贿赂犯罪体系由受贿犯罪、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犯罪构成。其中受贿犯罪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三个罪名,行贿犯罪由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刑法修正案(九)》刚通过)、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四个罪名组成。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司法实践中行贿现象屡禁不止,《刑法修正案(九)》提升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主要体现在:第一,完善行贿犯罪的财产刑,增加了罚金刑的规定,使其在经济上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进一步严格了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到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第三,严密了行贿犯罪的法网。增加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通过以上立法举措,进一步严密了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加强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一定意义上截断了受贿犯罪的源头,对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双管齐下,对惩治腐败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结语
解决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完全消灭更不可能,我们能做的是把它的发生可能性限制到最低。这一方面需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财产公开等制度;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的刑事法律和各项制度,而受贿罪立法体系的完善必然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能够适时修正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基本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反腐的需要。但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需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充分吸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髓,建立起符合中国司法实际的受贿罪立法体系。
[1]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李洁.受贿罪法条解释与评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95.
[3]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066.
[4]林亚刚.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41-142.
[5]杨兴国.贪污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16.
[6]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95.
[7]徐岱.犯罪数额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影响[J].中国检察官,2009(2).
[8]童伟华.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57.
(责任编辑:刘 芳)
Studying on Accepting Bribes:A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rocess
Xu Dai,LIU Yin-long
(Law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ystem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offences in China.The trac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from the year 1949 till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9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suggests that accepting bribes,as an independent crime,is separated from the crime of corruption,and formed its own system rapidly.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rends during this process:the change of accepting bribes crime itself and the change of the whole bribery crime system.The change of itself includes: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of conduct;the subject of crime is changing from‘whether he is a public servant’to‘what he did is related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not’;the scope of bribes expands from physical property to interests of property; both the amount of the bribes and the other circumstance of the offence are becom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firming the crime;The punishment to the crim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vere.The change of bribery crime system includes:the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is supplemented;the punishment to the bribery crime is becoming more complete.On the other hand,the punishment to offering bribes is becoming more severe.The State Legislature’s timely amending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basically meets the nee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te’s anticorruption movement,despite they can do more.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the one who accept bribes;legislative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D924.11
A
1008-2433(2016)01-0085-09
2015-11-06
徐 岱(1967—),女,吉林白城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刑法史、比较刑法学;刘银龙(1977—),男,山西朔州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生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