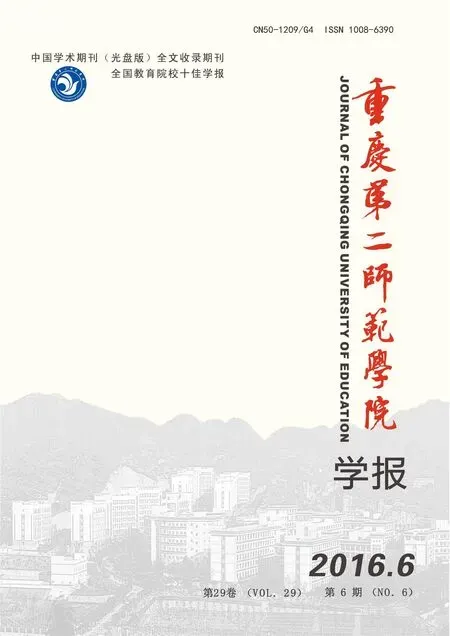抗战时期“佛徒号”献机运动论析
曾友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抗战时期“佛徒号”献机运动论析
曾友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发起“一元献机运动”,以期实现“航空救国”之梦。中国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一样,积极响应号召为空军建设捐款献物,但由于受国民党长期迫害佛教政策、佛教界内部纷争不断、日伪势力蓄意扰乱破坏等因素影响,佛教界捐献“佛徒号”飞机抗击日寇的目标最终落空。
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佛徒号”献机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飞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比不上日本空军,导致战争的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日军飞机到处肆虐逞凶,频繁轰炸中国前方阵地和后方无辜平民。在此背景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购买飞机献给中国空军,以期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航空救国”之梦。佛教界作为中国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僧众也不甘人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迅速发起了“佛徒号”献机运动,但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目标未能达成。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其背景,展示其经过,并对未达成目标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一、“佛徒号”献机运动的背景
1940年7月22日,125架日机分四批轰炸了四川合川县,投炸弹484枚、燃烧弹18枚,造成63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210栋又4300间房屋和90只木船损毁的惨重损失,[1]酿成了合川县历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七二二大轰炸”惨案。惨案立即引发了合川人民大规模的游行,民众在强烈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广泛宣传日机之所以能肆虐中国领空是因为中国空军缺少自己的战机,希望民众捐款捐物购买飞机用于中国空军对日寇作战。在此背景下,1940年12月,在合川县袁雪崖县长和施剑翘女士领导下,全县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一元献机运动”,卢作孚、康泽、陈立夫、胡南先、施则凡、徐悲鸿、张治中、吴国桢、宋氏三姐妹等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参与。仅短短四个月时间,就募款达45万元,献机3架,创全国献机运动之优异纪录。此举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各界群众纷纷表示赞赏和响应。1941年6月18日,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发布《重庆市政府为仿照合川县推动一元献机运动给所属训令》,号召重庆市各县依照合川模式施行。[2]1941年7月7日,“七七事变”四周年之际,中国航空协会正式向全国发布《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为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告全国同胞书》,并制定了《各地分会发动一元献机运动纲要》《一元献机运动实施大纲》《一元献机运动扩大宣传办法纲要》《一元献机运动宣传大纲》等。[3]该运动由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发起,各省分会会同各省的各级政府全面推行。自始“一元献机运动”正式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推广开来,并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元献机运动”浪潮。根据《一元献机运动实施大纲》第十七条规定,捐款达15万元者,无论个人或团体或县、区、镇,除给奖外,并得以飞机一架,用捐款者之名称命名。因此,以各地名称、行业名称、团体名称等命名的飞机不断增加,由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转交中国空军,用于空军将士与日寇空军作战。
身为中国国民一分子的佛教僧侣,自当不甘人后,立即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到“一元献机运动”中,以佛教徒的身份发起“佛徒号”献机运动。1941年8月初,中国佛教会甘肃省酒泉、高台、安西等七县佛教分会发起筹资捐献“佛徒号”飞机给中国空军的倡议,并率先捐款1000元。同时,他们致电中国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望其登高一呼,在全国发起一场佛教徒为中国空军捐献飞机的运动。[4]在太虚大师的倡议下,很快在中国佛教界掀起了一波“佛徒号”献机运动的热潮。
二、“佛徒号”献机运动的经过
身在陪都重庆的太虚大师收到甘肃省酒泉、高台、安西等七县佛教分会发起的“佛徒号”献机运动电函后,大加赞赏,个人带头捐款100元,且于1941年8月21日向全国佛教徒发出通电,呼吁各地佛教僧众立即捐款响应“佛徒号”献机运动。1941年9月25日,四川省佛教会率先响应太虚大师的倡议,并及时向四川各地寺庙丛林、佛学院、佛学社及缁素四众发出通电,呼吁积极响应太虚大师倡议向中国空军捐献一架“佛徒号”飞机。随后,又致电各省佛教会,呼吁更多省份的佛教会参加到“佛徒号”献机运动中来。为了扩大“佛徒号”献机运动,四川省佛教会制定了《四川省佛教会劝募佛徒号飞机捐款委员会办法》,并成立了“佛徒号”飞机捐款委员会,选举昌圆、本智、道悟、傅雨村、蓝世证5人为常务委员。根据该办法规定,献机活动以县为单位,各县佛教会首先自捐若干后再按该县寺庙数量劝募,各大丛林由常住先自捐若干后再按全寺人数劝募,各大佛学院由院先自捐若干后再按全院教职员及学僧人数劝募,各佛学社由社先自捐若干后再按全社人数劝募,缁素四众相互劝募尽量捐款。四川省佛教会将代表各佛教团体和个人收集相关捐款,并由《佛化新闻报》按期公布详细数目以示大公。[5]如1941年9月25日《佛化新闻报》公布:四川省佛教会200元、昭觉寺200元、草堂寺100元、广文法师50元、双流县佛教会20元、双流佛化学校20元、崇庆县佛教会50元、崇庆西山寺20元、温江爱道佛化学校20元、宝慈佛学社20元、定鉴和尚20元、宏一老和尚20元、宗镜和尚10元、焕齐法师10元、仁宽法师10元、圆海法师10元、佛化新闻报10元等,共收到捐款850元。[6]类似的捐款公示,《佛化新闻报》先后刊登了8次,有效地保证了“佛徒号”献机运动捐款账目的公开透明。[7]
在四川佛教僧众带动下,贵州、云南、陕西、广西、湖南、福建等省佛教僧众也纷纷响应,踊跃捐款。1941年10月27日,贵州省佛教会将独山县佛教分会169元、贵阳市寺庙131元共300元法币的第一批捐款汇往四川省佛教会。[8]1941年11月6日,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理事长等慈法师接中央社会部发布的“一元献机运动”令后,立即奔走呼吁,并组织成立了芒市、遮放、畹町三土司“一元献机运动”劝募委员会。根据预期,仅这一地区佛教徒的捐款就可能达到20多万元,可以购买一架“滇边佛徒号”飞机。[9]1942年1月,贵州安顺佛教会募集的440元汇给设在陪都重庆的献机委员会。[10]1942年1月,陕西大水和安康佛教会将分别募集的捐款100元、300元汇给身在重庆的太虚大师和重庆佛教会并转交献机委员会。[11]1942年1月14日,云南省佛教会将从全省各分会收集的捐款780元通过邮政汇交太虚大师。[12]1942年3月5日,云南永平县慧光寺、江顶寺、观音寺等共捐献1000元,并汇给太虚大师转交政府。[13]1942年3月12日,奉节佛教会利用邀请慧泉法师讲经之机募集捐款1718元,后通过中国银行汇给太虚大师转交中国航空建设协会。[14]1942年3月24日,重庆市佛教会收到罗汉寺、慈云寺、报恩寺、真武山以及定九和尚、觉通和尚、杨欧仑居士等献机捐款1000元。[15]1942年4月30日,陕西佛化社社长康寄遥居士从富平念佛会、蓝田念佛会、白河念佛会、淳化念佛会、渭南念佛会等佛教团体募得捐款1116元。[16]类似的捐款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截至1942年5月,“佛徒号”献机运动基本结束,持续时间达10个月之久,收到各地区佛教团体、寺庙和僧众捐款至少17120元以上。各地佛教界将募集的捐款或交由四川省佛教会转交成都市政府献机委员会,或由太虚大师转交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或直接汇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还有的直接交到当地政府的“一元献机运动”捐款委员会。根据1942年1月《四川佛教月刊》的报道,截至1941年12月底收到捐款12000法币,并于1942年1月16日交成都市政府献机委员会代转中国航空建设协会。[17]1942年3月26日的《佛化新闻报》报道,除四川佛教会募集的“佛徒号”捐款外,太虚大师代表中国佛学会收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和僧众汇来的捐款5120元法币,并转交中国航空建设协会。[18]仅通过以上两个渠道上交给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捐款达17120元法币,至于各地佛教界通过其他渠道上交给政府的捐款的具体数额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佛徒号”献机运动的捐款总额应多于四川省佛教会和太虚大师转交给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捐款总和,因为直到1944年10月,拉卜楞教区的僧民仍在踊跃捐款,并直接汇寄给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得到了政府的明令褒奖。[19]同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直到“一元献机运动”结束,佛教界筹集的捐款也未能达到15万元购买一架飞机的数额,预期目标终告落空。
三、“佛徒号”献机运动的评析
中国佛教界僧众捐献一架“佛徒号”飞机抗击日寇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若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长期对佛教的迫害政策,使部分僧众采取了不合作态度
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对佛教均采取迫害政策,或毁寺逐僧,或强占庙产,或庙产兴学。即便是在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政府对佛教的打压也未曾停止过。如在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地区,以抗战为名,政府抓拉和尚壮丁、强提庙产的现象屡禁不止。日积月累,导致佛教界大部分僧众不信任政府,并与之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抗争。“一元献机运动”是由政府发起的,在“抗战第一”、“民族至上”的背景下,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僧侣本应积极响应,但由于长期受政府打压和迫害,使得一些保守的佛教僧众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献机捐款是政府打着“抗战”的旗号来搜刮佛教界的钱财。1941年11月6日,湘南佛学院的茗山法师在《佛化新闻报》上发表的《“佛徒号”献机运动引起的争议》一文指出,一方面由于佛教长期遭受政府或豪绅的欺压,使得部分僧众认为“一元献机运动”是政府强加给佛教界的,尽管佛教僧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政府仍未停止对佛教的迫害,因此,对政府参与干预“佛徒号”献机运动的做法表示不满。另一方面,部分僧众认为,响应“佛徒号”献机运动并未真正体现报效国家和拥护政府,而应从自修或共修精神方面、从加紧救护训练行动方面、从办报纸杂志宣传方面支持抗战,这才是真正报效国家和拥护政府的表现。[20]事实上,从全国“一元献机运动”来看,政府确实收到了数额不菲的捐款,但由于当时中国海岸线和领空已被日军封锁,拟购飞机根本无法运回国统区。更重要的是,这些款项还常常落入贪官污吏和奸商之手,很少用于“航空救国”。把持捐务的商人大发横财,相关官员也可分肥,以致献机捐款到底有多少用于航空建设,从来都没有完整的统计,成为一笔无法算清的烂账、糊涂账。[2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佛教的长期迫害政策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僧众对“一元献机运动”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重要原因。
(二)佛教界内部纷争不断,使部分僧众对献机运动态度消极
一般来说,中国佛教界举办全国性的“佛徒号”献机运动,理应由中国佛教会负责发起,但由于以圆瑛大师为代表的保守派佛教人士领导的中国佛教会滞留在沦陷区上海,迟迟不愿将中国佛教会西迁至陪都重庆,而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革新派佛教人士在陪都重庆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意在取代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如此一来,佛教界内部的纷争更加严重。这样,组织开展“佛徒号”献机运动的重任就落在了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重庆和四川地区的佛教界肩上。在此背景下,四川省佛教会率先响应太虚大师的倡议,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组织开展全国“佛徒号”献机运动的重任。在“佛徒号”献机运动中,四川省佛教会组织开展的“佛徒号”献机运动可谓是声势最为浩大、机制最为健全、捐款僧众最为众多的。即便如此,其在规定的捐献期限内,四川省佛教会收到的献机捐款明显不如起初计划在1941年12月底前捐款达到20万元的预期。[22]根据《四川省佛教会劝募佛徒号飞机捐款委员会办法》规定,各佛教团体或寺庙均以会员或僧侣人数按名劝募,具体落实到每一团体或寺庙的个人,按照该办法,仅四川一省就将达数十万元之多。但从四川佛教会公布的捐献名目来看,捐款大都来自佛教团体或寺庙,个人方面只有少数佛教团体的负责人或寺庙的住持,捐款的普通僧侣不多。无奈之下,四川省佛教会不得不向各县佛教会发布催收捐款的通令和延长1个月的捐献期限。1941年11月15日的《佛化新闻报》报道,四川省佛教会向全省各地佛教分会发出《献期将届成数无多——省佛教会通令催收献佛徒号飞机捐款》通知后,各县佛教会仍行动迟缓,捐献收效甚微。[23]1941年12月24日,四川省佛教会再次发出《佛徒号献机展限一月 省佛教会再令各县上紧推动议决发起一元运动收效较易》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佛教会于1942年1月30日前将佛徒号飞机捐款上交四川省佛教会。[24]此时,四川省佛教会下发的通知已明显带有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意味。即便如此,响应者仍不多,直到献机运动结束,四川省佛教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区的献机捐款仍只有区区12000多元法币。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四川省佛教会尚且如此,其他省份佛教会的“佛徒号”献机运动更是收效甚微。如,等慈法师在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发起“滇边佛徒号”献机运动,起初号称仅这一区域捐款就将达到20余万元,能单独捐献一架“滇边佛徒号”飞机,事实上后来的捐款远远没有达到这一预期目标。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保守的佛教人士认为飞机将会造成大规模的杀伤,怀疑“佛徒号”献机运动的正当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佛徒号”献机运动可能会演变为鼓动或帮助他人杀生,从而触犯佛教不杀生的戒律。因此,综合来看,一方面是由于佛教界内部纷争不断,即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革新派与以圆瑛大师为代表的佛教保守派在佛教界如何参与抗战的方式上产生分歧,以致出现了各自代表的佛教势力相互拆台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佛教人士从佛教戒律上对献机运动不认同,尤其是身处抗战大后方的普通僧众,他们由于从未直接感受到日寇暴行带来的危害,对捐款购买飞机杀生而违反佛教戒律的行为不理解,但是基于当时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他们未敢明确表示反对,却采取了不参与或沉默的消极抵制态度。
(三)日伪势力蓄意扰乱破坏,沦陷区佛教界献机有心无力
江浙历来是中国的富庶地区,其佛教寺院财力也相对雄厚,但由于处在沦陷区内,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活动是日伪政府所明令禁止的。他们即便有捐款献机的这份爱国心,但深陷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他们的种种举动全都处在日伪特务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就将引来杀身之祸。在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下,沦陷区的绝大多数僧众选择了沉默,既不与日伪合作,也不公开表达对抗日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佛徒号”献机运动失去了沦陷区佛教界的捐款。更为可恨的是,为了应对中国政府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日本僧侣也在沦陷区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给日本军队的运动,沦陷区的一些中国僧侣在日伪势力的威逼利诱下,参与日本僧侣组织开展的佛教号献机运动。他们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日军和傀儡政府的军队购买飞机用于屠杀自己的同胞,其丑陋行为在抗战胜利后被控为汉奸和叛国者,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与此同时,失去了沦陷区富庶地区佛教团体、寺庙和僧众的献机捐款,“佛徒号”捐款预期效果难免大打折扣。而处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广袤的后方地区,人烟稀少,地瘠民贫,政府和民众财力十分薄弱,佛教界更是如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佛徒号”献机运动对广大国统区的普通寺庙和僧侣也是一种负担。
四、结语
中国佛教界发起的“佛徒号”献机运动是政府发起“一元献机运动”的深化和延续,尽管未能实现“佛徒号”飞机上天抗击日寇的目标,但其对当时中国宗教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不仅广泛地动员了中国宗教界人士乃至广大信众以更大热情投入到全民抗战中来,而且更以“佛徒号”献机运动突破了佛教护国的传统,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僧众爱国救亡运动新方式的先河。
[1]潘洵,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197.
[2][3]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战时动员:下[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823.823-832.
[4]陇县佛教会发动佛徒号献机 太虚大师呼吁集款响应[J].海潮音,1941,22(10):20.
[5]四川省佛教会献机运动致各佛教团体电 四川省佛教会劝募佛徒号飞机捐款委员会办法致各省佛教会电 致各募捐委员会函四川佛教会公函 致太虚大师电[J].四川佛教月刊,1941,12(9-11):8-10.
[6][7]本期收到“佛徒号”献机捐款[N].佛化新闻报,1941-09-25(204).1941-10-2(205).1941-10-16(207).1941-10-23(208).1941-10-30(209).1941-11-6(210).1941-11-13(211).1941-11-27(213).
[8]贵州省佛教会劝募响应“佛徒号”之踊跃[N].佛化新闻报,1942-11-06(210).
[9]滇边佛联会推进献机运动[J].海潮音,1942,23(1-2):19.
[10]安顺献机非常踊跃[N].佛化新闻报,1942-05-07(221).
[11]陕僧献机汇渝转献[N].佛化新闻报,1942-01-29(219).
[12]云南省佛教会响应献机致川佛教会函[J].四川佛教月刊,1942,12(12),13(1-2):1.
[13]永平教会捐献千元[N].佛化新闻报,1942-03-05(224).
[14]奉节佛教会讲慧泉法师讲弥陀经并劝募佛徒号飞机捐款[N].佛化新闻报,1942-03-12(225).
[15]重庆市佛教会献飞机捐一千元[N].佛化新闻报,1942-03-24(226).
[16]陕西佛化社康寄遥居士劝募飞机捐一千一百一十六元[N].佛化新闻报,1942-04-30(232).
[17]四川省佛教会首次缴佛徒献机捐款致献机委会函[J].四川佛教月刊,1942,12(12),13(1-2):2.
[18]佛徒号献机结束[N].佛化新闻报,1942-03-26(227).
[19]拉卜楞教区僧民捐款献机[J].海潮音,1944,25(11-12):27.
[20]茗山.“佛徒号”献机运动引起的争议[N].佛化新闻报,1941-11-6(210).
[21]姜长英.中国航空史[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158-159.
[22]佛教徒献机救国[J].田家半月报,1941,8(21):4-5.
[23]献期将届成数无多——省佛教会通令催收献佛徒号飞机捐款[N].佛化新闻报,1941-11-20(212).
[24]佛徒号献机展限一月 省佛教会再令各县上紧推动议决发起一元运动收效较易[N].佛化新闻报,1941-12-25(217).
[责任编辑 文 川]
2016-09-05
曾友和(1976— ),男,江西抚州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地方佛教史。
K265.9
A
1008-6390(2016)06-0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