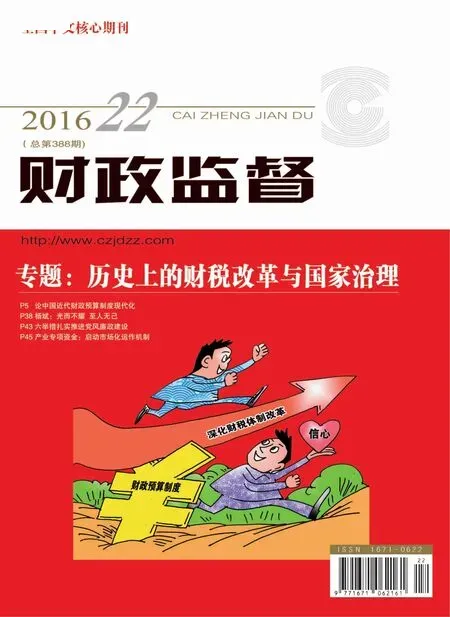公共性视域下的财税制度改革与传统国家治理
——以东周秦汉为考察对象
●童光辉 范建鏋
公共性视域下的财税制度改革与传统国家治理
——以东周秦汉为考察对象
●童光辉 范建鏋
作为系列研究,笔者试图通过财政史研究来论证一个理论命题:“公共性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古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东周秦汉之际,随着西周传统宗法封建制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编户齐民”体制上的皇帝郡县制国家;同时,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大国财政”也开始定型并不断强化。毋庸讳言,这种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大国财政”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经济财政,但其内在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财政公共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国家如何称职地履行社会管理者职能,在有效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同时处理好小农经济与大国财政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既是关系到王朝兴衰更替的根本问题,亦是后人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对于当前的财税制度改革和现代财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财政 公共性 中国财政史基础理论
一、引言
在之前的研究中,笔者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假说:“公共性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并且选择了中国早期财政史作为考察对象来论证之(童光辉、范建鏋,2015)。简言之,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之一,它要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和实现公共利益作为界定财政职能以及安排财政收支活动的口径和标尺,这在任何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下都概莫例外;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即国家履行其职能的实体是由相应的机构和个人所组成的,这些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既有谋求公共利益的潜力,同时也有出错的可能,而衡量和评估财政公共性充分程度的关键在于考察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分别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上述两种可能性。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历史文献来检验和论证的理论命题。
在这里,笔者将继续循着上述研究思路,并将目光聚焦于东周秦汉时期财政制度转型的事实特征和基本轨迹,并以此来进一步验证上述命题假说。众所周知,东周秦汉之际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转型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国家治理模式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晚清才被迫进行第二次大转型,但第一次大转型时期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境并没有就此完全消失,甚至有些问题还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变得愈加复杂和严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是东周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能够论证上述命题,不仅对于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构建,而且对于现实财政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有意义。
二、战争塑造国家:编户齐民的形成与秦汉帝国的崛起
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上,美国学者蒂利(Tilly,1992)认为,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15至16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越发昂贵,迫使各国的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动员和汲取更多的资源。对此,中央集权化、理性化的民族国家显然要比其处于封建式的分裂状态具有更大的规模效应和更强的汲取能力。后来,许田波(Hui,2005)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进行对比,认为导致中国和欧洲走上不同国家形成路径的秘密就在于战争。深究其中,许田波的研究结论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东周战争之于秦汉帝国崛起的决定性作用却是公认的。例如,杜正胜(1990)和许倬云(2006)等学者都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传统的“封建”制度渐趋崩坏,代替“封建”制度而起的是编户齐民制度,而促使这一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发生的最大动力,则是战争。
(一)编户齐民的制度涵义和发展轨迹
从存世文献来看,完整的“编户齐民”一词出现在汉代典籍中,是指中国古代“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杜正胜,1990)。进言之,“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许倬云,2006)。
当然,中国古代齐民的身份平等或地位相同是相对的。所谓的“齐”主要是针对西周时期民众身份“不齐”的事实而言的,因为在传统的分封采邑制之下,民众的身份既有“国人”与“野人”之别,也有臣属于国君的“公民”与臣属于卿大夫的“私民”之异。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平民的身份发生了由“不齐”而“齐”的重大转变。
1、全民皆兵的新军制和军赋制度改革。在西周时期,民众有“国”、“野”之分,身份是不平等的,服兵役和缴纳军赋是“国人”专属的权利与义务。在“国人”之中,服兵役者亦仅限于一家一丁的正卒,其余子弟并无兵役义务(“羡卒”);同时,全体“国人”以“丘”或“甸”为单位共同为服兵役者置办武器装备、提供衣食钱粮以及为死难者抚养遗属等,所需经费则出自于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因井田而制军赋”,兵役制度、军赋制度和土地制度三位一体(童光辉、范建鏋,2015)。进入春秋战国以后,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2年的五百多年间,强并弱,大并小,战争几乎没有间断。在这一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改革兵役制度,原先不必当兵的“羡卒”和没有当兵资格的“野人”先后被纳入征兵范围。尽管各国的改革进程和具体措施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征“羡卒”在前,征“野人”在后,从有限制、有条件的征兵逐步扩大到全民皆兵(杜正胜,1990)。与之相同步的是,土地制度和军赋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如前所述,在西周时期,“国人”参战所需的衣食钱粮、武器装备等来自于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治者是以土地来换取“国人”的军事服务。此后,西周时期以村社组织为单位的井田制渐趋崩坏,“因井田而制军赋”的运行模式也随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统治者以土地换取军事服务的做法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兵役与授田相对待,获田地则服兵役,反之亦然。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春秋中晚期以来,政府对于农民的授田表面上是西周时期政策的延续,但由于整个社会形势的变化,授田的意义却是大异其趣。在新的授田制下,虽然农民的土地来自国家,但是一经授予,并不收回;而且,政府在按照户籍实行普遍授田之时,还会在登记田地权属的簿书上附上耕者的名字,谓之“名田”,并据此来征租税、差徭役和征兵丁。
又,当时各国统治者曾先后扩大农田的亩制,每亩面积比西周时期要大,但政府分配给每户农民的田亩数依然沿用井田制的“百亩”之数,因为“百亩之田”正适合于一户农民耕作的能力,用来维持一家生计的需要(杨宽,2003)。在这种背景下,武器装备和衣食钱粮等军需改由政府承担,而政府又将这部分费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分摊到平民身上,史籍上所记载的“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初为赋”(《史记》秦孝公十四年)等事件,正是这一连串改制过程中的重要标识。自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即政府将户口作为军赋的课征对象)起,整个秦汉时期的各种人头税皆是以“赋”来命名的。比如,秦国(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又如,汉代成年男女有“算赋”之征;未成年幼童有“口赋”之征;应服兵役而未服者另有“更赋”之征。
2、个体小农经济的确立与土地税制的变迁。在西周晚期,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集体耕种方式已经初显败坏的迹象,到了春秋以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的问题更是表露无遗,农民不肯尽力于“公作”,致使“公田”上的农业生产逐渐没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勤于“私作”,不但尽心经营井田制中分配给农民的“私田”(份地),而且还积极开垦井田以外的土地。“公作”的衰落与“私作”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收入规模。因此,统治者出于争取民众支持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考虑,不得不承认既定事实,并且将分配给农民的份地和私下开垦的田地逐步予以私有化与合法化,实行“履亩而税”,代替原来井田制下的“藉”法或“彻”法。从存世文献来看,鲁国于公元前594年率先实行按亩征税的办法,史称“初税亩”,到了春秋中晚期以后,中原各国也普遍采用这一征税办法。总的来说,这一征税办法在推行之初,农民的负担水平并不轻松但尚不至于苦不堪言,“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墨子·辞过》),然而,从战国中叶开始,由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张,再加上权贵阶层的奢靡无度,“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而齐民小农则在战争和赋役的双重交煎下,“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地处西陲,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改革也比较迟缓,直到公元前408年(秦简公七年)才实行“初租禾”,按田亩多少征收租税,这比鲁国的“初税亩”整整晚了186年。然而,与山东列国有所不同的是,秦国是唯一充分地、有组织地利用土地资源和优惠政策招徕国外劳动力来促进农业发展的国家,授以田宅,使之成为自由民身份的个体小农,而将秦国本国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应付对外的军事战争。同时,对于服兵役的农民实行按军功赐爵位、田宅和奴仆的等爵制,以激发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塑造了一个组织坚韧、活力充沛的耕战阶层,而秦帝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股力量的支持。后来,有秦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汉代政权于建立之初便积极从事安定和恢复小农经济,并将之作为皇朝权力的支柱,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许倬云,2005)。
(二)地方行政系统的重建和国家组织形态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与编户齐民的形成齐头并进的是地方行政系统的重建,亦即,封建制的解体和郡县制的建立。县的建制始于春秋初期,是指国君直接统治的地方;它与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有所不同的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征调军赋的制度。最初,县通常设置在边境地区,既便于国君壮大其统治,又有利于加强边防;后来,国君为剪除强大士族,趁机没收其封邑,也设置为县,于是国境之内也有了县的建制。又,在春秋晚期,与县性质相同的郡开始出现,一开始亦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设置于边境地区,但因其辖区大、人口少,故而行政级别较县为低;之后,随着人口的膨胀,方才在郡之下分设若干县,遂成郡统县的关系(杨宽,2003)。由于改革较为迟缓,郡、县的设置皆非秦国首创,但秦国是战国诸雄之中最早一个从封建制中脱胎换骨全面实行郡县制的诸侯国,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郡和县,却始终难以彻底废除封建制(管东贵,2010)。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战争是促使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发生的最大动力,那么郡县制则是这一国家组织形态最终得以确立和延续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编户齐民的形成必须具备两项条件:一是户口登记制度的建立,二是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而这两项工作又有赖于地方行政系统来负责实施。相对于封建制而言,郡县制的最大特色是尚贤而非世袭,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国君视其政绩任用,而土地、人口及赋税的多寡正是官员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国君以此为抓手将中央政令推行于各地,进而借此控制和动员各种资源。反过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地方行政系统的重构使得他们从封建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后又以个体身份重新纳入国家组织。自此,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和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互为表里,成为此后两千来中华帝国的基本特征。
三、编户齐民体制下的大国财政及其公共职能范围
自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崛起后,建立在编户齐民基础上的“大国财政”的运行格局亦随之显现。概括起来,此所谓的“大国财政”具有三重涵义:一是财政职能的大国效应,尽管历代王朝的实际控制能力时强时弱,但自秦汉以后,政府全面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事务却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里,政府的公共职能范围较先秦时期要宽泛得多,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财政学所定义的三项职能:配置职能、调节职能和稳定职能(童光辉,2011)。二是财政收入的大国效应,即只要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土地和人口,就能使小农经济极其有限的剩余集中到国家手里,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三是财政支出的大国效应,由于财政职能范围的扩展和政府组织规模的膨胀,再加上统治阶层的奢靡消费等无节制的消耗,所以即便是在王朝建立初期,财政支出规模已是十分可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更是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增长态势,直至王朝覆灭。
这里,暂且先将目光聚焦于财政职能的大国效应,后两种大国效应则留待下一部分再讨论。诚然,现代财政学中所定义的三项职能,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提出的,认为政府应当在市场运行结果不合意时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尽管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笔者注意到,若是将上述三项职能及其分类办法视为一个学理层面的分析框架的话,它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和讨论中国古代财政的职能范围。自秦汉以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农成为了帝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是最具生产力效应的一种农业经济形式,但与此同时,相对独立的个体小农又是比较脆弱的,经不起任何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有赖于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来保护。所以,这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在中国绝非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仅为一个近代现象,而是政府始终以一个“老爸爸”的姿态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全面干预和控制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高王凌,2005)。
(一)配置职能
配置职能是财政固有的基本职能之一,自人类社会产生财政活动以来便已有之。又因为国家其职能的实体是由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和人员所组成的,所以可以根据历代官制的架构设置及其运行状况来推测当时财政配置职能的大致范围和主要内容。
1、宗教职能。政权高举神权的旗帜,借神权来论证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决定政权因革的合理性。在中国古代,宗教神学并不发达,人们较少以言论来论证神灵的权威,而是不厌其烦地申述神权是君主权力的来源,用以说明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决定政权因革的合理性。所以,历代王朝都将祭祀奉为国之大政,明文规定各种祀典和正式尊奉的神袛,设有主管部门,比如太常(奉常)为诸卿之首,礼部(春官、宗伯、祀部)一直被指定为国家的重要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普遍设置主管祭祀的部门和职官,上至帝后,下及各级地方行政长官,都必须亲自主持各种祭祀典礼(韦庆远、柏桦,2001)。所以,无论是大司农(治粟内史)掌管的政府财政,还是少府执掌的帝室财政,在宗教祭祀上皆耗费甚巨。对此,马大英(1983)在《汉代财政史》中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兹不赘引。
这里需要稍事提及的是,有学者将皇室支出分为两部分,一是皇室的生活费用,二是宫殿陵墓建造及郊庙祭祀等费用,并统统将其归之为帝室财政的范围。这种说法不太确切,因为宫殿陵墓的建造、特别是郊庙祭祀在当时应属于重大的国事活动,不能将其与皇室的生活消费混为一谈,所以宫殿陵墓建造及郊庙祭祀等费用中相当一部分开支是由大司农(治粟内史)所掌管的政府财政来承担的(林甘泉,2007)。
2、行政职能。国家依赖郡县制度和官僚政治来统治广大众民,官吏的选拔由世袭转变为尚贤,官吏的薪给也由食邑制转变为俸禄制。在西周建国之初,周人将血缘组织(宗法制度)和政治组织(分封制度)结合为一体,利用血缘组织的内聚力转化为政治组织运作的向心力,建立起了一个以姬姓周室宗族体系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族的华夏国家社会。然而,随着世代推移和环境变迁,政治组织逐渐脱离跟血缘组织的关系,再加上血缘组织本身内聚力的不断淡化,原本行之有效宗法封建制自西周晚期以后渐失统治效果,直至解体。同时,在宗法封建制的解体过程中,一种新的“政体细胞”开始出现,那就是“县”制;循此发展,到嬴政统一六国,终至成为推行于全国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由皇帝专制的“郡县制”(管东贵,2010)。
与宗法封建制相比,皇帝郡县制表现出了双重特征。
一方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君权仍以血缘传承为正当性基础,君权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家一姓的“莫大之产业”,皇室宗亲的开支消耗皆由国家财政供给,并单独设置一套职官系统来管理帝室财政,以区别于政府财政。但正如林甘泉(2007)所言,秦汉时期的帝室财政与政府财政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对立的,其意义在于帝室财政与政府财政关系的演变上,以及二者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地位的变化。在秦之前,君主的“私”的财政不仅是国家财政的主体部分,而且君主的“私”的财政与政府的“公”的财政其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汉以后,帝室财政与政府财政的分立是一种进步,而此后帝室财政在国家财政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削弱并最终归于国家财政,则是又一次进步,因为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凭借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任意侵吞国库。
另一方面,尽管皇帝在名义上拥有一切权力,但事实上一人之智又不足以治天下之人,而是有赖于官僚政治和郡县制度来维系皇权统治。具言之,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有总揽一切的宰相以及各有职掌的层级化、专业化的文武官员;同时,地方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延伸,其行政主管的任免控制在中央而集权于君主。这些大小官员大部分不再是凭借宗法血缘身份的封建世卿,而是以才学干禄的平民俊秀,全国各地人才通过相对开放的选拔机制进入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这也正是皇权统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关键所在,即在“家天下”之中保有相当程度“公天下”的一面。
伴随着官吏的选拔由世袭转变为尚贤,官吏的薪给制度也由食邑制转变为俸禄制。西周及春秋时期实行的贵族世官世禄制,只要维持贵族身份,采邑也就可以世袭拥有,相当于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王国。在战国秦汉以后,随着皇帝专制的官僚政治的确立,除了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官僚没有世袭的特权,而是实行据官职品级按规定时间领取报酬的俸禄制度。此后,尽管历代王朝的俸禄标准不一,但官吏俸禄始终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支出内容之一。
3、军事职能。随着秦汉帝国逐步将疆域扩展至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与行政系统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因而不得不耗费巨大的资源来维护边境安全、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诚如许倬云(2011)所言,“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就进入了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在秦汉时期,这一主控力量的疆域范围,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系统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并由此形成了“华夷有别”的华夏边缘。而且,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国家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把中国人或华夏族群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区的华夏)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所以各个朝代国力或强或弱,政治上或分或合,但是都不惜耗费巨大的资源来维持此边缘(王明珂,2006)。
当然,维持此边缘的方式有很多,或以武力驱逐、羁縻,或以婚媾和贸易等其他方式,但不论何种方式都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故此,军费与官俸一样,也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开支项目之一,而历代军费开支规模及负担水平既与当时的兵役制度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更替。是故,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在论及读史时,以为《食货志》和《兵志》最应当详细研读(台湾中华书局,1983)。
4、公共建设。作为维系大一统国家运转的纽带和载体之一,公共建设之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各类基础设施更为发达,但由此产生的正、负效应也更为显著。侯家驹(2008)在历陈大一统国家在经济上的缺失和优点时强调,在这么大的空间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再佐以统一的度量衡、法令规则、文字与器械制式,以及水陆交通路线之开辟,关卡之开放,使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大为降低,为经济活动提供广泛的外部经济,且因版图辽阔,个别地区可以根据比较经济法则,相互补充与相互支持,构成一般均衡经济体系。不但如此,大一统在经济上的积极贡献与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其实互为表里,而作为维系大一统国家运转的纽带和载体之一,公共建设之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各类基础设施更为发达。以道路网为例,“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程度,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遵循同一个道路网,政令由此传达各处,讯息由此上通下达,人才也由此周流于中央及地方”,与罗马帝国相比较,“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的统一。罗马则不然”(许倬云,2006)。
公共建设更为发达,但与此同时,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亦是成倍的增长,由此带来的正、负效应也更为显著,即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在维持大一统帝国运转的同时,不仅需要消耗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同时还需要役使相当数量的无偿劳动力,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赋役负担。所以,在讨论中国财政史时,决不能忽视了徭役制度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
首先,在中国古代,徭役的征调范围甚为广泛,“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文献通考·自序》)。也就是说,各级政府(包括乡、里等准政权机构)皆有权力征调徭役,而政府的种种需要皆可佥派为徭役来取得。
其次,徭役的征调对象通常以成年劳动力为主,即所谓的“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文献通考·户口考一》),所以,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户籍的编制和使用。宋代以前,政府只编造户籍而没有地籍,土地赋税等都登于户籍中;宋代以后,虽然有单行地籍的设立,但实际上,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地籍的作用和意义仍不能和户籍相提并论(刘志伟,2010)。
(二)调节职能
在现代财政学中,由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所决定的收入初次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客观上要求社会有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再分配机制,那显然只有依靠外部力量,以非市场化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而国家及其财政政策就是重要的外部力量之一。然而,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并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会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早在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初期便已有之。如果说商周时期的贫富差距主要发生在统治阶层和民众之间的话,那么士农工商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甚至被有识之士视为治国之大患,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患不均”并非提倡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主张执政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来调节财富分配状况,使之与人们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地位相一致,只是相对的公平。
进而,这种相对的公平在财政经济领域,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的期许和诉求。
其一,赋役负担的公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中,民众“作为天生之子,生民都是平等、公平的存在。在生民的层面上,天下是平等的领域,是公共性原理发挥作用之场所,其中并没有等级差别”。所以“汉代至唐代的民众,除去附载于别人户籍中的奴婢、部曲等隶属民,如‘天下百姓’所称呼的那样,一律都是以‘百姓’这样的身份被支配。在这一‘百姓’之中,尽管有工农士商的职业区别与贫富之差,但是作为‘百姓’,首先是被均一把握的:既是均一的分田所有者,又是均一的租税、徭役承担者。而根据资产额的户等分类与根据职业的四民分工分类都是从属性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所发挥的机能是导入负担的差别化,来修正现实中存在的因贫富、职业差别所造成的负担不平等。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负担”(渡边信一郎,中译本2008)。
其二,财富分配的公平。正如汉儒董仲舒所言,“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当然,政府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实现“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善良愿望?在这方面,历代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足以为后世镜鉴。
(三)稳定职能
“稳定职能”、“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都是现代术语,古汉语中并没有专门的词汇可与之对应,而只有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食货”。在古汉语中,“食货”是国家财政经济活动的统称,涵盖了衣食日用、户口田制、财政税收、货币理财、通商惠工等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事项和活动,而这里所讨论的财政稳定职能和宏观调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来调节物价水平和保障民食供应。
在中国古代,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二:一是外部风险,即由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外部因素所引致的经济波动;二是市场风险,即由市场机制内生的物价波动、土地兼并等因素所引致的经济失衡。前一种风险自古有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礼记·王制》)之类的政治劝诫,《周礼》一书更是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非常详尽且周密地规划了备灾赈灾制度架构和政策安排。后一种风险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现有历史文献表明,最晚在战国秦汉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思想家和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诸如《管子·轻重篇》和《史记·平准书》等历史文献都曾非常详尽地记述。在政策实践中,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粮食储备工作,形成了以常平仓(首创于汉代)、义仓(出现于隋代)和社仓(成型于南宋)为骨干的公共粮食储备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
四、聚敛的迷思:大国财政的税收悖论和治乱循环
所谓税收悖论(Paradox of Tax)是指国家在汲取财政收入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民众之所以愿意向国家支付税款的根本前提在于,他们确信国家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另一方面,税收也可能从私人那里汲取超额财富,侵害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在欧洲近现代史上,税收悖论是现代国家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核心命题,是理解财政发展与国家建设的一条主线索(Sacks,1994)。事实上,类似的命题同样存在于古代中国,只是采取的解决办法不同,由此产生的结果更是截然有别,而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亦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财政收入的大国效应
如前所述,秦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农在扣除必要的生产生活所需之后,能够用于纳税应役的经济剩余是比较有限的,《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晁错等人关于“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描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普通的农民家庭在正常年份除了辛苦从事耕种之外,通常还要从事副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以弥补生计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地位和社会长治久安等方面的考虑,将“轻徭薄赋”视为治国理财的金科玉律,有意识地将法定负担率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得益于财政收入的大国效应,农民手中较为有限的经济剩余也会形成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规模,在国家的运转提供充足财力的同时,又不至于剥夺民众的生存手段。但前提是,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所以,汉代政府的户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地方政府每年举行“案比”,定期调查登录户口;中央政府则是通过“上计”制度,要求地方政府逐级上报户口、垦田和钱谷等内容,并以此来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和监控地方财政的运行。
在东周秦汉以后,商品经济渐趋发达,但总的来说,国家能够从工商业部门或工商业者那里汲取的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不排除个别时期因特殊需要采取的重税和专卖政策)。例如,秦汉两朝曾将“市井之税”、“山海池泽之税”等工商税收划归主管皇室财政的“少府”管理,而“少者,小也,故称少府”(《汉书·食货志》)。应当说,这种财政收入结构的形成,与“重农抑商”的政策思维有着莫大的关系,即“执政者认为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工作,才能创造财富。也因此,他们认为农业生产者才是真正有能力负担租税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税负一向偏重,而工商业者只负担一些杂税而已”(赵冈、陈钟毅,2006),结果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二)财政支出的大国效应
如前所述,“轻徭薄赋”在中国古代一直被奉为治国理财的金科玉律。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能否真正实现“轻徭薄赋”,最终取决于国家的支出需要和财政状况。对此,古人亦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而,传统财政思想对财赋的征集和积蓄,都有某种加以抑制和寻求平衡的趋向(高王凌,2005),力主将财政支出控制在法定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问题是,政策实践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呢?
从第三部分的讨论中可以得知,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有五项最为大宗,分别是:官吏俸给、仪典花费、社会救济、国防经费和官府工程费用等。根据卢建荣(2009)的研究,在上述各项支出中,“前三项为士大夫官僚集团认为系必不可省。至于后两项,咸认能省则省,至少不可多。这也是基于这两项经费一旦使用无节,将造成入不敷出的赤字局面。然而,工程开销或许较能透过主观意愿予以节制,但国防费用的撙节恐非主观意愿所能奏效,因为战争并非片面想不打就可以不用打,打了想停就停。战争是消耗金钱的无底洞,古今一例……再者,工程建设,始终是古今帝王难以摆脱的诱惑,于此也成为帝王的销金库。”此外,自然灾害是人类日常生活领域的常态性事件,每当灾害发生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救济支出增加,收支压力也随之出现。故此,每当国家遭遇战争、灾害以及举办大型公共工程时,国家的法定收入(包括各种徭役的法定时间)将难以支持浩繁的支出需要,而统治者总要有一番增加财政收入和弥补收支缺口的作为,这就使得“轻徭薄赋”的低税理想与现实中的支出刚性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兼顾和平衡的矛盾。
(三)财政危机与税收悖论
上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决定了“轻徭薄赋”政策必然是建立在对内厉行节约、对外相安无事的基础上。惟其如此,一个较低的法定负担率方能满足国家的支出需要,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结余。例如,汉代经过“文景之治”后,“至今上(即汉武帝——引者注)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国家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统治者开始“内兴功作,外攘四夷”,各项财政支出迅速膨胀,不但耗尽了几代人的积蓄,而且使府库虚竭,国家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同时,由于国家原先从工商业部门或工商业者那里汲取的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商人阶层的富裕和国家财政的窘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繁荣时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与商人之间“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的缺失,促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来抑制工商业活动和打击商人力量,先是改革币制,而后又实行盐铁专卖,再是对工商业者开征重税(“初算商车”、“算缗”和“告缗”等),而且还通过对其他商品的买卖牟利(“平准均输”)等等。其结果是,国家在短期内汲取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却未能使国家财政的运行机制重新恢复到良性的轨道上来,带给民众更多的是伤害,而不是帮助,社会矛盾也愈加激化。
在武帝之后,昭帝和宣帝时号称中兴,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国家财政的开支规模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财政机制的失衡状态没有根本好转。自成帝至王莽,国家财政更是完全失控,直至王朝覆灭。可见,税收悖论及其解决办法与王朝的治乱兴衰相始终。
五、结论与启示
自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大国财政”属于一种典型的非市场经济财政①,其内在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与现代市场经济财政相去甚远,但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知,当时的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制度安排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性问题在整个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任何的执政者来说,这都是一个事关王朝兴衰更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命题,称职者兴,失职者亡,所以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权力架构和制度体系呈现出一个双重特征:在“家天下”之中保有相当程度“公天下”的一面。
当然,这种“公天下”是有限度的。单就财税政策而言,由于法定制度的不完善和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等原因,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税收悖论”问题,即国家在不断培植小农经济以固国本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摧毁之,历代王朝也在随之而来的横征暴敛和财政危机中走向了覆灭,没能跳出治乱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春秋以后,商品经济素称发达,但并没有就此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笔者曾在《中国古代政府管制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刍议》一文中曾有过一个简略的分析,恕不赘引。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1.Hui Victoria Tin-Bor.2005.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许田波.徐进<译>.2011.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Sacks,D.H.1994.The Paradox of Taxation:Fiscal Crises Parliament and Liberty in England,1450-1640[M].in Hoffman,P.T.and Norberg,K.(eds.)Fiscal Crises,Liberty,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450-1789,Stanford University.
3.TillyCharles.1992.Coercion,Capitaland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M].Cambridge:Blackwell.
4.渡边信一郎.2008.中国古代王权与天下秩序[M].北京:中华书局。
5.杜正胜.1990.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6.高王凌.2005.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管东贵.2010.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
8.侯家驹.2008.中国经济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
9.林甘泉.2007.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0.刘志伟.2010.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马大英.1983.汉代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台湾中华书局.1983.中国历代食货典[M].台北:中华书局。
13.童光辉.2011.财政的公共性:概念分歧、反思和拓展[J].财贸经济,2。
14.童光辉、范建鏋.2015.公共性: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基于我国早期财政史的初步考察[J].现代财经,5。
15.王明珂.200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韦庆远、柏桦.2001.中国官制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7.许倬云.2005.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8.许倬云.2006.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许倬云.2011.大国霸业的兴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杨宽.2003.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1.赵冈、陈钟毅.2006.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
(本栏目责任编辑:尹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