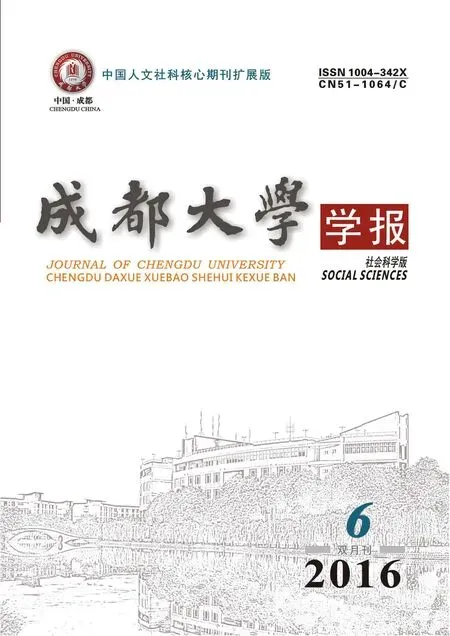熊伯龙《无何集》鬼神观简析
钟艳艳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熊伯龙《无何集》鬼神观简析
钟艳艳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作为我国无神论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相比同一时期的王夫之等人,熊伯龙很少为人所提及,他的无神论著作《无何集》一书也是在他辞世近百年之后才得以面世。但是,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承前启后,在无神论思想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位置,因而对熊氏无神论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把握熊伯龙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对《无何集・鬼神类》进行分析,呈现熊氏关于鬼神之道的基本认识及其以无神论为工具的缕析鬼神观念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熊伯龙;《无何集》;鬼神观;无神论
熊伯龙,字次侯,号塞斋,别号钟陵,湖北汉阳人。根据《湖北通志》推算,熊伯龙应生于1617年,卒于1669年。他于1649年考中进士,当时以善作八股文著称。
1666年夏,熊氏作《无何集》一书,这本书在他死后才得刊行,并得到与东汉著名无神论家王充齐名的赞誉。《无何集》全书以王充《论衡》为宗,本名为《论衡精选》,是熊氏将《论衡》中的精彩片段进行摘录并加入各家评述及个人看法综合而成。根据熊氏在《无何集》中的自述,《无何集》一书取名于《荀子》:“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1]313著书的目的是为“辟神怪福祸之说”、“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熊氏在《无何集》中将王充及其《论衡》置于极高的地位,评价其为“《论衡》之教兴,圣人之道明”[2]15。他继承了王充“气”生天地万物的思想,对各种神怪福祸之说皆采用自然的唯物主义态度加以批判。
一、熊氏《无何集》鬼神观思想的渊源
熊伯龙生于明末卒于清康熙年间,他出生的明朝末期社会昏暗、统治者腐败无能、官员冗杂、百姓麻木不仁,因而导致他对明朝政坛较为失望。在满清政权建立后,众多明代官员、思想家退出政治舞台,隐居山林以保“名节”,而熊伯龙却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取进士,后来官至内阁学士。朝代的变更以及为官的经历对熊伯龙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官员阶层,他能便利地接触到大量的史书典籍,对于历史上鬼神思想的发展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鬼神观,世俗社会流行的鬼神观念及鬼神崇拜祭祀行为都为熊氏的鬼神观的形成提供了资源。
(一)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特征及其对熊氏的影响
明末清初,绵延于中国大地数百年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清初社会滋生、萌芽。启蒙思潮的传播与自然学科的进步,使世俗社会的封建迷信受到巨大挑战。这一时期,本土宗教的发展也受到西方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唯物主义自然观冲击着清朝建立以来的鬼神信仰及世俗迷信,熊伯龙的鬼神思想受此影响颇深。
在社会治理层面,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后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使社会局势越来越恶化,各阶层民众之间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发。面对这一社会现实,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加强对宗教文化传播等的扶持,规范宗教信仰体系,以期从思想上推动社会稳定局面的实现。乾隆时期,清政府就组织了多次佛经翻译活动,将佛教经典译为满文、蒙文。经文间的互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但清政府只是一味简单地通过强化信仰的存在以稳定社会思潮,并没有看到社会发展中的阶级矛盾,以至于各宗教的发展与清政府的意愿相攀附,并与世俗迷信相结合导致其自身发展逐渐呈现出庸俗化的趋势。以佛教为例,清初的佛教延续了宋明时期以来发展日趋衰微之态势,虽然在统治者的扶持之下有所发展,但由于理论上并无较大创新,且受到西方早期启蒙思潮的冲击,并未受到大众广泛的青睐。民间信仰呈现出佛教教义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相结合,并吸收迷信习俗的现象,进一步杂糅衍生出众多佛教源生而来的民间宗教,如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天理教、信奉弥勒佛的清水教,以及主张吃斋念佛的长生教等。
清初,中国古代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达到巅峰状态继而走向终结。在此期间清代涌现出一大批诸如王夫之、颜元、黄宗羲等的无神论思想家,他们对有神论的批判大多集中于对佛教信仰的批判上,熊伯龙作为清代杰出的无神论者亦是如此。可以说,熊氏在《无何集》中对社会中鬼神信仰崇拜行为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现实社会中佛教“歪曲”发展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深深的无奈。看到了宗教发展庸俗化、低俗化的社会现实,进一步促使熊伯龙坚定不移地站在无神论的阵营之中,从而以对世俗社会流行的鬼神观念进行批判为己任以醒民志。
(二)王充《论衡》对熊氏鬼神观念的影响
在《无何集》一书中,熊伯龙对王充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尤其赞扬王充对孔孟之道的继承与发扬,称其向来以孔孟为宗。在王清顿为《无何集》所作的序中也准确地指出:“《论衡》一书,发明孔子之道者也。”赞扬其“不信妖异,不信鬼怪”[2]1深得孔子之意。熊氏在《无何集・卷之首》中赞扬道:“《论衡》者,入德之门也。《论衡》之教兴,圣人之道明”,“设当今之世,人人取《论衡》而读之,知神怪之说不足信。则信圣经贤传之言”[2]15。熊氏的《无何集》一书就是建立在对王充《论衡》中的无神论思想的详尽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之上的。他将《论衡》中体现的各类思想理论进行分类,形成了十三个类别的主题,其中就包括“鬼神类”,而该类别对王充鬼神思想的阐述又以《论衡・书虚》、《论衡・死伪》和《论衡・订鬼》等篇章为主。
从王充的“自纪”中可以看出,他虽为官,但未曾受到朝廷的重视,一生清贫。所作《论衡》一书在当时也未能受到文人的青睐,被人视为荒诞之作,在蔡邕和王朗的无意发现之下才慢慢得以流传。王充生活的汉代,朝廷鼓吹“天人感应”学说并由汉章帝亲自主持编纂了《白虎通义》,将孔子及儒家经典神秘化并尊为金科玉律。汉代社会谶纬学说流行,官方渲染有鬼论以役使民众,意图从思想上绑架劳动人民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而王充作《论衡》的目的正如他所说,是为了“疾虚妄”,对汉代的谶纬之风等世俗迷信学说投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而这正和熊氏的无神论思想倾向相契合,给熊氏的无神论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保证。熊氏的鬼神思想是建立在对王充鬼神思想的综合阐述基础之上的,王充学说对于熊氏思想的启发与引领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王充所提倡的“气”一元论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二气所生,死后复归于气,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在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所突破,而王充在其无神理论的论述中也积极吸取了科学技术的理论。譬如当政者宣扬人由兵器所杀之后会化为鬼火以愚弄百姓,王充结合科学知识,认为所谓的“鬼火”就是磷,是人死后精血转化为磷的物质表现,并非是鬼火。虽然他错误地将磷认为是死人的血液,但能给予鬼魂的迷像以科学的解释在他所处的时代已是一大进步。王充“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使其在论述鬼神、迷信之说时,善于将世俗流传的鬼神现象与现实事物存在相结合,进行物质规律层面的解释,这种思维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熊氏对鬼神的论证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熊氏在《无何集》全书中,不论针对何种世俗流行的谬论,都力求给予物质规律层面的解释,始终坚持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
二、熊氏《无何集》鬼神观的思想特征
熊氏《无何集》一书,共14卷,其中第3卷为鬼神类,虽占全书篇幅不多,但对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熊氏在《无何集》第三卷中引用了诸多思想家关于鬼神的认识及态度,总体上对王充《论衡》中体现的鬼神观念的批判做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摘录与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熊氏的鬼神观既睿智地分析了鬼、神存在的荒谬,体现了他的唯物立场,也偶尔陷入宿命论等泥沼而未能彻底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一)“物死不为鬼”
《论衡・订鬼》曰:“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3]931熊氏继承了王充的鬼神思想,认为世间无鬼,凡认为有鬼存在的只是因为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2]136熊氏分析认为,譬如庖丁解牛与伯乐相马,伯乐相马所见无非马者,庖丁解牛双眼所见皆为死牛而无生牛,皆是思念存想所致,自见异物。人之所以认为有鬼存在,只是疑心所致。“心怯胆寒,闻鸟兽声,见树木影,皆谓是鬼。夜行迷路,则谓鬼设帐。”[2]138熊氏将其讽刺为“草木皆兵”,皆是由于心中的谜团没有得到及时的破解所致。
关于人死后之事,熊氏则认为人死精气灭,更无化鬼之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3]871人由精气所生,精气即为血脉,人死后血脉竭精气灭,继而形体枯朽化为灰土,没有化鬼的基础和必要。“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2]116这是王充对“鬼”的解说。熊氏对这一认识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人的死亡只是简单的物质消亡的现象而不掺杂任何神怪现象。在人死后无鬼的认识基础上,熊氏又指出人死无知且不能害人。他认为人生于精气死后复归于精气,出生之前对人世一无所知而死后亦然。且人死之后肉体既灭,精气便无物质对象可依赖,形体与精气相互依存,天下没有独燃之火,那么就更不会有不依赖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气了。人死犹如蜡烛之灭,蜡烛既灭则火光不耀,由此推之,人死则其知亦不惠。如果说人死后仍有知,那么蜡烛灭了仍然应该有火光才是。在这里,熊氏继承了前代神灭论的思想,尤其是桓谭与范缜的思想。桓谭在《新论》中曾说“精神居形体,犹独火之燃烛”,“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能为之润泽”[4]176-177。范缜《神灭论》也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4]485
对于人死后可以害人之说的批判,熊氏继承了王充的观点,“凡人与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尖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败,不能复持刀,爪牙坠落,不能复啮噬,安能害人?”[2]124人与物的精神实为一物,人死就像物体消失一样,精神也随之消失,更不用说害人了。人死后肉体腐朽,肢体不存,无法驾驭利器杀人,因而便失去害人的物质基础及工具了。《论衡・论死》中说:“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语言,则不能害人矣。”[3]880熊氏进一步举例认为,人愤怒而害人是精神在胸中起作用,这就相当于“火炽而鼎沸,沸止而气歇”。人之将死,精气消失殆尽,自然无法愤怒而生害人之意,且人死相当于“汤之离釜”,因而无法害人。
由于古人相信人死后化为鬼,因而格外重视对于逝者及先祖的祭祀。墨子的“薄葬”主张便是针对当时人们过分在意祭祀之礼导致“厚葬”而提出的。在《论衡・祀义》中,王充认为世人之所以重视祭祀,是以为祭祀鬼神必定有福报而不祭祀则会有祸事发生。在这里,鬼神似乎扮演了宾客的角色,享用祭祀者的祭品及心意便会对其有所回报。而熊氏认为祭祀实质上是祭祀者“自尽恩勤”而已,鬼神未必会享用。况且,假设鬼神能够享用祭祀之物,那么天地之间方圆万里,仅仅歆享世人供奉的微薄祭品是难以裹腹的,人吃不饱尚且会发怒,倘若天吃不饱则应怒气更盛,更不用说报恩于人了。这样看来祭祖是由于“生存之时,谨敬供养;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示不忘先”[2]146。与其说祭祖是对逝去先祖的魂灵的畏惧,毋宁理解其为对逝者的尊敬。且世人行祭祀之礼时不注重自身修养只是片面的使献祭之物更为丰厚,且先辈在世时并不孝敬待其死后却格外敬畏其魂灵,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那么世上究竟有无鬼的存在呢?熊氏通过一系列的论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熊伯龙认为精神依附于形体,“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2]116,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他认为人由精气血脉所生,死后精气散血脉尽,无法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就像普通的野草春夏繁荣秋冬枯死一样,更不用说化鬼了。况且人生来福寿不一,难免会有亲朋骨肉分离的厄运,倘若人死为鬼,那么人死后便可与家人团聚,如此前可见古人后能遇来者,何乐而不为,岂不人人愿意为鬼?
(二)“畏死而后神明之说兴”
“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谓之神”[3]285,“神者,恍惚无形,出入无门,上下无根,故谓之神”[3]304,“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3]1100。这是王充对于“神”的认识。熊氏则认为人之所以相信世上有神的存在只是因为“畏死”而已。譬如人在渡江时担心大浪害人则认为江涛有神,惧怕火的威力则又有火神,皆是由于“畏死之心迫,而后神明之说兴”。熊氏举例当时的县官在破难决之案时便去城隍庙中求神,求神在梦中告知,继而抓出犯人,这也只是“以神道设教”,假借神明之口,并非真能在梦中见到神。
《无何集》卷三列举明朝永乐年间尚书铁弦被杀一事。铁弦被煮于油锅之中但身体却指着皇帝的方向,皇帝于是大怒,命侍从用铁棒固定他的身体,结果侍从反而被热油溅到身上导致肌肤糜烂。于是人们便认为铁弦死后仍有神存在。其实只是由于人们认为他是忠臣且赖于“作史者好神其事,妄增之”罢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吴王夫差杀伍子胥将其投于江中,子胥心中愤恨,借助江水的浪涛杀人。又如传书说孔子葬于泗水地,泗水为了孔子墓的缘故而却流。这是为了说明孔子之德能使水谓之却流“不湍其墓”,孔子之魂圣。熊氏对此事讽刺道:“孔子生时,推排不容。生时无佑,死反有报乎?”[2]109他以其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说明水之却流是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况且江河流动尚且有回复之处,名山大川偶尔也会改变方向,那么泗水偶尔却流也就不足为怪了。并由此得出结论:圣如孔子尚不能死后有神使水为之却流,更不用说传闻中的其他人了,那些说人死后有神的传闻都只是好事者徒增之罢了。
桓谭在向光武帝进谏时曾经说过,世人相信神怪、谶纬之说,皆是因为好事者为迎合世人“贵于异闻”的口味而“徒增之”。熊氏对此总结道:世上所传神怪之事“有时合者,偶然适中,非先知也。世人因有事偶合,故疑以为神”[2]426。“偶”、“适”二字,简单明了地表明了熊氏对于神的态度,大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意味。对于“神”,熊氏并未作出类似“订鬼”那样多的论述,不过寥寥数语,但却正中要害。
(三)“气”论物质说与“偶”论发生说兼存
熊氏的鬼神观思想在对以往无神论思想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沿袭了荀子与王充的思想,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综合为以下两点:
首先,熊伯龙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立场直面鬼神。
由于受到以往先贤尤其是王充思想的影响,熊氏在论述鬼神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其朴素的自然观对当时社会流行的鬼神之说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王充的“气”一元论思想发展至熊氏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譬如熊氏认为人由精气所生,死后复归于精气,这一点与王充的思想是一致的。面对当时人死为鬼、人死、有知、人死能害人之说,熊氏继承了王充的观点,认为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譬如世人盛传元世祖杀文天祥,待其妻前往收尸时发现文天祥的面色就和生前一样并无死去的痕迹。熊氏则认为,大概元世祖杀文天祥时恰逢十二月,“面如生者,尸冻如生耳,非文人死后面有异也。”[2]112这也是因为世人觉得文天祥为义士,为其冤死而惋惜,又有好事者迎合世人口味徒增之,与前文提到的铁铉案同。
常人由于心中已有鬼神存在的影子,因此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丝一毫“微妙”的现象便会“疑神疑鬼”。熊氏针对人性的这一弱点表示,人之所以认为有鬼神存在只怕是自己吓自己的成分居多而事实上并无其事。“余尝山居夜坐,闻有作呕恶声者,开户视之,乃以巨鼠。又尝卧后闻壁间弹指者,急其烛之,乃以叩头虫系于蛛网,不能脱耳。”[2]119倘若这两件小事发生在愚昧的民众身上,必定又要深深地为鬼神之说摇旗呐喊一番,而熊氏心中并无鬼神存在,且其怀揣一探究竟之心,以实际经验证明鬼神不存在,而后每逢他遇人言及鬼神之事都会列举这两件小事来打消别人“疑神疑鬼”的念头,捍卫其无神的立场。
其次,熊氏的鬼神观有时陷入偶然论、宿命论。
仅仅从《无何集・鬼神类》我们就可以获悉,熊氏在阐述其无神论立场的鬼神思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偶然论与宿命论的泥淖中。在其批判大量的鬼神异闻事件时,虽然着力借助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作为批判武器,自觉地使用“天道自然”和“气”生万物的观点解释某些鬼神现象,但与此同时,他将一部分导致人们产生鬼神观念的事件归咎于命运使然或偶然发生。在《无何集》中,熊氏对幸、偶、适三字的使用就多达数十处。譬如在论及孔子葬于泗水一事,时人以为孔子死后仍有神存在,概因其德圣导致泗水为之德感化,不忍“湍其墓”而“却流”。熊氏对时人的观点不予苟同,但他也并未从纯粹的自然界物质现象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只是将其原因表述为“泗水偶自却流”,事件的发生是偶然性的,其结果是熊氏并未对该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转向对人们的态度批判上,讽刺孔子在世之时未能受到重视,反而在死后被尊为圣贤。又如《论衡・命禄》中说:“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由此看来,鬼神之说的兴起导致世人将贫富与鬼神联系在一起,神明使人生活富裕而鬼则使人贫贱没落。这恰恰迎合了世人的世俗心理所寄,人们出于对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会对鬼神之道予以重视。而熊氏则认为,假使有鬼神的存在,它们控制世人生活的富裕与否也只是偶然的,富贵贫贱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推知神不灵而鬼无知了。这两处案例都能表现出,熊氏在对鬼神进行相关论述时,仍旧未能摆脱其时代的阴影,毕竟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宿命论不可能一夕之间消失殆尽。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明末清初文人思想家包括熊氏的无神立场大都涉及到对佛教的因果轮回、天堂地狱说的攻击,但佛教的轮回宿命思想注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熊氏的无神思想,使其在论述自己的鬼神思想时不可避免地时而偏离到了宿命论的轨道上。
三、熊氏《无何集》鬼神观思想的历史地位及价值
与熊伯龙同时代的著名无神论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在强调其无神论立场时,巧妙地将社会的腐朽与封建神学迷信加以联系进行批判,表现出昂扬的战斗力。他们对巫术、迷信等鬼神信仰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对无神论史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熊伯龙在批判呈现粗俗化趋势的佛教、道教和宗教化的宗明理学时,与逐渐东传的西方科学技术、启蒙思想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牙含章先生就认为,以熊伯龙与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无神论,完成了总结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历史任务,标志着中国古代无神论发展的高峰和总结。
(一)熊氏思想对中国无神论史发展做出的贡献
中国无神论发展至王夫之时,已达到相对完备成熟的程度。王夫之以自然观和人事为本论,阐明了无神论“贞生死尽人道”的生死观和鬼神观,但由于时代局限,他最终未能脱离神秘主义的氛围。他虽以气一元论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但却给鬼神置换概念,将其表述为形与神相交后知觉的产物。这就将其刚刚萌芽的对于封建神学产生根源的揭示扼杀于襁褓之中,而这一点最终在熊氏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熊氏《无何集》对宗教神学与封建世俗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清算,总结了无神论史上反神学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封建神学的欺骗性及其产生的根源做出了初步的分析。熊氏不止一次表示,鬼神观念的产生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困惑不解。而且人们对造成社会混乱的阶级原因缺乏认识,进而将社会动乱、自然现象归结于鬼神的操控,这就给封建神学的产生提供了滋养的沃土。熊氏在批判封建神学时,初步揭示了宗教有神论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并能意识到所谓鬼神的形象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他由人们创设出的江涛之神、瘟疫之神、山神、风神等自然神推出人们出于对自然压力和生老病死等现象的无力感与恐惧感导致了宗教观念的产生,同时还列举了大量“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的社会现象来揭示宗教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正是由于盲目愚信的人民大众无法正视、看清社会现实,才导致敬鬼拜神之风日盛,这在古代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熊氏鬼神思想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的启示
熊氏在论述自己的鬼神思想时,立足于无神论的立场,充分综合了各家观点,在其援引的文献中不乏各类笔记志怪小说,由此可以看出其用心之深、涉猎之广。而熊氏在论述自家思想时的写作手法也有其自身的特色。
其一,从《无何集》书中我们不难发现,熊氏擅长使用逻辑推理,通过对个别事例的描述逐步推导出一般原理。譬如熊氏在论证鬼神不能享用祭品因而也不会操控人生祸福时就推理道:鬼神不能享用祭品,那么就不能左右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福祸得失。而“福祸之起,由于喜怒;喜怒之发,由于腹肠。有腹肠者辄能饮食。不能饮食则无腹肠,无腹肠则无用喜怒,无喜怒则无用为祸福矣。”[2]146
其二,熊氏不仅捍卫着自己的无神立场,同时对于世人言传的鬼神之事进行尖锐的抨击。他保留了王充“疾虚妄”的精神,当有人沉迷于鬼神之说时,他也会做出力所能及的劝说,试图通过一人的微薄之力“醒民智”。而熊氏在辨认鬼神之说的荒谬性时,擅于旁征侧引,通过大量援引历史事实及史书典籍,以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四、结语
熊伯龙作为清代也是我国整个古代社会中杰出的无神论者,其思想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视角,将其鬼神思想放入无神论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公正客观地看待他的鬼神思想,正视其思想对我国无神论史的发展与推动。研究和挖掘熊伯龙的鬼神思想是对我国无神论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对当代无神论思想资料库的构成也有积极价值。当然熊氏的鬼神观思想仅仅是其无神论思想的一部分,对他的无神论思想的系统研究尚有待学界先进一起开展。
[1]王先谦 .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清】熊伯龙.无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两汉、隋唐部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刘晓红)
B249.9
:A
:1004-342(2016)06-61-06
2016-03-10
钟艳艳(1993-),女,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