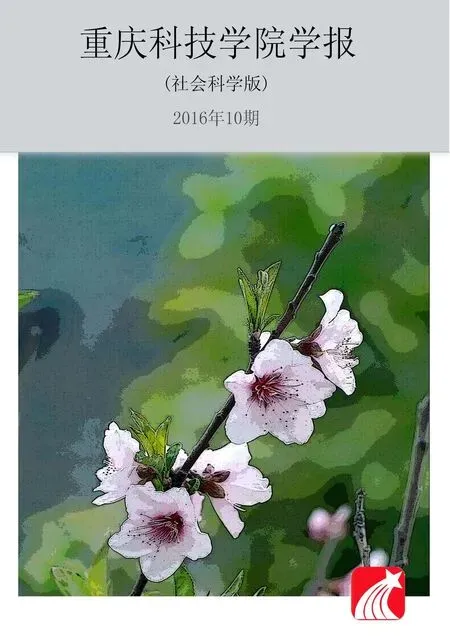王弼治国理论研究
张盈盈
王弼治国理论研究
张盈盈
王弼的治国理论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有关思想。他将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统一起来,提出了“因物自然”的观点,主张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实现“大治”,即所谓“因道立制”。
儒家;道家;因物自然;有为;无为
在治国理论上,董仲舒“以名为教”,侧重“正”与“教”,为统治者在思想上扫除异端,将统治阶层的思想贯彻到普通大众。董仲舒把“教化”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体现了儒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所具有的特殊价值[1]。教化的目的是“以名正物”,落实到普通百姓身上,演变为“以义正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义法》)“我”被纳入到“义”之中,意味着对“我”的约束和引导。以名为教的顺利实施需要德与刑的兼容。为了使得“以义正我”现实有效,董仲舒又将“义”与“法”联系起来,企图凸显“以义正我”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董仲舒以后,汉代儒家基本上贯彻了这种“有为”的做法。东汉章帝主持制定的《白虎通义》,更是将董仲舒的“教化”与“刑罚”的理论贯彻实施到各个领域,成为东汉的“国宪”。然而,这种治理方式以统治阶层的立场出发,无视普通大众的内心需求,因此必然走向衰亡。
一、无为而治
汉代统治阶层“以名正物”,独断专行,一律施行“名教”。无论是“教化”还是“刑罚”都表现出过度的“有为”,加速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君主为政,应以民为重,而过分强调“有为”的治理原则,就像手拿一个模子,百姓不符合模子的部分,一律压制,这必然导致对个体自然本性的伤害。王弼在《老子注》中批判了这种治理方式。
“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权威,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老子注》72章)
“僻”,邪僻。《诗·大雅·板》曰:“民之多僻,无自立僻”。郑玄注:“民之行多为邪僻者,乃女君臣之过;无自谓所建为法也。”因“民从上”,所以造成人民邪僻与社会混乱的原因在上者(统治阶层),而不在民众自身。如果在上者舍“清静”,行“躁欲”(为所欲为),去“谦后”,企图以权威行事,就会导致物乱民邪。“以威治民”,民不堪受其“威”,从而导致统治者与普通大众关系的崩溃。若一个朝代民心大失,那么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由此可见,“守静无衰”,“静为躁君”,对于统治者来讲,“清静”与“无为”极为重要。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以此致也。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老子注》57章)
企图以政治或权威止息邪僻之事,反而会使“奇兵”起。所谓“奇”,即“奇巧”、“诡秘”、“奇邪”之意。“忌讳”即“禁忌”。多增禁忌,以期“止贫”①,而民更加“贫”。“弥”,即“更加”。以利器治国,则国越昏弱。“利器”,指治国之器,智慧权谋之类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因为舍本逐末,“在上者”没有“以无为本”,施行清静无为之道而导致的。由于“民从上”,在上者若以无欲无求要求自己,那么百姓自然回归于“朴”的状态。所以在上者应“以无为本”,施行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源自《老子》。先秦时期,道家极力反对“有为”,认为它造成人性异化、社会混乱,无为而治才是统治者应该追求的治理原则。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对万物主宰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对于万物来讲,道虽“无为”,但所达的效果却是使天地万物运行不息。老子把“无为”作为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道的特质,这为“无为”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老子反对儒家那套“仁义”的治国方式,认为只有“无为”才能国泰民安。而关于无为治国的主体,老子认为其常常与圣人有关。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侍。”(《老子》2章)老子认为,最好的治国理政的方法便是圣人的无为之治,而所谓的“以德治国”、“以智治国”都是“国之贼”。“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5章)人只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天地对人来讲无所谓仁爱,所以圣人也不应讲仁爱。如果热衷“有为”,推行仁义,是废弃了大道的表现。无为而治的价值在于,它使万物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而这一点为王弼所继承。
“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老子注》23章)“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注》58章)王弼认为,道(无)的本质是自然无为,所以体道之君要以无为本,“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也是本体“无”特质。居“无为”的治理,才能“物得其真”。“真”是指事物天然、本然的状态。“物得其真”就是万物能够在无为而治的情况下保持其自然的或本然的状态。
“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老子注》38章)礼制起源于朴实之忠信丧失之后。礼,也是“名教”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名教之治”所标榜的“仁义礼节”实际上是对社会系统自然已足状态的破坏。“贵博施”、“贵正直”、“贵饰敬”等有为之治相对于无为来讲,都是为政之下策。不能做到无为,所以讲仁爱;不能做到仁爱,便又开始讲礼节:整体表现为一种道德逐次沦丧的下降过程。仁义本身是发乎内的,如果刻意而为之,就不免流入虚伪。在王弼看来,“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老子注》38章)。重视仁义礼节,如同“弃母舍本”,必然会导致争端与混乱。
“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故曰其政察察也。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老子注》58章)“夫任智则人与之讼,任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未有能使人无用其智力于己者也,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路径,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注》49章)有为而治是一种明察之智。万物都要殊类分析,制定繁琐的法令,明确赏罚的标准,但却不能真正达到政清令明。智与力都是有限的,繁琐的法令和刑罚只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社会陷入混乱,如同鸟乱于上,鱼乱于下。即便是“圣智”这样的智中之极,也是不利于统治的,而且还会带来灾祸。而施行无为之道,“察司”等监督的行为减少了,百姓逃避的行为也随之自然减少,从而使国家避免陷入无限的纷争。
“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老子指略》)邪淫所生的根源不是邪淫乱者,而是善察、滋章、严刑、善听。所以,无为而治方可避免邪乱之生。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注》63章)以“无为”做为政之道,是“治之极”,呈现出“无形”、“无事”、“无名”、“无政可举”的状态而臻于大治。所谓大治,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种状态。“大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老子注》17章)
在老子的哲学中,“无为而治”与“有为”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王弼基本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王弼的“无为而治”又是将“无为”与“有为”进行了统一,这种统一就体现为其“因物自然”的思想。
二、因物自然
王弼的《老子注》有25处提到“因”。《说文解字》曰:“因,就也。从口、大。”段玉裁注:“‘就’下曰:就,高也。为高必因丘陵,为大必就基队。故因从口大,就其区域而扩充之也。”因此,“因”的本意有凭借之意。其次,因又有遵循、顺着之意。在王弼的哲学中,“因”的实质是自然无为。汤用彤认为:“因即顺自然,即无为而自化。”“帝王行事,无论善举或刑罚,皆非矫揉造作,而顺乎自然。顺自然即顺性。”[2]“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注》29章)圣人“因而不为”,则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不会被破坏,同时又保留了人类对事物规律认识、选择、学习的可能性。王弼认为,万物秩序井然地共存,并非由于人为有形的管制。“因而不为”在客观上营造了万物平等发展的环境,万物因此而不会失去本然的状态。
“因”在王弼的名教理论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因”的是《管子》。“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管子·心术上》)这里的“因”有因循、因顺、随顺之意,主要作为方法或原则使用。“天道因则大,化则细。”(《慎子·因循》)《吕氏春秋》明确将“因”视作为君之术。“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吕氏春秋·任数》)这里与老子“无为之道”所并列的“因”,被提到了方法论的层面,成为君主治国治民的一种方法。这里的“因”即无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无为。与老子的“堕肢体,黔聪明”的无为相比,“因”更具有主动性。
《淮南子·修务训》:“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功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燥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无为之本意是无声、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这样的“无为”完全是消极的,是无法真正达到“道”之境的。“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指人类的活动应该因循对象而施行一定程度上的有为。但是这种有为不是“妄为”,而是将老庄“无为”转变成“因客观事物的自然状况而为”。张岱年认为:“《淮南子》的无为论主张凡作为应遵循物的规律,依凭物的资质,随顺物之必然的、内在的趋向加以人功,能如此便是无为。不顾物之客观情势,只凭主观的欲望,而任意作为。乃是有为。”[3]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原道训》)“不可为也”是“无为”的另一种说法,“推”则具有“有为”的倾向。此处,“自然”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因”强调对客观事物本然状态的尊重。“因其自然而推之”,即主体可以因势利导,不伤害事物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统治者在治国时,要根据事物的本然情况而实施“有为”。通过这一原则的贯彻,“无为”在政治实践领域具有了实践性。
王弼的“因物自然”思想,调和了“无为”与“有为”之间的矛盾。“何因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势也。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唯势也,故能无物而不成。”(《老子注》51章物由“因”而形,“因”所根据的也是“莫不由乎道也”,其实这一切都是本体“无”的作用。从“因”的对象讲,物的自然本性是自足的。“因而不为”,这样才能“物自宾而处自安矣”(《老子注》10章)。
“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老子注》41章)“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楗、绳约,而不可开解也。”(《老子注》27章因循物的自然或者本来状态,不伤害物的自然本性。在王弼的哲学中,“自然”与“无”、“道”的概念是相通的。“王弼用‘自然’去描述世界的秩序,他把天覆盖万物,地负载万物,万物之相克制,都叫做自然。”[4]
“因物自然”之“自然”是指“自然之性”,即是在事物没有人为作用下的本然形态;“关楗”、“绳约”的引申意义均为治世的一种手段。“因物自然”就是因循、顺着事物的自然本性,不设不施,不通过形器制物,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万物以自然为性。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老子注》29章)“因物之性”就是因循个体的自然本性,每一个个体都有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属性。“夫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优。故续凫之足,何异于截鹤之胫。”(《老子注》20章)万物本性自足,强行干预、恣意妄为就会伤害事物的自然之性。鸟类会本能地进行交配,寒冷地区的人会本能地穿皮衣御寒,这些均为“自然之性”。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王弼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是他并没像老子那样极力反对有为,而是巧妙地通过吸收黄老之学“因”的思想,将“无为”与“有为”统一起来。而后,王弼又将“因物自然”化为“随物”与“导物”的结合。
“随物而成,不为一象,故若缺也。”(《老子注》45章)“随物”即顺应物本性,不为达到目的而伤害物的本性。“不为一象”即是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而非有意去造成某一物象,保证万物的多样性存在。换句话说,“随物”就是圣王“不劳明鉴”,依据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成就个体。但是,王弼并非一味地提倡“随物”,因为放纵未必就真正利于个体个性的发展。基于对个体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责任与义务,王弼提出“导物”的主张。
“以方导物,令去其邪。以方割物,所谓大方无隅。”“以直导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于物也。”(《老子注》58章)所谓“方”,即普遍的价值原则(名教)。“导”即引导、导向、因势利导之意。不是把万物导向相同的方向,而是根据个体的不同能力,创造一种至真至善的发展空间。从个体角度上讲,“导物”是“有为”的做法,即根据名教规范,将个体导向臻于完善的状态。这在程度上弱化了名教的施行者与名教的被教化者之间的矛盾。通过“随物”和“导物”结合的方式推行名教,达到“善成”,这才是“大制者”所具有的韬略。
汉代名教的“治世以威”压抑与制约个体的自然本性,“民不堪其威”,结果可能导致“天诛将至”。针对汉代名教“以名正物”的弊端,王弼提出了“因物自然”的思想,它是“无为”与“有为“、“随物”与“导物”的结合。它在保持个体自然本性的同时,又能达到治世的目的。
三、因道而立制
王弼的“因物自然”思想在治国策略上体现出“无为”与“有为”的张力,君主治国既要“无为而治”,也不能抛弃“有为”;在理想秩序的追求上,崇尚自然秩序,同时又认为尊卑有序的名教秩序也是必不可少的,需“因俗立制,以达其礼”。王弼的“以无为本”,其本体存在的意义就是“由天道以言人事”。他虽然崇尚自然,但实际上是为名教寻找出路。他认为,名教所蕴含的政治伦理秩序对社会的规范来说是必要的,“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周易注·鼎卦》)。
“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五教之母,不曒不昧,不恩不伤。虽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老子指略》)木、水、火、土、金,构成世界万物,须是以“无”为根基。所谓“五教”,即是指五伦之教②。王弼以“不炎不寒,不柔不刚”的方式形容作为五物之母的本体“无”,以“不曒不昧,不恩不伤”来形容五教。“欲言无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老子注》14章)其中,“不曒不昧”是对本体“无”的描述。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大制者,以天下心为心,故无割也。”(《老子注》28章)“百行”与“殊类”泛指事物与道德品行等的产生是“真散”的结果。王弼虽然提倡“无为而治”与清静虚无,但是也肯定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圣人因其分散,故谓之立官长。”(《老子》28章)君主的人格形态是“圣人”式的君主,而君主的人物形态永远是以“官长”的形式存在。
“万国所以宁,各以有君也。”(《周易注·乾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若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周易注·屯卦》)王弼崇尚自然的社会秩序,同时认为若一个社会庶民百姓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则必然会造成秩序混乱。所以,“万国咸宁”必须要有“君”的存在。“众不能治众”,而是“以寡治众”。在“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由刚柔始交所建立的君主统治是以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自愿服从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自然的君主统治[5]。
“雷雨之动,乃得满盈,皆刚柔始交之所谓。屯体不宁,故利建侯。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处造始之时,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周易注·屯卦》)“天地造始之时”即“刚柔相交之时”,是“朴散则为器”的结果。“利建侯”即是“圣人因其分散而立官长”。王弼认为,天地造始之时,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万物萌动,此时是建立人类秩序的大好时机,并肯定了君王存在的合理性。“阴爻皆先求于阳,不召自往”,若君主具有谦和的品德,合民所求,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戴,并自愿服从。作为君主,只有谦和的品格是不够的,还需要“安民在正”,“弘正在谦”,“以贵下贱”,“应民所求”。
对于国家来讲,只建立君主统治是不够的,还要创立制度、制定名分,把人们的生活及对物质的追求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安定人心,避免抗争流血。
“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注》32章)“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周易注·讼卦》)设立制度与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有序,防止争乱。因为“契之不明,名实不符,职不在位,定会引起争乱。“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而为制”(《周易注·节卦》)。
“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而为制,主节之义也。节之大者,莫若刚柔分,男女别也。为节过苦,则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则不可复正也。”(《周易注·节卦》)“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覆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周易略例·辨位》)王弼认为,关于制度与秩序的建设,既要刚柔分,也要男女别。所谓分别,就是确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要建立这种秩序就要有节制,要“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周易注·节卦》),这样适中的制度能为人民所接受。王弼将“节”又分为“甘节”和“苦节”。甘即完美,这种完美的制度既要有尊卑贵贱之分,又要适合百姓之生存。“苦节”将带来灾难,因为“为节过苦”,节制过于严格,超出合理的范围,便会损伤百姓的自然之性。
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家族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是封建社会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儒家‘家国同构’的理念,家族中既讲尊卑等级,又讲交相爱乐的父子关系,扩展到国家就是君仁臣忠的政治伦常关系。”[6]“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王弼承袭了儒家重视“齐家”的传统,并对家族制度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天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注·家人》)家道正,则天下之道正。社会是由家构成,家族秩序是社会秩序的缩影。家族内部成员上下有等,尊卑有序,六亲和睦,交相爱乐,家族才会祥和。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这一点,王弼没有像老子那样反对树立尊卑秩序,而是重视家庭伦理,主张树立家长的权威。“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也。”(《周易注·家人》)王弼认为,家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是不能颠倒的,若是“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周易注·家人》)。
王弼“因道立教”的思想强调了在“以无为本”的自然秩序下君主、制度、秩序的必要性。其中,“无为”、“因物”是“大治”,对百姓也可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
四、则天成化
王弼的“无为而治”和“因物自然”还彰显了“教化”的作用。教化者不但要“因物自然”,而且还有则天而成化,最后达到“止物以文明”。王弼将“天之文”与“人之文”对比,得出“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的结论。
“刚柔不分,文何由生?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注·贲》)“刚柔”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指“刚强”与“柔弱”,如“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78章)。在《易传》中,“刚柔”与德性、分位、尊卑相连使用时也有“刚健”与“柔顺”、“刚尊”与“柔卑”等等含义。刚柔也指相互作用的两种力量,它们之间相互配合、相待相济。刚性与柔性两种力量相互交错而形成天文。天文是指天地自然运转所呈现出的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观天之文而知时变”,即“观察日月星辰等弄清时令的变化”。“止”通假为“治”,治理万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孔颖达对此解释为:“‘文明’,离也。”离卦的本义是太阳或日月附丽于天,与“文”“明”义通。可以将文明引申为人道原则。从“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可以看出,王弼明确反对暴力(威武)原则。程《传》:“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人文就是人伦秩序。王弼认为,人伦秩序是教化可以达到的。
“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周易注·习坎》)王弼认为,因为个体在自然的方面虽然“自然已足”,但在社会方面还有教化的空间。“本虽美,更可薉也”(《老子注》24章),“薉”的本义是荒芜,引申为恶义。不同于董仲舒的以“教”为主的“教化”思想,王弼的“教化”侧重“则天”,“德博而化”,“化成天下”。
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论语释疑》)“言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老子注》9章)“圣行五教,不言为化。”(《老子指略》)“言谁知善治之极乎!唯无可正举,无可形名,闷闷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极也。”(《老子注》58章)“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老子注》4章)前3条引文中,“化”均为“教化”。关键是王弼强调“则天”。观“天之文”而知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此处的自然规律又可以理解为“二仪之道”。“二仪之道”,就是天地之道。天地所法之道是自然,即自然之道。王弼认为,“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所谓“则天”、“因物自然”、“无为而治”,都是重视万物的天性的表现。化“人之文”为自然,即化当然为自然。“即是将普遍的道德规范或原则内化于主体,使之与主体的深层意识融合为一,从而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自然)。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便可以达到行不失时的境界。所谓德应于天,便是指遵循当然与合乎自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以德性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为前提。”[7]“天”,指万物之天性或自然本性。圣王依据个体的自然本性进行个别教化,不以既定的框架去控制与戕害个体。这种圣王之道就是“自然”的精神境界的呈现。在上者行“自然”之道,在下之臣民就会观察到圣王的作风而受到感化。王弼在《观卦》的注释中说道:“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已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则百姓自服也。”若统治者不设立刑罚,而以自然的境界对百姓教化,那么天下臣民没有不诚服的。这种自然之道是无形无象的,能够在百姓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就如同时间流转,四季更迭,谁能看见是自然之道使之发生?
注释:
①《老子》通用本:“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郭店楚简本《老子》:“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叛)”。陈鼓应认为,此句话郭店楚简本《老子》优于各本。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彭浩说:“‘畔’借作‘叛’,这两句意为:人主的禁忌越多,而人民多背叛。”参见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
②《左传·文公十七年》:“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孟子·滕文公》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增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17.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0.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78.
[4]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29.
[5]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193.
[6]朱汉民.王弼易理易学[J].中山大学学报,2009(4).
[7]杨国荣.善的历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7.
(编辑:王苑岭)
B235.2
A
1673-1999(2016)10-0007-05
张盈盈(1985—),女,博士,安徽社科院(安徽合肥230051)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
2016-08-25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