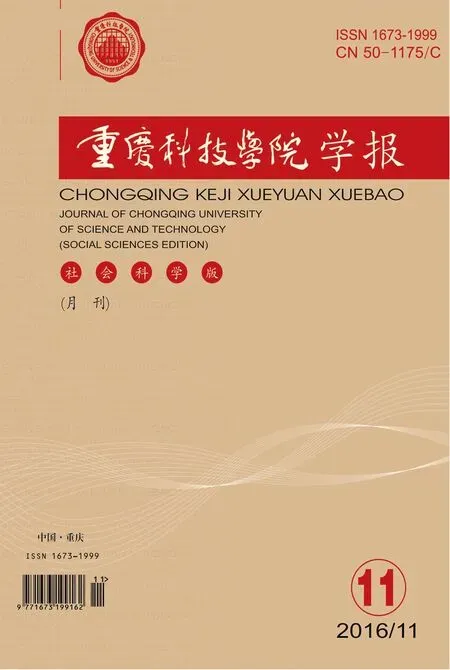在美与悲之间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訾西乐
在美与悲之间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訾西乐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美丽而梦幻,浪漫而神圣,充满永恒的魅力。颇具原始风味的湘西风俗呈现了巫楚文化的独特面貌,湘西乡民在生活中表现了优美的人生风貌;但在美的背后却充斥着悲的色彩,血腥与杀戮,脆弱与隐痛,渗透着悲悯的情怀。面对民族的愚昧与狂妄,沈从文以强烈的悲怆与孤独之感,在小说创作中把人性的美与悲表达得淋漓尽致。
沈从文小说;湘西世界;美与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有秀丽的山水风景,又有古朴简洁的民风,还有单纯善良的人们。但与美并存的却是悲。湘西世界中血腥、杀戮的场面也常常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只是他善于用一种平静、波澜不惊的笔调,将充满悲怆与隐痛的情境,以悲悯的情怀展现在作品中。正是这种自然而然的书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愫,形成了湘西世界中耐人寻味的美与悲。
一、湘西世界原始自然的美
杨义先生曾指出,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不该忘记他所展示的带有化外之风的湘西世界。他用抒情诗一般浏亮的笔致,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民风古朴,山川灵秀,保存着某种原始清新感和神秘感的内地乡土的人文景观”[1]。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描绘了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来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时刻被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和倾心,这都蕴含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风景之美、神巫之美和人性之美当中。
(一)如诗如画的风景之美
沈从文从小就对自然产生了浓厚的热爱之情,小时候的他屡屡逃离课堂,就是为了享受大自然所带给自己的快乐与自由。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自然山水浓墨重彩的描绘,在这种美丽的风景和自在的氛围下,促成了沈从文热烈奔放、富于幻想的性格特征。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自然美景和淳朴乡风民俗的熏陶,培养出沈从文对诗情画意特别敏感的特质。
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都对湘西世界的美丽风景进行了描绘,一幅幅绝妙的湘西画卷展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在《边城》中,沈从文对边陲小镇的山水这样描写道:“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对于湘西的民居,沈从文说:“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自然与人文恰到好处的结合,使得“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当翠翠有心事时,沈从文也是借助景物的描写来衬托人物内心的波动,“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而对周围景物的观察,更显示沈从文笔下的景与情的密切结合,“出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
在《月下小景》中,沈从文也对湘西的美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在成熟的季节,湘西世界“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泥土气味。一切光景具有一种节日的欢乐情调。”碉堡在月光的衬托下,也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美,“柔软的白白月光,给位置在山头上石头碉堡画出一个明明朗朗的轮廓,碉堡影子横卧在斜坡间,如同一个巨人的影子。”“山坡上开遍了各样草花,各处是小小蝴蝶,似乎向每一朵花皆悄悄嘱咐了一句话。向山坡下望去,入目远近都异常恬静美丽。”这种恬静和美好正是湘西的真实写照。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的一切风景都是美的,湘西世界也更像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带给人美的享受。真真切切的美都是沈从文对家乡的记忆与眷恋,因此,他会在作品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真诚而和谐,纯净而动人。
(二)梦幻浪漫的神巫之美
沈从文是少数民族,他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少数民族的风俗。因此,沈从文把创作的笔触伸到了生他养他的苗族居住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关于神的描写,如《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在这些小说中,沈从文把神巫之恋书写得充满奇幻色彩,也把湘西风俗展示得淋漓尽致。
作品中的主人公如神巫、龙朱、豹子等都是苗族人的骄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美男子。对于神巫而言,“他知道自己的风仪是使所有的女人倾倒,他不愿意把自己身心给某一女人,意思就是想使所有世间好女人都有对他长远倾心的机会。”而神巫遇到的居民,也同样美丽婀娜,“花帕族的女人,正仿佛是为全世界上好男子的倾心而生长得出名美丽的,下品的下品至少还有一双大眼睛与长眉毛。”这种描写既充满浪漫色彩,也带给人美的想象。
龙朱的美丽更是有着神来之笔的描写:“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他不但人美,而且“德行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龙朱才貌兼备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面对很多女人望而却步的情况,龙朱听从自己的内心,追求向往的爱情与美好。当他终于寻找到心仪的对象时,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
豹子是一个“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一个男子”,媚金“是一个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两个人因唱歌成了一对。虽然结局是悲剧,但豹子和媚金对感情所表现出来的热烈和真诚带给人感动。《月下小景》中的寨主儿子傩佑和小女孩的爱情,也同样感人至深,按照“本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这种带有少数民族气息的风俗,让两个人为爱而自杀,结局凄美动人。
沈从文笔下的这类小说是一幅幅湘西民俗风景画,是一曲曲苗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赞歌。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完整地反映了湘西苗族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习俗,如恋爱时对唱山歌,对歌成功后洞中幽会,“用白羊换媚金的贞女的红血”的习俗,以及苗族人崇巫信神等,生动地再现了苗族文化,尤其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独特风貌。沈从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了湘西的乡村生活方式,展现了湘西苗族人的灵魂,因此作品是值得回味的。
(三)善良朴素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2]沈从文的创作之所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是真实地描写了湘西的乡村,反映了湘西乡民的生活和性格特点,充分体现了湘西世界的独特风采和人性之美。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着善良的灵魂和朴素的品格。无论是摆渡的老船夫,还是掌码头的船总,都拥有美好的人性。老船夫虽然很穷,但送人渡河却从不收钱,即使勉强收了钱,也要把钱拿去买茶叶和草烟来招待坐船的人。掌管码头的顺顺,是一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喜欢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明事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
《边城》里的翠翠是一个清如山泉、纯如雪莲的少女,“翠翠在风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么乖,从不发怒,从不动气”。在她的身上,继承了爷爷老船夫的优秀品格:善良、勤劳、真诚、淳朴,体现了一个山乡少女的灵动与欢乐,如同山中流出的丝丝清泉,透明、纯净、香甜、清冽。
翠翠的爱情也如明月般皎洁、纯粹,“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在等待着、期盼着,这感情中有倔强、有执着、有坚毅,在时间的长河中,隐藏着一颗为爱而时刻跳动的少女的心。沈从文通过描写湘西少女一段缠绵悱恻而又跌宕起伏的爱情,吟唱了一首遥远而又古老的山乡牧歌,这充满了爱的温暖与恨的凄凉的往事回忆,传达出湘西青春少女对爱情的忠贞与坚守。这种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但又不泯灭的精神内涵,正是沈从文所要表达的对湘西山民的生命力的赞歌。
《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也都具有美好的人性,她们活泼、天真、可爱、机智,具有真的性情、善的美德和美的情操,这种性格构成了湘西小镇的和平、宁静,使得山乡到处笼罩着关爱和友好的氛围。从沈从文描写的湘西世界中可以看出,湘西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总是站在湘西“乡下人”的角度进行创作,歌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美好人性,赞美那里的风俗习惯。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湘西人的血液,他的创作情思始终萦绕着湘西这片热土[3],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也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二、湘西世界孤独隐痛的悲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的序言中曾为他的作品“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寻找出两条理由:一条是他自身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另一条是他的作品都是他“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4]。因此,在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也存在着血腥杀戮的民族冲突,刀光剑影的政治革命,它也有生活的种种艰辛和生存的苦难与无奈。但沈从文在描写这些悲剧时,善于用一种平和的口吻来表现,从而使得这种悲具有孤独隐痛的色彩。
(一)身份认同的民族之悲
湘西土著民族作为一个与外界生活习俗迥然不同的存在,不免有些落寞与孤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这个民族有着无法言说的凄凉。正如有的评论所说:“作者在提笔时,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又很痛苦。他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用秀丽的文字表现了一个民族发自内心深处的沉忧隐痛。长歌当哭,而愈显其悲,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5]
湘西地区的偏远、落后,导致了人们的愚昧与残酷。沈从文在行军时就目睹了血淋淋的现实:“有一次当我们从两个长满小竹的山谷狭径中通过时,啪的一声枪响,我们便倒下了一个。第二天路程中我们部队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
沈从文用一种平淡,甚至冷漠的语调来叙述当时的经历,细细品读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可以发现,反讽的意味充斥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漫不经心的描写并不能掩饰愤懑的情绪,这正是沈从文发自内心的悲凉与绝望,是对无辜牺牲者深沉的哀叹,是对民族野蛮方式的强烈指责,也是对民族悲剧最深层次的同情和无奈。沈从文在流露出深深的民族孤独感之后,也表达了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隐痛。
《边城》中的翠翠,性格敏感、脆弱、内向,这正是湘西少数民族孤独感的深切表达;《龙朱》《月下小景》中所描写的传奇故事,包含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沈从文以张扬的书写方式,弘扬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神巫之恋》中对神的爱慕与崇拜,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表达了对民族的认同感。沈从文正是通过描写湘西少数民族自然蓬勃的生命状态,以朴素真实的情感来体现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沈从文在小说《凤子》中塑造了一个精灵般的凤子,她是“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组织的化身”,是真、善、美的结晶,即湘西之魂。她既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实体,又是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既具有无处不在的魔力,却又只可远观而不可企及。通过对凤子意象的描写,沈从文以其独有的文化心理气质,通过对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深刻思考与理解,力图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
(二)隐痛存在的命运之悲
小说《新与旧》通过描写刽子手杨金标在两个不同时期的遭遇,对比了政治变革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状态,展现了历史的变迁、礼崩乐坏的现实。光绪年间的战兵杨金标,在执行杀人任务后,需要跑到城隍庙表演请罪的戏,县太爷下令重责40红棍,再给杨金标赏银。这是法律同宗教仪式的结合,“杀人仪式”具有抚慰精神的作用,同时告诫百姓,即使执行了官府的命令而杀人,也要受到惩罚。
然而在民国年间,军人的装备中已有手枪,不再需要砍头这种粗暴的方式。因此,当老兵杨金标奉命杀死无辜的革命者后,再次跑进城隍庙,试图表演谢罪的戏剧时,却被人们当作疯子痛打而最终死亡。杨金标的结局映衬出民众精神的失落,在没有精神寄托的恍惚中,在新与旧的对比中,从时代的变化看出历史的倒退。精神信仰的消失,给民众的生存带来了压力,革命的血腥、恐怖,显示出沈从文对暴力革命的深刻批判,表达了他对湘西现实世界中人们命运的思考。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忧虑地写道:“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氛,这样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轻人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6]由此可见,沈从文在描写湘西世界常与变的矛盾,当他感受到湘西世界受到现代文明挤压后,这种变化使得湘西人朴素、自然的品格逐渐消失,难以保存,他表现出焦灼的情绪。在过去与现代的对比中,沈从文对湘西世界蕴含着复杂的情感,这种思考把他的创作带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呼唤自然人性的复苏,然而,他也痛苦地认识到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必然会吞没这种自然人性,体现出沈从文对湘西前途命运的担忧与隐痛。
(三)脆弱无奈的人生之悲
湘西偏僻、闭塞的生存环境,承载着风景的优美与历史的厚重。湘西的土著居民过着如画般平静的生活,而在这种平静生活的背后,所有人都被网入了人生命运的大网中,不可避免地上演着一幕幕悲剧。这种悲剧是无奈的,沈从文在平淡的描写中流露出了幽远的情绪。
湘西原生态的生活造成了萧萧懵懂的性格,当她嫁给一个婴孩做童养媳时,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未想过逃离,甚至在她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反抗”这个词。湘西特有的伦理熏陶,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沈从文对萧萧的描摹,实际上是一种平静而又浸透伤感的倾诉,再现了童养媳的人生悲剧,这种制度无情地吞噬着少女的青春和幸福、爱情和生命。在小说结尾,萧萧的人生悲剧仍然被沿袭着,又一个“萧萧”重复着她走过的路。
短篇小说《菜园》是一部人生悲剧,作品无论是写儿子、媳妇的永远离开,还是写母亲最终的自缢身亡,都是轻言细语。沈从文在描绘出优美的田园风光时,赞美了真挚纯情的母爱,但在小说平淡的语言背后,渗透着无法释怀的悲哀,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隐隐悲痛。在宁静淡远的描写中,既折射出悲剧的深沉,又表达出生命的无常,感叹人事与命运的不可捉摸。
沈从文在小说中多次渲染了白色的意象,白色既是母亲精神世界的隐喻,又是美好品德的象征。母亲面对儿子、媳妇的离去,依然坚强地活了下来,这是生命的庄严所在。当玉家菜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玉家花园时,母亲的精神寄托也已消失。母亲选择在天降大雪,儿子生日之时自杀,留下的是一片洁白。这是沈从文对现实的批判,当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中难以存在时,也预示着湘西世界不得不变,湘西是怀乡的梦,梦终究会因为人生悲剧的存在而破碎。
三、结语
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理想世界,“湘西”所代表的人性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他的创作所负载的内容。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前途命运的思考,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贯穿在作品中,在美与悲之间,这种结合使沈从文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张力,从而使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特质,也使他的作品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1]杨义.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7(2).
[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3.
[3]邓立平.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J].今日科苑,2007(4).
[4]王继忠.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5]朱光潜,张兆和,等.我所认识的沈从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65.
[6]索晓海.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精神和社会生态状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
(编辑:文汝)
I207.42
A
1673-1999(2016)11-0073-04
訾西乐(1991-),女,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6-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