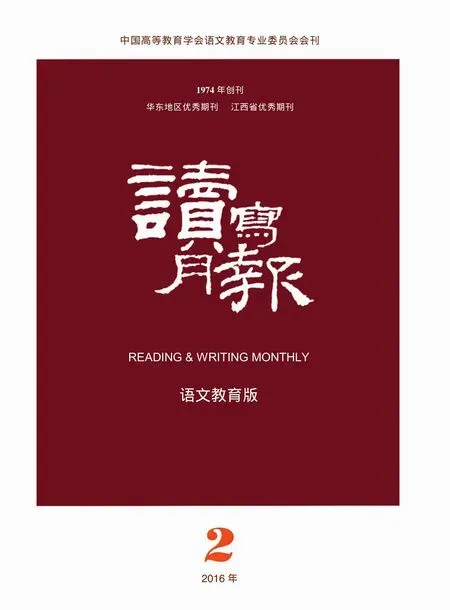“鞭策”教育中的人文之光
——从电影《爆裂鼓手》说起
杨诗卉
“鞭策”教育中的人文之光
——从电影《爆裂鼓手》说起
杨诗卉
电影《爆裂鼓手》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鞭策”及人文教育的相关思考。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已经出现自由泛滥的倾向,这无疑不利于人文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培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人文教育应渗透到大学教育中去,帮助学生丰富内在自我、建立健全理智和德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走向美好与光明。
《爆裂鼓手》;教育电影;教育反思;人文教育;自由
2014年一部名为《爆裂鼓手》的电影屡获世界众多电影奖项的提名,这是一部以音乐教育为主题的电影,被无数人冠上了“反励志片”的头衔。电影公映后,在收获众多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质疑、批评的声音出现,其大多是指向影片中乐团导师弗莱彻的教育方式。在众人心中,电影里的“教育”应该是像《音乐之声》那样,师生自然而然地共同达到生命的和谐与愉悦,亦或是应像《死亡诗社》那样,教师担负起救赎青年灵魂的责任。可是这部 《爆裂鼓手》——英文名为《Whiplash》(鞭策)的电影,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一、鞭策——“教育温情”的别样表达
影片中,早在男主角安德鲁参加第一次训练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导师弗莱彻对音乐近乎变态的挑剔,他那过于激进的教育理念在大部分人眼里都过于“残忍”,因为弗莱彻教学过程中所贯彻的是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理念,认为倘若学生因责罚而自暴自弃,那么他们注定无法成为强者。这一份苛责,其实是源自于弗莱彻内心深处“对于音乐的最真诚的爱以及最理想化的热情”[1],所以他要求学生演奏的音乐必须是不断趋于完美的,这正是出于对音乐所怀抱的一种最严肃、最尊敬的态度。
弗莱彻的耳朵里容不得任何音调的跑偏与节奏的拖拉,若有人不幸犯错,他会给你一个纠正的机会,但是若仍无法更正,那么你将面对弗莱彻那势不可挡的怒火。弗莱彻的怒火已经不仅仅是让你的自尊心受挫这么简单了,它如同地狱之火突然喷发而几乎让你的每个毛孔都惊悚地张开,那些极具侮辱性的、带刺的言语毫无防备地刺进你的毛孔乃至骨髓,让你抬不起头来。许多学生因此信心全无,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不少人正是从以上的这一角度来批评弗莱彻的严苛,因为这导致本该让人轻松、享受的音乐变成了一场残酷的角斗。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音乐,但总有少数人是要“创造”音乐的。对于只把音乐当作兴趣爱好的人来说,他们当然可以愉快地去学习,不必对自己太过严格。可是对于那些试图在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其中显然不仅只有“愉快的享乐”。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世界,但是人本身的天赋以及后天的努力都在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站在金字塔顶端被人敬仰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付出了多出于常人千百倍的努力。
男主角安德鲁属于“极少数”的阵营。他曾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上说,与其活到90岁红光满面但是死后很快就被忘记,他更宁愿像查理·帕克那样,即使33岁就丧生但是却因为在爵士乐方面的杰出表现而能够被世人铭记。对于有如此抱负的安德鲁来说,遇到同样有野心,想要培养一个伟大的爵士乐手的导师弗莱彻,是一件幸事。安德鲁在遇到弗莱彻之前,他的意志力并不强大,可能终其一生也找不到一个突破口冲破自己的极限。弗莱彻之于安德鲁,与其说是一个“导师”,不如说正如电影的英文名 whiplash一样,他是一个“鞭策者”。在弗莱彻的鞭策下,安德鲁深切体会到了竞争的激烈以及不进则退的残酷准则。他吃住都在练习室,因长时间与高强度练习而使手被磨破、出血,而他只是放入冰块中冷敷一会,简单包扎,又继续练习。安德鲁在演出前出了车祸,躺在血泊中时,脑袋里也全是鼓点的声音,他从被撞翻的车子里爬出来,依然去参加演出。音乐之于安德鲁绝不是茶余饭后陶冶情操的玩物,而是他整个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或许有观众会为安德鲁感到痛惜,认为安德鲁是弗莱彻强势教育下扭曲的产物。但是我们显然更应该将之理解为,这是一个人倾尽全力、渴望做到杰出时“自觉”的选择与努力,只有这样的“内因”与“内驱”才可能如此持久而坚韧。同时,安德鲁要实现这一异于常人的生命意义,也确实离不开弗莱彻的鞭策。安德鲁与弗莱彻之间已经形成了很深的羁绊。弗莱彻对安德鲁愈严厉苛刻,安德鲁便愈想做得更好,这是一场剑拔弩张的博弈与较量。弗莱彻不断以各种残酷的方法激发安德鲁的潜能,推动安德鲁不断向极致与完美靠近。这样的关系类似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与魔鬼。表面上看,似乎靡菲斯特在将浮士德导向罪恶,但实质上却也激发了浮士德的向善之力。同样,弗莱彻看似在用他极端的苛责使安德鲁走向毁灭,实质上却是让安德鲁的意志在这场博弈中变得坚强,将自己练就得更为完美。
然而,当《爆裂鼓手》这部电影出现在众人视野中,导师弗莱彻却被当作教育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因为他似乎离人文教育所要求的宗旨相去甚远。可是,正如弗莱彻自己所说,他所做的,绝不只是挥挥棍棒这么简单,而是要不断地使他的学生们冲破自己的极限,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弗莱彻也的确看透了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胆怯、窘迫的打鼓少年内心的渴望,它就像一簇微暗的火,被深藏在心底隐隐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光。这样的火光,很可能就在少年成年不久后渐渐熄灭,他变成一个简单的上班族,打鼓成了一项业余爱好,甚至可能再也拿不起鼓槌,曾经的梦想只化为一个可以跟儿孙回忆的谈资。但是弗莱彻却发现了这只火苗,并且使它愈燃愈烈。难道这不是比让学生“快乐地学习”更难的事吗?此外,整部电影的基调也抛弃了传统教育电影中饱含的温情,其中的教育理念近乎残酷。弗莱彻几乎很少赞扬学生,他认为,最害人的一句话是:“嗯,还不错。”这让人不得不反思,在近些年以来,老师们一直在贯彻的“温暖教学”、“鼓励教学”的教育理念是否真的是培养一个学生所必需的?每一句违心的“鼓励”,除了让当事人好受一些外,起不了任何作用,它既不会让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更不会使人有所长进,反而是那些虽然刺耳却中肯、在理的批评,能让人在面红耳赤之后,自省、进步、成长。正如维柯所言:“如果你意识到在某些地方,他受了骗,出了错或偏离了正道,不要让他继续错下去,而要尽可能地细心选择该说的话,针对他的毛病给予忠告。雅典的公民会用公共诅咒贬斥那些误导迷路的人,他们会控告他违反了人的社会的自然。”[2]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导师弗莱彻那过于严苛的教学实际上正是一种别样的“教育温情”。
二、人文教育——培养独立自由之人
虽然《爆裂鼓手》中的教育理念有其新颖独到之处,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成为当下人文教育改革中的楷模,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存在。弗莱彻虽能够鞭策出一个音乐奇才,但是安德鲁却在一次比一次激烈的较量中,不断失去自我,用影片导演的话说:“安德鲁最后的成功虽然让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以喜剧收尾,但其实安德鲁内心最纯真的东西已经死掉,这其实是一个人的悲剧。”[3]因此,在为《爆裂鼓手》中的音乐导师弗莱彻“平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反思,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像安德鲁这样的个人悲剧发生的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2012年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可见,在物质主义、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大学教育也未能逃过此劫。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教师的教导与影响下,现行的教育或许能够培养出人才和精英,但他们同样有可能像《爆裂鼓手》导演口中的安德鲁那样,内心某一块最纯粹的东西已经丧失了。换句话说,他们或许深谙这个社会“适者生存”的规则,并且还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一切,使自己站在这个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但是,你却不能够说他们的生命是丰盈的。况且“大学应指示社会发展方向”[4],只有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大学才能够向社会输入更多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主体。可以说,我们能从一代大学生身上,看到一个社会的雏形。
所以又需要回到“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教育首先所要培养的应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的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尤其是在传播媒介发展迅速,信息碎片化严重的当下,保持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思想客观性与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当代大学生却普遍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的能力,他们要么无法或者不敢言说与主流思想不同的话语,习惯了沉默,要么拥有从众心理,人云亦云。这无疑与教育体系中让受教育者不够自由的思想环境有关。但是在当下,人人又都在伸张自我,似乎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就是人的终极幸福。不过我们也都看到,在拥有普遍自由的大学中,催生出的只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格局。那是一种极端的、盲目的自由,甚至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为所欲为。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责备一些大学老师过分严苛,而那些对学生过于放纵的老师们却极少受到指摘——当学生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吃早餐、玩手机甚至睡觉时,讲台上的老师并不以为然,于是这些大学生们变本加厉,情况愈演愈烈。这虽是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低下与德性的缺陷,但这个缺口却在一些大学教师的放纵下愈来愈大。虽然人理应具备基本的道德观来对自身进行约束,但是道德如水般无形,它也需要制度的规约,需要一个指路人,一个鞭策者,尤其对处于成长期尚未定型的大学生而言。这也是由于当下教育的两个极端造成的——我们的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往往太过狭隘,其教育的目的在于考试分数的提高,而禁锢了学生的思想与自由。到了高等教育,大学环境却又太过散漫,让这些刚刚挣脱“牢笼”的学子更加没有了方向,逐渐怠惰,从而走向平庸。因此,当下大学环境中的“自由”并不有利于培养具有“自由之思想”的人。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5]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决定他的现实的自由”[6],而精神世界的开阔与个体的经历、见闻、学识都息息相关,个体经验的局限性需要通过接受教育加以改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孤陋寡闻的、闭目塞听的人,不可能真正实现个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所谓的‘自由选择’其意义是大打折扣的。”[7]因此,我们需要在大学中进行实实在在的人文教育,引导学生丰富他们的内在,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之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
归根结底,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他们的个人理智逐渐走向健全的理智,而这需要自制和德行的根基。因此,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对大学生进行规约,鞭策他们不断向完美德行靠近。笔者认为,这需要更为深入地普及人文教育。我们社会的功利性对教育的毒害日益加重,人们普遍更为重视有实际用途的科学、技术教育,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科学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社会带来显著的进步,可是,倘若人性本身没有得到完善,人的理智和德行的健全进度远远滞后于社会进步的话,这将会在未来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性。反之,“当人们能正确地思想,当他们的思想撞击出火花的时候,就是感到幸福之时。”[8]这也是人文教育的目标所在。
当下普遍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得大学教育成为了一堵用书本知识垒砌的高墙,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文精神、理性精神的阳光照进生命的缺口,围困在高墙里的学生像井底之蛙一般,以为自己所见就是全部真理,鲜有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契机,甚至缺失那样的能力,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蜂拥而至的碎片化的信息面前无法进行有益的思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并逐渐成为碎片化的产物。我们的教育应该更加 “重视与追寻生命的完整性存在”[9],也许在诸多大学教育“改革者”的鞭策下,终有一天,能将那高墙砸出一道裂缝,让人文的曙光照向每一位受教育者。
注释:
[1][3]MattFagerholm.RiseOfAStar,DeathOfA Soul:DamienChazelleOn “Whiplash”,Interviews, 2014-10-13.
[2][意]维柯:《论人文教育》,王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77页。
[4]杜维明:《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解放日报》,2010年8月15日,第8版。
[5][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利: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 314页。
[6][7]马凤岐:《自由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第34页。
[8][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9页。
[9]詹艾斌:《寻求和确立生命与教育的必要方向》,《教育科学研究》,2014第3期,第80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曾诚
——纪念《表面工程与再制造》杂志创刊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