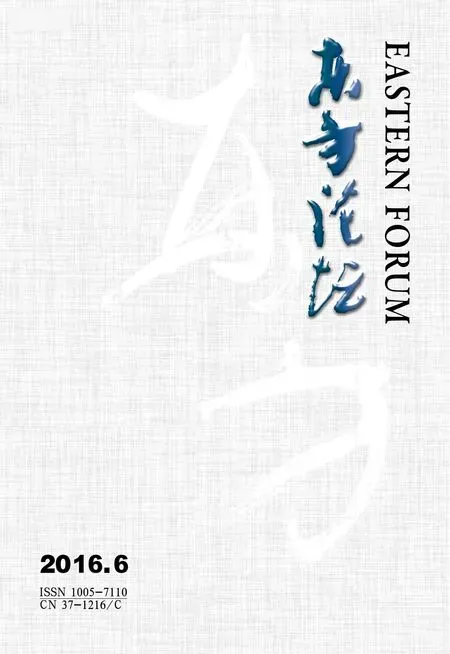为何传统?何为传统?
——当前语境下重审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及其概念辨析
闫 晓 昀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为何传统?何为传统?
——当前语境下重审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及其概念辨析
闫 晓 昀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下,重新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契机已经成熟。无论从现代文化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五四”以来“盲目西化”的不尽人意还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重审传统文化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然而,回溯传统并不意味抱守残缺,而是在现代视野中重新理解“传统”的内涵,使优化和升华后的“现代民族传统文化”能为现代民族文学建设和文化复兴提供保障与指导。
民族;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传统;现代
自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随军事入侵渗透至中国起,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自足状态也随之终结,基于传统农业文明构建的中国文化以此为原点,走上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西化之路。概括而言,西方文化主导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段,即反帝反封建时期(包含“五四”和与之相应的民主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当前的全球化时期。每一次思想风暴,均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们也无法否认西方价值理念对于中国文明进程的推动。然而,如同“四夷”的存在曾经激起家国民族对于边界和本土思想文化的保护意识一般,当前的“全球化”语境对于民族文化个性的消磨同样激发了类似的焦虑,必须承认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渗透已经使民族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文化失根的可能性促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迫切地需要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保持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个体价值,“文化身份”确认因此成为沟通文化与文学并实现上述诉求的迫切需求,对文学领域而言,这也是实现本国优秀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得以芬芳绽放的基础保障。“文化身份”最初是一个来自于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从整体文化生态来看,文化身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迫切话题,即使一直在强力输出价值观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为其模糊势态而焦虑。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要防止民族传统及其文化精粹淹没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已经逐渐走入关注视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中青年作家即曾表达过重审民族文化传统的愿望并积极实践,指出文化决定人类和文学,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而当下,无论在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对民族文化质素的强调中,还是在学界对于传统的重新解读里,都暗含着以优质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的潜台词,以期寻找中华文明得以生存、延续与发扬的文化优根,发掘其所内含的积极力量和优秀组成,并以之为依托促进民族文化与精神品格的再生。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由民族文化认同所表征的“个性”与“优根性”,已经代替先前对于“共性”的盲求和对于“劣根性”的批判,成为本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并获得掌声的根本方法,在当前家国民族同心追逐“中国梦”的宏大诉求中,重新估定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亦是“梦圆”的必经之途,毕竟,中国之“梦”萌发并生长于“中国”这一核心理念之中。
可见,无论从外部语境还是内部诉求来看,重审民族传统文化均势在必行。除去当前“文化形势”这一“导火线”之外,此一“势在必行”还有其独特的原因与价值,本文即以此为据,力求详尽阐释当前文化语境下重审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及方法,并试图探求理解“传统”的方法。
一
从现代文化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看,重审传统文化有其“根深蒂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现代进程中的文化实践似乎已经证实,越是在文化身份模糊的融合时代,对文化之根的寻求越为自发与迫切。本文开篇处曾提到现代化过程中的三次西方文化浪潮,每一次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均在文化焦虑下产生了“寻根”热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浪潮)虽以对传统的抗拒打开了现代思维,然而仍有一脉坚持向民族传统致敬,并试图从中寻找重建民族品格的方法。虽然如何更有效地实现中华文明进化,是激烈的思想革命还是温和的自我升华仍是未解的题目,但此一脉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恪守,在当前无疑具有不逊于现代思想革命的价值。这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式回归从未停止,及至政治解冻后的“寻根文学”时期(第二次浪潮),对文化之根的寻求已成为作家更为自觉的行为,其影响也远不限于对政治文学的反抗,而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第三次浪潮),对传统的回归已经不单纯是文学领域的一个侧面,更是上升为社会整体的显性诉求,以确保民族文化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形象繁荣于世界舞台。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每当思想与文化走向更为开放的新境遇,我们总会回转身形,向传统中寻找支持,且思想环境越自由越开放,对传统的回望越频繁,异质文化越强势,对传统的眷恋越热切。这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问题:其一,依恋传统是人类的精神本能,即使最为严苛的思想控制,也难以真正消解传统之恋;其二,对“国别文化”而言,一种可称作“民族文化主义”的观念深存在国民文化心理的深层,正是它保证了传统不死。因此,在现代文化主体观念中,传统文化常常以一个复杂的双重形象存在:在意识的表层,它是罪魁祸首、食人恶魔与人性刽子手,必须以彻底的“反传统主义”来祛除,然而在意识的深层,它却是值得依恋甚至令人同情的。所以,虽在现代之初,身负危机意识的现代知识者们曾试图以“全盘西化”的理想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痼疾,然而,因这一文化上的偏激态度从本质来看未能遵循文化主体的深层心理,而在具体实践中频遇曲折反复,主体们也从未真正终止对传统的回望。假如跳出时空限制,站在当下角度来看,也许这才是现代主体真正的内在诉求。在传统文化结构急遽解体的二十世纪初期,尽管这一诉求被遮蔽,但也并未在异质文化压倒性优势的威胁下消失。曾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胡适,甚至在晚年成为一个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主张重审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这些也许可视作对该论点最为直接的例子。传统文化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国民思想和其文化产品中,几千年来已深入民族精神血脉深处,成为创作主体的精神内殿,自觉地引导着主体在遭遇文化侵袭的时刻捍卫着它的尊严与地位。如果我们在传统中收获了文化优越性与归属感,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重审传统是“保守”甚至“倒退”的,更何况传统的根脉如此之庞大深厚,跨过如此久远坚固的民族文化传统接纳异质文化,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扬弃地继承传统文化,发扬其优秀之处,应当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席的环节,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更为自由开放的背景下,其意义更是不容忽视,倘若无视其意义,也无疑等同于从根源上否定了民族文化的存在价值,荒芜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使现代主体陷于文化上的流离失所之苦痛。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文化先锋们运用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配的理性和怀疑精神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P126),正是这种价值重估导致了思想的革命。新兴的现代知识分子尝试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在这场“除旧布新”的文化运动中遭遇全线溃败,从中心退向边缘。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的确存有阻碍文明进步的糟粕,然而,对传统文化的反抗自发生伊始即陷于过度激烈的极端境界。带着“全盘西化”的理想,批判者们对传统文化大多采取一概否定的方式,以致糟粕与精华一并舍弃,甚至走向了非理性的极端,从意识形态高度打击传统文化价值观,有意回避平实公允的讨论。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被无限放大,而其优质因素则被缩微成无关紧要的潜流。然而,“盲目西化”并未带来预想的结果,这也为今天重审传统文化的工作提供了反思的起点与外部机缘。过度批判消解了对话的可能,导致了“新文化”必定优于“旧文化”,且必将战胜“旧文化”的简单逻辑,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下,传统文化可谓完败,似乎其思想产物仅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礼教以及“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1](P268)。这一言论是否公允暂且不论,在此值得强调的是,即使这些看似必须“连根拔起”的中国所“独有的宝贝”,实际上并未被“全盘西化”的理想肃清,鲁迅笔下麻木的民众仍在当代改名换姓地存活,迷信与愚昧仍在当下的乡土中国中保持着残存的生命力,而国民性批判的话题在文学书写中从未中断。西方文化的救赎,显然并未取得预想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带来先进思想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忽视的负面干预。“现代”使乡土中国产生了“前”“后”之分,尽管不能否认其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但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精华是否已在“现代”的过程中蒙尘?自然、社会与人是否已在“工具理性”的裹挟下异化?这些“后现代”的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种种问题似乎提醒着我们,西方理念奠基下的现代文明同“我乡我土”至少存在不兼容成分。中国并未经历西方历史演进的过程,在文化源头上差异甚大,假若我们仅仅为一些理念所吸引而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便会自然而然地陷于“意义创造”的藩篱,将想象的意义投射到口号之上,依据偏颇的理解来解释名词并以此为据解决问题,这种解释常常与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思想没有多大关系,而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形式主义的谬误,使西方文明的精华难以为我所用[2](P21)。非思想性甚至盲目暴动的文化迷信向来是创造的障碍,何况从对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品格的原始追求来看,以彻底打倒中国传统的思路来迎接现代也并不合理,自由与民主的获得从来不是依靠一种思想对异己的镇压而实现。要使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必须使之得以消化,“汉化”为与中国实际相适配的思想范式,而实现其“汉化”,则需在“自我”的观照下接受“他者”,将西方理念内化于重建中的民族文化体系,盲目吸收有害无益,而“全盘西化”观念的形成正是未能把握这一根本原则的结果,由之而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也是此认知错误的产物。“全盘西化”的倡导者们将传统中国的各个组成要素视为“同质”之物,而这种“质”在其看来理所当然是陈腐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应当尽数舍弃的,因此,在其观念中,政经体制的落后即等同于文化体系的落后。事实上,经由漫长的历史沉淀而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这与“化合”式的西方文明秩序有所不同,其中内含着多种不同的成分与不同的发展倾向,这些成分与倾向有其独立的品格与生存空间,其中不乏先进思想与优秀文化。因此,全盘颠覆式的反传统思想运动看似示好“现代文明”,其本质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这一激进的反传统运动与潜存于民族记忆深层的“文化民族主义”冲突时,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内涵复杂的思想张力,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造成了“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2](P175),而查补这些文化偏颇所造成的“漏洞”还需从“前现代”中寻找“补丁”。毕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体系,其对现代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纠偏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偏激之处,传统文化势必将以其相异的价值取向进行强力修正,以防止中国现代文化陷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认知误区。总之,在借西方文化来反抗传统、实现现代的方略中,无论从西方文化自身还是从中国文化土壤的特异性来看均有障碍,而当我们发现颠覆传统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的时候,也是反思应当开始的时刻——我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借鉴是否是准确到位、得其精要的?我们是否真诚地将其作为思想与文化的指南针,而非仅仅借其来充当支持与辩解反传统运动的工具?我们所遗弃的传统是否毫无价值?而我们所热衷的西方文化,是否无所不能……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反思过程中总结究竟怎样的“现代”是我们需要的现代,怎样才能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使中国实现现代,而重审传统,正是这一反思工作应当迈出的第一步。
三
曾有学者指出,“思想史上可能有突然的飞跃,但是那常常是来自精英和天才的思想,一般的知识和思想却不会有突然的变异,它只是在缓缓地绵延……传统的残存是如此强烈的粘固剂,而历史的象征是如此坚固的石块砖头,要在一时就掀翻它是不那么容易的”[3](P78)。这一言论在如今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的崩塌而消失殆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支撑民族观念世界数千年的基本文化结构解体后,稳固可靠的文化新权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重建。因此尽管抱有美好的愿望,但文明的进化没有捷径,我们日渐察觉到,中国文化的前行之路从根本而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温和过程,而试图割裂文化传承而制造天翻地覆的突变只能造成思想范式的失序,中国现代历史上并不缺少与之相关的沉重事实,因此有学者才会无不感慨的结论道,“历史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得到好处,少有坏处。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是一部激进主义获得极大的成功却又变成极大的灾难的记录”[2](P561)——我们从未否认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历史带来的巨大意义,然而以决裂的方式追求现代的到来,忽视了文化规律的制约,终将是缘木求鱼之道,毕竟,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外来的异质思想必须与本民族思想有某种契合点,才有可能被接受、融合,正如有论者所言,“传统架构解体以后并不蕴涵着每一个传统思想与价值便同时都失去了理智上的价值。一些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虽然因原有文化架构之解体而成了游离分子,这些游离分子有的失去了内在活力,但有的却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可能。”[2](P259)此类论断,为在当前语境下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如何反思传统并重新考量其内涵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也明确标识出内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颠扑不灭的渐进规律。这种规律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对具体的现代文化主体而言也是难以跨越的戒律。即使在“五四”时代,那些最为坚定的反传统主义者也缺乏摧毁并重建中国文化体系的内在力量,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虽已被深深地撼动,但仍未完全解体,在这一“夹生”的语境中,他们仍然视某些传统的价值与信念为当然,而改变这种“当然”,需要漫长而痛苦的文化磨合。在文化发展规律的制约与引导下,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坛(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上从未彻底退场,“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4]始终蔓延在文学版图中。当前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整体诉求及追逐“中国梦”的文化大语境中,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不仅在学术界异常活跃,而且无论在官方还是民众话语中,传统文化的优秀质素也得到了广泛的认识与敬仰,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遭受冷遇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品也重获青睐和推崇,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重新获得了公允的理性思索与评判,其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宣传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总体而言,传统文化的地位以及与文学的关系同二十世纪初期相比是大不相同的,且越近当下,对传统文化的攻击越少,亲和越多。传统文化潜行姿态的改变印证了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性,由此所折射的文化态度及文化环境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论述种种主观意识、客观现象及普遍规律,即是为这种“耐人寻味”寻找结果——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时机已逐渐成熟。
四
重审民族传统文化,并在“取精用弘”中实现其现代复兴,是现代反思引发的必然文化取向,也是本土文化心理渴求的结果和文化重建的内在要求。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加以创造性地转化,使之成为我们现代民主自由国家在文化与道德上的基础,是在确保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时使现代文明更具合理性及合法性的首要条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审传统并不意味着抱守传统文化残缺,也非盲目痴迷于文化优根性的魅力,否则这将与“全盘西化”在偏激程度和负面影响上并无二致。实际上,这种“全盘传统化”的重审方式也不存在生成条件,毕竟,审视的主体已是经受现代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而非传统士大夫,且其审视的客体为现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主客体的“现代化”使审视者们能够自觉地以更为开阔高远的视野来反思传统,令重审工作在起初便带有了浓郁的现代特性。因此,现代文学发生以来,即使如沈从文等明确地致敬传统的作家也绝不是以反现代为目的,而是从人的精神层面关怀着现代性,呼唤着一种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个个漂泊无定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现代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自落笔伊始即表现出极为现代的特性。在这种纠葛甚至矛盾的表现中,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一组颇有意味的关系,交错互融,难以割裂,使作为专有名词的“传统”与“现代”也变得面目模糊,其约定俗成的含义,似乎也并非如其表象一般边缘清晰。
因此,在现代语境中重审传统文化,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做出更明确的阐释。就“现代”而言,笔者认为,“现代”与其说是一个历史时段,不如说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它绝不等同于“西方文明”甚至约定俗成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终究有成有坏,其“成”功效显著,其“坏”也制造出颇多隐患。因此,“现代”更应当被视作一个形容词来理解,用以描述一种有利于思想认知、文化品格及社会秩序合理性提升的趋势,毕竟,我们无法说先秦时代有关人生终极真理的讨论是“传统”的,也不能不承认《红楼梦》中对封建文化不合理性的暴露与之前或同时代文学相比是“现代”的。这似乎也提示我们应当重新理解“传统”一词,这对当前重审传统文化的工作而言至关重要。从本质上来说,“传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尽管它极易被理解为封闭、复古、保守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传统”本身蕴含着无尽的变数。以文学为例来言,即使在文化结构极为稳定的古代社会,文学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对)也并非凝固于一种静止状态,而是经常借助异族文学特色来丰富和补充其民族特色,只不过这种调节缺乏主体自觉意识,未能改变民族文学的质的规定性。进入现代社会后,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使民族文学与社会体制一样,均在质的层面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文学的“传统性”也在其动态机制的牵引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它既承续了传统文学的民族性精华,又接纳了民族社会形态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新变,以现代文化为依据为自我注入了新因素,进化成为新层次上的传统性。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历史境遇的不断变迁使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呈现出时代性的变化,文学的传统性也不断刷新,但这种具有时代性的“刷新”往往是在对立统一的辨证演变中对固有的“文学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发展和超越,纵使新变,其变之根基仍在“传统”的大版图之内。因此,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绝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概念,它始终处于被制作和被创造的开放过程,永远指向无穷的可能性,同自闭和倒退绝不等同。正如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阐释的那样,传统是过去与现在在不断的遭遇、冲突、融合中产生的种种可能,它是流动的而非凝滞的,是变化的而非确定的,是一个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这一阐释从根本上消解了现代与传统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可分割提供了来自哲学层面的论据,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与阐释“传统”提供了思索契机。在“现代”观照下对“传统”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做出必要说明,有利于我们明确在当前语境下重审传统文化的动力与目的,亦将为重审传统文化的工作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事实上,如果意识到传统并不意味着陈腐倒退,而现代也并不等同于文明先进,那么便可发现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悖,古老的传统中亦有推进文明前行的现代因子,而现代也不等同于反传统,而是传统的自我筛选、转化、优化与升华。以现代为背景和目的来回望传统,收获的将并非单一、对立的某一方,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现代民族传统文化”,而这一暗示着融合与共生的偏正短语,或许是为何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殖民与同化的洗礼之后,其文学仍能作为特异性国别文学参与世界文学谱系绘制的最简明准确的答案。毕竟,文学的现代化并非以消除文学的传统特异性为前提与目的,它对待各民族文学的态度既非同化也非合并,其本质意义在于为各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更充实的营养和更丰富的参照系。因此,在具体方法上,重审传统,不是简单地重返过去,它应当以追逐“现代民族传统文化”为指向,施展从内到外的融合行为,既非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来拒斥“异质文明”,也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洋务运动”来维护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精神,更非“全盘西化”的谬论,而是力求审慎地对待传统与现代,既祛除传统文化糟粕,吸纳现代文化精华,也在谋求现代化的同时,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根性组成在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并发掘其之于“现代”的意义。简言之,当以现代人的眼光,带着今天的问题,在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从自身中寻找实现“文明进步”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外来思想寻找相应的契合点,考量中国应当怎样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打开现代性之维。这既是用现代视野对传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过程,也是用传统力量纠偏现代弊端的过程。因此,我们在现代语境下回溯传统,重审具有根性意义的传统文化并取精用弘,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内蕴了负载传统和反观现代的双重目的,是现代中国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体系、新的价值学说和新的意义世界所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寻找使“现代”在古老中国抽枝结果的方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人格、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之举。
在现代思维的观照下重审传统文化,将会逐渐在审视的过程中构建起一个现代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型。它将建立在对传统中国文化及现代西方文化真正的了解上,而非仅凭对两者(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教条式理解来构设中国文化,它应当是中国的、现代的,既具古典气韵,又有现代新风。这一整合生成的全新文化体系无疑拥有巨大的意义空间,能够贴切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品格和深层文化心理,确立民族文化身份,强化民族文化深度,保障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性,纠偏西方文化席卷下文化与文学的异化,呼唤与引导着优雅、和谐、审美的民族新文学的诞生,并能促进理论建设的“现代中国化”进程,建立可准确、贴切地理解本国文学魅力的批评体系。它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起点,是理解并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展示自身魅力、走向世界的前提。这将是当前语境下重审传统文化所结出的芳香果实,同时亦是我们迫切期待重审传统文化的原因与动力。
[1]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 韩少功.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J].文学月报,1986,(6).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Necessity and Concept of Reviewing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YAN Xiao-yu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 The time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 culture is already mature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deep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modern culture subject, the failure of the blind Westernization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r from the universal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econsid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both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However, backtracking tradition does not mean clinging to incompleteness.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the optimal and sublimed "modern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can provide guarantee and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juvenation.
identity of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modern times
G12
A
1005-7110(2016)06-0071-06
2016-04-26
山东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研究项目“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价值辨析研究”(15BZBJ08);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Z2014044)
闫晓昀(1982-),女,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