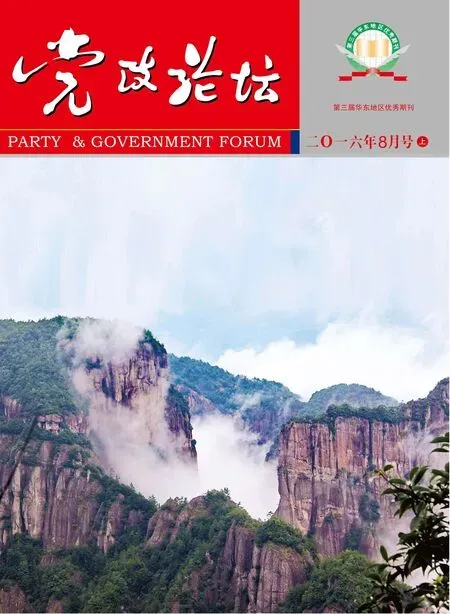对英国脱欧公投的思考
○ 秦纾心
对英国脱欧公投的思考
○ 秦纾心
2016年6月24日下午,英国公布了“脱欧”公投的最终结果,“脱欧派”以51.9%:48.1%的微弱优势战胜“留欧派”,决定了英国脱离欧盟的命运。消息公布后不久,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公投结果发表讲话并宣布辞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英国人的这一决定不仅影响着本国的社会与经济,也牵动着欧盟各国、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显然,脱欧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无可避免。对此,社会各方众说纷纭,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但无论何种观点或多或少都牵涉到“民意”这个话题。笔者无意对脱欧的结果予以评价,只是觉得仅凭公投结果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决策是否太过草率?那么,何种程度范围内可以适用公投,公投后是否有相应的复议措施,如何避免极端民主泛滥导致民粹主义的复苏,政府如何负担起国家机器的担当与责任?由英国脱欧公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脱欧公投:民意的取与舍
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辞职演讲中说道:“每一个英国公民的决定导致英国将走上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的选择应该被尊重和执行”。然而,就笔者看来,51.9%与48.1%的比例并不能成为尊重每一个民意的有力证明。退一步来说,纵使公投这一行为代表的就是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百分之三点几的微弱差距也并不存在体现大多数人意愿的这一说法。应该说,两边阵营旗鼓相当,脱欧派并没有以压倒性的比重战胜对方。如果将那51.9%的民意代表整个英国的民意,这种民意置剩余48.1%的英国民众于何地?难道他们就不代表民意了吗?
其实,事后媒体披露的投票地区分布图及投票率图也从中折射出了英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综合来看,留欧派集中在英国发达城市即所谓的精英地区,包括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加的夫、大伦敦及牛津地区。而其他地区普遍支持脱欧。从投票率上看,大城市的投票率也低于其他城市。两幅图所反馈的信息显而易见。这是一场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间的博弈,而精英阶层最终输了这盘棋。不同的经济实力、不同的利益考量使这两个阶层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精英阶层更多是从长远的经济发展诸如资本市场及全球市场来考量从而选择留欧,而大众更多看到的是显性的利益权衡,例如就业、移民、资源。因此,理所当然地,脱欧在他们眼里无疑是上策。
如此看来,卡梅伦的那一句“执行民意”多少有点欠妥了。据有关方面调查,83%的英国科学家反对脱欧;在英国经济学家中,90%认为脱欧会损害英国经济。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复杂的经济预估,显然一个经济学家的投票和超市店员的投票背后所依附的理由支持不在同一水平上。由此可见,在关乎国家命运或涉及专业领域的议题上采用简单多数的公投形式显然是有弊端的。毕竟绝大多数人对国家大事包括高度专业化的议题考虑并不深远,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理性,其着眼点往往只在自身。甚至,因囿于视野的限制,有些人还易受片面舆论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成为博弈双方的一颗棋子。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民主,当你以为全民公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时,说不定这大多数人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利益。从这个意义看,这场公投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历史重演:民主还是民粹
纵观整个投票过程,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古代社会的极端民主制。
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度发端于古代希腊,并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从那一小片领土逐渐弥漫至世界大部分角落。古希腊是一个实行直接民主的国家,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最典型的便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表决方式,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当需要决策重大事项时,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虽然制定陶片放逐法的本意在于保护民主体制不受破坏,防止僭主政治或寡头政治再起。但这种形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公民的盲从性。例如,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一向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却无情地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位不识字的农民递过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为惊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共者”,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
无独有偶,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是极端民主下的另一牺牲品。苏格拉底认为“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正如黑格尔所述,苏格拉底哲学和雅典传统理论两种不可调节的矛盾,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发生。苏格拉底的哲学理论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但是与当时雅典制度所相悖。一个是意识、知识的法律,一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当两种不可调节的法律相碰撞的时候,悲剧便发生了。
上个世纪前叶和中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很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一个“政治动员和全民狂热的时代”。而今,在国家利己主义盛行和民粹主义崛起的趋势下,很难说历史会否出现惊人的相似。
民粹主义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点似乎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煽动而对其实施操纵和控制,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
当精英民主过渡到大众民主,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其利益和政治期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在所有诉求上达成一致,因此非常容易被某一个具有民粹特色的议题动员煽动。诸如公投中的这种讨论和动员模式,既容易为民粹主义的崛起创造机会,也有可能为政治人物有意识地操纵和利用民粹主义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正因为这一特色,大众民主制度下的国民政治参与通常通过间接民主的方式实现,很少采用民众直接投票决定国策的直接民主方式。尽管这种间接投票也不一定能完全代表“民意”,但却是经过权衡后的民意。
三、政府角色:放任还是引导
众所周知,英国对欧盟的猜忌和不信任一直存在。也许是出于大选考虑, 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他赢得2015年的大选,会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有机会选择继续留在或退出欧盟。可能觉得胜券在握吧,事后英国政府又将原定于2017至2018年间的公投时间提前至2016年举行。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英国政府对脱欧公投的结果缺乏预判,公投前对脱欧后果的解释也并不充分,欠缺对民众足够的交待。虽然卡梅伦在公投期间坚定表明自己留欧的立场,但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议题上,把如此重要的决定权轻率地贸然交给处在懵懂中的大众,笔者认为政府并没有尽到执政者应有的职责。从决定公投到公布结果,卡梅伦扮演的角色似乎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投票者,而不是一个有责任的领导者。直到最终结果揭晓,卡梅伦也似乎只充当了一名给英国脱欧结果敲响最后定音锤的判官。作为执政者的引导责任呢?
由此可见,极端民主运作下的决策有时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上。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撰文说:“退欧可能是英国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残政策。没有一个谨慎的决策者会冒这个风险。”萨默斯的潜台词大概是说,当今的所谓民主社会,政客们最可逃避或推卸责任的方式之一大概就是公投了。的确,如果所有议题都交由“公投”决定,这和古希腊时期的陶片放逐法有何区别?政府拥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以及强大的智囊团队,到头来却让一群懵懵懂懂的普通人来做决定。笔者认为,这是政府借用民主概念逃避执政者的责任。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具有法定的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因此有责任有义务处理国家大事,特别是关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起码不能在把议案交由公众决定时连带把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一起丢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想要独善其身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大国,不仅有责任妥善处理好本国的事务,也有义务在国际上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决定都会对国内、国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此次公投就是一例。一场局部地域的投票和信息披露就导致了全球股市的震荡以及汇率的震动。可以说,这次公投,由于英国政府错误预估了结果的走向,才导致如今的尴尬局面。然而这些都是在公投初始阶段就应该预料到的。作为一个大国,为了获取自己甚至还无法确定的利益而贸然退出欧盟,由此给周边国家、亚洲地区乃至全球带来的震荡和损失,也是一种失责。
(上海农商银行)
(责任编辑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