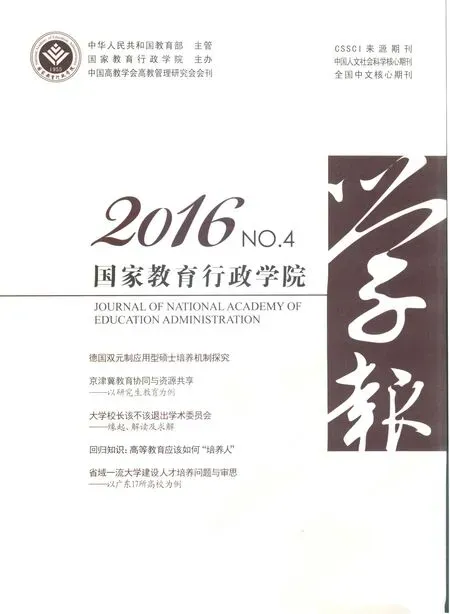回归知识: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培养人”
周 序(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回归知识: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培养人”
周序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知识在高等教育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高等教育应该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这一提法将二者人为地对立起来,却忘记了传授知识是培养人的重要途径。要让知识在人的培养当中发挥作用,必须努力将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而这依赖于大学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高等教育;知识;培养人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这一原本针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争议而提出的疑问,[1]不但在中小学教育当中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在高等教育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或许就连问题的提出者自己对此也是始料未及的。2015年笔者曾经做过一场关于知识传授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的讲座,当场就有老师质疑说:“你怎么会宣扬传授知识?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培养人啊!”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当中,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以知识为中心或以知识为本的教育理念……最大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过于形式化、抽象化和空心化,从而远离人,远离人的内心世界,远离人的生命本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创新人才的培养。尽管知识在教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教育的中心和本体毫无疑问应当是人,而不应是知识。知识是为人服务的。知识充其量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只有人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2]甚至有人认为“对于当代绝大多数本科学生来讲,有关高深学问的需求已经基本丧失”。[3]诸如此类观点并非个例,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不夸张地说,用“培养人”来代替“传授知识”,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种流行的主张。
一、知识传授遭遇危机
自现代大学诞生之日起,知识就一直是大学的核心元素。蔡元培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如果有人想把传授知识的机构与教育机构分开来,就大错而特错了”。[5]但时至今日,知识在大学当中的地位却受到了动摇;知识传授在高等教育当中也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一些人看来,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意味着“学生往往作为容器而存在,把知识装进大脑即为教育的成功”。[6]这样的教育会导致学生对现成知识结论的死记硬背和囫囵吞枣,并影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形成。因此,现成的知识结论对学生来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即便多少有那么一些价值,那知识结论也无需通过课堂教学来传授,因为在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人们获取知识结论往往非常便捷,“手机上网,应有尽有”、“百度一下,你就知道”,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云数据技术的发展,在课堂上听老师讲一个小时,获得的知识量往往还不如上网浏览十分钟获得的信息量大。既然通过听课来获得知识结论显得过时而低效,那么坚持要在大学课堂中“传授知识”,自然就显得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了。
上述理由虽然说明了“提供现成的知识结论”已经落伍过时了,却不能证明“知识传授”无益于人的培养。或许在很多人眼中,这二者本就是同义词,但其实这是对“传授知识”的一种误解。传授知识包含但绝不仅限于提供现成的知识结论。真正意义上的传授,还需要对学生进行启发、提醒,帮助学生归纳、总结,不一定是要记住最终的知识结论,但一定要对这一结论产生自己的思考:或同意,或批判,或领会,或提升,最终是将老师提供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发展。举个例子来说,于丹读《论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并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知识传授”。但于丹的传授并不只是向学生“提供”或“呈现”她读论语的心得体会而已,她还对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得”进行了华美隽永、引人入胜的讲解。讲解的价值并不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她本人的观念,而在于它成功地吸引了听者的动机和兴趣,从而引起学生的自发阅读、思考和讨论。这样,学生收获到的就不仅仅是于丹的心得体会,更多的是在于丹的“心得”基础之上进行阅读、反思和批判之后建构起来的、自己的“论语心得”。有谁能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建构出自己的“论语心得”,和于丹的传授之间毫无关联呢?没有于丹的传授,很多学生也就不会产生自行阅读、思考的动机,也不会产生批判、提升的欲望了。因此,于丹提供的“知识结论”虽然谈不上深刻,甚至还存在不少错误,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被评为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她的论语心得甚至还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潮,关键就在于她的传授过程上面。这样一种让学生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的知识传授过程,显然不是“把知识装进大脑”几个字能够概括的。因此,“传授”绝非知识的简单“灌输”或“呈现”,如果我们错会了“传授”之意,就很可能对其进行误批误判。
有人主张通过让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建构来掌握知识来代替“传授知识”。在倡导自主学习、自由思考的今天,这类观点颇为流行,似乎知识只能是建构的而不应该是传授的。考虑到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主张在高等教育应该让大学生自行建构出知识结论的声音更是不在少数。但需要注意的是,建构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几乎没有哪位大学教师会在学生完全不了解一个新领域内容的情况下让学生去“自主建构”而自己不“讲课”;也很少听说哪所大学的“探究”所占学分比“讲课”所占比例还高。任何建构,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知识基础之上,而大学生作为专业领域的初学者,他们在中小学阶段积累的基础知识常常无法支撑专业课的学习,有必要补充大量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因此,由大学教师进行知识传授,在传授的过程中通过恰当的方式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唤醒他们对知识的热情,乃至对“建构”的积极性,一如前文所述于丹对论语心得的讲解,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学当中“讲课仍然继续占统治地位:它为教授们提供了补充和解释教科书的机会”。[7]讲课这种传授知识的方式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批而不倒,取而不消,这本身就证明了“传授知识”在高等教育当中的旺盛生命力。这样我们应该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一开篇就写道:“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8]而这一责任自然应该交给高等学府去完成。
二、知识作为“人”的基础
既然知识传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于是我们就要问:知识在高校人才培养当中究竟应该居何地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高等教育哲学当中去寻找答案。布鲁贝克介绍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的哲学,一种是政治论的哲学。认识论哲学“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9]追求的是学术性的理论知识,越来越精确的知识才能使人感到满足。在认识论那里,知识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追求。政治论哲学则看重的是知识的应用性,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10]可见,无论是理论知识本身,还是理论知识的应用价值,高等教育的追求始终都是围绕“知识”这一元素来展开的。那么,以培养人才为宗旨的高等教育,如果回避知识或者轻视知识的传授,那无疑就偏离了方向,在“知识产业”“知识经济”盛行的今天更是如此。所以说,一个所谓“培养得好”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知识贫乏的人,而应该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知识传授太多,会束缚大学生的思维发展,影响到大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因此,比起掌握知识来,培养思维无疑是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市场。然而提出这类观点的人无疑忘记了杜威的告诫。杜威曾提醒我们说:“基本的事实是:讲课是刺激、指导儿童思维的场所和时间”。[11]讲课显然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传授知识的形式,讲课之所以有益于思维的锻炼,就是因为思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知识基础之上。这就好比“我思”并不能表达一个清晰的意思,只有“我思考了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越是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思维,越需要以足够的知识积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知识,尤其是高深知识,注定会是大学生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基础。
知识应当成为“人”的基础,和知识必然成为“人”的基础是两回事。缺乏知识,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有了知识就一定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时常听到很多大学生抱怨说学习专业知识不如去考证、专业知识毫无用处,这样的观念有时候还很流行。于是我们要问:高等教育中的知识传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解的时候,这时知识主要是以“公共知识”的形式存在的,但学生需要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个人知识”。“个人知识”是波兰尼使用的一个概念。波兰尼认为,传统的客观主义知识观走向了机械,它将可经验的事实看成是一切科学和真理的标准,坚持主客二分的原则,这样就否定了人在知识当中的参与作用,把人的热情、人性等个人成分从知识当中彻底地清除了出去。这样一种“与我无涉”的、客观而普遍认可的知识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但波兰尼却将这样一种看待知识的思维方式形容为“大规模的‘现代荒诞性’”。[12]因为在他看来,“即使在最精密的科学运作过程中,也都有科学家个人的必不可少的参与”,[13]既然知识生产的过程如此,知识学习的过程也不应当例外。知识只有和学习者发生密切联系,和个人已有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兴趣意向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具有生命力。这个时候,“公共知识”就转化成了“个人知识”。“个人知识”并不否定知识的客观性,而是要强调个人的情感、意志、兴趣、参与等等在知识当中的价值和地位。
大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即是将客观知识纳入个体认知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个体的情感、意志、思维等因素被激活,那么他们所学的知识就从“公共知识”转化成了“个人知识”;但如果个体的参与程度不高,那么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就更多地停留在“公共知识”层面——那是大家的知识,但不是我的知识,很难“为我所用”,前文所述的很多大学生抱怨学习专业知识不如去考证,专业知识毫无用处之类,其实就是未能将作为“公共知识”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之故。而当我们实现了学生在知识授受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做到了知识的内化,那这个时候知识就毫无疑问地可以为“人”的培养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这样的提问方式,先入为主地将知识传授和人的培养对立起来,构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从而将“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但事实上,知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和基础。通过传授高深知识来实现“培养人”的目的,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正确途径。
三、如何传授“使其成为人”的知识
要实现从“公共知识”向“个人知识”的转化,需要教师随时注意知识的更新换代,越新的知识越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同时知识教学还应走出“自娱自乐”的象牙塔模式,兼顾知识的应用性,德里克·博克将其称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14]意味着高等教育要更多的为社会发展服务,让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而要做到上述两点,教师教学技术的提升就成为关键。
客观地说,很多大学教师的知识传授水平还不高。笔者在观察中曾多次发现,在一些传授知识不甚得法的大学课堂当中,“学生自顾玩手机、打瞌睡、背单词、递纸条和胡乱涂鸦比比皆是”。[15]这种情况绝非个别高校的特例,有人指责很多老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单向灌输,“缺乏课堂交流的教学过程”;[16]有人批评一些老师的讲授“很多时候都是照本宣科”,[17]缺乏自己的分析与点评;还有人认为,大学的课堂往往“气氛沉闷,教学过程单调死板”;[18]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授课甚至被形容为“茶壶煮饺子”、“余音袅袅,杳不可辨”、“口中含有热豆腐”、“草草停课”。[19]在这种情况下,新知识难以入耳,应用性也得不到彰显。大学生对知识的兴趣无法被激活,无法调动自己参与的热情,自然难以将高深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影响。需要明确的是,与其说这是重视“知识传授”才影响到了“培养人”,不如说是很多老师不善于传授知识因此才妨碍了学生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将精力集中到如何提升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上,而是将矛头对准知识传授,主张干脆不要传授知识了,那就无益于因噎废食,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泼了出去,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如何提高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其实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有人主张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20]有人强调大学的课堂教学应重视基于学生经验的“生成”;[21]还有人认为“教育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教育必须奠基于教学活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之中”,[2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类改革主张,可以概括为“教学理念的变革”。其逻辑依据是:大学教师进行知识传授的效果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他们的教学理念较为落后;只要更新了他们的教学理念,传授质量就能够得到提升。但令人烦恼的是,虽然诸如“以学生为中心”之类的理念已经相当普及,但大学的知识教学质量却并未随之水涨船高,高校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甚至被形容为“口号高于行动,形式大于内容,成效乏善可陈”。[23]失望之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有人说,是因为“重科研轻教学”的环境,让广大教师无暇顾及教学。这一说法或许有部分道理,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因为我们看到,广大教师并不是从不留心教学,而是也对各种建立于新理念基础之上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积极尝试;不少高校也都设置了各种以自主探索、研究性学习等理念为核心的实验班;教育部2009年启动的“珠峰计划”也被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的一次尝试。[24]应该承认,很多大学教师即使是在科研压力繁重的情况下,也为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果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我们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努力的方向——革新教学理念上面。或许,教学质量的提升并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随着理念的革新而万事大吉。
马克思曾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25]提高知识传授的质量,无疑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要实现“解放”,仅仅依靠思想(理念)层面的活动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现实的手段”。比如,如何在清晰而准确地传授知识,如何通过适时地提问和启示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如何通过案例对比促进学生对结论的认同或反对,如何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的线索和框架从而促进知识的内化……一句话,教学绝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技术问题。试想,如果一个教师都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如何设置课堂提问,不清楚怎样启发学生,不了解怎样安排环节流程……我们还能指望学生会喜欢上这门课,并进而对相关知识内容产生兴趣和参与的热情吗?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无论是学术界的研究,还是高校组织的教师培训,对理念的重视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对技术的重视。缺乏了必要技术的支撑,理念的落实自然会受到影响。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只能采取自己讲半个学期,剩下的时间让大家轮流做小组报告的形式,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对缺乏技术支撑的理念的真实写照。而事实上,相当多的大学生对这样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是比较反感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技术”掌握得好的教师,学生不但喜欢听他们的课,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知识的授受过程当中,从而实现从“高深知识”向“个人知识”的转化。除了前文所述的于丹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钱志亮老师和厦门大学的易中天老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钱志亮和易中天的教学,幽默诙谐,自成一家,他们虽然没有采用何种“新理念”,仅仅是用最传统的“讲授法”在授课,但却能够把原本枯燥的教育知识和文学理论讲得生动风趣,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热情。学生会在听课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老师传授的知识和自己已有的经验相互对照,从而或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或发现其中的疑问并留到课后自行探索。在这个时候,教师传授的“公共知识”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知识”,也因此促进了他们的成长发展。如果我们说于丹、钱志亮、易中天等人即便不能称得上是严谨的学者,但至少是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话,那么在教学的技术方面以他们为榜样乃至向他们看齐,应该对提高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颇有裨益。
这样看来,学生能否将知识内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教师传授的“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是决定他们成长发展状况的关键所在。而这依赖于教师教学技术的掌握水平。如果大学教师能够掌握令人称道的教学技术,那么课堂就绝对不会是简单灌输和“填鸭式”教学,知识也就不会成为“培养人”的阻碍,反而会是学生成长发展的推动力。当我们不再将“传授知识”和“培养人”相割裂、相对立地来看待的时候,“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或许就会成为大家自觉的共同选择。
[1]张正江.教育的本质: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与王策三先生商榷(续)[J].教育发展研究,2005,(3):36-38.
[2]孟建伟.生活乃教育之根: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3,(22):31-34.
[3]王一军.大学课程:发展学生“个人知识”的必要与可能[J].高等教育研究,2011,(4):64-75.
[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蔡元培.蔡元培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9.23.
[5]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49.
[6]刘艳侠.不同知识类型学习中的师生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14,(8):82-86.
[7][8][9][10]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张维平,徐辉,张民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95.12.12.14.
[11]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13.
[12][13]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14]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舟,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5]周序,王玉梅.回归技术:大学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必由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15,(6):71-75.
[16]周作宇,熊春文.大学教学:传统与变革[J].现代大学教育,2002,(1):15-21.
[17]梁中贤.讨论法: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J].中国高教研究,2012,(1):104-106.
[18]刘智运.必须重视大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J].教学研究,2010,(1):33-37.
[19]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N/OL].2012-09-15(2015-10-10).http:// www.infzm.com/content/80797.
[20]杨彩霞,邹晓东.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理念建构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5,(3):30-36,44.
[21]程广文,陈笃彬.论教学的生成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8,(1):81-83.
[22]潘斌.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J].高等教育研究,2006,(5):7-12.
[23]吴康宁.创新人才培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3,(1):11-15,50.
[24]周光礼,黄容霞.教学改革如何制度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的兴起[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5):51-52.
[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
(责任编辑朱玉成)
Return to Knowledge:How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Educate
Zhou Xu
Knowledge defines a ma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hich is the core task of the university. The debate whether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spread knowledge or educate people is in fact groundless since teaching knowledge is the primary means of education.To retur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to its essential place in education and to better help students to transfer public knowledge into personal knowledge,we must depend on the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higher education;knowledge;education
G642
A
1672-4038(2016)04-0053-06
2016-02-08
周序,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