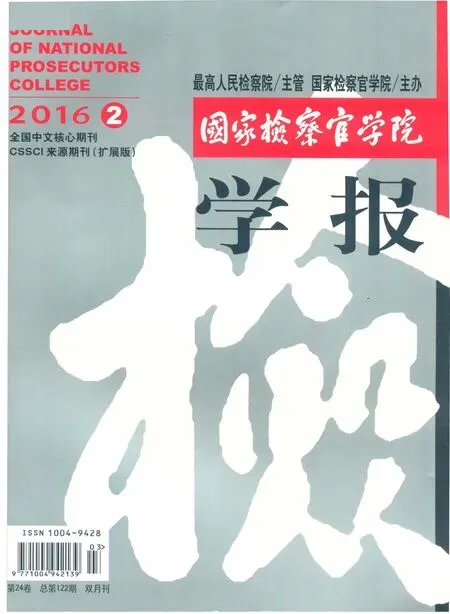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
赵一瑾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23)
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
赵一瑾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23)
摘要:商事合同以追求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兼具一定的公法属性,体现商事交易的习惯和规则,商主体在行使商事合同解除权时呈现出与民事合同的差异。《合同法》分则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在商事合同中应当限制适用;当商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需要限制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对非商人一方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一般采用较短的时效规则。研究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及《民法典》的编撰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商事合同解除权限制规则法律适用
引言
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对民商事合同并未予以区别,虽然《合同法》中一些条文体现了商事合同的特征,但难免在具体制度与规则设置上顾此失彼。商事合同注重效益,遵循商事交易规律,因此商事合同解除权具有独特的行使规则。虽然有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性,*江平教授认为:委托合同分为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合同法》410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仅适用于民事委托合同中。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法学》2005年第9期。崔建远教授也认为:在商事委托合同中,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应当限制适用。参见崔建远、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但立法上仍缺乏统一的商事法律适用规则。由此导致商事审判中同案不同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等不利后果,检察监督也缺乏法律依据。商事合同解除权因合同解除原因的不同,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其中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民商事的差异性也比较突出,尤其是商主体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法律适用规则较为混乱,因此本文以该问题为研究重点。
研究商事合同解除权,必须先对“商事合同”的概念进行学理上的界定。各国对于商事合同概念的界定虽不相同,但大多建立在“商主体”与“商行为”的概念基础之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商事合同概念,但在买卖篇中不仅对某一特定领域内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易进行了特殊要求,还对其交易规则做了明确规定。英国法中主要通过判例的方式对商事合同中的特殊规则进行规制,并将商业合同定义为“双方当事人为了营业而签订的合同”,随后又区分了消费者合同与非消费者合同。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和《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都涉及到了商事合同的概念,这两部法典虽然都没有就商事合同提供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消费者合同”,二者都提供了明确的定义。参见吕来明、郝春峥:《商事合同制度适用初探——兼谈“商事通则”中商行为一般规则的建立》,《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例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并没有直接对“商事合同”的概念予以界定,而是通过合同的主体是否属于商主体,或者合同交易的性质是否具有商事性来判断是否属于商事合同,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参见吕来明、郝春峥:《商事合同制度适用初探——兼谈“商事通则”中商行为一般规则的建立》,《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本文对商事合同的界定,参照《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做法,以“商主体”及“商行为”为中心,即商事合同是指商主体之间签订的,以营利性为目的,进行商事交易的合同。我国《合同法》中涉及商事交易性质的合同有: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技术合同等十四种合同。*参见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该书认为涉及商事交易性质的合同有:买卖合同、供电、水、气、热力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14种合同。但商事交易内容发展日新月异,新形式的无名合同层出不穷,上述十四种合同很难涵盖所有商事合同的类型。本文将通过对几种典型商事合同中解除权行使的限制规则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
一、限制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原因
对于商事合同解除权进行限制,是相较于民事合同而言的。商事合同解除权具有特殊性,其行使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商事合同解除权设置的基础与民事合同差异
与民事合同追求公平的价值取向不同,商事合同更加注重效益。由于基本价值取向的差异,商主体订立商事合同的目的在于营利,而民事合同则更多体现的是诚实、信用,两者在合同解除权行使规则的设置上必然存在不同。例如,民事委托与商事委托的合同基础不同,在传统民法上“受托人的承担义务并不需要对方付出代价,因此,也可以单方面的解除合同。但根据诚信原则,中途辞职不得在不利于委托人的时期进行,否则即视为有过失,须由其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但确有正当理由的,如重病、出征等,自当别论。”*周枂:《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04页。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的委托人任意解除权,其设置基础在于民事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一旦信赖基础发生动摇,委托人当然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是在商事委托中,商主体订立合同的基础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若赋予商事委托人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则很可能有失公平。又如,《合同法》第232条规定了出租人对于不定期租赁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该条对于任意解除权的设置,更多的考虑的是对于民事出租人利益的保护,但在商事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对于租赁的房屋可能基于商业用途,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若在商事租赁合同中不加区分的适用《合同法》第232条,不仅会损害商誉、造成经营收益的减少,还可能使商事承租人丧失赔偿请求权。
(二)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可能影响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原则是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商人从事商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害其他商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参见周林彬、官欣荣:《我国商法总则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法律适用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虽然民法中也有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但民法中的公共利益一般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商法中的公共利益更多涉及到“市场秩序和经营利益”。*同前注[6],第442页。某些商事合同的可能会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交易相对方的利益,甚至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对于这些合同的解除一般会有商事特别法予以规定和限制,在必要时,公权力会介入这一私法领域中,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进而达到稳定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所以,这些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更加严格。例如,一些商事合同在合同订立之后,需要履行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才能生效,在完成审批程序并生效后,这些商业合同不可能再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恢复到合同成立之间的状态。较为典型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所签订的投资人协议。协议签订完成后,若有一方没有履行义务或者经协商,可以解除协议。不过,如果投资人协议与公司相关文件都已经递交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工商管理部门也做了相应的记录以后,这样的协议就不能随便解除。如果一个投资人没有按照协议要求缴纳出资,其他投资人不仅不能解除合同,还要共同对外承担出资不实的连带责任。这是因为投资人协议经过工商部门审批后,公司依法成立,其不仅是投资人之间的协议,还作为商事交易的主体,对第三人承担商事交往中的公司责任。投资人协议具有不再仅具有私法属性,其还具有一定的公法性质,协议的解除要受到《公司法》等商事特别法的调整。即使投资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其也应当履行《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解散的有关规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公司清算程序,甚至通过诉讼的方式解散公司。与投资人协议相类似,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可能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等因素,其解除程序较一般的民事合同而言更加严格,仅可以通过诉讼和仲裁解除合同。
(三)商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遵循商事交易规则
商事活动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一些商事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已经具有一定的固定模式,甚至形成了行业惯例,商事合同作为商事活动的主要载体,合同的解除也必须要符合商事交易的惯有规则。例如:不良资产转让合同与普通的债权让与合同不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置政策性强,风险性高,收益也高,与等价交换合同有很大差别;实物资产的不良债权交易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转移,并不是一般物品的买卖关系,所以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的解除受到特殊的限制。在最高法院公报中的沈阳银胜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胜天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华融沈阳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银胜天成公司与华融沈阳办签订《债权及实物资产转让协议》,转让了含有债券资产及实物资产的资产包。后因部分实物资产(不动产)存在权属争议不能过户,银胜天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部分转让款。一、二审判决均判定按照协议,银胜天成公司已经向华融沈阳办支付了所有转让的款项,可是华融沈阳办却没有将实物资产转到银盛天成公司,造成了银胜天成公司的损失,判处合同解除,华融沈阳办部分返还合同款。最高法院进行了改判,其在审判中认为资产包在买卖时都是以整体的形式,当然交易取消时也是整个的取消,资产应当全部返还。该案的资产转让合同中的实物资产和所涉债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肆意分割,银胜天成公司将资产包中的剩余部分返还,这么做对于华融沈阳办来说并不公平,因此合同不能解除。最高法院充分考虑了不良资产转让中风险承担规则的特殊性,资产包应整体转让,不得拆分,作出了符合商事交易规律的公平判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125号民事判决。
(四)商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具有专业优势
民事合同的主体多为地位平等的自然人,而商事合同的主体一般双方为商人,或者一方为非商人。*此处的“商人”是指:专指以营利为目的、经登记并以商品生产经营为业的个人和组织,并进一步提出确定商人的目的性(营利为目的)、登记性(注册登记为必要)、营业性(持续性经营为常业)标准,据此标准将商人分为商自然人(如小商人,可登记为商人也可登记为商人)、商合伙(如合伙企业)、商法人(如公司)。参见李玉泉、何绍军:《中国商事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在一方为非商人的情况下,由于非商人一方在专业性、信息的获取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法律一般倾向于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具有代表性的是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一般在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及相关投保信息的掌握方面,对于保险人而言,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因此《保险法》对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条件规定的较为宽松,而保险人若要解除保险合同,则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商事合同主体一方为非商人的典型合同,还有股票、债券、期货交易及储蓄合同等,在该类合同纠纷中,商人一方的优势地位明显,如果不加区分的赋予商事合同双方同样的解除权,则很有可能损害非商人一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该类商事合同中,均应严格限制商人一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二、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一)商主体行使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分则中规定的任意解除权,更加适合于在民事合同中适用,典型的如委托、承揽合同等,这些民事合同关系建立在对特定人的信赖基础之上。一旦这些合同具有商事性质,以营利为目的,受托人、承揽人等为履行合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人力和时间,若仍然不加区分的适用《合同法》分则中的合同任意解除规则,不仅使商主体受到巨大损失,还可能导致合同解除后其无法主张损害赔偿。如何对商主体行使任意解除权进行限制,以下将对几种典型商事合同中解除权的行使进行探讨。
1.商事代理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合同法》第410条赋予委托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可以适用于民事委托合同,但在商事代理性合同应当予以限制。对于专业代理商,若法律赋予其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将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如果赋予委托方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可能会给整个代理商行业强大的冲击。由此看来,这项规定并不适用于商事代理合同的案件,至少在有长期商事代理关系的商主体和专业代理商不应拥有单方任意解除权,而应施行更为规范严格的合同解除条件。
在商事代理合同中,代理商作为营利主体,它以追逐营业利润为目标,因此,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对民事代理人与商事代理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同前注[6],第405页。对商事代理人而言,代理合同的解除意味着商事代理人营业利润可能灭失,若法律规则允许委托人随意解除代理合同则会使商事代理人失去从事商事代理法律行为的动力。因此,有必要限制商事代理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以适应商事代理的营利性特征。
例如,在万宝龙单方终止代理协议案中,*参见王婧:《万宝龙单方终止无期限代理协议》,《法制日报》,2009-02-02。因为国瑞信公司对万宝龙公司前景的看好以及信誉的信任,其在为万宝龙公司作前期市场开拓时投入了大笔成本,然而万宝龙突然单方终止代理关系,使国瑞信公司前期投入的成本付诸流水。国瑞信受偿无门,商事代理中商业信誉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无法实现。又如在上海盘起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虽然根据《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参见徐瑞柏:《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上诉案判定解析》,《民商事审判指导》(2008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可见,如果对于商事代理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10条,不仅代理商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甚至连损害赔偿权也会受到损害。
为使此类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在对现行《合同法》第410条关于任意解除合同的规定适用时范围不应过于宽泛,而应当将其适当限缩,使之仅适用于非等价的或者无偿的委托合同,并注明其不适用于商事代理合同。否则那些专为委托事务而成立公司,其从事经营活动或是为完成委托事务而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向、经营领域,亦或是为了被委托事务的顺利完成要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拓展市场、发展客户,这些代理商的自身利益会会受到极大损失,显失公平。同时,在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也应当明确限制商事委托合同的解除权。
2.物业管理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物业管理合同案件中当事人是否享有单方任意解除权,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不同认识。在广州市中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新中国大厦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案涉《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具有委托合同性质,可以适用《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由委托人单方解除物业管理合同。中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新中国大厦的管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业主方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显然会损害中怡物业管理公司的利益,但由于现行的法律对于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无名合同,法官在法律适用时无法可依,商主体的损害赔偿也无法主张。
应当明确的是,物业管理合同不同于以“信任”为基础的民事委托合同,其是建立在等价有偿基础上的商事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0条的理论基础是无偿合同的信任理论,而物业管理合同的信赖基础是受托人的商业经营能力,此时的信赖基础已经与无偿委托不同,物业管理公司以逐利为目的,需特意投入以获得报酬,委托人任意解除合同将损害物业管理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对解除权主体进行了限制,仅赋予了业主任意解除权而没有赋予开发商任意解除权。对于业主方的任意解除权,笔者认为也应当严格限制,不能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
若是要赋予业主单方随时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的权利,则对物业管理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是十分不利的,尤其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处于刚刚步入市场化阶段,并且物业管理行业的本身特点就是对持续性和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管理企业一方一旦享有单方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都有可能导致小区的物业管理行为高混乱度和低效率性。对于物业管理合同的限制,也应参照上文中对于商事代理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论述,在立法上明确物业管理合同与普通委托合同的区别,限制开发商及业主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当中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有关章节并没有直接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适用任意解除权,但《合同法》第287条规定“本章(建设工程合同章节)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合同法》第268条又规定了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发包人似乎应当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但从我国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来看,发包人的任意解除权均应当受到限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面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规定了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几种情形。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合同解除方面,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并不能适用。其原因在于如果赋予发包方像定作人一样的权利,在上述司法解除中,没有必要再一一列出关于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况。发包人的解除权被严格的限制为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况,即在法律实践中,除了这几种情形,发包人不能解除合同。再者,关于对这一项司法解释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其目的就是“通过明确解除合同的条件,防止合同随意被解除,从而保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全面实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为建设工程付出了大量的资金及劳动力,其不同于普通的定作合同。从《合同法》第286条的立法本意看,之所以赋予定作人任意解除权,是为了防止在交易情况发生变化,定做的成果不再为定作人所需时,如果继续为了交易稳定而维系合同则可能给定作人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定作人可以通过解除合同救济权利。因为定作的成果通常情况下是不具有流通性的,等到成果完成后若定作人不再需要该项成果,就很有可能出现没有途径转让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以避免资源浪费为目的,法律允许在定作人不再需要定作成果的情况下可以及时解除合同,从而减少双方损失。但是,在商事交往中,定作人解除合同往往是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减少资源浪费,如果不对其任意解除权进行现则,则可能会导致权利滥用,违背了法律赋予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初衷。因此,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前提应当限定为:确认定作人不再需要定作成果,且必须在定做成果完成之前行使权利。相比承揽合同而言,施工成果相比普通的定作成果更难以流通于市场。如果合同因发包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而终止,如果想把施工成果转让给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不仅会造成大量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工程的承包方来说,也显示公平。另外,从合同解除的后果来看,如果赋予发包商和普通定作人一样的任意解除权,则其解除合同的行为不仅不属于违约,承包商还无法向发包方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其在合同解除后的权利救济亦会受到损害。因此,发包方的任意解除权不能滥用,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适用《合同法》第286条时,应当做限缩性解释,其适用范围不宜扩大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4.商事租赁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区分民事租赁和商事租赁,当租赁期限届满,则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出租人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英、美和法国法都对商事租赁合同和民事租赁合同加以区别规定,其中都从租金的调整和租期保护,法定续展权和赔偿请求权*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一),徐进、李又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85页。对商事承租人进行了特殊保护,尤其是法国商法明确规定了承租人的商事租赁合同的续展权,否则出租人要赔偿承租人因被剥夺续展权而遭受的损失。*参见张民安、龚赛红:《商事经营场所租赁权研究》,《当代法学》2006年第7期。1953年9月30日法国法令第35条宣告“凡产生不能行使租约延展权之效果的协议无效”。*参见[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0页。法国学者Didier指出:“商事承租人在商事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时,对其租赁物享有续展的权利;如果此种续展权被损害,商事承租人即享有权利请求出租人赔偿。这些权利被人们称之为租赁权,也被称之为商事财产权。它是根据公共秩序所产生的权利,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任何条款或规定,无论其形式如何,如果剥夺承租人的此种权利,其条款或规定无效,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同前注[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没有区分民事租赁和商事租赁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其中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规定商事承租人的法定续租权或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法定续租权和优先承租权并不相同,法定续租权是指不改变租赁合同中期限以外的约定,仅是期限的更新,而优先承租权是在同等条件下重新签订了一份新的合同,其中最容易出现纠纷的是租金的调整。而我国合同法对此并没有进行详细规定。而是将其留给当事人自身约定。出现纠纷时,由于租赁合同期限已满,商事承租人仍占有租赁物进行经营,法院往往适用《合同法》第235条及《解释》第18条判决承租人于一定期限内腾房并支付使用费,丝毫没有考虑商事承租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所得的成果:良好的商誉、*关于商誉(又称good will)的本质,比较权威的观点当属美国当代著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在其专著《会计理论》中介绍的三个论点,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其中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于企业的良好形象及顾客对企业的好感,这种好感可能起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有利的商业地位、良好的劳资关系、独占特权和管理有方等。由于这些因素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且又无法入账记录其金额,因此商誉实际上是指企业上述各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故好感价值论亦称无形资源论。参见[美]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王澹如、陈今池译,立信会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稳定的顾客群以及未来经营的收益面临可能的减少等问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租赁合同不分民事租赁和商事租赁,都统一适用《合同法》第235条及第236条,即出租人在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有权决定是否解除租赁关系。显然,如此规定对商事租赁人的权利设计不完善,没有对商事租赁合同终止后的续租权予以规定,会致使商事承租人权利不保。在西关竹园竹升面老铺租赁纠纷案中,西关竹园竹升面老铺在经营了8年之后何去何从呢?是政府出面调解方多少维护了承租人一点利益,*广州市和平西路8号西关竹园竹升面老铺经营的是广州传统的食品竹升面,该面铺在原址已经经营了8年,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生意比以前更加红火,恰好该铺位的租赁合同又到期了,出租人要求由原来的月租金9000元涨至18000元,承租人觉得难以承受,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知名老店面临搬迁的命运。该事件被报导后,老店的命运受到广泛的关注,政府相关部门也积极介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老店以月租金13500元继续承租下去,得以在原址继续经营,而出租人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实现了业主与租客利益的双赢。参见《租金谈妥,竹园老店不搬啦》,《南方日报》,2012-06-15。而在北京南三环皮鞋商贸城的解租纠纷案中,*该商贸城的经营单位承租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招商,许多商户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业主因经营单位未按时缴纳租金,提出解约。这不仅使大批承租经营摊位的商户投入血本无归,也将带来巨大的间接损失。这一案件法律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由经营单位补齐租金及滞纳金的基础上,继续承租使用?如出租人坚持,不解除似乎无法律根据,此种情况下,经营的公司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根本没有续租权保护一说。承租人则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法院在诉讼中根据《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简单解除租赁合同,对承租人的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或解除合同时的赔偿权不予支持,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厦门沃尔玛与新鹭东方商贸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案,*参见中国商事仲裁网:http://www.ccarb.org/news_detail.php?VID=21046,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0月13日。最终厦门中院支持了出租人解除合同的请求,丝毫没有考虑作为商事承租人沃尔玛公司的营业权的保护。因此,在商事租赁合同中,应当赋予商事承租人法定的续租权或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在商事租赁合同租期届满后,应限制商事合同出租人行使合同解除权。
(二)商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解除权的限制
在商事合同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由于商人一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出于对非商人一方的保护,应当对商人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予以限制。
1.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商事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在保险合同中体现较为明显。《保险法》第15条规定了投保人具有任意解除权,而对保险人则的解除权进行了专门的限制。*《保险法》第16条、第35条专门限制了保险人的解除权,只能在出现第17条第2款、第28条、第36条、第37条、第54条、第59条规定的情形下才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仅在投保人或受益人存在重大过错,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费或者在投保时隐瞒了可能会影响保险费率的重大情况时,保险人才具有合同解除权。同时,对于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方式的规定较为繁琐,如《保险法》第54条规定,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且不符合合同的年龄限制,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不仅要向投保人退换手续费及报废,并且规定了较短的权利灭失期间,即该解除权在两年内不行使则保险人丧失该条规定的解除权。
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任意解除权进行特殊限制,主要是因为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一般处于强势地位,其比投保人在专业知识、信息掌握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因此其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尽到告知义务,明确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其没有尽到这种告知义务,则法律赋予其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在法律适用时也将作出有利于投保人一方的决定。
2.储蓄合同中银行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储蓄合同与保险合同相类似,普通的储户无论在专业知识及信息的获取上,相较于银行而言,均处于劣势地位,若对于银行的合同解除权不加以限制,则很可能给损害小储户的利益,还有可能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例如,湖北丹江口的普通储户盛某,1989年将2000元存入银行,存单上写明24年到期后可得本息共22万元。但当存单到期后,银行却告知其存单失效,本息只给8400元。银行的解释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1989年曾下发了紧急通知,并进行了公告,保值储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24年的存单已经失效。银行是否可以因政策变动而解除合同引发争论。*参见党小学:《24年存单,银行能反悔吗?》,《检察日报》,2013-10-16。银行并不能以央行政策变动,且已尽告知义务为由而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必须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央行的政策变动,既不属于情势变更,又不能归为不可抗力,因此不能作为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在合同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银行必须按照存单的约定支付相应的本息,其拒绝支付存单约定的本息属于违约行为,作为违约方,银行也不能享有合同的解除权。在储蓄合同中,银行往往是储蓄政策的制定者,储蓄合同也一般以格式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储蓄合同纠纷发生时,若对于储蓄合同是否可以解除存在争议时,一般应作出有利于储户的解释,银行一方的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三)商主体行使解除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从对上述几种典型商事合同中解除权行使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般限制规则。对于商事合同中商主体行使解除权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合同法》分则中虽然规定了合同主体具有任意解除权,但该规定是建立在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之上,当该合同具有商事性质时,法律适用的差别较大,该类合同如委托、定作、租赁等合同。该类合同中商主体限制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应当为:《合同法》分则中关于合同任意解除的规定,不能扩大适用到以营利性为目的的商事代理、物业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事租赁等商事合同中,在这些商事合同中,商主体不得行使任意解除权。若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
二是典型的具有商事合同性质的合同,但合同一方为非商人。该类合同除上文分析过的保险合同及储蓄合同外,还有非商人一方以投资为目的签订的股票、证券、期货,以及其他具有商事性质的无名合同。在这一类合同中,关于限制商主体一方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为:当商事合同一方主体为非商人时,商主体一方的合同任意解除权应予以限制。若双方对于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约定不明或法律适用存有争议时,应结合商事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履行情况等,作出有利于非商人一方的解释。
三、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限制
对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属性在学术界存有争议,但一般认为由于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权行使的期间为除斥期间。由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故解除权行使不需要征得解除权相对方的同意,即享有解除权的人有权依单方意愿表示而干涉他人的法律关系,所以解除权的行使必然会对解除权相对人的利益造成影响。如果权利长时间不行使,那么当事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会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对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十分不利。*参见崔建远、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权所对应的除斥期间既可以法定的,也可以约定。而如果没有法定又没有约定时,守约方催告所确定的期限,即为除斥期间。但是,《合同法》第95条中关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并没有明确规定,相较于民事合同而言,商事合同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其解除权行使期间应当受到限制。
(一)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的特殊性
山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海汇公司)与谢宜豪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参见朱铁军:《合同解除权不能滥用》,《人民司法》2011年第12期。海汇公司向谢宜豪转让了公司股权,谢宜豪又向第三人转让了公司股权,由于谢宜豪及第三人均没有交付股权转让款,海汇公司在五年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合同。法院认为,山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五年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应视为自愿放弃行该解除权。实际上法院在判决结果中引用了“权利失效”理论。“权利失效”理论,即指当事人拥有可以行使的权利,但是在权利有效的期间内权利并没有得以行使,致使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权利人不欲行使该权利。即使权利人欲再次行使该权利,而由于当事人的行为在权利有效期内出现矛盾,按照诚信原则,应对权利行使予以禁止的措施。权利失效原则,是一种为防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特殊规则。*参见王泽鉴:《权利失效·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45页。
由于“权利失效”而造成的解除权消灭,完全可以看成为商事合同交易中的效率要求和外观主义的典型反映。例如,在商主体之间进行货物买卖时,若买方在接受商品时即使发现商品并没有如宣传中的让人满意,但并没有主张解除合同,而是依照相对合同中约定价格低的价格对货物进行了交易,卖方对此一般也不会存有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事后买方仍然处在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之内,合同的解除权也不再归买方所有。同样,对于卖方而言,其若以双方交易价格低于合同约定价格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也不应予以支持。权利灭失原则,对已经形成的商业交易秩序进行维持,可以有效避免合同在解除之后的一系列损失赔偿、追偿原物等行为,避免已经达成的交易被解除。这一制度,在买卖的货物不适合搬运(例如套装安装后不方便二度拆卸,安装高精度仪器等)的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综上,即使“权利失效”表面上是民商事行为均适用的一项规则,但是基于商事交易中快捷性、综合性、专业性、外观主义的特性,在考量个案中权利失效是否成立时,需要率先参考合同性质对于形成权利失效期间长短的影响,也就是在商事合同中,权利利失效期间更为短暂,以此来满足商事交易对于效率的特殊要求。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的商事合同中,解除权除斥期间不一定均规定的较短。比如:《韩国商法典》第651条规定,“保险人得知其事实(即投保方故意或过失未告知重要事项或者虚假告知)之日起一个月内,限于签订合同之日起三年内,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已知该事实或因重大过失而未能知道时除外”。*姜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日本商法典》第644条也有类似之规定,“该项解除权在保险人自得知解除原因之时起一个月内不行使,即行消失;自订立契约之时起经过五年时,亦同。”*同前注[27]。因此,商事合同中一般规定较短的除斥期间,较长的除斥期间为例外。
(二)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的法律适用规则
对于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应当如何限定,我国《合同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了买受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该规定可以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商事合同类型,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律未对除斥期间予以明确规定之前,如何确定“合理期限”呢?
由于商事合同追求快捷、安全的特征,其权利长期处于不稳定过状态会影响交易的效率及交易安全,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较短。在商事合同中,除非有特别法的规定,一般均可以类推适用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中,关于解除权一年不行使,权利即消灭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撤销权等其他形成权的除斥期间也规定为一年,合同解除权也可以参照其予以规定,可减少法律适用时的混乱;二是商事合同解除一般涉及第三人,其更注重外观主义,解除权的行使,会导致合同关系被废止,则现有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如果允许解除权人在过长的期限内解除合同,则可能破坏现存的经济秩序,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及时行使解除权,有利于确定违约损害赔偿关系,在违约情况下,违约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两年,如果解除权期限过长,即使权利人主张了解除权,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也难以得到保护。因此,商事合同中解除权行使的期间应当明确为:除因商事合同的特殊性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特殊的解除权除斥期间外,解除权除斥期间为一年,一年不行使,权利消灭。
结语
随着商事活动的快速发展,商事合同的类型日益复杂化、专业化,本文选取的商事合同类型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仍较为片面性。在个案的法律适用中,还应结合商事合同的特殊性质、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要完善我国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规则,首先应当在司法实践中树立商法意识,避免运用法官、检察官的民事司法判断来替代商事司法判断,应遵循商事交易的特殊规律及行业习惯,在商事合同约定不明时,应结合商法的价值取向对合同进行解释。其次在立法技术层面,一是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对现行的《合同法》进行修改,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限制规则法定化;二是通过最高法院判例和审判政策,将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法律适用的特殊规则,在典型案例中予以明确;三是在未来的民法典总则中,将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的一般规定予以法定化,并明确商事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则。
(责任编辑:赵玉)
Special Restrictions on the Rescission Right of Commercial Contract
ZHAOYijin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ercial contract is to pursue benefits,and the commercial contract has public law character and reflects the commercial transaction habits and rules,so there i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 from civil contract when the commercial subject exercise the rescission right of commercial contract.Regulations o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ontract law” about exercising the rescission right wantonly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apply in commercial contract.When one party is non-commercial subjects,the rescission right of commercial subjects should be restricted so as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non-commercial subject specially,and generally a shorter time period is adopted during the exercise of rescission right of commercial con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special rules of application of rescission right of commercial contract has a positive meaning to regulate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as well compile the “civil code”.
Key Words:Commercial Contract;Rescission Right;Rules of Restriction;Application of Law
Zhao Yijin,Ph.D.Candidate at Law Schoo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Assistant Prosecutor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Guangdong Province.
Law Forum
法学讲坛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6)02-0151-12
作者简介:赵一瑾,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