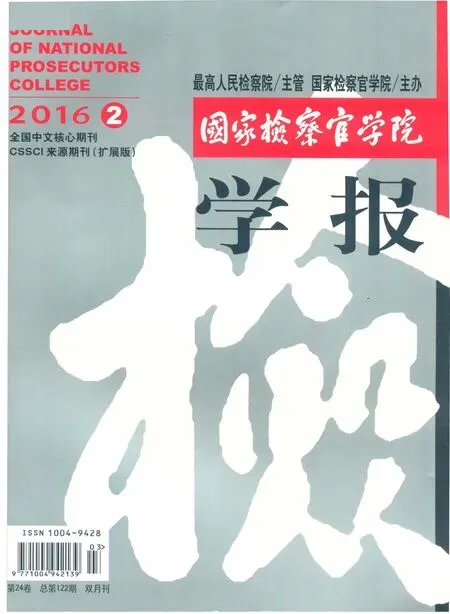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的矛盾解析
周锦依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的矛盾解析
周锦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自《刑法》设立第191条洗钱罪以来,关于该法条与其他相关法条的重合规定,该法条的修正过程与其立法初衷的冲突,以及洗钱犯罪的严重性与该法条司法适用率低下的巨大反差,均存在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对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分析,不难发现,全球化的影响、对公约义务之履行以及来自国际组织的经济制约,均在左右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方向。因此,对我国洗钱罪设立、修正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不应脱离国际反洗钱框架。与此同时,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进程也如同一个缩影,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权在当下已然受到以及未来可能受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与介入。
关键词:洗钱罪立法进程矛盾现象国际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关注多集中于立法修正,却鲜有涉及对该罪名设立及发展因由的探讨。然而,伴随着洗钱罪立法进程中诸多矛盾现象的出现与凸显,以严重社会危害性作为洗钱罪立法必要性的充分理由和以特定方式清洗特定犯罪所得作为洗钱罪打击重点的立法初衷也在逐渐受到挑战与质疑。面对当下理论界对我国洗钱罪存在意义认知的模糊不清,以及对该罪名修正方向把握的模棱两可的现状,有必要厘清并分析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的诸多矛盾现象,以揭示真正制约我国《刑法》第191条设立与发展背后的因素。
一、洗钱罪立法进程*我国对洗钱罪的惩治最早始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对涉毒洗钱的规定。然而,由于当时对洗钱行为的入罪化只是局限在毒品犯罪领域,且对洗钱入罪化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毒品犯罪。因此,涉毒洗钱罪尚不足以视为当下普遍意义的洗钱犯罪。因此,本部分论述的洗钱罪之设立,是以我国1997年《刑法》第191条设立的洗钱罪为源头展开的。中的矛盾现象
(一)洗钱罪设立的必要性与刑法供给充足的矛盾
近年来,对洗钱罪设立必要性的探讨,鲜有学者述及。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因履行相关国际公约义务而设立洗钱罪外(该内容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详述),最有说服力的当属不断被国内外反复强调的洗钱犯罪之严重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推进世界各国将洗钱行为入罪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当今西方社会,对洗钱危害性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纯理论推测转向实证分析,各类洗钱危害论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质疑与挑战,该种质疑与挑战并非否认洗钱犯罪的危害,而是反思其危害是否确有理论推测的那般严重。然而,仅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增设洗钱罪的唯一门槛,则未免有失妥当。诚如有学者所言:“只有确实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而现行刑法规范体系对类似行为的规制又无法涵盖问题行为时,才能说真正存在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付立庆:《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及其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换言之,即便洗钱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满足了刑事可罚性这一大前提,对其进行入罪化也仍需建立在现有刑法规范不足以规制类似行为的基础上。然而,对1997年修订刑法典的相关规范进行回顾便不难发现,第191条洗钱罪设立的必要性并不明显。
1997年《刑法》颁布伊始,除了增设的第191条洗钱罪之外,与之类似的罪名还包括第312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该条文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此后在2009年经过《刑法修正案(六)》的修订,变更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罪名也更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由于第349条中的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是从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中“窝藏毒品、毒赃罪”*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12月颁布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涉及以下三个罪名: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毒赃罪;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罪。更名和演变而来,*我国1997年《刑法》第349条全部保留了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窝藏毒品、毒赃罪”的罪状,只是将法定刑修改为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以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档次。此外,将“窝藏毒品、毒赃罪”更名为“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从而在称谓上更能体现该罪的行为方式。而“窝藏毒品、毒赃罪”的设立又是源于我国对1988年《维也纳公约》义务的履行。因此,追本溯源,《刑法》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即可视为国际意义上的涉毒洗钱犯罪。反观1997年《刑法》增设的第191条洗钱罪,虽然也将毒品犯罪纳入了上游犯罪当中,但是因其立法归类(第191条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该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则被限定在了金融领域。如此一来,《刑法》第349条规定的洗钱方式甚至更广于第191条中的涉毒洗钱。显然,在涉毒洗钱领域,《刑法》第191条与第349条规定的内容已然发生了重合。相比之下,《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则相对宏观与概括得多。根据法条的表述,“赃物”作为上位概念,既可以包括“毒赃”,也可以包括来自于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而根据《刑法》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规定,所谓“窝藏”,意在隐匿暗藏。除去对赃物物理形态的隐匿,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很难否认对赃物来源与性质的隐匿不能被纳入到窝藏赃物的理解范围。而“转移”,旨在表述一种行为过程,词语本身并未限定转移的方式与方向。因此,除去最直观的将赃物从A地转移到B地,通过金融机构、贵重金属交易所、乃至地下钱庄等将赃物转移以逃避司法机关追查的行为,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转移赃物”。相比之下,“收购”与“代为销售”虽然是较为具体的赃物买卖行为,但其亦可视为洗钱的行为方式。因为,若洗钱犯罪的本质在于切断犯罪所得与犯罪间的联系以逃避惩处,那么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任何方法都可能被利用。故而,《刑法》第312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实际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根据《刑法》初设第191条洗钱罪时的规定,洗钱的对象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以及走私犯罪;洗钱的行为方式也因为其立法归类*由于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归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所以金融管理秩序被普遍认为是洗钱罪侵犯的客体之一。而集中在利用银行等金融系统对犯罪所得的掩饰、隐瞒。尽管在《刑法修正案(六)》颁布以前,理论与实务界都将“行为人是否具有掩饰、隐瞒赃物来源和性质之目的”作为区分《刑法》第349条和第191条的标准,*谢望原:《颠覆传统赃物犯罪基础上的重构——对修改后洗钱犯罪的正确解读及其评价》,《人民司法》2006年第9期。但是谁能完全否认这种标准不是在《刑法》增设了第191条之后为了刻意区分两罪界限而作出的呢?毕竟,单纯从语言表述上理解,很难说《刑法》第349条中窝藏、转移赃物等行为本身不能具有隐瞒赃物性质和来源之目的。
(二)洗钱罪立法初衷与修法违背初衷的矛盾
当然,仅以相关立法足以规制洗钱犯罪来否定《刑法》第191条的存在意义并非没有任何质疑的空间,最有力的反驳当属——类似于集资诈骗罪之于诈骗罪,洗钱罪的设立正是为了重点打击利用银行等金融机构清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的行为,《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的量刑差异便是该打击力度的最好证明。*根据1997年《刑法》颁布伊始的规定,第312条的法定刑确实是最轻的,仅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而第349条的法定刑则分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以及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档次;第191条的法定刑也是最高可达10年有期徒刑。然而,近年来洗钱罪的修订完善过程以及学界对该罪名的认知趋势却与这一颇具说服力的立法初衷发生了矛盾。
近年来《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修正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洗钱的行为方式还包括对非金融领域的利用;*200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给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一)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等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二)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三)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合法”财物的;(四)通过买卖彩票、奖券等方式,协助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五)通过赌博方式,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六)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入境的;(七)通过前述规定以外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上游犯罪范围进行扩增。司法解释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刑法在设立第191条之初对“利用特定行为方式洗钱”的重点打击,现今的《刑法》第191条已然打破了洗钱犯罪必须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壁垒。与此同时,经过2001年和2006年两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订,第191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已在过去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基础上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显然,《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重点打击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打击范围的扩展却大有从有限性向无限性发展之态势。究其原因,则是我国长久以来被国际社会所诟病的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过窄的缺陷。近年来在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认知,即将《刑法》第349条、第312条、第121条之一*由于国际反洗钱框架将资助恐怖主义犯罪也纳入了反洗钱监管体系中,故而,我国将《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第121条之一资助恐怖主义罪也列入广义洗钱罪的范畴。以及第191条视为“广义的洗钱罪”,从而将一切犯罪都纳入到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中。如此,便可在不改动现有立法的情况下实现对上游犯罪的扩容。
司法解释力图将洗钱方式从过去局限于金融领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以及理论上创造的“广义洗钱罪”概念亦在打破《刑法》第191条对上游犯罪的限制。这不禁让人疑惑:洗钱罪究竟是一个个罪,还是一个类罪?若是一个类罪,为何将洗钱犯罪视为一种不限手段与上游犯罪,而仅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为行为特征(广义洗钱罪)的理解,在我国《刑法》初设第191条之时并不存在?至少根据当时的理论与司法实践,即便《刑法》第349条可以理解为涉毒洗钱,也没人会认为《刑法》第312条是洗钱罪。此外,洗钱罪的设立究竟是为了打击“特定方式”清洗“特定犯罪所得”的行为(《刑法》第191条设立之初),还是为了打击利用一切方式清洗“特定犯罪所得”的行为(经过修订后的《刑法》第191条)?抑或是为了打击利用一切方式清洗一切犯罪所得的行为(广义的洗钱罪)?如果是最后一种,其与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312条经过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的修订已更名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其中对行为方式的规定更是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兜底性表述;法定刑也在最初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的基础上新增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档。此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第10条又新增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将我国广义的洗钱罪视为打击清洗一般犯罪所得(第312条)的同时,重点打击对7类特定犯罪所得的清洗(191条),又为何在《刑法》设立第191条之初,第312条的行为方式却被理解为不应具有对赃物来源和性质的隐瞒目的?以上种种困惑不得不让人反思以特别法作为洗钱罪之设立必要性的合理性。在《刑法》设立第191条之初,其立法的本意旨在打击利用金融领域清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的行为。只是,当该种规定与当下的洗钱犯罪情形已然不相符合时,上述打击重点(行为方式和上游犯罪的限制)也就自然成为了《刑法》第191条需要突破的重重障碍。实际上,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又或是理论上广义洗钱罪概念的出现,不过都是在排除适用《刑法》第191条的种种限制,只不过前两者更为直接,而后者相对迂回罢了。然而,这个排除的过程本身难道不是与我国设立洗钱罪时以特定对象、特定行为方式为打击重点的立法初衷相矛盾吗?
(三)洗钱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法》第191条低适用率的矛盾
据学者统计,“1997年至2009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以《刑法》第191条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仅20余件”。*刘伟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司法》2009年第23期。可见,自《刑法》设立第191条洗钱罪后的十年时间内,该法条的实际适用数量可谓寥寥无几。这一情况亦在2012年2月全球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FATF)对中国出具的互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详见下表):*参见Mutual Evaluation 8th Follow-up Report China,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 s/mer/Follow%20Up%20MER%20China.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2月28日。

洗钱类犯罪年定罪数额量刑的人数第312条(可以适用于所有洗钱行为的罪名)200810318176502009106131761720101138318031第191条(针对7种上游犯罪的罪名)20083420095920101214第349条(针对毒赃洗钱的罪名)200859692009567820106190合计3251053562
根据以上统计,如果以“广义洗钱罪概念”来界定我国设立的洗钱罪,那么刑法第312条无疑是我国惩治洗钱犯罪的主力军。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我国长久以来对洗钱犯罪的打击都是通过刑法第312条来实现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存在价值?而如果说刑法第312条的适用很大一部分仍归功于对传统赃物类犯罪的定罪处刑(即对赃物的窝藏、转移、销售),国际意义上的洗钱犯罪仍然有赖于《刑法》第191条的适用,那么第191条如此低的适用率与我国一直声称的严重的洗钱犯罪问题却又实在难以匹配。尽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反洗钱报告中,破获的洗钱案件大有逐年递增的态势,*参见王新:《反洗钱:概念与规范诠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但报告中却微妙地使用了“涉嫌洗钱案件”的表达。如此含糊而概括的表述方式也着实让人难以明辨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适用情况是否确有改善。诚然,导致《刑法》第191条适用率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我国银行等金融系统内部的反洗钱监管尚处于初级阶段,监管经验的相对不足以及效率的相对较低必然会影响洗钱犯罪的查获几率;司法机关在实务操作中为了免去证明特定上游犯罪、特定行为方式,以及行为人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之目的证明责任,而避繁就简的适用《刑法》第312条,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第191条的适用率。单以适用率低去否定洗钱罪的存在必要性亦不客观。但这种“实然”状态与“应然”需求之间的巨大反差,至少为人们重新认知该罪的缘起与发展因由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矛盾现象之原因分析
根据上文论述,《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立法进程确实存在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困惑与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然而,对矛盾的揭示并非否认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必要性,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引发矛盾的原因而发现作用于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的真正因素。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看似是国内立法的自主选择,但该选择的出现又却是源于“国际要求”这一更深层次的因素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视野重新置于全球化的国际反洗钱运动当中。
(一)全球化——洗钱罪立法必要性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跨境流动,洗钱犯罪绝不可能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与打击的重点。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开放的金融体系为各国间的资本流通提供了便利;网络支付平台在允许人们进行跨地域资本操作的同时,也让国家的货币管制形同虚设;而电话银行与网络银行对传统面对面交易模式的突破,更为非账户持有者进行账户交易操作提供了可能。无疑,全球化对洗钱的意义在于清洗赃款的具体操作与赃款的流转轨迹均可跨国实现。若用更为直观的方式表达,便是洗钱者完全可以将其在A国犯罪所得的赃款转移至其在B国开设的账户,再在C国将其兑换成现金消费后最终将交易所得转运至D国。如此一来,一国便再难仅凭一己之力实现对洗钱犯罪的打击。
尽管一国对国内洗钱犯罪的打击有赖于本国相关立法与政策的执行,但是对跨国境洗钱犯罪的有效治理却唯有站在国际的层面才能够实现。*参见Vito Tanzi,“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in Intarnatimel Monetary Fund,IMF Working Paper 96/55,washington DC,1996,p.11.而类似于两国间就某项犯罪开展刑事司法互助须以双重犯罪为前提,普遍化的国际反洗钱刑事司法互助则须以各国打击洗钱犯罪的共识为前提。这一共识,即是洗钱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入罪化的本质所在,而这也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维也纳公约》首次要求各缔约国将清洗毒赃行为入罪化的初衷。这一点,在美国代表团对《维也纳公约》的评价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代表团曾如此赞许该公约在引渡方面的卓越贡献——“尽管毒品犯罪一直被公认为是可引渡的犯罪,但是清洗毒赃犯罪之引渡问题在过去却并未受到普遍认可。公约对该种行为犯罪化的规定,无疑促成了国际社会将清洗毒赃犯罪纳入可引渡犯罪的共识”。*Reproduced in Gilmore,W(ed.),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combat money launder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20.虽然1988年的《维也纳公约》对洗钱犯罪的规定还局限于涉毒洗钱,但自《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巴勒莫公约》)将洗钱作为独立犯罪予以打击以来,公约对洗钱行为入罪化的根本意义却未曾改变。
如此,便能够理解我国1997年《刑法》在已有第312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以及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情况下,仍然增设第191条洗钱罪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我国《刑法》增设第191条洗钱罪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国内现有立法适用的补充,而在于设立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共性”的洗钱罪,以为我国将来与各国顺利开展具体的反洗钱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基础与前提。换言之,正是基于全球化的作用,世界各国在惩治洗钱犯罪中彼此关联、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迫使具有一定“共性”的洗钱罪出现在了各国刑法之中。
(二)公约义务——洗钱罪立法标准
全球化无疑是引发世界各国设立洗钱罪的源动力,而如何将该股源动力转化为具有共性的标准以满足未来普遍性的刑事司法互助需求,则不得不诉诸于国际公约。
1988年《维也纳公约》作为联合国颁布的第一个涉及反洗钱的公约,虽受限于涉毒洗钱犯罪,却为后续公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与模板。其中,该公约对洗钱行为方式的规定便基本被后续相关公约吸收与采纳。根据《维也纳公约》的规定,洗钱方式主要包括七种——转换、转让、掩饰、隐瞒、获取、占有和使用。其中,转换、转让、掩饰、隐瞒四种行为方式为强制性要求,成员国必须将其纳入到洗钱罪的规定中;而获取、占有、使用三种行为方式则属于选择性要求,即当有违本国宪法原则或法律制度基本概念时,缔约国可以选择不将这三种行为方式入罪。此后,“上游犯罪”的概念开始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于2000年颁布的《巴勒莫公约》中,洗钱犯罪的适用对象也开始被明确拓展至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腐败犯罪、妨害司法犯罪以及最高刑为四年以上自由刑的公约界定为严重的犯罪。*《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6条第2款(b)规定各缔约国应将公约第2条所界定的所有严重犯罪、公约第5条(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第8条(腐败犯罪)、第23条(妨害司法犯罪)确立的犯罪列为上游犯罪。与此同时,该公约亦允许各成员国依照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排除自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虽然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亦对反洗钱有所涉及,但是该公约对洗钱入罪化的规定却基本是对《巴勒莫公约》相关规定的照搬。*参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3条,《巴勒莫公约》第6条。故而,仅就入罪化而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要求。*即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4条创新性的提出将窝赃行为入罪化的要求,也因公约所使用的“缔约国考虑采纳”之表述而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性。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于1999年开放供各国签署的另一个并未直接涉及洗钱犯罪的公约——《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却因资助恐怖主义犯罪与洗钱犯罪之密切的关联而被纳入了国际反洗钱框架中。
反观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从设立到修正的过程不难发现,我国对洗钱罪的修正过程即便不是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全吻合,也基本是按照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不断完善与发展。而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进程既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过程,也是公约制约与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国《刑法》第191条的立法进程与其设立初衷间的矛盾,所生疑惑便可释然。固然,在我国设立《刑法》第191条之初,将利用金融领域清洗特定犯罪所得作为打击重点的洗钱罪的设置,与当时的国际反洗钱需求基本吻合。然而,伴随着国际反洗钱运动的发展与推进,国际社会扩张反洗钱体系适用范围之需求却在不断通过公约传递给各缔约国。换言之,我国履行公约义务不断突破已有限制以拓宽洗钱罪适用范围的过程,亦是我国不断修正国内立法以迎合国际反洗钱需求的过程。
(三)国际组织经济制裁——洗钱罪立法的保障力
即便是国际公约,其对各国刑事立法的影响也仅依赖于各缔约国对公约义务履行之自觉态度。换言之,如果各缔约国拒绝履行相关义务,公约也并不存在任何强制措施迫使缔约国遵守。不得不承认,单从公约对一国刑事立法的影响力来看,纵使形式上不存在,其实质上也仍然给各国留下了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公约影响的选择空间。只不过,该种刑事立法的选择空间在国际反洗钱组织的作用下变得不复存在。
成立于1989年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无疑是目前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反洗钱组织。其制定的《FATF 40条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借鉴《维也纳公约》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银行系统洗钱的声明》(以下简称《巴塞尔声明》)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改进国家法律制度”、“完善国家金融系统”、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三大领域的规定,为确保国际反洗钱举措的有效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FATF的《建议》甚至不具有如同国际公约一般的法律约束力。*参见Sherman,T,“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Combat Money Laundering: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in MacQueen,H L(ed.),supra,note 7,p.18.即便《建议》中的诸多内容在相关公约中有所体现,其自身效力的产生却仍依赖各国政府对《建议》的认可及实施自愿。然而,FATF通过“自评”、“互评”、以及“后续跟进举措”而构建的一整套“经济制裁机制”却为约束各成员国按照《建议》要求实施具体反洗钱举措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评”与“互评”,均是对成员国具体实施《建议》情况的评价。只不过“自评”的主体是该成员国本身,而“互评”的主体则是除本国以外的其他FATF成员国。而“后续跟进举措”则是指经过阶段性互评之后,FATF将继续对被评估国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与检验。通常,被评估国会被要求在‘互评’完成的两年后向FATF递交一份报告以呈述该国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情况。如果FATF认为问题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便会进一步缩短报告周期以敦促该国加大完善力度。*参见“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Annual Report 1999-2000”,Paris,pp.20-22.然而,如果成员国现有反洗钱举措与《建议》之要求差距甚大且经过上述步骤仍无法及时有效的改进,FATF将会采取更为严厉的跟进措施——“经济制裁”,即FATF会向其他成员国、或观察国发布声明,以要求各国谨慎处理、或者拒绝处理与上述问题国家间的交易往来。更有甚者,FATF会中止甚至取消对应国家在FATF中的成员国地位。*参见“Third Round of AML/CEF Mutual Evaluations: Process and Procedures(October 2009)”,Paris,FATF p.14.对于上述经济制裁的客观效果,1995-1996年间发生于土耳其与FATF之间的对垒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当时的土耳其因未将洗钱行为入罪化等一系列问题而被FATF列为严重不符合《建议》标准的国家。在先后两次敦促土耳其采取相应改进措施未果后,FATF最终于1996年9月19日向其他各成员国发布声明以限制与土耳其的经济往来。在强大的经济制约下,土耳其“终于”在同年11月迅速制定并颁布了《洗钱犯罪预防法》。不难发现,FATF所构建的“经济制裁机制”极大地弥补了《建议》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缺陷,而“经济制裁”的存在甚至使FATF的《建议》在实质上拥有比公约更强大的约束力。
回到对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要求,根据《建议》的最新规定,FATF要求各成员国应当按照《维也纳公约》以及《巴勒莫公约》的规定完成洗钱行为的入罪化。*参见‘The FATF Recommendation’ Feb.2012,Recommendation3,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 /recommendations/pdfs/FATF_Recommendations.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15日。与此同时,根据FATF对上游犯罪的解释,其仍然希望各国尽可能地将上游犯罪拓展至一切犯罪或一切严重犯罪。即便不能实现,也至少要满足《维也纳公约》以及《巴勒莫公约》规定的犯罪类型。*参见‘The FATF Recommendation’ Feb.2012,Interpretive Note to Recommendation 3(Money Laundering Offence),Article 2,3.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commendations/pdfs /FATF_Recommendations.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15日。而根据两大公约的最低标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当包括:毒品犯罪、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腐败犯罪、妨害司法犯罪以及最高刑在四年以上自由刑的犯罪。显然,如果仅将我国的洗钱罪理解为《刑法》第191条,其根本无法达到FATF提出的最低标准。也正因如此,FATF在2007年对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做出的第一份评估报告中,便将我国的洗钱罪界定为《刑法》第191条、第312条与第349条的集合体,*参见“First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 on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mbat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th June 2007). P. 22.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 reports/mer/MER%20China%20full.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2月28日。从而成功地将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拓广至一切犯罪。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近年来倡导的“广义洗钱罪概念”不谋而合。此处,笔者并不想考究到底是学界对广义洗钱罪概念的创造引发了FATF的该种界定,还是FATF的报告结论左右了学界对我国洗钱罪的认识趋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拒绝FATF对我国洗钱罪界定的同时,又不对《刑法》第191条进行大幅度的更改,我国也极有可能面临当年土耳其所招致的“经济制裁”。实际上,FATF对我国进行评估的当时,亦指出了《刑法》第191条与第349条,第312条之间在规定内容上的重复和逻辑矛盾。*同前注[27]。只不过,相较于顺利实现将我国洗钱罪适用于一切犯罪之目的,这些矛盾与冲突对FATF而言显然并不足以影响我国反洗钱义务的履行。如此看来,近年来不顾《刑法》第312条、第349条,以及第191条之立法渊源与逻辑关系而强行将其融合为国际意义上的洗钱罪之认识趋势,亦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只是,对该种合理性的理解不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内部体系,而应诉诸于国际组织的外在制约。由此看来,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进程亦是在国际组织强大经济制约的威慑下形成的。
三、对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矛盾现象的反思
(一)对洗钱罪立法进程的客观认知
通过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现象及原因分析不难发现,不断调整国内立法以迎合国际反洗钱要求才是引导我国洗钱罪从设立到修正的根本动力所在。在此背景之下,对我国洗钱罪的存在必要性、立法轨迹,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之把握,不应脱离全球化背景及国际反洗钱体系。
首先,对我国洗钱罪存在必要性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洗钱行为侵害金融领域、妨碍司法活动等社会危害性。事实上,创设具有一定“共性”的罪名以为将来大规模开展全球反洗钱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双重犯罪”之前提保障,才是各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设立洗钱罪的直接目的所在。诚然,我国《刑法》第349条和第312条确实在行惩治洗钱犯罪之“实”,但我国却仍然需要按照公约规定增设具有“国际共性”的洗钱罪(《刑法》第191条)以确保惩治洗钱犯罪之“形”。而《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在适用率上的巨大反差亦是对上述“形”与“实”的一种有力证明。
其次,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轨迹的认知不应受制于该罪以特定上游犯罪为打击对象并以金融领域为打击重点的立法初衷。洗钱罪立法缘起于国际反洗钱运动的客观现实,意味着国际反洗钱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走势。我国洗钱罪设立之初的立法定位因其与当时反洗钱政策的吻合而具有合理性,我国突破既有限定以拓宽洗钱罪的打击范围亦因其与当下的国际反洗钱要求的一致而具有正当性。实际上,洗钱罪修法路径与立法初衷的违背过程恰恰是我国反洗钱立法与国际反洗钱要求相统一的过程。后者是洗钱罪发展演变之“本”,前者则是洗钱罪发展演变之“末”。
再次,对我国洗钱罪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不应固守公约或国际组织的既有规定。尽管,国际反洗钱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洗钱罪的修法方向。但是,公约及国际组织规定的制定亦受制于国际反洗钱宗旨。换言之,唯有立足于国际反洗钱之根本,才能前瞻性地预见洗钱罪的发展方向,而非被动地追随国际反洗钱要求亦步亦趋地进行国内立法修正。根据全球反洗钱运动缘起之动机(“追缴犯罪所得以断犯罪动机”)、兴起之土壤(“全球化背景下赃款跨境自由流转”)、近年来发展之态势(“不断扩大反洗钱监管领域并积极扩容上游犯罪范围”),不难发现,实现对跨境赃款追缴的全球性合作才是国际反洗钱体系产生与演变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反洗钱标准是影响各国洗钱罪发展方向之“表”,反洗钱根本才是左右各国洗钱罪修正趋势之“里”。
(二)对立法所受国际影响的理性应对
诚然,我国洗钱罪从设立到修正均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且该种影响与制约甚至超越了本国立法与修法的内在需求,而一度成为左右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的主导。然而,国际社会对我国立法自主性的干预却并不意味着我国对洗钱犯罪的刑事规制只能机械地履行公约义务并践行国际反洗钱标准。事实上,相较于对国际反洗钱规范的形式解读与硬性吻合,全局性地把握“国际反洗钱宗旨”、“国际反洗钱标准”,以及“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更有助于合理平衡我国立法自主性与国际社会的干预,并理性应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规范与国际反洗钱要求间存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
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进程,即是我国在“本国立法及修法空间”范围内,不断按照“国际反洗钱标准”调整现有法律以服务于“国际反洗钱宗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际反洗钱标准”是形式要求,“国际反洗钱宗旨”才是本质目的,而“我国的立法及修法空间”则是将上述形式要求转变为本质目的的实现路径。换言之,唯有经过各国的立法与修法,国际反洗钱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其目标与价值。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社会制约与影响我国洗钱罪立法的过程也恰恰是我国参与并利用全球犯罪治理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则是影响一国对反洗钱国际司法合作配合与参与程度的关键因素。例如,我国若固守《刑法》第191条对上游犯罪种类的既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则不利于我国借助现有国际反洗钱合作机制对规定种类以外的其他严重犯罪进行跨境追赃。因此,对我国立法自主性的把握应立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立法与修法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国内规范与国际反洗钱标准“形式上”的一致性。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立法与国际反洗钱标准的统一度越高,我国对全球反洗钱追赃机制的参与及利用程度就越高。另一方面,在我国立法与修法空间不足、甚至不允许的情形下,则应当立足于国际反洗钱体系实现跨境追赃国际合作之根本,通过寻求其他路径解决我国因立法差异而造成的弊端以达到与国际反洗钱标准“实质上”的一致,从而避免因追求与国际标准形式上的统一而引发国内立法或司法的矛盾与混乱。毕竟,国际公约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方式即便是出于扩大公约适用范围之需求,亦在无形中为各国自主构建立法规范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三)对我国刑事立法未来走向的有限预测
从某种意义而言,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进程不过是我国刑事立法权受到国际影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伴随着《维也纳公约》、《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巴勒莫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继颁布,以跨国犯罪为主要打击对象,以国际条约和区域条约为打击依据,并以国际组织的相关举措为打击保障的全球犯罪治理体制(the regime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crime)*参见Valsamis Mitsilegas,Peter Alldridge and Leonidas Cheliotis,Globalisation,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Hart Publishing,2015,P.153.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该体制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唯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对跨国犯罪的有效打击”。*参见Neil Boister,An Introduction to Transnational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因此,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司法互助以联合全球力量打击“共同敌人”则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国家责任。事实上,不仅仅是洗钱犯罪,对恐怖犯罪的规制,对贪腐犯罪的打击,以及对有组织犯罪的治理都属于全球犯罪治理体制的内容。这便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一国刑事立法的影响与介入亦将延伸至上述各个领域,我国刑法典中也将有更多罪名的设立或修正并非基于本国适用之需要,而是为了配合国际打击之需求。固然,对洗钱罪立法进程的分析,因其立足于特定的国际反洗钱规范及反洗钱保障举措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国际制约因素的作用原理及应对方式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换言之,作为全球犯罪治理体制下国际社会干预国内立法的缩影,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进程无疑为预测我国刑事立法可能受到的其他类似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与借鉴。不可否认,如何根据国际犯罪治理机制的需求修正国内现有法律,并在协调国内刑法规范的同时,真正提高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参与度,不仅仅是洗钱罪研究的重点所在,其还将成为腐败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共同目标。
(责任编辑:操宏均)
Analysis on the Paradoxes dur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in China
ZHOUJinyi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icle 191,which is about money laundering in China Criminal Code,several paradoxe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verlap with other relevant articles,amendments derivation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and disharmony between the seriousness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its seldom practical judicial application come into being.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ose contradictions,basing o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nti-money laundering process is necessary.Actually,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oblig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l play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in China.As a result,it is essential to consider the international anti-money laundering framework while discussing the evolu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legislation.In addition,the criminaliza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also acts as a kind of epitome revealing how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have influenced and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domestic criminal legislative power.
Key Words:Money Laundering;Criminalization Process;Paradoxe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Zhou Jinyi,Ph.D.Candidate at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6)02-0118-11
作者简介:周锦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