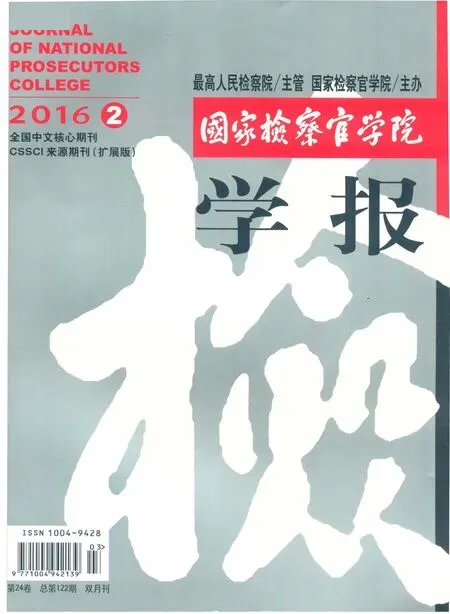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破解
李明蓉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 福州 350013)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破解
李明蓉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福州350013)
摘要:口供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重要证据。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性决定了其诉讼证明容易依赖口供,进而威胁口供自愿性,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要破解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应当从制度上增加证据的来源渠道,设立特殊的证明制度和规则降低证明难度,并提供其他必需的条件支持,提高口供自愿性,实现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口供口供依赖贪污贿赂犯罪口供自愿性证明规则
相对于其他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证明对口供的依赖性更强。口供依赖既会影响口供的自愿性,也给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带来了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承认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人权保障,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人权保障有不同的理解。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展开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当区别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取得和使用,采取合适的制度设置降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依赖
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使得口供的证据价值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明显,案件办理在客观上较为依赖口供。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的重要作用
第一,口供是重要的定罪证据。贿赂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其证据结构中不能没有口供,如果受贿人始终不认罪,也没有行贿人的口供或证言,就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笔者组织了一个课题小组访谈了将近150位法官、检察官、律师,95.7%的受访者都认为口供在贿赂案件中很重要。其中62.6%的受访者认为口供在贿赂犯罪案件中非常重要,只有1位检察官和5位律师认为口供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的作用一般,无人认为口供在贿赂犯罪案件中不重要。对于贿赂犯罪的认定来说,口供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相对于贿赂犯罪,口供在贪污犯罪中的作用较小,因为贪污犯罪案件的书证较多,但该种案件在主观罪过、赃款去向、赃款用途、往来账目走向等问题上也需要口供加以证明。具体而言,贪污犯罪共同犯罪和群体性、关联性犯罪多,证明共同犯罪故意、内部分工等对口供的需求较大。随着职责分工不断细化及内部制约的加强,一些行业个体作案难度加大,出现了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倾向于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网进行贪污贿赂犯罪。犯罪人既有一把手、经办人,又有中间人,比如共同贪污、套取医保、新农合补偿款等类案件,就是多人合作、细化分工的共同犯罪。而认定贪污罪时,在证明资金不正当流向的证据中,书证占主要部分,但要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占有财物的主观意图,口供则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实践情况来看,口供在证明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方面,有着其他间接证据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即其他证据,不管是证人证言,还是物证,都很难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转移公款时的心理状态。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最清楚,当时为何有如此行为,又是在怎样的主观意图下有如此行为。而行为当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很可能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的界分。因此,尽管贪污犯罪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从总体上而言不及贿赂犯罪对口供的依赖程度高,但口供在贪污犯罪的证明结构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整个证明犯罪的证据结构中,贪污贿赂犯罪对口供的依赖度很高。
第二,口供是重要的量刑证据。刑罚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被告人的悔罪程度进行量刑,而口供是判断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坏的标准之一,因此,口供所反映出的被告人认罪与否以及在刑事诉讼哪个阶段认罪与量刑轻重有着一定的联系。台湾学者认为,“被告于犯罪后的态度足于显示其可责性与危险性,被告在犯罪行为后的态度与行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刑事裁量事实。”*刘邦绣:《认罪与刑罚》,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9页。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是判断被告人悔罪表现、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认识以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重要根据。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被告人通过口供表达出的是否认罪的意愿对于量刑有着明显的影响。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即是口供影响量刑的典型体现。从实务来看,被告人认罪与否对于量刑轻重存在重要影响。*笔者曾访谈了29位刑事法官,绝大多数刑事法官认为有无认罪供述对于量刑是有影响的。
(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性的成因
贪污贿赂犯罪的隐秘性、职权性、反侦查性强等特征,使得口供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上贪污贿赂犯罪的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需要,共同形成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存在高度依赖性的状况。
第一,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的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要件之一,但有些行政审批事项没有行贿受贿也会正常得到审批,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正常履行职务所带来的利益客观上可能是相同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利用职务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对应关系也难以证明。*詹复亮:《反贪侦查热点与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根据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因果关系。实务中的做法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口供中承认是收取贿赂后为对方谋取利益的,不管行贿方的利益是否原本就是应得的,都视为受贿方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二,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赃物去向的证明。首先,赃款赃物的去向难以查明。贪污贿赂犯罪智能性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犯罪之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就设计好了如何不被发现、如何规避侦查逃脱惩处的对策。其中,赃款的转移、隐匿,犯罪行为被发现后躲避、逃逸是最惯常的办法。贪污贿赂犯罪可能是一家人都参与的,关系的紧密容易形成攻守同盟,阻碍案件侦查,加大犯罪证明难度。有时赃款赃物被转移到国外,或者被转移至家人、亲朋的名下,除非相关人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说明,否则证明难度很大。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常以贪污受贿的款项用于公务,没有非法占有作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抗辩理由。在我国,人情关系也是公务活动摆脱不开的影响,即使在公务中,为地方、单位争取项目、资金甚至争取荣誉也要请客送礼。因此,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有时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所得赃款赃物去向的掩护,如果检察官无法证明这种情况的真假,律师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法官认为事实真伪难辨时,有可能对被告人从轻发落,甚至驳回公诉人的指控。因此,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检察机关经常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调查赃款赃物确实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口供自然就是首选证据。再次,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要件的证明困难。违反规定挪用公款是“归个人使用”还是归单位使用与是否构成挪用罪密切相关,而归个人使用很难由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现出来,证明难度自然很大。
第三,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都以一定的数额为构成条件,贪污贿赂达到一定数额才是刑法打击的对象。这就形成了在最低数额线下的贪污贿赂行为不是犯罪的不利结果,“立法上为腐败分子预定了一个不小的行为空间,司法实践中的刚性掌握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的贿赂贪污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犯罪数额是贪污贿赂案件必须明确而常常又是最难以明确的问题。具体来说,时间久远的贪污受贿数额的证明以及多笔贪污贿赂数额的证明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明难点。尤其在受贿案件中,“一对一”的证明困境体现在数额时更为典型,确定贿赂数额过于依赖口供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些证明难点往往依赖口供加以证明,再以口供提供的线索查找相应的细节证据印证。只有这样,调查证明的难题才有可能会迎刃而解。
第四,人情往来与非法收入的区别。据统计,有60%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年节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中国这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在重要节日或者事件上送钱物,在公众看来合乎情理,这就给对行为人行为的定性增加了难度。同时,行贿与受贿双方的犯罪手段也由原来的直接送收财物向事后受贿、海外受贿、以借为名、以租为名、委托理财等更为隐蔽的受贿形式转变。*李辰:《受贿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一般情况下,对于是人情往来还是非法收入的界定可以根据双方是否有权力交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等作为判断依据,但在一些灰色地带,有认罪口供作为证据仍然是办案人员增强内心确信的重要方式,检察人员也才能够有信心说服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可见,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中,口供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口供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
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性的负面效应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中,口供在证明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据结构中占有明显的比重。若没有措施降低口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体系中的构成份量,必然导致高度的口供依赖。一旦对口供形成一种制度依赖,口供中心主义便会产生,违法获取口供、刑讯逼供等问题自然难以避免。
(一)口供依赖性高与口供自愿性低成正向相关性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结果,是侦查机关千方百计要获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进而可能威胁口供自愿性。口供依赖性高,意味着侦查人员缺乏有效的措施获取刑事诉讼证明所需要的证据,于是,在讯问场所的封闭空间里,利用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强取口供导致口供丧失自愿性就是必然。口供依赖性越高,非法获取口供的概率越高,口供自愿性就越低。为避免对口供的过度依赖,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要努力走精细化初查基础上的有效侦查的道路。但实践中,受制于各种条件,绝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的重要内容,仍是获取被调查对象的口供,再通过口供提供的信息去调查更多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尤其是了解办案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他贿赂事实或其他人的贿赂事实。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办案的目的也同样是能够更有把握地获取被调查对象的认罪口供以查办更多的贿赂犯罪案件,尤其是多人向一人行贿或一人向多人行贿的窝串案。若规范不足、制约失效,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强烈意愿很容易转化为强迫获取认罪口供的行动,口供自愿性自然难以得到保证,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立法目的都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口供的结构性依赖: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中心主义的温床
一般而言,贿赂犯罪行为通常都单独进行,没有第三人在场,口供对于复原犯罪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贿赂犯罪“在证据方面形成了能够证明犯罪的直接证据少、间接证据隐秘、主观罪过的判定依赖口供的特点。”“在贿赂案件中,仅凭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来定案存在困难。而口供的重组功能,恰好能够满足侦查中对贿赂案件认定的需要,突破因时间和技术带来的侦破瓶颈,加速案件的侦破进程。”*孙陆军、李建丽:《贿赂案件对口供的依赖性分析》,《群文天地》2012年第12期(下)。所谓的口供重组功能是指口供因其反映案件事实全面性、直接性的特点,具有将间接证据的碎片重组而还原案件事实的功能,能够描绘出犯罪行为的全部内容。据此,贿赂犯罪形成了对口供的结构性依赖。所谓结构性口供依赖是指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构成内含的直接证据只有口供,*这里将非法行为人的言词证据都定性为口供,如尽管行贿人、买卖毒品人员的行为有可能不构成犯罪,但他们的言词证据与其他没有涉案的纯粹证人的证词是不一样的,把它视同口供更能反映它的特性。客观上形成案件的诉讼证明和判决依据高度依赖口供的一种刑事诉讼状态。特定类型的犯罪指对合性、隐秘性强的犯罪,如贿赂犯罪、毒品犯罪。若某类犯罪案件确实存在结构性口供依赖,则各办案部门必然高度重视口供,甚至容易形成口供中心主义。其表现就是:过度重视口供,忽视其他证据,进而违背程序规制,违法取供;以有罪推定思想看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客体地位,忽视人权保障。
结构性口供依赖是特定类型犯罪内含的,仅依靠刑事诉讼法的严格要求、办案人员的认识到位、能力水平提高等外部因素,无法解决这类案件可能存在的口供中心主义问题。只有依靠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足够的条件支持,增加这类案件的证据来源,同时降低证明难度才有可能解决结构性口供依赖的问题。
(三)口供依赖导致实务中的不规范应对:隐性认罪交易
口供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有着直接、完整、全面的证明价值。至今为止,口供仍然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其作用难以替代。“有时候只有透过讯问,才能侦破刑案,无论有没有什么科学办案的辅助,或者警员、私家侦探技巧如何高超。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没办法讯问嫌犯,侦查结果就大打折扣。”*[美]佛瑞德·英鲍等:《刑事侦讯与自白》,高忠义译,商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4页。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口供都是重要证据,讯问作为一种侦查方法,其在侦查中获取口供的作用无法被取代,而要想取得讯问的成功,说服被告人自白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为了获取自愿性高的认罪口供,办案人员经常采取答应可以改变强制措施或可以从宽处理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从而顺利推进刑事侦查,并有可能因此发现其他相关案件。但客观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和办案人员承诺,并不具备平等协商的性质。办案人员承诺某些优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认罪口供,这具备交易的特征。但这种交易是实务部门在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自发行为,不具有规范性,且大多数又在侦查阶段使用,不为外界所知,其后续可操作性都存在很大问题。基于其隐匿性以及缺乏应有的规则支持,本文称之为隐性认罪交易。在现实条件下,办案机关既要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回应国家、社会对反腐败问题的关切,同时又面临着技术侦查和公共信息来源缺乏、贪污贿赂犯罪证据稀缺、口供依赖严重的困境。办案部门从履行自身职责必要性的角度出发,选择进行隐性认罪交易,是实务部门解决问题的务实应对措施。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隐性认罪交易存在着秘密性、不规范、交易结果可能无法实现等问题。
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破解路径
破除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制度性依赖,是刑事司法制度要不断努力的一个重大方向。在当前条件下,应当考虑从完善侦查机制入手,加大对侦查权的约束,扩展证据来源,同时适度调整证明规则,鼓励犯罪嫌疑人自愿做出自白,降低证明难度。
(一)约束侦查权与增加证据来源
设置严谨细致的程序,真正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约束,是保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自愿性的基础。同时,增加证据来源,减轻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依赖,进而降低侦查人员强求口供的意愿,确保口供自愿性。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还应设置程序性规则,因为严谨、细化程序可以真正执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有效地将不具有自愿性的口供排除于定罪体系之外。
第一,在庭前会议中明确设置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首先,明确排除非法口供的要求是启动庭前程序的法定理由。控辩双方只要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要求,法官即应安排庭前会议。其次,明确参加人员。除了公诉人、辩护人外,被告人也应该参加庭前会议,提出理由,提供证据,参与讨论。再次,明确庭前会议决定对排除非法口供的效力。庭前会议应有书面记录,各方签字,法院应该以形成的结论作出书面决定,达成共识的予以明确,不再进入庭审。认为口供自愿性存在问题的,应在庭前会议时播放有疑义时间段的录音录像,以期达成共识。录音录像能够明确证明口供自愿性或明确证明没有自愿性的,法官都有权作出是否排除口供的决定。已播放录音录像的,庭审时不再播放,控辩双方对于法官的庭前决定不服的,在庭审时仍可以进一步阐明理由。
第二,设立专门的非法证据排除庭审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凸显约束公权、保障私权价值的重要载体,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规定,但都规定在证据一章,在庭审中却没有细化的可操作的程序。虽然法律规定在侦查、起诉、审判中都可以排除非法证据,但正式、规范、公开的庭审程序仍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主要的实质性载体,庭审程序应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设计专门的程序。第一,启动。庭审正式开始后,法官应该专门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请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方提出请求并且阐明理由和初步证据的,法官应该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官也可以依职权决定进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第二,审查及证据展示。庭审调查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况,公诉人有责任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口供合法性。庭前没有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的,庭审时应该播放,但可以播放被告人认为侦查人员有非法取供行为的时间段的录音录像。第三,侦查人员出庭。只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侦查人员都应当出庭作证说明情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本质就是调查、审查侦查行为合法性,在侦查行为遭到质疑时,侦查人员有责任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权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缺乏外部力量的介入制约是职务犯罪案件刑事诉讼制度倍受外界质疑的重要原因,因此,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在口供合法性受质疑时,更应该出庭说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最后,决定。非法证据排除庭审程序进行之后,法官应该当场作出决定。为了庭审的顺畅进行,决定可以口头作出,在判决书中再正式体现。为避免庭审过于冗长,非法证据排除的决定可以复议,但不允许上诉。
2.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贯彻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在讯问时高度封闭的空间内,相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情况总令人担忧。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初衷就是防止刑讯逼供以保障人权,因为它以声音、图像的方式记录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全程记录讯问过程,可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也直接、完整地记载了被取证对象所陈述的内容。因此,完整、真实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弥补沉默权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位,在确保取证行为具备合法性时,也保证口供自愿性。
首先,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技术性外部制约监督力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和支持,如果能够真正落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讯问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的自愿性和讯问的合法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其次,可以通过实时的内部监督和事后的第三方监督完善录音录像制度。职务犯罪侦查讯问时,检察技术部门的人员负责录音录像,审录分离,确保录音录像的完整、真实、清晰。加上纪检监察部门的经常性检查、监督及事后复查,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有效执行。再次,可以设立事后第三方监督机制,以弥补缺乏第三方同步监督的不足,解决同步录音录像因内部操作被质疑的问题。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第三方人员参加(如律师、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抽查检察机关所侦查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录音录像,既验证口供的自愿性以取得社会公信力,提高司法威信,又可以督促检察机关严格依法规范地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技术性外部监督、内部制约、事后第三方监督等机制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对于讯问行为的全程、同步、动态监控,基本上能满足保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自愿性的要求。
3.检察机关信息查询机制的建立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信息查询能力严重不足,因为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无障碍查询的权力,检察机关在查询涉及贪污腐败犯罪的信息资料时,经常遭遇部门保护、地方保护或不负责任的互相推诿等难题,尤其是基层检察院遭遇的查询难题更多。发现和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信息的大量需求和信息来源不足的矛盾,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建立财产实名和公开制度以切断官员以职权谋私利的“发财路”。官员申报的财产信息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证据来源,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真正确立和落实,将使官员的财产收入公开化、固定化,所申报的财产可以成为官员所拥有合法财产的证据。贪污贿赂所得的财产见不得阳光,就丧失了成为合法财产的借口和途径。其次,立法明确授予检察机关顺畅查询公共信息和涉案公职人员财产、资金等信息的权力。公共信息查询关注的是涉及职务犯罪的基础性信息,即单位基本信息、人事信息、资产信息、出行信息、通讯信息等。再次,检察机关还应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办案信息系统,即“收集、整合、运用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有关的,能引发启动侦查、有助于侦查破案工作开展和认定犯罪案件信息,以启动、支撑和辅助破案、定案的办案系统。”*陈波:《职务犯罪信息化侦查实战操作》,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除了举报类信息的收集和研判外,检察机关在办理的各类案件中,都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的人员信息、案件信息,建立职务犯罪信息情报系统和管理使用制度,统一收集、管理、运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可能涉及职务犯罪或其他案件的信息,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案件线索以及在逃人员、行贿人员等侦查信息,由此可以解决各办案部门分散办案,相关信息因与本案无关而弃之不管的信息浪费现象。
4.技术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
新刑诉法规定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但规定内容粗犷不细致,且缺乏操作程序,实务中难以运用。事实上,新法实施之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几乎没有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取证的,与立法初衷相差较远。*笔者访谈了检察机关从事自侦工作的40多人,并做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是技术侦查措施只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行踪,用于取证的几乎没有。因此,改变技术侦查制度以秘密规定来规范的现状和习惯性做法,以法律规范取代政策规制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既要做到有效地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取证,增加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来源,减少口供依赖;又要规范合理地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从制度上杜绝滥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可能,防止侵犯个人隐私及对社会和个人的其他伤害。应该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明确初查时就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有效地增加证据来源。同时,将技术侦查法治化,解决技术侦查缺乏操作程序的问题,让技术侦查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真正发挥作用,既增加证据来源,也对腐败官员形成有效威慑。
(二)证明机制及鼓励自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证明机制对于口供的定位,关系到口供在诉讼中的定位和价值,关系到口供与各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认罪口供与控方有着正向的诉讼利益关系,与被告方则有着反向的诉讼利益关系,而且对双方诉讼利益影响都很大。因此,控方急于获取认罪口供,被告人则千方百计否认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天然弱势地位,侦查人员极易使用违法手段强迫获取认罪口供。可见,完善证明机制,就要改变目前认罪口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构成体系中分量过重的问题。除了增加证据来源之外,降低证明难度,才能真正达到降低口供依赖、确保口供自愿性与惩罚贪污贿赂犯罪并重的目的。
1.设立习惯排除规则
习惯排除规则是指不得以任何商业、行业、职业的惯例作为自己收受财物行为的辩护理由,也就是说公务人员履行职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相关人员的财物。香港地区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第19条规定:“在有关本条例所载罪项之任何诉讼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条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专业、行业、职业或业务之惯例,而作为辩护理由。”新加坡1985年《防止贪污法》第22条规定:“在依据本法进行的任何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不得接受表明本法提及的任何报酬是任何职业、贸易、使命或传唤方面惯例的证据。”马来西亚、文莱、澳大利亚、巴哈马等国的反贪单行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巩富文:《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我国是一个讲究人情往来的国家,贪污腐败犯罪分子经常以此为借口,为自己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辩解。而司法实务中,也确实存在将认定为人情往来的财物从贿赂总额中扣除的做法,给贪污贿赂犯罪留下了狡辩的借口,也给司法认定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更给民众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惑。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习惯排除规则,明确公务人员可为和不可为的界线所在,去除不必要的模糊空间,既让人知晓守法的内容,也为执法明确依据。
2.明确贿赂推定规则
所谓推定,“是指基于事物之间的普遍共生关系,或者说是常态的因果联系,由基础事实推出待证事实(又称推定事实)的一种证明规则。”*樊崇义、冯举:《推定若干问题研究》,龙宗智主编:《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所谓贿赂推定,是指在被控涉嫌贿赂犯罪的诉讼中,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收取、接受或者支付、给予了对方财物,除非被告人提供反证,否则就推定该被收受的财物为贿赂财物的一项证据制度。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案件的特有的一项证据制度。”*阮传胜:《论贿赂推定及其适用》,《河北法学》2004年第11期。对于贿赂这种对合性犯罪来说,贿赂推定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贿赂犯罪事实的证明难度,尤其是关于贿赂犯罪的主观故意、目的的证明,若无推定制度,就几乎只能根据口供才能证明。贿赂推定可以有效破解贪污贿赂犯罪证据收集的困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契合当前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彭新林:《腐败犯罪案件程序问题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4页。推定规则通常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推定的证明标准肯定低于一般的证明,通常情况下,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依经验法则就证明了推定事实的存在,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相反情况,因此允许提出反驳的证明。第二,因为推定是为了解决证明困难、提高证明效率而由立法者做出的价值选择,因此基于对公务人员廉洁性的要求,其应说明财产来源。因此,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例外,推定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司法实践来创制。第三,可以反驳。推定是法律规定的,控方只需证明存在基础事实,即可推定证明难度较高的推定事实的存在,但并不等于推定事实一定存在,因此是可以反驳的。
需要注意的是,推定制度只是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控方仍然要承担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在贿赂犯罪案件中,控方仍需证明被指控者有收受或者给予他人财物的基本事实。“贿赂推定的适用,只能解决行为性质之争,而无法解决有否收受、给予财物这类事实认定之争。亦即推定的结果具有特定性。”*同前注[14]。当事人如果不能提供反驳证据,那么,就推定给予财物的行为是贿赂的犯罪行为。
3.奖励自白
奖励自白,既是承认口供具有重要证据作用,充分发挥口供证据价值,提高口供使用效益的务实态度,也是提高口供自愿性的有效措施。
第一,规范的奖励自白制度是司法信用的保证。新《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第2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的法律规定。”但对于坦白后如何从宽却没有进一步规定,法律也没有兑现从宽的具体规定,导致坦白者面临司法惩罚,不坦白者反而因为取证困难而逃脱法律惩罚的困境,司法因此丧失信用。只有建立鼓励自白制度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更重要的是,实务中的隐性认罪交易,经常会出现侦查人员的承诺最终无法得到兑现的情况,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危险”的“赌博”。这一则加剧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二则对侦破案件不利,三则从总体上加大了社会成本,更降低了司法威信。因此,有必要在侦查阶段就建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认罪协商程序鼓励犯罪嫌疑人作出自白。
第二,鼓励认罪,提高自愿性自白的司法效用。贪污贿赂案件一般历时较久且没有案发现场可以勘验,证据发现难及不稳定的特征更为明显。同时,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素质都比较高,具有相对较高的反侦查能力,做事不留痕迹或少留痕迹,要以证据还原事实真相确实很难。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方式,对一些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赔退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解决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和证明难题,作用很大。
4.认罪协商制度:建立中国式的奖励自白制度
司法案件的过度负荷导致各国刑事诉讼走向了协商之路。*林钰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因此,许多国家都有刑事诉讼认罪协商制度,虽名称各异,内容也有差异,但实质都是公权力一方与被告方关于认罪或量刑的协商,都要以获得自白作为协商的条件。虽然协商性司法被认为动摇了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不强迫自证己罪原则和严格证明原则,*同前注[17],第149-156页。但是因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定纷止争的实用主义效用和社会接纳的现实,各国仍然乐此不疲地加以实践。台湾学者也认为:“各国法院审判情形指出自白认罪率高,应当与实行自白认罪即宽大处理的刑事政策具有直接关联性,如自白认罪得不到奖赏只有傻瓜才会认罪,无论是从真实主义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诉讼经济价值层面,被告任意性之自白且符合真实性情况下,该自白认罪之被告减轻其刑或免除其刑,应属合理与必要且优先之刑事政策。”*刘邦绣:《认罪与量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48页。
在我国,建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认罪协商程序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即防止不透明协商对法治的破坏和产生新的腐败。具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建立中国式的奖励自白制度——认罪协商机制,具体包括:污点证人制度和行贿人坦白免责、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共同犯罪自白减免其刑、有罪答辩量刑减让。
第一,污点证人制度和行贿人坦白免责制度。所谓污点证人制度是指为了降低取证难度,指控较严重犯罪,有未经法律处理的与该犯罪相关的犯罪行为污点的人,愿意与国家司法机关合作,根据法律规定享受一定法律豁免的制度。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可以解决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明难度高,不利于打击腐败的问题。“有些犯罪,由于作案手段隐秘,作案方法智能,检控方往往很难或者无法取得有利的证据,如果就此放纵了犯罪分子,则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利用污点证人,可以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樊崇义、王建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0页。
贿赂犯罪是对合性犯罪,从内部打破堡垒是最有效可行的证明犯罪的方法。“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法律后果模糊,难以促使行贿人自愿说出贿赂的全部事实。要获得贿赂犯罪的证据,“在行贿与受贿这两种具有相对性的犯罪中,选择后者,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作为打击重点”,“有了坦白免责法律制度的保障,贿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行贿人就会消除担心因作证而殃及自身的顾虑,增大信心和勇气及时地供述全部案情,侦查机关也得以清除种种侦查障碍,保证贿赂犯罪案件顺利侦破。*郭建:《贿赂罪的特殊证据规则探析》,《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第二,贪污贿赂共同犯罪人自白减免其刑。很多贪污贿赂案件都以犯罪嫌疑人认罪作为侦破的开始,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运用大量侦查谋略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和认可,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在自愿状态下的认罪口供。在实践中,有大量犯罪嫌疑人认罪,特别是贪污贿赂共同犯罪的从犯认罪,为证明主犯的罪行提供证据,换取较轻程度的人身强制和减轻处罚提供可能,侦查机关也都会酌情考虑向法庭建议减轻处罚。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第8条规定:“犯第4条至第6 条之罪,于犯罪后自首,如有所得并自动缴交全部所得财物者,减轻或免除其刑;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与此相配套,台湾地区还制定有《证人保护法》,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供述与案件有关的重要待证事项,使检察官得以追究其他正犯、共犯的犯罪的,可以就其供述所涉及的犯罪,减轻或者免除其刑。美国也有类似规定。为了获取证人的作证支持,美国检察官有权豁免有罪证人,可以向有罪的证人签发豁免书,“保证他们不会因为作证所涉及的问题而被起诉——伪证罪和妨碍审判罪的起诉除外。对于那些知情人来说,这种豁免书很有诱惑力,因为他们只要与检察官合作,就可以免除自己的某些罪过……对检察官来说,这都是获取重要证据的有效途径。”*何家弘:《美国检察机关承担公诉和自侦职能》,《检察日报》,2014-11-25。基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发现和证明的难度以及打击的必要性,确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建立坦白免责制度,以宽恕一个较小的犯罪为代价,打击严重的贪污腐败犯罪行为。
第三,检察官量刑建议权: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建立认罪协商制度与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密切相关。在整个诉讼中,有罪判决应当被看成是对被告人利益的最大损害,故作为一种对其程序性和实体性权益减损的补偿而给予适当的量刑减让则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被告人未能通过量刑减让对其权益的放弃获得补偿,不仅在程序上是非正义的,而且有罪答辩作为一项鼓励性的制度也难以推行。”*牟军:《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确立被告人认罪能够得到量刑优惠并明确量刑优惠的幅度,尽可能细化被告人认罪所能得到的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幅度,是通过有罪答辨的量刑减让让被告人自愿供述的重要方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认罪协商的量刑减让要有明确的规范,既要给予认罪人较为明显的量刑优惠,以达到鼓励认罪的目的,同时又不宜给予控方太大的权力,否则民众会对认罪协商的合法性产生强烈质疑,最终可能导致该制度无法执行。在认罪协商程序中,确认被告人确实是明智、自愿的认罪之后,审判程序可以直接进入量刑审理部分。
结语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主要原因是证据来源稀缺、取证手段不足、犯罪特性导致的证明难度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口供依赖的问题,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找突破,破解贪污贿赂犯罪口供获取和运用的实务难题。口供自愿性是口供制度的核心问题,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制度不能仅仅解决口供自愿性问题,还要适应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此要以系统性思维看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问题,从增加证据来源、设立特殊证明制度和规则降低证明难度以及提供其他必需的条件支持等方面,去除口供依赖,提高口供自愿性,同时不影响严惩贪污贿赂犯罪。
同时,需要申明的是,口供对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对待口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重视口供但不惟口供;重视口供,但不走向口供中心主义。要辩证地认识口供中心主义与口供重要性二者的差异,掌握好二者的平衡,关键就在于文明、合法、有效地获取和运用口供。文明合法地获取口供就要确保获取口供手段的合法性,就要建立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有效制度,就要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一是建立确保合法取得口供的制度,规范侦查人员的行为,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二是确保口供自愿性。建立判断口供自愿性的机制和规则,建立鼓励自白制度。三是增加证据来源。增加证据来源就要为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部门提供必要的可行的取证手段,增强技术和信息支持,有效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取证。四是降低口供依赖,就是要有合理的刑事诉讼制度支持,消灭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因素,完善各项机制。五是要建立特殊的证明制度,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明难的问题建立推定制度等。
(责任编辑:付磊)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High Dependency on Oral Confession i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
LIMingrong
Confession is an important evidence i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The litigation proof is easy to depend on confession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which leads to involuntary confession and wrong cases.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source of evidence should be increased by institutional reforms,special proof system and regulations to lower stands of proof should be established,other necessary supports should be provided,and the voluntariness of confession should be enhanced in order to punish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severely.
Key Words:Oral Confession;Oral Confession Dependency;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the Voluntariness of Oral Confession;Proving Rules
Li Mingrong,Deputy Chief Procurator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Fujian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D9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6)02-0129-12
作者简介:李明蓉,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