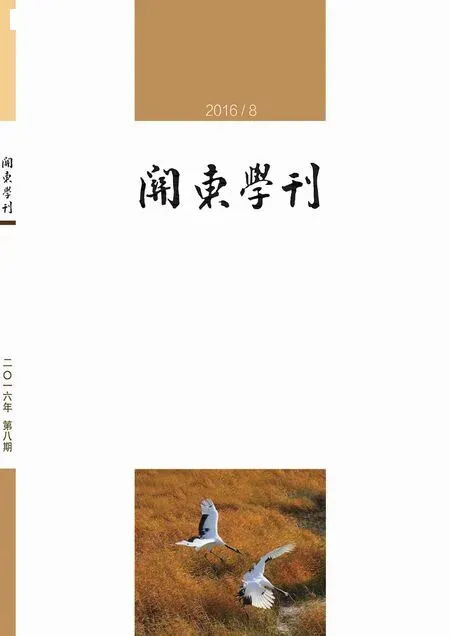“私奔”中的思维修行
——论熊培云诗歌的理性“诗想”
柴高洁
“私奔”中的思维修行
——论熊培云诗歌的理性“诗想”
柴高洁
熊培云自“思想国”开始,一直抱持理想和自由之精神,不但以富含思辨色彩的众多文章立世,并且在缪斯的国度积极探索,拓展另一写作维度的一切可能。熊培云的诗虽属其“文体私奔”的计划外“尝试”,然而凭借诗人灵魂之真诚,思想之浑厚,在躁动不安的周遭此在耕耘“存在与意义”,在时空大格局下寻找锁定“天命”,丰富了新世纪诗歌的写作路向。期间,以自主、独立、怀疑和否定为旨归的“理性精神”成为彰显其诗作优卓的砝码,在思维修行中开垦出了富有意义、热情和痛苦的诗之“乌托邦”。
熊培云;理性;“诗想”
当“重返八十年代”成为一面旗帜并被指认为诗之“乌托邦”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熙攘的社会并不是诗之理想的“黄金时代”。虽然有传统纸媒、现代网刊以及自媒体的煽风点火,创造了诗歌文本井喷的繁荣姿态;虽然有诗朗诵、诗歌节、诗歌奖以及种种诗学论坛在精神层面的推波助澜,还有诗歌元素、诗歌因子与物质消费文化媾和下摆出的“诗意栖居”,诗仿佛正在跨越彩虹桥抵达梦想的彼岸。
其实不然,与其说诗歌现在是繁荣、自信,在坚守中突破前行,不如说诗歌变得更为纠结、焦虑、尴尬、拮据又不失几分孤傲。“出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历史节点开始,已然成为一种姿态,不管是诗人还是诗作。所以,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之路,尽管“热闹”,但摸索、徘徊和挣扎还是成为一种“新常态”。既然“出逃”成为不得不的“使命”,那么方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那些日常主义、及物写作、个人化写作、新口语等写作路向的实践,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内容都给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然而,在精神层面,逃向内心,进行自我思考的自我写作,可能是恪守诗歌精神、维系诗歌灵魂的有效选择。
逃向诗人内心,并不是收缩诗人的眼界和窄化诗歌的表现维度,而是更忠实自我灵魂的感知,在精神自由和批判在场中使诗歌成为精神提升物。期间,独立自主地介入文化、社会,处理时代生存问题以及歌哭生命周遭的此在,承担诗歌的使命和诉求,使诗歌成为源于个人话语又超越个人话语的灵魂意象化展现,书写自我,共鸣时代。
从这个向度看熊培云逆行“逃向”诗歌的“文体私奔”,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不仅是其多年诗歌夙愿的有意探索,更是用个我之心抚摸社会之必要归宿,当然这种内心外化的灵魂审视展现出的不仅是真诚的欢爱,更有不可避免的无奈和疼痛。正如熊培云自己所说:“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熊培云:《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要写作?》,《自由在高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0页。以理性为主导的思维修行,在熊培云的诗作中显影为寻找意义、思索时空、分析自我、探讨责任、讽刺社会、消解崇高等等主题,而“诗想”的旗,又在困厄的社会孕育并照见心里的阳光,“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也是已然沉睡的过往。”*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一、“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熊培云诗作中的存在与意义
“理性”作为一个关键词,在西方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可说成是担纲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手,西方诗坛中也可梳理出一条“理性探索”的诗歌发展脉络。于中国而言,因为“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太过强盛,以至于“理性”一直相对疲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于中国新诗显得尤为紧要。理性,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在新诗批评中虽不常见,但也并非毫无先例。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为卞之琳诗集所写的评论中,谈及了“理性”的重要意义,“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0页。。理性一词在穆旦这里锻接了“理智”,而今天综合智性和文化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则与之有较多共性。
说到知识分子写作,就不得不提一下熊培云的身份问题。正如熊培云在其《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论著中所呈现出来的,他是一位不断寻找自我,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思想行者”。而这样的“修行”,必定离不开以自由、独立、自主、怀疑、否定等为旨归的理性精神。以此而论,熊培云诗作中的“理性”呈现也就“顺理成章”,正如其自述:“我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我宁愿将这种回归视为我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34页。。所以,这场“文体私奔”,裹挟着理想与理性,在缪斯的国度继续完成熊培云对现世的思考。
“私奔”,总能带给我们对达成美好情感愿望的诗意想象,但与此同时还连带着一种无奈以及不得已的解脱诉求。熊培云说:“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28页。但正是这种困顿中的清醒与超拔,可能给诗人带来另一彼岸,击碎荒谬,去往存在与意义共有的不是乌托邦的乌托邦。
“你是你的宇宙,最古老的王者/你感受,生命从此有了时间/你思想,大地从此万物奔流/你归于寂静,世界再无消息”。(《存在》)简简单单的几行诗,内蕴了关于“存在”的无限思考,与宗白华的小诗《夜》:“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闪烁”,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首诗同样语言凝练,富含哲理,宗白华小诗描述了诗人看到繁星时的感悟。诗人觉得自己是万星中的一个,宇宙是伟大的,诗人是渺小的,但是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一张明镜,虽然那么多星星,但实际都装在诗人的心里。也就是说,诗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没有这个世界就没有诗人;但反过来说,当没有诗人时,这个世界还真的存在吗?这或许就是熊培云诗句“你归于寂静,世界再无消息”的真谛。这里多少与宋代哲学家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思想类似。但熊培云在思考“存在”之意义的同时,更多是对于“自我”的建构,就是说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关键是“自我”的完善与圆满。所以,熊培云才说:“我承认人生是荒谬的,但另一个方面我也承认人内在的神性。”*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28页。
所以,在《宿命的诱惑》《镜中的上帝》《理由》《放下》《星月夜》等诗作中,除了继续对于“存在”的不可知、荒诞与不可理喻的表达之外,还有《虚度》《这世上有两个你》《一个人的人海》《其实我们并不拥有》《暴风雪》等诗作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建设与高扬。读熊培云的诗作,一种对于“个我”的分析解剖成为持续的诗歌内驱力,也是贯穿诗集前后的内在精神线索。比如《虚度》一诗,没有什么绚丽的技巧和高卓的意象,只是用不能再简单的语句慢慢陈述,而“我不说你是一个好人/我不说你是一个坏人/我只知道你是一个虚度光阴的人”的不断重复产生的紧迫感,又使得诗作内蕴了时间流逝,活着何为的思想张力。尤其是最后“我看到人生最大的苦难与虚度/莫过于日日辛劳却生无所依/成为一个未遇天命的人”的收束,拔高了诗意的格调,使主题看似平凡,实则回到了如何“成就”“个我”的元命题。诗中出现的“我”“你”两个人称指代,“我”是诗人也是诗中人,而“你”并不仅仅是“他者”,也是诗人对另一个自己的倾诉和提醒。这种从“个我”分拨出的二元或多重性格,在《这世上有两个你》《谁没有两颗心》《找我》等诗作中亦然。当某一首诗的个性成为多首诗之共性,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其实表达了诗人的某种心理——在黑夜与矛盾中反省自己、追逐自由、坚守理想、锻造灵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最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做最好的自己。”*熊培云:《后记: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重新发现社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所以,“外面还黑着/挡不住我在屋里点灯/我早已学会了/自己唤醒自己/于绝望的深谷”。(《冬日》)
需要关注的另外一点是,熊培云诗中对“个我”的不断丰富,并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精神梦幻,而是接续着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入狱身先、悲智双圆”的济世情怀,也正如熊培云所说:“责任心真是个好东西,我们的人生尚有些希望,多是拜其所赐。因为有了对他人的责任心,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种自救的维度”*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12页。。这种责任感,表现在诗作中首先是一种对于自由灵魂的引领。比如《致哀伤的人》,诗人告诉我们,或许在前行的路上总是一片迷雾,但也可能下一步就是“光亮”,而在此之间,如何走到那个临界点,唯有自由的灵魂,哪怕是身处逆境深渊,我们也可以有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用“快乐而自由的灵魂啊/去担当你生命中最需要的担当”。其实,关于人生的禁锢与自由,也就像诗句最后所述,“说什么别无选择/你只是选择了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有时候真正禁锢我们自己的,并不是身外的物质、社会、体制和国家,或许就是我们内在彷徨迷失的心。牢笼的圈禁,或许只是我们为了追寻自由时疲于应付世俗而忘却了最初的梦想,所以诗人也在另一首诗中反省与提醒自己和他人,“我为没有倾尽所有的自由与诚意向道歉道歉”。(《我道歉》)
其实,对于自由的关注与引导,一直以来都是诗人思考和写作的焦点,“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的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熊培云:《后记: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自由在高处》,第298页。对人的命运、对社会的持续关注,必然会涉及到时代特色,会感受到“现代化”不仅仅是阳光雨露,更有可怕的黑洞。所以,诗人的责任感还体现在对于“异化”事件的关注。比如《人形昆虫》把大城市引以为傲不断向外扩张的环路比作一圈圈的蜘蛛网,网住的不是花团锦簇,而是漂泊者不管留下或是离开都约等于悲剧的无可奈何。《生命在银行里》用一种反讽的笔调,活脱脱地描述出了现代人,把时间换成金币,把生命安葬于银行的无厘头的生存姿态。而《后现代爱情》《破碎的人》《手机》《谋杀》等诗作,更是赤裸裸地把现代媒介以及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呈现出来。借助各种媒介终端以及网络的极大便利,确实,我们的信息时代加快了社会前行的脚步。然而,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先进性背后,其实还有着对人与人关系的割裂,“两人躺在一起/却又各自拔营/私奔千里”(《后现代爱情》);也有着信息传播中众口铄金的言语暴力,当把他者的隐私当成自己调侃的必要,可怕的“大多数”的话语权其实就成为一把伤人的带有血槽的利器,在炫耀自己虚无的感伤时,又在他者的伤口洒了一把盐,所以,“一个绝望的人/以一种示众的方式/再次被谋杀”。(《谋杀》)
对于这些人们已然习以为常的“习惯”,犹如并不容易发现的癌症细胞慢慢吞噬了人的精神和肉体,诗人看到生命周遭如此“荒唐”,尚能思索现象背后产生社会“化合反应”的原因,当然离不开诗人对现实观照的理性精神。正如台湾诗人和诗评家简政珍所说:“诗人足以自重的,不是他有口出呓语的权利,而是以文字赋予外在世界一个秩序……真正的成熟不是漫无节制的奇想,而是投入自我和外在世界的辩证。”*简政珍:《诗的瞬间狂喜》,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34页。所以,熊培云的“自我和外在世界的辩证”还体现在诗人对社会深层次的辩证思考。《衣冠禽兽》《偷生》《理由》《最后的世界》《悲剧的诞生》等诗篇,诗人用具体的意象表达了抽象思维空间中的对立或对抗状态,并且说明了这种“对抗”的虚无本质。比如《衣冠禽兽》,对于“衣冠禽兽”的指认,并不在于何谓“禽兽”的问题焦点,而在于你是否异于常人的“赤身裸体”而穿戴有“衣冠”,所以,诗人说出一种貌似建立在道德高度之上的对他者的审判,其实只是源于被审判者的“与众不同”。“道德审判每天都在进行/每天审判的却不是道德/而是你和他们不一样”(《衣冠禽兽》),这种现实指认,类似福柯在其论著《规训与惩罚》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审判”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所以,“全副武装/审判/手无寸铁//奴隶坐上了审判台/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有罪”。(《审判》)
以此,我们大致看到了熊培云诗中关于存在,关于意义,关于人的际遇的思考在“个我”“他者”“社会”等主体中的相互辩证。当然,并不是某首诗就只是特定地彰显了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是一种精神与肉体,思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混融。在世界正在慢慢失去其丰富性和想象力时,用诗的自由放飞思想。也正如诗人所说:“诗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它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我们生存的意义,道出了一些隐秘的内情……”*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21页。
二、“你是你的沧海一粟”:熊培云诗作中的时空之魅
相信读过熊培云《自由在高处》的读者应该会受触动于这么一句话,“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熊培云:《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要写作?》,《自由在高处》,第10页。。这句话出现的前提是作者感慨于辞去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自费出国留学,所以“空间上远离国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时间上找回自己”又是什么意思呢?比较详细的答案在作者的另外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序言里,其中“空间之维与时间之维”*熊培云:《自序:问世间国为何物》,《重新发现社会》,第15页。一节阐释了作者对“人是时间单位”的理解,而这种对“时间”的持续思考在熊培云诗作中一以贯之。
因为“时间”不可再生的残酷性,自古以来,对“时间”易逝的惆怅成为众多诗人们倾心的诗歌母题之一。确实,作为一维线性流动的时间,每个人其实都只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流,虽然我们无从把握,但我们又无时无刻不在时间中游走。“正如席勒所讲的,时间就是人的生存的情状,一旦否弃时间,人自身的存在也就被否弃了。”*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所以,面对似有序而无状的“时间”,如何理解,如何把握,或者说如何诗化时间,在一种迷离和模糊的瞬间感受中去把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为哲学家和诗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此外,与“时间”并存的“空间”,又在另一个维度提供了思绪延展的方向。如果说时间代表着流动和流逝,那么空间则象征存有和存在。从这个向度说,诗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和破解了时空密码,才能体味存在和意义,才能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划分,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诗意世界。
“你从你的孤独的道路上来/他也将朝他孤独的道路上去/他可能走向任何地方/唯独不会走向今天的你//你回不到你的过去/也帮不了过去的你/你是你的沧海一粟/你是你的万千可能之一种”(《你是你的沧海一粟》),在这首诗的空白处,熊培云旁注如下,“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我们却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活法。此亦所谓,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44页。从诗和旁注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诗人思维中的时空类似“共时”呈现的多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时间”在这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持续流转的线性形态,而是从“原点”到“终点”间并行发散出的一切“片段”。“你”之所以是“你”,或者“你”之所以不是“你”都在于此。从这个向度我们再去看《存在》《第一次囚徒》《无常》,就会惊奇地发现诗作的优卓之处。《第一次囚徒》是熊培云诗作中少有的长诗之一,抛开诗中关于存在与意义的讨论,单看“时间”的呈现方式,我们会发现诗中的“时间”仍然不是线性的,而是被若干个“第一次”定格在特殊的时空之内,并且这若干个“第一次”出现的“今天”也以“片段”的方式展示,因为“今天是我剩余生命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我在今天活了很久/我在今天经历所有的第一次”。其实,之所以诗中对于“时间”有如此表达,还要归因于熊培云对于“人是时间单位”的认知。“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只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个工具,用于测量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运动。所谓人是时间单位,也是指人是一系列自己可以主宰的运动的集合。”*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66页。也就是说,“时间”是面向个体的,是个体的唯一存在,同时也就关乎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这种观点类似于狭义相对论中提出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时间的说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带有标签独立的,除非两个人处于绝对静止的状态。
既然时间是个人可以主宰的运动的集合,既然“走不回过往/逃不进将来/第一次覆盖第一次/今天覆盖今天”(《第一次囚徒》),那么如何最大化填充时间的虚无,也就成为诗作表现的另一个焦点——天命。“天命”是诗人独特的生命感悟,在《我醒来算了》《Bing Present》《生活在湖边》《天命昭昭》《孤星》等诗作中,都对此进行了肯定和赞美。比如《Bing Present》中诗人告诉我们,与其活在“过往的悲伤”,“将来的沉重”以及“现世的荒唐”中而慌慌张张,不如“找到自己的天命”,把其他一切交给命运。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天命”于诗人来说并不是不可知的“命运”或“宿命”,“天命”无所谓好坏,它是可以寻到并通过自我努力而完成的精神认同,是对抗生存迷茫,摆脱欲望,保持清醒状态的赤子初心。“天命”的状态应该是浮士德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求,而“天命”本身的意义建构则在于“我”的足够强大,在于认识到“我就是远方之远方”,“我就在彼岸之彼岸”,“我就是群山”(《孤星》)。至于如何使“我”保持热情且富有意义的人生状态,就又回到了上述关于熊培云诗中对于“存在与意义”的表达和对于“个我”的不断丰富。当然,诗中与此相关还出现了很多“寻找”的行为意象,“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在祖先的土地/流浪四方”(《一代人》),“没有历史和地图/没有暴力和杀戮/在心理寻找世界/最后的乌托邦”(《除了美,我一无所知》)、“第一次出远门/扒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我去城里/找寻光荣与梦想”(《回家的少年》)。这些行为意象,标示了诗人在追寻守护“天命”及完善“个我”并推及“他人”过程的艰辛及坚定。所以熊培云说:“如果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熊培云:《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29页。
总体来看,熊培云的诗抱持理想坚守内心,用理性的思维修行不断填充个我生命之存在与意义。当然,也像熊培云诗集序言中所述,诗集并没有着意在意象建构,更多地是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的思考。确实,理性的思索扩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和写作方式,但另一方向也使得部分诗作“意义”大于“审美”。但无论如何,写诗是一种独白,并在独白中吐露时代的声音,“表面好似藉由文字捕捉那已逝去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却是填补那瞬间的空茫,好似一切人生的浮沉皆是难以改变的残酷事实。而最残酷的是眼睁睁的看着时光溜走”*简政珍:《诗的瞬间狂喜》,第24页。。诗人以心灵时间取代客体时间,以创作铭记一度的存有,在“私奔”中完成了另一维度的生命体验。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也照进你的心里/所有向善与自救的门/敞开着……/我是理性/是力量/是善良/是一生中所有的/热情与痛苦/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夏日》)。
柴高洁(1985-),男,文学博士,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郑州 4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