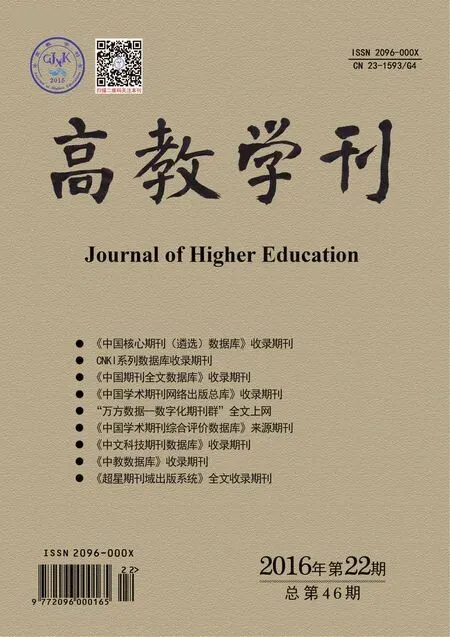浅析“文以载道”观对梁实秋的影响
陈曼燕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浅析“文以载道”观对梁实秋的影响
陈曼燕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文以载道”是中国历代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但到了“五四”时期及此后一段时间,它却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中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梁实秋,他对这种传统的批判同样是不遗余力的。尽管他有意的想与其划清界线,却最终无意的重蹈它的“覆辙”。因此,文章将以其文论与作品为依据,阐述“文以载道”对梁实秋的潜在影响。
“文以载道”;梁实秋;批判;潜在影响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化的全面重估,“文以载道”作为中国的文学传统,自然也被视为批判的对象。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着矛盾状态的。他们在对“文以载道”进行批判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将此重新纳入新文学的传统之中。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梁实秋,尽管他后来也并不反对将文学当作一种宣传的工具,但是他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却始终是不遗余力的。由此,我们很容易地将他的“人性论”主张与“文以载道”做清晰的划分。但其实,梁实秋的文论与创作实践还是未能摆脱这种文学传统,它对梁实秋的影响是潜在的。
“文以载道”既是中国的文学传统,那它就必定呈现出不断被继承与阐释的特点。在各家各派的理论中,尽管对于“文”与“道”的具体含义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把“文”当作“道”的载体却有着相似之处。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经肯定《诗经》的作用,他说:“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1]孔子在这里是说学诗不仅有利于修身,还可以通过修身来实现辅助君主的政治理想。此后,从曹丕的《典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对于经国大业的作用也得到了强调。而第一次明确提到“文”与“道”之关系的是唐代的韩愈。他在《争臣论》中就曾说:“修其辞以明其道”[2]。到了宋代的周敦颐,他在《通书·文辞》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文以载道”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学说也一直延续着它的生命力,并逐渐成为不可动摇的文学传统。
到了五四时期,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躯者开始彻底地对传统文化进行重估。而“文以载道”在此时也受到激烈的批判。在众声喧哗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生执着于“人性论”的梁实秋所发出的声音:“汉儒以六艺为正宗,以文学为辞章,把文学的地位看得很轻了。李汉韩昌黎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韩愈答刘正夫书:‘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矣。’……这都是把文学当做了贯道载道之技艺,极轻视文学的了。”[3]这是梁实秋在三十年代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根本就没有过合乎文学发展的文学思想,并指出:“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3]在梁实秋的表述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实秋虽然推崇传统的儒家文化,主张以理性节制情感,但是对于文学之标准却有着与早期新文化运动者同样的理解,这体现在他们都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
这里提到早期新文化运动者,为的是与后来的相区别。因为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文化先驱者们渐渐意识他们虽有意与这种传统划分界限,却无意间又陷入了这种文学模式之中。所以,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纷纷为带有浓厚的社会功利性的文学作辩解。其中,朱自清在四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更为清楚,他说:“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4]也就是说,对于早期比较激进的主张,许多人都已沉静下来进行反思,并进而承认“文以载道”的合理性。那么,一向反对将文学工具化的梁实秋对于这样的文学模式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梁实秋在理论上似乎还存在着不太严谨的地方。因为他在五十年代曾发表过《文学讲话》这篇文章,刚开始他还指出:“世上一切事物皆可作为工具,文学当然亦可作为工具,对于使用者有益,对于文学无损。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借用性质,不要喧宾夺主以为除此即无文学。”[5]而到了文章的后面,他却说:“我们中国旧有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我们嫌其迂腐,不肯再加接受。奈何习焉不察,竟至采纳那别有用心的‘工具’‘武器’的看法?”[5]可见,梁实秋在表面上虽没有反对将文学当作工具,但是他对于“工具”一词却是心存排斥的。而且,对“文以载道”这种文学传统的态度,他在理论上也是相互矛盾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或许是因为梁实秋有他自己的文学标准。在他看来,文学所要表现的是常态的人性,这种人性与时代无关,与阶级无关。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这与他对“文以载道”的理解存在偏差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文”与“道”都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为“文”大体是指一种文字表现形式,在此不再加以赘述。而“道”既有孔子的伦理之道,也有陶渊明的自然之道、朱熹的经世治国之道……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就处于正统的地位,伦理道德、忠君爱国的思想从民间到士大夫阶层都已具为无形的约束力。因此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文学评论与作品中,就自然体现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特点。就算是表现个人的情感与追求的作品,它同样也需符合社会公认的思想标准。不然它怎禁得起“吹尽狂沙始到金”历史命运?也就是说,不管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与“文以载道”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功能性的诉求。在这个问题上,朱光潜有过精辟的论述:“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志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实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载道’,根本不是两回事。”[6]如果以他这种标准去衡量,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就自然会或多或少带有“文以载道”的色彩。
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又何尝不说明了这一问题。
梁实秋在接受白璧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服膺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原因在于它们的相通之处都是提倡理智对于情感的制约作用。对于文学作品,他同样认为有内容与形式之分。但是,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表现一定的思想与情感,而形式却是次要的。他在《文学的美》中就曾说过:“文学不能不讲题材的选择,不一定要选美的,一定要选有意义的,一定要与人生有关系的。”[7]而在《文学的纪律》中,他也提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平和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8]可见,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不同,梁实秋是想借文学来表达一定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他一贯所坚称的“人性”。
至于什么是“人性”,梁实秋也坦言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实,不同作家的人性标尺都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一方面,人性乃所以异于兽性。简单的饮食男女,是兽性;残酷的斗争和卑鄙的自私,也是兽性。人本来是兽,所以人常有兽性的行为。但是人不仅是兽,还时常是人,所以也常能表现比兽高明的地方。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操,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们所谓的人性”[5]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梁实秋的文学思想也是带有一定功能性的,他所追求的“人性”实际上就是他认为的“善”,是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与“中庸之道”。因此,像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不也体现了出一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吗?只不过,他所载之“道”与当时的文学潮流在具体内容上是不同而已。
谈到梁实秋的创作实践,也许这并不能为他受“文以载道”影响提供太多的依据。因为他的作品多为散文,而散文是一种比较个人化的体裁,所以很多作品未免显得随意而主观。虽是如此,这种带有功能性作用的也不乏其文。品读梁实秋的作品,起先多有“谐趣叠生”的印象,但细细体会,作品在这种诙谐之余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味。这种意味有时让人冷静下来反观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有时能使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如《谦让》中就以幽默的语气揭露了生活中的那些虚伪造作的嘴脸,并引发读者对于“礼让”这种美德的思考。此外,在《槐园梦忆》这篇追忆程季淑女士的名文中,梁实秋在文中所洋溢的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更是让读者深受感动。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教育”?当然,梁实秋也许并未真正有意识地在他文章中赋予过多的意义。因为,“文以载道”观对他的影响只是潜在的。
由此可见,梁实秋与他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者一样,虽然都自觉地批判“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却又不自觉地继承着这样的传统。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悖论的现象,其实也不然。因为对任何文学变革而言,没有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就没有文学的创新。那么,致力于建立新文学传统的梁实秋与其他文化先驱者怎能置身于这种规律之外?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208.
[2]韩愈.韩昌黎文集(第2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3.
[3]梁实秋.现代文学论M//梁实秋文集(第1卷)[M].鹭江出版社,2002:397+400.
[4]朱自清.文学的严肃性M//朱自清全集(第4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480.
[5]梁实秋.文学讲话M//梁实秋批评文集[M].珠海出版社,1998:219-220+221+221-222.
[6]朱光潜.文学与人生M//朱光潜全集(第4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62.
[7]梁实秋.文学的美M//梁实秋文集(第1卷)[M].鹭江出版社,2002:507.
[8]梁实秋.文学的纪律M//梁实秋文集.(第1卷)[M].鹭江出版社,2002:141.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is a literary tradition in China.But in the"the May Fourth Movement"period and after a period of time,it has been a fierce criticism.Liang Shiqiu,who appeared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lso criticize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stongly.Although he deliberately wanted to steer clear of it,but ultimately repeated the mistakes.Therefore,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 works as the basis,elabor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theory on Liang Shiqiu's writings.
"W 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Liang Shiqiu;criticize;the potential influence
I206
A
2096-000X(2016)22-0261-02
陈曼燕(1979,01-),女,广东汕头人,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初级职称,现就职于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