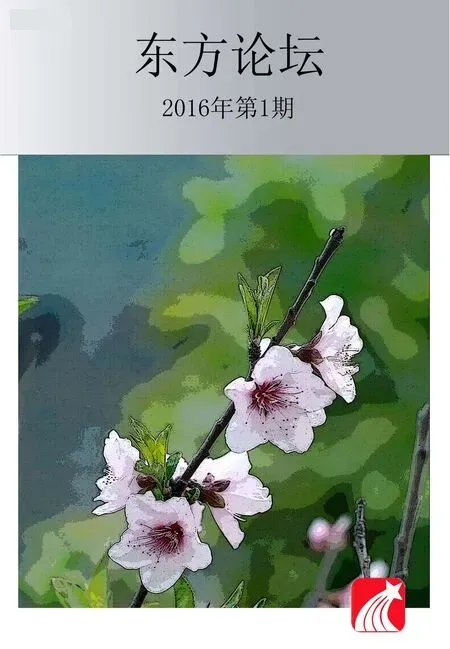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区家乡文学初探
张 芸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区家乡文学初探
张 芸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区家乡文学(Heimatliteratur)的主题是讴歌“乡村”“土地”“田园”“家乡”“血统”等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对以大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进行猛烈抨击,对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进行强烈质疑。家乡文学的思想倾向十分保守,甚至有一定的反智主义倾向,展现了德国社会思潮从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成为纳粹第三帝国时期血统与土地文学(Blut- und Bodenliteratur)的前驱。
关键词:德语区;家乡文学;传统农业;现代文明;反智主义;文学形态
一、家乡与家乡文学概念
在德语文学中,“家乡”(Heimat)这个概念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它的含义涉及地理的、社会的、情感的、哲学的、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自19世纪以来,德语区的许多重要作家都频繁地在各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个词虽然意义极为宽广,但总体来说他是一个饱含着个体情感和生活体验以及感受的词,它的内涵只有在与历史及文化空间的一定关系中方能展开,一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的结构恰恰是能够适合“家乡”这个概念成为一整个时期人人所关注的重点。家乡是一种“空间的与社会的整体”,“它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归属感和总体感”[1](P46)。在这个意义上的家乡概念可以满足人类根本上对“保护、行动和认同”的需求。
19世纪以前,“家乡”这个词在德语文学作品中使用得较少,出现时也并不包含主观感伤情绪,它大多指的是祖辈的老屋、庄园及其周边环境。随着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成员流动加速,“家乡”一词原本朴素简单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更多情感上的含义。19世纪下半叶德国农业经济结构解体,德国历经迅猛工业化的过程,人们离开祖辈生活的乡村来到都市谋生。在20世纪的动荡中,工业化、战争、革命也迫使人们背井离乡。随着故土的丧失,家乡概念日益上升到人们的意识层面,因而19世纪以来德语文学中对家乡的叙述具有个体的感伤色彩。
在精神层面,19世纪20世纪两个世纪中西方的形而上结构、价值体系也同样经历了深刻的巨变。原本笃信不疑的价值体系遭到摒弃,曾经存在的精神上的安全感、归属感不复存在,在被逐出曾经的精神家园之时,家乡一词逐渐有了形而上的内涵。家乡不仅指一方故土,也不仅仅是个地域的概念,同时也是个宗教、哲学概念。家乡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家乡这一概念发展的思想背景是现代人的社会与价值观念及精神位移(displacement)。在文学表达上,“家乡”是通过对家乡的言说来构建的,只有在失去家乡,并将对家乡的追忆诉诸文字时,才形成家乡,意即家乡是通过文字形成的一种情感想象[2](P5)。在精神层面对家乡的怀念也是德语区家乡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家乡文学的思想渊源
16世纪和17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黄金时期,欧洲其他主要民族基本上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德意志民族在这个时期由于受到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的影响,在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严重滞后,因而德意志民族在欧洲成为一个“后崛起的民族”[3](P17)。19世纪是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盛行,而这个历史时期德意志社会的历史状况不足以产生民族主义思想,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上要定义德意志民族,只能从精神、灵魂、语言、文化、共同起源等角度进行定义,根据莱美特(Lämmert)的分析,赫尔德、雅阔布·格林和席勒都从语言、文化、精神角度来定义过德意志民族,而其他欧洲古老民族的民族定义在19世纪则更多地从共同的政体等角度来定义[4](P22-27)。有关德语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及德意志民间传说的学科都被视为对建构民族意识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这造成了19世纪德语文学具有内倾和向后看的特点。“心绪”(Gemüt)和“内在性”(Innerlichkeit)这类概念都成为可以描写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德语词汇。“德意志种族思想在旧式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之前并未获得发展。它的兴起归功于普鲁士的爱国者和政治浪漫主义,而不是贵族及其代言人。德意志种族思想的产生是为了团结全民族,反对外族统治,它的创始人不到边境之外去寻找同盟者,而是想在全民族中唤起一种同根意识”[5](P234)。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使德语和德语文学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种最广泛的认同标的,就成了时代的首要任务。
19世纪是各种思想和各种“主义”自由激烈竞争的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竞争中占了上风。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民族概念与民族生成的有机论相结合,纯粹精神与纯粹血统相挂钩。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物质化过程,转向由血统、土地等具体事物来象征的神秘而不确定的力量。一切美好、纯粹、真实的事物都属于德意志的过去,人被纳入出生地周边的圈子里,血统、习俗的传说、祖先的声音成为一种具备价值判断的维度,而现社会大都市则展示着堕落和颓败[6](P87)。“民族这个概念渐渐地演化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世间最高价值的体现。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概念。一切与本民族有关的都是美好的,而异族则代表不正义和邪恶。这种方法将民族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成为一种信仰而确立。”[3](P17)民族概念不仅成为整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而且还成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成为衡量整个德国社会的一项准则。民族主义至上的家乡艺术运动以及家乡文学运动就在这样的思想氛围里登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民族概念在德国的意识形态化,与之密切相关的“家乡”(Heimat)概念在这一思想变化的背景下同样历经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家乡”是承载着历史、血统、习俗等维系民族存在的神秘力量的重要概念。这与欧洲现代文明以自然科学、技术和工业等需要可量化的理性思维为基础的思潮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经过浪漫化的农村思想发轫期,就有人将都市现代文明视为非自然的、不符合德国国情及民族特点的事物加以排斥;而将土地、泥土和乡村风貌视为一种具有联合民族的力量,进而宣扬一切农民的、农业的和乡村以及小城镇的生活方式为真正合适德国民族特性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家乡”一词从某种个人心绪的流露转化为一种有约束力的价值。符合这个“家乡”价值的事物,被冠以积极的美好的意义,不符合这个价值的事物,被贬为消极负面的。“家乡”一词历经了价值化过程,家乡概念也随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好乡村与丑陋都市所代表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在家乡文学中形成。
三、家乡文学的文学史溯源
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初期,由于文化、文学承担着定义德意志民族的重任,晚期浪漫派作家们对民间文学极为关注。这种关注奠定了现代德语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发展路线,即对原生态的德国农民和农村题材的重视。浪漫派作家们发现乡村生活方式和空间逐渐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因而产生了文化悲观的思想。维也纳会议(1815)后,文学在政治高压下分化为三月革命前(Vormärz)和彼得迈耶尔(Biedermeier)文学。彼得迈耶尔文学的作家倾向于描述身边琐事,不过问政治,对家乡、田园和自己的生活小环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家乡文学”的源头在德意志的比特迈耶尔文学,而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语区的诗意现实主义文学,也同样成为家乡文学的重要支柱。
这个时期的诗人和诗人在很大部分上属于市民阶层,他们试图通过构建一个田园诗意的家乡来弥补现实政治生活的缺失。诗意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小家乡”的描写。家庭、村庄、小城镇是它的同义词,构成了家乡的外在元素。德语区的现实主义作品前面之所以有“诗意”这一修饰语,是因为与英法等国描写都市或城镇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这一时期德语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背景以乡村为主。“小家乡”(Kleine Heimat)意味着退缩,甚至是绝望,坚持着值得坚守的旧事物。家乡的一切往往通过微笑的幽默和对细节的刻划表现出来。从高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凯勒(Gottfried Keller)、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和斯托姆(Theodor Storm)开始,乡村世界在德语文学作品中就被塑造为一个和谐统一的田园社会结构,那里的人们纯朴勤劳,尚未被所谓都市文明所侵蚀。高特赫尔夫创作了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他致力于刻画农民的心理、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的思想倾向于保守,在宗教中寻找避难所。奥地利作家斯蒂夫特以“柔和法则”进行创作,将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小事作为真正伟大崇高的事物来描述,以此来应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巨大矛盾。斯蒂夫特的代表作《晚夏》就是以主人公回到一个小镇的生活为主题来阐释他对伟大和崇高的理解。主人公与外界的事物不存在任何内在关系,外界事物仅作为家乡以及熟悉的事物的对立面存在。斯蒂夫特的家乡位于波西米亚森林,他的家乡概念与家乡景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艺术与特定的风景相联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源自斯蒂夫特。他将家乡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内容,并通过诗意加以生动地展现,风景也因此第一次在其存在的深度和广度上得以诗意地实现。”[7](P139)在斯蒂夫特笔下,对家乡的描述为后来的家乡文学设定了许多视角,例如房屋与财产、都市与乡村的对立等等。在斯蒂夫特的短篇小说集《彩石集》中,他将最黑暗的一篇小说《电气石》(Turmalin)置于都市场景中,足以说明他对都市文明的理解。
斯托姆作品中的浓郁的乡愁也表达了他对家乡概念的理解。对斯托姆来说“家乡”是由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环境构成的;这种熟悉给人安全和舒适感,同时还能给个人以发展的机遇和空间。高特弗里德·凯勒通过对塞德维拉这个小镇的人物的塑造创建了一个对拘于外省和小镇的家乡的批判模式,他对家乡存在的父系宗法关系进行了反讽。他通过幽默对一个特定范畴作为整个社会存在的现实进行了异化。
在19世纪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环境下,相互补充、相互对立地使用“家乡”这一概念日益增多,而且通过诗意现实主义逐渐形成了一种纲领性的基础。“小家乡”这一术语意味着一个狭小世界的幸福。家乡概念隐含着对一个健康的世界的认同。所以首先主要是那些身处巨变中惴惴不安的小资产阶级认同“家乡”的客观价值。通过对“家乡”概念的客观化和普遍化,家乡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一种意识形态。1871年统一后,德国开始了迅猛的工业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过程带来了德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家乡急剧丧失,这刺痛着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对农民和农村的颂扬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也得以更大程度上的展现。家乡文学艺术运动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有三个因素尤为重要:其一,社会成员在地域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加大;其二,在进行都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生活方式日益没落;其三,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化为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形成德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反工业的复辟思潮,家乡文学中的家乡概念就在这种思潮中历经了一个狭隘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由于德国内部的流动性加大,使个体失去了与某一个地区的联系,以前在法律意义上将家乡等同于祖屋和农庄,而此时家乡概念无法给大部分民众提供这种地域和情感上的认同,于是个体的认同感被极大地动摇。而在这种情况下,将家乡意识形态化,很容易得到随着家乡消失而失去了认同感的一群人的赞同。在这个意义上的“家乡”逐渐成为“家乡文学”的中心概念。第三帝国时期的血统与土地文学中对家乡风貌、民族和族群之爱就是在这样的家乡概念基础上拓展而来。[8](P216)。
四、家乡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创作纲领及主题
家乡文学的作品中展现德国的族群(Stamm)和德国的山水风貌,讴歌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强调土地与家乡的关系,家乡文学的美学基本原则根源于诗意现实主义,因而这个流派作品以其所描绘的狭小空间来象征性地反映整个世界。家乡文学的艺术纲领是:家乡文化不仅要跟上德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而且要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民族文化[9](P27)。而这一宏大的艺术主旨能否得以实现,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文学流派对大都市充满了仇视和厌恶,在对都市的工业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充分表达了对理性主义、科学发展和进步、对知识阶层的不信任,流露出反犹思想和血统论观念。家乡文学在很多方面为后来的血统与土地文学(Blut- und Bodenliteratur)提供了思想基础。
德语区家乡文学的重要作家来自奥地利和德国,主要有路德维希·岗霍夫(Ludwig Ganghofer:Das Schweigen im Walde 1899 《林中的静默》)、弗里德里希·林哈特(Friedrich Lienhard)、尤利乌斯·郎贝因(Julius Langbehn: Rembrandt als Erzieher Von einem Deutschen 1890《教育者伦布朗》)、彼得·罗瑟格尔(Peter Rosegger)、路德维希·安岑格鲁伯(Ludwig Anzengruber)、阿道夫·巴特尔斯 (Adolf Bartels: Die Dithmarscher 《迪特玛舍尔人》)、威廉·封·波棱茨 (Wilhelm von Polenz:Der Büttner Bauer 1895《农夫比特那》)、克努特·哈姆荪(Knut Hamsun: Segen der Erde 1917 《大地的福祉》)、恩斯特·瓦赫勒(Ernst Wachler)、亨利希·索恩莱(Heinrich Sohnrey)、卡尔·亨利希·魏格尔 (Karl Heinrich Weggerl)、康拉德·贝斯特(Konrad Beste: Das heidnische Dorf 1930《荒原小村》)、古斯塔夫·福棱森(Gustav Frenssen: Jörn Uhl《约尔恩·乌尔》、赫尔曼·罗恩斯(Hermann Löns: Wehrwolf 《人狼》)等等。
家乡文学家和理论家在一些杂志上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和意愿。宣传家乡文学艺术纲领以及创作的机关杂志刊物主要有:《艺术守护者》(Kunstwart),这个杂志的人员同时组织出版了家乡文学运动的另外一个纲领性杂志《家乡文学与民俗丛刊》(Die Heimat. Blätter für Literatur und Volkstum)、《德国家乡》(Deutsche Heimat)、《艺术和民俗丛刊》(Grüne Blätter für Kunst und Volkstum)、《家乡快讯》(Flugschriften der Heimat)、《高原》(Hochland),《田野》(Das Land)、《高塔》(Der Tüermer)、《家乡园地》(Heimgarten)等等。
家乡艺术往往将家乡的风貌、泥土与土地描写为艺术和人类一切发展潜能的营养土。“从家乡的泥土中向着天空生长,无论风暴还是阳光。”[10](P136)林哈特自1900年后负责主编《家乡》杂志。他开篇明意地在发刊词中说:“家乡是一块带着根茎的坚实土地,生长着植物和生命,存活着各种有机体;以真正的成熟的心智沉入它那健康的真理和温暖中去就是从机械主义和无病呻吟的问题中解救出来。生命之路、万物的灵性化若不在清新的原野上难道还能在理论的斗室里完成吗?”[11](P197)
在家乡文学中,家乡概念与土地概念密切相连,土地是构成家乡的最重要的元素。家乡即对土地的所有权:“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土地,尤其是拥有了一片地产之后,才可以算是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乡。”[9](P17)“只有自有的农田和土地能够保障家乡的存在,而失去土地财产也同时意味着失去家乡,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人。”[10](P136)土地这个元素,化为家乡文学中最常用的词“泥土”,成为家乡艺术纲领中的最重要组合之一,即家乡等于对家乡风貌、民族、对族群的热爱。家乡文学的一大特点是以“地区精神”(Ortsgeist)来对抗“时代精神”(Zeitgeist)。“从泥土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是土地的灵魂。”[9](P17)。有了家乡的土地,就必然拥有这块土地上所承载的一切美好特质。与之相反,在家乡文学家的笔下失地的农人是可怜的无根的人:“土地就象他们的摇篮。…… 离开土地,他们就象落叶,飘零在寒风中。成为现代社会的破砖烂瓦!……失去了根。从家乡的土壤中拔起,不再有在别的地方生根的能力……。只有一点是共同的,无家可归。他们离开了土地,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大地母亲的力量。”[12](P362)
波棱茨(Wilhelm von Polenz)的小说《农夫比特那》(1895)中,农民的儿子古斯塔夫因在城中部队里服役久别家乡,回乡后见到父母的农庄,作者通过这个农民的儿子抒发了对“家乡”的感怀:“在朦胧的秋天的浓雾中,村落浮现在他的眼前。一种奇异的、不可名状的、感伤的情感涌向这位年轻人的心头。他在军营里面生活了五年,不再认识他自己的家。当然,这里没法跟都市比!但这里的茅草屋顶、泥墙、山墙上的横板都有其独特之处,这是城里房屋的豪华立面所无法替代的:这里是家乡!”[12](P135)在此处家乡的情感通过村落的整体图景隐隐地传导出来。这种情感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宽慰。郎贝因也写道:真正德国民族性格的教育或曰一切教育的特点在于,先离开家乡来到异地,而后又从异地再回到家乡[9](P120)。家乡文学家中郎贝因的影响最大,他提出的有关雅利安人重生的意识形态内容形成了家乡文学艺术纲领的最本质基础。在郎贝因的代表作《教育者伦布朗》中包含了家乡文学的许多重要元素,例如反理性主义、反大都市、对家乡概念的意识形态化等。
阿道夫·巴特尔斯也是家乡运动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倾向于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我们的家乡艺术与德国的最初朴的情感一脉相承。这个艺术要在全德国展开,这只是伟大民族家乡运动的一个部分,它的主旨是‘反击自由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观念中平庸的、千篇一律的作用以及空洞的帝国论调;它将国族情感建立在一种强烈的对家乡的感情之上,为现代人坚持一个家乡并再给予他这个家乡’。”[13](P5)巴特尔斯对“家乡艺术”这个概念的最终成形作出了关键性的理论建树。巴特尔斯认为简单的乡村生活中蕴含着使人健康的基本纲领。家乡文学中的重要对立“健康-病态”最早见于他的笔下。“家乡文学”中有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以这些词汇来表达家乡文学家的价值判断,例如“爱”“献身”“健康”。与所赞扬的家乡的健康、和谐的田园生活以及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相对立,“病态”“颓废”“堕落”等反映大都市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词汇也经常出现在家乡文学中。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马克斯·莫尔道(Max Nordau)从“病态”这个词又衍化出“蜕化”(entartet)一词[9](P54)。后来的法西斯文艺理论家常常接过“蜕化”这个词用来批判德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
亨利希·索恩莱(Heinrich Sohnrey)同样是家乡艺术中的重要一员,他在1894年创办了杂志《田野》(Land)并担任主编。他的作品的旨趣在于对工业社会到来之前的农业社会进行美化,作品语言充满了怀旧的感伤,以此颂扬农村生活,进而对文明、教育、技术革新进行贬损。“不是大都市,不,在外部的原野才有可能生长出新一代的诗人和艺术家。反对大都市、为诗意和艺术而进行的争斗才刚刚开始。”[14](P216)索恩莱将这一过程想象为生物法则和自然法则的发展过程;他以形象的语言来描绘这一意象:“常青的树木,带着新鲜的露珠,滴落在幽谷里。”而这正是大自然中的民族的写照。索恩莱总结道:“都市的对立面是农村。”[14] (P215)巴特尔斯则更为直接地喊出了:“远离柏林!”的口号,而获得许多家乡文学家的赞成,在这之后,又在这个口号之后加上了“前往魏玛!”或者“前往拜罗伊特!”等口号[9](P32)。魏玛成为许多家乡艺术家眼中最具德国特色的小城。一些家乡文学家在离开柏林之后,纷纷在魏玛定居。巴特尔斯、林哈特先后在魏玛定居,而瓦赫勒在拜罗伊特定居。家乡文学运动的最著名口号“远离柏林!”中的大都市“柏林”包含着所有家乡文学家视野中的都市负面因素,而在论证家乡文学艺术纲领时,对大都市的否定也往往成为家乡文学必要性的出发点。这些著名的口号体现出一群在大都市里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得不退回当年德国二三线城市的小资产者的基本观点和生活态度,也体现他们的狭隘视野和保守基调。
“农民精神就是家乡精神”[10](P128)在家乡文学中通过对乡村生活的美化,家乡概念形成价值体系,被置于其他价值概念之上。家乡文学对“家乡”概念进行了狭隘化和意识形态化。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家乡概念原有的众多含义被削减为“质朴健康的乡村世界”。家乡概念因而也被压缩到“农业-田园风光”这类元素上。这些元素的正面含义与带有负面意义的大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家乡”概念在家乡文学中也逐渐转变为反对“大都市”“大都市地狱”“混凝土山”“沥青荒漠”“都市丛林”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对家乡的渴望也随之变成了对“根”、对“简单生活”“乡村的田园景致”“对怡人的自然风光”的渴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与“毫无意义的都市”相比较对立。因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家乡文学”中的不少作品被视为文学价值不高的感伤俗文学。
在德语区的家乡文学较为集中地表现了保守思想,这一点较同时期欧洲其他工业国家的文学更为明显。法国、英国的文学中虽然有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问题的描述(如狄更斯的作品),但很少通过将城乡对立,对城乡进行二元化价值判断的方式进行。英法作家为大都市如巴黎或伦敦感到自豪,而德国家乡文学作家却对柏林这样在德国统一之后的大都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8](P14)。大都市被视为是家乡的对立面,被塑造成为一种造成“无根的存在方式”威胁性力量。这种独具德国特色的家乡文学及其后来的变种“血统与土地文学”体现了德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由于德国社会在政治、法制体制、社会心理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工业化社会的准备,因而对工业化对德国社会的冲击要大于其他欧洲国家。家乡文学中出现的城乡割裂状态不仅体现了德国的社会分裂,同时也体现了德国社会的思想分裂。现代文明和技术高速发展必然带来相应的价值体系的变革,而“家乡文学”所展现的价值取向与这一时代的变革完全脱节,是对因而它无论在思想倾向、价值取向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显得十分保守。
在家乡艺术中大都市被表现为颓废之都,是社会的泥淖,大都市体现文化低俗化。因此林哈特以“高原”这一意象以及“高雅艺术”这一概念来对抗都市文化所谓的低俗化。林哈特认为,大都市是繁复铺陈奢华讲究的处所,但这种文化品位比“没有文化更加粗俗”。家乡文学家认为,大都市是工业化、商业资本主义的处所。都市人口的不正常激增是一种罪恶,使得大都市如同吸血恶魔一般把周边乡村的血液全部吸干,造成整个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解体。因为这个家乡艺术家所代表的农业社会结构中的小农阶层和都市中的小资产阶层受到自下而来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挤压,所以反对工人运动的民主诉求,控诉整个社会中下层所陷入的社会经济窘境;他们同时也受到金融资本的威胁。林哈特在发泄对大都市文化的不满时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大都市中的文学、艺术和音乐。[9](P30)
在家乡文学家眼中的大都市的弊端首先表现在都市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业发展的中心,这种状况虽然能吸引很多人前往大都市,但在家乡文学家眼中却是负面因素。家乡文学家们反复强调自然科学与工业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心灵的枯竭以及文学艺术的衰退,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对立起来。这样的观点展现出强烈的反智色彩:“德国人历经自然的、天真的时代;随后又拥有科学的和自觉的年代;他们还将拥有艺术的、天真而自觉的时代。而最后一个时代是教育的顶峰。不必在其它的教育阶段非必要地停留太长时间,这样才符合这个民族自身的基本利益。而中世纪的骑士时代被新时期的教授时代所替代。现在最新的人类时代将要到来。德国人要在‘人’和‘教授’之间进行选择。”[9](P67)而郎贝因直接各个不同的“时代”相互排斥地罗列出来,从而使人得出当时的“科学”时代是未来时代的障碍。同时他将“教授”与“人”相对立,这种对立与后来法西斯统治时期将人分为“人”与“低等人”“人”与“非人”并没有多大差距。郎贝因以极端的言辞来否定科学:“所有的科学,无论是否是德国的,就其本质来看都是不高贵的。除非科学家本人也是造型艺术家。”[9](P46)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不过是进步的代名词,而进步在家乡文学家眼中却是一种负面价值,非理性主义是正面的价值。阿道夫·巴特尔斯将反科学思想表达得更直截了当:“我们不信任电报、铁路、蒸汽船、电灯、股票,并认为仍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是反动的。”[13](P194)
对家乡文学家来说语言是知识的赘物,而知识又是“意志瘫痪的原因,是一种反面力量,使人丧失创作力。”[15](P18)既然不需要理性,不需要分析,更不需要思考,那么家乡文学家就需要通过心绪(Gemüt)和内在性(Innerlichkeit)来替代这一切。过分强调“内在性”和“心绪”使激情在家乡小说中经常出现,而理性思考却少见。因为激情属于个体范畴,而激情却具备普遍性;激情可以摧毁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风和日丽时候的突然间出现的一种命运的风暴;而思考却能够将人从漂浮不定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证明的,去感觉或者什么也感觉不到”[11](P191)这意味着家乡文学家们摒弃理性,将非理性主义写入自己的创作原则。“感受”与“证明”的对立在家乡艺术中成为“智识”与“心绪”的对立,而最后演化为“精神”与“灵魂”的对立。
反犹主义是家乡文学和家乡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在家乡艺术中,通往反犹主义的途径很多。反理性主义、反国际主义、反工商主义、反金融资本主义、血统论、反大都市倾向都可以导向反犹主义。在家乡文学家眼中,犹太人与心灵、内在性等典型的德国民族特性无关,文学与诗属于一种犹太人无从知晓的灵魂范畴;反之,真正的德国人与现代主义同样无关,因为德国属于工业社会前的时代;家乡文学家将德国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浪漫化处理,这种农业经济结构与现代社会的金融资本主义无涉。这样通过把犹太人与金融资本划等号,将犹太人视为金钱的象征,从而把犹太人彻底地排斥在德国的经过诗意化的农村社会之外。在家乡文学家中阿道夫·巴特尔斯是反犹的主要吹鼓手。他在进行文学史写作时,以作家的种族属性作为区分作家的优劣的标准,这为后来的法西斯文学史家慕洛特之流留下了先例。1922年,在讨论德国的家乡文学和家乡艺术运动进行回顾时,巴特尔斯认为家乡文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犹太人是家乡文学的敌手,因为家乡文学能够增强德国的民族特点,所以就天然地成为了犹太人的敌人。而犹太人又控制了德国的报刊,所以犹太人就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来对付家乡文学。”[17](P197)
五、家乡文学的主要价值取向与评价
社会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合力使“家乡艺术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德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艺术潮流,它在1890年后的二三十年里形成了其最具特点的轮廓。家乡文学是家乡艺术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土壤是保守主义。通过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反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发展,它在极大程度上传播了文化悲观论、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反现代主义。它意图将整个德国文化的发展置于乡村和部族的基础上。1871年德国统一后,家乡成了“风貌”“民族特性”和“过去”的同义词,家乡这个概念同时也被赋以农业-生物化(在血缘意义上)等人种学的内涵。它的很多思想元素转入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中去。第三帝国的重要文学理论家慕洛特就曾经说道:“农民是北方德意志种族的最重要载体。”[16](P51)。
家乡小说的主题往往相似,只是人物活动的地理场景有所替换。家乡小说是通过对特定的社会模式、情节进展、时代关系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方面是通过将社会现实切割出一个部分来完成的。但是切割出来的这部分在小说中却不被视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成为特殊的社会生活全部。与之相应,家乡文学从文学传统中掘取了特定的主题和材料来进行拼凑,形成了一种文学史上的特殊组合。家乡文学的作家们过于沉浸在自己所营造的和谐的乡村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因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干扰,因为社会的发展既不符合他们对社会的期许和认识,又不符合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家乡文学正是他们对这种“干扰”的强烈反应的表达。从家乡文学流传的广泛程度可以看出,家乡文学的承载阶层如何来寻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平衡缺失的原因,以及他们希翼通过什么样的文学来确立一种新的存在稳定性。
在德国产生的与民族、土地、血缘等概念密切相关的家乡文学与欧洲的现代文学发展总体上趋势相反。家乡文学中展现的都市与乡村、文明与文化的对立与19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文化”与“文明”之争相互映衬。当时全欧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是,工业社会的形成抛开了一定的利益群体,社会多元性的性质日益彰显。现代工业社会需要以理性为基础进行分析、计划、计算才能够正常运转。而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家乡文学”运动恰恰以反理性的姿态来猛烈抨击现代社会的这一理性基础。家乡文学艺术运动的主要力量正是来自那些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那类人。对农民和土地的礼赞在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或许有一定意义,而在工业社会中则显得十分保守落后,给人以一种时代倒错之感。这种充满情绪地反对现代社会非人际关系的组织结构,实际上表达了惯于群集的那类人无法忍受在大众社会中的个人孤立,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社会地位危机恐慌的综合表现。
家乡文学与血统与土地文学(Blut-und Boden literatur)之间并无明显的过渡。赫尔曼·罗恩斯(Hermann Löns)被称作荒原诗人。他的历史小说《狼人》(Wehrwolf,1910)就介于家乡小说和血统与土地文学之间,罗恩本人成为创作血统与土地文学的榜样,他的代表作《狼人》对血统与土地文学的不少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血缘的力量源远流长,它能够跨越世纪、国家、政党甚至跨越语言;它比一切都更要强烈。”[9](P130)这部小说介绍雅利安血统的农民的生活史,小说中的血统元素后来得到了第三帝国时期文化当局的高度(的)赞扬。因为讲述了雅利安农民在三十年战争时期,通过斗争战胜了异族,从而获得了土地。这一点成为纳粹叫嚣夺取生存空间的先声。罗恩本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家乡文学过渡到血统与土地文学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从1900年至1933年,家乡文学在很多方面与血统与土地文学相通,但在进行评价时,如果直接将二者相提并论会造成二者之间关系的模糊。正如诗意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经过一定的变化进入家乡文学一样,家乡文学的内容和结构上的一些元素也经过改造进入了血统与土地文学。文学所呈现的内容更加尖锐化和极端化,例如在这个时期都市根本就不再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进入文学作品,也不再作为消极的图景出现。家乡文学是文学与社会历史形成一个的框架:1918年战败后,战败的后果及其通货膨胀不仅仅影响到原先的一些承载阶层,同时也危及了作为家乡小说的读者群的社会中层,因此农村的社会模式被视为最后的一个绝对安全的所在; 农民的形象也就再次成为一个原始的古老的指导形象。1933年后,文学与农村场景的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政治框架完全不同于家乡文学时期。
家乡文学在美学和思想上有一定缺陷,许多介绍德语文学史的书籍基本上跳过这个流派,直接进入对德国自然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派别的介绍,几乎不提及家乡文学的存在。但正因如此,德语文学史上后来出现的、又不得不提及的纳粹倡导的血统与土地文学则成了一个较为突兀的现象。家乡文学是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必须正视的文学现象。家乡文学所展现的是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冲突,较好地反映了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思想观念激烈冲突与斗争,是德国思想史发展一个脉络的重要一环,是在民族主义蜕变为种族主义过程中的文学表现形式。家乡艺术作为文学运动与德国当时方兴未艾的自然主义文学构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德语区家乡文学的介绍也极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Bredow, Wilfried von; Foltin, Hans-Friedrich. Zwiespältige Zufluchten:Zur Renaissane des Heimatgefühls. Berlin/Bonn, 1981.
[2] Schaal, Björn. Jenseits von Oder und Lethe.Flucht, Vertreibung und Heimatverlust in Erzähltexten nach 1945 (Günter Grass-Siegfried Lenz - Christa Wolf). Trier, 2006.
[3] Plessner, Helmuth.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politisch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Gesammelte Schriften VI, Frankfurt am Main 1982.
[4] Lämmert, Eberhard. Germanistik - Eine deutsche 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67.
[5]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 Conrady, Karl Otto.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Drittes Reich“. In: Germanistik - Eine deutsche Wissenschaft Beiträge von Eberhart Lämmert, Walther Killy, Karl Otto Conrady und Peter v.Polenz. Frankfurt a.M.1967.
[7] Rempel, H.. Aufstieg der deutschen Landschaft.Das Heimaterlebnis von Jean Paul bis Adalbert Stifter.Gießen (Lahn), 1964, S.139.
[8] Bastian, Andrea. Heimat.Eine begriff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in verschiedenen Funktionsbereichen der deutschen Sprachen. Tübingen 1995.
[9] Rossbacher, Karlheinz. Heimatkunstbewegung und Heimatroman. Zu einer Literatur-soziologie der Jahrhundertwende. Stuttgart, 1975.
[10] Langbehn, Julius. Rembrandt als Erzieher. Von einem Deutschen. Leipzig/Hirschfeld, 1890.
[11] Lienhard, Friedrich. ,,Heimatkunst“. In: Neue Ideale. Gesammelte Aufsätze. hrsg. v. G. H. Meyer, Berlin/Leipzig 1909.
[12] Polenz, von Wilhelm. Der Büttnerbauer. Berlin, 1909.
[13] Bartels, Adolf. ,,Heimatkunst. Ein Wort zur Verständigung“. In: Grüne Blätter für Kunst und Volkstum. München/Leipzig, H. 8 (1904).
[14] Sohnrey, Heinrich. ,,Der Kampf gegen die Großstadt (für das Volkstum) auf literarischen und künstlerischem Gebiete“. In: Heimat 2 (1900).
[15] Wachler, Ernst, Läuterung deutscher Dichtkunst im Volksgeiste. Berlin, 1897.
[16] Mulot, Arno. Das Bauerntum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unserer Zeit. Stuttgart 1937.
[17] Bartels, Adolf. Die Deutsche Literatur von Hebbel bis zur Gegenwart, 2. Teil:Die Jüngeren. Leipzig 1922, S. 179.
责任编辑:冯济平
Heimatliteratur in the German Language Zon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ZHANG Yun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
Abstract:The motifs of the German Heimatliteratur (regional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re the "agrarian area", the "soil", the "rustic life", the "home region" and the "blood-bond". Many writers of Heimatliteratur tried with these ideas to describe a traditional agrarian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which was fading away in the process of German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expressed a vehement skepticism against the rationalism, the modernism an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were embodied by the life in metropolis. They had a rather conservative inclination in aesthetic taste and in the way of thinking as well, and they we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ti-intellectual. The German Heimatliteratur is a transitional phenomenon to the offi cial German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Third Reich, the blood and soil literature.
Key words:German language zone; German traditional regional literature; traditional agrarian structure; modern civilisation;anti-intellectualism; literary phonomenon
作者简介:张芸(1965-),女,福建福州人,文学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德语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27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