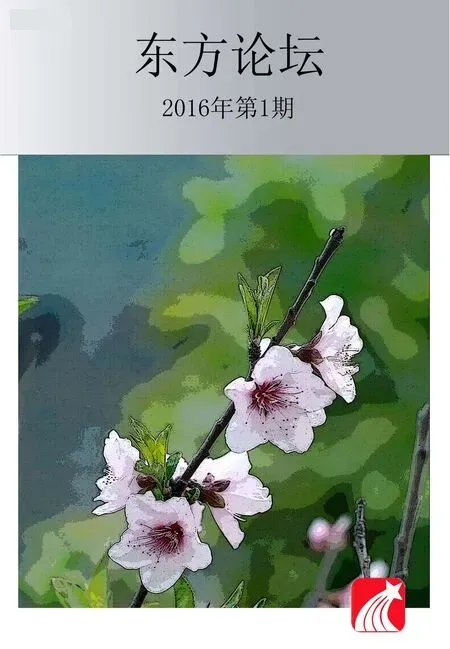“伦敦媒体经验”与老舍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之建构——兼及《四世同堂》英译问题
魏韶华 刘致远(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伦敦媒体经验”与老舍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之建构——兼及《四世同堂》英译问题
魏韶华 刘致远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伦敦媒体经验”指老舍寓居伦敦时期对弥漫于周围、无处不在的各种媒体的感知与经验,因为这些媒体超越了今天狭义的媒体概念,故称“泛媒体”。它关乎老舍一生的思想与创作。那些“泛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书写对老舍的心灵构成了极深的精神创痛,促使他建构起最初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属老舍的异国经验最为丰富,也属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最为清晰。这甚至直接影响到日后他在美国时期亲自参与的《四世同堂》英文翻译。
关键词:老舍;“伦敦媒体经验”;国家形象
一、“伦敦经验”中的“泛媒体”
1924年9月10日老舍乘坐德万哈号轮船抵达伦敦,是老舍生命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至1929年夏结束在伦敦的教书生活,伦敦5年是老舍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作家的“精神原点”。 对这一精神原点的意义,老舍是有充分自觉的,他认为自己设若始终在国内,就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
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为老舍带来了空前的视觉和精神刺激,这让他有机会和能力质疑中国的旧文明和旧生活,跳出中国文化的窠臼,从而完成现代文化人格的塑造。置身伦敦的老舍,以教书为主业,可是,他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这座大都市的环境氛围的包围之中,由这些全部体验所构成的观察、观感、思绪和思索等构成了老舍独特的“伦敦经验”。这一经验包括可视的器物文明比如街道、楼宇、美术馆、动物园、植物园、教堂、火车、汽车、电车、地铁(地道火车)、公共汽车(公众汽车)、自行车、摩托车(摩托自行车)、电话(电话机)等对老舍的视觉和精神刺激,而更深层的碰撞则来自精神软环境比如媒体环境等。
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领导着世界的潮流,其中,新闻传播业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 更是代表着世界传播业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老舍客居伦敦时期,英国传播业发展正步入大众化商业报刊阶段, 考虑甚至迎合大众趣味的一批新的大众报刊纷纷涌现,其代表是所谓的“ 三每报” , 即哈姆斯沃斯的《每日邮报》、皮尔逊的《每日快报》和哈姆斯沃斯的《每日镜报》。这些大众报刊的出现所形成的冲击波及到高级报纸原有的严肃风格。由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所带来的变化, 彰显了现代报刊的信息传递和舆论宣传功能, 读者群迅猛扩大。报刊想要获得办报独立性,就必须实现经济自主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告成为报刊的重要财政来源,其运作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的生存空间。在报纸购阅者急剧增加、定价降低的情况下,发行人都会出售报纸上的广告版面。这一英国新闻传播新动态,被敏锐的老舍纳入自己的视野:“工人们多是叼着小泥烟袋,拿着张小报,在家门口儿念。”[1](P604)在《我的几个房东》中,老舍仍能清晰地记起多年前伦敦的房东达尔曼,说“假若他还有什么说的,便是重述《晨报》上的消息与意见。凡是《晨报》所说的都对!这个老头是地道的英国市民。”他太太的“意见不但取自《晨报》,而且是由达尔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几段《晨报》。”他女儿“只看《晨报》上的广告。”还“在分类广告上登了一小段广告——教授跳舞”。小说《二马》中的李子荣有时候靠翻译广告增加收入;他还建议古玩店在“《亚细亚杂志》和东方学院的《季刊》全登上三个月的广告。”[1](P529)在一个媒体时代,人们知道,“做买卖顶要紧的是广告。”[1](P427)李子荣懂得利用广告效应做买卖,华工砸铺子,李子荣“故意的在事后躲开,好叫马威的像片登在报上,(一种广告,)。”[1](P622)伦敦一到夏天,“车站上,大街上,汽车上,全花红柳绿的贴着避暑的广告。”[1](P451)老舍在这里揭示了现代传媒对城市普通市民的精神影响。“外国人最怕报纸,可是也最喜欢把自己的姓名,像片,全登出来。这是一种广告。谁知道小玛力?没人!她一在报纸上闹腾,行了,她一天能接几百封求婚书。”[1](P607)东伦敦的华人砸马家铺子,报纸纷纷做夸大报道:“各晚报的午饭号全用大字登起来:‘东伦敦华人大闹古玩铺。’‘东伦敦华人之无法无天!’‘惊人的抢案!’‘政府应设法取缔华人!’……马家古玩铺和马威的像片全在报纸的前页登着,《晚星报》还给马威像片下印上‘只手打退匪人的英雄’。新闻记者一群一群的拿着像匣子来和马威问询。”[1](P618)通过一个事件的媒体反应,老舍表现了当时英国媒体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传媒与资本的结合。《二马》中写温都姑娘“手里拿着张报纸,正看最新式帽子的图样。”小饭铺里, “人人手里拿着张晚报,(伦敦的晚报是早晨九点多钟就下街的。)专看赛马赛狗的新闻。”“英国人自要有报看,是什么也不想说的。”[1](P445)“晚报上一大半是赛马和足球队比赛的结果,人们在早晨九点钟便买一张,看看自己赢了没有。看见自己是输了,才撅着嘴念点骂外国的新闻,出出恶气。”[1](P531)伦敦市民已深知负面新闻禁不住报纸的宣扬。[1](P599)不合世俗伦理的事,“报纸上一宣扬”,“一家子也全跟着毁了!”[1](P603)老舍认为普通英国人的观念是由报纸上看来的。杂志也开始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在小说《二马》中写到:“凯萨林坐在椅子上,掏出一本杂志来。”[1](P504)写到李子荣参加《亚细亚杂志》的征文,[1](P518)还提到“无线电广播”。[1](P531)进入老舍视野的媒体环境,除了报纸、杂志、广告、广播等狭义媒体以外,还包括与现代传媒有关的电影、戏剧以及市民通俗小说等。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其统称为“泛媒体”,而把由“泛媒体”所构成的环境称为“泛媒体环境”。
老舍关注“泛媒体环境”,关注“泛媒体环境”对普通人的影响,作为中国人,他更关注“泛媒体环境”对中国的书写及其后果。即西方人的“讨厌中国人也全是由报纸上,电影上看来的。”《二马》中的保罗就喜欢看“骂中国人的电影”[1](P532)普通市民的逻辑是:“设若中国不是一团乱糟,外国报纸又何从得到这些坏新闻呢!”“篇篇电影是那样,出出戏是那样,本本小说是那样,就算有五成慌吧,不是还有五成真的吗?”[1](P454)报纸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城市市民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晚报”“晨报”等各种报纸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也深深地影响着城市市民,而“泛媒体”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报道、虚构和想象最能刺激老舍那颗来自弱国之邦的脆弱的心灵。玛力看的“报纸上说:中国人屠宰了英国人。”[1](P419)她跟母亲辩论道:“我今天在报纸又看见三张像片,都是在上海照来的。他们把人头杀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不但是挂着,底下还有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在那块看电影似的看着!”[1](P459)在小说《二马》中留有老舍“伦敦经验”的直接印痕,其中多次提及白种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夸大报道和妖魔化书写:“东伦敦”是“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的是找些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就是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劳耐苦,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1](P394-395)这里,老舍深刻揭示了英国“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书写及其恶劣影响,受其影响,“中国人都好赌”“凡事守秘密”等都成为是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固定认识。[1](P613-614)出现于这部虚构小说中的这些文字是带着作者的深深隐痛的,其中有老舍全部“伦敦经验”的泪痕悲色。
“泛媒体”的中国观对英国人形成了一种类似精神控制的东西。仅以电影论之,在人类这些最早的活动影像里,匪夷所思的习俗、麻木狡猾的神态、病弱的身体,构成了其中的“中国形象”。保留在早期记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抬轿的苦力与轿子里的权贵,进出租界的外国军队,饥馑的孩童和无家可归的难民。[3]这里有真实,更有西方人对他者窥探的目光。除纪录片外,西方人当时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电影多是有明显辱华倾向的。《二马》中的亚历山大就以金钱诱惑老马参演辱骂华电影:“我现在帮着电影公司写布景……现在他们正作一个上海的故事,他们在东伦敦找了一群中国人,全是扁鼻子,狭眼睛的玩艺儿……这群人专为成群打伙的起哄,叫电影看着真像中国……导演的人看这群人和一群羊完全没分别;演乡景他们要一群羊,照上海就要一群中国人。”[1](P561)媒体影响人心形成普泛的社会偏见,又反过去影响媒体制作者。这个电影“是英国最有名一位文人写的。这位先生明知中国人是文明人,可是为迎合人们心理起见,为文学的技艺起见,他还是把中国人写得残忍险诈,彼此拿刀乱杀;不这样,他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许。”[1](P620)电影对英国市民心理起着决定性影响。老舍在伦敦时,“繁华热闹的伦敦”“七百万人”,足“有四百个电影院”。[1](P612)《二马》中的马威喜欢并且经常去看电影,“他常看电影里的英雄。”[1](P417)还常请玛力去看电影。当温都太太第一次见到前去求租房屋的马家父子时,就拿他们与电影中的中国人做比:“看着:这俩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心中未免有点疑惑。”[1](P412)普通英国人对中国人用毒药害人的“信仰”就来自电影。在玛力的意识中,“中国人的用毒药害人是千真万确,一点含忽没有的。”因为,“自要戏里有个中国人,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电影,小说,也都是如此。温都姑娘这个警告是有历史的,是含着点近于宗教信仰的:回回不吃猪肉,谁都知道;中国人用毒药害人——一种信仰!”[1](P418)老舍清醒地看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泛媒体”的中国形象书写脱不开干系。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人“要是不讨人嫌为什么电影上,戏里,小说上的中国人老是些杀人放火抢女人的呢?”[1](P454)在英国的中国人深知英国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1](P446)“温都姑娘警告她母亲留心毒药以后,想起前几天看的那个电影。”除了电影还有小说,马威就“看过英国小说——中国人用毒药害人的小说。”[1](P419)马威对玛力说:“你们看不起中国人;你们想中国人的时候永远和暗杀,毒药,强奸联在一块儿。”“我知道你们关于中国人的知识是由造谣言的报纸,和下贱的小说里得来的。”[1](P580)“外国人在电影里,戏剧里,小说里,骂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习惯。”“中国戏台上不会有黑脸曹操,外国戏台上不会有好中国人。这种事不是感情上的,是历史的;不是故意骂人的,是有意做好文章的。中国旧戏家要是作出一出黑脸曹操的戏,人家一定笑他不懂事;外国人写出一出不带杀人放火的中国戏,人们还不是一样笑他。”[1](P580)老舍指出这一偏见是“有历史的”。
二、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反思
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前,中国就已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是变化的“变色龙”,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被描述为一个富庶与贫穷、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的多面复合体。仅以英国而论,对中国的书写也由来已久且变化多端。早在14世纪,曼德维尔就在其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描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17世纪,英国甚至兴起过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一度成为英国人追逐的时尚。那个时期,英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美好的。进入18世纪后,英国国力增强,优越感助长了霸气,加之英国特使马戛尔1793年出使中国失利,遂在英国泛起一股污蔑中国之风。拜伦笔下的中国人是被嘲笑的对象,雪莱更是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蛮族”;狄更斯对中国也抱有偏见,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中国怎样可能有哲学呢?”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编》中,中国人更是贫困、奸诈、怯懦、愚昧的代名词。进入19、20世纪,人们对中国的想象与书写又从17-18世纪期间的理想化形象,变成了过激、好斗的滑稽丑陋形象。中国慢慢成为一个僵化、落伍、残暴的帝国,中国人傲慢无知、卑鄙无能、邪恶无耻而又野蛮好战,令人瞬间想到鸦片烟鬼和东方黄祸。值得重视的是马戛尼尔出使中国一百周年的1893年,英国的皮尔逊(Charles H Pearson,1830-1894)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一书,大力鼓吹有色人种尤其是中国人的“可怕”,它直接导致了席卷西方的“黄祸论”出现。
生活在英国的老舍对英国“泛媒体”中的中国书写非常关注。在小说《二马》中提及的狄·昆西就是一个对中国抱有种族偏见的英国作家。温都太太“把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找出来念;为是中国客人到了的时候,好有话和他们说。”[1](P411)可见19世纪以后,西方人已经把中国人和鸦片联系起来。狄·昆西现通译德·昆西(1785-1859)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其忏悔录《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自述其鸦片吸食经历,也在虚构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他声称自己宁愿同疯子或野兽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在中国生活。他关于中国的著述正是忠实地展现英帝国殖民心态的自白书。
以老舍在英国的时间推断,有一个小说虚构人物,老舍不会不知,他就是“傅满洲”。20世纪初出现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创作了13部傅满洲系列小说。主人公傅满洲集聪明、狡诈、凶残、狠毒于一身,是恐怖和邪恶的化身,令西方人防不胜防。角色原型来自伦敦警方的一桩刑事案件,案件涉及当时华人聚居的“中国城”莱姆豪斯区,罗默所任职的杂志社派他跟踪报道该案件,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当地华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罗默接触到一个绰号“金先生”的毒品贩子,是非法地下活动的组织者。罗默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13年,题为《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在以后陆续发表了《傅满洲归来》《傅满洲面具》《傅满洲新娘》等12部;另外还有中篇《傅满洲的暴怒》,三个短篇故事:《傅满洲的词语》《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眼睛》,使傅满洲这个中国恶棍成为英伦三岛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随着罗默定居美国,傅满洲系列借助美国的大众媒介——好莱坞电影,使得这个负面中国人形象广泛出现于美国的影视、广播、电视及报刊上,为美国随后的“排华”政策奠定了基础。正是受到电影中中国人固定形象的影响,“外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矮身量,带辫子,扁脸,肿颧骨,没鼻子,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儿,撇着嘴,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两条哈巴狗腿,一走一扭。”“中国人可有舍得钱买胰子洗脸的?”“中国人向来是哈着腰挨打的货。”“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袖子里揣着毒蛇,耳朵眼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炮,一挤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从心里打哆嗦的。”[1](P435-436)这似乎说的就是“傅满洲”。
中国的落后,外国强势媒体的歪曲报道与书写,使旅居西方的中国人处境艰难。“中国城有这样的好名誉,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的。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要说讲体面的人家了。”[1](P394-395)“普通英国人都拿中国人当狗看。”[1](P567)“全看不起中国人。”[1](P517)“巡警是动不动就察验”住在东伦敦的中国工人,“多么好的中国人也是一脑门子官司。”[1](P447)“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阴险诡诈,长着个讨人嫌的黄脸。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脏,臭,糊涂的傻蛋。”[1](P522)“普通的人谁不把‘中国人’与‘惨杀’联在一块儿说!”“和中国人在一块儿,生命是不安全的。”[1](P547)“转眼是工夫就有丧掉生命的危险。”[1](P568)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弱国子民,老舍感慨道:“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1](P394-395)在这里老舍揭示了,普通英国人的中国观与泛媒体环境有关,不能亲历中国的英国人的中国形象几乎全部来自泛媒体所提供的二级经验。当尹牧师带着两个中国人寻租住房时,温都太太说:“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她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把她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所得来的中国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1](P398)“为钱去服侍两个中国人!叫亲友看不起!”[1](P495)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和个人自尊心都很强的青年,老舍所承受的屈辱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三、“伦敦媒体经验”与国家形象传播意识
身处20世纪20年代伦敦的老舍对英国“泛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不仅有敏锐的关注,而且有深入的思考。这一精神创痛使老舍具有了国家观念,完成了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之构建,其早期作品尤其是《二马》《小坡的生日》等的写作带有了明显的对西方的抵抗性,他要通过自己的笔写出真实的中国人,他们有缺陷弱点,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西方人具有同样的意识、情感等。“黄脸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蔑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4](P172)老舍还分析了这些负面中国形象书写的来历和因由——傲慢与偏见:“我颇有几位交情很好的外国朋友。”“他们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为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另一派恰恰是与此相反。”“他们的主张不同,而主张之本质却是一样——偏见。”“他们都是外国人,都带着外国人那股自居高明的劲儿。所以他们不但谈论,而且要写成文章,教全世界都晓得他们是中国的救主。”“这些救主很难伺候。”“他们的偏见,以及用偏见养成的傲慢,使他们会把东洋与西洋的礼貌一概忘掉。”老舍提醒他们:“能把傲慢收起去,而虚心的多研究一点什么。中国正在改变,需要批评,而批评不能拿空洞的偏见作基础。”[5](P340)《二马》中出生在中国的保罗回国后在书房里这样“展览”他的“中国”:“一根鸦片烟枪,一对新小脚儿鞋,一个破三彩鼻烟壶儿,和一对半绣花的旧荷包。”[1](P469)在这里,老舍揭示了“中国”只是一个供西方消费的“他者”,只是一个猎奇的对象。《二马》中的温都母女外出歇夏,为求“新奇独份儿”,“帽子上绣着个中国字。”[1](P523)古玩店圣诞节前进货主要考虑英国人的消费心理:有中国刺绣,中国玩艺儿,中国旧绣花的衣裳。西门爵士买了件“老中国绣花裙子”圣诞节送给夫人。[1](P538)亚历山大的书房墙上挂着“中国人作寿的喜幛子”。[1](P560)范掌柜请求美术家在他的饭馆墙上画上:“小脚儿娘们,瘦老头儿抽鸦片,乡下老儿,带着小辫儿,给菩萨磕头。”“美术家所知道的中国事儿正和普通人一样。”“设若普通英国人讨厌中国人,有钱的英国男女是拿中国人当玩艺儿看。”[1](P569)正是出于这样的傲慢与偏见,“普通英国人知道的中国事没有一件是好的。”[1](P470)老舍深知,国家民族间的傲慢与偏见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是形成民族国家间隔阂的主因。直到40年代,老舍仍然持续关注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与交流。他说;“一点知识,最是误事。民族间的误会与冲突虽然有许多原因,可是彼此不相认识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6](P384)“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在一本西洋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小说里有这么一段:一位西洋太太来到中国——当然是住在上海喽,她雇了一位中国厨师傅,没有三天,她把厨师傅辞掉了,因为他用筷子夹汤里的肉来尝着!在这里,筷子成了肮脏、野蛮的象征。”“因此,我想,文化的宣传才是真正的建设的宣传,因为它会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敬,而后能互相帮忙。不由文化入手,而只为目前的某人某事作宣传,那就恐怕又落个一手拿一根筷子吧。”[6](P384-385)这些思考与老舍的“伦敦经验”尤其是英国“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书写有着密切的关联,媒体的责任是沟通,而不是制造隔阂。
除了媒体的偏见所造成的精神阻隔以外,中国的实际落后也是中国遭受歧视的主因。“英国的普通学校里教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知道中国事的人只是到过中国做买卖的,传教的;这两种人对中国人自然没有好感,回国来说中国事儿,自然不会往好里说。又搭着中国不强,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再说,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能看得起咱们!”[1](P460)面对外国对中国的否定性书写,作为中国人,一方面要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掌握国家形象传播话语权;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壮大自己。“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在今日的世界上,大炮飞艇就是文明的表现!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因为我们的陆海军不成。”[1](P471)“中国不但短大炮飞艇,也短各样的人才。”[1](P472)“写文章的要招人笑,一定骂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骂着没有危险。”“哪样学问是中国的特长?没有!普通人小看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缺点多了,简直的说不清!我们当时就可以叫他们看得重,假如今天我们把英国,德国,或是法国给打败!更好的办法呢,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顶有人才的!你要什么?政治!我们的政治最清明啊!你要什么?化学!中国的化学最好啊!”[1](P517)英国人的傲慢来自英国的强势:“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1](P584)老舍清醒地看到:“自要中国人能把国家弄强了,外国人当时就搁笔不写中国戏了。人类是欺软怕硬的。”[1](P620)
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一定也在老舍的关注视野之内。“因为念英文,在街上买了些二角钱一本的英文小说来念。”[7](P400)在这些报摊小说中充斥着迎合大众趣味的对中国的妖魔化书写。老舍说:“近年来西洋有许多描写中国人的小说,十之八九是要凭借一点知识来比较民族的不同;结果,中国人成为一种奇怪好笑的动物,好像不大是人似的。”他呼吁西方人“以描写人生的态度来描写中国人。”[8](P218)其实,老舍早期小说尤其是《二马》,其写作姿态明显带有对西方的抵抗性特征。在谈及《二马》的创作时,他说:“因为念到欧战以后的文艺,里面有几本是描写中国,我便写一个中国人怎样在伦敦。”[9]《小坡的生日》是这一抵抗性写作的延续:“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时期,想写一个华侨千辛万苦开辟南洋的小说,可是因为生活不够,没写成。”[9]这一遗憾在《小坡的生日》里得到了部分补偿。老舍一直想去南洋,就是“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像康拉德小说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优劣,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巨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9](P175)“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9](P176)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属老舍的异域经验最丰富,也属老舍在民族国家形象传播方面的思考最为深刻与持久。早期的“伦敦经验”使老舍比其他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关心异国的中国形象书写。为此,他呼唤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自觉,他批评中国人“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1] (P533)小说《二马》中说:外国人喜欢中国的老人,因为他们“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而“中国的青年们虽然也和老人一样的糊涂,可是‘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1] (P522)虽然空泛,可毕竟是进步。 他认定:“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1](P471)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台儿庄大捷后老舍的激动: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全世界的人都换了一对眼睛来看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开始认识我们的伟大。”“中国人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有骨气的民族。”[10](P520)
深深植根于“伦敦经验”的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不仅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而且直接影响到40年代他在美国所亲自参与的《四世同堂》英译。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并不是在原作基础上逐句翻译的,而是在翻译过程中,由老舍本人进行了大量删节,其动因是什么?我们以为,与老舍基于“伦敦经验”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有关。正是在遥远的英国,老舍开始把文学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其“文学原点”渗入了作者独特的“伦敦体验”,其中蕴含着以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强烈意欲。因为,他深切体会到,除自己的国家极度贫弱外,正是西方对中国的蔑视性书写使国家和子民受辱。在《二马》中,老舍通过几个普通英国家庭中的大部分成员对中国人的歧视与憎恶,揭示了英国社会普遍的排华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重要来源——不负责任的“泛媒体”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
当1946年老舍来到美国,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美国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同样令老舍难以忍受。美国人在19世纪末以来对中国的认识,不仅延续了欧洲对中国的否定性认知,而且到过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回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成为美国人认识中国的重要来源。如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所写的《中国人的素质》就把当时的中国描绘成《圣经》中的“大洪水前的人”即“史前人”。费正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影响了美国几代人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就是以这部书为素材“想象”中国和中国人的。到20世纪中叶,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作为一个族群的在美华人和作为“他者”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属性,一直在社会主导性强势话语下作为“被看”“被书写”的对象。
美国政府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交流,目的是希望他们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被邀方来说,他们也有着向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强烈意欲。老舍说:“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我觉得一部小书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11](P408-409)由于国家落后和对外文化和国家形象传播的缺失,“无论是在纽约,伦敦,还是罗马,我都得低着头走路。人家看不起中国人。”[12](P449)丰富的异国体验使老舍意识到,必须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使外国了解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中国。
老舍在赴美之前,已经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中国人并不是西方人眼中“阴柔的、停滞的、女性化的”中国,而是跟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一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力量已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四世同堂》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就是担负着这样的国家形象传播的使命而诞生的,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必须考虑美国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而这正是老舍在《四世同堂》英译中进行繁复删节的动因。
由于老舍有着较为明确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这就要求作品要尽可能使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老舍的潜在读者是广大的美国普通民众。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个发达的工商社会,大众阅读以休闲性娱乐性的快餐文化为主,故事追求曲折离奇,叙事节奏相应较快。正是为了赋予《四世同堂》英译本以“美国节奏”,老舍在与浦爱德的合作中对原作进行了大量删节,这些删节,大多表现在对原作“零时距”内容与枝节情节的删节上,如对祁瑞宣在学生去参加庆祝保定陷落游行时复杂心理活动的删节,如在原著第五十九段中详细介绍祁天佑在生意上的困顿无奈以及含冤自尽的过程,随后的第六十段与六十一段都是描写祁家人在得知祁天佑死讯之后的悲恸与埋葬过程。但是,故事性与戏剧性的增强并没有使英译本减少原著的思想性,相反正是英译本中包含的这种强烈对比,使读者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力量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老舍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取名《黄色风暴》,“黄色”暗含着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北平特有的天气状况,以及故事中人物的肤色特征;“风暴”是一个颇具力感与动感的词,它不仅指历史风暴,同时也暗含着中国人民的无比威力,以与西方人眼中的“阴柔,安静,女性化”的中国人固有形象区别开来。
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还体现在对小说中的风俗处理上。在赛珍珠的《大地》中,作者“主要体现在对土地神像、祖宗崇拜以及拜佛心理的记述:对婚、丧、生子风俗的记述;对城市下层贫民生活的叙述;对中国蓄婢纳妾、裹小脚的描写;对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对杀女婴和人口买卖、赌博、嗜烟等恶习的显示。”但这些富有“中国情调”的描写,未能摆脱美国社会所熟识的对中国的固有想象。而林语堂为了向美国人展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小说中对小脚、纳妾、婚礼等的详尽描摹可以见出林语堂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同时,仍未逃脱西方文学文本中的“套话”。《四世同堂》既是一部抗战小说、文化反思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风俗小说。作品按照中国传统节日顺序展开叙事,每章开头,往往紧扣战局变化,细致描绘古都年风节俗。这些节日不仅具有丰富的礼俗文化特点,同时也极富喜庆特色,例如在《四世同堂》中写到的中秋节、五月节、北平夏季的水果时节、祝寿等。老舍把大大小小的事件穿插在各种传统节庆的现实的凄凉气氛中,正是为了烘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同时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对北京民居风俗、民居建筑等的介绍。这些内容很多是“零时距”的叙事部分,在老舍对大量的“零时距”部分的删节中,这些风俗风物的介绍却被保留下来。从The Yellow Storm中,异国读者可以领略到中国人浓厚的人情味。
参考文献:
[1] 老舍.二马[A].老舍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 老舍.我的几个房东[A].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肖同庆.早年记录片里的“中国形象”[N].人民日报,2004-11-30(16).
[4]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老舍.批评与偏见[A].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 老舍.筷子[A].老舍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 老舍.读与写[A].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老舍.人物的描写[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0] 老舍.致台儿庄战士(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A].老舍全集: 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 老舍.旅美观感[A].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2] 老舍.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A].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冯济平
"London Media Exper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o She'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cating National Imag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Storm
WEI Shao-hua LIU Zhi-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The London media experience refers to Lao she's stay in London and his contact with all kinds of media or to be more exact, pan media. It has a bearing upon his thought and creation during his lifetime. The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pan media deeply hurt Lao She, prompting him to consciously communicate the national image. Among modern Chinese writers, Lao She's exotic experience is the most abundant, and his awareness of communicating the national image is the clearest. This even directly infl uence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Storm whil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Lao She; London media experience; national image; awareness of communication
作者简介:魏韶华(1963-),男,山东东阿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刘致远(1992-),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东亚影响力研究”(批准号:14BZW1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6-10-2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