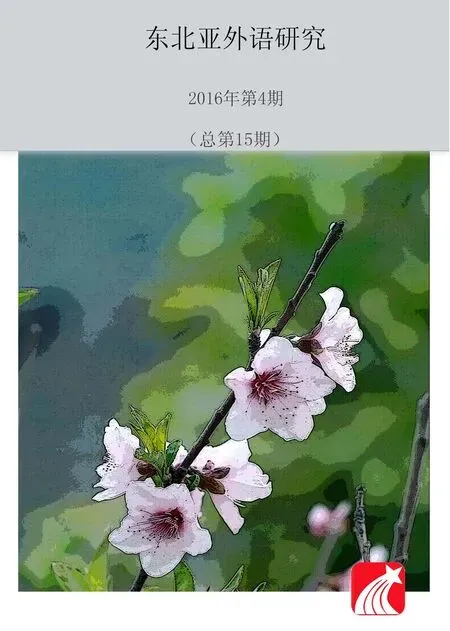自然不存,人之安在?
——论生态伦理观照下《夜猎》中的反乌托邦图景
郑永旺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自然不存,人之安在?
——论生态伦理观照下《夜猎》中的反乌托邦图景
郑永旺1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评论界对科兹洛夫的长篇小说《夜猎》的反乌托邦属性认识基于文本中与极权主义相关的内容,即这个世界之所以疯狂,是因为高压极权政治所致,人若要突破生存的困境,就要突破行为底线。本论文在生态伦理的视域之下,分析小说中世界末日图景的生成原因,指出反乌托邦的存在以上帝的缺席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为标志,在这样的时代,人只有放弃生存,才能获得生存。
生态伦理;反乌托邦;《夜猎》;生态文学
一、《夜猎》的创作基调与内容的关系
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崛起,一是与俄罗斯文化基因有关,这个基因就是“从俄罗斯文学的源头开始,大自然的形象就在悲欢离合的际遇中陪伴主人公左右”(周湘鲁,2009∶2);二是与20世纪兴起的世界性生态保护热潮有内在的联系,即文学除了审美作用外,还应有拯救自然的功能,“人类的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它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周湘鲁,2009∶6)。生态伦理强调,自然不是简单的“物”,而是有思想的机体,所以普里什文断言:“自然对人充满了敌意”(Пришвин М. М. ,1983∶424)。但自然对人类的敌意源自人类的戕害,这也是科兹洛夫(Козлов Ю. )的长篇小说《夜猎》所要强调的。其结果是人类与自然双输。
小说创作于1987-1993年之间,这是俄罗斯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以文化渗透等多种方式削弱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作者字里行间显然在暗示另外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帝国,那这种情况的成因一定与战争有关,而且这个帝国的环境不可能适合人类生存。
作家巴甫洛夫(Павлов О.,1998)指出,“《夜猎》所描述的图景代表了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未来的焦虑,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良心,而科兹洛夫、托尔斯泰雅等作家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称他们为边缘的现实主义作家”。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的看法,笔者认为,《夜猎》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并秉承了某些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小说中精确地指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作品在新现实主义的包装下,夹带了俄罗斯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私货,比如对死亡的认知,对神在世意义的领悟等,同时也隐约可见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元素,如对宏大叙事的解构等(转自科兹洛夫,1999∶4)①。但如果将问题锁定在作品的反乌托邦性本身,则可能忽略其中隐藏的另外一些重大问题,小说故事之所以充满了反乌托邦冲动,是因为“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是反乌托邦思想的镜像时期”(Юрьева Л. М., 2005∶9)。科兹洛夫的《夜猎》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在“界线”问题上是有重大区别的,《我们》中的“绿色长城”以外,是未受现代文明破坏的、相对原始的空间,至少I-330们还希望为自己找到一片绿洲,但对于《夜猎》中的安东们来说,那个美好的南极大陆,同样不适合生存。因此,《夜猎》是一部具有反乌托邦末日图景的、以生态伦理为底色的长篇小说。
《夜猎》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残疾人乐园”。主要讲述安东与叶列娜和残疾人的故事。安东跳火车后误入一片核污染区,在此邂逅残疾人格利沙。在离开这个群体独立生活之后,安东又遇见来自塔斯马尼亚并了解南极大陆国家的叶列娜。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佐拉,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一部分的精彩之处是作家塑造了一个奇特的老太婆形象,她的存在解释了无论是这个首都在努库斯的超级国家②,还是遥远的南极大陆,都不能为人类提供舒适惬意的未来。第二部分为“文化部长”。以安东进入省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为主线,勾勒出安东的人生从悲剧到喜剧然后再到悲剧的曲线。小说中的事件像许多反乌托邦小说一样,指向遥远的未来——2200年前后。安东所在的地区是毗邻意大利省的帕诺尼亚YI低地省。《夜猎》不是那种崇尚空洞的文字游戏和貌似玄妙的谈经论道之作,作者能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其本质,并以哲人的智慧之笔支撑在现实的土壤上来鸟瞰未来。但是,小说中的未来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如果极权政治体制没有垮塌的话,未来的地球只会遍体鳞伤。
反乌托邦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结局基本都具有悲剧色彩。依巴赫金的观点,如果“人的生活时空不过是统一而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片断”(巴赫金,1998∶76),那么人在这样随时可能丧命的世界图景之下,就是一种非常卑微的生物。悲剧色彩源自主人公安东性格的双重性:动物性③和人性。小说倾注大量笔墨来描写主人公的动物性。这种习性的养成和生活环境有关,在生态伦理观普遍被践踏的情况下,人变成动物几乎是进化的必然选择。从安东被送进保育院之日起,他就学会了运用森林法则为自己的生存争得可怜的空间。在核污染区,他为了活下去给格利沙等残疾人工作,在这些残疾人被杀害之后,他为了躲避追捕,藏于地下,以吃蚯蚓为生。小说以《夜猎》(Ночная охота)为书名颇有深意。“夜猎”中的ночной(黑夜的)缘自希腊语ξ,该词以各种词形渗透到斯拉夫语中,如古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为Нощь,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为Noc,其意为“一昼夜里从太阳落山到太阳升起这个时间段”(Ильяхов А. Г., 2010∶296)。但从整个叙事过程看,ночной显然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夜”是混沌之神卡奥斯(Chaos)的女儿,是世界万物的源泉。根据赫西俄德《神谱》的解释,正是这个“夜”生下了死亡、梦、衰落、忧伤、饥饿、欺骗和无序(Ботвинник М. Н.等, 1994∶103)。而“夜”所生下的几个儿女恰恰构成了这部小说中的人类生存图景,“夜”在书名中作为限定语预设了安东必须面对一系列生死考验。охота(狩猎)源自俄语动词охотиться,一般指人通过某种工具或者设置陷阱获取动物的行为及方法,一般来说,这个动作所指涉的客体为除人之外的野生动物。但小说对这个单词作了新的阐释。当安东发现自己的残疾人朋友被残酷杀害后,突然心中升起一股难以控制的杀戮欲望。
安东突然领悟,他心中所有复杂尖锐难以控制的感受事实上源于人对人的杀戮欲望……此时此刻他的猎物便是残酷地猎取了手无寸铁的残疾人的职业杀手……但他是个例外,他这个刚刚学会打枪的人却要去猎取真正凶残的猎人。
(科兹洛夫,1999∶ 149)
可见,“夜猎”表现安东个人命运的走向,旨在折射未来世界的疯狂与怪诞。所以,科兹洛夫笔下的现实“不同于叶·施瓦尔茨的《蛇妖》,也异于基·布雷切夫的《宠儿》,更有别于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现代童话”(转自科兹洛夫,1999∶3)。安东没有借助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完成自己命运的转折,他在一个残酷的、难以存活的世界里实现了从逃犯到文化部长的跨越。然而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依照“夜猎”所规定的手段挑战现实的苦难。因此,在2200年这个反乌托邦时空,安东必须成为一名善于“猎人.”的战士和嗜血的人形野兽。
安东的命运悲剧还表现为他对爱情的态度和他个人爱情故事的结局。在他所生活的世界里,连爱情这样高尚的、人类专属感情也可以通过赤裸裸的女性肉体进行生物学意义的分析,从而剥离了这种情感的崇高意义。他清楚地记得生物老师让教体育课的女老师脱去运动服,在桌子上摆出各种高难动作以解释爱情是什么,如生物老师所说的那样,“当两性的性器官一旦接触到一起,男人和女人便会迸出火山一样的激情,讨厌的性器官顷刻间会变成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宇宙昨天和今日,这短短的6-7分钟是人所梦寐以求的生活中的最终目的”(科兹洛夫,1999∶84)。然而,这6-7分钟仅仅是生理上的感受,与所谓的爱情无关。13岁的他就和一个叫康的黄种人姑娘开始了所谓的成人生活。康甚至可以当他的面和别人性交,这与动物的交配行为没有区别。而康姑娘所属的人种受核污染生育器官被破坏,所以可以与任何人发生关系而不用担心生育之苦。人慢慢退化成动物,或者不如动物。动物的性行为以生育为目的,而人的性行为以爱情为前提,但如果两者都缺失,那么性就变得十分丑陋不堪。爱情是美好的,以爱情为媒介的性同样是美好的,而且具有唯一性,“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会对性报以尊重”(劳伦斯,2003∶3)。但生存显然比获取性的享受更为重要。所以,当他在污染区邂逅叶列娜之后,他所遵循的森林法则开始发挥作用,即“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免遭背后的袭击,就要善于消灭自己的同类,这是安东的信条”(科兹洛夫,1999∶25)。尽管如此,安东身上依然闪烁着那个时代十分稀有的人性微光。这如微尘般的善以安东对爱朦胧的向往和对采取行动的诠释表现出来。小学时的玩伴,一个在那个时期十分罕见地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女孩被匪徒枪杀之后,他意识到爱的珍贵和失去爱的残酷。而当他的同学布鲁诺、康姑娘等人相信美好的生活愿景,为此宁愿去劳动训练营之时,他冒险跳下飞奔的火车来赌一下自己的未来。
二、安东视角下的人类生存悲剧
小说中几乎不存在安东缺席情况下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限知视角”所产生的叙事效应。科兹洛夫借用安东的目光让读者与末日图景照面。亨利·詹姆斯发现,“小说艺术的成功与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家所选择的视点”(转自殷企平,1998∶27-28)。视角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能否确定其中所描写的事件具有真实性和亲历感。而“事件”(событие)是指人物实现文本中“语义场”(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оля)的“穿越”(переход),这种“穿越”基于两点:第一,主人公的行为是不是作家和读者能够接受的;第二,“穿越”能否引发一系列后果,即如何能保证在主人公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他人物的活动具有合理性。正常情况下,以第一人称为基础视角的小说情节建立在主人公“知情”前提下,没有“我”的参与,任何其他事情的发生必须引发“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反应,才能出现“色生香味触法”的诸多可能。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扎米亚京的《我们》和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许多忏悔录体裁及自传体裁都喜欢这种写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限知视角”。虽然第三人称视角在许多大型史诗作品中被作家经常采用,并具有“上帝视角”的效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科兹洛夫显然对“上帝视角”进行了限定。这种限定关系体现为几个人物关系的链条。
第一链条是安东-路易-福凯依-斯列莎系列。安东通过路易知道自己的办公地点在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福凯依,从而也确定了斯列莎的特工身份。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地方,隐藏着庞大帝国的后门,这个后门就是操控国家的计算机。该视角强调濒临末日的地球看似被极权政治所控制,但超级国家存在不被人所知的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攻破的漏洞。
第二链条是安东-格维多-尼古拉-不管部副部长系列。前两个人是安东在匪徒占领省城后第一次政府成员选举会议上认识的,此二人一直想方设法诋毁Reinstallation,是安东生命最大的威胁。该视角描绘出安东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涯。
第三链条是安东-格利沙-叶列娜系列。安东在残疾人乐园的时光与这两个人密切相关。该视角强调人在任何恶劣的生存环境里都能为自己想出活下去的办法,描述人和自然博斗双输的过程和结果。
第四链条是安东-佐拉和奥马尔-科尼亚维丘斯-兰开斯特系列。该链条主要讲述安东如何从一名开小差的中学生成为文化部长的经历,描绘出在诸神之死的年代,人是如何变成上帝的,以及上帝又是如何被物化的末日图景。
然而,“限知视角”限制了安东的表达,或者说,安东由于个人的阅历、知识结构和年纪等原因,无法表达小说更深刻的意蕴,所以必须借助其他办法来增加“限知视角”的功能,即亨利·詹姆斯所推崇的“油灯说”(lamp),让一组人物围绕在主人公的周围,像油灯一样点亮主人公视线的盲点,这种办法可以解决“视点人物智力平庸时,过分依赖单一视角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殷企平,1998∶27)的问题。小说中这些“油灯”就是佐拉、叶列娜和科尼亚维丘斯等人物,正是他们补充了安东叙述的不足。
第一盏油灯是帕诺尼亚YI低地和南极大陆的知情者叶列娜。
独特的时空构成是反乌托邦小说的标识,小说中恶劣的环境成了反乌托邦时空的注册商标。除了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锁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段外,《夜猎》中存在一个与当下世界对应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南极大陆。扎米亚京在《我们》中明确了在“绿色长城”外存在一个野蛮人的世界,“长城”是两者之间的界线,该界线不仅仅是主人公Д-503的心理界线,也是一条实存的物理界线。在纳博科夫的《斩首的邀请》里,辛辛那图斯把这个世界用Там(彼岸世界)来表示,实际上这个Там不过是辛辛那图斯对可能现实的一种模糊理解,换言之,这个Там仅仅具有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在许多反乌托邦小说中,都存在一个与当下现实对应的可能的世界,《夜猎》亦是如此。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在于能给主人公(或小说中的其他人)以某种遐想或希望。
与《我们》中的D-503通过“古屋”,进入“绿色长城”外的世界不同,安东没有登上他所向往的南极大陆上的美好国度。
关于南极大陆的故事,由小说中的油灯之一叶列娜临死前讲述的,该大陆成了令安东魂牵梦绕的理想国。通过这盏“油灯”,安东看到了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理想国也是由极权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叶列娜打火机上一行白色的小字“光荣属于苏共”和“镰刀斧头组成的图案”(科兹洛夫,1999∶57)说明,那个以六个大胡子为首的国度其实尚没有消失,只是原来的极权主义者被人赶到了南极大陆,建立起了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对安东所在的世界而言,那个国家的确令人神往,遗憾的是,在南极大陆和安东的国家之间有一条人为制造的漂浮在海洋上的核污染带,任何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穿越这条隔离带是必死无疑的。很显然,核污染带具有《我们》中“绿色长城”的作用,只是该“长城”十分不友好。问题是,这个理想国和安东的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小说让人思考的地方。
这个超级国家充满了令人绝望的末日情绪,它是作为乌托邦的对立面反乌托邦存在的。换言之,这个整日在核污染区游荡的女人固执地认为,南极的极权制度要比她所在国家的制度优越,因为南极国家是按斯大林的计划打造出来的理想世界。
1952年11月18日,斯大林决定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然而上帝此时派天使降临导弹发射场。
(科兹洛夫,1999∶132)
这个奉行视“民主”和“自由”为“十分肮脏的东西”的南极之国,一切行为都受苏联共产党的控制(科兹洛夫,1999∶135)。小说中的苏共在被赶到南极大陆后,变成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组织。该组织利用对南极大陆之外的资源建立起一个封闭的乌托邦圣地。叶列娜所幻想的就是能再次回到那个美妙的地方。这个依靠核污染带保护自己的地方究竟到底是不是人类最后的伊甸园,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从南极之国的构建过程和人的生存方式看,这个地方同样是反乌托邦。“《我们》中大一统国里的人们通过对自由的有效控制使人们获得了无限的物质满足和享有统一的无差别的幸福生活”(Павлова О. А., 1997∶62),南极之国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各行各业正常运行的超大核反应堆,在《夜猎》中,这个地方相当于《我们》中的“大一统国”,但是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以牺牲超级大国的生态为代价的。安东一方面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筹划能够去此地,另一方面他深知,他面临的末日图景全是这个南极之国造成的,“我们在这儿虽生犹死,他们在那边花天酒地,用核废料毒害我们”(科兹洛夫,1999∶137)。叶列娜作为“油灯”的意义不仅如此,但“南极之国”的确点亮了安东对生活的渴望。叶列娜临死前所说的一番话更验证了她的确具有“油灯”的功能。
“你母亲叫什么名?”安东又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
“莱特,”叶列娜说,“太平洋方言的意思是‘光明’。当我在油轮上穿越死亡带失去知觉时,我朦胧之中感觉到妈妈在一道黄色的闪光中望着我,她本人就是一盏灯”。
(科兹洛夫,1999∶144)
正是这盏“灯”点燃了安东心中的希望,让他在以后的冒险生涯中能够勇于“猎人”,因为他时刻向往有一天能够来到这个梦想中的乌托邦。
第二盏油灯是玩转现实世界的计算机专家福凯依。
福凯依是小说第二部“文化部长”中的一盏重要“油灯”,他照亮了超级大国一个不被人知晓的角落,该人物的意义在于诠释科学技术这个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元素在该作品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且暗示人对自然所犯下的罪过,技术是脱不了干系的。
安东的办公地点是市图书馆,此处的看门人福凯依是以酒鬼的形象出现的,而作为知识的圣殿图书馆所收藏的最后一本书是2014年出版的《民主主义者台式日历》,文化产品在一个匪徒横行的社会是奢侈品。当生存成为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时,文化不过是当权者统治民众的遮羞布。因此,当安东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出现在《民主报》报社的时候,他敢于用手枪威胁总编要在“明天报纸登上天气很热”(科兹洛夫,1999∶283)的字样。与《我们》、《美妙的新世界》和《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夜猎》缺少技术主义的气息,除了在描述核污染和武器(如直升飞机、坦克)之外,只有极少的几处情节出现了和电脑设备相关的信息,如在召开第一届政府成员选举会议上,当兰开斯特大尉发言时,安东发现,“一些人掏出便签纸,还有一些人在膝盖上支起Notebook,随时准备记下大尉英明的思想”(科兹洛夫,1999∶261)。在缺少技术主义气息的环境里,到处充斥着依靠机械暴力的帕诺尼亚YI低地省竟然在图书馆里有一台能操控安东命运的计算机。安东因自己的Reinstallation政策的失败面临死亡之时,福凯依告诉了他,这个庞大的国家行政中心和各省的联络全依赖计算机,如果能使最高权力机关相信,安东的政策是成功的,那他将躲过这场劫难。
“老人家,”在那天夜里安东将床上醉醺醺的福凯依扶起,“我们要编写一个程序,其要点如下:中央选举委员会承认大选结果,承认除格维多、尼古拉和不管部副部长之外的所有政府成员的任命决定;名为Reinstallation的新思维理应受到表彰,为此中央将从国家预算中拨出10万亿卡拉卢布支持帕诺尼亚YI低地省;重要要求邻省要与帕诺尼亚保持友好的关系,并如数归还偷走的车皮……”。
(科兹洛夫,1999∶366)
技术掌控命运的命题在小说中并不成立。技术以设备为载体,计算机的使用者福凯依尽管通过黑客软件成为亿万富翁,但他之所以依然蜗居在图书馆肮脏的小屋里喝着散发霉菌气味的自酿啤酒,是因为在一个拥有金钱缺少支配金钱的武器的现实里,金钱毫无用处。拥有安装了红外瞄准镜狙击枪的兰开斯特大尉最后被人用枪狙击,其肥壮的尸体制成食品出售,因为在一个缺少正义和公理的世界,自认为拥有狙击枪就是上帝的兰开斯特忘记了,匪徒和政客之间没有区别,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就是生存的铁律。福凯依的故事说明,科学技术必须在理性的约束下才能为人类造福,否则就会像安东所断言的那样,“技术,尤其是复杂技术永远是与人敌对的。它仿佛会读懂人的想法并在决定性的时刻……进行破坏”(科兹洛夫,1999∶395)。福凯依让安东知道了超级大国的运行仰仗计算机网络,这网络让福凯依生财,让安东的Reinstallation获得短暂的认可,最后也是网络让安东面临灭顶之灾。
三、上帝是谁
作为一部在生态伦理观照下的反乌托邦小说,《夜猎》除了表现女性在世界末日图景中的悲惨命运外,还提供了末日图景中理解信仰和宗教的新思维。
信仰和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每个民族,因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信仰和宗教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不过,在卡西尔那里,信仰和宗教都是神话思维的结果,他在《人论》中对此的解释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原逻辑的、神秘的东西,都是神话解释或宗教解释由之出发的诸前提,而不是解释的方式”(卡西尔,2003∶127)。但信仰和宗教合并一处成为不可拆分的思想共同体是在信仰被谱系化之后的事情,是人们把一种普遍的神话思维当成确定不疑的真实,并按照世代相传的仪轨加以强化之后的事情,比如,当人们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和超自然现象感到迷惑时,当人们希望摆脱死亡获得永生时,信仰作为宗教的形态开始产生。但“信仰(вера)一词缘自拉丁文(verus),即俄语的правдивый和верный,其意为说真话,即信仰者认为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是真实的、正确的和合法的”(Ильяхов А. Г., 2010∶97)。但宗教(религия)则为信仰者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религия一词缘自拉丁文religio,其意为“虔诚”、“圣物”和“崇拜之物”(Ильяхов А. Г., 2010∶376),其最初的含义为“基于对神(Бог)和诸神(боги)信仰的前提之下的世界观和世界感受”(Ильяхов А. Г., 2010∶376)。但总体说来,上帝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从而把上帝作为实现永生诉求的不可思议之物。所以,死亡成为宗教信仰得以广泛普及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卡西尔所说的人之所以信仰宗教,在于“宗教产生于对神的绝对依赖感”(卡西尔,2003∶144)。但是,依赖感的存在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人们借助宗教真切地触摸到了上帝的力量,即便这种力量实际是幻象;第二,宗教和权力联姻,使得信仰成为捆绑人们思维的绳索。
《夜猎》中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但人们摆脱死亡的愿望并未消失。宗教与信仰在小说中的人物那里,成为对上帝的戏谑,成为统治者或者个人攫取权力以及震慑民众的工具。所以,与其说把反乌托邦世界中的基督教理解为“世界观和世界感受”,不如说是以宗教之名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话语。于是,宗教在危机四伏“人可以猎人”的环境中演化出新的形态。
上帝是《夜猎》的关键词,无论安东,还是小说中的其他人,都反复以上帝的名义或者以否定上帝的名义来确定自己行为及信念的合法性。而上帝到底是谁,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人们说出“上帝”(God/Бог)这个词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拟人化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在圣经的《旧约》里,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捏制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上帝首先是“他”而不是“她”,弗洛伊德指出,上帝是“一种父亲的替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被夸大了的父亲……他是一个在童年世代所看到和体验到的父亲的摹本”(转自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2007∶156)。简而言之,所谓的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权威之化身。但在安东所生活的2200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生存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国家仅仅是一种观念之时,人所仰仗的权威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而是武器——一种能替代上帝的新宗教,安东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新宗教的主要特点是将武器神化,从袖珍手枪到坦克和导弹运输车之类的庞然大物都有了相应的神位”(科兹洛夫,1999∶8)。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空间里,上帝一定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复数概念体现为:第一,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上帝就意味着混乱,而且上帝不一定是以“圣灵”(Святой дух)的方式存在着的;第二,上帝有很多其实就意味着上帝已死。
如果不是以“圣灵”的方式存在,那么上帝一定会以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又因为上帝是善的化身,所以权威性在场的结果是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实际情况相反,在叶列娜看来,世界上的一切混乱皆是上帝所为,“上帝是有一回打开其中的一个地狱,把自己的圣子接入天堂,另外一次上帝将人分类,让一部分人进入如阴间一样的乐园,上帝为另外一些人在充满生机的地球上建起了这所人间地狱,其内部情况和阴间的天堂一般无二”(科兹洛夫,1999∶33)。安东和叶列娜等人的绝望来自上帝的沉默,所以,当安东坐进直升机驾驶室准备开动这架从未接触过的机器怪物时,他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被野蛮的无序所统治,野蛮的无序如果被严明的有序所取代,另一种更加野蛮的无序会取而代之”(科兹洛夫,1999∶174)。野蛮不但可以制服另外的野蛮,也可以对付机器,“他越是果断地驾驶,飞机反而愈是驯服”(科兹洛夫,1999∶174)。兰开斯特大尉相信上帝,但他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立陶宛人,这个“上帝掌握着能使人产生美德的神秘射线”(科兹洛夫,1999∶222)。作为这个地区最有权力的人,当他端起安装了红外瞄准镜的狙击枪时,感觉自己就是上帝,上帝“是一切现实存在”(科兹洛夫,1999∶224)。当然,对于斯列莎来说,“巴鲍斯特拉斯·唐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巴鲍斯特拉斯”(科兹洛夫,1999∶285);对于福凯依来说,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信息流和数据包;对于佐拉来说,她所能支配的身体就是她的上帝,上帝就是能玩转男人的女性性器官。但对于安东们而言,上帝是个摆设,他虽然以各种名义在场,其实这种在场等于缺席。复数的神等于宣告上帝真的死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没有明确告诉读者上帝死亡的原因,但对上帝之死可能的原因作了暗示,这暗示的背后是人的身影:
真的,人是一条肮脏的河流。为了接纳这条河流,人们必须是海,且本身并不变脏。
(尼采,2000∶7)
几乎可以确定,人的肮脏可能是造成上帝死亡的原因。人必须是海,才能洗净自身的肮脏,但人在尼采的眼中是卑微的生物,“你们走过了由蠕虫变人的道路,可是你们中仍有许多人是蠕虫”(尼采,2000∶6)。反乌托邦小说《夜猎》的末日图景就是蠕虫们的杰作,这种图景之所以和上帝是谁的问题联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宗教信仰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基因,但在《夜猎》中,这种基因发生了变异。而基因的变异往往和人所受的污染有关,污染可以源自核辐射,也可以与人的价值取向有关。这种变异甚至和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任光宣等,2010∶24),另外,按罗兰·巴特的说法,“上帝的观念通常不可避免地与真理、在场、启示、意义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转自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2007∶157),即上帝虽然是虚拟人的形象和幻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摆脱他的话语。因为上帝就是创造世界的to be句型,即“使……存在”,何光沪把这种句型理解为上帝神性的显现。
摩西五经说上帝耶和华是“自有永有”(I am what I am),“有”即存在,这里“存在”的原文有“使……存在”之意。因为耶和华即雅赫维的原文Jahweh或Jah,与西伯来动词jyh或hwh(是、在)有关,这个动词有运动的内涵,有“导致……存在”之意,所以世界的本源即耶和华本身,就是一种赋予存在的活动,即创造活动。
(何光沪,2003∶187)
《夜猎》没有否定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原创者的想法,但否认这个原创者拥有继续驾驭这个世界的能力,否认他是唯一支配万物的力量。to be对于安东、兰开斯特和科尼亚维丘斯等人来说,世界不仅可以是被创造之物,而且还可以是可改变之物,改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破坏是改变,使其美好也是改变,改变是to be的意义所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④强调上帝和意义之间的联系,“道”即语言、即逻各斯、即意义,但这个意义的实现即便在宗教和信仰之中也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一种就是“自有永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弗雷泽所提到的宗教的权力诉求,“如果宗教所包含的首先是对统治世界的神灵的信仰,其次是要取悦于它们的企图,那么这种宗教显然是认定自然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塑的或可变的,可以说服或诱使这些控制自然进程的强有力的神灵们,按照我们的利益改变事物发展的趋向”(弗雷泽,2006∶53)。安东和兰开斯特等人同样在宗教中看到了这种企图,任何当权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玩转宗教。
《夜猎》对上帝存在意义的阐释实际是使人回归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洞穴喻中所看到的景象。安东就如同那个习惯了在洞穴生活的人,他把上帝比做那射向他眼睛的夺目阳光,这道阳光让他所看到的世界发生了变异,具体而言,上帝又是构成自我心理安慰的工具,是 幻象。鲍德里亚仿真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幻象”(simulacrum)和“仿真”(simulation)强调,西方的全部信念似乎都押在所谓“表征”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赌注上:即一个符号可以指向一个深层意义,一个符号可以和意义交换,而且,这一交换是得到上帝的保证的。幻象的产生也与尼采之“上帝死了”的言说有关,“上帝之死”的负面后果是“否定上帝就意味着否定世界背后的任何终极目的,结果就是否定我们的生活因之而可能具有的意义背景”(格里芬,2003∶95)。上帝之所以可以模仿是因为上帝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信念符号,所以,在安东的眼里,圣经不再神圣,上帝不再庄严,信仰是自我欺骗的言说。早在1922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里,斯宾格勒(2006∶464)就指出过,上帝死后,人可能会摹仿上帝,而且这种摹仿是有原因的,“他(人)胆敢扮演上帝的角色;因此很容易理解:这些人为的事物——因为在这里,技艺是作为自然的对立概念而出现的——最早发明者和专家,尤其是锻工技艺的保护者,何以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且视情况而将他们看作是敬畏和恐惧的对象”。人创造了自己的崇拜对象上帝,认为他能够凌驾于人之上,但是,当上帝无法让他的独子耶稣在世间行使三种力量(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所说的“奇迹、神秘和权威”)时,当武器具有和这三种力量相同的功能时,人不再战战兢兢地“胆敢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像科尼亚维丘斯和兰开斯特等人一样,毫无顾忌地称自己就是上帝。
宗教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神向自己虔诚的信徒许下了无限美好的后生命状态,以消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但是,当神发现他所创制的世界已经坏掉,他同样可以借助洪水等灾害毁掉他的子民,如其所言,“我要使洪水泛滥到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⑤。《夜猎》的人物对上帝可以毁灭一切的言说很感兴趣,因为这种话语为现实的可怕寻找到了一个无法证明的借口,比如叶列娜在谈到上帝与毁灭关系时就发表如下宏论:
上帝之永恒完全是上帝自己将一切对自己有利的答案归于自己的账下,而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说成是人类的罪恶,这未免有些荒唐。
(科兹洛夫,1999∶45)
叶列娜信仰上帝,但她的信仰随着她生命走向终点之时发生了变化,她对上帝的“善”提出质疑,“随着我的生命里程的日趋缩短,我对上帝的信仰也日趋摇摆不定”(科兹洛夫,1999∶44)。而她的朋友安东对上帝存在意义的理解和死亡相关。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个人的生存是以他人死亡为代价的,即“一个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哪怕是危险的行动,只要该行动以别人的死亡来延缓自己的死亡就行”(科兹洛夫,1999∶351)。换个视角看上帝和安东的关系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在兰开斯特眼里,上帝是偏爱安东的,他让很多人死于非命,但却让安东能够死里逃生,“上帝为什么让那么多的人白白送死,偏偏让你死里逃生?”(科兹洛夫,1999∶223),但对于安东而言,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了解死亡世界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害怕死亡,越是害怕,越可能死去,所以,“安东不怕死。死亡和工作、睡眠、性及饮食一道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兹洛夫,1999∶49),因为安东比任何人都清楚,上帝对人的“最终奖赏只能是死亡”(科兹洛夫,1999∶351),既然如此,何不把死亡当成自己的上帝进行战斗呢?
信仰得以深入人心的条件(除了国家的干预之外)就是有一些愿意为宗教践行自己信念的人,要有一些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或者《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一类的信仰者,但是在2200年的世界,这样的信仰者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从未显示过他的神迹。这里的景象与瓦尔拉莫夫在《沉没的方舟》里所展现的图景十分相似,人的精神世界之丧失使得妖孽丛生,《沉没的方舟》中的柳博之所以能够用“末约教会”的名义为非作歹,是因为俄罗斯处在神已经离场的时代,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谈及的酒神精神占统治地位的蛮族文化时代。在《夜猎》中,神离场的时代已经降临,任何以上帝的名义组织起来的活动都无法唤起人们信仰的热情。按理说,遍地死亡景象的帕诺尼亚YI低地省更能激发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宗教能够以如此局面向人们暗示,宇宙之中存在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表述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⑥,但遗憾的是,神未能显圣,因为这个100多年都没有出版过书籍的地方,这些关于上帝的故事只能是传说,而传说最容易被个体的需要所异化。诸个体中不仅有貌似正常人安东,也有经历核辐射的妓女、刑事犯、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比如一个经过了九年辐射伤害的人们突然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类物种,他们“想在钽铀放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建党工作。签名,盖戳,一切都搞得有模有样”(科兹洛夫,1999∶219)。人类异化的力量如此可怕,以至于导致文化的丧失,除了安东的那本《堂吉诃德》外,已经找不到可以传承上帝神圣力量的载体了,于是,上帝在反乌托邦的末日图景中就是一个虚构的真迹。
注释:
① 本段引用信息出自于笔者和傅星寰共同翻译出版的《夜猎》中序言部分“世界末日之后的追寻——破译<夜猎>(代序)”。
② 根据小说的交代,这个城市位于吉尔吉斯。
③ 这里的动物性特指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残暴化过程,强调人性特征的缺席。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
④ 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
⑤ 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17节。
⑥ 新约·罗马书第4章第17节。
[1] Ботвинник М. Н., Коган Б. М.,Рабинович М. Б.,Селецкий Б. П. 1994.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 Ильяхов А. Г. 2010.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нтичные корн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Z]. М.: АСТ·Астрель.
[3] Павлова О. А. 1997. «Мы» Е. Замятина как роман-антиутопия (к проблемам жанр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A]. Павлова О. А. Твор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Е. Замятина: взгляд из сегодня в 6 т. т. 6[C]. Тамбов: Изд. Тамб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4] Павлов О. А.1998. 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OL]. http://lib.ru/ PRОZA/PAVLОV_О/kritika,2010-12-3.
[5] Пришвин М. М. 1983.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 5[M].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6] Юрьева Л. М. 2005. Русская антиутоп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 ИМЛИ РАН.
[7] 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 2007. 汪正龙 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 巴赫金. 1998. 晓河 贾泽林 张杰 樊锦鑫等译. 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9] 弗雷泽. 2006.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译. 金枝[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0] 格里芬. 2003. 孙慕天译. 后现代宗教[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1] 何光沪. 2003. 月映万川[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卡西尔. 2003. 甘阳译.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3] 科兹洛夫. 1999. 郑永旺 傅星寰译. 夜猎[M]. 北京:昆仑出版社.
[14] 劳伦斯. 2003. 张丽鑫译. 性爱之美[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5] 尼采. 2000. 黄明嘉译.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6] 任光宣 刘涛 任明丽 陈方. 2010. 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7] 斯宾格勒. 2006. 吴琼译.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 上海:三联书店.
[18] 殷企平. 1998. 詹姆斯小说理论评述[J]. 外国语,(4)∶25-30.
[19] 周湘鲁. 2009. 俄罗斯生态文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
With the Nature Gone, Where can Human Beings Exist?——The Prospect of Anti-utopia in Night Hu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The critics’ recognition of the anti-utopia attribute in Kozlov’s Night Hunting is based on the contents associated with totalitarianism in the teхt. Namely, it is the high pressure of totalitarian politics that caused the craziness of the world. If one wants to survive the plights of living, he ha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om-lines of all sorts of behavior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by eхamining the reasons that the Doomsday vision generates in the novel, holds the opinion that it is the degra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bsence of God that mark the anti-utopia reality, and if one wants to survive in a society like this, he must ignore life.
ecological ethics; anti-utopia; Night Hunting; ecological literature
I106
A
2095-4948(2016)04-0003-08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13&ZD1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研究”(06JJD75047-9900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化思潮演变及其影响研究”(14JJD740002)的阶段性成果。
郑永旺,男,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