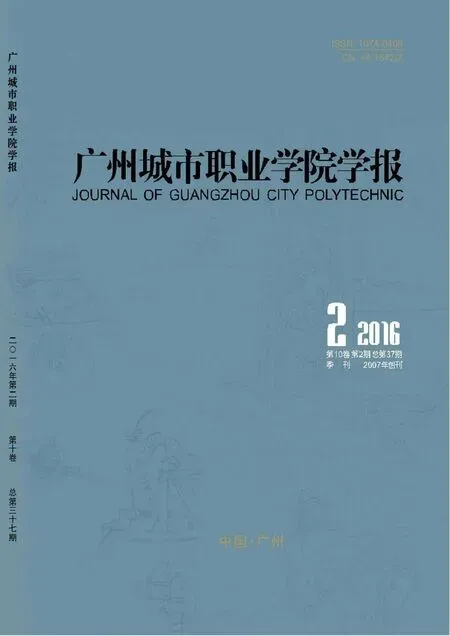《阿Q正传》经典地位的三维解析
周逢梅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阿Q正传》经典地位的三维解析
周逢梅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阿Q正传》的经典地位可以从思想性、文体学和艺术性三个维度进行解读。无论从解剖社会和国民心理的思想深度,还是对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性的文体实践,及融通中外、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上来看,《阿Q正传》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其文学经典地位不是一般的小说能够轻易取代的。
关键词:《阿Q正传》;经典;思想性;文体学;艺术性
在鲁迅的作品中,《阿Q正传》大概是人们研究和谈论最多的小说。这部小说早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近些年来又被评为“影响世界历史的100部名著”,甚至在许多外国百科全书和辞书中,都可以查到关于《阿Q正传》和阿Q的条目。而国内对《阿Q正传》的研究和阐释更是数不胜数,截至2015年3月,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阿Q”为篇名的文章已达两千多篇。这些都足见《阿Q正传》的文学经典地位。然而,近来学术界也有不少质疑《阿Q正传》艺术成就的声音,媒体上也时有《阿Q正传》从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除的报道,并引起热烈讨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部小说的经典地位的认识分歧。本文试图将《阿Q正传》放到中国小说史上,从思想性、文体学和艺术性的三重维度对其文学经典地位作出解析。
一、思想性维度:解剖传统社会和国民灵魂的杰作
中国古典小说成型较晚,一开始就不能不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由于儒家“崇善”倾向[1]和“文以载道”的精神长期占据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流,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与社会真实性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的距离,以致小说的虚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的真实缺陷。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瞒骗。”[2]中国小说中的“大团圆”表面上是娱乐读者,实则是借这种皆大欢喜的形式愚弄读者,在整个国家民族病入膏肓的时候仍以这种形式“娱乐”读者,则无异于让可怜的读者饮鸩止渴,“娱乐至死”。《阿Q正传》最后一章明明写的是阿Q糊里糊涂地被审判和执行死刑,却以“大团圆”为题,这种设置不仅仅是反讽,更是对传统叙事文学虚伪性的彻底颠覆。
因此,深刻的批判性是《阿Q正传》超越于传统小说的一个显著标志。不仅如此,这也是支撑其文学经典地位的一个首要因素。在《阿Q正传》的研究史上,大体存在两种典型的研究模式或解释路径:一种是论述阿Q的苦难遭遇和他走向“革命”的必然性,认为鲁迅借阿Q表达了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评,这种模式可以称为“革命话语模式”;另一种是以阿Q的愚昧人格作为基点,论证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认为鲁迅是在借阿Q表达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愿望,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启蒙话语模式”。两种模式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然而,“革命话语模式”和“启蒙话语模式”至少在一点上是能达成共识的,那就是《阿Q正传》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指向,前者尖锐批判了封建制度和传统社会精英对阿Q这一底层农民的残酷压迫,后者则深刻揭示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统制下的扭曲的国民性,因此,“革命的寓言”和“启蒙的寓言”背后隐藏着同一个寓言,即“社会历史的寓言”,或者说,如何医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病症,进而拯救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
(一)在中国小说史的思想谱系上,《阿Q正传》首次通过阿Q这一底层农民形象,深刻揭露了国民灵魂的丑陋。中国古典小说虽然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但是无论贾宝玉、林黛玉、诸葛亮,还是孙悟空、林冲、鲁智深,人物形象虽十分丰满且具有鲜明特色,但很难说哪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国民的典型性格,因而几乎都只有个体的意义。这里的原因大概在于:第一,上述人物形象基本上不属于纯粹的底层民众,无法代表中国最大多数的普罗大众;第二,从“崇善”角度塑造人物形象,容易导致人物形象的高大化和完美化有余,而批判性和深刻性不足。第三,古典小说作家限于当时的条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缺乏中外比较意识。《阿Q正传》则不同,阿Q属于农村中的短工,即雇农,处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物质和精神上都极端贫穷,但又积聚了中国农民的许多负面性格:愚昧麻木、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软怕硬,等等。这样一个底层“小人物”,没有姓名、没有来历,更谈不上有任何功绩,鲁迅竟然要郑重其事地为他“立传”,显然站在同情他的立场的。但鲁迅揭露出来的阿Q式的国民“精神胜利法”,则不仅指出了国人“爱面子”的民族文化心理,更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国人在“面子”观念表象之下的种种性格畸形和怪症。在社会落后和精神蒙昧的时代,阿Q 的“精神胜利法”意味着“人的非人化、 废人化与草芥化, 是彻底丧失了人的尊严、 主体和自我的精神世界的退化与动物化”[3]。而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性格实际上代表了整个绝大多数国民的性格。阿Q形象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传统社会里中国国民丑陋的众生相。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曾经留学日本,并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化作品,正因为他对西方文化有着较深的理解,又留学日本,“身在异国,刺激多端”[4],才能够以比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显然是此前的古典小说无法达到的。而中外比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与传统的比照,中国相对于西方列强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传统相对于现代的不足。由于始终秉持着清晰的中外比照意识和现代—传统比照意识,鲁迅的小说写作就具有了浓重的思想史意义,他所有的小说归根结底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5]。也正是由于这种清晰的中外比较意识,鲁迅的小说于是具有了显著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阿Q显然是中国的,但他又不难为外国人理解,因为鲁迅对阿Q负面性格的揭露原本就是以世界现代文明作比照的,这种性格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前现代社会成员的共性。这就难怪印度作家班纳吉说:阿Q“用来安慰自己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6]
(二)在中国小说史的思想谱系上,《阿Q正传》的批判意义还在于通过塑造未庄人的群像,从根基上揭露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深层痼疾。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具有批判性的小说。相对而言,《金瓶梅》更侧重社会批判,《儒林外史》更侧重文化批判,《红楼梦》则兼具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但三者的共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即基本上都是对中国封建上流社会和精英文化的批判,侧重剖析了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权贵鱼肉百姓的社会阴暗面以及僵化的儒家礼教和科举制度对文化人的毒害。晚清谴责小说仍以写官场和上流社会为主。实际上,上述小说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仍不够彻底:其一,作者主要批判的是自己更为熟悉的上层社会或文化人的生活,而对下层社会往往还是比较肯定的。例如《红楼梦》虽批判了贾雨村、王熙凤这样的上流人物,对刘姥姥这样的底层人物还是同情和肯定的。其二,作者往往还保留着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还指望着明君清官的出现。晚清谴责小说即是如此。《阿Q正传》则聚焦到中国社会的底层,从根基上来批判和解构传统社会和儒家礼教的大厦。在批判的同时,作者并未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更谈不上对明君清官的指望,这就更突出了作者对病入膏肓的传统社会和儒家礼教的彻底批判态度和革命立场。
从根基来批判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不仅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一个小小的村庄看到大中国的弊病,更由于中国社会的弊病自上而下不断发酵,通过对基层社会的解剖,更容易看清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病根到底在哪里。例如,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大都认同晏阳初提出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民存在贫愚弱私四大病症,这在《阿Q正传》中就很容易看到。阿Q穷得连房子都没有,只能寄住在土谷祠里,到最落魄的时候棉被、毡帽、布衫全都没有了,再后来又卖了棉袄,只剩下裤子和破夹袄。且由于没人叫他做短工,断了收入来源,最后只能去尼姑庵偷萝卜。阿Q的“愚”是十分明显的,不仅不识字,而且愚昧保守。他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放葱叶反放葱丝,他嘲笑“假洋鬼子”的老婆竟然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认为遇到了尼姑就“晦气”,而杀革命党则“好看”。 阿Q的“弱”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头上有癞疮疤,辫子发黄,廋骨伶仃,但又极为敏感,不愿听到任何与“癞”有关的词语,遭到欺负了只能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阿Q的“私”从他对革命的想象可以看得很清楚,元宝、洋钱、洋布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老婆,对小D的使唤和打嘴巴……总之,“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阿Q只是未庄农民中弊病最深最重的一个,许多未庄人并不比他好多少。王胡、小D、吴妈都是和阿Q一样深受贫愚弱私之苦的小人物,而愚昧和自私则几乎是所有未庄人的通病。鲁迅通过阿Q形象告诉国人,中国社会已经贫愚弱私到了极点,要改造社会则须革命性的全盘改造,修修补补的改造已经不可能管用了。
二、文体学维度: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的鼻祖
众所周知,小说的文体分类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所谓中篇小说,即篇幅介于短篇和长篇之间,故事容量较大,具有鲜明的人物和较多的故事情节,能够较丰满地反映某个具体时间段内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小说[7]。但这一分类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小说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文体规范进行创作的自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为典型且成就最高的当属章回小说。章回小说分回标目、故事完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由于中国古典小说由史传、话本发展而来,难免留下这些文体的痕迹,也因此与现代西方小说截然不同。例如俞平伯评论道:章回小说不仅充斥着“无意味的延长”、“无限制的连缀”、“不调和的混合”,而且结构上“一塌糊涂”[8]。因此,文学革命兴起后,用短篇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成为五四一代文学家的志趣和使命。此时短篇小说文体的勃兴,反衬出的正是这一代文学家“对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全面反叛”[9]。
然而以短篇小说来刻画一个人物的某个典型特征或几个性格截面,叙述一个简单的事件则可,要以短篇小说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某个具体时段的社会生活则面临篇幅不足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短篇小说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但无论评论者还是读者都对这一西洋文学样式并不满足。显然,习惯了情节曲折而完整的章回小说的中国读者一时还不能适应片段化的现代短篇小说。而评论者则质问道:“中国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10]鲁迅作为一个兼具思想家身份的文学家,虽为现实所迫常常选择小篇幅的短篇小说作为“呐喊”的文体工具,但强烈的“为人生”的创作使命迫使他去塑造一个能够呈现中国国民性的典型而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就必然要越出短篇小说的篇幅。这大概正是《阿Q正传》成为中篇小说的缘由之一。
《阿Q正传》是产生很早且成就极大的中篇小说经典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的鼻祖。
首先,《阿Q正传》是较早用现代白话创作且完全符合中篇小说要求的小说。《阿Q正传》作于1921年,此时现代文学革命发生仅4年多,中国文学界还处于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此时的小说作品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阿Q正传》则是当时名副其实、不可多得的中篇小说。孙犁认为,大凡中篇小说都具有如下五大特征:一、应该极力创造典型人物;二、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较完整的历史面貌;三、有可能塑造较多的人物;四、有较多的情节变化;五、写作手法单纯明朗。这些特征《阿Q正传》都是完全具备的。因此孙犁认为《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是研究中篇小说创作的“最好范本”[11]。当然,关于中国古代有无中篇小说仍有争议,笔者不完全赞同《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的提法,而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的鼻祖。还有学者认为,中篇小说最首要的审美特征是故事的完整性,即以完整的故事来表达作家的审美理想[12]。《阿Q正传》显然也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小说看似散漫,写了许多人物,但这些人物都是围绕着阿Q而存在的。小说写了阿Q的琐事、生计、求爱、造反等许多事件,但中心线索很清楚,即阿Q怎样一步步走投无路,走向革命和死亡,符合中篇小说以较为单纯的线索组织起较为复杂的情节、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典型特征。
其次,《阿Q正传》既尝试用较长的篇幅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又力图跳出古典章回小说的窠臼,实现了现代中篇小说文体的突破。《阿Q正传》本为《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的约稿,每周刊一篇,这种方式似乎可以一直写下去,直到读者厌烦为止。但鲁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让阿Q“及时”死亡的结局。这是古典章回小说很难达到的,体现了鲁迅对章回小说弊病的清醒认识和有意规避。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的写法实际上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13]。这是很敏锐的察觉。鲁迅借鉴西方短篇小说的写法来写作《阿Q正传》,使作品一开始就避免了章回小说无限制延长和扩展的弊病;同时,由于作者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又使得它与短篇小说仅写一个事件或事件片段区分开来。另外,《阿Q正传》将“讲故事”与“写人物”紧密结合,故事为人物服务,而不是像旧小说那样为讲故事而讲故事[14]。作品选取阿Q一生中几个典型事件而非写其整个一生,写到高潮处突然收住的写法,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虽显得单纯,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则可谓恰到好处、意味深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阿Q正传》的艺术价值“显然受到过誉”,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则是张爱玲的《金锁记》[15]。这种观点呈现出来的过于看重艺术技巧、忽视思想性的偏颇是十分明显的。笔者无意比较《阿Q正传》与《金锁记》在艺术技巧上的高下,如果仅从中篇小说文体的形成史来看,二者虽同样塑造了丰满传神的典型形象,都只用不到三万字的篇幅就讲述了一个完整精美的故事,也同样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如心理描写),都力图突破中国旧小说任意道来、拖沓冗长的写作套路,但前者的写作早于后者整整20多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二十年代《阿Q正传》在现代中篇小说文体上的突破,很难想象能有四十年代《金锁记》的诞生。更何况《金锁记》对人性之恶的揭露明显受到了鲁迅小说的影响[16]。
三、艺术性维度:融通中外、独具特色的艺术典范
一个时期以来,总有人质疑《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认为其艺术价值被高估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司马长风的论点,他认为:文学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士大夫文学,建立平民文学,《阿Q正传》却有许多古文词句;主人公阿Q没有统一的个性,如既胆大妄为又卑怯懦弱,既狡猾又麻木,等等;作品中竟没有一个好人,是反真实的[17]。这些论点虽然揭示了部分事实,却是十足的偏颇。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年代正值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渡时期,白话文尚未完全确立,作品含有一部分文言词句当无可厚非,况且作品中使用文言词句很多时候是为了增强艺术效果(见下文分析),而非泥古崇古。而阿Q两重性的性格恰是其性格复杂性的体现,且并未冲淡其主导性的性格(精神胜利法)。例如他既胆大妄为又卑怯懦弱,其实是在弱者面前胆大妄为,在强者面前卑怯懦弱,在弱者面前取得胜利他可以获得心理满足,在强者面前失败他同样可以靠精神胜利法“转败为胜”, 获得心理满足,二者表面上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至于作品中没有一个“好人”,这并不能构成否定一部经典作品的有力证据。规定一个作品中必须出现一个“好人”,恰恰是一种机械的文学观。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好人,而在于作者有没有对“好社会”和“健全的人”的价值诉求。鲁迅借这样的人物安排,正是为了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严重病症,“引起疗救的注意”,充分体现了他对“好社会”和“健全的人”的期盼。
《阿Q正传》虽以思想性的文学经典名世,但其艺术性同样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笔者仅从典型艺术和讽刺艺术的角度做一点论证。
(一)典型艺术。文学即是人学,写出鲜活的典型人物是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天职。塑造典型的基本方法在中西方是有共性的,既可以是在大量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塑造典型,也可以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人物原型为基础,汲取其他素材而塑造成典型。鲁迅曾说过自己的小说往往取前一种塑造方法,即“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18]。正因为惯常使用这种方法,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从语言、行为、生活习惯上来看具有江浙一带的特征,但从思想文化的内在层面来看,又具有浓重的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共性。这就难怪茅盾刚读到《阿Q正传》时就敏锐地发现,鲁迅写出了“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19]。
在塑造典型的具体方法上,鲁迅则融合了中西艺术中的不同方法。在叙事方面,作者延续了中国小说惯用的顺叙,但避免了中国古典小说原原本本讲述主人公一生的方法,而是借鉴外国小说截取人物一生的几个片段的写法,只写了阿Q的生计、恋爱、革命等几个事件。在外貌、语言描写等方面,《阿Q正传》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白描法。 除了人们熟悉的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那一段经典的语言描写外,作品中白描法可谓俯拾即是。例如对阿Q的外貌,作者只用极少的几笔,“阿Q赤着脯,懒洋洋的,瘦伶仃的”,“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常被人揪住“黄辫子”,一个可感的形象就留在读者脑子里了。作者只用简单几句语言描写,“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就让阿Q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的性格跃然纸上。正因为在典型塑造上鲁迅用力甚勤,且巧妙地结合了中西方典型塑造的方法,才能有阿Q这一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这大概是为什么明明是一部以思想性奠定其地位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让无数读者爱不释手的原因吧。
(二)讽刺艺术。《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力作,这得力于作者在讽刺艺术上博采众长,加以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讽刺风格。对比是常用的讽刺手法,鲁迅在《阿Q正传》中多处用到了这种手法。如阿Q尚未“中兴”时,与赵太爷攀本家不成,还被打了嘴巴。赵太爷呵斥他:“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而等到阿Q宣布要造反后,赵太爷则怯怯地叫他“老Q”。开始不让阿Q姓赵,后来则礼貌地叫“老Q”,前后的鲜明对比是对赵太爷势利、狡猾的性格的尖锐讽刺。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态度的对比进行讽刺的写法,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少见,例如《儒林外史》中的胡屠夫在范进中举前后对待范进的态度即是一种鲜明对比。但除了以上的常用对比手法外,《阿Q正传》还独具匠心地运用了许多新颖的对比手法。如:1.名实对比。“名”与“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尤其儒家哲学十分讲究“正名”和名实相符。鲁迅在《阿Q正传》一开始就引用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为读者点出了名实问题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屡屡出现名实不符,尤其是作者为小说每一章所取的标题,大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名实不符。例如阿Q的“中兴”不过是去参加了城里的盗窃团伙,“恋爱”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想和吴妈“困觉”,“革命”不过是盲动,“大团圆”更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上的大团圆,这些其实都是鲁迅故意以名实的对立造成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2.语体对比。即文言和白话的对比。《阿Q正传》第一章写道:“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这里在白话语体中突然插入文言语体,其实是作者故意为之。将生平业绩写入传记本是大人物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用“著之竹帛”的文言语体写出来更显得正经八百,但越是正经八百,用在这里却越显得与阿Q的小人物身份极不相称。3.表达方式对比。作者在客观叙述的时候不时插入议论文字,也常常能达到讽刺效果。例如,在写到阿Q摸了小尼姑的脸后躺在土谷祠里想入非非时,小说突然话锋一转,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这里作者通过表达方式的变换营造出一种“间离”效果,让读者跳出阿Q和未庄的狭小视界,放眼整个传统中国,从而看到了整个中国与阿Q和未庄之间的同质性。这样的议论文字放在这里,不仅没有显得啰嗦,反而使作者对阿Q的批判升华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鲁迅对于纯粹的幽默并无太多兴趣。他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20]。他看重的是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讽刺。他对《儒林外史》十分赞赏,认为吴敬梓能够“秉持公心,指摘时弊”[21],没有让自己的讽刺之作落入个人怨愤和哗众取宠的俗套。而他更欣赏的则是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是“喜剧性的兴奋”和“深刻的悲哀之感”的结合[22]。《阿Q正传》就是以果戈理的方式写作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大团圆”一章中阿Q临刑前“使尽了平生的力”立志要画一个圆的圈却没有做到时,虽觉得夸张和好笑,却总感到心情沉重。
总之,无论从解剖社会和国民心理的思想深度,还是对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性的文体实践,及融通中外、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上来看,《阿Q正传》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其文学经典地位不是一般的小说能够轻易取代的。
参考文献:
[1] 江守义.儒家道德在小说叙事中的历史演化[J].孔子研究,2006(1).
[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6.
[3] 逄增玉.《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问题的再思考[J].文学评论,2007(5).
[4] 许寿裳.许寿裳文集(上卷)[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208.
[5]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自编文集·集外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67.
[6] 陈漱渝.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魂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42.
[7] 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3.
[8] 俞平伯.谈中国小说[J].小说月报,第19卷(2).
[9] 王晓冬.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77.
[10] 郑伯奇.伟大的作品底要求[J].春光,1934(1).
[11] 孙犁.孙犁选集·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4-146.
[12] 洪治纲.回眸:灿烂与忧伤[J].小说家,1999(2).
[13] 仲密.阿Q正传[J].晨报副刊,1922—03—19.
[1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9、261.
[15]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111.
[1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17] 茅盾.读《呐喊》.查国华、杨美兰.茅盾论鲁迅[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5-7.
[18] 鲁迅.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5.
[20]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M].满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93.
(责任编辑潘志和)
收稿日期:2016-03-25
作者简介:周逢梅,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08(2016)02-0062-06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to The Classical Status of Biography of Ah Q
ZHOU Feng-mei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e classical status of Biography of Ah Q could be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i.e., ideological content, stylistics and artistic. No matter analyzed from the depth of thought when anatomizing the socie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or the pioneering stylistic practice to the modern nouvelle, or the featured artistic writing which combined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styles, Biography of Ah Q is undoubtedly the classical writing and its statu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will not be easily replaced by common novels
Key words:Biography of Ah Q; classical; ideological content; stylistics; art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