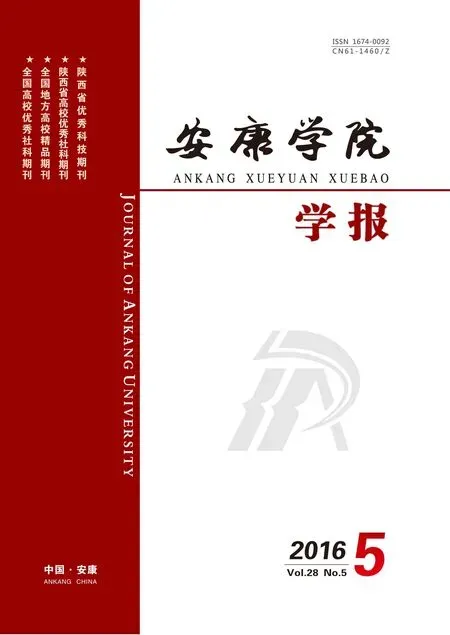希腊幻想与三岛由纪夫《潮骚》的乌托邦写作
李勇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希腊幻想与三岛由纪夫《潮骚》的乌托邦写作
李勇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希腊文化精神对三岛由纪夫的生活理念及早期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小说《潮骚》表现得尤为显著。它通过对西方牧歌文化传统的借用与“牧歌情调”的营造,试图发掘与再现古希腊文化与日本原始渔业村落共同体的共通精神。对异域风情与过往时代的激情描绘,使《潮骚》呈现出浓郁的乌托邦写作特征。在乌托邦文学虚构与真实的二元辨证关系中,《潮骚》清晰地折射出战后日本及作家精神世界的“废墟感”。
三岛由纪夫;《潮骚》;牧歌情调;乌托邦写作
1951年12月25日,以《朝日新闻》特别通讯员的身份,三岛由纪夫开始为期五个月的海外旅行。此行踏访了美洲和欧洲的很多国家,但是让三岛由纪夫印象最深的还是希腊;他如痴如醉地沉浸于希腊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及建筑雕塑艺术。希腊旅行的见闻与体验,使其随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浓郁的希腊文化情调,小说《潮骚》 (新潮社,1954年) 更是将三岛由纪夫的希腊崇拜推向了巅峰。它以古希腊牧歌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亚》(Daphnis and Chloe,2—3世纪)为蓝本,试图将极具牧歌情调的爱情罗曼斯(Romance)及其潜含的希腊文化观念移植到战后初期的日本。然而,无论就三岛由纪夫的惯常创作主题与风格而言,还是就战后日本的社会历史与思想动态而言,明快的海岛风情和单纯的爱情故事均显得格格不入。这并不难解释,《潮骚》实际上属于乌托邦写作,希腊式的海岛乌托邦构成了作家本人及战后日本的反向寓言。海岛乌托邦越是明快和谐,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世界越是阴郁纠葛,战后日本越是废墟化。
一、作为自我疗救的希腊精神
关于《潮骚》的创作背景,三岛由纪夫曾说:“头年我刚访问过希腊,情绪上达到了迷恋希腊的最高峰时期,因此无论看什么东西,都与希腊的幻影重叠在一起”[1]290。心中萦绕不绝的“希腊幻影”,是《潮骚》最终得以浮出水面的原初动机。三岛由纪夫的希腊之行,并非消费娱乐时代的旅游观光,而是精神信仰层面的文化朝拜与精神治疗。
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认为,旅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要在自身内部整合更多的相反因素,并且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去实现自己所具有的可能性”[2]。从哲学的视角看,旅行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对奇异世界的无限憧憬;旅行者会清晰地划分出此地与彼地的界限,将日常生活与奇异世界放置于对比序列中。有关异国异地的印象与记忆是一种心理镜像,折射出对本国及日常生活的感受与评价,可能认同,可能不满,更有可能是两种情绪的复杂混合。三岛由纪夫的希腊之旅则相对简明清晰,希腊崇拜构成了其潜在的自我精神抗争与重建。
具体而言,三岛由纪夫的“希腊幻想”主要由自然风光、生活状态、希腊精神三个层面组成。首先让三岛欢欣鼓舞的是希腊的自然风光。他在游记散文集《阿波罗之杯》中写道:“今天,又是绝妙的蓝天,绝妙的风,强烈的日光……是啊,希腊的阳光超过了温和的程度,过于裸露,过于强烈。我从心底里热爱这样的日光和这样的风。”[3]237希腊风光美在于明朗与热烈,与讲究“阴翳”的日本美学观可谓天差地别。关于“阴翳”,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写道:“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4]。无论建筑器物、饮食起居,还是古典艺术、审美哲学,日本古典文化都呈现出浓厚的阴翳美。它和日本古典美学中的“物哀”与“幽玄”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且渗透着深重的佛教无常与虚无感。不论是“阴翳礼赞”的日本古典美,还是三岛由纪夫此前小说创作的主色调,均具有昏暗压抑的倾向。相形之下,希腊的自然风光与生活状态则洋溢着自由而饱满的生机和活力。三岛在《我迷恋的东西》一文中曾对希腊与日本的生活状态进行过比较分析:“在意大利和希腊,在干燥的空气中,到处都在使用的大理石材料,这些都没有阴影,归根到底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美上。映现在旅行者的眼帘里的,是他们在唱歌,开怀地享乐人生,仿佛惟有现在才是活着的。我简直像被这种看似肤浅的拥有光明的神秘所深深地吸引住。只想藏身在黑暗中,对深刻的民族和艺术渐渐地不感到有魅力了。”[5]从阴翳到明朗、从压抑到享乐的时空转换,对三岛来说,此番希腊行旅无疑是一种精神释放。
然而,最使三岛由纪夫心醉神迷的是重视“外面”的希腊精神。他说:“希腊人相信外部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基督教发明‘精神’之前,人类根本不需要所谓的‘精神’之类的东西而自豪地生存着。希腊人思考的内部世界,总是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左右对称。”[3]238希腊精神到底在何种程度上重视“外面”,实际上并不重要。将外面的身体与内面的精神作为二元相对的一组概念,是三岛思考人性的思维模式之一,亦是其理解希腊文化的固定视角。在古希腊人体雕塑与奥林匹克竞技中,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智完整而和谐地统一于裸露的身体。身体甚至成为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关键词,正如三岛所论的:“在希腊,不必说也知道有柏拉图的哲学,虽然我们首先被肉体所吸引,透过肉体美,进而被更高层次的纯理性所吸引。若要到达所谓纯理性的极点,非得通过肉体美之门不可,为希腊哲学的基本思考”[6]197。
和古希腊文化的身体崇拜不同,日本文化大体来说将身体作为负面的存在。三岛曾说:“在日本,佛教从否定现世、否定肉体出发,不仅不把肉体本身作为肉体来评价,也绝不会有将肉体作为超越肉体之事来评价。直率地说,就是没有肉体崇拜一事。”[6]197否定身体,实则是对现世生活的否定,将人过度地拘囿于意念世界中。在童年与少年时代,三岛本人就生活在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拉锯中,半自传体小说《假面告白》 (1949年)对此有深入地描绘。这后来转化为三岛由纪夫早期创作的惯常主题。《假面告白》中的主人公身体孱弱,长久被禁锢在祖母充满病痛与老朽气味的卧室里,形成了耽于幻想的习惯;在自我嫌弃的同时,他深深地迷恋上现实生活中普通男人青春健硕的身体。自我幻想的世界被痛苦地拒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随后出版的《爱的饥渴》 (1950年)亦复如此。女主人公悦子沉湎于幻想而无法自拔:“所谓生存的意义就是不断出现在眼前的这种统一的幻觉,或者只不过是以一种试图溯及不该溯及的生存意义中产生的生存的统一的幻觉。”[7]她对壮实憨厚的年轻男佣三郎深怀幻想式的爱恋,然而当三郎坦诚对她的爱之际,她却产生了一股如坠深渊的绝望感,于是用锄头杀死了三郎。及至《禁色》 (1953年),三岛的创作已表现出浓郁的希腊文化印记。主人公南悠一具有俊朗的外表,犹如古希腊的青铜阿波罗塑像。但是,这种几近完美的青春美却是破坏性的,让人遗憾地沦为老作家俊辅报复女性的工具,俊辅恶魔般扭曲的灵魂最终吞噬了悠一的青春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禁色》中俊辅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反思一定程度上亦是三岛由纪夫的自我反省。小说写到:“要是把它们一丝不改地搬进作品,那是违背俊辅意志的,他憎恶活生生的现实。他抱着这样的确信:天赋的任何部分,自我流露的部分都是虚假的。不仅如此,他的作品缺乏客观性,同他的创作态度,同他顽固地坚持失去了的、固执的主观意志有关。这同他仇视活生生真实的态度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8]三岛的早期创作过多地沉溺于想象、梦幻、倒错、血与死亡的精神世界,对此他已厌烦。希腊之旅,适逢其时地成为一场自我疗伤。三岛尝试着自我改变,试图平衡身体与精神的紧张关系。他在《太阳与铁》中说:“从被‘表面’的深层所吸引的时候开始,我就预见到我需要进行肉体的训练。”[1]354为了锻造强健的身体,三岛在1952年学习游泳,在1953年接触了拳击,自1955年7月坚持不断地练习举重。如此痴迷于身体训练,其实是想通过肌肉的锤炼实现一种朝向“表面”的思想蜕变。后来,原本瘦弱的三岛的确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硬汉”身型。与此同时,他在小说创作中也着意改变,《潮骚》史无前例地讲述了一个大团圆的爱情故事,呈现出明朗欢快的色调,男女主人公的身型与精神气质均具有古希腊人体雕塑的特征。
二、牧歌情调与海岛乌托邦的建构
为了充分地传递希腊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环境描写上,《潮骚》均刻意地去模仿古罗马作家朗戈斯(Longus)的牧歌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亚》,尤其着意重现这部牧歌小说荡溢于字里行间的“牧歌情调”(Pastoral Mode)。
作为文学体裁的牧歌(Pastoral),起源于古希腊的西西里岛,是对田园风光与牧羊人生活进行描绘的一种诗歌写作模式。公元前二、三世纪的西奥克里特斯(Theocritus)据说是最早进行牧歌创作的诗人。尽管如此,西方文学牧歌传统真正的确立者却非维吉尔(Virgil) 莫属。其拉丁语写就的《牧歌》 (Eclogues,前42-37)奠定了牧歌的基本模式与风格。贾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就论到:“《牧歌》把‘纯粹’的草原风光、或多或少理想化的农夫淳朴的爱情及歌谣与较为复杂的诗歌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诗人利用牧歌的形式,间接地谈到当时的政治和当代的诗人。这些诗篇为所有欧洲语言树立了牧歌的典范。”[9]和早期牧歌写作相比,维吉尔既增加了虚构性与浪漫情调,又极为强调现实指向性,意在忠实地再现当时乡村生活的苦难。另一位对西方牧歌传统做出巨大贡献的便是朗戈斯,其用希腊语创作的《达夫尼斯与赫洛亚》标志着“软牧歌”的成型。“软牧歌”实际上是指“牧歌生活的甜蜜化” (A sweetening of pastoral life),排除现实生活与政治的旨归而使牧歌生活越来越脱离现实和理想化,即越来越乌托邦化。
将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小说及牧歌情调移植到日本,对于出生、成长在大都市的三岛由纪夫而言,并非易事。因为它既要符合日本渔业社会的风土民俗,也要满足战后日本社会的异国情调想象。在日本水产厅工作人员的推荐下,三岛选定了坐落于伊势海湾的神岛,以此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并分别于1953年早春和晚夏对这个小岛渔村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生活体验。犹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沈从文的“边城”,《潮骚》的真正主角是“歌岛”。按照三岛的说法来看,这是一个“与文明隔绝”“充满朴素人情味的美丽小岛”[1]290。与充满着失败沮丧氛围、与此同时日益商业化的战后日本相比,这座小岛仍旧完整地保留着日本传统渔业乡村共同体的生活风貌。三岛由纪夫刻意营造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倾向,使《潮骚》构成了对战后日本与自我的双重逃离。只有通过对偏僻落后海岛渔村的描述,才能呈现日本原始文化中固有的希腊精神。
对于战后日本读者而言,《潮骚》优美旖旎的海岛风景,无疑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娱乐至上的消费时代,“风景”(Landscape)通常是满足视听之欲的文化消费品。国内外的普通读者往往以这样的消费心态来看待小说《潮骚》以及电影改编版《潮骚》 (1975年,西河克己导演,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的风景。然而,这不是三岛审视与描述“风景”的角度。他更倾心于塑造“心景”(Soulscape),外在的风景与内在的情感水乳交融在一起。这就使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困境迎刃而解。三岛想要从“外面”来描写人物,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心理描写,那就极有可能陷入以前小说创作的模式之中。“心景”恰恰提供了一种外在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方式。在《潮骚》中,三岛通过系列化的海景图,间接地全程展现了主人公新治的内心波澜起伏,海的形象与新治的男性形象最终二合为一。
更为重要的是,《潮骚》的海岛风情图还蕴藏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寓意。近年来日益勃兴的风景研究,越来越习惯于将“风景”视为一种文化寓言。米切尔 (W.Mitchell) 在 《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1994年)中说:“自然的景物、石头、水、动物,以及栖居地,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心理,或者政治比喻中的符号;典型的结构和形态都可以同各种类属和叙述类型联系起来,比如牧歌(The pastoral)、田园(The georgic)、异域(The exotic)、崇高(The sublime),以及如画(The picturesque)。”[10]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 (Landscape and memory,1995年)中也论到:“如果说我们整个的风景传统是共同文化的产物,那么同理,它也是在丰富的神话、记忆以及夙愿的沉淀中构建起来的传统。”[11]实际上,《潮骚》的海岛风情图也有这样的文化祈愿,不仅要实现三岛的希腊梦与慰藉战后日本社会的创伤感,而且要勾起对传统日本渔业社会共同体的历史记忆。
在海岛风景民俗描写中,三岛由纪夫突出了原始自然神崇拜的宗教因素,《潮骚》因此可以被称为“神的物语”。它不仅展示了渔业共同体以海神崇拜为中心的神道信仰,而且描绘了大量与日本神道相关的活动,比如八代神庙的祈福与还愿、祖先忌辰祭拜、盂兰盆会、只有女性参加的“庚申神之会”等。古希腊宗教与日本的神道均属于多神教,对此种宗教类型三岛颇有好感。他认为,所有原始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拟人化的,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唯心论的自然观;唯心论的自然观与原始村落的共同体意识相辅相成,多神教观念中人格化的自然有助于个人灵魂的净化,人与自然在适当的距离上保持着独立而和谐的关系;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多神教的唯心论自然观日渐式微,基督教与现代自然科学事实上是“反自然”的,基督教在使自然神化的同时也使人类疏漠了自然,而现代科学过度物化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割裂[1]225。在原始村落共同体的多神教信仰中,人类对众神的情感是双重的,是“希望和恐惧”并存的。这不仅使人与自然保持着有距离的和谐关系,而且依靠自省的力量建构了强大的共同体意识和道德观念。
在传统农牧业社会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比较视野中,三岛由纪夫歌颂了原始乡村共同体的身体美意识与爱情观念。在评价与描述主人公新治时,多次出现了“气力”一词。“气力”强调的是在日常劳作中发达的身体机能,这是传统农牧业社会最为看重的。在三岛看来,身体之美与人体机能的充分施展紧密相关。他指出:“男人有斗争的机能。女人有妊娠与育儿的机能。不忠实于自然赋予这种机能的人,没有理由是美的。”[12]然而,三岛却遗憾地注意到,现代都市文明崇尚的是“装饰美”,农牧业时代的“机能美”已然式微。《潮骚》之所以浓墨重彩地刻画主人公们的裸体,正是要彰显机能化的身体美意识。与此交相辉映,《潮骚》还讲述了一个颇具《万叶集》情调的渔村爱情故事。三岛论到:“描述日本人最健康的恋爱就是《万叶集》一书。《万叶集》中的恋情,不像欧洲、希腊般具有哲学背景的恋爱。仅将古代民族率真的肉体欲望,融入日本人温柔的心情、纤细的生活感情中,素朴而坦率地描述美丽的离情、久别重逢恋人的喜悦等。”[6]7三岛剔除了情色因素,塑造了青春活力的身体以及纯洁质朴的爱情。
总而言之,在古希腊精神以及日本原始渔业文化的影响下,三岛由纪夫的《潮骚》塑造了一个弥漫着“牧歌情调”的海岛乌托邦。其故事空间远离现代日本的都市,其创造方法背离了三岛惯常的小说写作原则,可以说《潮骚》是三岛由纪夫对战后日本与自我的双重逃离。
三、战后日本社会与乌托邦的瓦解
作为“疗伤之旅”的希腊之行,三岛由纪夫发现了健康、阳光、生机勃勃的希腊美,这给《潮骚》带来了一股质朴清新的气息。然而,《潮骚》看似明朗,实则潜含着黑暗的斑底。文本的不稳定性,是牧歌文学的普遍特征。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 指出,牧歌既是歌颂式的(Celebratory),也是轻蔑式的(Pejorative)[13]2。牧歌文学在内容上是自相矛盾的,“歌颂式”与“轻蔑式”的分野取决于牧歌文学的阅读视角。如果仅聚焦于文本内部所呈现的质朴乡村世界,牧歌情调是成立的,但如果将阅读视野延伸至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牧歌的真实性就会被破坏,牧歌情调随之便毁灭。正如理查德·詹金斯所论:“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类型,牧歌可以成为它自身的批评者,有时,我们甚至可以在牧歌中听到反对牧歌的声音。”[14]
《潮骚》同时具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个面相。就三岛由纪夫小说整体创作而言,可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大部分,其发表途径截然不同。纯文学作品主要在正统权威的文学杂志上连载,或者直接发行单行本;而通俗文学作品则主要在女性杂志上连载。三岛为何热衷于撰写通俗文学呢?美国三岛由纪夫研究专家唐纳德·金(Donald Keene)提到了两个理由:“经济上的因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同那些有名的文艺杂志相比较,发行数很高的妇女杂志的稿酬就显得非常高了”“三岛写通俗小说的最大理由,是想满足读者的任何文学嗜好,并为自己具有这种能力而高兴”[15]。出于题材和写法的缘故,《潮骚》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赢得了大批普通读者的青睐。在此后的再版过程中,《潮骚》常常被纳入以“青春文学”“少年少女文学”等为主题的系列丛书中。创作初衷是希腊美的再现,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在通俗文学界获得成功。
借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理论,《潮骚》同时存在着“作者式”(W riterly)和“读者式”(Readerly)两种阅读倾向。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简单说来,‘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本,易于阅读,对读者要求甚微。与此相对的是‘作者式文本’,它不断地要求读者去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Constructedness),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16]“读者式”是通俗文学的阅读方式,大众读者关注的是文本的显性层面;而“作者式”则是纯文学的阅读方式,精英读者凭借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自觉的阅读策略,对文本的隐性层面展开深入剖析,文本内部复杂的叙事策略、文本的写作风格与作家的创作意图、文本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随即浮出水面。仅就《潮骚》而论,牧歌情调会因“读者式”阅读而产生,也会因“作者式”阅读而消失。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在《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中评论说:“有些作品,其成功迅即而至,以至于在挑剔的读者眼中,成功侵蚀了这些作品,《潮骚》便是其中之一。它完美的明晰本身就是一个陷阱。”[17]
阅读“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读者不会在乎故事的发生背景,或者说从未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故事背景可让读者去考察。《潮骚》却无法如此来阅读,因为三岛由纪夫明确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战后日本的偏远海岛上。对真实性的追求,使得小说家不得不将海岛内外的真实风貌描绘出来,这最终成为破坏海岛乌托邦的不和谐声音。1941年,三岛由纪夫在文学杂志《文艺文化》上发表了处女作《鲜花盛开的森林》,直至1970年11月25日“惊世赅俗”的切腹自杀,其创作生涯历时30年。这恰恰也是日本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30年。具体来说,此种巨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日本战败、美国的军事占领(紧随其后的是日本战后非军事化、美国化的改革)、经济飞速发展以及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三岛由纪夫在1969年回顾到:“25年前我憎恨的东西多少变了形,但至今依然顽固地继续活着。岂止继续活着,令人震惊的是,它以它的繁殖力渗透了整个日本。那就是战后民主主义和由此产生的伪善的可怕毒素。我曾以为这种伪善和诈骗术将会同美国的占领一起结束,可是,我的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日本人自己竟主动选择它作为自己的体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如此,实在令人震惊。”[13]463对战后日本社会难以抑制的悲观绝望,就像幽灵一样存在于其作品中。在《假面告白》 《金阁寺》 《午后曳航》等小说中,青少年的成长危机实则是战后日本的隐喻。《潮骚》却一反三岛惯常的创作模式,不再塑造精神危机少年,不再展示战后日本的废墟感。既追求乌托邦式明快单纯的牧歌情调,又要逼真地展示战后日本海岛渔村的风景民俗,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为“软牧歌”及乌托邦文学的故事背景一定是模糊化或遥远的,如此一来,“虚幻的真实”才不会遭到质疑。
余华曾如此评价三岛由纪夫:“他过于放纵自己的写作,让自己的欲望勇往直前,到头来他的写作覆盖了他的生活。”[18]对三岛而言,写作是一座自由自在的乌托邦;残缺的生活在写作中得以弥补,梦想的生活在写作中得以实现,写作才是作家心向往之的完美生活。在整个创作生涯中,《潮骚》是三岛希腊崇拜的巅峰时刻。尽管对古希腊宗教与艺术做过细致地考察,但是作家的希腊文化观还是掺杂着过于自我及感性的因素,最终演变成为“希腊幻想”。这就使《潮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乌托邦文本的特质。然而,这却与三岛由纪夫的创作初衷相背离。他想追求“真实”,在战后日本的文化基质上挖掘其魂牵梦绕的希腊特质。犹如三岛对待写作与生活的态度,在《潮骚》的小说叙事中,“幻想”试图覆盖掉“真实”。但是,写作的世界再广大,也还是被包裹在作家的生活之中,三岛也无法扭转这一事实。战后日本既是《潮骚》的写作时代,又是《潮骚》首次面对读者并获得大众喜爱的阅读时代。绮丽多姿的“幻想”不仅无法消抹掉和战后日本相关的诸多“真实”,而且更能呈现出战后日本文化的“废墟感”。
[1]三岛由纪夫.太阳与铁[M].唐月梅,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2]中村雄二郎,山口昌男.带你踏上知识之旅[M].何慈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
[3]三岛由纪夫.阿波罗之杯[M].申非,林青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4]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M].陈德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4.
[5]三岛由纪夫.艺术断想[M].唐月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39.
[6]三岛由纪夫.新恋爱讲座[M].林皎碧,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3.
[7]三岛由纪夫.爱的饥渴[M].唐月梅,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87.
[8]三岛由纪夫.禁色[M].杨炳辰,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9]贾斯帕·格里芬.维吉尔[M]//理查德·詹金斯.罗马的遗产.晏邵祥,吴舒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9.
[10]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
[11]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M].胡淑陈,冯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4.
[12]三岛由纪夫.残酷之美[M].唐月梅,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318.
[13]TERRY GIFFORD.Pastoral[M].London&New York:Rout ledge,1999.
[14]理查德·詹金斯.牧歌[M]//理查德·詹金斯.罗马的遗产.晏邵祥,吴舒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99.
[15]唐纳德·金.三岛由纪夫的世界[M]//叶渭渠,千叶宣一,唐纳德·金.三岛由纪夫研究.北京:开明出版社,1996:33.
[1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27.
[17]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M].姜丹丹,索丛鑫,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4.
[18]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70.
【责任编校朱云】
On the W riting of M ishima Yukio’s The Sound of W aves Influenced by Greek Fantasy and Utopian
LI Yong
(College ofLiterature and Broadcast,Xianyang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The spirits of Greek culture had greatly influenced Mishima Yukio’s life attitude and his early works.The Sound of Waves,which showed as the peak of Mishima’s worship of Greek culture,weaved the fundamental landscape and everyday life of Japanese antique fishing island into the literary pattern of western pastoral tradition,trying to express the mutual spirits of Greece and ancient Japan.Absorbed in the description ofexotic country and pastgolden time,ithad formed strong characteristicsofUtopianwriting.Through thedialecticsof fantasy and reality,nihilistic sadnessofMishima Yukio and Post-war Japan was fully disp layed.
Mishima Yukio;The Sound ofWaves;pastoral mode;Utopianwriting
I106.4
A
1674-0092(2016)05-0074-06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6
2016-03-09
咸阳师范学院“青蓝人才”资助项目(XSYQL201504)
李勇,男,陕西蒲城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