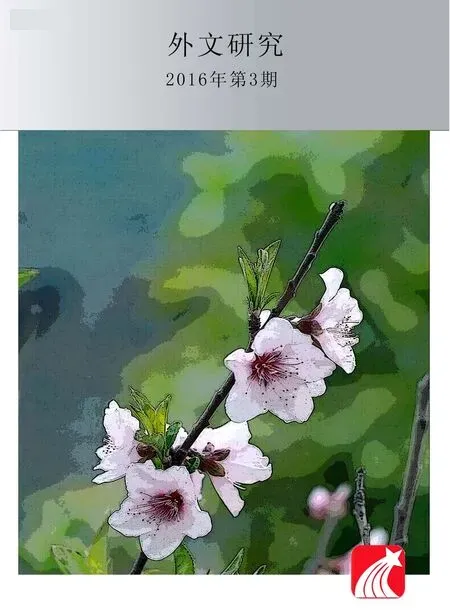对“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的反思
宁波大红鹰学院 周忠良
对“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的反思
宁波大红鹰学院 周忠良
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构建独立的翻译学理论体系,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须打破“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的局面。本文分析了造成“话语生态失衡”的原因,反思了中国译学面临的“三重失语”困境,考察了近年来译学界反拨“话语生态失衡”的主要途径,指出译学界须以反省性的自觉,对当今中国译学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建设性重构。唯有如此,才能面对强势的西方译学话语,建立学术自尊和自信,确立对中国译学学科话语体系本己身份的认同,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生态失衡;译学话语体系;原因;三重失语;反拨途径
一、“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探源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辉煌的翻译历史,因此译学遗产极为丰厚。但在近现代,译学研究曾长期在“直译”与“意译”的论争中停滞不前,译学议题也未曾跳出严几道“信、达、雅”理论的阈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必须建立翻译学”*1951年,董秋斯(2009)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首提建立翻译学。1987年,谭载喜发表论文《必须建立翻译学》,标志着学界开始在论争中启动现代翻译学的系统构建。的呼声中,译学界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方式,开启了一场规模巨大、延续至今的“西方译论引进运动”,其瞩目的成就,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翻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译论的引进,为中国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扩大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对于推动中国译学的当代构建的影响和意义不言而喻。但不可否认,这场译学话语引进运动带来的后遗症,就是西方译论大量涌入中国译学研究疆域,攻城略地,牢牢地树立了“话语霸权”,导致当代中国译学话语生态严重失衡*“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国际译学话语格局中“西强中弱”的话语权力关系;二是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内部“西强中弱”的话语权力关系。因篇幅所限,本文所指仅限后者。:传统的、本土的译学话语处于边缘位置,形形色色的西方译学概念、范畴和理论充斥译学研究空间。可以这样说,如今中国译学理论体系中的主流话语大多来自西方,带着异域胎记,极少有核心概念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事实上,当代中国译学体系的构建主要依赖对西方译学话语的移植。当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就是一部西方译论的引进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引进了奈达(Nida)、卡特福德(Catford)、纽马克(Newmark)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一时间动态对等、翻译转换、交际翻译等术语成为流行词;接着,“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Bassnett)、勒弗菲尔(Levefere)、佐哈尔(Zohar)、赫曼斯(Hermans)、图里(Toury)等相继登场,意识形态、赞助人、操控、多元系统、翻译规范等术语进入国人研究视野,并主导着国内译学的“文化转向”;再之后便是斯皮瓦克(Spivak)、韦努蒂(Venuti)、德里达(Derida)等人的后殖民和后现代翻译理论引领译学潮流,女性主义、翻译政治、权力话语、抵抗式翻译、解构主义等术语成为研究新宠。这场“西方译论引进运动”引进了包括概念、范畴、理论和范式等西方译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要件,从而以“四位一体”的体系实现了对传统译学话语的整体切换,使传统译学话语在本土遭到外来话语的严重挤压,被放逐到中国译学研究疆土的边缘,其讽刺性的后果,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家园,不得不操异域话语谈论本土的翻译经验,用别人的话讲自己的故事。
造成“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的原因,除了对异域译论的大量引进和吸收,还在于长期以来对传统译论的批判和否定,导致我们对之产生了陌生感和疏离感,因而忽视了传统译学遗产的丰厚价值。王宏印(2003: 8)将中国传统译论定义为“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传统译论根植于传统文化,取诸于传统哲学和美学范畴,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支流,因而在表述方式和精神特质上均深具传统文化韵味。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是理性不足和诗性浓厚,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虚实相生等话语,表现为“立意提纲挈领,表意画龙点睛,往往将博大精深的理论用几个字表述出来,意蕴悠长,耐人寻味”(段峰 2006: 182)。传统译论发端于佛经翻译。古代译经家在长达千年的译经实践中凝练出大量译论,其中不乏深刻洞见。但这些译论大都散见于“序”、“跋”、“例言”或“译文点评”之中,以“散金碎玉”而非“理论体系”的方式现世,如唐玄奘的“五失本”、“三不易”、“求真喻俗”等,其理论价值容易为谙熟西方学术话语规则的现代学人所低估。事实上,在当代中国译学话语实践中,客观存在一种不认同传统译学话语价值的倾向。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翻译观念而无翻译理论。也有学者将传统译论丧失话语权的局面归因于其话语方式不合西方学术话语规则,“我们国家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和翻译思考的传统,但因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方式不太符合今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学术话语方式,所以渐渐失去了话语权”(许钧 2012: 10)。这些观点虽论述角度有异,但背后隐藏着相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即用现代西方学术话语规则体系作为衡量传统译学话语的标准,而轻视了中国传统译学话语作为独立于西方的、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的独特价值,反映出“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下的“学术话语权力关系”:我们对西方译学话语的自觉服从。
当然,译学话语生态失衡以及学界对传统学术话语的陌生和疏离,也是我国文化、学术和教育大环境长期共谋产生的结果。自晚清以降,中国历经数次“西学东渐”和“传统文化批判”浪潮洗礼,“西方先进、传统落后”已然深入人心,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虽近年“国学热”兴起,但已积重难返,长期形成的传统割裂之寒冰非一日可以消融。就教育而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传统文化均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现代学人传统文化底蕴薄弱。例如,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中,因学科属性的关系,西方文化理所当然备受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文化在课程设置中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院校的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文化渗透存在很严重的‘一边倒’倾向,母语文化教学在英语或其他语种专业教学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叶慧君、王鹏 2010: 117)。在翻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西方译论通常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以西方译论为理论框架的硕博毕业论文触目皆是。因此,“吃进口洋奶粉长大”的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更加熟悉和亲切不足为奇。
二、“三重失语”困境
“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导致中国译学处于“三重失语”的困境。
首先是面对传统译学话语体系的失语。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留下极为丰厚的译学遗产,可以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参照。然而,将传统话语长期放逐到译学疆域的边缘已经使我们对之产生了疏离感和陌生感,导致我们难以与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与传统译学话语进行对话是全面了解和有效利用我国译学遗产的第一步。若缺乏与传统对话的能力,我们就难以对之进行解读、挖掘、转换、吸收,就必然导致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因缺乏历史逻辑和文化底蕴而显得摇摆不定和底气不足。对此,吕俊(2014: 1)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译学学科发展主要方向的迷失:“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译学研究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犹如一条失去主河道的河流,向四下漫溢,既看不到主流,也看不到流向。”
其次是面对当代中国翻译实践的失语。对西方译学话语的大量引进以及不加批判的接受,使中国译学研究患上了“西方译学话语依赖症”:依赖异域话语言说本土的翻译问题;一旦剥离了西方译学话语,就面临无话可说的境地。然而,产生于西方语言文化土壤、以西方翻译实践为基础、以解决西方翻译问题为价值导向的“他者”译学话语,即便对于我们而言拥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也难以实质性地解决中国本土翻译问题。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若强行将西方译学话语嫁接入中国译学疆域,难免水土不服,犹如淮北之枳,虽叶与淮南之橘相似,其实味道大不相同。“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性的东西,各国翻译理论都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文化土壤中”(陈福康 2000: 477)。因此,“以研究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为主,才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应回归的正道”(张经浩 2006: 61)。唯有根植于当代中国翻译实践,我们才能凝练出契合自身经验的理论,才能结晶出具有中国特质的译学话语体系。
再次是面对国际译学同行的失语。“在全世界搞得热火朝天的译学研究中,中国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潘文国 2012: 3)。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导致的巨大“话语逆差”:一方面,大量引进的西方译学话语已经全面占领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可供输出的原创性译学话语不多。缺乏独立的学科话语体系,就无法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获取国际话语权威更无从谈起。“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与话语权威的统一”(郑杭生 2011: 27-28)。中国译学界要在国际译学话语格局中拥有说话权利和话语资格,获得说话权力和话语权威,起码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掌握了本土翻译研究的发言权,对本土翻译研究议题具有阐释、设置和主导能力;二是自主发展出可以为世界译学界普遍接受和应用的译学话语,为推动世界译学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突破失语困境,在国际译学话语格局中获得独立和平等的话语身份。
三、反拨“译学话语生态失衡”的途径
近年来,随着学界文化自觉的增强和理论意识的觉醒,“译学话语生态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失语”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与反思。在话语实践层面,学界开始以实际行动尝试对之进行反拨,其主要途径可以归纳为“四化”,即对传统译学话语进行“现代化”、对本土译学话语进行“国际化”、对西方译学话语进行“本土化”以及译学话语“创新化”。
所谓“传统译学话语的现代化”,就是要在现代学术话语规则的观照下,对传统译学话语探真索源和梳理整合,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现代阐释和转换,以激发传统译学话语的活力,利用传统译学话语的价值进行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探真索源”就是要对传统译学话语进行“复原式”研究,其根本意义在于“恢复传统译论的本来面目”,通过“复原传统译论的问题意识、实践基础、理论权威”,达到“进入原译论的话语体系并将其置入原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理解、阐释”的目的(陈达、龚小萍 2014: 14),也就是要采取“历史性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的策略,尽可能回溯到传统译学话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以把握其含义,避免“以今目古”和“以西目古”造成的扭曲。“梳理整合”就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和现实的眼光对传统译学话语进行审视,摄取其对当代译学话语构建有价值的成分加以利用,避免“盲目崇古”。“现代阐释”就是要以当代学术语言、逻辑和规范对传统译学话语进行解读,赋予传统译学话语以现代学术特征。“现代转换”就是对传统译学话语的概念、范畴、理论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应用,使之进入当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充实当代中国译学话语内涵。“现代转换”是传统译学话语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传统译学话语资源为当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传统智慧和东方气质,使之具备独立的话语身份。在将传统译论现代化方面,南开大学王宏印(2003)所著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令人印象深刻。该书以传统译论文本为基础,梳理了传统译论所涉及的重大论题,并在现代翻译理论的观照下对之进行系统性的诠释与转换。例如,将玄奘的“五不翻”论转换成“一词多义”、“文化局限词”、“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神秘色彩的词语”和“感染力”等五个现代译论范畴,实现了古今译论的有机通融,对于我们利用传统译学资源构建翻译学科话语体系很有启发意义。
所谓“译学话语国际化”,并非“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强调的是“接”,就是在“西强中弱”的不平等话语关系的语境中,中国译学界在承认自身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的前提下,通过“接收”国际先进的译学话语来达到与国际同行的“同轨而行”。“国际接轨”就是要通过接纳国际话语来达到为国际所接纳的目的,所以特别重视跟踪、引进和回应国际译学议题,采取“思他人之所思,言他人之所言”的方式以获得国际话语空间。“与国际接轨”是一种“拿来主义”式的话语策略,在我国现代译学发展的初期,有利于我们在短期内实现话语更新,提高中国译学话语水平,并与国际译学界“接上话”。但是,“思他人之所思,言他人之所言”,如果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就容易被强势话语控制,丧失学术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我国不少翻译研究成果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验证或应用,而对其进行反思、质疑、证伪、发展的却很少”,“结果是翻译研究文章数量多,但真正有学术见地、有理论价值的却不够多”(许钧、穆雷 2009: 87)。这正是“译学话语生态失衡”下学术自主性缺乏和学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典型症候。
“本土译学话语国际化”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译学话语翻译成外语送出国门。“国际化”就是以恰当的路径、合乎逻辑的方法、无障碍的语言向国际译学界展示、传播我国传统的、本土的译学话语,使之走出国门,为世界所理解、接受和应用,由此提高中国译学的国际学术贡献度,促进中国译学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因此,“国际化”是一种“送去主义”式的积极的话语构建战略,通过话语输出,使中国译学话语为世界所认同和接受,从而在国际话语格局中获得独立平等的身份,改变西方霸权下的话语秩序。当然,要进行“国际化”,中国译学界首先须摒弃“惟西是从”和“自我轻视”的“边陲思维”,以反省批判的精神,自觉抵制对西方译学话语的依赖。“国际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向国际译学界展现中国译学话语的本土气质,通过“凸显话语差异”的“自我再现”策略来构建自身话语身份。当然,应“凸显”的“差异”是中国本土译学话语的精神内核,在语言表述和学术规范方面要“与国际接轨”,否则就难以为国际同行接受和认同。在推动中国译学话语国际化方面,已故香港学者张佩瑶教授堪称学界典范。早在10多年前,张佩瑶(2004)就呼吁建立“翻译话语系统”,其编著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更是她自己参与中国翻译话语系统构建的成果。张佩瑶“有意识地运用身为译者和编者的权力介入文化政治”(张佩瑶 2010: 10),为凸显中国译学话语的差异和消除西方读者的文化障碍,在该书体例的编制上采用了独特的编、译、评、注的方法,实现了翻译史实呈现、古代译学话语翻译、译人译事评论和传统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营造一种历史文化的纵深感和语义上的层次感”,使西方读者“明白中国与西方译论何以会同中有异,以及异之所在”(张佩瑶 2007: 39)。该书是中国学界首次以专论的形式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传统译学话语,对于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传统译学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西方译学话语本土化”,就是要在“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观照下,以本土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将西方译学话语的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翻译实践相结合,使之服务于本土翻译实践,以建立起立足本土、涵容本土气质的译学话语体系。 作为一种积极的话语构建实践,“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对“他者”话语进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扬弃,通过对异质话语的批判性接受与合理改造,使之有机地融入本土译学土壤,以形成具有本土气质的译学话语体系架构、阐释方法和研究范式,使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真正具备独立自主的理论和实践品格,确立对本己话语体系的身份认同。要对西方译学话语进行本土化改造,首先要认识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自觉的批判意识,对西方译学话语慎思明辨,戒除全盘吸收和强行嫁接。其次,要以“他山之石,可以治玉”的态度,对异质话语进行扬弃,使之有效参与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译学话语创新化”也是根本性扭转“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学术创新是一个学科永续发展的驱动力,也是一个学科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如果缺乏学术创新能力,那么构建独立的学科话语体系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本文借用李春华(2011)文化创新类型划分方法,将译学话语创新分为“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和“融合性创新”三大类型。“突破性创新”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创新,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它意味着超越现有的学科话语体系,运用全新的概念在一个更高的知识系统中开展研究。由于其颠覆性和“异端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通常在短期内不易为既有知识体系接纳,但一旦获得话语空间,学术影响力会大幅提高,甚至会主导学术议程设置和引领学术发展动向。“渐进性创新”是一种改良型的纵向创新,表现为对现有学术成果的深化、拓展和补充,使之更加丰满、成熟。例如,基于Mona Baker的翻译共性假设理论,通过对翻译体汉语的宏观统计特征、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的考察,对明晰化、简化和规范化等译语共性进行证实、证伪和修正,从而推动共性假设理论在汉英语言对中的发展,就属于渐进性创新范畴。“突破性创新”话语是“全新的东西自己先说”,而“渐进性创新”话语是“接别人的话继续说”,因此更容易在短期内得到既有话语体系的承认,但如果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容易被他人话语左右而无法突破其“势力范围”。“融合性创新”就是基于现有理论间的内在联系,逻辑地整合其特点和优势,催生出一种具有新质特征的话语形态。采借性、集成性或交叉性是“融合性创新”的显著特点。“融合性创新”的译学话语,最典型的莫过于近10年来兴起的“生态翻译学”,其显著之处,就是“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译学研究,从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跨科际研究 ‘关联互动’,并最终融入它们所共同依托的生态系统,从而构成翻译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胡庚申 2009: 3)。“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者们力图改变我国原创性译学话语相对匮乏的态势,以“打破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统天下’并终结东西方翻译理论生态‘严重失衡’的局面”和“构建东西方翻译理论真正平等对话的平台”为己任(思创·哈格斯 2013: 1),成为参与当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前所述,现代中国译学的概念体系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因此,“中西译学话语生态失衡”态势还将长期存在。在现阶段,中国译学话语创新仍然不得不依靠西方译论进行渐进性创新和融合性创新。不过,也要认识到,创新可以激发学术活力,但也会把人带入歧途,所以要处理好理论创新与学术规范的关系。确保翻译研究的创新符合翻译学科的内在规律,遵循学科的内在逻辑(傅敬民、许志方 2014)。
四、结语
随着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研究渐成外语界“显学”,译学研究队伍日渐壮大。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独立的学科”并不意味着“学科的独立”。后者的实现,则有赖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成效。“中国译学建设的基础,乃话语建设”(杨晓波 2011: 13)。从根本上扭转“话语生态失衡”的局面是建设独立的译学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鉴于此,学界须以反省性的自觉,对当今中国译学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建设性重构:一方面,要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译学话语体系进行全面审视,检讨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要以明确的目标指向性,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展手术式的话语体系建设。唯有如此,才能面对强势的西方译学话语,确立学术自尊和自信。而基于文化自觉的学术自尊和自信,是获取学术话语权,推动中国译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缘走向中心的前提条件。
陈 达, 龚小萍. 2014. 译学继承与发展: 传统译论现代化新论 [J]. 上海翻译 (4): 13-16.
陈福康. 200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董秋斯. 2009.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C] // 罗新璋, 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601-609.
段 峰. 2006.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3): 181-187.
傅敬民, 许志方. 2014. 谈谈翻译研究的创新与规范 [J]. 上海翻译 (4): 11-12.
胡庚申. 2009. 生态翻译学: 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 [J]. 上海翻译 (2): 3-8.
李春华. 2011. 有关文化创新的几个问题 [J]. 理论探索 (3): 3-7.
吕 俊. 2014. 目前我国译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J]. 上海翻译 (3): 1-6.
潘文国. 2012. 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 1-7.
思创·哈格斯. 2013. 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进展与趋势 [J]. 上海翻译 (4): 1-4.
谭载喜. 1987. 必须建立翻译学 [J]. 中国翻译 (3): 2-7.
王宏印. 200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 钧. 2012.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 [J]. 中国翻译 (1): 5-12.
许 钧, 穆 雷. 2009. 中国翻译学研究30 年(1978—2007) [J]. 外国语 (1): 77-87.
杨晓波. 2011. 中国话语与中国译学 [J]. 上海翻译 (2): 11-15.
叶慧君, 王 鹏. 2010.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母语文化教学的思考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9): 117-120.
张经浩. 2006. 主次颠倒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 [J]. 中国翻译 (5): 56-61.
张佩瑶. 2004. 对中国译学建设的几点建议 [J]. 中国翻译 (5): 3-9.
张佩瑶. 2007. 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 [J]. 中国翻译 (6): 36-41.
张佩瑶. 2010. 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郑杭生. 2011.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 27-34.
(责任编辑 侯 健)
通讯地址: 315175 浙江省宁波市 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重构:余华小说《兄弟》的译介研究”(Y201432725)的阶段性成果。
H059
A
2095-5723(2016)03-0089-06
2016-07-22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