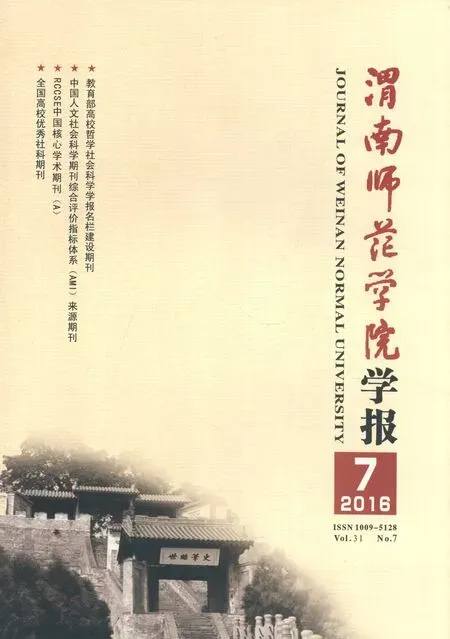论周公度的“童心”写作及其意义
——以小说集《从八岁来》为中心
宋 宁 刚
(西安财经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1)
论周公度的“童心”写作及其意义
——以小说集《从八岁来》为中心
宋 宁 刚
(西安财经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1)
摘要:周公度的小说集《从八岁来》,以一个生在乡村、名叫小宽的七八岁孩童的眼光和口吻贯穿始终,讲述了他童年生活的点滴,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小说,而首先是一部优秀而独特的小说集。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他的孩童式的感受,令人读来,或忍俊不禁,或叹为惊奇,或若有所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书写的“真”(真诚、真实、真心)。可以说,周公度的如此写法,是双重意义上的“童心”写作:既写出了一个孩童的“童心”——真实内心及其生活经验;也是一个成年人满怀绝假纯真的本心和体贴理解的真心,去书写和创造这些篇章的。这部小说集对于当代小说创作具有启示意义,它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实践。
关键词:周公度;《从八岁来》;童心说;真实
诗人、作家周公度,是目前国内一位出色的70后写作者,也是陕西文坛令人瞩目和值得关注的一个才俊。早在十几年前的世纪之交,周公度就活跃在中国诗坛,与许多诗歌现场和事件都有交集。十几年来,他以其独特、丰富和极具个性的创作,让人不时感到耳目一新,也不断带给读者惊喜。他的诗歌、随笔,都写得轻盈微妙,别成一体,字里行间,留下无限空响和微风一样的气息,读后掩卷,余味悠长。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臧棣在谈及周公度的诗时曾说:“周公度的诗比较犀利,有洞察感,非常精准、锤炼。他的诗歌的想法非常内秀。在类型上,他的写作偏向于知性写作,诗人用先知的面具或口吻。他写的比较低调。知性写作有一个核心,就是要把编撰的经验如何带到更广阔的人类的背景之中……如何把内心的经验放到更广阔的人类的背景之中,需要很大的拿捏功夫。……周公度是隐性的波德莱尔,他在很多方面显得比较内秀,这种低调的处理,风度有节制。”[1]
的确,犀利、洞察,精准、锤炼、知性、内秀、低调、节制……都是周公度诗歌创作的主要特点。不过,这些特点,却不只属于他的诗。实际上,它们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周公度的随笔和小说中。
一
周公度最新的小说集《从八岁来》,我是笑着读完的,也是沉浸在对童年和乡村的回忆中读完的。这部新近出版的集子,以一个生在乡村、名叫小宽的七八岁孩童的口吻和叙述视角贯穿始终,讲述了他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主人公所经历的故事,还是他的孩童式的感受,让人读来,都或是忍俊不禁,或是叹为惊奇,或是若有所思……流连顾盼其中,不忍释卷。一如作家张炜所说,这部书,是“一封(封)带着露水图像的乡村书简”[2]封底。因为它的真——真诚、真实、真心,才牵动每一个“收信人”的心。
回想同类题材的作品,从文字的诗意、机智、俏皮和满满的慧心来看,几乎鲜有可比。而其叙述口吻之与孩童相契、“不隔”,则会让人想起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3]。只不过,后者是个回忆录式的长篇,叙述上也多带有俄国式的庄重、沉实,从幽默、微妙、童趣和举重若轻等“指标”来看,不免略逊一筹。
其实,《从八岁来》也可当作长篇来看待。因为它有“小宽”这个小主人公贯穿小说的始终,每个长短不一的篇什也都以他的口吻来展开叙述。一路读去,各个故事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暗中勾连、互为支持,共同勾勒和托举出主人公不同的性格侧面,“小宽”的形象因此显得立体、饱满、层次丰富。
读完整部书,想到小说中的“我”——“小宽”,因为好奇、想看热闹,在一群对峙和酝酿着打架的大伙伴之间傻傻地问:“是谁打谁?为什么打?”最后被双方抓住痛打了一顿,依然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当“姐姐”为他出了气,并且要求,如果“小河”(打了“小宽”的男孩)的爸爸回来不打“小河”,就让“小河”的姐姐“小莹”嫁给“小宽”时,“小宽”竟还惦记着“小锤”(打他的另一个男孩)也有个姐姐(《你们在打谁啊》)!
这个 “媳妇迷”,女生看他一眼、跟他说一句话,都要“想半年”的小宽,有着天真的“虚荣”和“早熟”,也因此而有无数的糗事。比如听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在看电视时说了句“真好看”,就学着电视中主人公的模样,要妈妈给他买件花格子衬衫穿上。根本没有(时间和意识)去想,女同学的那句“真好看”,是指电视好看,还是男主人公的穿着好看。哪怕妈妈买来的衣服太大了,他也要穿着去学校。结果被那个女生的好朋友拦住告诉他:“毕芸芸让我告诉你,你太不要脸了,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穿得像流氓的!”当即,被如此打击、甚至“羞辱”的“小宽”“盯着地面,想尽快找个地缝出来”[2]10-13。
这个有些自以为是、又有着强烈自尊的七八岁的男孩,有着令人称奇的经历:在地头树下与一个大姑娘的“奇遇”(《我家的树》);在船上遇到会写诗的小女孩(《月下小诗》);站上他家院里晾衣服的铁丝,给他表演走钢丝的“安静得像个风筝”一样的卖艺女孩(《走钢丝的女孩》)……说是“奇遇”,其实大多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会遇到的“普通”经验。呈现在小说中的这些“奇遇”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惊奇和特别,更多的是因为作者有一种发现文学的微妙之处的高超能力以及他虽然妙笔生花、却不让人觉得过于铺陈、以至虚假的叙述才能——实际上,虽然小说的叙述常充满诗意,作者的叙述却时时会让我们忘了这些文字是由人所写,而是直接地透过文字只沉浸在小说的叙述当中。
二
小说中,多少带有些作者身影的主人公“我”——“小宽”,身上具有许多属于孩童、又超出孩童的令人惊奇的观察和感受力。他跟母亲去看吕剧《墙头记》,母亲说,千万别娶个这样的媳妇。他“没有辨认清楚”,后来这个戏在别处上演时,他又去看,“记住了这个媳妇的脸型:椭茄子脸孔,削薄的的嘴唇。眼神瞪得让人打一个踉跄”[2]10。他注意到自己年轻的班主任老师“瘦瘦的,腰很细,腮和鼻子上有几粒雀斑”,“上课时,我喜欢盯着她的脸看,后来连她的背影和腿也喜欢了。她也喜欢对我微笑。她的牙齿白白的。嘴唇抿成弓背的形状,像在牙齿和嘴唇间含了一颗糖”[2]14。如此详细和“不规矩”的观察,实在让人有些惊讶。如果对我们自己的童年经历多一些回忆、检视和沉思,而不是急于下道德性的判断,我们大概会承认,这些看似让人意外的观察,其实都是真的,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不愿意去承认罢了。
这个大胆地观察自己班主任的“小宽”,两个星期后,竟然给老师写了一封让人哭笑不得的信:
毕老师,我今年七岁了,再有十三年我就二十岁,就能娶你做媳妇了。
你等着我啊。我会对你一辈子好![2]14
不知那位收到这封信的老师会有何反应?作为读者,我们读这封信,大概不会将其当真;但同时,又没法不认真对待。它带给我们的是忍俊不禁,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不容粗率对待的纯真。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堪称“小大人”的“小宽”有这种似乎超出他的年龄的观察和感受力,他才有那么多的故事,让我们感到一次次的意外和惊叹。在《从八岁来》中,类似的细节和内心感受之描写,实在还有不少。
朦胧的爱意、强烈的欢喜、尴尬、颜面扫地,甚至偷窥……初读之下,我们同样可能心生疑问:这是一个七八岁小孩的真实感受吗?仔细想一想,如此经历与感受,其实既不奇怪,也不为我们所陌生。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都可能有过的经历。只不过,我们在一闪念的瞬间之后,就轻易地放过了它,从未如此清晰地表达过,甚或,从未如此认真地正视过。也因此,当作者以他清透的笔,准确细致地描绘、托出这些事实时,我们既感到陌生、惊奇,乃至疑惑,细想之下又会觉得不仅似曾相识,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熟悉、真实和亲切。
周公度了解他笔下的人物,也懂得如何写小说。他知道沈从文的话:要贴着人物写。所以,他笔下的男孩才会如此夸张地感知:“河水流了一亩地那么宽的时间。”[2]28“过了至少有一年的样子,他们才分开。”[2]33“这一刻有一年那么长。”[2]149“我妈的感慨里有一万年的时光。”[2]175“小棠的双手紧紧地交叉着贴在胸口,全身发抖。她完全被吓呆了。至少过去了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才稍稍恢复了平静。”[2]335这些,是相对论的绝好注脚,也是对孩童的专注与感受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发现与描写。
与此类似的,是“小宽”对另一些事物的“衡量”。比如他说:“槐树中间的一棵榆树有三个我高。”[2]22在他眼里,西瓜的大小,可以分为“一手掌的,两手掌的,两手掌以上的”[2]71;而那与他年龄相当的女孩子,“她的身高比我矮一只小鱼”[2]179;他因此知道,“每个伙伴都像女孩子喜欢镜子一样喜欢着每一个黄昏”[2]165;并且认为:“女孩子们的谎言,比男孩子要丰富上一棵大树上的树叶那么多。男孩子说谎的品种,就像一株西瓜秧苗上的西瓜,怎么数也数不到十;女孩子说谎的品种,就像秋天的枣树和夜空里的星辰,你看一眼就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2]137……这样的语言和譬喻,真实地表现了一个乡村小男孩的心理和眼光,与人物的年龄和性格特征高度吻合,也显示出作者对小说人物的把握之精准。更不用说,他的这些诗一般的譬喻,由于从孩童的视角出发,带给我们与成年人不一样的陌生和新鲜的阅读感受。
同公度到底是诗人。即使写小说,也同样清晰地显示着其作为诗人的面貌和本色。我指的不仅是上述譬喻,还有书中俯拾皆是的充满诗性光芒的句子,比如:
她的双眼凝成两根尖锐的线射向我。[2]3
我担心她发现我在树上看到了他们的样子,全身紧张得像螳螂一样绷紧了身体。[2]33
她重新严肃地看着我。她把乌黑的眼珠换成了两排小钉子。[2]37
雷声咔嚓嚓地传输入我们脚下雨水覆盖的地面,像镰刀触着柔嫩的草茎。而我们仿佛只是草茎间隙柔弱的风。[2]119
那串珠一个一个数过的声音像是露水从早晨的草茎低落在我的心尖上。[2]143
她的声音比船下水波的声音还要清晰。比月光还要清脆。像一块玉石打碎在冰凌上。[2]180
这样的句子,在《从八岁来》中,简直不胜枚举。它们或奇特、精准,或新颖、清晰,与小说的整体气氛完美和谐地成为一体。作者写那个走钢丝的小女孩:“她看我一眼。闭上眼睛稍稍停了一下,慢慢展开双臂,像风筝一样安静。”[2]154写围成一圈做游戏的孩子:“每个人的脑袋专注着环形的圆心,臀部朝外,像在湖泊中埋头进水捉食的鹅。空闲的手穿过与身体间的缝隙支在外面,一只又一只手,那么茁壮有力!”[2]162写夜晚坐船去外婆家,“水波的表面仍然有些午后的微热,脚掌时不时触到浅水处的水草,粗粝的感觉,应该是丑陋的木锯藻,滑腻柔软的感觉也许是一条胖胖的鲫鱼脑袋……银色的月光像冬日的薄霜铺满了河滩。我的影子像外婆家墙壁上剪纸一样照在船头的甲板上”[2]170。这些都显示着作者对小说人物和乡村样貌真实而又诗意描绘。这些诗一样的句子,是作者为小说而写下的,也是作者作为诗人的眼光与敏锐感受之结晶。
除了以上述及的、在小说中不胜枚举的充满诗性光芒的句子,我们更可以看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所写出的有如叶脉上的透气孔一样细小、微妙的气息。比如:
她上下打量着我,神秘地笑着,没有再和我说话,转身走到菜园另一头的梧桐树下,坐下翻一本画册。那是我家的树。
她的笑影响了我的心绪。
我心里起伏不已,把嫩茄子都摘掉了。还碰掉了不少茄子花。[2]17
在“她”的打量和笑,与“我”的心绪之间,有多少暗示和无尽的意味感?为什么强调那是“我家的树”?为什么在说摘掉了嫩茄子之外,不忘强调“还碰掉了不少茄子花”?
又比如:
一个比我略微高一粒芝麻的女孩站在两扇门的中间,她穿着轻薄、柔软的衣服,脸上是夜色与房内的灯光交汇出的昏黄的颜色,不能看清楚她的细致样貌,但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她眼睛发出的凌厉的带着刀刃的力量,可以在我家院子里一秒钟之内挖个深深的小坑把我埋掉。[2]151
“小宽”眼中所看到的女孩、衣服、夜色、灯光,与小说情节的内在紧张血溶于水般地交融在一起,既显得轻盈优美,又不显得单薄和廉价,而是很好地推动了故事的内在发展。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周公度的“文字中隐藏内容,远比表面显露出的深远蕴藉”[2]封底,诚哉斯言!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文学的普遍规律,正如钱锺书《管锥编》中引《宗镜录》的话:“遮言为深,表言为浅。”[4]840显然,周公度是深谙“说破乏味”的要旨的。阅读《从八岁来》,我们会时时感到作者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的用心之处。于是,在阅读的会心之余,就不禁莞尔,或者捧腹。
三
周公度善于发现、也善于描写女性的美。在他的随笔集《机器猫史话》[5](尤其该书的前半部)中,这方面的特点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不同的是,由于文体的差别,在后一部书中,他的书写尺度更大,也更为袒露。其相同之处,则是文字上的精简以及文字背后作者的“顽劣”。如果说在《机器猫史话》中,周公度直抒胸臆般地描绘了他对女性的爱恋,那么在小说集《从八岁来》中,他则是将自己隐身在小说主人公“小宽”的后面,借“小宽”的口和眼,让我们领略了他对女性之美的描画——当然,这一次是从孩童的视角,勾画出于懵懂中成长的孩童对女性之美的观察与注目。
小说中,由“小宽”的眼睛去看,无论是漂亮的女同学、比他大一些的姑娘,还是年轻的女老师,无不显出动人的美:
(音乐老师)她嘴巴小小的,说话甜甜的,腰细细的。[2]23
小莹的眼睛在她家院子里昏黄的灯下,像珍珠蘸着露水。[2]31
(小棠)她的背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柔软。[2]217
年轻女孩子……她的嘴角笑成了月牙的模样,比小棠的笑容好看一千多倍。[2]228
小文的姐姐把善意的笑声当作了珍贵的祝福,此后的每一天她都是那么青春,她全身散发的饱满气息,足以把全村庄所有树木的树叶擦洗一遍。[2]235
(上高二的女孩)她身上有嫩嫩的鲜草的气味。[2]43
(小河的姐姐)她换了一身无袖浅色碎花的连衣裙,裙子把她的腰衬得细细的,看上去非常清爽,秀美。让我精神一振。[2]103
(挖沙人的妻子)穿着清凉、简洁的无袖衬衫,凉鞋,及踝的裤子,齐耳的剪发,像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漂亮又自信。[2]169
没有人说话。只有船舱外的水波声,和小女孩轻微的鼾声。……她的脸是小鱼脑袋的样子。秀气的尖尖的下巴。蓬乱的一绺儿头发掩着她长长的睫毛。她的嘴巴也是小鱼嘴巴的样子。[2]173
(小女孩)她月光下的样子像一棵古代的小小的花树。[2]178
她的眼睫毛长长的,像麦芒一样亲切又拒人身外。她眨下眼睛,眼睫毛好像在扑闪着河水里的月光。[2]105
从这众多的对女性之美的描述中,我们大约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隐性的波德莱尔”,一个对美有着高度迷恋的饕餮之徒——即使以上列举,远非全部。
仅就这一点来说,《从八岁来》作为一部小说集,虽然是以八岁的孩童为主人公的,却绝不是写给“八岁”孩童的,更不能被看作儿童文学。周公度的与《从八岁来》中的叙述相似的短篇小说《我的泪水》,被收入《2014年陕西文学年选·儿童文学卷》[6]135-146,不能不说是一个误会。实际上,作者周公度只是从一个八岁孩子的目光和经验展开小说的叙述。就此而言,《从八岁来》首先是优秀的小说、纯粹的文学,而不是什么儿童文学。
当然,《从八岁来》作为一种提醒,唤起了我们重新认领自身的生命经验,尤其是孩童时期的经验。但这些,首先是对于走出了孩童生活的青年和成年人才可能的。同时,这样一部书,它自然也是写给“八岁”乃至十八岁、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的。年轻人,由于自身距离孩童的经历更近,更容易接受和认同,也有这个道理在其中(据说周公度此书在网络上颇受年轻人喜欢)。从作者这一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他都没有让自己的笔越过恰当的、悦目继而悦心的尺度,他很好地把握着语言和叙述的分寸,干净、轻微,点到为止,没有与小说的整体风格相扦格,而是使之极为协调地与小说文本成为休戚与共的整体,仿佛清早的草叶与露珠、潮湿的泥土与晨雾、田间的耕牛与炊烟……高度和谐一样。
在小说集的前面,周公度借用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加的一句话作为题记:“真实是甜的。”而《从八岁来》中,周公度也的确写了很多的甜。
会笑的女孩眼睛甜甜地笑着。[2]152
(老师)她的牙齿白白的。嘴唇抿成弓背的形状,像在牙齿和嘴唇间含了一颗糖。[2]14
(走钢丝的女孩)她们弄出的种种声音搅动了夏夜里的空气,使得我的呼吸里有了微微的冰糖的甜意。[2]150
她把柔软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两颗眼珠里装着黑色透亮的糖。[2]36
我站在它巨大的树冠下,久久地仰望着它。像仰望一尊神一样专注;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神的光芒。神的光芒像乡村小径上免费施与的白糖。[2]38-39
我听到小麦擦着布袋内壁的哗啦声,和师父静得有些甜的呼吸声,还有我家的小麦与别家的小麦相遇的沉甸甸的汇合声。[2]141
她站立的姿势像她的名字一样。
毕芸芸。我查了很多遍《新华字典》,“芸”字是一种香草的名字。
我似乎都能闻到她身上软软的香气了。[2]200
她的脚趾新染着红指甲,还有轻微的凤仙花的味道。[2]201
这些——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像被夏天阳光晒软了的糖果一样的”[2]172句子,和它们所属的小说篇章一样,散发着引人入胜的、甚至带有诱惑意味的淡淡的甜味。那是童年的味道,也是乡村和回忆的味道,带着田野或水草的气息。那童年是复杂而又单纯的,那回忆是轻盈而又深长的。它们都属于童年的真实。
更加属于童年真实的,是作者对糖和甜味的反复描写——虽然反复,却花样迭出,毫无重复之感。有理由相信,周公度之所以对这甜味念念不忘,是因为他知道糖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或许意味着一切——如果再加上玩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些描写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作为作者,对自己笔下孩童的了解。我们甚至会猜想,这份了解,是来自于作者写作之前所下的功夫,还是来自他的童年记忆,抑或来自他至今不改的像孩子一样对糖的喜爱?
四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他著名的《童心说》中言道:“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7]368正如“童子”是“人之初也”,“童心”也是“心之初也”。某种意义上说,周公度在《从八岁来》中的写作,与他之前在儿童诗集《梦之国》[8]中所做的一样,是双重意义上的“童心”写作:既写出了一个孩童的“童心”——真实的内心及其生活经验,也将一个成年人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和体贴理解的真心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正是以这颗最初的“童心”“真心”,才可能写就这些令人不忍释卷的美妙篇章。在《从八岁来》的“序”中,作者以一篇题为《回忆我说过的谎话》的简短却肯綮的文字,进行了自我检讨:“这些年来,我说了多少谎话……”通过反省,他深刻地发现,谎话与虚荣紧密相连,与懦弱比邻而居,与懒惰又是最佳拍档。 他坦承:“我在回忆儿童时代之际,才明白自己是一个愚蠢的可怜人。”也因此,“虽然有些晚,我才想到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展现一个不伪装的笑容,写一封简单的信笺,去一个心意从容的地方,种一株不娇嫩的小树,倾听一首乡间的民谣,跟随一颗勇敢的心,爱一个会发脾气的人。拥有一个真实的童年,一个清澈的回忆”。这些夫子自道的话,也旁证了上述“童心”和“真心”之说。就此而言,“拥有一个真实的童年,一个清澈的回忆”,是《从八岁来》的一个主旨,也是作者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一个初衷。
上述的这些描写和小说集中的其他精彩描写一样,让人读来,或欣喜、莞尔、沉醉,乃至向往……无论哪种情形,都会让人感到,作者以一支轻盈而幽微、简洁而透彻的诗笔,发现、也写出了童年更多的真实。它们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与“回忆”,是带着甜味的真实,或说,带着真实的甜味。它让我们感到,一个敢于承认自己虚荣,并因此重新获得真实的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唤回多少春风、阳光、青草、露珠和泥土的潮湿的芳香。
在《从八岁来》的封面上,小说集的英译名被唤为LoveLetterstoChildhood,直译则是“给童年的情书(信)”。或许,这个译名道出了作者的另一半心曲。也即,对周公度而言,这的确是他写给童年的情书(信),当然,也是写给生活的。它不是写给某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同时,也是写给所有人的。相信读者自然会读到属于自己童年的某些熟悉的内容;或者,即便从那些陌生而令人惊奇的文字中,也勾起只属于我们自身的回忆。
不夸张地说,《从八岁来》对于当代小说创作极具典范意义。它以自身的轻盈、透彻、殊少年龄限制等诸多优势,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实践。将其放置在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陕西小说版图中来看,则更是意义非凡。正如它是个异数,它也反拨、修正和改变了长期以来陕西的文学创作面貌。就现实的情形来看,作为小说家,周公度远没有被接纳,更不用说重视。他给予当代小说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也是前瞻性的:无论是语言的诗性,感受力的真实、透彻、直接,还是叙述的取舍——复杂的单纯,以及他的价值立场——已然稀缺的善意,都是如此。
2014年,周公度可圈可点的儿童诗集《梦之国》出版面世。一年后,他又为读者捧上了更令人击节的《从八岁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续集”,应该是大致不差的。《梦之国》中的“我”,那个小男孩,长大几岁之后,就成了《从八岁来》中的“我”——名叫“小宽”的男孩,而心思也更多、更显丰富和复杂了。作品的篇幅因之更长,生活的广度也因此而得到铺展。
《从八岁来》展示了一个小男孩的丰富内心,也呈现了一幅诗意的乡村画卷。作者周公度曾借小说主人公“小宽”之口说,“自然的美妙与乡村的每一个细节紧密相连,我们只是生活在其中,从来不去赞叹”[2]237。《从八岁来》也因此而可以看作是作者写给乡村、自然、人生童年与童真的赞歌。它唤醒我们关于童年、乡村和自己内心的记忆,丰盈我们对于童年的想象。它打开的是一扇门,透露出诗意的光,期待每个读者从中认领或已模糊的自己。
参考文献:
[1] “文学陕军”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摘要[J].陕西文学界,2014,(6): 32-35.
[2] 周公度.从八岁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 [俄]阿克萨柯夫.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M].汤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4] 钱锺书.管锥编(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 周公度.机器猫史话[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6] 阎安.2014年陕西文学年选·儿童文学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 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周公度.梦之国[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朱正平】
On Zhou Gong-du’s “Childlike Innocence” Writ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LoveLetterstoChildhood
SONG Ning-gang
(Liberal Art College,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Love Letters to Childhood, written by Zhou Gong-du, links the whole story up with the eyes and tones of a seven/eight-year-old boy named Xiao Kuan who grew up in the village, relating bits of his life during the childhood. Above all else, it is not a children’s novel in an ordinary meaning but really a collec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unique style. The main protagonist’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his feelings from a child’s eyes give readers impressions with laughing, surprising and pensive moods. And these are because of the “inherent quality” (sincere, true, true intention) written by the author. That’s to say, such approaches by Zhou Gong-du are the writing of childlike innocence in double meanings.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writes a child’s childlike innocence, his true heart and experience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lso appears an adult’s original intent full of pure falsehood and pure truth and his true intention with consid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oth two visions write and create these chapters. Therefore, thi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has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re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novels and furthermore enriches our writing practice of the latter.
Key words:Zhou Gong-du; Love Letters to Childhood; childlike innocence theory; true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7-0026-06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新世纪陕西小说“场”的构型与趋向研究(15JK1278)
作者简介:宋宁刚(1983—),男,陕西宝鸡人,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哲学与诗学、中国当代诗学问题研究。
【秦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