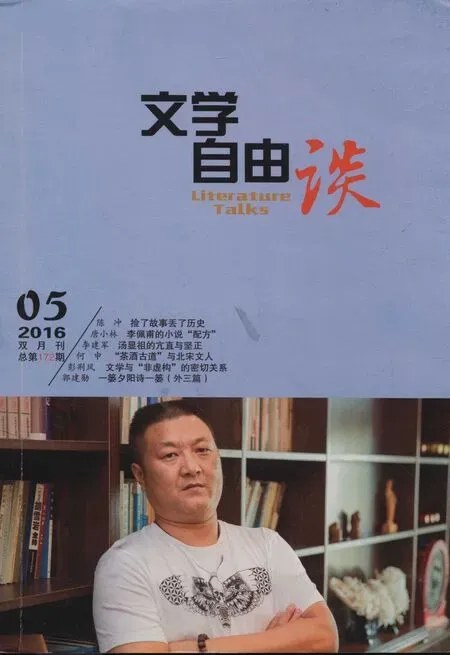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陈忠实传》:忠于历史,实于作家
□陈红星
《陈忠实传》:忠于历史,实于作家
□陈红星
2016年4月29日,作家陈忠实先生逝世,官民同悼,哀荣备至。在这一文化事件下,与陈忠实及其作品有关的话题再次成为广大读者关注的热点,而邢小利所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一书自然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通过对《陈忠实传》的认真研读,我深切感觉到这确实是一部忠于历史、实于作家、评传结合且颇有理论建树的作品,是研究陈忠实及其文学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学术著作。这部作品不仅从生平方面让读者对陈忠实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陈忠实研究的一些微观和宏观认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有拨云见日和犹如四两拔千斤作用的重要观点,从而廓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模糊认识。
《陈忠实传》体现了作者对于与陈忠实有关的人、事、物的严谨求实的精神,体现了传记作品的严肃性和作家本人的史家态度。如陈姓祖先迁徙蒋村的时间、蒋村村名的来历、陈忠实上初中时的助学金数额、陈忠实和柳青的三次见面、《无畏》的创作过程、陈忠实的个人藏书、《白鹿原》出版后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史实的钩沉,为读者提供了关于陈忠实研究的相对可信的资料;对一些尚不能确定的问题,也注明是聊备一说。这样的严谨态度和真实性,增加了《陈忠实传》的权威性。
真实性方面的另一个体现,是作者刻画了真实可信的陈忠实本人形象。如陈忠实关于在“文革”中受毛主席接见的纪念文章、请《北京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刘恒吃羊肉泡馍、撰写《白鹿原》书讯的过程、对国家关于城乡政策的区别问题的看法、谈对官员上下台的感受、“不愿意这样大过生日”的态度等,这些细节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于陈忠实的认识,为读者还原了有血有肉的传主形象。可以看出,作者对陈忠实采取了平视的观照视角,这就避免了将其神秘化和神圣化。
对传记作品,读者更为关心的是它的逻辑性,即:在涉及人生的重要节点时,哪些人、事、物对传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节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样,一部传记作品才呈现为有机的统一体,而不是毫无关系的事实罗列,读者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传主的人生轨迹和发展逻辑,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思考。
《陈忠实传》很好地满足了这些期待。比如,让陈忠实产生写小说念头的赵树理,让他产生强烈好奇心的神童作家刘绍棠,让他“把截断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接通了,干涸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也润泽了,变得有些僵硬的思维也柔软了,灵活了”的《西安日报》的张月庚,将他的散文《水库情深》推荐给《陕西文艺》的徐剑铭,在他倍感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帮他解困的崔道怡,向《人民文学》推荐《信任》的王汶石,鼓励和支持他的杜鹏程,以《人生》获奖从而刺激了他的路遥,从“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到“咋让咱把事给弄成了”的评论家李星,高度评价《白鹿原》的何启治等等。可以说,陈忠实的成长、成熟和成功,与他生命中出现的这么多文学好心人密不可分。
在传记的认识性上,《陈忠实传》最大的亮点和意义在于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了陈忠实及其文学世界,廓清了读者及研究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模糊认识。这些认识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二是宏观层面。
先说微观层面。《陈忠实传》对一些敏感话题做了严肃的探讨。如陈忠实对女性的态度问题——由于早年目睹了一位男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陈忠实终生与女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甚至影响到其作品中人物的性别比例。在《陈忠实传》中,作者没有做庸俗化的隐私“揭秘”,而是从创作层面去追根溯源:“纵观陈忠实的人物塑造,总体上看,写男性多,写女性少。即使是他的代表作《白鹿原》这样一部描写一方地域50年历史风云和生活变迁的巨著,也是群雄竞出,而只有寥寥数个女性。此种叶繁花稀的创作性别偏差,显然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深层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理有关。”这体现了作者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的学术高度。再如陈忠实对创作中的政治问题的认识,书中提到了2008年10月陈忠实在宁夏大学的谈话:“要把真正的政治和极‘左’政治区分开,不能用给人造成极大伤害的极‘左’政治来概括所有政治,同时排斥所有政治,不能因噎废食。作家感受生活,完成生活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思想,作家的思想也可以看成作家的政治……”我以为,这种对政治具有正本清源作用的观点,才是作家应有的认识。
对陈忠实阅读古典诗词的原因,《陈忠实传》认为:“一直以来,陈忠实的阅读,基本上是功利目的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写作。他主要写小说,偶写散文,他的阅读也就主要围绕这么两个方面。”而在《白鹿原》完成的前后,他却将兴趣转移到了阅读中国古典诗词上面,而这其中,他读诗赏词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等待《白鹿原》书稿审读意见的日子里,“此时他之读诗词,不是想读,不是爱读,完全是为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样的救心之法,想来不会真正进入诗词的意境。”后来,他获得了一连串的肯定意见,“他的心放下了,踏实了,心态也放松了,自由了,他才被古典诗词之美打动了,被古典诗词的万千气象和意境感染了,最后竟然沉湎其中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要能阅读古典诗词,是需要一定的心境和处境的。也许,心境来自处境,处境影响心境。”陈忠实阅读古典诗词的例子证明,中国古典诗词是被一定的心境孕育的,也能反过来孕育一定的心境。
陈忠实何以在50岁以后特别钟爱散文?邢小利认为:“散文是一种贴近心灵的文体,比起小说能更直接更自由地抒发作家自己的生命感受与体验。同时,散文是一个与创作主体自由而活跃的生命状态关系密切的文体。陈忠实之迷恋散文,也显示了他生命状态的自由和活跃。”作者客观地分析了陈忠实由小说转向散文写作的缘由,在不同生命阶段散文创作的特点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和阅读中国古典诗词一样,作家的写作也和人生的生命状态有很大关系。
关于《白鹿原》的创作动机,我们固然可以从《人生》获奖所产生的刺激、李星的激励、陈忠实个人的艺术探索等方面来探讨,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忠实从一位乡村老汉的“太阳的升落”这个隐喻所领悟到的来自生命的压力;正因为这样一种压力,他才需要创作一部“垫棺作枕”的作品。这是从形而上的高度认识了《白鹿原》创作的无形推动力,也是《白鹿原》创作最为根本的人生动力。这样来理解陈忠实的创作动机,就和作家的人生价值追求这一根本问题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具有了人生论的意义。
在宏观层面,《陈忠实传》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一是故乡对陈忠实的意义。邢小利指出:“陈忠实写完一篇或一部作品,往往在文末缀上时间地点,地名喜欢用带‘村’或‘庄’的字,感觉像在农村。这也反映了陈忠实浓厚的乡村情结。”陈忠实将自己的工作室称为“二府庄”,也包含一种“乡村情结”。他人生的前五十年生活在乡村,年近花甲时又回到了乡村。他说:“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这种气场就是他所说的“老屋是一种心理蕴结”;在邢小利看来,这正是一种“给心理以力量的蕴蓄”。我认为,“心理蕴藉”是理解陈忠实与故乡的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词,它概括了故乡对于陈忠实的文学意义。邢小利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陈忠实在“摸上60岁的时候,复归老屋祖居,一个人再住上两年,仔细分析,除了逃避或者说躲开他屡次有意无意提出的‘龌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时,他也要重新打量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这正是故乡对于陈忠实的意义,它孕育和哺育了陈忠实的文学与人生。
二是关于陈忠实的人生价值取向问题。邢小利认为,虽然陈忠实“性格中无关于隐,甚至丝毫无关”,但是“如果仔细读他复归原下这一阶段的散文,就会发现他居然步上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走过的路子,归去来兮,隐于乡村”。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存选择,陈忠实也一时无法超越。邢小利分析说:陈忠实“出身贫寒的农家,从小受苦受难,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奋斗挣扎,在文学之路上走得也不易”,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浮出水面,放出光彩。“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轻言淡泊,又怎么会自我隐退且甘于寂寞呢?一直没有的人怎么会轻言放弃呢?”这是理解陈忠实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中的之语。另外,关于陈忠实的身份定位,邢小利认为:“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谱系上看,陈忠实就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这一点对于理解陈忠实的文学思想和个人定位非常重要,它廓清了长期以来读者和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三是关于陈忠实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问题。《陈忠实传》认为:“在描写社会的乡村和自然的乡村两方面,鲁迅和沈从文,双水分流,各有侧重,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侧重于展现社会的乡村,一个侧重于描绘自然的乡村的艺术流向。而陈忠实在承续展现社会的乡村这一脉的同时,在艺术上不断更新,也吸收和融入了现代小说的魔幻、心理分析等艺术表现手法,而他的《白鹿原》更是表现了文化的乡村。”并评价说:“陈忠实是描写农民生活、乡村社会和文化的高手。”这是陈忠实对于乡村创作所赋予的新内涵,也正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之所在。
四是关于陈忠实研究的意义问题。《陈忠实传》的最后一节,将陈忠实的精神进化比喻为由蛹变蝶:“听命与随顺,反思与寻找,蜕变与完成,三级跳跃,陈忠实走过了从没有自我到寻找自我最后完成并确立自我这样一个过程,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作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研究陈忠实的真正意义:陈忠实就是一个作家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实现创作新高度的缩影。
《陈忠实传》以大量的人生及文学事实,为我们描述了陈忠实的漫长而艰难的文学人生,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邢小利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朴实真挚,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感受到了仿佛身临其境的陈忠实的旧日生活,也看到了作者邢小利个人的性情志趣。可以说,《陈忠实传》既是一部忠于历史、实于作家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超凡脱俗、引人入胜的纪实作品。
当然,正如邢小利自己所言,“也有许多还没有写出来。……写出来的,有重要的,也有不重要的;没有写的,却还有很多我认为是重要的,甚至是特别重要的。”“这部书还有许多不足,这是我日后要尽力弥补的。”(邢小利:《我为什么写陈忠实传》,《光明日报》2016年5月6日)随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不断演进,对于陈忠实及其创作的研究则可以跳出其在世时的某些局限性,从而获得一种更客观更公允的认识和评价。这是续写《陈忠实传》的意义之所在,也是陈忠实的研究界和读者所翘首以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