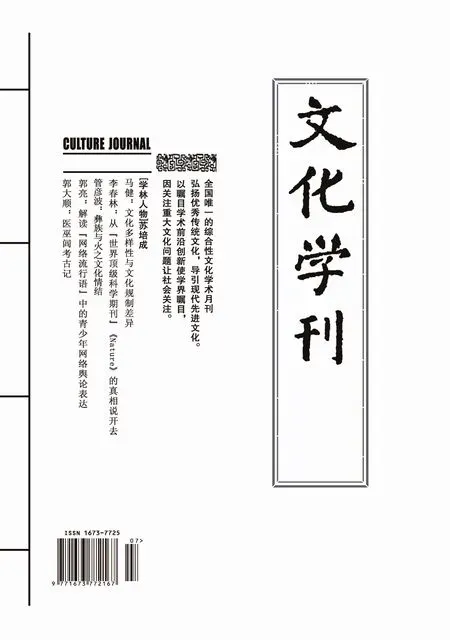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兴起的原因
邵鹏宇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师范教育部,江苏 常州 213161)
【文史论苑】
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兴起的原因
邵鹏宇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师范教育部,江苏常州213161)
清代学术的最高峰就是乾嘉学术,而考据学是乾嘉学者治学的重要方式。考据学在清代兴起的原因主要有外在时代背景压抑和内在学术理路变迁等。乾嘉学术乃至清学正是建立在对明末清初社会的反思之上。笔者便结合相关学者对清代考据学的研究,就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论述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兴起的原因。
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
一、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学简述
清代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集大成的时代,也是最后的黄金时代。清学发微多端,在各方面都有后人所无法企及的建树,但纵观清学,总能从代表学者的著作中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治学线索,一种从考证古代经典为基础继而扩展到各个领域的治学方式,就是考据学。在后学的学术史回溯中,考据学也称为“实学”或“朴学”。清代中期兴起的乾嘉学术直接就建立在考据学的研究之上,并以此形成众星闪耀的学人群体和庞杂博大的知识谱系,成为清代学术的最高峰。
王国维曾对考据学的重要性进行过高度评价: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且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1]
清代经学大师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的付勘标志着清学进入了总结时代,他晚年在《拟国史儒林传序》[2]中仍饶有兴趣地希望对本朝学人做一个学术史回顾,而这其中几乎所有列举的代表人物也都是精通考据学的鸿儒。
考据学成就了乾嘉学术的知识系谱,乾嘉学术也延续了考据学扎实质朴的学风,而探讨考据学在清代乾嘉学术兴起的原因正是窥探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关键所在。
二、外在时代背景的压抑
清代初年,尚未从悲痛沮丧中恢复的汉人士大夫,都在主动反思前朝覆灭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那些视野广阔、气节高尚的学者,纷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士大夫精神,但随着复国的希望渐渐湮灭,大多数汉族士大夫只能选择顺从或消极反抗,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悲观主义。清代初期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更加重了这种绝望的情绪,传统的儒学似乎就要坠入万丈深渊,这种无力感和恐慌始终笼罩着遗民阶层。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言中已认识到清初外在时代背景对学术的压抑已不可避免地为清代学术确立了研究方法和风向。
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话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越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龄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3]
在后世许多学者眼中,“文字狱”和“寓禁于修”等具象化上层压力对学术自由风气的压制是考据学兴起的外因,特别是在非考据学家的眼中,繁琐考证、不问世事的治学方法是学人奴化退化的重要标志,但孟森在《清史讲义》中对“文字狱”和“寓禁于修”的历史评价有一番独到却不失理性的见解:在嘉道社会危机产生之后,尤其是那些出生于清末的学人中,呼唤变革、除旧迎新的激进思想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而清代的一切文化压制手段,在他们眼中都会无限地放大和扭曲,这也是近代学术史研究常被政治派别挟裹的怪圈。[4]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5]
三、内在学术理路的变迁
学术史研究归根结底还是应从学术本身出发,学术史研究尽管无法摆脱外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但内在学术理路的变迁也不容忽视。清学正是建立在对明学空疏学问误国的反思惩戒之上,乾嘉学术博古通经的大儒无不深知明学之弊,考据学的兴起更像是一种对学术史的勘误和补救,而这种倾向甚至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由杨慎、归有光、唐顺之等先见之明的学者开始检讨。[6]
清代考据学兴起于清初,定型于乾嘉年间。清初三大家首先就是为了批评陆王心学而重新拾起考据学的工具。追本溯源的汉学始终是学者寻求经典元义最扎实的基本功,而宋学随着清初科举等官方层面对朱子学的大力提倡也逐渐开始复兴,这两者都是清代学术走向正常化的关键。清初大儒的复国情结彻底断绝后,迅速投入到对明学负面作用的批判中。学者的良知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明代的覆灭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政治经济的腐化,更标志着明代文化和学术的堕落。
翁方纲在《姚江学致良知论》曾分析道:
考订之学,则与致良知之学正相反对。以愚区区之见,则良知既不必自名其学,而考证诸家精心研讨,以汉儒为名乎?岂汉学果能悉究乎?则吾谓考证之学实自马端临、王应麟、黄震之徒而后浚发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子门人之绪得之。孟子固曰:夫道,一而已矣。然则学一而已矣。[7]
他从汉学和宋学两方面出发肯定考据学在治学方法上的重要性,这几乎是“学”在任何时期的唯“一”出路,王阳明的心学也不外如此。但纵观心学的发展理路,明学在后来的确不够重视考据学,缺乏对汉宋之学必要的尊重。同时,翁方纲在《自题校勘诸经图后》中对明学的批判和对考据学复兴的渴望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考订者,为义理也。其不涉义理者,亦有时入考订。要之以义理为主也。”
钱穆更是认为:“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者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己及乾隆,汉学之名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8]
明末清初的大儒不仅是清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明学的埋葬者。他们重拾了在有明一代不断被忽视的考据学,是汉宋真正的继承者和复兴者。《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云:“专门经训,授受源流,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人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这就是明末清初学者普遍的心声。明代重虚轻实的八股科举、道学讲习、心性禅悦等弊端,使明学不仅不能保留学术的知识遗产,也不能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潮流,在某些激进学者看来,明学甚至是亡国之音,尽管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负面的评价还是逐渐被后学所接受。
因此,乾嘉学术兴盛之后,清代学术界都服膺于考据学的博大精深,这是外在时代背景和内在学术理路双重作用的结果。乾嘉学术是清学的最高峰,也是考据学最辉煌的时代,尽管如此,乾嘉学者万万没有料到,这也是传统学术夕阳西下的最后盛景,这或许也是传统和现实两难抉择的历史规律。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二十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20-721.
[2]徐世昌.清儒学案(第3册)[M].北京:中国书店,1990.290-291.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4][清]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M].中华书局,1981.364.
[5]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A].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8.
[6]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A].吕叔湘.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233-234.
[7]徐世昌.清儒学案(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658.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责任编辑:王 崇】
K092
A
1673-7725(2016)07-0205-03
2016-05-05
邵鹏宇(1983-),男,江苏常州人,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