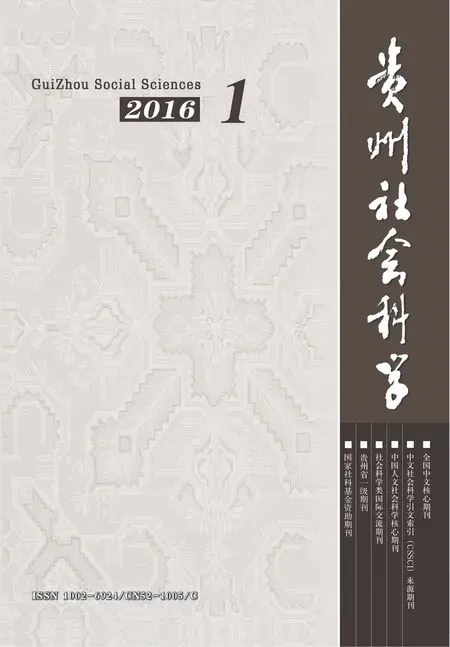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传承与生境耦合
罗成华 刘安全
(1.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2.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传承与生境耦合
罗成华1刘安全2
(1.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430073;2.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涪陵408100)
土家族摆手舞经历了自发传承、断代、解封以及复兴四个文化变迁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历史变迁是一个自然过程,无论是发生于武陵山区山地自然环境,还是经文化交流、制度影响以及人为建构而引起其文化内涵的转换,作为一项活态的民族文化,都必须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系统紧密结合,才能彰显出生命活力。
土家族摆手舞;文化传承;生境耦合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境。文化的生境决定了该项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进程。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在生计模式变迁、国家意志强力渗入以及非遗文化自我发展张力的合力推动之下,文化传承的生境发生改变,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成效也褒贬不一。本文从土家族摆手舞传承发展历史入手,探索其与所处生境的相互关系与元素取舍,以图从中发现彰显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生命力的路径。
一、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变迁
(一)改土归流前的土家族摆手舞自发传承
改土归流前的土家社会是一个以土司制度为根基的族缘社会,土司时期的土家族人过着以“游耕”为主的游动性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没有过多地接受汉文化的传播。“州属向来土俗,无论亲疏,即外来行客,一至其家,辄入室内,甚而坐近卧榻,男女交谈,毫无避忌。”[1]
摆手活动的传承活动也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禁与改,“每逢岁时令节,各官舍把下乡,俱令民间妇女歌舞侑觞。设府后,正月元宵尚有逐队来署者,呵止之,自称旧历如是”。[2]摆手舞是在一种原始自发的民俗传承,表达着原始的信仰,体现出“娱神”、“娱人”的单纯功能。
(二)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摆手舞断代
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后,以郡县制代替土司制,推行里甲制、绿营制,行大清例律,确立了汉族制度;同时,禁止、废除和改变与其不合的土家族文化事项,强行推行官方的价值观。作为祭祀土家族祖先神灵的传统习俗的摆手舞,因其“男女相聚而歌”,有违礼数,有伤风化,被冠以“恶俗”之名,严令禁止。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以“忠孝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文化,提倡移风易俗。要求筑宗祠、立家先、修墓碑以规范祭祖活动,而对于土家族所传承的摆手祭祀活动,视为“迷信神鬼”,就连土家族语言和地方方言也被当作“黑话”加以打压和禁止。
从改土归流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包括摆手舞在内的大部分土家族文化受到政府政策的压制,不得不停止和改变,汉族习俗渗入到土家族传统之中,使得土家族文化发生变迁,一些纯粹的传统土家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被遗弃而丧失。
(三)新中国初期的土家族摆手舞解封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土家族摆手舞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获得了解封的机会。1956年,湖北省来凤县卯洞民族文化馆干部陆训忠等在河东乡采风时,发现了“摆手堂”,并由此发掘出了“摆手舞”。1957年15日,民族学家潘光旦第二次在川(渝)鄂湘边界调研,观看了摆手舞,并和彭荣子等老人进行了座谈,最后评价说它是“一种历久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牢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3]1957年,土家族被国家认定为单一民族,其民族文化的发掘整理得到了党、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湖北省、湖南省和四川省都派专人进入土家族地区对其文化进行调查和整理。经过文艺工作者的调查整理,编纂了《土家族民间舞蹈间乐集成》等资料。湖北省来凤县舍米湖文艺宣传队彭昌松等7人,先后到恩施、武汉表演摆手舞,受到王任重、张体学等领导的接见。
(四)80年代以后土家族摆手舞复兴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后,鄂湘渝相继成立了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文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各项民族文化资料集、研究丛书陆续整理、发表。作为土家族标志性的文化项目摆手舞更是成为文艺展演、文化研究和文化推介的重头戏。1980年5月21日,湖北省来凤县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县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摆手舞表演;1983年12月1日,恩施自治州组成千人摆手舞队,举行盛况空前的摆手舞大游行。 2003年3月,国家文化部正式授予酉阳“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摆手舞)称号。
随着摆手舞的复兴,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的摆手舞在新时期迎来了发展高峰,并开始尝试创新。原生态摆手舞、舞台摆手舞、操化摆手舞、广场摆手舞、健身摆手舞等多种推广形式被呈现出来。1993年,重庆市酉阳县派代表队第一次演出了根据原生态摆手舞改编而成的《摆手祭》;土家族摆手舞由舍米湖原生态的4个动作发展为18个动作,并创作成功2套广场健身摆手舞。2008年正月,为庆祝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湖南(湘西)永顺双凤村自发组织了中断60余年的摆手舞祭祖活动,其间,开展了跳摆手舞、唱摆手歌和茅古斯表演。
二、传统土家族摆手舞与其生境的同构
摆手舞作为土家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与其自然与人文社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性从不同民族文化对生命现象的分类、评估、利用和改造中得到反应。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正是在于其关注什么样的自然生态系统,利用什么样的生命现象等方面呈现出千差万别。”[4]段超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成机制,这种机制至少包括了三个主要因素:地理环境、族源和人文生态,“地理环境是民族文化生长的基本条件;族源决定该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人文生态影响民族文化发展方向。”[5]
(一)自然环境对传统土家族摆手舞的形塑
生活在特殊自然地理空间的人群可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思维特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烙上地理特征的印记。土家族摆手舞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同样也受到自然环境的规约和影响。
第一,传统土家族摆手舞流传在酉水、沅水、澧水、乌江流域,这一区域地貌多样,以山地为主,山峦重叠,河流纵横。山区地理环境造成了土家族地区与外界的相对隔绝,影响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为土家族摆手舞长期独立传承提供了空间条件。
第二,山地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了决定了土家族传统渔猎、刀耕火种式农业生计方式的选择。摆手舞传承的大部分故事与动作内容也都源于山地农业生计方式,如“撒种”、“纺棉花”和“磨鹰展翅”等动作都是对日常劳作和生活的模拟。正如湖北省舍米湖摆手舞传承人彭昌义(已故)所言:“撒种、雄鹰展翅两个动作就好像我们在坡上种苞谷、撒豆子的样子。撒了种,怕雀子吃,当然要赶雀,雀子怕老鹰,我们就在土里插上笋壳叶的棍子。山上风多,笋壳叶被吹得飘来飘去的,好像老鹰飞来飞去的,就可以吓跑雀子。祖先们就跳出了雄鹰展翅的动作。”[6]
第三,传统土家族人多居住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地,“居高山者,寒多暑少,盛夏被不脱棉,晨夕必烘于炕,故收获较迟,一切蔬菜皆过时始食。”[7]气候气温条件对其民族文化发生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一年生计由于气候制约,开春晚,农历三月才陆续从事生产,农历十一月进入冬季,人们多选择闭门烤火。冬季长期的息作,为摆手舞的传承提供了时间保障。
第四,土家族地区处于湘鄂渝黔交界地区,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东邻南楚,西抵巴蜀,川湖肘腋,滇黔咽喉”,[8]是为“全国地理中心地带”、“古代中原与西南之间的通道”、“长江经过之区”。这个地区与汉族地区直接相交,决定了汉族文化与土家文化的交流,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汉族文化的遗存。同时,由于土家族地区也是西南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西南各少数民族也与土家族文化产生交集,带来文化交流与借鉴。
(二)土家族传统社会生态与摆手舞文化内涵建构
费孝通曾指出武陵山区的文化特征:“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9]自称为“毕兹卡”的土家族聚居在武陵山区,他们传承的民族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风格,是因为省际边区特殊的文化生态的作用和影响形成的。而传统摆手舞就是“土家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中不断演变、发展的一种习俗。”[10]
第一,摆手舞承载土家族祖先信仰文化。同治版《来凤县志》的转引“昔覃氏祖于东门关伐一异木,随流至那车,复生根而活,四时开百种花。覃氏子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复落,尤为异也”,有了一种关于土家族摆手的起源观点,这其中反映了从神迹而来的祖神信仰。被土家族人奉祖先的神灵包括八部大王,“大二三神”和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等。八部大王是土家族奉信的“茅人”祖先,在湘西永顺双凤村传习“茅古斯”中的剧情反映了土家原始先人生活真场景,并能指出祖先茅人栖息地。“大二三神”是土家族传说中的三位祖先。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红脸叫真珠大神,黑脸叫连珠二神,白脸叫显珠三神。而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则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家族人物。土家族每到年节、三月三和牛王节等岁时节庆,都会有祭祖行为。而每有群体性祭祀活动,都会跳摆手舞,以祭其祖。
第二,摆手舞继承了多元文化遗存。从土家族摆手舞的舞姿特色其“同手同脚齐出”与古巴人的巴渝舞“龙行虎步”相比较具有极大相似。大摆手舞的队列“披甲”、“拉弓射箭”也和巴渝舞曲中的“矛渝”、“弩渝”雷同。摆手舞的“男女相携,蹁跹进退”和“赴节而舞”暗合了越濮文化特征。而楚文化中的凤鸟图腾和火崇拜也在摆手活动中大行其道,摆手时队列中央必须点燃大火,众人绕火而舞,而在大摆手仪式中出场须有龙凤大旗。
第三,摆手舞传承传统生活知识。大小摆手舞传承了不同的内容,大摆手表演战功,模仿军队的战阵和战舞;小摆手则是祝神祈福,娱神育人。从舞蹈动作来看,舞以锣鼓为引,模拟日常生活,再现民族迁徙、狩猎征战和农桑耕织。摆手歌则是直接的言传身教,如:直/嘎/多/里/嘎/多(要吃饭就要挖土);斯/嘎/多/子/龙/多(要吃肉就要喂肥猪);斯巴/大/多/棉花/扎(要穿衣服就种棉花);嘎/达/拉/它纳/打它/多(吃穿哪一样都不差)。
三、现代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生境变迁及其适应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土家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系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摆手舞也随之嬗变。可以说“经过历史洗礼的摆手舞,已经从简单的宗教仪式成为当今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仪式’”。[11]
(一)现代土家族摆手舞对自然生境的偏离
虽然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但是人的自身的社会性也决定了文化系统在保持与自然生态相契合的同时,必须会超出自然系统,使得民族文化与自然生境的偏离无法避免。
时至当代,至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武陵山地区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都不同程度的减少了。留给当代人的栖居地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从而对当代土家族乡村(村户)建设产生影响,人们不再把逐田或逐林而居作为修建住宅的首要原则,而是选择临路、临街、交通方便作为重要选址依据。另一方面,依附于自然环境的传统生计也必然发生改变。比如狩猎,我们不难从土家族茅古斯剧情中得知野猪是当时主要的猎物,而现在野猪仅生存于偏僻的乡野,且数量极为稀少。与之相应,狩猎这种传统生计模式在当代已基本绝迹。摆手舞活动中传承的原始农业和狩猎等传统生计知识,在现代学科知识体系面前也显得格外陈旧和不堪实用。
(二)现代土家族摆手舞文化内涵的变迁
土家族摆手舞从历史走来,它所蕴含的文化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取舍的过程。现代土家族摆手舞通过村落自发传承、学校教育传承以及社会媒体宣传传承等方式,让摆手舞在当代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就其文化内涵本身而言,现代摆手舞发生了较大的变迁。
第一,从祭祀仪式到民间艺术。现代土家族摆手舞已经淡化了祖先祭祀功能,从1950年代开始,摆手舞一直就是作为土家族民族舞蹈项目加以收集、整理,出于某种需要,传统摆手舞活动的前奏部分,如净场、请神等环节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而见于各处的宣传交流资料都是以“民间传统舞蹈”来说明。而摆手舞的“操化”和“广场舞化”更加坐实了这一认知。
第二,从民族信仰到娱乐健身。传统摆手舞是土家族祭祀祖神活动的主要环节,它的传承来源于祖神的信仰。无论远古的始祖神,还是近古的有名姓的祖先神,都可是以通过摆手活动的固定的神圣场所(摆手堂,大二三神庙)、参与热情(村落共同体全员参与)和对同姓祖先的信奉(同姓或依附的兄弟)来获得族群的认同感。现代摆手活动作为民间传承的艺术,可以在多个公共场所展演,传承者更愿意注意肢体动作的准确性和摆手舞的健身效果,而对于习跳者的身份并无关注。
四、余论:现代性建构生境下的现代摆手舞发展走向
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变迁是一个自然过程,无论从其发生于武陵山区山地自然环境,还是经文化交流、制度影响以及人为建构而引起其文化内涵的转换,时至当代,它仍然是生存于土家族民众中的优秀民族文化。随着时代进步,特别是科技发展,使得人类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逐步减弱,人们传承的文化也相应地受人类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更加明显。当下,文化生境的变迁已严重地影响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仅仅凭借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张力去实现与其当代传承生境的有机耦合,确实是力有不殆。
正是因为土家族摆手舞在传承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与社会生境的融合,当代的社会制度、生计方式、生活观念以及人们所受的现代知识教育,无一不对传统摆手舞的传统意义产生消解作用,越来越明显偏离自然生态系统。我们一方面要快速修复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合理地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来重构和创新民族文化与生境耦合系统。在国家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政策的规制、市场经济因素的推动以及当代土家族人所接受的现代知识体系影响等方面综合作用下,土家族摆手舞在当代完成了它的现代性建构过程,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12]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表象来看,理所当然的是做好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在当代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过多的外部因素干预和程式化的传承,得到民族文化的“形”,而丢失了民族文化的“神”。事实上,我们不仅要靠社会力量建构民族文化的当代形态,而且要保护和维护好民族文化生存的根基,即自然生境,从而在当代民族文化传承中保持其浓厚的生活态,彰显其生命活力。
[1]毛竣德.鹤峰州志.风俗·附文告[Z].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2001:56-57.
[2]顾彩.容美纪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306.
[3]张祖道.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M].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218.
[4]罗康隆.论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运行[J].青海民族研究,2010(2):64-71.
[5]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
[6]彭振坤.来凤县舍米湖文化资源的调查报告[J].土家族研究,2004(4):8-15.
[7]李勖.来凤县志·风俗志(同治版):卷二十八[Z].来凤县史志办在线资料: http://www.laifeng.gov.cn/szb/ .
[8]林翼池.来凤县志(乾隆版)[Z].来凤县史志办在线资料:http://www.laifen.gov.cn/szb/:63.
[9]费孝通.武陵行(上)[J].瞭望,1992(3):8-10.
[10]熊晓辉.土家族摆手舞源流新考[J].怀化学院学报,2006(3):7-9.
[11]覃琛.武陵山区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变迁与争论[J].民族艺术研究,2011(2):11-16.
[12]赵翔宇.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重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4(4):62-65.
[责任编辑:明秀丽]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12YJAZH18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武陵山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2014YBSH042)。
罗成华,土家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刘安全,土家族,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历史人类学。
[C957]
A
1002-6924(2016)01-088-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