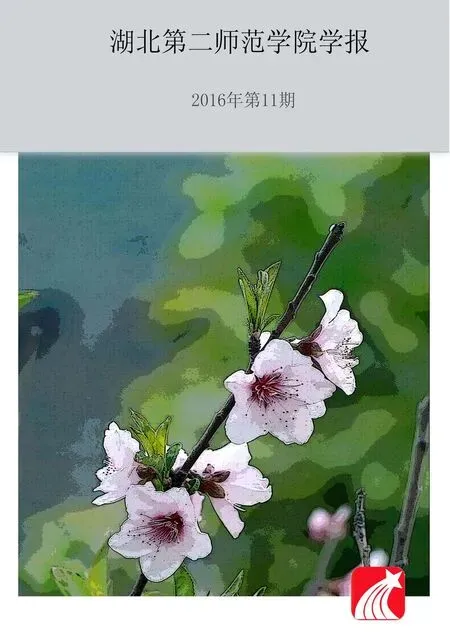我国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生成要素探究
潘 超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音乐系,福州 350108)
我国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生成要素探究
潘 超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音乐系,福州 350108)
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体制以及美声唱法的引入,促使我国歌唱艺术发展进入了转型期。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我国传统歌唱中可贵的“即兴”创作却在新的语境中逐渐失去其地位,影响着传统歌唱艺术“文化身份”的建构。其中,原有生成语境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因而,反观我国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的生产要素可助于我们探究成因、启示未来。
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背景;要素
1927年冬,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专,它的开始不仅“标志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也意味着我国歌唱人才的培养体制的巨大转变,走上了一条借鉴“西欧”专业化、标准化、批量化教育模式的新道路。西式教育理念引入,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我国传统歌唱艺术中可贵的“即兴”演唱却在新的语境中逐渐失去其地位,淹没于西欧美声艺术教育体制中。
这种模式化、标准化的歌唱体制倾向于塑造歌者的共性特征,如“讲究整体共鸣,充分发挥人声的共鸣腔体作用,因而,它的音量宏大,穿透力强。注重三个声区的统一,音域广宽,声音幅度大,强调声音的连贯、流畅、柔美、重视音色的圆润、明亮、悦耳、发音纯净。……讲究音乐的表现及作品的风格。声音的管状及竖向运行,有垂直感,并采用混合共鸣。”[2]等,从而影响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建构与发展。然而,越是标准化、严格化的体制土壤,越是不适用于我国本土歌唱艺术的文化特征,无法建构出独具特色的“身份标识”。
正所谓“框格在曲,色泽在唱”,即兴性是我国传统歌唱艺术的灵魂。即兴注重的是歌者自身对音乐的体验感知,充分发挥的是“人”的潜创造力,这也是戏曲、民歌、说唱等我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核心及动力所在。在美声歌唱体系及教育体制的冲击下,民族声乐艺术虽源自于传统,却也走上了“千人一面”的标准化道路。然而,音乐艺术发展之根本是创造。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回望传统,审视歌唱艺术珍贵的即兴演唱特征以及其生成语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即兴演唱生成的文化要素、语境进行探究,以期改变当下模式化的声乐教育语境。
一、知识经验:即兴之基础
即兴性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主要特征,作为“庶民百姓和文人士大夫直抒胸臆的一种艺术形式。他们往往是由感而发,引吭高歌,即席吟唱,即兴鼓瑟弹琴。在职业、半职业的社班里,由于没有专职的词作家、作曲家,所以,演员经常兼词作家、唱腔设计和作曲家于一身,择调创腔,即兴发挥,兴到情随,依字行腔,以腔传情。”[3]然而, 这种即兴歌唱行为并非是单一的无意识的生理促动,而是建立在歌唱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的,其中的含义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出一辙。
原本内化于歌唱者身体的是一种隐性化的知识体系。人们通过即兴发挥,将记忆中的曲调或是故事梗概进行即兴创编,形成一首首新的歌曲作品。因而,虽然即兴演唱是一次性的,求新存异的,但又无法离开人们原有的知识经验,以所积累的曲调为框格进行即兴改编。由此可见,“即兴创作是在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上创作,是在继承原来音乐基础上的创作,所以创作者对于整个乐曲的风格、内部各个部分的关系及发展的把握,基本上仍属于概括化的抽象思维的结果。对于各种潜在可能性的筛选与决策,虽然是即时选择,但依然有其理性思维因素的存在。”[4]
这一特征对于当下民族声乐艺术即兴演唱仍能可以带来一定的启示。即兴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不应陷入一种“随意”论的错误观念,需要歌者具有大量的曲目积累、深厚的文化知识。这其中我国各个地域的民歌、戏曲、说唱作为母语文化是即兴创作的知识基础,也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创作演唱的基础。除了要掌握上述音乐作品之外,也应该博识广闻,对西方美声艺术、以及与人们最为亲近的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等音乐风格也应了解一二。
首先,民族声乐创作者需要熟读它们,了解音乐演唱的语言要素。而演唱者更要有广博的积累,在大量曲目学习演唱的过程中,逐渐将这些歌唱知识积累下来,内化为自身即兴创作的音乐血脉。其次,在学习多样化的音乐知识过程中,通过对比方可体会差异、体味不同的文化韵味,也将助于冲破原本一元的、唯西方的“中心主义”之误区。当然,这些都需要歌者具备勤奋刻苦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
二、口传心授:即兴之路径
口传心授是我国传统歌唱艺术的主要传承方式,同时也为即兴演唱生成提供了重要路径。“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实际传承过程中,有直接使用口、手、耳的口头传承;也有使用乐谱的书面传承。过去无文字的时代里,历史和文化知识都只有依靠包括音乐在内的民俗事象进行传授,口头传承自然是当时最便利的方法。……并形成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5]口传心授虽然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但是在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它所突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的传授特征,凡是与演唱相关的音乐知识的获取都要靠师傅的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心领神会而获得,这是一种活性的、心与心沟通的传承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位老师都有自己对演唱的看法以及经验总结,没有形成模式化、统一化、标准化的演唱法则。同时,它注重的是歌唱者个人的感知以及创造性发挥。虽然当下的教育体制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但是教师大都是学院派出身,他们更像是一套既定标准体系的传达机器,而不是个体创造性的认知,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模仿占据主导,越是靠近这个统一标准的演唱才是优秀的。
此外,口传心授的教育过程也为学习者提供了即兴创作的条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框格在曲,色泽在唱”。前者所说的是老师是一个引路者、指导者,他所提供的是一种生存技能、而不是死的知识体系。因而,教师将自己的经验教授给徒弟,最终还需要徒弟自己去领悟、去发现新的规律,这便为即兴性演唱提供了自由空间。而在具体的歌曲实践中,歌者们坚守着框格却不拘泥于框格,无论是演唱的规律,乐曲的意味、动作的程式等都需要自我品味。
因而,传统歌唱艺术的传承过程中,口传心授的形式为即兴演唱提供了生成条件以及发展的空间。久而久之,这种演唱习惯便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定势。从中我们也看到,口传心授为学习者和教授者都提供了自我创造的空间,没有被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定死死地框住。而在现代教育体制中,那些自认为继承了美声精髓的歌唱者们,歌唱的音色是标准的是统一的,演唱的方式是既定的,乐曲的风格以及细节的处理也是不能改变的。在这样的新的歌唱语境下,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也逐渐走向标准化的道路。那些甜而腻、脆而甜的音色观、为达到这一演唱审美而形成的标准化训练体系、方法,让即兴性、多样化没有存在的空间。而我们看到最多的则是一个个风格多样的作品,作曲家赋予的多样化成为民族声乐艺术多样化的动因,而演唱者能够发挥的余地少之又少,更无法谈及创造性、即兴性。
三、道法自然:即兴之思想
即兴性创作是在我国传统哲学“尚自然”的思维渗透下孕育而生的。我国千百年的思想精髓为其发展、生长指明了方向。春秋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此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发展规律,他认为道是无形的,其真谛是在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状态中发生意义。因而,我国先民们在歌唱过程中,也一直遵循着自然的生成法规,形成了重视内在情绪流露、展现其真实情感为目的的演唱艺术。而西方声乐艺术则是在“神权”为主的“灭人欲”思想下生成的。人们没有自然地、发自内心地歌唱自由,歌唱只是营造神圣环境,人与神进行沟通的媒介。它需要一套既定的、标准化的歌唱标准,以能够达到合唱式的声音效果,从而表达空洞的神明感。当然,标准化的歌唱也便于统一教化基督教徒。而在我国,又是另一番歌唱景象。人们自身的演唱状态、歌唱情绪都是可以自我发挥的,是时刻变化着的,演唱的内容、演唱的方式及情感也会随之不断地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没有受限于歌唱技术,也没有禁锢于“作曲家”设定的作品标准:即遵循以往的歌唱经验,又随着自己的感受时刻呈现出新鲜的意味。这便是“自然之道时刻都在变化之中”[6]的发展真谛。
当下的民族声乐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继承西方的美声体系后,打破了“自然之道”的哲学理念。作曲者与演唱者职能的分离,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之间形成一对难以调和、统一的矛盾体。原本可以自由歌唱的农耕场地变为了今天依靠演唱违约作品的音乐厅。演唱者如何拿捏这其中的“创造性”成为问题的关键。因而,现行的教育机制从开始就为学生灌输的是尊重原作、诠释原作、还原作者意图的歌唱思维。不允许他们在歌曲的旋律、节奏以及唱词上进行即兴改编,在情感处理上也只是尽量回归原作,很少融入歌者自己的想法,进行二度即兴创造。
这种固化的歌唱思维也影响了现代教育体制中传承的民歌作品、戏曲作品演唱,这对于学校体制中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来讲无疑是一种传承危机。被人们熟知的花儿王“朱仲禄”、民歌王“石占民”的风格都是独有的,歌唱“味儿”足、情感真挚、自由开放,每次演唱都有心的体验与创造。他们的歌唱并不需要被提炼成一个技巧规则被他人所遵守。几乎所有民歌、戏曲、说唱的传承人都能如此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当这些作品进入到所谓的“学院派”教育语境中时,歌唱者们将这些作品进行了再加工,每一句每一字都处理得天衣无缝、完美至极,但这时,源于自然、传承自然之法的传统歌唱艺术,也便失去了本真的生命力,成为一层不变的歌唱标本。因而,在西洋教育体制掌控下的歌唱传统,如何回归“自然为本”的演唱本能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农耕文化:即兴之土壤
传统歌唱艺术是生长在农业社会背景下的,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局限于劳动场所及生活场所等空间。人们没有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没有ktv、广场舞等现代娱乐方式,没有便利的交通可以享受旅游带来的轻松快乐。稍显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促发劳动人民产生了通过歌唱方式抒发内心情绪的动机。这种原始的促动,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都是即兴而发。如在田地里,人们齐声歌唱、相互配合完成劳动任务,形成了劳动号子歌唱形式。在山野间的男男女女,通过空气媒介,以声波的形式,跨越大山的障碍起到沟通人们情感、交流信息的作用,从而产生了山歌、情歌等形式。而在城镇的巷子深处,一个个悦耳的叫卖声,传递的是今日杂货贩卖的主要名目,这便形成了货郎等说唱音乐形式。
我国农耕社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连动性关系。歌唱这门艺术也无时无刻不展现人际关系。如以表达劳动、婚姻、生活等为内容,为即兴表达提供了生成土壤,重视变量多于定量。而西方神权社会背景中产生的美声作品并不是表达人的情感,而是营造一种神圣的音乐氛围。人在这过程中只是传达信息的没有生命的载体。因此,美声歌唱十分强调统一性、和谐性,不倡导个人的个性发挥,采用统一的音色,用“近器声”的发声方法,达到空灵、浑厚的声效。可见,中西演唱艺术自开始生成土壤就不同,也注定了走上一个注重统一、标准化,一个注重个性、变异性的发展道路。
五、结语
任何音乐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特有的文化语境,歌唱艺术亦是如此。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机制传入后,我国声乐人才培养走向了普适化的道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水土不服等“后遗症”。其中,文化语境的改变、生成动因的退化,都慢慢吞噬着我国传统歌唱艺术重最为宝贵的即兴歌唱传统。鉴于此,有必要反观传统,探究即兴演唱生成的要素,以古鉴今,为我国民族声乐未来发展之路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1]孙继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15.
[2]孟晓师.民族声乐在其发展中的审美变迁[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1997,(4).
[3]王耀华著.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523.
[4]郭小利.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95.
[5]刘富琳.口传心授释义[J].中国音乐,1997,(4).
[6]申小龙.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59.
责任编辑:胡栩鸿
A Study on the Factors Leading to Impromptu Singing— A Chinese Traditional Singing Art
PAN Chao
(Music Department of Zhicheng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With the arrival of modern times and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el canto, the singing art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influenced to enter a transition period. In the meeting and blending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precious impromptu sing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nging art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position in the new context, which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singing art. And the change of original context is the main cause. Therefore, a study on the factors that generates traditional Chinese singing art can help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inspires the future.
traditional singing art; impromptu singing; background; elements
2016-09-15
潘 超(1986-),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声乐。
J617.13
A
1674-344X(2016)11-004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