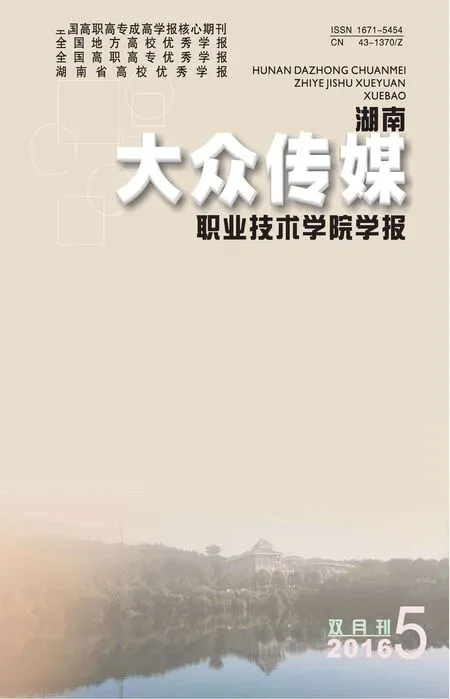邵氏黄梅调电影中的东方美学元素
李小雨
邵氏黄梅调电影中的东方美学元素
李小雨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类型。邵氏黄梅调电影是戏曲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邵氏黄梅调电影蕴含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有东方彩色的美学元素,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征服了海内外观众,也奠定了这个电影类型在影史上的地位。
黄梅调电影;邵氏电影公司;东方美学
1955年,导演石挥拍摄了我国第一部黄梅调电影《天仙配》。次年本片在香港上映,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一些香港电影公司立即跟风拍摄黄梅调电影,以期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其中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3年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可谓此类电影的巅峰之作,不仅创下了在台湾连映六个月的奇迹,更在金马奖获得六项大奖,证明了黄梅调电影在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据统计,自1958年的《貂蝉》到 1977 年的《金玉良缘红楼梦》,30多部作品占去港台黄梅调电影所有产量的3/5,不但成为黄梅调类电影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定义了这个类型的电影在影史上的意义。一言以蔽之,邵氏黄梅调的发展历程几可谓此类型电影发展历程的大概。[1]邵氏电影公司作为黄梅调类型电影美学的集大成者,以一系列黄梅调电影形成此类电影的类型,也奠定了黄梅调电影这一电影新类型的艺术特征,并且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因此,选择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来进行分析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一、民间传奇式的故事主题
电影是一门探索的艺术,无论故事主题、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方面,总是尝试带给观众以新鲜感。人们评价一部电影是新电影,指的是电影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是观众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而中国戏曲多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在后人的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完善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同一故事题材可以被改编成京剧、豫剧、评剧或是其他剧种,但讲述的故事内容是差不多的。观众看戏曲,不是为了追求全新的故事,而是在唱、念、做、打的戏曲表演形式中寻求与内心期望的契合。回到邵氏黄梅调电影中,细数这三十几部电影,可以发现更多的故事主题集中体现在民间传奇和爱情故事中。
掀起邵氏黄梅调电影滥觞的《貂蝉》取材于古代四大美人的传说,讲的是东汉末年太师王允利用貂蝉的美色,挑拨吕布斩杀奸贼董卓的故事。《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花木兰》等,更是取材于民间久负盛名的故事,观众对这些故事耳熟能详。最特别的是,邵氏黄梅调电影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直接由我国传统戏曲改编而成,比如《鱼美人》就改编自越剧《追鱼》,《玉堂春》改编自评剧《全本玉堂春》,《魂断奈何天》改编自潮剧《告亲夫》,《双凤奇缘》改编自黄梅戏《女驸马》,《凤还巢》改编自京剧《凤还巢》,还有1977 年由李翰祥导演的邵氏最后一部黄梅调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更是改编自我国四大名著的《红楼梦》。[2]
以观众熟悉的民间故事/戏曲为蓝本重新改编成电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源于邵氏电影公司的大制片厂制度,拍电影讲究流水线作业,追求多快好省。邵氏希望通过电影的奇观手段,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刺激和情感体验,对于故事层面的掌控自然弱了一些。然而这种不自觉的方式反而为探索黄梅调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对于民间故事的推广也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打上了民族的记忆烙印。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历史孕育了无数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唐三千,宋八百”本就是中国戏曲的一大优点。而通过中国传统戏曲/传说故事的引入,能够激发观众探索背后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满足观众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怀念和追思。邵氏黄梅调电影除了本埠和台湾市场外,主要的市场是东南亚诸国,也就是说是为广大的海外华人提供一个理想中的传统中国印记,以满足他们对于故土、故国的思念。早期香港粤语电影也正是由于其蕴含的中国元素而得到东南亚观众的认可。黄梅调电影采用国语发音,辅以大量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同样暗合海外华人观众的心理。邵氏公司通过一部部黄梅调电影不断制造票房奇迹,也让观众在电影中一遍遍圆满着自己的中华情思。
二、电影语言的重点在人物本身
传统戏曲的重点放在名伶本身,通过他们的唱念做打而自成一派艺术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也就是说,看戏其实看的是戏曲演员本身,观众的目光一刻也离不开演员本身。然而,看电影是看电影语言的综合呈现,演员只负责动作和对白,大量带有情绪色彩的空镜头也能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因此,电影里面才会出现大量渲染情绪的空镜头。邵氏黄梅调电影“在叙事手法上借鉴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模式”,沿袭了“一人一事一线”的叙事模式;[3]演员在表演上则遵循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更多地将电影镜头放在主要演员身上,通过他们的肢体及语言来推进故事。
在邵氏黄梅调电影的代表作《梁山伯和祝英台》中,前十几分钟电影镜头一直对准祝英台,记录她如何女扮男装说服父母让她去读书。随着梁祝二人相遇,电影镜头一直记录着二人的相遇相知、结拜求学、三载同窗和十八里相送等场景。最后摄像机一边记录梁山伯求爱不成、因病而逝的凄凉画面,一边记录祝英台含恨出嫁、撞死在梁山伯墓前,电影直到二人化蝶飞去结束。可以说,除了电影字幕及少量用来镜头切换的空镜头,电影镜头一直聚集在二位主人公身上。传统戏曲其实就是一个长镜头,从头到尾记录下演员的表演形式而已。黄梅调电影借助电影这个综合性的工具,将传统戏曲表演的“一桌二椅”扩展为广阔的室外空间,丰富了戏曲的表演场地。在电影中,演员该骑马就骑马,该划船就划船,不再像戏曲舞台上仅仅拿个鞭子象征性地示范一下动作。电影演员在“银幕的影像动作既非一般故事片的动作常态性,也非歌舞片的动作创造性,而是一种由高度规范化的‘唱做念打'动作组成的‘程式性'”;[4]同时通过镜头切换,带给观众不同的审美体验,不同于传统戏院里面固定座位上观众的观看体验。然而黄梅调电影始终摆脱不掉戏曲舞台限制的就是演员本身,此类电影的叙事和情感都需要演员自己去表现,一旦镜头离开了演员,观众会产生观看上的断裂感和情感上的不连贯。
故而有学者认为,与其说观众追求“看电影去”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在追求“看戏曲去”的心理情境。黄梅调电影演员表演时常面对观众,很少有侧对或背对观众的场景,这也说明在演员不自觉地带有为台下观众表演的意识。中国戏曲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并不独立存在,它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亡——景在人身上。中国戏曲要求观众将目光放在人身上,采取反观的审美方式。[5]
三、电影视听语言的综合性体现
黄梅调电影是黄梅戏和电影相结合的产物,因其电影中有大量好听易唱的黄梅曲调唱段而得名。之所以不叫黄梅戏电影,是因为黄梅调不仅移用了黄梅戏的基本曲调,还将中国其他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以及民歌的曲调,只要是大众乐意接受的全部都拿来“为我所用”。但更为重要的是,邵氏黄梅调电影中的“黄梅调”,已经不是原来黄梅戏中的“黄梅调”,而是经过了改造的“黄梅调”——一种现代乐人的本地化、通俗化、简易化的处理,变得易学易唱易传。[6]因此这里的戏曲唱段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戏曲,而是带有民间色彩的更富有亲和的咏唱形式,再经过现代音乐理念的处理,是为了更符合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且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演员不是真正的戏曲演员,而是电影演员,这也正说明演唱部分不需要很深的艺术功底,其好听易唱的曲调不仅电影演员可以胜任演唱,重要的是可以快速为观众所熟知,因此在电影院才会出现观众跟着电影场景大合唱的画面。
1963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引起观众巨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观众习惯欣赏中国戏曲,尤其是广东粤剧。但这一时期的粤语片由于黑白摄影和录音技术的不完善,制作粗制滥造,很难满足观众日益苛刻的审美需求。而《梁山伯与祝英台》采用彩色摄影,丰富了电影画面,由外国公司进行电影录音,提高了音乐的质量。“它的生产、发行、接受环节都融入了现代化元素,并与观众的现代生活关联”,可以说它是一部“商业体制下类型成熟的产物”。[7]这部电影将传统黄梅戏中的道白及唱腔由较难懂的安庆方言改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辅之由歌星以通俗的发声方法代演唱的插曲,再加上凌波、林黛俊美的扮相,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将黄梅调电影推上艺术的巅峰。
有学者认为,“戏曲电影的拍摄要在诗画原则上与戏曲统一,并且要创造意象。”[8]邵氏黄梅调电影采取了“将戏就影”的创作思路,也就决定了它写意风格的场景。由于摄像机代替了观众的视角,凭借其自由灵活的特点,黄梅调电影摆脱了戏曲舞台的限制,可以走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拍摄外景,营造一种写实的风格。通过搭建金碧辉煌的内景和风光无限的实地取景,电影的视觉画面得以丰富,抓住了观众的吸引力。“戏人电影”最先体现出“平远”布局的空间意识,观看片中的布景,颇有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活动的立体空间。[9]但这个特定空间,无论是荒郊野外,还是贵胄庭台,或是简陋茅屋,都不以焦点透射作为空间构造原则,反而制造空茫而简洁的远景,使空间失去深度感,且多以摇镜头追求向左右延伸的平阔的空间感。
另外,邵氏黄梅调电影在镜头选择上多采用定镜拍摄和长镜头,很少有仰拍和俯拍,多是平视角度的中景和近景。平视角度的定镜拍摄明显就是为观众服务的,在拍摄过程即假定了观众的观看视角。长镜头可以完整记录一个表演片段,不破坏人物动作和情绪的完整性,更是为了契合观众的看戏心理。同时演员可以不受场地限制自由出入各种背景画面,虽然在动作上依旧带有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虚拟化特点,但相较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无疑有了更大进步。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的黄梅调电影热潮减退,伴随着国语武侠片和兴起和粤语片的复兴,邵氏黄梅调电影在1977拍摄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中走到尽头。回顾邵氏二十几年拍摄的三十几部黄梅调电影,呈现出中国戏曲电影的黄金时期。正如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戏曲片作为电影中唯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弘扬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电影类型,其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需要人们给与更多的关注。”[3]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陈炜智.丝竹中国,古典印象——邵氏黄梅调电影初探[M].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44.
[2]任志芳.20世纪中后期邵氏戏曲电影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2.
[3] 丁璇,周爱军.求同存异 繁荣共进——“中国戏剧与中国电影互动发展”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1(1):56-60.
[4]蓝凡.氍毹影像:戏曲片论[J].戏剧艺术,2011(3):78-90.
[5] 蓝凡.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兼论戏曲电影的类型基础[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6(2):94-105.
[6] 蓝凡.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7-42.
[7] 龚艳.两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港沪戏曲电影往事[J].电影艺术,2012(6):140-144.
[8] 李菁.戏曲电影:在戏剧、电影和政治的交界处——戏曲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戏曲艺术,2012(3):24-26.
[9] 吴平平.戏曲电影艺术论[D].南京:东南大学,2006.
The Oriental Aesthetic Elements in Huangmei's films
LI Xiao-yu
(College of Drama and Film-TV,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Shanxi 041000)
Drama movie is a unique typ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nema in China,Shaw the huangmei opera film is the drama of a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nema.Shaw studios as a type of the huangmei opera film master of aesthetics directly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is type in the history.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shaw the huangmei opera film unique Oriental aesthetic elements, and reduction of huangmei opera films for the audience thought and art.
huangmei opera films;Shaw studios;Oriental aesthetics
A
2016-09-09
李小雨(1990-),男,河南邓州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批评、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