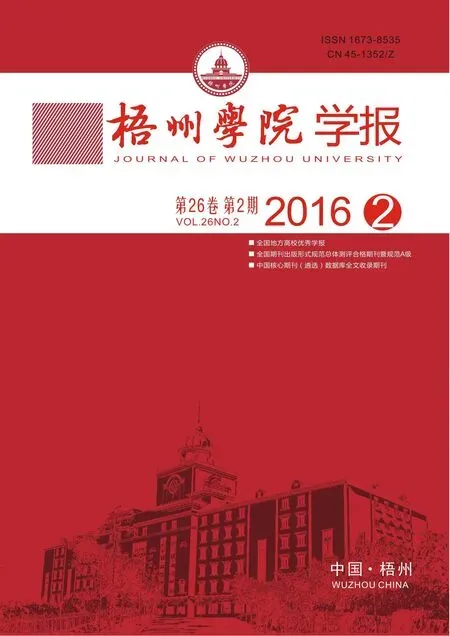淡极始知花更艳: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和合之美”
董劭敏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淡极始知花更艳: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和合之美”
董劭敏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0)
[摘要]“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世间万物以处理相互间矛盾的方式来昭示存在本体的基本途径与方略,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审美中所呈现出的美学追求。《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多面性的文学形象,正如她“自写身份”的诗中所题,“淡极始知花更艳”,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她性格中有情与无情的交融,以及处理自我欲望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间关系所带来的多重性,这种浓淡之间迥异却相谐的“和合之美”,是薛宝钗这个形象所具有的独特美感,也是中国士人阶层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的体现。故以红楼梦脂汇本为基准,探究评析薛宝钗身上的“和合之美”。
[关键词]薛宝钗;和合;外儒内道;审美风格
薛宝钗是《红楼梦》(1)中“作者用功最深,读者也最难理解”[1]的人物形象,对其研究争议颇多。文本阐释空白造成了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多义性评价[2],从《20世纪薛宝钗研究综述》《近十年薛宝钗研究述评》两篇历时性研究综述来看,学界在面对薛宝钗形象的多面性时,偏重于用世俗尺度或单一审美原则进行评判,集中于“四德俱全的封建淑女形象”[3]“节情以中的理性精神”[4]等论题的重复研究,更多地关注其悖论的一面,而忽视其外部关系与内部机理的整一和谐,以及从“不同话语的对话”[5]切入分析。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观念入手,分析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和合之美”。
一、何谓“和合”?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红楼梦》薛宝钗人物形象身上,不仅凝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思想文化要素,更传达出文学艺术上丰富立体的美学魅力。具体来讲,“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世间万物以处理相互间矛盾的方式来昭示存在本体的基本途径与方略,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审美中所呈现出的美学追求。
(一)“和合”:一种处置矛盾的方式
“和合”思想融汇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其词首见于《国语》“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和合之道”能调和五教,使百姓安身。它的基础是矛盾,“和实生物,同则不继。”[6]470《红楼梦》中绘写了种种矛盾,薛宝钗面对矛盾的处世态度,正是“和合”文化的一种表达。
一般谈及“和合”文化往往偏重于儒家的“中庸”“中和”[7]。儒家的“和合”精神从审美的维度上为人的行为创造出一种以“融通”为核心的理想范式[8]。亦即“执两用中”“应时处顺”。这成为人们寻求理想的人生行为方式,以及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调适的重要法则。
相形之下,道家的“和合”思想容易为人所忽略,与儒家“执两用中”的“合适”之“和合”不同,道家的“和合”之道,不在追求内外的调和一致,而是企望在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兼容的关系,“行莫若就,心莫若和。”[9]40《德充符》重点论述了“内外兼融”的境界:“德者,成和之修也”[9]53,“充者,足于内也;符者,内外合也”[10],在“和合”的境界里,内不以好恶伤身,外则于物合宜。具体来说,道家的“和合”思想可以细化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和气: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道家认为,和气产生于矛盾双方,而二者共存生物的基础,在于矛盾双方不以追求绝对的一致为目的,以在两极之间保持平衡或互补的状态处理问题。
庄子的处世观便包含着“向上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与“向下以安命无为、顺世从俗”两个方面,外在的无情顺势,并不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俗处”体道之人在精神上逍遥于虚阔之境,在处世中行为上顺世随俗,以此来保全生命和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外化而内不化”,而这种态度上的两重性便是“和气”辨证思想的体现。
其次,和道:和光同尘,是谓玄同——系统运作的整体思想。“万物与我为一”,宇宙是以道为整体的自然系统,从根本上是合一的,要从整体上看问题。老子所谓的“和光同尘”,是指以无所偏的心境待物,践行“宇宙合一”的整体系统观。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9]45,道家主张以“整体合一”的眼光看待事物,善与恶、有用与无用并非孤兀地体现,而应将其置于整体的视角之下观照。
作为一种面对矛盾的处理方式,与对抗或逃避不同,“和合”的结果是共存而生,可以颐年。整一于环境,便能避免中道而夭。在《人间世》中,庄子通过匠石之齐的故事,论述“无用之用”的道理。世间的嘉木良材,因其有美材之质,则剥则辱,终至“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以树喻人,才华的昭彰如果不能站在“整体合一”的视角下,融合于环境,非但不能带来得寿永年,反是招致打击而半途夭折,有时唯有“无所可用”,方能得“若是之寿”。可以看出,道家以“和道”运作的整体思想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二)“和合”而兼美:《红楼梦》的美学趋向
《红楼梦》的美学风格,可以体现在曹雪芹对薛宝钗、林黛玉的“兼爱”上。他并不“贱肥贵瘦”,而是塑造表字“兼美”的秦可卿这一人物形象,“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和合”薛宝钗、林黛玉二者之美。光绪年间话石主人亦指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宝玉兼爱”,提出兼具薛宝钗、林黛玉之美是贾宝玉的理想,他爱林黛玉风流婉转,也心驰薛宝钗“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人物的审美理想,间接反映着作者的美学倾向。
这种“兼美”所表现出的作者的审美理想,不仅对于表现《红楼梦》主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以此为基础,我们深入研究《红楼梦》的文本,可以发现薛宝钗的人物形象也具有这种美学魅力。
二、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和合之美”
(一)外在儒家“中和之美”:礼之用,和为贵
薛宝钗之“和”,外在体现在她为人处世和行事上,一如贾母所喜的“稳重和平”,她在其行为上常常是世故圆融、和乎人心的,突出显示了儒家的“中和之美”。
薛宝钗“罕言寡语”“温柔敦厚”的举止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需求与贾府复杂的环境相融合,使得她个人、乃至整个薛家以一种良好的形象在贾家客居。她“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半时,园中姊妹处也要度时闲话一回”,心思细密,礼数妥帖;生日宴前贾母问她喜好,她便依长辈往日素喜,说些“热闹戏文”“甜烂之食”;元妃赐下灯谜,她知是一首“无甚新奇”的七言绝句,“一见就猜着了”,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王夫人为金钏儿投井垂泪,她重在宽慰姨娘,并不多说同情死者之语,只是不避忌讳将自己的新衣作为装裹;大观园“兴利除弊”时,她提出“小惠全大体”,将每年归账拿出部分,散与园中照看当差之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2],显见的,薛宝钗外在形象及处事上的“稳重和平”,是一派“中和之美”。
(二)内在道家“相合之美”:成和之修,内外合也
在《红楼梦》里,“一僧一道”的设置以及论《南华经》等情节的描写多次流露出作者的道家思想倾向。儒家“中和之美”显见于薛宝钗,“从外观看薛宝钗是和谐的体现”[13]。而其言行中,又常有与她素日所为不相吻合的细节,过去更多看到薛宝钗身上儒家“中和”的一面,薛宝钗身上看似不谐的“内和”,是“和合之美”的更深层面。
在《红楼梦》里,多以寓所喻居者性情,林黛玉居潇湘馆,暗比“娥皇女英泪斑湘竹”之典,而薛宝钗所居的蘅芜苑,引人注目处便是它的矛盾不谐。远远观去,蘅芜苑“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贾政乍见称“无味的很”,却不想“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直称“有趣”,这种内外迥异、别有洞天的格局可以理解为是薛宝钗人格的写照,而遮蔽的玲珑山石之后,苑中并不是流俗或穿凿的格局,而是遍植“杜若蘅芜”,并有茝兰、清葛、金簦草、玉蕗藤、紫芸、青芷这些《离骚》中的香草,如潇湘馆中湘竹有约定俗成的美人逝情薄命的意味,《离骚》中香草的意象也有其一贯的意蕴——高洁品质和美好理想,这正与曹雪芹对她“山中高士”之誉恰合。
而这种内外修成的“和合之美”,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行就与心和——辩证的“和合之道”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的花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文中以雪为喻,展示出她心底冷的一面。金钏儿自尽,她安抚眼前的姨妈,不避忌讳赠衣装裹,却没有过多地垂怜逝者,只淡淡说她糊涂;柳湘莲妻亡出家,她也并不在意,只嘱咐哥哥记得酬谢一同行商的伙计。她的冷不止对旁人,也对自己,文中她直接的情感表露甚少,贾宝玉挨打后,她虽红了眼眶,却终未落泪;林黛玉语出讥讽,她“借扇机带双敲”之后也只是一笑收住。脂砚斋形容她“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上文已提,薛宝钗处事守“中和”之道,若将此与无情的评价相观照,则她的行事作风全然因循于礼法世故。但对应道家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说,外在的无情顺势,未必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亲疏一观,抱守温和”[9]222,和薛宝钗“不亲不疏”的行事相类,外在处世上,庄子提倡顺世应物。而薛宝钗的内心指向,书中也常透出端倪。
例如,虽然薛宝钗在人情世故中八面玲珑,在利益社会中如鱼得水,曹雪芹仍是将她称作“山中高士”,她曾辛辣地讽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横行无道之人,寓小题以大意,表达作者“想说又不敢说的‘伤时骂世’的话”,“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她虽然顺应时世,内心却对污浊的现实怀着强烈的批判。又道“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表现出她内心棱角分明、不群于世的一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虽倡“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9]36,但亦有激愤之时。
“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9]37,看那空旷清净的地方,心无杂念,则悟道生慧、自性光明,至此还不能凝止,便是形坐神驰。四十回中,作者借领刘姥姥游园,以闺阁陈设布置,侧写诸小姐品格喜好,至薛宝钗,“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卧房是私密之地,对卧房的布置折射出主人的内心,“虚者,心斋也”[9]36,卧房的空旷映照出的是心境的空明,对外物的无所贪求,她也“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不执恋于颜色,而返之观注内在。
另外,薛宝钗的圆融理性也多表现在与长辈、下人的交往中,在信任的人面前,她虽也温厚,却逐渐流露出自然率真的一面。“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林黛玉开她玩笑,她便“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芦雪亭联诗前打趣湘云“你回来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了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揌上些,以完此劫”。
薛宝钗谓为“无情”,而“无情”作为“没有情感”之义使用,首出于《庄子》:“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9]54,意即超脱情物之累,“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9]295。精神的空间在“枝经肯綮”的现实中只是一个狭窄的缝隙[9]29,外表与人为群,不会损害内心的宁静。无力改变残酷无情的现实,便将对自由的体悟和追求,限制在精神的范围内,以顺世实现对自由的超越。“德充于内,物应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14],这种外在的顺世应物,与内在的虚阔清净相反相成,辨证合一。
2.无所可用,为予大用——整体性的“和合之道”
薛宝钗身负华彩,却以无用为用而用之。她出众的才华与低调的行事,同样是“和合之道”的一种表达。
薛宝钗博学多识,颇具才干,藕香榭与惜春论画,通晓商贾为岫烟赎当,兄长采买归来商议酬谢伙计……世事洞明。但她处贾府之中,却并不才尽其用,未曾稍显锋芒,众人评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王熙凤说她“拿定了主义,‘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只做个温厚周全的看客。助贾探春“兴利除弊”时,尽管许多实用的建议是她所引导,但始终把握客居的身份,不肯喧宾夺主。五十六回《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庚辰本中批“宝钗此等非与阿凤一样,此则随时俯仰,彼则逾蹈也”,以“随时俯仰”释“时”字,评薛宝钗慧眼独具,切合“随分守时”的特质。分明身怀美材,却小心收敛,不似王熙凤要强精干,因劳心周旋伤身落疾,也引得夫婿与下人暗怀怨忿,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薛宝钗从整体着眼,不用己身,反有所用,正是无用之用,“予求无所可用久矣,今乃得之,为予大用。”
在文中,薛宝钗也表达过这种以无用为用、整体运作的“和合”思想。她饱读诗书,诗社中不过是应时之作,却屡屡夺魁,典故章句每每信口道来,偶抒文章见解则别开生面,但她却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其余诗词之类,不过是闺中游戏”,常劝身边女伴不必太看重诗文,“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又劝林黛玉莫读杂书,“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她虽以“非分内之事”为据,却也点出对女子怀才现实的担心。
一是为着怕心思放在杂书诗文上,“移了性情”,此处与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担心贾宝玉读“道书禅机”恰为对照,所虑都在“移性”,她虽反对别人参禅,却仍认为这种“移性”是“悟了”,被评“非宝卿不能谈此”,只是如贾宝玉后来感知的,她“知觉在先,尚未解悟”,又何必让别人“自寻苦恼”。
二是担忧“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子广有才名,反易招惹非议,不得善果。“其拱把而上者”往往“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
有才华本身并不是坏事,坏事在于自恃才高,以及别人认为你才高,接踵而来你要面对的种种情况。很多时候,比是否拥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你所处的环境是否容得下你有这样的才华,是你是否具备能担负起你才华思想的态度心境。觉悟如贾宝玉,感知到“缘起性空”之后,便觉世间“碌碌”“无趣”,自寻烦恼,而知觉在先的薛宝钗、林黛玉却反不记挂,游戏其间。显才彰秀,而不自洽于环境,不知系统合一之道,招致祸患,倒不如昏昏闷闷,无用以用。薛宝钗将无用作为有用,并不囿于有无之别,而将所用视为一个整体,因循肌理,和通为一。
三、“和合”而深邃:薛宝钗人物形象的多元文化内涵
(一)中国知识分子“外儒内道”人格形态的体现
薛宝钗人物形象上“中和”与“德和”的合一,可以观照出中国士人阶层“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从形成过程到精神结构都有其相似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始终贯穿了人格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内圣外王”理想在现实中失败,在理想与社会之矛盾的深刻感受中,道家本质上针对儒家政治和伦理进行调整和改进的特点,使得这种超越性的态度和传统儒家精神构成互补格局。“外儒内道”最初只是出于一种策略来化解随政治现实而产生的内心冲突,随着历史的演进,它逐渐上升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成一种稳定性精神结构,在更高层次上满足人们安身立命的需求,重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态,积淀为贯穿“士”阶层精神始终的理想人格。
屈子志向难申、投江汨罗,而郭象“名教即自然”、白居易“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应世策略的转化。“钗于奁内待时飞”,曹雪芹谓薛宝钗为“士”为“君”,某种程度上虚托薛宝钗为中国士人阶层人格理想的承担者。薛宝钗形象儒道“和合”、互为表里的特点,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外儒内道”人格形态的体现。
(二)道家主导的精神内核
薛宝钗身上呈现出中国士人阶层“外儒内道”的人格形态特点,而何种思想作为主导存在于她的精神内核之中,依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一致赞同“入游其樊”的情况下,儒家与道家的一个区别点,在于他们面对道德与势位的分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儒家认为“士志于道”,他们的“仕”与“隐”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倾向和现实精神,纵然“归隐”,依然存在“道”与“势”的两立所带来的心理冲突,隐居为“求其志”。相反,道家在面对“道”与“势”的分离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主张因循自然,以“顺物缘性”的游世态度来面对悲剧。
在前八十回“草灰蛇线”的设伏中,曾多次出现“飞鸟各投林”之后薛宝钗面对悲剧所秉持的心态。曹雪芹笔下众人所写诗中多寓谶语,面对惨淡的将来,不同于“红消香断有谁怜”“人为悲秋易断魂”“偏是离人恨重”,薛宝钗从无变徵之音,面对风雨迁延,她只道“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咏絮词时,众人皆因柳絮无根无着,悲慨世事无常变迁,身命不能由己,她则“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直抒她在乱纷纷的“蜂围蝶阵”之中,“任他随聚分”的淡泊安然。不同其他姊妹一派悲声,世间规律不可改,她臣服其中,安然接受,不管置于何种境地,都处之泰然。所居处蘅芜苑也恰与“恒无怨”谐音,身已尽力,便始终无怨。戚序本第七回双行夹批她“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正是庄子所言的“不择地而安”。
生日点戏时,她顺了贾母之心点的热闹戏文,却也是她所自喜“填的极妙”,盛赞的那支《寄生草》,虽说“没缘法转眼分离乍”却也只“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面对无常,不相执着,历经变迁,保持着内心的平和,这正是老庄所主张面对“道”与“势”两立时安命游世的人生态度。
(三)人文关怀:基于“和合”尺度的审美观照
“有一种标准认为,‘要想对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现象或者一种历史思潮做出公允的评价,就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其对社会发展是否起进步作用’。”[15]常用的评价标准,是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但从另一角度入手,“和合”本身是一种审美情感境界,美包含对象的统一,“如果我们能从表象之杂多性中实现统一,那就会给主体带来一种快感,因而我们就说这种表象的统一体是美的”[16],这在人物身上体现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主体的历史与当下、自体与环境之间是否能形成均衡“和合”的艺术境界。
从社会环境上看,薛宝钗面对着个体理想与社会情境的矛盾,而社会的改变,总是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逐渐发生,不会立即改变。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体因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倾向。“和合之道”基于人文关怀的尺度,不是帮主体去改变自己以促进整个历史进程中社会的发展,而是在当下的人与当下的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使个体和环境协调,使人能以一种适合的位置放置在现时的社会中。马尔库什的批判理论中有关多元美学建构部分反映出对这种“和合”尺度审美的认可:人类的统一应该被理解为不断对话的持续过程,这种对话建立在不同文化与不同生活形式之间的实践团结与创造性宽容的基础之上,而不仅是在一个主体道德范畴下思考。“和合之道”使得不同立场之间调解的对话发生,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得到平衡,这种交互平衡的有机运作就包藏着美学意蕴。
在薛宝钗幼年之“淘气”与当下之“随分”、济世理想与利益社会之间,“和合之道”作为一种人文关怀,统一了矛盾的两端,构成均衡“和合”的审美关系。“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6]495,在这样无情与有情、行就与心和的融合中,薛宝钗形成了其特有的人物审美风格。
注释:
(1)本文分析仅限于《红楼梦》前八十回,全部引文均出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
参考文献:
[1]杜贵晨.红楼人物百家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白灵阶.关于宝钗的藏与露[J].红楼梦学刊,2006(1).
[3]文致和.论薛宝钗[J].红楼梦学刊,1980(4).
[4]高宇.儒家理想人格和薛宝钗形象塑造[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1).
[5]燕连福.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J].求是学刊,2008(7).
[6]王树民,等.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姚维.道家和合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1998(5).
[8]罗昌智.和合之美与当代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之建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1).
[9]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王夫之.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王国轩.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王海洋.薛宝钗文化人格及其哲理评价[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1).
[14]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杨春时.文艺理论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孔文静)
收稿日期:2016-01-13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16)02-0054-06
[作者简介]董劭敏(1990-),女,福建福州人,广西大学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