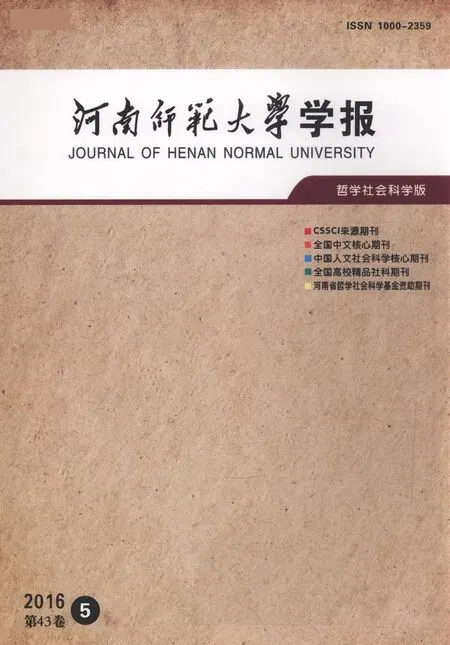秦汉帝国的边境:来自周边的帝国观
——国际简帛学视野下的边境出土简牍研究
[韩]金 秉 骏
(首尔大学 东洋历史系,韩国 首尔)
秦汉帝国的边境:来自周边的帝国观
——国际简帛学视野下的边境出土简牍研究
[韩]金 秉 骏
(首尔大学 东洋历史系,韩国 首尔)
因为权力存在于政治中心,所以规则是由中心制定并被制度化的。而想要将规则付诸施行,就要向周边派遣官吏。反过来,周边地区是受中心统治的区域,中央派出的官吏在周边施行中心制定的制度,贯彻中心的原则。所以,似乎可以说,如果理解了中心,就能够准确把握其基本结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规则最终如何适用现实仍主要取决于周边。虽然中心的统治者不得不为持续贯彻规则而考虑周边的立场,但和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周边地区人的感受肯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有必要反过来全面审视周边,尤其是在研究周边存在问题的“帝国”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国”,一般被认为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但至少其中一部分王朝是符合东西方世界均认可的“帝国(Empire)”这一概念的。“帝国”一般被定义为通过武力占领周边区域,将其变成自己的统治区域的同时,对其实行全面且持续性统治的国家。无论是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所谓的西方帝国,还是秦汉帝国、隋唐帝国、明清帝国,或是蒙古帝国等东方帝国,都具有这样的属性。也就是说,虽然王朝和帝国指的是同一实体,但王朝仅将居住于中心地区的编户齐民视为皇帝统治的对象,而帝国关心的对象还包括新占领地区被纳入统治的其他民族。在将以武力占领的区域纳入自己的疆土之后,各帝国在统治方式的问题上产生了差异,而统治方式往往是决定帝国能否持续的重要因素。有时对占领地施行高压式统治会招来被占领者的反抗,最终导致帝国崩溃。有时虽然采取了尊重被占领者习俗的统治方式,但仍激起边境的混乱。也正因如此,帝国的边境统治方式成为把握帝国特征的重要历史指标。
众所周知,简牍开辟了秦汉史研究的新纪元。那些秦汉时期简牍的主要内容如实地记录了在帝国中心制定且施行于全国的律令,以及依照这些律令推行的文书行政。这些都是真实反映秦汉王朝中心规则的内容。所以,大批学者开始关注律令和各种文书中记录的官制、身份及刑罚等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简牍实际上都出土于帝国的边境。也就是说,统治理念虽然在帝国中心制定,但真正贯彻之地却在边境。因此,律令和文书行政在边境推行这一点,可以说是了解秦汉帝国特质的决定性一环。然而,这一点却往往被学界所忽视,甚至在研究像敦煌、长沙、武汉、里耶这些简牍出土地区时,也极少会有学者站在周边地区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地方是如何接受中央统治的。因为无论如何,与边境相比,人们往往更关心中心。
自汉武帝在韩半岛北部设立乐浪郡后,这里就成了秦汉帝国的边境。因此,站在这里,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不同于中国的视角来审视秦汉帝国。更何况这里与中国国内的边境区域不同,因为它现在属于其他国家,这里的人显然更具备周边人的立场。事实上,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半岛人都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秦汉帝国。亦即,在理解帝国中心制度这方面,比起强调普遍性而言,这里的人相对更关心周边地区的独特性和土著民问题,更重视土著民是如何抵抗帝国统治的,以及因为这些抵抗,帝国不得不降低统治强度,最终委任当地土著民来进行自治式统治,或干脆放弃这一区域等问题。不得不说,这样一个与帝国边境统治有关的主题,是一个能够很好把握秦汉帝国特质的主题。然而,在中国,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学者们只关注中心的普遍性问题;反过来,在韩国,作为外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只重视所谓周边地区的特殊性问题。其结果是,我们始终都无法正确地评价秦汉时代的帝国特征。
韩国学界之所以一度过分强调周边的特殊性,是因为在韩半岛基本没有发现过秦汉时代的简牍。直到1990年,与西汉时期乐浪郡有关的简牍在平壤出土,才打破韩国学界的沉寂。当时在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中发现了《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和《论语》。虽然这些资料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数量上来看都极少,但它们毕竟是从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离帝国中心相当远、受到帝国统治力度微弱、且生存着妨碍统治的土著民、位于东方尽头的韩半岛发现的。所以它与以往在敦煌和居延等地出土的资料一样,是全面把握秦汉帝国特征的难得资料。
本文将利用平壤出土的《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和《论语》,分三部分探讨秦汉帝国的边境统治问题。首先论述中心对周边的解读方式,或者说通过中心地区的律令和制度,来确认乐浪郡简牍文书所具有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央统治是如何被贯彻到边境的。其次论述周边解读周边的方式。关注边境地区,将乐浪郡与中原以及其他边境区域出土的简牍进行对比,从而对乐浪郡简牍的意义加以补充。再次论述周边对中心的解读方式,通过我们所了解的乐浪郡简牍的意义,来进一步探讨中心帝国当时是如何计划统治和扩展边境的。事实上,这些方式不仅适用于乐浪郡简牍,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其他出土边境的简牍研究。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名为《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的木牍,横向5厘米,纵向23厘米。就是在这样一块小小的木板上,记录着西汉元帝初元四年乐浪郡25个县的户数和人口,此外,还附记了相较前一年人口的增减情况。此年乐浪郡有43845户,28万余口,比前一年增加了584户、7598口。
乐浪郡的户口簿就是这样一块小木牍,据此好像只能看到乐浪郡的县名和户口数。然而,如果了解中央颁布的律令中有关户籍的规定就会感受到,这个简单的户口簿其实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户籍是每年八月在乡里制作出来的,户籍的副本和按里集计的帐簿会被移送到县,而后封印保管于文书库,按县集计的簿籍再上报到郡。《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就是通过这些流程制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乐浪木牍本身是通过由里典和里老所负责的百姓直接申报、乡里户籍的制作、向县里移送副本、封印保管等文书行政程序才成形的。
除了户籍外,乡里还同时制作像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各种帐簿。此外,以此为基础,还会单独集计户口数的增减,年龄、性别数字,免老、新傅、罢癃数字,垦田、田谷数量。荆州市纪南镇松柏村出土汉简分别记录了南郡属县和侯国免老、新傅、罢癃的数字。尹湾汉简《集簿》依据这样的帐簿制作出了各种项目的集计。尹湾汉简《集簿》所记录的项目之一——较前一年度的人口增减数,在乐浪木牍中也记录了。可见制作乐浪木牍的目的是为制作其他账簿提供依据。
东汉末年的徐干在《中论·民数篇》中说,制作包括户籍在内各种帐簿的原因,是通过户籍制度掌握百姓的身份和财产,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行政制度,进行社会管理。天长县出土的户籍簿正面记录了户口集计,反面记录了算赋。它们和松柏汉简出土的各种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尹湾汉简《集簿》中记录的户口数以及垦田、田谷数一样,都是为了征收税役而制作的。而且,只有制作了户籍,才能实现确保治安的什伍制和连坐制。也就是说,乐浪郡户口簿的制作,其实是为税役和治安而实实在在展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此外,将各种帐簿一一制作、移送、接受、确认等复杂文书行政的存在,说明当时能够解读制作文书的多数官吏是各尽其责的。与此同时,当时在乡里安排了制作文书的乡啬夫,在县廷、诸曹和啬夫组织中则安排了令史和佐、史等吏员。
乐浪木牍户口簿虽然只是一块记录了乐浪郡所属25个县户口数的简牍,但它再现了当时在乐浪郡为了征收税役和施行律令统治,人们有条不紊地制定基础户籍和推行文书行政的事实,其工作成果是掌握了乐浪郡43845户和大约28万余口的情况。根据以往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心与边境的二元构图下,律令统治和文书行政只能在中心得以正常推行,对于边境居住的众多异民族却很难切实掌握他们的情况,所以,在边境地区是无法正常施行律令统治和文书行政的。然而,通过乐浪户口簿,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郡县统治的原则无论是在内郡还是在边境都可以得到普遍实施。由此可以确认,帝国征服了周边异民族之后,既不放弃那些地方,也不将统治权委任给土著民,而是选择了普遍式的统治方式,将在中心实施的律令统治原封不动地施行于此。
在发现乐浪郡户口簿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套《论语》。这套《论语》与河北省发现的定州本以及现在通行本都无太大差异。儒学是帝国的核心理念,《论语》出土于处在帝国边境尽头的乐浪郡,说明当时帝国除了想要在边境尽头施行律令统治外,还曾试图实现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
帝国对乐浪郡的统治,在设立郡县以后得以持续下去。乐浪郡设立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乐浪郡户口簿记录的时间是元帝初元四年(前46年),前后经历了62年,这里的人口变为43845户、约28万余口,比前一年户数增加了0.64%, 口数增加了2.82%。此后又过了48年,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户口数被记录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郡的户数为62812,口数为406748。此间平均每年户数增加0.79%,口数增加了0.76%,表明前文所说的律令统治和文化统治在此地确实得到了积极有效的实施。
再讨论第二个问题。除了律令外,大部分简牍都是在边境出土的。河西的敦煌和居延,以及湖南省的里耶,就是其中具具代表性的地域。如果说乐浪是汉帝国的东方尽头,那么敦煌和居延就是汉帝国的西方尽头。里耶则是边郡中一个遥远的、深处险峻群山之中的边县。在这些地方发现简牍,说明中央制定的律令和依其施行的文书行政曾在此处得以实施。就像乐浪郡户口簿所记录的那样,这些地区与内郡一样曾实施过积极的编户齐民统治。
然而,虽然在这些地方确实施行了基本的制度和律令,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与内地完全一致。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为了防御国境之外的敌人,这些地方设有军事防御设施。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大部分简牍,都是在构成这些防御设施的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等都尉所属的候官和烽燧发现的。根据里耶秦简中“皆蛮夷时来盗黔首徒隶□田者”(9-554)、“反寇攻离乡亭鄣吏卒各自备牢反时”(9-32)的记录可知,当地时常遭受蛮夷的攻击,为了抵御攻击,需从各处通过更戍(“更戍士伍城父阳翟执”8-1517)、罚戍(“罚戍士伍资中宕增爽署迁陵书”8-429)、适戍(“城父蘩阳士伍枯娶贾人子为妻戍四岁……”8-466)、屯戍(“廪人□出廪屯戍簪褭襄完里黑”8-1574)等方式来征集戍卒,配置在当地。特别是远离县城的启陵乡,一定配备了军事设施。乐浪郡也常受到周边高句丽和濊貊的攻击,所以设有东部都尉和南部都尉,在出土的户口簿上记录了其所属的县名。
第二,规模上的差异。比起内地来,边境各县的户口数相当少。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一般情况下一个县的规模为1万户。相比之下,边郡的户数则相当少。依据《汉书·地理志》可知,边郡只有1千户到3千户。边郡所属的边县户数更少。里耶秦简所录洞庭郡迁陵县的户数,在150户到200户之间。乐浪郡户口簿所录乐浪郡提奚县有173户,海冥县有338户,含资县有343户。不要说达到内地县的平均规模,就是一个乡(一乡1000户)的规模都达不到,充其量也就是内地两三个里(一里100户)的规模而已。
但这种差异只是站在中心的立场上对比得出的。因此,尽管强调中心和边境的差异,但对于边境的认识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帝国为了统治边境,在治民机构之外还增加了军事机构(部都尉),但这种军事机构并不具备治民的功能,像制作户籍和征发税役这类治民功能仍由郡县来担当。此外,虽然一个县连二三百户都不到,但县的组织机构、主管官吏以及依此而行的律令统治和文书行政,却与大县几乎没有区别。洞庭郡迁陵县设置了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司空曹、布曹、狱曹、令曹8曹和官啬夫主管的10余个部门、100余名官吏、400余名官奴婢,以及数百名戍卒。乐浪郡的边县也设有包括功曹在内的诸曹和主簿等。
最后讨论第三个问题。要准确把握帝国边境的情况,就一定要关注边境的人。因为帝国统治的不是地,而是人。帝国控制了周边之地后,并不会驱赶当地人,而是会想方设法将当地的土著民置于统治之下。虽然也有徙民的情况,但基本上会参照土著民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统治方式。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土著民也存在不同类型。比如,古朝鲜灭亡后,在其地域设置了包括乐浪郡在内的四个郡。当时这里的居民既有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一直在此繁衍生息的土著民,也有西汉初期由燕国逃亡而来的卫满集团,这些人是古朝鲜的主要构成成员。除此之外,还有周边一些像真番一样曾臣服于古朝鲜的小国之民。那么,这个地区被控制后,帝国是统一管辖所有的人,还是将他们分开进行单独治理,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目前至少可以确认,帝国对古朝鲜直接统治的地域和臣服于古朝鲜的周边小国的对待方式存在差异。周边小国被划分为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而乐浪郡设置在古朝鲜的中心位置。在实施郡县制之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统治方式,这可以通过秦占领巴蜀后施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得以确认。帝国对身处周边小国包围的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和巴郡一样,一定程度上允许延续此前的君长秩序,同时试图把它纳入郡县统治的制度之下。而对于曾是古朝鲜直接管辖下的乐浪郡,最终却和蜀郡一样,采取了将每个人都编入户籍的统治方式。
有意思的是,君长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制度导致了户籍的异常。笔者注意到,在君长秩序被认可的情况下,每户的口数比平均数值高出很多。真番郡和临屯郡被废后,若按照乐浪郡户口簿初元四年(46年)的数字来计算,曾是古朝鲜直辖的地域每家平均口数为5.60口,但曾为真番郡和临屯郡的地域,数字达到了7.24—7.71口。据《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2年)乐浪郡每户口数为9.48口,假定其中包括每家4—5口的一般小农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应该是将小君长当作户主,统计其麾下属民户口得出的结果。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乐浪郡,洞庭郡和迁陵县也是如此,应当为土著民的新黔首,106户中有成年男子1046名,一户之中竟然有10名以上的成年男子(“新黔首户百六,男千卌六人,小男子□”16-950)。
此外,乐浪郡直辖地区还出现了旧统治阶层卫满集团和被统治阶层土著民这两种人。前者是自汉流亡而来的人,后者是具有悠久土著传统的群体。汉帝国占领了周边地区之后,是否会询问当地居民过去的出身,加以区别对待呢?对此,我们需参考张家山汉简和岳麓秦简的《奏谳书》案例,因为它们记录了秦占领楚、设置郡县时,对自秦逃往楚的秦人和本土楚人区别对待的情况。虽然理论上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具体论述,但事实上在降服之时以及之后,是否系统地采取了申报编入秦户籍的措施才是问题的关键。
关注土著民,还需要考虑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处于帝国周边的诸多异民族和内地人有很多不同。他们有的不从事农业生产,而选择保持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应该对应不同的租税征收方式。对不从事农耕者是无法征收田租的,因此,就不得不考虑不同的征收方式会给这些人带来怎样的负担。
语言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在睡虎地秦律中有关于行政业务需通过文书形式来处理的规定(《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有事请也, 必以书, 毋口请, 毋羁请”)。但像语言完全不同的乐浪郡这种情况,除了更需要依赖文书行政外,还会产生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占领初期,因为要处理紧急行政事务,所以不得不派遣熟知汉字和文书业务的内地官吏来此处充员。乐浪郡曾从辽东郡得到过“初吏”的支援。洞庭郡迁陵县也如里耶秦简“资中县令史阀阅”简(8-269)所载,得到了他郡官吏的补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著民最终还是要代替这些外地官吏来参与治理工作。所以,在文字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是当务之急,这时词汇和语法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乐浪郡所使用的土著语的语法结构不是“主-谓-宾”,而是“主-宾-谓”,而且还有终结形语尾和助词的问题。所以,渐渐地土著民也就不得不开始寻求其他适合自身的更好方式来解决语言问题。
我们以乐浪郡为中心讨论了土著民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土著民的情况在帝国边境随处可见。几乎在同一时期被占领且设置了郡县的南越地区,和乐浪郡的情况十分相似。它由本来就居住在那里的土著民、从内地移居而来的赵佗集团以及周边臣属的小国构成。河西地区、西南地区的情况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显然也存在类似的土著民部族。所以,立足于作为周边地区的乐浪郡土著民的视角进行观察的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域。
以上讨论了看待帝国边境地区的视角问题。乐浪郡户口簿和《论语》的出土让我们了解到帝国对边境地区和内地一样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统治。但如果考虑到在边境居住的土著民和他们的出身、习俗以及语言等特殊性的话,则可以更加生动地再现当时帝国在边境实施的政策。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摒弃以往认为边境是与中心相隔绝、绝对异质的特殊存在,以及中心的律令和制度单向影响边境的片面观念。
一个帝国的边境问题往往与其中心问题紧密相连。边境土著民的反应一定会引发统治者的应对,而怎样应对又是一个关乎帝国整体财政和军役征发的重要课题。《盐铁论》中大夫与贤良争论的很多内容,不正是与如何进行边境统治这一问题相关联吗?
[责任编辑 王记录]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