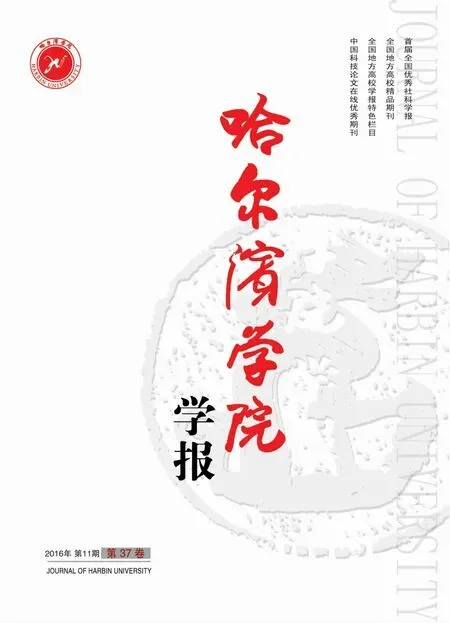康德中国文化观的哲学逻辑
胡 磊,赫秋晨,刘连朋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康德中国文化观的哲学逻辑
胡 磊,赫秋晨,刘连朋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呈现的中国文化观背后,隐藏着其自身的哲学逻辑进程:中国人之“理性”的发展程度较高,因而中国是“最开化的国家”;然而,这并不代表理性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在理论理性方面,中国人尚未达到“概念”的高度,更没有对理论理性自身进行批判,因而只是传授道德信条或陷于神秘主义;在实践理性方面,中国人并没有用“纯粹实践理性”对“一般实践理性”进行批判,没有将道德建立于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之上,因而只是执著于旧的习俗礼仪。
《自然地理学》;中国文化观;理性;理性的自我批判;自由
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以“中国”为标题,对中国的民族习俗和个性、礼仪、宗教等多方面进行了集中论述,尽管篇幅有限,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广泛,这是康德最为集中地表达其对中国文化认识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客观的表述背后却隐藏着康德强烈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正是奠基于康德自己的哲学理论之上的。
本文试图以《自然地理学》为出发点,探讨康德之中国文化观背后的哲学逻辑进程。
一、《自然地理学》的产生及其道德、政治取向
应康德的要求,弗里德里希·特奥尔多·林克根据其手稿编著了《自然地理学》,[1](P151-156)这部分手稿是康德开设《自然地理学》课程时所用的手稿,该课程始于1756年,结束于1796年。[2](P766-767)
而实际上,“在1756-1762年间,他只出版了三本小册子,包括课程内容的介绍和一篇私人性质的文章”,这其中就包括在1757年复活节出版的仅作为“课程内容介绍的《自然地理学教程(Entwurf und Ankündigung eines Collegii über die physischen Geographie)》”。[3](P170)从《自然地理学教程》的具体内容来看,此时的课程内容并不包括对不同地区人文特征的介绍,仅仅是一些关于海洋、陆地、气候等方面的自然地理知识。[4](P3-13)然而,到了1765年,康德在其发布的《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中,在“自然地理学”课程一栏中宣称他已“逐渐扩展了这一纲要”,并认为“这一学科将是一门自然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地理学”。[4](P315)此外,康德指出:第二个部分考察人,按照人的自然属性的多样性和人身上属于道德的东西在整个地球上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同样刺激的考察,没有它,人们就难以对人作出普遍的判断,而且在这里,相互之间进行的以及与古老时代的道德状况进行的比较将为我们展现一幅人类的大地图。[4](P315)
与最初的“自然地理学”课程相比,1765年的“自然地理学”课程发生的重大变化就在于增加了对“人”的关注,从原先的“自然的地理学”,变成了“自然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地理学”,康德认为这是“一些变化大有裨益的教学方式”。[4](P316)他指出,希望这一“广义的地理学”能使年轻人“为一种实践理性作好准备”。[4](P314)因此,《自然地理学》一书与康德的哲学理论尤其是道德哲学理论是紧密关联的,而这也是康德自己认可的。
从上述分析可知,《自然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内容(道德的、政治的地理学)是在1765年正式确立的,并以讲授“自然地理学”课程的方式形成,其形成过程在1765-1796年。这是康德哲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绝大多数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发表的。就康德人生经历而言,1764年,康德40岁,这是康德由青年时期走向成熟时期的转折点,康德认为40岁是一个人品格定型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在此时,康德的社交圈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也逐渐变得高度规律化,逐渐变成了我们通常印象中的那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康德。[3](P180-198)
因此,无论是从“自然地理学”这门课程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康德的人生历程来看,《自然地理学》不容小觑,它历经康德最重要的时期,隐藏着重要的哲学背景。
而就《自然地理学》的具体内容而言,该书对“中国”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论述中,“中国”这一节篇幅最长,涉及内容最广泛;并且在《论人》这一章的第七节——“人在其鉴赏方面的彼此偏离”中,康德所列举的四个方面都以“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1](P318-319)而在论述其他地区或人种诸如“东京”“巴布亚陆地”“卡尔梅克人”[1](P382;P393;P404)等处,都提及“中国”。可以说,“中国文化状况”是康德“道德的和政治的理学”所关注的焦点。
但是,康德是从何处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这些信息呢?康德一生未曾远离哥尼斯堡,他对中国的了解都是通过他人提供的信息间接获得的。首先是耶稣传教士所提供的大量信息,甚至可以说,17、18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便是耶稣传教士传回的资料。[5](P12-19)这一点也在《自然地理学》中得到了确认,康德在其中多次提到“传教士的报道”。[1](P380-382)再者,是通过一些旅行者(包括来华商人)的游记来获得。康德曾指出,他“通读了一些精明强干的旅行家关于各个国家的最基本的描绘、各种旅行的普遍历史”;[1](P4-5)最后,就是对康德产生重大影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等思想家关于中国的评论性的资料。
不过,尽管康德从多种途径获得关于中国的各方面资料,但由于这些传教士、旅行者只是初步接触中国文化,接触时间、范围十分有限,因而这些资料难免是片面的,而即便是有些思想家颂扬中国文化也是出于特定目的:抨击欧洲自身的宗教和政治制度。[6](P887-890)这也就意味着康德对中国的了解尽管渠道广泛,但无疑是不够全面、不够透彻的。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将更加依赖于自身的理论视角。换言之,康德之中国文化观是奠基于其自身的哲学理论之上的。
二、“最开化的国家”与对“理性”的肯定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的“中国”这一节的开篇处写道:“在这个大国的北部,冬天的寒冷强过欧洲相同的平行处。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且最开化的国家。”[1](P377)康德在此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开化”的国家,自然是考虑到中国的文明成果,如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提及的中国的复杂的语言、规范的律法和习俗以及针灸、印刷术、大运河,等等,而这些是当时欧洲所不及的,再加之受17、18世纪的“中国热”的影响,[5-6]大批思想家对中国的赞颂同样使得康德有理由给中国冠以“最开化的国家”的称号。
然而,康德对“开化的”(或者说“文明的”)一词的使用却并非仅仅由于对“文明成果”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文明成果”所代表的是人类“理智”的发展,即人类“理性”的进步。
“开化的”与“野蛮的”相对。如康德曾提及:“摩尔人和回归线之间的其他民族通常能够令人吃惊地奔跑。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野蛮人,也都比其他文明民族更强壮,这源自于他们自小就被允许自由运动。”[1](P315)而之所以“野蛮”正是由于“理智发展”不够健全,之所以“文明”乃是由于“理智”的充分发展。康德论述道:“邓·乌罗阿察觉,在美洲的卡塔赫纳和周围地区,人们很早就聪明起来,但他们在理智上却并不以同样的程度继续成长。”[1](P315)“温带,尤其是温带中间部分的居民比世界上人的任何其他种属身材都更漂亮、更勤劳、更诙谐、在其情欲方面更节制、更有理智。”[1](P316)甚至在提及“旅行者”时,康德都不忘加上“理性的”这一限定词,可见“理性的发展程度”是康德评价“人之发展水平”的关键尺度。因此,当康德说中国是“最开化的国家”时,同时也在承认,中国人之理性的发展程度是远远高于那些野蛮人的。
可以看出,对“理性”的肯定同样渗透在《自然地理学》中,这本看似非哲学性质的著作,其实背后隐藏着康德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而当康德对中国文化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自然也是以“理性”为评价标准的。而实际上,这是17、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大陆的整体特征——对理性的肯定。莱布尼茨曾认为欧洲应当首先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以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7](P9)沃尔夫亦是如此,他指出中国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7](P33)总之,对理性的肯定是欧洲大陆在启蒙时代的整体特征,康德亦是如此。
三、“传授道德信条或神秘主义”与“未经批判的理论理性”
虽然肯定理性,但这并不代表理性自身毫无问题。事实上,在康德看来,人们往往将理性误用,而这正是由于没有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康德现在所需要做的正是构建一个“法庭”,以对“理性的合法性”进行裁决,该法庭即“纯粹理性批判”。[8](P3)
这一批判分成了两步:“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与“对实践理性的批判”。而这一哲学逻辑进程恰也渗透于康德的中国文化观之中。先来看康德对中国哲学理论的看法及其背后的“对理论理性进行批判”的哲学逻辑。
“事实上,康德的确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宗教发表过演说,而这些都包括在其自然地理学课程的框架内。”[2](P768)康德在为《自然地理学》演讲作评注的手稿中写道:
“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是传授一些为王孙所设计好的道德信条……并且提供了许多先前中国王孙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2](P765)
显然,康德对孔子仅仅“传授道德信条”的做法极为不满,因为在康德看来,对“概念”的分析是理论理性所必需的,也因而是哲学所必需的。因此,中国人在理论理性方面显然是不完善的,康德也因此直接断言“在东方,哲学将是不会被发现的”。[9](P62)既然中国人尚且没有达到“理论理性”所要求的“概念”分析的高度,那对于理论理性自身的批判,中国人更是差之远矣,因此,要想达到康德所希望建立的“严格科学的哲学”更是遥不可及。
因此,当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评论中国的佛教,认为“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意见,认为无(Nichts)[10](P382)是万物的起源和终点,因此有一段时间无感觉并放弃一切工作是虔敬的思想”[1](P381)的时候,与其说康德认为“把‘无’看作世界的起源和终点”是“独断主义”的,不如说康德会认为这是“神秘主义”的,因为,尽管独断主义没有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至少他们达到了“概念”高度,而对于尚且没有达到“概念”高度的中国人而言,当他们谈论“无”的时候无疑将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提法。
当然,不能因为中国人缺少“概念”分析,就说中国人完全缺少理论理性,最多只能说中国人的理论理性还不完善。而实际上,如果站在康德“对理论理性进行批判,为理论理性划定界限”的高度来看,无论是尚未达到“概念”高度的中国人,还是西方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都可以说是未曾对理论理性自身进行批判,因而难免在运用理论理性的时候造成一种僭越——从现象界向自在之物的僭越。因为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只能对现象界有效,而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自在之物而言,理论理性无能为力。因此,中国的“无”,西方的“上帝”“灵魂”“自由”这些属于物自体世界的东西都是理论理性自身的僭越。
总之,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康德认为中国尚没有达到“概念”的高度,“理论理性”极不完善,而对于“对理论理性自身的批判”而言,更是差之远矣。因此,当康德说“中国是最开化的国家”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一句赞美之词。
值得指出的是,康德这种“仅立足于自身理论立场来评判中国文化”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康德的言论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文化从来不是西方所发展出的“概念式”的独特样态,中国人的思维更不是康德所追求的“纯粹理性”的思维,相反,中国文化重“领会”“体悟”,重情感的沟通……这些是康德所没有认识到的。而康德的这些“误解”则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
四、“执著地崇拜旧习俗”与“未经批判的实践理性”
康德对理论理性进行批判的目的很明确,即将理论理性限定在感性经验世界,以便为“信仰”留下空间。[8](P22)而这就意味着,上帝存在、灵魂不朽、自由理念这些自在之物虽然无法通过理论理性进行“认识”,但可以作为“悬设”,在实践理性中成为“信仰”以指导理性的实践运用。[11](P173)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自在之物如何成为信仰?这就需要从“纯粹实践理性”中引导出作为绝对有效的“道德法则”,以此来说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在实践理性中成为“信仰”的必然性。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纯粹实践理性(既按照其理论运用又按照其实践运用)才是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源泉”。[11](P173)
这里的关键在于,康德认为这些“道德法则”是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获得的,作为绝对有效的道德法则,它不同于立足于“一般实践理性”而得出的习俗教条;前者是排除一切“经验性的内容”的,即仅仅是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提出的,而后者则没有摆脱“经验性内容”,只是由“一般”实践理性获得的;前者也因此是必然有效的,而后者则因未摆脱经验内容的影响而是偶然性的,不是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因而应当用“纯粹实践理性”来批判“一般实践理性”。[12](P3-7)
显然,中国人的做法恰好与康德的价值取向相违背,因为中国人过分执著于那些基于“一般实践理性”提出的习俗礼仪:
他们的第一项法律是孩子对父母的顺从。如果一个儿子打父亲,则整个国家都为之震动。所有的邻居都被审问。他本人则被判处凌迟成上万片。他的房子以及该房子所处的街道被摧毁且不再重建。第二项律法是对上司的顺从和恭顺。第三项律法涉及礼貌和礼仪,等等。
康德对中国旧习俗、旧礼仪的批判仍有很多,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这些旧习俗、旧礼仪只是基于“一般实践理性”所做出的规定,其中掺杂了过多的“经验性内容”,因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不会为人们普遍遵守。而即便是人们遵循了这些习俗礼仪,也往往只是“合乎义务”,而不是“出于义务”。两者的区别在于,“合乎义务”只是服从于外在的规范,而这种服从往往是为了达到其他的功利性目的,如“对上司的服从和恭顺”可能只是为了“升职”;而“出于义务”则是仅仅“为了义务而义务”,即没有其他的功利性目的,“义务本身”就是其唯一的目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则可能出现下属公然违抗上司的命令的状况,当然前提是下属认定上司的命令是不道德、不合理的。[12](P17-26)
因而在康德看来,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而“合乎义务”的行为往往掺杂着外在的功利性目的,通常体现出人的“虚伪”的一面。出于义务的行为是遵循了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的行为,而对这些法则的遵循意味着理性的“自律(Autonomie)”,而只有这种“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相反,遵循旧习俗礼仪只是“他律(Heteronomie)”,只是外在的规范约束,因而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对“自由”的追寻则是康德整个哲学的使命。
如果联系康德的人生经历,将更容易理解为何康德会对“习俗礼仪”进行如此强烈的批判。少年时期的康德是在由新教的敬虔教派控制下的腓特烈中学度过的,在这里,每次上课之前都会念一段祷词,午餐和放学之前各唱一段圣歌,教师须时刻谨记自己是在“全在的上帝”的监督下上课。[3](P77-87)繁琐的规章制度使得康德备受压抑,以至于康德后来回忆自己在腓特烈中学时,认定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日子。[3](P77)显然,中国人繁琐的习俗礼仪与康德在腓特烈中学的经历如出一辙。
五、结语
《自然地理学》形成于康德的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时期,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的地理学”,还是一部“道德的和政治的地理学”,因此,康德在其中所表达的中国文化观是奠基于其自身的哲学理论之上的:
首先是对“理性”的肯定,人之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中国之所以是“最开化的国家”正是因为中国人比那些野蛮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发展了自己的理性能力。然而,尽管与野蛮人相比,中国人的理性发展程度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理性”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的,因为中国人的理性同样是未经自我批判的理性,其理论理性是极不完善的,它没有上升到“概念”的高度,只是传授道德信条;而对于“对理论理性自身的批判”而言,中国人亦没有达到,其直接谈论自在之物的做法更像一种神秘主义。
同样,中国人并没有运用“纯粹实践理性”对“一般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只是立足于掺杂着经验性内容的“一般实践理性”,执著于旧有的习俗礼仪,而不是通过遵循“纯粹实践理性”提出的“道德法则”达到“自律”,因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
但是,康德这种“仅仅站在自身理论立场来评判中国文化”的做法有失偏颇,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立场来看,康德的言论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13]
[1]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Stephen R.Palmquist,Cultivating Personhood:Kant and Asian Philosophy[C].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 GmbH&Co.KG,2010.
[3]〔美〕曼弗雷德·库恩.黄添盛.康德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I(1757-177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德〕利奇温.朱杰勤.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6]〔法〕安田朴.耿昇.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德〕夏瑞春.陈爱政,等.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8]〔德〕康德.邓晓芒.杨祖陶.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成中英.冯俊.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0]K niglich Preu 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r. Kant’s Werke IX:Logik·Physische Geographie.Pdagogik[M].Berlin a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 Co,1923.
[11]〔德〕康德.邓晓芒.杨祖陶.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德〕康德.杨云飞.邓晓芒.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刘美玲.当代视角下的荀子礼法制度伦理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1).
责任编辑:魏乐娇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Process in Kant’s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HU Lei,HE Qiu-chen,LIU Lian-peng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Kant’s idea of Chinese culture in “Physical Geography” implies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process:Chinese develop their philosophy of “reason” to a very high level so China is “the most civilized country”. However,this doesn’t mean that reason is on the “right” way. Theoretically speaking,Chinese didn’t achieve the 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 They didn’t criticize reason itself but teach morality and go to the direction of mysticism. Practically speaking,Chinese didn’t use “pure practical reason” to criticize “general practical reason”,which means they didn’t put moral on the “moral law” of pure reason but stick to customs and rituals.
“Physical Geography”;the view of Chinese culture;reason;the critique of reason itself;freedom
2016-04-08
吉林大学2015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项目编号:2015110001。
胡 磊(1995-),男,山东淄博人,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赫秋晨(1994-),女,吉林通化人,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刘连朋(1963-),男,吉林大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佛学研究。
1004—5856(2016)11—0014—05
B516.3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