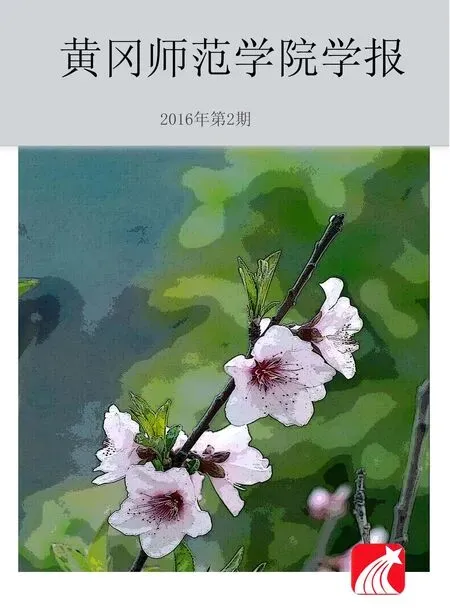黄孝方言NP后的“两个”①
汪化云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黄孝方言NP后的“两个”①
汪化云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两个”在黄孝方言中置于名词性成分后用作复指,与其元代出现的用法相同,也与清后期“俩”刚产生时的用法一致,代表了“两个→俩”语法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其中“联合短语+两个”可能有歧义,主要原因是因为“两个”的复指对象可以仅仅是前面的人称代词,也可以是整个联合短语。“两个”还虚化为表示“交互”意义的助词,与其在北方官话中合音为“俩”、发展成人称代词和部分名词的双数标记不同。
团风方言;“两个”;复指范围;歧义;重新分析
官话中的“俩”是“两个”在口语中的合音[1],大约在清后期的某些汉语方言里就已经形成并较多使用了。[2]长期的发展使得“俩”与“两个”在句法功能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3-4]:“俩”主要用于人称代词、指人名词之后,“两个”主要用于指人名词之前。这使得“俩”演变为北京话等北方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双数标记。[5]江淮官话黄孝片(本文简称“黄孝方言”)没有这个合音的“俩”。其用于名词性成分后的仍是“两个”,一般是作为数量短语复指前面的成分,在一些结构中则演变为表示“交互”意义的助词,表现出与北方官话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主要以湖北省东北部的团风县方言为例讨论其分布特征,然后结合汉语史和其他汉语方言,简述其“两个”语法化的主要路径以及后置的“两个”在语法化历程中的地位。
一、“两个”的复指对象
团风方言中的“两个”音⊂niɑ?□ko。作为数量短语,“两个”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等,构成“两个是红的、我要两个、两个桌子、两个毛病、两个人、他的两个”之类结构;也可以用在名词性成分后面,与之构成复指短语“NP+(跟+NP+)两个”(少量为偏正短语)。后一类用法,与元代汉语中没有合音为“俩”的“两个”用法相同(以下各举元代文献中相应的一例以资比较)。这有以下3种类型。
(一)代词+两个 这个结构中的代词主要是人称代词,也有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代词和“两个”构成复指短语或偏正短语,主要用以指称人,也可以指称事物,这有3个次类。
1.人称代词+两个。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构成指人的复指短语“他们/你们/我们+两个”:
(1)你们两个一路一起去。︱我在这下[xa⊇]儿这儿等他们两个。︱他对我们两个说了的。
比较:小梅今日绝早自家走了,干我们两个甚的事?(《全元杂剧·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二是构成指人的复指短语“你/我/他/他□ni?‘老人家’的合音/你□ni?+两个”你/我/他/怹/您俩,即用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表达双数,如同普通话的“你二人改装划船到对岸”一样:
(2)我骤就是不喜欢你两个。︱他□ni?两个到哪里去了?︱他对于对我两个总不好。
比较:恰才体审你说的言语是实了,今我两个告与帖木真去。(《元朝秘史·卷六》)
例(1)“他们两个”之类与例(2)“他两个”之类的意义一样,但后者有着明显的口语色彩。
2.单数指示代词+两个。跟普通话类似,单数形式的指示代词“这、那、姐中远指代词,那”在名词性成分前,只能用作指示而不能用作代替,因而其跟“两个”也只能构成偏正短语,如“这两个/那两个/ 姐两个”等,合起来指称人或物的双数:
(3)这两个(指人或物,下同)不好。︱我喜欢那两个。︱姐两个下都[xa⊇]要不得。
比较:想着存孝破了黄巢,复夺取大唐天下,他的好地面与了这两个,可将邢州与了存孝。(《全元杂剧·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
同元代以来的文献中一样,复数形式“这些、那些、姐些”后面也不能出现“两个”。
3、疑问代词+两个。疑问代词只有不表示具体数量的“哪”可以构成“哪两个”,没有“哪个两个、哪些两个、么事什么两个”之类说法。同样,“哪两个”也是偏正短语:
(4)哪两个敢去?︱你不要哪两个?︱他对于哪两个好些?
比较:(刘夫人云)小番,阿妈那里有两逆贼么?(莽古歹云)是那两个?(刘夫人云)一个是康君立,双尾蝎侵入骨髓;一个是李存信,两头蛇谗言佞语。(《全元杂剧·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
(二)名词+两个 这类名词都是表示具有相互关系的集合名词(简称“集合名词”),如“夫妻、学友”等,构成“父子两个俩、娘伙儿两个、爷伙儿两个、妯娌两个、叔侄两个”等复指短语:
(5)塔里他家夫妻两个会做生意。︱我不么怎么喜欢这叔侄两个。︱对于那弟兄两个客气不得。
比较:(薛净云)我兄弟两个,曾见你半厘錾口儿?是那个要了你银子,说清廉不清廉?(《全元杂剧·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栏记》)
除组合中本身有“伙儿”的以外,团风方言中上述例子中的“两个”都可以用表示对待关系且可以表示双数的词缀“伙儿里/伙儿的”替换而基本意义不变:夫妻两个≈夫妻伙里;父子两个≈父子伙的。(当然,“伙儿里/的”也可以表示多数,如:学友伙里同学之间、同学们、行事伙里同事之间、同事们、娘伙儿的娘和儿女们,就可以表示超出两个的对象。因此,“伙儿里/的”是用于指人的集合名词的复数标记。)
(三)联合短语+两个 包括4个次类:
1.名词/名词短语+(跟+)名词/名词短语+两个。名词或名词短语一般指单个的人,如果组合为“非指人名词/名词短语+两个”,那大多是拟人用法。这类复指短语很常见,如“二哥三哥两个、二班的小毛跟三班的三毛两个、这个猪跟那个牛两个”之类:
(6)我问了二哥三哥两个的。︱(地主对放牛娃说)猪跟牛两个冒没有吃,你就不能吃。
比较:后来到太祖时,都教做了答剌儿罕官人。惟合答安、脱朵延两个无子嗣。(《元朝秘史·卷一》
2.代词+跟+名词/名词短语+两个。其中的代词均为单数的人称代词;名词/名词短语多指单个的人或动物(多为拟人)。如“他跟二哥两个、我跟那个同学两个、你跟这个猪两个”等:
(7)你跟那个猪两个,哪个聪明些?︱莫麻烦他跟二哥两个。︱要不得。你把我跟那个同学两个当苕盘当傻瓜戏弄。︱你跟狗子狗两个下[xa⊇]都冒吃,我即刻儿马上来喂你们。
比较:(正旦云)妹子,我想你除了我呵,便是个第一第二的行首,你与那村厮两个作伴,与他说甚么的是?(《全元杂剧·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3.名词/名词短语+跟+人称代词+两个。名词/名词短语一般是指单个的人或动物(多为拟人),构成“二哥跟他两个、爸爸跟我两个、那个狗子跟你两个、三哥跟他两个”之类复指短语:
(8)我只要二哥跟他两个。︱三哥跟你两个下去。︱
狗子跟你两个下好[xɑu⊃]吃。
比较:(正旦唱)俺哥哥因为少吃无穿来投托,曾被我赶离门恰和他两个(引者注:俺哥哥和他两个)厮撞着。(赵令史云)是你的哥哥,便和他厮见,也不妨事。(《全元杂剧·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栏记》)
4.人称代词+(跟+)人称代词+两个。结构中的两个人称代词可以是联合短语(详下),构成指人的“我(跟)你两个、他跟你两个、我跟他两个、你(跟)我两个”之类复指短语:
(9)我(跟)你两个去看下[xa⊇]子看一下。︱我相信他跟你两个。︱你对于对我跟他两个不错。
比较(详下):感你两个好意。我虽醉有句话与你两个说:想人生青春易过,白发难饶。你两个年纪小小的,则管里被这酒色财气迷着,不肯修行办道,还要等甚么?(《全元杂剧·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从上面的简介来看,团风方言中后置的“两个”构成复指短语,除了拟人用法,大多是表示人的双数。即该方言用词汇手段“两个”表达人的双数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语法形式,与元代以来的汉语书面语相同。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在整个黄孝方言中普遍存在,除了少量词汇差异,各方言点在语法方面与团风方言完全相同。例如黄孝方言东片的黄梅方言和西片的孝南方言的用例:
黄梅:渠两个他俩还冒没来。︱哪两个要去?︱渠喜欢嗒这两个,不欢喜尔你妯娌两个。
姆妈妈妈跟尔两个一阵一起去。︱渠就是嫌弃我跟二哥两个︱老师对不住尔跟渠。
孝南:他两个他俩还冒来呀?︱你不喜欢哪两个?︱
我相信乜那两个,不相信你弟兄两个。
哥跟你两个一路一起去。︱你莫怪他跟大哥两个。︱你把我跟他两个当苕傻瓜?
二、“NP+(+NP)+两个”的歧义与“两个”的虚化
第一节所举的例(1)到例(7)共7个用例,涵盖了“名词、代词、名词短语、代词+名词”与“两个”构成的7种复指短语和偏正短语。这些短语及其构成的句子都不存在歧义。但是,例(8)、(9)却有歧义。例如两例的第一个句子就存在括号中的歧义:
(10)我只要二哥跟他两个(“二哥跟他两个”可以是两个人或三个人)
我跟你两个去看下[xa⊇]子(我和你们两个共三个人去看一下︱我和你共两个人去看一下︱我跟随你们两个人共三个人去看一下︱我跟随你共两个人去看一下)
前一例有两义,后一例有4义。显然,前述3大类9个次类中,只有“名词/名词短语+跟+人称代词+两个︱人称代词+(跟+)人称代词+两个”两种格式可能有歧义。相应地,如果没有上下文,元代文献里的两个例子也可能有歧义。如前举最后1例中“我……与你两个说”,也可能是两个或3个人。以下先分三小节讨论造成歧义的三个条件,然后在第四小节讨论与之相关的“两个”的虚化问题。
(一)导致歧义的原因之一 “两个”前出现单数形式的人称代词。上述存在歧义的句子,其共同点是“两个”前出现了单数形式的人称代词。这类代词在“两个”前既可以指称单数,也可以指称双数,与前面单数的NP相加,“NP+跟+我/你/ 他+两个”就存在是指称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的歧义,即“两个”可以复指整个“NP+(跟+)我/你/他”,也可以仅仅复指单数形式的人称代词“我/ 你/他”:
(11)我跟你两个说(你=你/你们)。︱二哥跟他两个说(他=他/他们)。
如果“两个”前出现的不是单数人称代词,那么因为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是用作指示、作定语,整个结构只能表示两个,不存在歧义;而名词或名词短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则或表示单数(只能与前面的成分构成联合短语被“两个”复指)、或表示复数(只能被“两个”复指),也不存在歧义。例(1)-(7)就是这样。这就是说,只要结构中的“两个”前不出现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就可以避免上述歧义:
(12)我跟你两个说→我跟小万两个说(共两个人)︱我跟你们两个说(共三个人)
(二)导致歧义的原因之二 两个名词性成分中间的联系词为“跟”。同北京方言一样,团风方言的“跟”兼属连词、介词。在两个名词性成分中间,既可以表示联合关系,充当连词;也可以用于介引其后的名词性成分做状语,充当介词。这就使得例(10)的第二例可能有两个意义,连同“我/ 你/他+两个”构成的歧义,一个句子就可能有四个意义了,又如:
(13)二毛跟我两个去。(二毛跟随我共两人去;二毛跟随我们两个共三人去。二毛和我两个都共两人去;二毛和我们两个都共三人去。)
如果两个名词性成分中间的联系词不兼类,那么就减少或者消除了歧义:
(14)老王和你两个说。(只有两义:“老王和你两个”是三个人或两个人)
(15)老王随倒随着你两个说。(只有一义:“老王和你两个”是三个人)
例(14)的“和”为联合连词,虽然借自普通话,显得较正式,但在团风方言中不兼介词,也就没有理解为介词的歧义;但是,“你”可以指单数或双数,因此其歧义没有完全消除。例(15)中的“随倒”是虚化尚不彻底的介词,没有兼属连词的歧义;且因为介词宾语“你两个”是复指短语,只能表达“两个”的意思,因而整个句子没有歧义。
(三)导致歧义的原因之三 句中没有否定词、副词、能愿动词等修饰成分。这实际上是由上述(二)派生出来的条件,上述有歧义的句子莫不如此。又如:
(16)姆妈妈妈跟他两个说。(“姆妈跟他两个”是两人或三人;“跟”是连词或介词)
如果句中出现否定词、副词、能愿动词等修饰成分,那么这类词的语义指向都是前面的名词性成分,且只能出现在两个位置:其一,这类词出现老师下跟我两个说笑话(没有歧义:老师都跟我们两个说笑话)
例(17)、(18)仍有歧义,是因为“他”的所指仍然可以是一个(“他两个”指一个人的现象比较特殊。详下)或两个,其歧义限于(一)中的范围。例(19)的范围副词“下”都指向前面的普通名词,意味着“老师”不止一个,其后的“两个”即使在意念上也绝不包含“老师”,其“我两个”只能表示“我们两个”,句子也就没有了歧义(详下)。
其二,这类词出现在动词前面,也可以减少句子的歧义:
(20)你跟他两个莫说。︱伯伯跟他两个能够说。︱老师跟他两个下说笑话。例中“莫、能够、下”的语义指向为前面所有的指人NP,“跟”只能是连接这些名词性成分的连词,因此其歧义限于(一)中的范围:“NP跟他两个”可以是两个或三个人。
以上三点,反映出导致“NP+跟+我/你/他+两个”歧义的原因只有两个,即“跟”存在的兼类和单数形式的人称代词指称对象的多少。黄孝方言其他点同样存在此类歧义,从略。
(四)“两个”的虚化及其重新分析 上文说过,“我跟他两个说”的“跟”如果是介词,那么这个句子就有涉及两个人或三个人的歧义。涉及三个人的意义很好理解,“跟”前的词指称一个人,“跟”后的词语指称两个人,共三个人。但这个句子如果只涉及两个人就不好理解:施事“我”是一个人,“跟”介引的“他两个”怎么也是指一个人?(如例(10)、(11)、(13)、(14)、(16)-(22))事实上,这类句子在整个黄孝方言以及毗邻的河南省的中原官话中都广泛存在,无论介词“跟”前后成分相隔多远,“两个”都像是表示“跟”前后所涉人数的总和。而且,句中使用“两个”却显得方言味儿更地道。这大概是因为“跟”兼属连词的缘故:在用作介词的时候,仍然残存着连词的某些特征,使得句子的主语和介词宾语仿佛可以被连接为“两个”。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难以进行精确的句法分析从在“跟”的前面,导致“跟”只能是介词,因为连词前是不出现这类成分的。这就消除了“跟”的兼类导致的歧义(另详下):
(17)你莫跟他两个说(歧义:你别跟他说︱你别跟他们两人说)
(18)伯伯能够跟他两个说(歧义:伯伯能够跟他说︱伯伯能够跟他们两个说)
(19)而赋予“两个”以地位:说“两个”是修饰谓语动词吧,不像;这个弱化了的成分在语音上属前,“代词+两个”必须连读。说是双数标记吧,“两个”前的直接成分又只能是表示单数。而且,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上述感觉不确——句中的“两个”都可以删除而不改变基本意义:
(21)我不跟你两个说(=我不跟你说)。
(22)姆妈多时就早就冒没有打算跟你两个说(=姆妈多时就冒打算跟你说)。
这就是说,从表达的角度看,“两个”在句中是冗余成分。这就导致了“两个”的重新分析。考虑到其上述特征,我们应该将这个“两个”分析为助词,即分析为多少带有一点“交互”意义的助词。
北京话的“俩”与中原官话中的“两倌”[6]一样,都是由数量短语进而虚化为双数标记,这似乎反映出北方官话的某些共性。而“两个”在黄孝方言中却虚化为助词,与其在北方官话中合音为“俩”,走的显然不是同一个路子。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南方的汉语方言,没有关于成熟的双数标记的报道,而双数标记在北方的官话方言中却大量存在,这是否与相邻的阿尔泰语系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影响有关?[4,7]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三、讨论
(一)文献中“俩”演变的路径 上文所述团风方言的歧义现象,除了“跟”兼属介词、连词造成的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两个”对前面词语复指的范围:是复指联合短语,还是复指人称代词?从第一节不难看出,元代“两个”的复指范围可以是联合短语,也可以仅是人称代词,与团风方言相同。这种现象在“俩”出现之初仍然存在:“俩”在清后期的《八仙得道》中仍存在这样的用法:
(23)如今见你俩说得可怜,少不得把我的实情告诉你们吧!
(24)白牛号泣应令……跟在李玄后面,和飞飞、颠颠俩一同来至紫霞洞。
可见这个“俩”和用在名词性成分前(俩老头儿)、独立做句子成分(买了俩)的“俩”一样,只是一个合音的数量词,可以复指前面的代词和联合短语。发展到现代,“俩”对前面复指的对象不能是联合短语了。根据张道俊(2006)文章中的数据推算,在120余万字的《王朔文集》中,“俩”字用于名词性成分后的为243例,其中用于人称代词后的195例,占80%以上,具体情形是;
我们俩(36例),你们俩(53例),他们俩(35例),她们俩(5例),咱们俩(13例),谁们俩(1例),我俩(5例),你俩(3例),他俩(12例),她俩(1例),咱俩(31例)
其余48例用在“父子、妯娌、娘儿”等集合名词和指代词后,没有复指联合短语的。这说明北京话的“俩”确如刘丹青(2009)所言,发展成了人称代词的双数标记——念轻声,一般附着在人称代词后,意义虚化而不附着在联合短语后复指,即不再是一个合音形式的数量词。但“俩”也较多用在表示相互关系的名词后表示双数,因此“俩”不仅仅是人称代词而且也应该是部分名词的双数标记。
更进一步,《官场现形记》中的“俩”不能出现在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后,没有“我们俩”的说法:
(25)当下便有一个老禁卒说:“我带你去。我先替你通报,你俩好说话。”
(26)起先他兄弟俩斗嘴的时候,一众家人都在外间,静悄悄的不敢则声。
这就说,不同的历史文献可能反映出“两个”这样的语法化路径:
“两个”后置复指名词性词语(元代文献)→后置的“两个”合音为“俩”复指名词性词语(见《八仙得道》)→“俩”用在集合名词和单、复数的三身代词后(见《王朔文集》《儿女英雄传》)→“俩”只能用在集合名词和单数三身代词后(见《官场现形记》)
其中《官场现形记》中的用法,显然比《王朔文集》、《儿女英雄传》中用法语法化程度高。这个演变路径中,“两个、俩”所附成分的生命度越来越高,符合Corbett关于数与生命度关系的分析。[8]至于不同用法出现时间的先后有些矛盾(《八仙得道》成书时间较《儿女英雄传》早),可能与不同作者所操方言中“俩”的发展速度不一有关,将另文讨论。
(二)历史演变的共时表现 汉语方言中的“俩”。据我们的初步调查,“俩”的复指对象在各方言中不一。如“我跟他俩、小王跟我俩”,在辽宁沈阳、丹东可以表示两个或三个人,也就是既可以复指前面的联合短语,也可以只复指人称代词;这意味着其“俩”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数标记,跟《八仙得道》的用法类似。在北京、河南浚县、山西大同,一般表示三个人,即“俩”只能附着在人称代词而不是联合短语后。其作为双数标记,与王朔的用法一样,语法化的程度较高。在山西平陆的中原官话中,双数的表达“只能在单数形式‘我’、‘你’、‘他’后加‘俩’构成‘我俩’、‘你俩’、‘他俩’而没有其他的形式表示。”[9]“俩”的语法化程度显然比北京方言还要高一些。其双数形式“我/你/他+俩”与复数形式“我们/你们/他们、我都/你都/他都”分工明确,没有“我们俩、他都俩”之类说法。平陆方言的“俩”显然是更为纯粹的双数标记,是普通话中没有的、发展得更快一些的双数标记。“俩”在不同地域方言中的特征,正是其历时演变的共时投影。
(三)上文所述“两个、俩”在不同文献和不同方言中的用法分别对应,正是其语法化在共时、历时两个平面的反映。我们将另文讨论。而黄孝方言中置于名词性词语后的“两个”,显然处在这个语法化链条的前端,其活化石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注释:
①主要发音合作人为陈金仙、王卫东(团风)、董秀芳、荆亚玲、辛永芬、王冬梅等老师先后分别提供了北京、大同、沈阳、丹东、浚县等地的方言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J].语文研究,1994,(4).
[3]张道俊.“俩”与“两个”的句法功能差异及其原因[J].孝感学院学报,2006,(2).
[4]王彦琳.“俩”的多角度分析[D].北京语言大学,2007.
[5]刘丹青.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J].方言,2009,(2).
[6]汪化云,李倩.固始方言的“两倌”[J].中国语文,2015,(1).
[7]王天佐.试说汉语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的关系[J].民族语文,1986,(4).
[8]Corbett,Greville G.《Number》影印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贺强.平陆方言的人称代词[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3).
责任编辑 张吉兵
H172
A
1003-8078(2016)02-0066-05
2015-10-28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2.18
汪化云(1953-),男,湖北黄冈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BYY027;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A740084;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FYZ002。